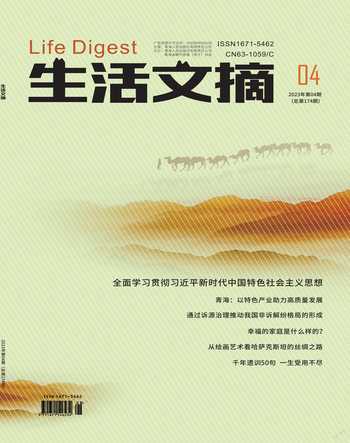黄河西岸的小村庄
在我童年十三四岁的时候,跟父辈第一次去了我向往的黄河岸边“夏阳”,以前人们把合阳县东王乡称作夏阳,现在已经更名为洽川镇。洽川镇有个小村子叫南菜园,这个村和我们家族竟然有不解之缘。
那一年,我刚刚学会了骑自行车,只能从“永久牌”二八大杠的三角处套着晃晃悠悠地骑行,我便兴高采烈地给我大(方言,父亲的意思)说我会骑自行车了,就哭闹着要去我心里向往的水乡,这个位于黄河西岸的南菜园村。我们家乡和家庄乡西城村到洽川南菜园村足有四十余里,要翻二条大沟,去一次真的不易。由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每年父亲只能安排我们和大伯家的少数人去老姑家拜年。终于机会来了,父亲带领我和大伯家大哥和二哥,还有五伯,我们六个人骑三辆自行车,天不亮就开始向洽川出发,途经金水沟,沿“文革”煤矿,现在叫合阳第一煤矿,走着坑洼不平的路,小心翼翼地下坡,一路上大家相互关照,十分小心谨慎骑行,在坡下沟底很远就能看见煤矿竖井架上灯光很亮很亮,我们瞬间来了精神,父亲赶忙整理好行李,又带领大家开始爬坡。我坐在车子的梁上,父亲推着后边自家的堂哥,大约又走了四里的坡路,用了快一个多小时,就上了塬,到了沟东的平政乡百里村。
此时,天才蒙蒙地亮,听到鸡鸣狗叫此起彼伏,村庄巷道里才有不多的人在走动。庄户人家大门贴的春联非常醒目,什么“爆竹声声除旧岁,锣鼓咚咚迎新年”“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过年储粮十余担,压岁有款上千元”,村大队部的春联是“佳节庆新春,总结劳动经验,和风吹绿野,迎接生产高潮”,有个家户门上还贴着黄对联,说明这户人家有人去世还没出服哩。穿过了平政乡,开始步入平坦的柏油路面,还有一段下坡路,车子就像飞一般。
这时,一轮红日从东方的地平线上升起,红彤彤的,有点耀眼,金光四射,田间的麦苗像似乎洒了金子,村庄和大树被阳光普照得光芒万丈,路上的行人瞬间多了起来,东来的西往的,都是年节走亲戚的。那个年代,合阳人家家拜年,都是蒸几个内心是用调和料面稍黑一点的面,外边包上一层特白的面,人们叫喜馄饨馍,也叫调和馍,这就是拜年的必备之品。拿这些礼馍主要是年节去看望长辈老人,同时,利用拜年互相走动,交流一下一年来的生产、生活情况。路途比较远的亲戚一年只去一次,因此我们去黄河岸边老姑家拜年的机会是多么难得。
很快,我们到了新池乡的沟北村,翻过一条小沟从金家庄的一条小路继续前行。在赶路途中,父亲给我们讲起了我们为啥要去洽川南菜园的缘故。我们村在和家庄长洼村东,一个自然村叫西城,属于当于人说的十二个城,还有一个半阁城不算数,实际都是一个村子,杨家城、肖家城、良石城,西城、长洼城等,叫的城是为了防土匪,让人一听那是个城,就不去了。在解放战争时期,我们村南的岭上实为秦长城遗址,驻扎着国民党的部队,西城、长洼一线是过渡区,彭德怀的西北野战军、王震共产党的部队在澄城皇甫庄一带,当时拉锯战时,我爷爷是北山游击队的联络员,挑个卖油糕的小担,一头炉子锅,一头面糖油,走街串巷,为游击队提供情报和联络,护送部队人员。在国共交恶内战时期,家里人走散了,都失去了联系,组织安排奶奶和大部分家人到了王家洼的伏蒙村,我父亲在这里认了一个姐姐,对父亲和家人特别的好,九岁的父亲与这个姐姐一起生活了三年之久,感情很深,这是我的一个姑。另一部分人我外祖父和外祖母,为了避战到王村的南菜五家营。父亲的亲姑因战乱走散不知了去向,四伯、五伯还在部队,全家人彻底分散,各奔東西。一九四八年合阳解放,全家人逐步回迁,终于在一九四九年底得以团聚,但父亲的亲姑,我们叫老姑却没有一点音信。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我们村有人去今天的洽川“夏阳渡”渡口坐船去山西,在渡河途中,船哨工问起:“你哪里人”,我村人说:“我是和家庄渠西城的。”船工说:“我们南菜园有一个你们村的人。”我们村这个人后来把这个消息捎回到了家,这才找到了父亲失散多年的姑姑,此时已过去了十五个年头了。后来方知,我老姑已嫁给了当地一张姓人家,并生了子女。老姑的掌柜他们几代人都以卖踅面为生,在当地很有名气。后来由于政策的原因,在合作社时代,不再从事卖踅面的营生。父亲说我老姑的儿子名叫张栓锁,我叫张伯,我张伯娶妻种氏名叫淑贤,是有名的种菜务农能手,记忆中每年张伯常常套着牲口装上一车大白菜、菠菜、红白萝卜给我们把菜送到塬上,每年有了我张伯送的菜,我们就能过一个好的年,塬上人由于缺水,无法种菜,这让其他村里的人十分羡慕。
听到父亲讲述这些,我更向往黄河西岸我的老姑家,不由得心情越来越激动和迫切。我们大约用了四个多小时,终于站在塬头上,看到犹如银蛇的黄河了,东西摇摆,河心的心字形沙洲有无尽的芦苇摇曳,散落在大河以西有八九个自然村,袅袅炊烟飘直游荡,笼罩在村子上空;洽川这个地方人多地少,因此村子住得紧凑,把有限的土地腾出来多以种菜为主,那时的洽川人和我们塬上人都没有吃鱼的习惯。到了七八十年代,东雷抽黄工程竣工后,省水产研究所在这里引进了罗非鱼等品种获得成功,在洽川建立了万亩水产养殖基地,我们合阳人才开始有福气能吃上人间的美味,各种各样的水产品鱼了。现在的洽川水产养殖品种繁多,黑乌鲤、娃娃鱼、大小龙虾都很有名,黑鸟鲤、莲菜已是国家的地理标志产品,年产量五万吨左右,是全国水产养殖重点基地之一。现在的洽川,鱼塘和莲菜种植南北的滩涂望不到边际,十分壮观,有不是江南胜似江南之感,景色宜人,晴好天气时可以清楚地看到延绵的中条山和雄伟的华山主峰。
再又说到黄河西岸的南菜园我老姑家,她家住在洽川西山下的一条小巷里,我们和父亲一行来到了老姑家门前时,张伯和娃们都在门口早早地等着我们,张伯家房子是倒背厦子,院子很宽敞,门前的场地却不是很大,在崖边上长了一棵枝繁叶茂的老槐树,前边不远处的大田里能看到绿油油的菠菜和各种菜蔬。能看到南菜园自喷井冒着蒸气,井边白雾蒙蒙,水是常温的,对我们从旱塬来的这些人来说,真觉得不可思议和非常新鲜。原来,洽川这地方水资源十分丰富,每个村都有好几眼这样的自喷井,水还不用电,不用柴油机,却能常年这样“哗哗”地流淌,最后汇入湿地和黄河。后来我有幸在杨凌上了陕西省省水利学校,学了水利才知道他们这里是合耀单元380裂线水在合阳洽川是出露点,那时上游取水少,洽川这一块出露流出时压力才这么大,井喷高达到二三十米,堪称奇观。
我们在张伯家吃饭时,听张伯讲他们村的菠菜在东王最有名,可能也是地热水的原因。他们洽川还有个世界性的水文化奇景,在黄河滩涂中犹如七星北斗布局,镶嵌着七眼神秘的“瀵泉”。洽川人把最大的一个瀵泉叫马瀵,在明清时,官府还有专人骑马护渠的“水官”,马瀵的水浇朝邑大部分良田,还造福了大荔的许多百姓。在张伯家儿子的带领下,我第一次还看到了洽川的王村瀵,这个瀵有十来亩大,实际上这也是380的泉水,能看见泉眼涌动翻滚,引水渠把水引到了南边的稻田地里,那时洽川人也开始种植水稻了,而且品质也非常好,这也解开了我在张伯家能吃到米饭的缘由。从南菜园向东走了大约一公里处,我第一次看到了母亲河黄河,黄河水流很急很大,向南流向了大荔方向。黄河堤坝高有两三米,有了这个黄河大坝,才保护着洽川这块万人的生命安全和大片良田不受水患。
黄河西岸的洽川南菜园村,随着生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开放、全面“五位一体”政策落实、脱贫攻坚的推进,今天的这个小村庄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加之东雷抽黄、二黄相继建成,洽川已成为国家风景名胜区4A级景区,342国道、沿黄公路已建成运营,洽川的各村已逐步融入陕西的大旅游当中,产业结构得到了新的调整,适逢乡村振兴的惠民政策,特别南菜园村也与时俱进,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加大各类特色蔬菜园区建设,打造一村一品品牌,百姓生活日益改善,小小的南菜园村已成为黄河西岸的一颗明珠。
作者简介:
马刚,原合阳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