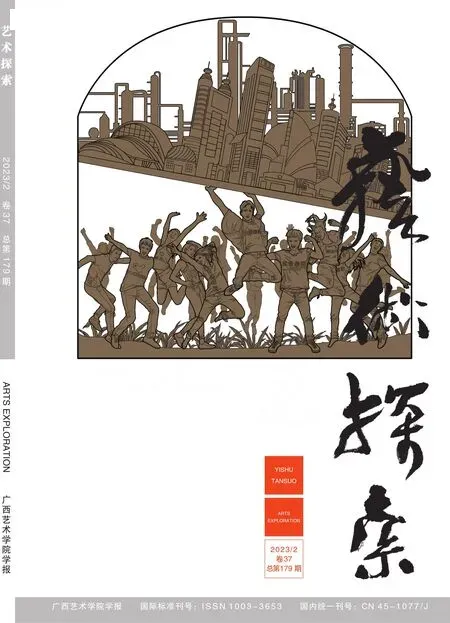思想、制度与皇家艺术机构:元明书法教育的三个向度
彭再生
(四川大学 艺术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5)
在传统中国社会,书法教育显然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它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当时普遍的思想、哲学观念与上层统治者制定的政策、制度,这些因素牢牢地掌握着书法的命脉,影响着书法的内涵、审美原则、发展倾向与发展规模。
长久以来,儒学是最具力量的思想因素。从周朝贵族教育的“六艺”之学到唐代的“书判取士”,再到宋徽宗在翰林院开设“书学”一科,书法之学与儒家的教育、制度紧密相依。儒学对于书法而言,并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学问,而是维系其生存的基础。古代社会在思想以及“王朝循环”的连贯性上已经表明,儒学是某种贯穿其中的精神道统与意识形态,它深深植根于整个汉民族的精神内核与知识系统。正是因为这种统摄性,文人士大夫普遍雅好的书法深受儒家精神的影响,儒学在一开始就以自己强大的力量塑造了关于书法的种种价值观念与审美趣味,并赋予书法最深厚的文化来源。“夫书者六艺之一,儒者所当事也”[1]197,士人们的心灵也在书法实践中获得充分的愉悦和满足。在他们看来,不仅书法是通往政治目标的桥梁,而且精通书法的儒者也被认为是具有最高品味的文化精英。
宋代是儒学与士人地位达到巅峰的时代,而紧随其后的元朝却使这种状况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作为马背上的骁勇征服者,元朝统治者如何对待汉民族的精神、文化传统决定着书法的命运。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凭借武力夺取了政权,他所采取的政策又是什么?这段由元至明的历史,不仅向我们展现了文化、艺术本身强大的生命力,也展现了儒学、统治者意志与书法教育之间的相互关系。
一、儒学与科举的存废
(一)儒学
13世纪上半叶,在蒙古人的铁蹄之下,偏安一隅的南宋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整个汉民族尤其是士人群体面临极为深重的灾难和危机。这种危机不仅来自亡国之痛,更来自知识与信仰无以为继的恐慌。在这种情形下,作为社会结构支撑与知识道统的儒学的命运成为汉族士人普遍关注的中心。而与之相应的另一面则是,元朝统治者需要采取有力的手段来确立其政权的合法性地位并巩固统治。显然,慎重地对待儒家及汉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是关乎其统治的关键性因素。其一,尽管蒙古族统治者都是信奉武力的骁勇善战之士,但他们也很清楚“天下可从马上得,却不可自马上治”的道理。文治是他们不得不考虑的策略。其二,儒家思想传统根深蒂固,掌握和利用这一文化命脉方能俘获天下之心而维持统治的稳定。其三,从深厚的思想文化到完备的制度体系,旧王朝的文化与制度对于他们而言是富有吸引力的因素。因此,他们能够听取当时一些儒士的建议,试图有效地吸纳和运用儒家文化来治理这个新兴的王朝。①早在元太祖时期,成吉思汗就听从耶律楚材等儒士大夫的建议,吸纳汉族文化。其子窝阔台即位后同样延续了这样的方式。《元史·列传第三十三》载:太宗窝阔台时期,“楚材又请遣人入城,求孔子后,得五十一代孙元措,奏袭封衍圣公,付以林庙地。命收太常礼乐生,及召名儒梁陟、王万庆、赵著等,使直释九经,进讲东宫。又率大臣子孙,执经解义,俾知圣人之道。置编修所于燕京、经籍所于平阳,由是文治兴焉。”这些争取儒士和设置经籍所的办法为儒学在元朝的延续奠定了基础。
至元八年(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参照旧王朝的方式建国号为“大元”。“大元”即出自列为儒学群经之首的《易经》:“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这表明元朝统治者对儒家文化及国家治理制度的某种遵从,其释放出的信号也多少安抚了承受国破之痛的汉族士人之心。“(忽必烈)思大有为于天下,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2]57通过广泛任用刘秉忠、姚枢、许衡等汉族有为之士,制定国家政策,实践儒学复兴②至元四年(1267年),元世祖将太宗时在山西平阳设立的经籍所徙置京师,积极加强传统儒家经典的整理、传播。,忽必烈进一步强化了吸纳汉文化的治国方略。
至元十三年(1276年),蒙古大臣不忽木联合坚童、太答、秃鲁等向忽必烈上疏,提出兴办儒学和学校的主张:
为今之计,如欲人材众多,通习汉法,必如古昔遍立学校然后可。若曰未暇,宜且于大都弘阐国学。择蒙古人年十五以下、十岁以上质美者百人,百官子弟与凡民俊秀者百人,俾廪给各有定制。选德业充备足为师表者,充司业、博士、助教而教育之。使其教必本于人伦,明乎物理,为之讲解经传,授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其下复立数科,如小学、律、书、算之类。每科设置教授,各令以本业训导。小学科则令读诵经书,教以应对进退事长之节;律科则专令通晓吏事;书科则专令晓习字画;算科则专令熟闲算数。或一艺通然后改授,或一日之间更次为之。[2]3165-3166
所谓“国学”,即儒家经典之学;而“使其教必本于人伦,明乎物理,为之讲解经传,授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的教育目标也完全是儒家传统理念。因此,这份奏章可以看作一份提倡儒教兴国的纲领性文件。其中,对学生、师资、教学内容等都作了详细的陈述和建议。关于教学分科,其参照的是传统国子学的主体内容,并将书法教育列入儒学的教育体系之中。
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侍御史程钜夫向世祖面呈“兴建国学”的方案,并受世祖委派下江南寻访旧朝遗逸,共得儒士二十余人。其中,后来在元朝历史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的宋朝皇室后裔赵孟頫即为此次征选人才的首选。这一事件在元初的儒士中产生了重大反响,为汉族士人实现进入仕途的传统目标点燃了希望。③元初儒臣郝经曾言:“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陵川集》卷三十七,吉林出版集团,2005年)在这些侍奉元朝的儒士看来,保护传统儒教之道的运行才是汉民族延续的根本,也就是说,只要儒学延续,儒家礼制、宗庙得到尊崇,儒士得到任用,就可以将汉民族的命脉传承下去。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元朝设立国子学,规定“凡读书必先《孝经》《小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次及《诗》《书》《礼记》《周礼》《春秋》《易》”[2]2029,并设立江南各路儒学提举司。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令江南诸路学及各县学内,设立小学,选老成之士教之。或自愿招师,或自受家学于父兄者,亦从其便。其他先儒过化之地,名贤经行之所,与好事之家出钱粟赡学者,并立为书院”[2]2031。至此,元朝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完整的学校教育体系。④正如元儒黄溍所言:“自京师至于偏州下邑,海隅徼塞,四方万里之外,莫不有学”(《金华黄先生文集》卷十,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儒学教育进入兴盛时期。中央官学包括国子学、蒙古国子学等,地方官学有路、府和州县学。书院制度则是官学教育的有益补充,它大大提高了普通民众接受教育的机会,也使得儒学更加深入地进入各个地域,并带来地方性儒学学术中心的兴起。
从书法教育的角度,无论是中央的国子学,还是地方官学以及各级书院,习字都是其基本的科目和内容。只是在正统的学校教育中,习字往往以规范、端正为取向,注重的是实用教育。“诸生所习字,合用唐颜尚书字样……习大字一纸,小字一纸,务要模仿精工,字画端谨,通晓前贤笔法,毋得率略及有浥污。”[3]101-102元代的书院也多以“楷敬”为准绳。故而,书法的艺术教育更多地需要从学校之外的大文化中去实施,如某些具有艺术修养的士人开办的更具开放性的私人书院或其他渠道。此外,虽然文献显示的官方教学内容主要是技法与楷则的习得,但或许并不能代表教育过程中的全部真实。因为,作为有着悠久传统的民族艺术,书法的艺术性因素往往会在技法获得之后就不自觉地闪现出来,成为人们追求的价值。
至大四年(1311年),酷爱儒家文化艺术的元仁宗即位,进一步推行儒术治国的政策。“命国子祭酒刘赓诣曲阜,以太牢祠孔子”[2]545,“以宋儒周敦颐、程颢、颢弟颐、张载、邵雍、司马光、朱熹、张栻、吕祖谦及故中书左丞许衡从祀孔子庙廷”[2]557。皇庆二年(1313年),元仁宗诏行科举:“朕所愿者,安百姓以图至治,然匪用儒士,何以致此。设科取士,庶几得真儒之用,而治道可兴也。”[2]558由此,在元初统治者那里多有动议的科举得以正式实施。科举的恢复对儒学地位的强化起到了进一步的促进作用。在科举考试中,理学确立了官方正统之学的最高权威。“致海内之士,非程、朱之书不读”[4]169,“非程朱学,不试于有司”[4]140,程朱理学著作成了官定教科书与科举考试的依据。在元代统治者的推动下,程朱理学最终完成与科举仕进之间的制度化链接,成为一种政治权力话语。[5]251这也为明代儒学的走向埋下了伏笔。
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称帝,结束了元朝不足百年的统治,是为明朝。出身乡野的朱元璋为了巩固通过武装斗争建立起来的王朝,在文化上采取了远比元朝更为高压的政策。其中,至为重要的方面就是进一步强化了儒学的工具性,不仅以程朱理学为至高无上的正统,更是利用其“存天理,灭人欲”等条纲作为驯服精英群体的武器,并结合科举等严格的制度化措施来钳制社会的思想。这种情形直到明代中后期心学崛起才渐被打破。
(二)科举的存废
元朝前期,科举废止。元世祖时期,虽有几次欲实行科举,但最后都由于种种阻力未能实现。这对元代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仕进资源几乎为蒙古人所垄断,而汉族群体则处于政治的边缘地位。虽然统治者也征选优秀的汉族精英担任政府官员,但数量极其有限,汉族官员担任的职务也多远离权力的中心地带。“贡举法废,士无入仕之阶,或习刀笔以为吏胥,或执仆役以事官僚,或作技巧贩鬻以为工匠商贾”[2]2017,被断绝了仕进之途的汉人只得调整自身出路,转而从事其他各种各样的行业,而这些行业在传统的士人社会大都被认为是低贱的。这就造成了文化精英群体的下移。
有一部分人投身于文学、艺术,或将文学、艺术作为日常排忧解闷的途径,这就为优质文化的传播与普及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并使元代社会呈现蓬勃的文化活力。元曲、书画等艺术的发展就有赖于这样的社会环境与文化场域。书法教育的情形也有着类似的效果。其一,在此前主要是作为精英艺术的书法得以延展至更广泛的阶层,带动了社会群体的参与。其二,书法的抒情功能得到强化,在正统审美观念之外,迸发出更为多元的取向。其三,职业书画家迫于生存而不得不参与的市场交易行为,使得他们需要根据市场的反应作出审美或风格上的调整,刺激了书法及书法教育在观念上的开放。
到了元朝的第四位统治者元仁宗时期,科举终于得以恢复。1313年,仁宗下诏重开科举,并钦定科场程序,确定了此后科举作为人才选拔制度的官方形式。“举人宜以德行为首,试艺则以经术为先,词章次之。浮华过实,朕所不取。”[2]2018注重实用,主张“经术为先”的指导政策规定了考试的基本取向。考试内容为《大学》《论语》《中庸》《孟子》等儒学经典,但特别指定 “并用朱氏章句集注”作答[2]2019。如此一来,朱熹的《四书集注》就成了科考的标准答案而被推向神圣的地位。由此可见,与宋徽宗朝时注重词赋文采,甚至将绘画纳入科举不同,元代科考偏于义理知识,将思想知识化,实用理性远远超越了审美、文学精神。这就从选拔制度上限制了思想的自由活动空间,也削弱了关注艺术与表现的因素。这种倾向无疑会导致多方面的后果,于书法教育亦不例外。
科举的施行为汉族儒生开启了一条重拾入仕理想的道路,让他们趋之若鹜。但事实上,元代科举实施的力度非常有限,通过科举考试入选的官员也很少。自1315年始,科举每三年举行一次,整个元朝总共只有1139名进士,而且按照规定,其中一半为蒙古人与色目人。[6]640这和宋朝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因此,儒生们的处境并没有因为科举的重启而出现太大的改变,他们中的大多数仍然延续着此前的出路。另一个方面,科举的实行让更多非汉族人士参与到汉文化的学习之中,经过四书五经的熏陶,加深了对汉民族文学、艺术的理解,其中一些人的艺术实践也为书法、绘画增添了新鲜的活力。
到了明代,元代关于科举的一些主导思想、考试科目在很大程度上都得到了继承。如前所述,明太祖时期,不仅标榜程朱理学作为绝对正宗,亦明确规定了考试内容和文章作答方式。
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诏天下立学,制定禁约十二条,并传谕立石于学宫,以令天下悉从:“国家明经取士,说经者以宋儒传注为宗,行文者以典实纯正为尚。今后务将颁降《四书五经性理大全》《资治通鉴纲目》《大学衍义》《历代名臣奏议》《文章正宗》及历代诰律典制等书,课令生员诵习讲解,俾其通晓古今,适于世用。其有剽窃异端邪说,炫奇立异者,文虽工弗录。”[7]1247于此,其控制言论、钳制思想的目的可见一斑。而“体用排偶,谓之八股”[8]1693的文体要求则进一步束缚了应试者的思想与表达方式。大多数儒生不得不皓首穷年、终其一生,埋头于官方规定的书目之中,不敢有半点逾越。
明代科举考试中与书法教育紧密相关的是,书法被明确作为选举与考试的内容列入其中。《明史·选举》称:“所习自《四子》本经外,兼及刘向《说苑》及律令、书、数、《御制大诰》……每日习书二百余字,以二王、智永、欧、虞、颜、柳诸帖为法。”[8]1677又:“初设科举时,初场,试经义二道,《四书》义一道;二场,论一道;三场,策一道。中式后十日,复以骑、射、书、算、律五事试之。”[8]1694科举入官的人员中,有些就是直接凭借书法优长入选的。因此,明代接续了唐代以来以书法取士的传统,只不过由于严格的规定与限制,人们的艺术思维受到束缚,书法教育的成果也就大打折扣甚至适得其反。
二、元文宗朝的奎章阁
元朝虽然重视儒学,但这种重视的根底在于新王朝对于旧有文化体系的依存,他们的出发点和基本目标是维护政治统治的需要,因此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复兴儒学超越性的价值,汉族士人也难以摆脱尴尬的处境。而且元初的几个统治者大都不识汉字,不通汉文,其本身对汉文化理解有限,对传统汉族艺术更难以切身体会,故作为儒道之末的文艺自然处于统治者无暇顾及的领域。此后,随着蒙古族皇子和贵族子弟从小对儒学包括汉族文艺的学习,这种情形才渐有改观。
1328年,对汉文化和传统艺术推崇备至的元文宗即位,带动了宫廷推重文艺之风的发展。文宗雅好书画,留心诗词,《历代画史汇传》称其“作字法晋人”[9]40。他即位后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在京师新立一个汉学和艺术的学术机构作为内廷的官署,即奎章阁。[10]16这大抵是元朝历史上最具象征性的彰显文艺的事件。
在朝廷行政体系中,奎章阁是一个集合了多种功能的特设机构,其职级(正二品)仅略低于中央最高文化机构翰林院和集贤院。[9]64就其宗旨而言,虽然表面上冠以“延问道德,以熙圣学”[11]815、“以祖宗明训、古昔治乱得失,日陈于前”[2]4178的政治功能,但客观上偏重于文艺。奎章阁下设三个主要机构:群玉内司(掌阁中图书宝玩,康里巎巎为第一任监司)、艺文监(掌译事校雠等)、鉴书博士司(掌品定书画,1330年特任柯九思为鉴书博士),[12]70其中鉴书博士司得到皇帝的垂青最多。同时,在奎章阁的诸种功能中,还有教育一项。1329年3月,奎章阁设授经郎二员,“以勋旧、贵戚子孙及近侍年幼者肄业”[2]732。由于奎章阁浓厚的艺文氛围,这些贵族子弟们接受的文艺熏陶和训练也是得天独厚的。
奎章阁集中了其时一些重要的文臣学士和艺文之士,虞集、康里巎巎、柯九思等都为任职于斯的著名人物。来自江南的书画精英也时常出入其间。陶宗仪《南村辍耕录》称:“ (文宗)非有朝会、祠享、时巡之事,几无一日而不御于斯。”[13]70“文宗之御奎章日,学士虞集、博士柯九思常侍从,以讨论法书名画为事。”[13]84由于皇帝的临幸,奎章阁的书画品鉴及艺文活动非常热烈并席卷至整个宫廷。
在宫廷之外,以其皇家艺文机构的崇高地位,奎章阁推动了举国上下的文艺浪潮:文人艺士们奔走交流、相互陶染;鉴藏活动更加活跃;艺术家的地位也得到了空前提高。这必然带来艺术从事者的骤增与艺术教育的兴盛。此外,正如石守谦的研究所表明,此一时期的艺术赞助行为也异常活跃,皇族成为最大的艺术赞助者,蒙古人、色目人纷纷参与到艺术赞助之中。赞助的对象则包括柯九思、朱德润等士大夫及在野的文人艺术家。[14]137-142
由是观之,文宗朝的奎章阁在弘扬文艺方面作出了卓著贡献,它的成立和运行弥补了有元一代在传统文艺政策与皇家艺文机构设置上的先天不足,并极大地推动了元末汉文化与书画艺术的发展。奎章阁兴盛的那些年,倪瓒、杨维桢、方从义等正处于艺术的少壮时期,在宫廷及举国艺文风气的影响下,其艺术之精进是可以想见的。
三、中书舍人、台阁体与官方的书法控制
朱元璋虽然出身草莽,但对儒家文化包括传统艺术怀有本能的好感,亦知晓书法对于儒生的价值,以及利用艺文来进行文化统治能达到的广泛而深入的效果。从科举制度到宫廷机构设置,朱元璋采取了一系列比前代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政策来强化对书法的规范与限制。一方面,确立以书法取士的制度,在人才选拔上加强书法方面的内容。《明史·选举志》:“选人自进士、举人、贡生外,有官生、恩生、功生、监生、儒士,又有吏员、承差、知印、书算、篆书、译字、通事诸杂流。进士为一途,举贡等为一途,吏员等为一途,所谓三途并用也。”[8]1715明初实行的“三途并用”制度规定了书法可以作为入仕的正式渠道,“善书”者可通过这一渠道进入朝廷担任官职。另一方面,设置负责朝廷文书书写的专门机构——中书科,“以省中诸节目寄之舍人,故称科,而无堂官”[15]521。由此,原本承担朝廷机要政务的中书省改造为专司书写朝廷文牍的机构,而中书舍人便是书写任务的具体承担者。
洪武至永乐年间,中书舍人由十数人增至三四十人,再加上其他担任宫廷誊抄缮写工作的书吏,组成了一个特别的宫廷书吏群体。[16]207然而,由于是受皇帝的管制以及出于官方文书的书写需要,他们的书法无论是在取法还是风貌上都受到了极大的限制。明孙能传《剡溪漫笔·院体中书体》称:“国朝正德中,姜太仆立纲以楷书供奉西省,字体端正,但近于俗,一时殿阁诸君及诸司吏胥皆翕然宗之,迄今无改,谓之‘中书体’。乃其鄙拙亦日以盛矣。”[17]543这种由姜立纲形成的楷书书写模式称为“中书体”,也正反映了中书舍人在书法上拘谨媚俗的体势与“人云亦云”的面貌。一方面,他们需要迎合帝王的口味,并相互标榜以示听命于皇权;另一方面,繁重的书写任务与统一规范,更使其逐渐呈现出千人一面的程序化倾向。这种倾向的发展是在整个宫廷中形成一种被称为“台阁体”的书风。
永乐年间,这种保守、应制的台阁体书风达到顶峰。其中声名最大的代表人物就是为皇帝所极为推重的沈度、沈粲兄弟,而尤以沈度为尊。《皇明世说新语》载:“太宗征善书者,试而官之。最喜云间二沈学士,尤重度书,每称曰:我朝王羲之。”[18]373明太宗朱棣之所以对沈度如此青睐有加,恐怕在于沈度书法符合他的审美趣味以及通过书法来加强社会规范性力量的统治政策。顺应朝廷倾向及皇帝喜好,沈度书法以端楷为主,点画规整,形貌庄严,呈一丝不苟、正襟危坐之态。这种规整久而久之就变为了一种竭力的自我束缚,战战兢兢间不敢越雷池一步,而丧失了有血有肉的个体的情感融入。在帝王的推重下,二沈书法获得了其时高不可攀的地位,成为全国上下纷纷效仿、传抄的对象。马宗霍称:“逮乎永乐,朝士益不复以古为法,惟近师詹宋。二沈宸眷最隆,声施最盛,度楷粲草,兄弟争能。然递相模仿,习气亦最甚。靡靡之格,遂成馆阁专门。”[19]164沈度的书法样貌即如同机器复制一般风行于世。
然而,这种应制的僵化书风给书法教育带来了极大的伤害。它使得书家以及从小接受习字教育的儒生学子们钻进了一个看似漂亮的管道,并在这种近乎俗气的漂亮之中沉溺、流连,以至于忘却了自我与书法本身的价值。由是,他们的才华、个性乃至举国的书法教育也就成了统治者书法控制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