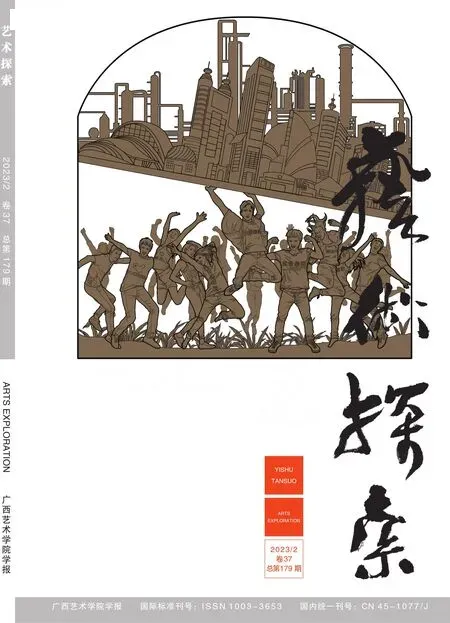澳大利亚原住民美学:与永恒梦世纪的神圣结合
理查德·L.安德森 文 刘先福 译 李修建 校
(1.堪萨斯城艺术学院,美国 堪萨斯城 64101;2,3.中国艺术研究院 艺术学研究所,北京 100102)
感觉使我们认识到,明显而直观的世界不易被忽视。但是,心灵如果有机会进行反思,那么它往往会宣告另一个更重要的领域——超越了感觉的世俗层面——的存在。大多数人是否都曾预见过这样的世界,在那里能感受到神的威严、爱的狂喜,或如数学家和哲学家所说:“凭借毕达哥拉斯式的力量,数字支配着万物流转”[1]13。对大多数西方人来说,这样的顿悟是例外且反常的,但对澳大利亚原住民来说①传统澳大利亚原住民的生活、文化和艺术受到殖民地经历的深刻影响。本文的后记将描述一些由此导致的改变。除了这一部分,本文剩下的内容将描述澳大利亚原住民曾经存在的生活方式和信仰。,超越当下经验的世界具有令人信服的真实性,且十分重要。精神信仰与原住民的生活息息相关,深入研究澳大利亚原住民美学可知,艺术与仪式一样,是人类接触这个模糊世界的主要手段。
澳大利亚原住民文化是少数几个能延续到20世纪的狩猎采集文化,原住民丰富的艺术品使我们对他们的目标更加感兴趣。此外,澳大利亚美学的精神特质也引发我们关注,迫使我们去探索原住民心中更遥远的角落,去寻找和审视人类灵魂与自然精神对话的声音。对澳大利亚原住民来说,这种声音是一种仪式艺术。
一、原住民艺术的文化语境
澳大利亚原住民的数量本就不多。在这个和美国大陆差不多大的岛屿,早期的欧洲开拓者只碰到大约30万人(比罗得岛目前人口数量的1/3还少),成为殖民地后,澳大利亚的人口数量又锐减了9成。现在,约500个传统部落中的大多数被分成许多半游牧(semi-nomadic)部落,每个部落的成员都不到100人。西阿纳姆地(West Arnhem Land)就是原住民人口稀少的例证,这个地区位于澳大利亚北部,目前居住人口不足1 000人,我们关于传统澳大利亚艺术和美学的大量资料都来源于此。
这些部落在澳大利亚大部分看似不适宜居住的沙漠和草原地区生活得相当好,这主要归功于一种简单又有独创性的技术。挖掘棒和研磨石让妇女能从土地中获取并准备食物,长矛、投矛器、回旋镖能帮助男人打猎。(不是所有群体都有回旋镖,那些拥有它的群体,在狩猎中使用得更多的是不能返回的类型,而能返回的类型主要用于娱乐活动。)剩余的实用物品并不多:原住民制作的用于打仗的盾牌和棍棒,绳索、树皮、木制容器,树皮和茅草搭建的房子。他们用来切割和加工木头的工具有石斧、锛子、楔子、凿子,生火的工具是火钻和火锯。
与物质文化的简单相比,原住民的精神生活相当复杂。比如,澳大利亚传统的亲属制度就一直让西方学者大伤脑筋。澳大利亚宗教对于局外人来说也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课题。其最基本的前提是,在过去某个不确定的时期,原住民称作“永恒梦世纪”(eternal dreamtime)的神话精灵在乡村游荡,它们的活动形成了当今景观的显著特征,比如水坑。在它们的旅行中,梦世纪的精灵带来了丰富的原始植物、动物,人类以及许多人类的风俗习惯,如仪式、歌曲和血统原则。人们认为永恒梦世纪的灵魂在人类时代会继续存在。通过讲述它们的旅行(即神话),重演它们的活动(即仪式),原住民相信世界原初的和谐与繁荣状态将会持续下去。举行各种各样的仪式是平等且多元的图腾群的责任,也就是说,这些图腾群与某种特定的可以追溯他们起源的动物有着共同的象征性,并与它们保持着一种亲近的关系。
二、原住民艺术
从传统来看,澳大利亚艺术丰富多彩。虽然原住民语言中没有与艺术相对等的词语,但是有些词指代特定的艺术媒介,如图像艺术、雕刻、歌唱、说书、仪式舞蹈。[2]306与其他半游牧族群一样,澳大利亚原住民擅长使用所有媒介中最便于携带的——人的身体。②大多数原住民艺术是神圣的,而且它的创造者坚决认为,它只能给参加过入会仪式的个体看。因此,大多数风格和媒介将不会在这里展示。有一些树皮画(bark painting)是可以给外人看的。尽管这些画没有展现原住民的全部技艺,但它们还是会让观众了解澳大利亚中北部一些常见的风格。他们有割痕纹身(scarification)。纹身的创作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在新的刀口上涂抹灰烬或泥土,另一种方法并不常见,是把蚂蚁放在刀口上以引起刺激。[3]由此产生的疤痕有多种用途。有些作为哀悼或者入会仪式的一部分;另一些则用于显示有疤痕者的社会地位(男性与女性相对,经过入会仪式的成年人与未成年的青年人相对);还有一些仅仅是让纹身的人看起来更有魅力。
许多原住民群体使用绘画来强化个人的外表。如东北阿纳姆地的做法是首先在身上涂抹油脂,然后用赭土画出复杂的图案。绘画图案“属于”个体自己。除了仪式价值,其中的图案是有经济价值的,可以用来交换或售卖。[4]61-62
服饰在澳大利亚原住民那里是罕见的或不存在的。有些原住民的下体围着流苏,但那是为了装饰,而不是遮挡身体。还有些人戴着项链、头环、臂环、腰带。一些地区,原住民在身体上作画,用血液做粘合剂把木棉花的绒毛粘到身上,形成有质感的纹样。头饰可能是身体上最为精美的附加物。如澳大利亚中部的阿伦塔人(Arunta)把头发拢在头顶,用小树枝别住周围的一束头发,形成一个高达2英尺的头盔状结构,有时还用些雕鹰的羽毛进一步装饰。[5]610-612
身体装饰并不是澳大利亚视觉艺术的唯一媒介。一些部落在来自粗树的大而平的树皮上绘制了画作,遍布大陆的数以万计的岩画也都被记录在案。在阿纳姆地,一些岩画描绘了日常生活或者是“神话事件的公共版本”,其创作是“‘为了孩子开心’或是‘为了娱乐’。也就是说,故事讲述虽是在一个轻松的氛围中进行,但服务于教育目的”[6]110。其他的艺术则作为巫术活动的一部分,服务于超自然功能,被认为出自魔术师般的弥弥(mimih)精灵之手,或者再次被认为是梦世纪真实存在的痕迹。[7]112岩石艺术的一种风格是“X射线绘画”,其以解剖学上精确的多色风格,不仅描绘了动物的轮廓,还描绘了它们的内脏器官。有些弥弥画作以单色描绘了人的线条,而人手的印模可看作是另一种形式的岩画。
许多原住民部落创作三维艺术作品,其中最重要的是仪式用品,叫作“储灵珈”(tjurungas)——它是由木头或石头制成的扁平的、椭圆形的或圆形的厚板,长度从2英寸到18英尺,通常绘有复杂的画面和雕刻的纹样。[2]367原住民也制作牛吼器(bullroarer),把椭圆形的木板用绳子捆上,在空中旋转,它们会发出一种可怕的吼叫声。如在东北阿纳姆地,雕刻师会制作祖先和动物的木制头像或者全身像。在其他地方,他们将大型图案刺入树里,用于入会仪式和作为墓碑。阿纳姆地的原住民用泥土、沙子和原木,在地面上制作巨大的高浮雕。玛格丽特·克鲁尼斯·罗斯(Margaret Clunies Ross)和希雅特(L. R. Hiatt)[7]目睹了五个此类沙雕的建造过程,它们的最终占地面积达到600平方米。有的部落制作篮子,以露兜树的纤维、红色长尾小鹦鹉的羽毛、白色绒毛、毛皮和人的头发作为装饰。
澳大利亚艺术存在地域和媒介的差异,但它在风格上总是优雅而简洁的。它的制作者使用了一种“主观视角”,表现的不是事物在人眼中短暂出现的样子,而是它们在大脑中永远存在的样子。艺术家也经常按照惯例来制作他们的作品,用一些典型特征来表现整个主题。库普卡(Kupka)用以下措辞来描述树皮画:
原住民画家通过拆开、重组和再创造自然的形式,达到某种抽象,就如许多“现代”(modern)画家那样,然而,抽象并不是他的目标。相反,画中的每一条线和每一个点都有一个真实的意义,能被已入会的人识别出来。事实上,外人无法理解这些作品,反而是它们的一种优点。[8]96
在原住民文化中,表演艺术至少和图画以及造型艺术同样重要。独唱和合唱对构成神圣和世俗生活来说都是必须的。歌曲通常伴随着各种鸣锣声、咯吱声和迪杰里杜(didjeridu),迪杰里杜是由一根挖空的桉树枝做成的单音管,演奏时会发出一种怪异而独特的声音。有些歌曲文本被组成最多达300首单曲的套曲,每一首都带有密集的象征意义。③Ronald Berndt, Love Songs of Arnhem Land,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6. Catherine J. Ellis, Aboriginal Music: Education for Living Experiences from South Australia,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 1985.
三、艺术在原住民宗教中的运用
原住民宗教对永恒梦世纪的普遍关注,是澳大利亚所有艺术产生的源泉。大多数原住民宗教及相关艺术可分为两类:一种是用来增加法力,目的是保证食物供应的有效和增长;一种用来帮助年轻人进入成年状态。
以增加法力为功能的原住民艺术有多种形式。狩猎成功为大量洞穴壁画的创作提供了动力。如埃尔金(Elkin)所述:“一个人看到河里有一条大鱼,他把鱼画在长廊上,这就确保他能再次看到这条鱼并捕获它。”[9]15有的东阿纳姆地人相信,佩戴有凝血吊坠的项链能使他们提高狩猎效率。[2]275在金伯利高原(Kimberleys),当人们从胳膊中取血并涂抹在神圣画作上时,绘画和血液这两种因素就得以结合起来。也有原住民群体把木棒雕刻成动物的形象,以确保它们所代表的物种丰产。一些牛吼器的使用也是出于同样目的。
增加法力仪式的对象是丰产母亲库娜皮皮(Kunapipi 或Gunabibi),但是仪式的目的不应该被曲解。原住民并不希冀用仪式来强迫库娜皮皮为她的信众直接提供食物。他们更雄心勃勃地希望,她能使万物的自然秩序永久化,因为它们最初是在梦世纪中被创造的。这样的自然秩序包括充足的降雨、植物的生长、动物的繁盛,最终的目标是给人类提供食物。[4]28
如果增加法力仪式意味着使自然世界恒久存在,那么入会仪式的表演就是使人类世界保持稳定。特殊的秘传知识,只掌握在已入会的成年人手中,必须代代相传。这要通过心理上令人信服的仪式来完成,青年男子(也有一小部分青年女子)经由入会仪式进入永恒梦世纪的奥秘中。
对入会者来说,一些秘密的揭示是通过歌舞来完成的。但是仪式中最深层的含义存在于有神力的雕刻棒、细绳、木杆、浮雕和牛吼器中,它们和随处可见的“储灵珈”,被认为是梦世纪精灵的体现,且是在入会仪式使用后唯一未被破坏的物品。仪式实施者一般通过拔掉几颗牙齿或一缕头发,或制造割痕来改变入会青年的外表。然而,最普遍的做法是各种类型的生殖器损伤,包括对男性的割礼和下切割礼(即沿着阴茎底部切开尿道),对女性的仪式性玷污。
增加法力和入会仪式是原住民宗教艺术情结中最重要的部分,但不是唯一的部分。如一些树皮画虽然用于入会仪式,但是大多数都是为了向孩子(和陌生人)传递关于梦世纪那些不太深奥的信息。
大多数的澳大利亚原住民仪式,不仅是宗教性的,也是实用性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为了原住民获得想要的物质结果而做出的努力。它基于这样一种信念:人类的福祉依赖于梦世纪精灵的持续活动。伯恩特夫妇认为,原住民仪式上的绘画和雕刻“是当下关于往昔神圣叙事的物质再现,是联结人与神的纽带”[2]7。④卡瑟琳·爱丽丝(Catherine Ellis)讲了一个故事,阐明了艺术在西方和原住民社会中的重要性存在差异。她在上中学的时候,参加了一场辩论,辩题是“作为音乐家的自己”。至少在她的(西方)社会,音乐家是与律师或牧师同样重要的。她在辩论上输了,英国同学告诉她:“我们本想把票投给你,但是没办法。为什么你不让自己的身份是教师、护士或者医生呢?音乐家是什么用也没有的” 。多年以后,在澳大利亚,爱丽丝认识到原住民文化中,“一个部落社区中最饱学的人,是那个‘知晓许多歌曲’的人。这一个体由他的音乐知识以及他所属民族的智慧形塑而成” 。Catherine J. Ellis, Aboriginal Music: Education for Living Experiences from South Australia,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 1985, p1.
四、原住民美学:艺术的变体
显然,艺术在原住民宗教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但有两个问题:艺术之宗教功效的基础是什么?又是什么让艺术成为永恒梦世纪一类必要的附属物?答案的线索就在原住民对梦世纪的理解中。穿行于原始乡村的神秘存在被认为从未离开过。作为永恒存在,它们今天仍然活着。然而,作为超自然物,它们能改变外在形式,它们在今天通常以自然现象的面貌出现,如特别的岩石、高山、动物。尽管现在的样子是伪装的,但是梦世纪的精灵仍与它们的人类后代紧密相连。的确,一个图腾部落的成员可能不会杀害或者吃掉他们的图腾动物,因为对他们来说,这么做无异于手足相残或自相残杀。
在原住民的观点中,与梦世纪精灵的合作对人类生存来说是绝对必要的。埃尔金和伯恩特夫妇评论道:
追踪袋鼠是不够的,必须去影响它,这样它才会在射程以内。瞄准鱼本身并不能保证精准,它必须为渔夫的矛所牵引。为了这样的目的,咒语、仪式、绘画和圣物……才有效,因为(猎人)和动物、植物、自然现象,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存在于一个伟大的道德或者社会秩序中,每一个都取决于另一个——人的职责是仪式,大自然的职责是生产食物。如果人类疏忽大意,大自然就会失败。[4]2-3
这些观察告诉我们一个原住民美学的基本原理:艺术是一个导管,把凡人的需求和愿望传达给梦世纪的精灵。一件艺术作品的每一处细节都被认为是再现“图腾群或集合地的英雄所经历的事件和状况。当艺术家雕刻和绘画时,他可能通过唱圣歌的方式将这一意义‘铭刻’于作品中。后来,它被尊为人与英雄或祖先之间的神圣纽带,并成为后者归属的创造性条件”[4]7。触摸一下“储灵珈”就意味着与超自然领域进行直接的身体接触,这种接触确保了凡人和梦世纪精灵的共生永存。
因此,我们从原住民的信仰中可以看出原住民美学的基本逻辑:人类福祉需要梦世纪精灵的祝福;这些超自然现象受到仪式的影响;而艺术作品——歌曲、舞蹈和装饰过的仪式物品是仪式的有效组成部分。既然人类的生存最终取决于艺术,那么澳大利亚原住民创作出大量的概念复杂的艺术也就不足为奇了。
原住民美学的这一主要前提有时会更进一步。通过艺术,人类不仅与永恒的梦世纪相沟通,他们实际上也进入自己的灵魂世界。如埃尔金和伯恩特夫妇所说,仪式的参与者“成为英雄或祖先……通过扮演重现祖先或伟人所做的一切,他也成为一个生命的给予者”[4]3。瓦尔比利人(Walbiri)相信,梦世纪的精灵在扮演他们的舞者身上体现(balga)出来,他们用神圣的古鲁瓦里(guruwari)图案装饰着舞者[10]198。⑤凯莉依诺雷姆(Keali' inohomoku,私下交流)已经注意到,凡人转化为精灵只会发生在跳舞的过程中。然而,一个人越是频繁地转变,他的精神力量就越大,他就越接近(隐喻地)于成为精灵。一些证据表明,舞者在这一极限状态中的本体比在正常状态更加真实,伯恩特使用了“jimerran”这个词,其指的是人们在圣地上的活动,可以翻译为“制造他们自己”,即成为他们真正的精神自我。[11]144澳大利亚传统文化的其他组成部分也支持这种观点,即个体能与梦世纪的世界联合。如人们都相信,一个妇女碰巧经过伪装成动物的梦世纪精灵身边时,如果精灵进入她的身体,她就怀孕了。生出的孩子被认为体现着对应物种本身的灵魂,那是孩子的超自然父亲。这样,一个人可能声称自己是一只袋鼠,因此有责任与其他拥有袋鼠灵魂的人一起,举行与他们的图腾信仰相适应的仪式。[11]200
原住民美学以宗教和哲学为基础,但它也有一个非常真实的心理基础,使传统澳大利亚人的个人生活充满强大的灵性。原住民宗教的正式教育在他们青少年时期的入会仪式上,但更早的时候,年轻人思想的形成就受到永恒梦世纪的影响。在盛大的歌舞狂欢会(corroborees)上,通过歌唱或打节拍来为舞者们伴奏,不仅仅是刚参加入会仪式的人,即使是最小的孩子也一定能感受到仪式表演的力量。随着舞蹈持续到深夜,孩子们在歌声和舞蹈的笼罩下睡着了,他们在视觉和表演艺术的影响自身与永恒梦世纪的联系中,进入自己的、字面意义上的“梦世纪”。[9]11通过艺术,原住民体验到对灵魂世界的真正认同。
正如个人的灵魂生命在出生前就存在一样,人们认为灵魂生命在人死后也会继续。一个人在死后会继续过另一种生活,就像活着的时候一样。艺术再一次影响着这一转变的发生。死者的尸体上绘有他们图腾群的图案,有时头发要编织成一条辫子,这条辫子也被奉为神明。[2]390,409
身体作为梦世纪灵魂容器的观念是许多其他传统仪式实践的基础。因为血液对灵魂延续生命和凡人延续生命同样重要,所以许多仪式需要从参加者的手臂或阴茎中抽取血液,以便将其洒在仪式上的物品或人身上。(在这样的语境中,红赭石有时被用来代替血液。)在实行割礼的地区,男子的神圣篮子可能装饰着蜂蜡挂件,这些挂件包裹其主人或近亲的包皮。[2]381
在原住民的思想中,仪式和艺术的作用是极其强大的,给自然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增添了色彩。澳大利亚中部是无比荒凉的半沙漠地带,那些依靠石器时代的技术在此生存了上万年的人类,显然具有伟大的实用创造力。毕竟,澳大利亚人是世界上回旋镖的唯一发明者。而且,他们对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和经过时间检验的生存技巧很有信心。⑥“一个阿纳姆地区的妇女曾有一次颇为傲慢地提及,当她看到一个斐济传教士在教区花园里劳作,因为一些植物已经死亡而忧心忡忡时,她说:‘你的教民大费周折地劳动和播种,但是我们不需要这么做。所有这些东西都在那里等着我们,祖先最终把它们留给了我们。你们和我们一样依靠太阳和雨水,但是区别在于,我们只需要在粮食成熟的时候去收割。我们并不需要费那么大劲儿。’” Ronald Berndt, and Catherine H. Berndt, The World of the First Australia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4, p93.但是在日常生活中,神秘的和主观的维度占主导地位,他们认为生命的灵魂基础——永恒的梦世纪,比世俗的、可见的世界更重要。
五、原住民美学的艺术分支
刚刚描述的原住民审美体系并非孤立存在的,而是对创造力和艺术生产、艺术在男性和女性入会仪式中的作用、恋爱巫术和原住民审美标准,以及艺术的世俗用途,都有着显著影响。例如,由于艺术的神秘功效只存在于仪式环境中,因此大多数神圣的原住民艺术只是短暂存在。经使用后,它可能会被遗忘、自行分解,或被故意销毁。还有一些物品,如“储灵珈”,被认为是梦世纪精灵的永久居所,是这一规则的例外,岩画和雕刻也是如此。但是树皮画、地面雕塑,当然还有大多数身体装饰和表演艺术都是昙花一现,尽管它们的创作过程要花好几个小时。
艺术的转变能力也限制了原住民艺术风格的创新。事实上,传统的澳大利亚人相信,永恒梦世纪的精灵只会对某些艺术作出回应,那些艺术是精确复制的平面图案或传统模式的表演。一些群体认为,如果歌手在仪式表演中因记忆出现瞬间空白造成小失误,则应该停止演唱,并从头开始,以确保仪式的超自然效果。⑦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原住民艺术是静态的和不变的。有时候一个部落会从它的邻居那里借鉴文化要素。据记载,有些个体为部落引入了新的歌曲、舞蹈或者图案。在伊尔卡拉(Yirrkala),这样的创作只能通过梦境产生,一旦被接纳,这样的创作就会同样受制于原住民艺术发展的一般规律。Richard A. Waterman, and Patricia Panyity Waterman,"Directions of Culture Change in Aboriginal Arnhem Land",in Arnold R. Pilling and Richard A. Waterman, eds., Diprotodon to Detribalization: Studies of Change among Australian Aborigines,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0, p107-108.
在许多澳大利亚族群中,标志着从青年向成年过渡的成人仪式非常重要,尤其是对男性而言。割礼伤口流出的血象征着一个男孩与母亲的亲密关系被切断,他的灵魂与老年入会者的灵魂结合在一起。但在另一个层面上,在这些场合从仪式主角的阴茎和手臂上抽取的血液也与梦世纪精灵建立并确认了神圣联系。如同在“储灵珈”上使用的红赭石,确保了梦世纪精灵带来的福祉,反过来又促进了人类的子孙繁衍,以及为人类提供食物的自然物种的丰产。
尽管不同地区的女性入会仪式各不相同,但是大多数都与性、生育和环境主题等相结合。罗纳德·伯恩特(Ronald Berndt)在阿纳姆地搜集的三首长篇情歌套曲,清楚地表明了这层联系。这些歌曲极具诗意地揭示了原住民对浪漫的看法,尤其在揭示灵魂和情色美之间关系方面具有启发性。例如,有一首歌描述了年轻的女性站在寒风中,向着男人抛媚眼,摆动着臀部,展现婀娜身姿时的吸引力。[12]57值得注意的是,该文本将女孩描述为mareiin,这个词语“通常可翻译为‘神圣的’,(尽管)在这里它传达了一种格外吸引人的或美丽的特质”。[12]
性、美和生育的结合也出现在其他语境中。例如,在古尔本岛(Goulbum Island)的歌曲中,雍古(Yulunggul)灵魂“象征阴茎,而雨(象征)精液;女性的属性是血和云……性交,无论是象征性的还是实际的,都会带来想要的雨季,而雨季反过来又会促进生育能力”[12]80。
对生育和健康的考虑是原住民个性美观念形成的基础。原住民人认为,畸形和残疾是丑陋的,他们非常看重健康的身体、干净的皮肤,甚至健康的头发。他们有时会通过化妆来提升健康的外表,比如用脂肪涂抹头发和身体。但是,我们了解到,“压力最大的是年轻人。一个刚刚进入青春期的女孩是最理想的配偶——她拥有小而圆的乳房,在生育多年后也不会下垂。年轻的男孩,特别是那些刚参加入会仪式的,也是最理想的配偶”[12]162。
恋爱巫术可以被很好地理解为一种通过使用物体或动作来获得性征服(同时也包括繁殖)的努力,而这些物体或动作的力量取决于它们的美学元素。原住民相信,正是情歌的诗意赋予它激发恋人性欲的力量,并吸引他或她无可逃避地卷入与歌者的爱情中。此外,男性有时会绘制洞穴壁画,描绘胸部突出或下体拉长的女性;男女性爱或女性在精液顺着腿流下时跳舞;或者身体有明显怀孕迹象的女性。这些都是模仿巫术(imitative magic)的例子,艺术家们相信他们所描绘的幻想会成真。
原住民审美观在本质上是非常神圣的,大多数澳大利亚艺术的创作都有明确的宗教用途。但一些传统艺术确实出现在东北阿纳姆地的非仪式语境中,如各种群体制作的带有装饰性雕刻和绘画的长矛、投矛器、桨、线轴和儿童玩具。精美的篮子、垫子和网都是为了日常使用而制作的,一些世俗的身体装饰,如项链和臂章,也都极具艺术性。尽管这些物品具有实用性,但它们的美学价值来源于推动神圣艺术创作的同一信仰体系。关于世俗物品上的神圣图案,埃尔金指出:
这些图案本身就很神秘——充满宗教力量,它们连同相关歌曲和圣歌,赋予所装饰的武器或其他物品一种“美德”。如此“丰富”的武器不仅更令人着迷,而且威力更大。它被赋予了一种来自创造历史的英雄的力量,这种力量通过神话和仪式的媒介,始终为人类所拥有。[13]9
尽管在澳大利亚传统社会中,宗教艺术对世俗艺术有影响,但这两个领域截然不同,这种差异强调了宗教艺术的优先地位。与宗教艺术相比,世俗艺术与传统的联系不那么紧密,因此,当宗教艺术的创作者必须精确复制旧图案时,世俗艺术的创作者可以在现实主义或象征主义表现之间进行选择,且可以进行一些创新。宗教与世俗的区别也影响了原住民艺术家的地位。在东北阿纳姆地,能够绘制神圣图案被认为是一种伟大的天赋,只有少数受上天眷顾的人,才能获得较高的地位,并获得与他们的努力相应的价值。相比之下,世俗艺术的创造者既没有获得地位,也没有得到补偿。[4]110
有时候,世俗艺术与宗教的联系强调了艺术传达信息的重要性。在澳大利亚西部的巴尔戈(Balgo),伯恩特夫妇看到男人们在板子上画着周围乡村的地图。表面上,他们记录了关于特定地点的图腾信息,但当男人们相互交换图腾板时,他们获得了当地和远处地形的知识。[2]114同样,X射线画提供了有价值的解剖图,为任何想要猎杀所描绘动物的人提供了有用的信息。最后,带有雕刻和装饰的“信息棒”(message sticks)也很常见。信使会带着这样的“信息棒”,与其说是象征性地传递信息,不如说是证明他口头说明的重要性和准确性。[3]107
六、结论
对狩猎采集群体美学体系的描述,证明了即使在技术、人口和劳动分工方面与西方差距最为明显的民族中,也能找到艺术精神。传统原住民确实创造了艺术,尽管田野调查者经常注意到他们没有“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 art's sake),原住民艺术家确实在艺术创作中体验到真正的快乐,这种满足感将对“美”的感官满足,与对精神和社会意义的理智欣赏相结合。[2]306,350,352;[3]167;[4]10-11;[13]10;[14]9-10;[15]7-8
田野调查者还一致指出,原住民在技艺欣赏水平方面存在差异,他们奖励特别有天赋的个人,特别是原住民歌手和迪杰里杜演奏者,他们经受了长期刻苦的训练。虽然原住民艺术家得到承认,但是他们不是可以依靠佣金来维持生计的全职专家,而是需要融入社会环境,从事适合其性别的所有活动。⑧如:Jones, Trevor, "Arnhem Land Music, Part 2, A Musical Survey",Oceania,1956/7,28(1):1-30; A.P.Elkin, Ronald M. Berndt,and Catherine H. Berndt, Art in Arnhem Land,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0, p110;Charles Percy Mountford, "The Artist and His Art in an Australian Aboriginal Society",in M.W. Smith, ed., The Artist in Tribal Society, Free Press of Glencoe, 1961,p7; F.D. McCarthy,"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s of Australian Aboriginal Art", Journal and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New South Wales, 1957, vol.9, part1, p13-14。
但是,原住民艺术最重要的意义不是艺术家的社会融合,而是艺术本身所衍生的审美体系的文化融合。原住民美学不仅适用于更广泛的社会概念体系,它还在将信念统一、阐释和转化为具体策略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这种信念使得人们相信,通过艺术可以和永恒梦世纪所有重要的精灵进行直接的、亲密的、真正的接触。任何地域的艺术中,精神意蕴都不可或缺,这在澳大利亚原住民艺术中尤为显著。显然,如果这一维度被认为是审美创造中最珍贵的方面,那么对澳大利亚原住民来说,虽然他们的物质文化很简单,但是他们创造出一些世界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艺术。
七、后记
传统原住民文化的根基可回溯到数万年以前,在一些社区中,目前所描述的长期建立的实践和观念仍有待发现。然而,除了这些社区以外,自从在两百年前成为英国殖民地后,澳大利亚的许多情况已经发生了改变。与所有古老的原住民艺术形式相对应的还有诸多当代艺术,它们反映出非原住民文化的影响。同时,原住民民族对世界的影响也远远超出自身范围。幸运的是,对这些变化中许多独特部分的研究和描述已经陆续出版。⑨具体可参:Sylvia Kleinert and Margo Neale, eds., Oxford Companion to Aboriginal Art and Culture,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正如本文其他地方所述,下面的评论将首要关注阿纳姆地区的艺术。关于澳大利亚中部的发展情况,建议读者查阅其他资料(如:Andrew Sayers, Australian Ar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141-145;V. S. Megaw and M. Ruth Megaw, "Painting Country: The Arrente Watercolour Artists of Hermanns burg" in Sylvia Kleinert and Margo Neale, eds.,Oxford Companion to Aboriginal Art and Cultu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197-204)。包括赫曼斯堡(Hermannsburg)重要的水彩画家阿尔伯特·纳玛吉拉(Albert Namatjira),“成为了他那个时代最著名的原住民,也是那时为数不多的澳大利亚艺术家之一,留下了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Andrew Sayers, Australian Art,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141.
二维绘画中发生的改变揭示了原住民与非传统之间显著的相互作用。如前所述,岩壁上的绘画长期以来有着多种用途,从引导年轻人了解神话中可以明示的方面,到成为梦世纪手工作品的表征。在雨季,因为全家旅行要搬离岩石住处,原住民会另造小屋,屋顶覆盖着从澳洲桉树上剥下来的树皮,树皮上绘制的人物和图案与那些公开的岩画上的图像相同。
在欧洲人到达澳大利亚后,一些人对岩画产生了好奇。其中一位是英国生物学家、墨尔本大学的鲍德温·斯宾塞(Baldwin Spencer)教授,他注意到岩画和树皮画的相似之处,以及后者可以购买并带回家研究的事实。到1912年,斯宾塞开始在阿纳姆地委托创作并购买树皮画,他以品质极高的烟草来支付。[6]112随着学术界对树皮画兴趣的增加,树皮画的商业市场迅猛发展。它们先是通过教会商店销售,后来也在澳大利亚议会原住民艺术委员会资助的社区艺术中心售卖。
尽管树皮画已经成为一种产业,是制作者重要的收入来源,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艺术形式在原住民民族中已经失去了原有的文化意义。薇薇安·约翰逊(Vivien Johnson)说:
现在(澳大利亚中部)的昆云库人(Kunwinjku)一般不住在岩画艺术现场附近,树皮画和市场上销售的纸画已经开始在世俗领域的宗教知识传播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绘画现在有两种用途和两类受众:在昆云库人中,它用于道德说教;在远离这里的地方,它则是推广文化的力量。[16]211
曾经专属于参加过入会仪式的男性所独有的一些树皮画图像,现在可以卖给原住民人以外的顾客,但同样的,文化的作用力是相互的:至少对于昆云库人来说,有意识地分享这些图像,可以向外界展示他们自己的文化有多么强大。[16]211
原住民绘画也经历了其他的置换方式。近几十年来,一些个体进入了美术的世界。在早期阶段,他们似乎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复制传统绘画(在树皮、纸或画布上),要么采用以欧洲为中心的非原住民世界的架上绘画风格。然而,1984年出现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在悉尼萨里郡(Surry Hills)的艺术空间举办的一次展览成为了分水岭。在那场名为“ 古利人艺术’84”(“Koori Art'84”)的展览中,25名原住民艺术家(一些来自阿纳姆地)展出了一些虽然技艺繁复但是以原住民经历和情感为主题的画作。社会现实主义和“对抗性意象”[17]267是那时的主流。 “古利人艺术’84”开创了一个先例,原住民艺术家在那之后举办了大量架上绘画展,同样使用美术绘画作为媒介,以强有力的方式表现原住民关切的话题。
班杜克·马里卡(Banduk Marika,生于1954年)的生活展示了20世纪初以来,阿纳姆地绘画所经历的巨大变革。[18]637-639马里卡的父亲马瓦兰(Mawalan)和她的叔叔马塔曼(Mathaman)长期以来一直从事传统树皮画制作,但当20世纪30年代伊尔卡拉建立了一个正式组织后,他们成了最早一批为售卖而作画的人。(马塔曼1959年创作的一幅画,在1996年以71 250美元的价格售出,这是树皮画有史以来的最高价格。)可以预见,随着非原住民澳大利亚人的到来,澳大利亚不仅出现了树皮画市场,而且对原住民文化和土地都构成了威胁。由于树皮画在传统上被用于(与其他物品一起)验证原住民群体与他们居住村落的关系,因此,马瓦兰和其他雍古头领,成为1963年阻挠伊尔卡拉采矿开发的“树皮请愿”(Bark Petition)组织者,也就不足为奇了。⑩树皮请愿书——一块树皮,中间是一段用雍古语和英语写的文字,周围是传统彩绘图像——被送到澳大利亚议会,触发了原住民的土地权利运动,最终导致1976年《原住民土地权(北领地区)法》的出台。Howard Morphy, "Art and Politics: The Bark Petition and the Barunga Statement", in Sylvia Kleinert and Margo Neale, eds., Oxford Companion to Aboriginal Art and Culture,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100-102.
马瓦兰·马里卡不仅把传统绘画技艺教给了儿子,也教给了女儿(包括班杜克·马里卡),他是该地区第一个这么做的人。班杜克在28岁时搬到悉尼,开始版画创作,并成为堪培拉艺术学院的常驻艺术家。1993年,班杜克利用版权法阻止了一家地毯公司未经许可复制她的图案。自那时起,班杜克就一直担任澳大利亚国家美术馆、北领地博物馆和艺术馆的董事会成员。与此同时,她的麻胶版画和丝网版画受到广泛好评,在美国、印度、埃及、努美阿和新加坡展出。
除了作为一名艺术家创作作品外,班杜克还积极参与将艺术和传统文化联系起来的事业。1990年,她在纽约易洛魁的首个原住民集会点上发表讲话。有一份声明确认她获得了澳大利亚议会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艺术委员会颁发的2001年红赭石奖(Red Ochre Award),其中部分内容如下:
她在原住民艺术、版权和文化遗产问题方面的知识和专长受到高度赞赏。班杜克是她所在社区的一位长者和艺术家,经常被要求在原住民和非原住民文化之间,以及传统和当代习俗之间,提供建议、进行磋商并从中协调。她与斯蒂芬·佩奇(Stephen Page)合作,担任2000年悉尼奥运会开幕式的文化顾问,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⑪声明的结尾写道:“意识到文化协议,在接受红赭石奖的提名之前,班杜克征求并得到了来自她自己社区的许可。”http://abc.net.au/message/blackarts/visual/banduk marika.htm.
因此,就用了两代人的时间,马里卡家族已经从在名为伊尔卡拉(Yirrkala)的小海滩营地制作传统树皮画,转变为班杜克在国家和国际艺术界参与艺术活动。班杜克并不是唯一一位职业生涯从传统走向全球的原住民画家。原住民画家的作品曾在两届威尼斯双年展展出。1985年,原住民艺术家艾薇儿·奎尔(Avril Quaill)在悉尼协助建造了一幅大型壁画[19]126。
原住民视觉艺术也影响了澳大利亚的流行文化。例如,澳洲航空公司的两架747-400喷气式飞机已经喷涂上原住民设计的图案;从T恤到高级女装,原住民图案随处可见。⑫Margaret Maynard,"Indigenous Dress",in Sylvia Kleinert and Margo Neale, eds., Oxford Companion to Aboriginal Art and Culture,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384-390.
与视觉艺术一样,原住民表演艺术在某些情况下保持不变,而在其他方面则反映了两个世纪以来与殖民主义势力的密切互动,有时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例如,迪杰里杜曾经只在澳大利亚北部被发现,现在不仅成为整个澳大利亚原住民民族的象征,而且还远渡重洋,成为对新世纪(New Age)运动和世界音乐感兴趣的美国人和欧洲人的流行乐器——以致人们对采伐这么多树来做制造乐器的材料是否会影响环境提出了质疑。在阿纳姆地,马宁格里达(Maningrida)艺术和文化合作社甚至创建了一个网站,尝试让非原住民用户了解迪杰里杜的历史,以及它在原住民音乐和文化中的复杂作用。[20]344
也许更可预见的是,结合了原住民与非原住民元素的流行乐派已经出现。例如,在1990年,来自阿纳姆地的一群人组建了第一个原住民摇滚乐队,取名约图银地(Yothu Yindi),并录制了唱片《条约》(Treaty),该唱片曾登上澳大利亚流行乐排行榜。凯瑟琳·奥因(Kathleen Oien)指出:“从那时起,这个乐队获得了国际认可,并在澳大利亚一家大型唱片公司制作了几张专辑,这有助于提高对本土流行乐的认识和理解”——这正是乐队希望实现的目标。[21]335来自阿纳姆地的另一个群体,布莱巴拉穆吉克人(Blebala Mujik)也坚决要将当代音乐和传统音乐都纳入自己的曲库。奥因说:“当被问及是否可以在教育CD光盘上使用他们的一首传统歌曲时,乐队同意授权,但附带条件是还要加上一首摇滚歌曲,因为他们想表明自己既能表演传统音乐,也能表演现代音乐。”[21]337“ 古利人艺术’84”展览以来,原住民艺术家的大多数美术作品都倾向所表达的主题具有话题性,原住民流行音乐经常以同样的方式,解决对音乐家背景特别关注的问题。与情歌不同,“他们更愿意处理对自身社区重要的话题,比如与土地的关系、社区问题,以及对历史和当下不公正的抗议”[21]339。
原住民舞蹈的发展轨迹与绘画和音乐类似。例如,大获成功的班加拉舞剧团⑬Lisa Meekison, "Bangarra Dance Theatre",in Sylvia Kleinert and Margo Neale, eds., Oxford Companion to Aboriginal Art and Culture,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367-369.在表演中融入了传统与现代的舞蹈动作。迪亚卡普拉·穆尼亚伦(Djakapurra Munyarryun)于2002年以首席舞蹈家的身份退休,他还担任剧团的创意顾问,不仅提供了可以作为编舞基础的传统故事,而且根据其家乡——东北阿纳姆地的达林拜(Darlinbuy)——老人的意见,用于加工的素材是确定可以公开的。因此,与上文提到的版画家班杜克·马里卡一样,穆尼亚伦也是联结本土传统艺术与当代全球观众之间的纽带:班加拉舞剧团从纽约到爱丁堡再到约翰内斯堡都有演出,穆尼亚伦还带领1 000名原住民舞蹈演员参加了2000年悉尼奥运会的开幕式。
原住民文学也有相似的发展过程。同绘画和舞蹈一样,口头文学在传统文化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如今,古老的故事往往通过书面文字广为传播。原住民作家的小说、诗歌和戏剧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广播、电影和电视也是如此。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作品反映了传统文化和当代文化的方方面面。例如,莎莉·摩根(Sally Morgan)非常成功的剧作《我的位置》(My Place),就是以原住民和非原住民后裔间的个体关系,以及殖民进程在澳大利亚的展开方式为主题。⑭Philip Morrissey,"Aboriginal Writing",in Sylvia Kleinert and Margo Neale, eds., Oxford Companion to Aboriginal Art and Culture,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316.默里剧院的艺术家大卫·莫瓦利亚里(David Mowaliari)解释了老说书人莫林·沃森(Maureen Watson)的话:
故事的传统作用是提供意义以形塑世界,解释世界为什么是这样的,以及我们与它的联系……基督教、马、丰田车、金钱、艾滋病和酒精的到来——这一切都需要故事、舞蹈、绘画和歌曲。如果我们不能讲述它的故事,我们怎么能驾驭它?我们又如何接受、拒绝或使用它?[22]349-350
原住民文学的杂交也有一个全球维度。例如,诗人兼散文家蒙多罗罗(Mundorooroo)就受到弗兰兹·法农(Franz Fanon)、马尔科姆·埃克斯(Malcom X)和鲍勃·马利(Bob Marley)的影响。
在这些原住民艺术因欧洲殖民而发生改变的案例中,有几个主题是显而易见的。最明显的是,新出现的风格和流派将传统文化因子与来自国外的元素相结合,形成了独特而重要的综合艺术。但无论哪种情况,新旧文化交融一直都受到原住民与非原住民不平等社会地位的制约,而原住民艺术家利用艺术媒介来捍卫和加强自身及其文化。这场战斗还没有结束。例如,截至20世纪90年代末,有200多个包含原住民内容的网站,其中约1/3由原住民组织或个人创建。[23]312但即使在互联网上,原住民民族的身份和遗产也存在争议。因此,一家名为“马宁格里达艺术与文化”的艺术合作社在其网页写道:“每个图案都代表了艺术家的个人梦想,本质上是神圣的。艺术家们已经允许他们的作品在互联网上展示,供公众观看和借鉴。然而,乔治·加尼吉巴拉(George Ganyjibala)和吉米·安贡古纳(Jimmy Angunguna)这两位老者认为,根据传统规定,绘制他人的图案或者未经许可的复制都是一种犯罪行为。请尊重作品中所体现的灵魂”(http://www.bu.aust. com/~maningrida/gallery/gallery.htm.) 。⑮大卫·纳森(David Nathan)指出:“网络和‘原住民’社会系统有诸多共同之处:都由网络组成,信息传递迅速,个体的参与取决于他或她在网络术语中所表达的认同。” Nathan, David, "The World Wide Web" ,in Sylvia Kleinert and Margo Neale, eds., Oxford Companion to Aboriginal Art and Cultu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312.
另一个经常影响原住民艺术的因素是旅游业,它现在是澳大利亚最大的产业。[24]391直到20世纪80年代,澳大利亚一直试图通过宣传其自然环境来吸引游客,这其中包括海滩的休闲氛围、内陆引人注目的风景,还有独具特色的野生动物。但随着国际游客变得越来越见多识广,很明显,澳大利亚文化遗产(即原住民文化遗产)的营销将吸引更多游客并能带来财政收入的增加。⑯澳大利亚旅游委员会的网站上写道:“根据1998—1999年澳大利亚原住民旅游的官方调查可知,来自所有国家的85%到95%的游客,是因为想要体验当地原住民旅游才前往澳大利亚。这一数据可能会随着世界范围内37亿观众观看奥运会开幕式而增加。”http://www.aussie.net.au.这样,随着原住民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导游、节日和其他涉及他们自己族群的活动中,原住民的身份认同和控制权也会成为争夺的领地。
与过去几千年来澳大利亚原住民艺术缓慢的变化速度相比,近200年发生的事件是灾难性的。但多亏了大量的文献和分析,我们才可以清楚地看到古代的历史并没有被抹去。相反,它存在于大批艺术作品中,有些作品复制了它们早期的内容;有些尽管在形式上差别很大,但仍然是行得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