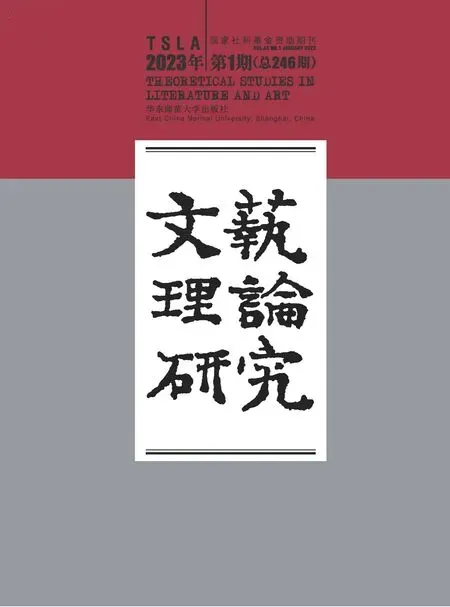走向融合的元宇宙:电子游戏与数字身体之变
韦施伊
元宇宙仿佛是一夜之间忽然火热起来的概念,但究其本性,我们可以发现,电子游戏是元宇宙最主要的先导形态。电子游戏给人的最首要的感觉是沉浸,更具体地说,是那种玩家按下按键却不关注所按下的按键的感觉(Kirkpatrick130),玩家会觉得是“我”在跳跃、奔跑、攀爬,而并非“我”在控制器/手柄(Joy-Con)上按下X键、Y键和ZL+B组合键。这种感觉在经典的“屏幕-控制器”组合的固定电子游戏平台中得到尤其明显的体现,它们尽可能地分散玩家对实际身体和周围环境的注意力,吸引玩家长时间驻足屏幕世界,实现沉浸感,在游戏合拍的节奏中体验到心流(flow)。①随着移动技术的发展和可穿戴设备的普及,电子游戏呈现出了一种更接近元宇宙的面目:越来越仿真化,并且借助互联网速的提升,虚拟现实设备与网络深度整合,形成仿真型互联网,这正是元宇宙的本质形态。更重要的是,元宇宙并不是对真实生活的代替,它与生活世界深度整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形态。这一深度融合,不是深度沉浸,而是一种适度沉浸中的自如切换。这也是电子游戏通往的方向,我们不需要,也不会花一整段相对长的时间停留在虚拟世界中,而是随时地、短暂地在虚拟和现实中切换。玩家能在虚拟世界中存在,却又能随时保持对现实世界的注意,在两者的切换之间,在与屏幕互动的同时并不遗漏对现实信息的捕捉之间,体验到边际性、跨越性的身体和世界感受。看起来,我们似乎更少地“沉浸”了,其实恰恰相反,我们更深地和虚拟相纠缠。
沿着这样的观察,我们将首先发现,在电子游戏时代,数字世界已经从单一规则的独立宇宙逐渐过渡到全面融合的元宇宙,电子游戏其实正作为元宇宙的一个基础范例被我们所体验;其次,在这样的转变中,沉浸的意义也发生了更替;最后,借助维利里奥(Paul Virilio)对“分神”(absence)②现象的描述和解释,得以理解在“新沉浸”情境中,我们全新的身体状态和知觉模式。
思考数字身体,我们要扭转几个固有的想法。首先,身体并不先于,也不外在于数字游戏而存在,恰恰是在数字环境中,数字身体才被生成和作用。其次,数字身体并不是单纯的虚拟身体,那种无实体的数码存在物,或者某个虚拟化身,也并不是与技术高度装配的科幻场景里出现的“赛博格”,它完全可以是最为普遍的、随处可见的拿着手机或游戏机的玩家身体,这个身体已经是和数字技术互相博弈、适应过的游戏化了的数字身体。第三,游戏不是世界或社会活动的部分,而是作为我们整个的生活形式,我们和我们的生活世界是如何动态交互地共同构成的,这一点在电子游戏中尤为明显(技术、资本、知觉、反馈、观念、体系等),所以电子游戏世界将作为元宇宙的先兆被优先体验。在这里,我们沿着电子游戏的本性讨论元宇宙环境下,数字化的身体会产生何种改变。
一、 从封闭走向开放的数字世界
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曾总结游戏的如下几个特征:1.自愿。游戏必然是自愿的,服从命令的活动不过是对游戏虚有其表的模仿,并不是真正的游戏。2.游戏步出了“真实”的生活,是非平常的活动。3.游戏的隔离性与局限性。这一点同时体现在游戏有时间上的起始终结、空间上的特定范围和心理上的界限:
一切游戏的进行和存在都限定在事先划定的场地,标定的边界既可能是物质的边界,也可能是想象中的边界,既可能是有意识划定的边界,也可能是理所当然的边界。正如游戏和仪式在形式上没有明显的区别一样,“神圣的场地”和游戏的场地也没有明确而显著的区别。角斗场、牌桌、魔术圈、神庙、舞台、屏幕、网球场、法庭等等,无论在形态上还是功能上都是游戏场地,是禁止外人涉足的、孤立的、或用藩篱圈定的、神圣化的场地,遵守特定规则的场地。(赫伊津哈11)
在这里,赫伊津哈提出了“魔术圈”(Magic Circle)的概念,指的是游戏在日常的、普通的世界中,划出了一个临时世界,有其绝对而独特的规则和秩序,专门用以执行某种单独的行为,进行某种特殊的活动,游戏者对游戏本身的边界与尺度也有所意识,同时,这一圈界反过来也被社会共同的约定所保护。这个概念表明了将游戏与现实相分离的想法,虽然赫伊津哈承认,游戏的元素体现在我们生活和文化的方方面面,但是他依然认为,游戏本身作为一种独特的活动,仍将我们从现实世界中排除,带入一个暂时性的领域。
萨伦(Katie Salen)和齐默尔曼(Eric Zimmerman)继续了对魔术圈的思考,强调魔术圈作为游戏世界与现实世界的边界,魔术圈作为“圈”,封闭性是它的首要特征,“作为一个封闭的‘圈’,它所包围的空间是封闭的,并且与现实世界相分离……从根本上来说,魔术圈是游戏发生的地方”,玩一个游戏,就意味着进入一个魔术圈,游戏划定了一个与外部世界相区隔的自足世界,“一个新的现实被创造出来,它由规则定义,玩家得以居于其中”(Salen and Zimmerman95-96),游戏世界更像是现实世界的一个子集,玩家可以进入和退出。
如果说以上的讨论,更多的是基于实体游戏(比如网球、丢沙包、围棋等),那么尤尔(Jesper Juul)则进一步分析了电子游戏中的“魔术圈”。相较而言,电子游戏的魔术圈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因为电子游戏的空间是由输出设备(显示器、音响等)和输入设备(键盘、手柄等)所构成的,所以它也据此直接被划分出了一个游戏/现实的区隔。在足球的实体游戏中,球场占据着一块空地,划出了相应的边线,当足球出界时,游戏会被暂停,因为足球从魔术圈所划定的边线跃出,滚到了现实世界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尤尔说,在电子游戏中“没有任何一个‘球’可以出界”(Juul165),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显示屏里的数码足球能滚落到你家里的地毯上。
但是,我们在这里还需要再仔细地甄别一下。例如,在足球类电子游戏《国际足联》(FIFA)中,它同样有划着边线的场地,球员传球时,足球也不时会出界。然而,在这个时候,足球并没有掉落到现实的客厅中,而是滚到了看台边缘。这个球从一个“游戏场地”滚动至一个“虚拟世界”,也就是说,在这里,魔术圈的区隔作用失效了,它所预设的现实与游戏的边界功能没有实现,因为这里增加了虚拟世界的一环。游戏的世界不再是现实的一个子集,游戏世界本身成了一个超集,它足以容纳那个包含着虚拟边线的魔术圈所划定的足球运动,它也同样承载着看台观众的呐喊、场边教练的走动、买卖球员的交易窗口等。
一方面,由魔术圈所封闭的游戏世界,在电子游戏时代已经无限地膨胀,它不单是游戏发生的地方,还同时允许许多其他的事情发生和运转。另一方面,游戏世界也在试探着“球”出界的可能。在《精灵宝可梦GO》中,皮卡丘就从游戏里跑到了玩家所居住的大街上,它能够绕开行人奔跑跳跃,和杰尼龟互相追逐。在这样的情境中,整个现实似乎都是游戏的现实,游戏对物理现实进行了叠加覆盖。可以说,游戏与世界发生了新的融合(convergence),游戏成了我们的新现实。
如果说每一个游戏都各自遵循着自己的规则,建立着自己独立的宇宙,那么,如何从某个单一的虚拟世界过渡到一个元宇宙(Metaverse),则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元宇宙,由前缀“meta”(意为“超越”)和后缀“verse”(“宇宙”的简称)组成,“它的字面意思是超越物理世界的宇宙。更具体地说,这个‘超越的宇宙’指的是计算机生成的世界,区分于超越物理领域之外的形而上学或精神概念的范畴”(Dionisio, Burns III and Gilbert6)。尼尔·斯蒂芬森(Neal Stephenson)在小说《雪崩》(SnowCrash, 1992年)中首创了元宇宙一词,用户通过计算机终端登入元宇宙,以化身形式在这个虚拟世界中参与人类社会的全部活动,有别于参数设置和特定目标的数字游戏环境,元宇宙是一个和物理世界平行运作的开放的数字世界。
目前,元宇宙还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但存在这样一个基本的共识,即元宇宙是由互联网逐渐演化发展的一个实时共享的在线世界,是线上、线下多平台融合组成的一种新的经济和文明系统。元宇宙的实现仰赖着以下四个方面的技术发展:沉浸的现实感(immersive realism)、访问和身份的泛在性(ubiquity of access and identity)、互操作性(interoperability)和可扩展性(scalability)。《第二人生》(SecondLife)可以说是元宇宙的前身,它极其接近于我们对元宇宙的想象。在这个游戏里,用户通过化身形象(身份)在模拟世界中漫游(沉浸感),并且任意地点都能接入游戏(随地)和其他玩家(朋友)进行实时互动(低延迟),游戏提供多种玩法,可以恋爱、上课、购物、听演唱会等,甚至可以不玩任何游戏(多元化),最重要的是,在游戏中你所赚取的“林登币”(Linden Dollar)可以兑换成现实货币(经济系统),这个游戏世界依靠大量活跃用户建立着自己的各种体系(文明)。③由此可见,元宇宙,第一,在生存方式上,让人类能够实现现实和虚拟的两栖生活,但它并不是以虚拟取代现实的方式,它更强调虚实融合而非区隔,在元宇宙的语境中,再去谈论虚拟与现实之分,是无效的、无意义的问题,因为没有任何的事物是彻底的现实或完全的虚拟的。第二,在感官维度上,元宇宙能够扩展人类的感官系统,在一个综合感官中,人类能够获得新的情感关系和价值坐标,更为开放和富有创造力地去思考和生活。
现在谈论元宇宙,似乎显得为时过早。但正如弗卢塞尔(Vilém Flusser)所言:
从当下看,那是一个神话般的社会,有着与我们此时截然不同的另一种生活。在那里,当前科学的、政治的和艺术的范畴会变得难以辨认,甚至我们的精神与生存方式也会蒙上一层新颖而奇异的色彩。这个社会并不存在于遥远的未来,实际上,我们已站在了临界点上:那神话般的、新的社会与生活结构已经在世界与我们自己身上显出痕迹。我们身处在一个正在浮现的乌托邦之中;它慢慢浸染我们的环境,渗入我们的毛孔。在当下,发生在周遭或我们自身生命中的事情如梦似幻,以前所有的乌托邦(不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都在这个世界面前显得苍白乏味。(弗卢塞尔,“警示”1)
元宇宙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虚拟世界,因为它是虚实相融的,现实世界是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时,它也不能够简单地被想象为电子游戏,因为它包含着更多元的生活面貌。虽然元宇宙暂未真正实现,但在一个比喻的意义上说,电子游戏的世界是我们对元宇宙学习、适应和畅想的一个“新手村”,就像我们在玩《植物大战僵尸》(Plantsvs.Zombies)的第一关之前,游戏会设置一个新手导览,它教会你怎样收集太阳、种植植物、对抗僵尸,然后我们才能开始自己的闯关。这就是所谓新手村的意义。我们虽不能知道元宇宙确切的模样,但在“新手村”获取“装备”“技能”的过程中,我们能够获得未来元宇宙的基本生存技能和生活方式,那个开放的宇宙值得被我们期待。
二、 重解数字沉浸
沉浸(immersion)源于拉丁语“immersio-nem”,由词根“mergere”(陷入、浸入、下沉、淹没)和词缀“in”(进入、在)组成,形容的是淹没于水(或其他液体)中的体验,一般在比喻意义上使用该词,比如,沉浸式电影、沉浸式音乐、沉浸式文学,甚至是沉浸式化妆,它表达了一种在艺术鉴赏或其他活动中,那种引人入胜、忘乎所以、全身心投入的状态。“我们在心理上所寻求的沉浸式经验,是那种我们在大海或泳池中所体验到的相同感受:被一个完全不同的现实所包围,就像水和空气的不同,它占据了我们所有的注意力,和我们整个的知觉装置。我们享受从所熟悉的世界中走出来,享受由这个新天地所产生的警觉感,享受在其中学习如何行动所带来的快乐。”(Murray99)从珍妮特·莫里(Janet Horowitz Murray)的表述中可以看到,沉浸一词侧重于表达我们愉悦的心理感受,而关于那个“新天地”,那个从“空气”置换成“水”的新现实,我们关心得还太少。
无论是日常中还是学术上,我们对沉浸的使用都过于含混,它只传达了一种囫囵不清的面貌。尤其在数字技术和通信技术高速跃进的当今,我们对“新天地”的沉浸,已经早已不限于对文本空白所召唤的意义填补,或是静止坐在剧院中被巨幕笼覆的震惊。当你登陆《第二人生》,“换”上喜欢的衣服、发型、肤色,去学校上学,去赌场赌博,跟远端登陆的陌生人搭讪,出售货品,买卖地产时;或者当你打开《超级马里奥:奥德赛》(SuperMarioOdyssey),在里面甩动帽子,附身在不同物品身上和酷霸王搏斗时;抑或是在你低头看着手机屏幕和抬头观望现实之间切换时,你都感受着全新的沉浸。
可以说,电子游戏不仅最大限度地要求着沉浸,最大程度地体现着沉浸,也最大限度地更替着沉浸。第一个沉浸,指的是沉浸式技术,得以创造出虚拟数字环境和媒介空间;第二个沉浸,指的是用户状态和心流体验;第三个沉浸,是对沉浸观念的更新。
沉浸式技术(Immersive Technology)指的是一种多感官(主要是视觉和听觉)的数字环境,它用数字内容扩展或完全取代了用户的真实环境。这种技术模糊了物理世界和模拟世界之间的界限,从而创造一种沉浸感(Daassi and Debbabi2)。最主要的沉浸式技术,是AR技术(“Augmented Reality”,增强现实)和VR技术(“Virtual Reality”,虚拟现实)。AR着力于在现实环境中叠加数字内容,让用户可以在物理世界中与数字内容进行实时互动,它捕捉现实世界的数据,将数字内容融合其中。如,用户可以在自己的身体上虚拟试穿衣服、试用口红等,又如,《侏罗纪公园3D》游戏中的恐龙能够追逐或躲避用户,对用户的动作作出反应,就像它们和用户“同在”一个现实中。VR则侧重于将真实内容叠加在虚拟环境中,比如上文提到的《第二人生》游戏,它创造了一个能够模拟真实生活体验的虚拟世界,让用户产生并相信自己“在那里”的感觉。
这种“在那里”(being there)的感觉,被定义为在场感(presence),也被称为电传存在(telepresence,或译为远程存在)。沉浸所意味的那种身临其境的在场感,所描述的是人们(用户)在媒介世界中真实存在的印象,“指的是个体在多大程度上感觉到存在于媒介环境中,而不是非媒介的物理环境中……这个[媒介环境]可以是时间上或空间上远程的真实环境或者是一个由计算机合成的虚拟世界”(Steuer76),它被定义为:
一种心理状态或主观感知,在这种状态下,即使一个人当前的部分或全部体验,是由人造技术产生或过滤而来的,可这部分或全部的感知仍不能准确知悉技术在这种体验中的作用。除非是在最极端的情况下,个体可以正确指出她/他正在使用该技术,否则就“某些层面”和“某种程度”而言,她/他的知觉会过度关注在知识、物体、事件、实体和环境上,就好像技术没有参与其中。(Lombard)
也就是说,这种在场感,首先是对物理世界的分心和忘却,是对虚拟世界的投入,其次是对技术媒介的无意识或不察觉。这就使在场感导向了心流体验。
心流④和在场感一样,也是沉浸体验的表现。它由米哈里·契克森米哈(Mihaly Csikszentmi-halyi)于1975年提出,描述一个人在某一活动中感到全神贯注、充分参与的精神和身体状态,其特征为强烈的参与度、目标与反馈的明确性、集中的注意力、自我意识缺位、扭曲的时间感、挑战的难度和所需技能之间的平衡,以及对整个活动的掌控感。心流和在场感是互相作用的,前者集中于我们在技术媒介中的行动状态,后者则偏重在支持这种行动的技术环境和媒介空间。心流能够加强我们的在场感,而在场感能够更好地帮助我们展开具体行动。
无论是由技术媒介所打造的虚拟环境还是我们在虚拟世界中的种种活动,沉浸都旨在让我们的感知全然淹没其中,以做到“对物理世界的阻隔”(Biocca25)。也就是说,我们在游戏的沉浸状态中,会对按下的按键无意识、对按下按键的手无意识、对窗外的响动无意识、对光纤通信的传输无意识……可这样的状态似乎只是一种“沉浸的神话”,是一种极端理想的状态。实际上,我们在玩电子游戏的时候,并不总是对现实世界分心的,而是同时保持着对两个世界的注意力。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更浅或更少地“沉浸”,相反,我们已经更深地“沉浸”在融合现实中了。
布兰登·基奥(Brendan Keogh)通过观察一位一边在手机上玩《糖果粉碎传奇》(CandyCrush)一边不时抬头看看是否到站的女士,发现了一个“等待中的身体”(body-in-waiting),这正是我们最典型的也最日常的游戏状态,“玩家仍然对它们周围的实际世界保持一定的关注,尽管他们也关注(和建构)着呈现在手掌大小的小屏幕上的虚拟世界:乘坐巴士时,在咖啡馆等朋友时,等待广告结束时”(Keogh58)。在技术穿戴和移动技术普及之前,在固定平台和控制器上玩游戏给我们造成的稳固印象是公共/私人、在场/不在、分心/注意、实际/虚拟的二元对立,而如今我们介入电子游戏的常态恰恰说明了这些分野其实从未真正存在过。
相较于我们对沉浸的旧有理解,如今融合现实里的“沉浸”,体现为我们一方面能够在电子游戏的虚拟世界里感受到一种在场感,同时又能意识到我们处于实际世界的这样一种跨越式的融合状态。电子游戏让实际和虚拟的身体/世界的融合变得更为明确,而这种融合也成了电子游戏的基础。
三、 分神:数字身体现象学
“等待中的身体”帮助我们更新了对沉浸的理解,发现了虚拟与现实世界的融合,同时也敦促着一种从身体到元身体的跨越式理解。乔纳森·克拉里(Jonathan Crary)对这种身体的等待状态别有洞见,他将此形容为“悬置”(suspension),“它暗示了一种在惊奇或静观中固定、抓住某物的可能,在这种状态中,专注的主体既无法动弹,也没有着落。不过,与此同时,悬置还是一种取消或一种打断的状态,……它既是一种全神贯注,又是一种缺席或延搁”(克拉里10)。我们每个人每天几乎都对此有所体会,当我们打开手机,等待游戏加载(loading)时,我们的眼睛盯着屏幕,做好了随时进入游戏的准备,但我们的身体仍保持紧绷地等待(不是放松的),我们既是专注的/在场的(presence),同时又是悬置的/不在的(absence)。
维利里奥试图为这种矛盾性的身体状况找到更为根源性的解释,他用“分神”来描述日常生活中的我们意识的微小断裂,在这一空挡中,我们察觉不到时间的经过,这小段断裂前后的意识也能够无缝衔合,致使我们觉得无事发生。这种失分神状况每天持续频繁地发生,也是所谓“失神癫”(picnolepsie):
分神时常突如其来地在早餐发生,而被松开、翻覆于桌上的杯子则是一个常见的结果。分神延续了几秒,其开始与结束都是突然的。诸感官保持警醒,然而却对外在感受封闭。回复也如开始般即刻发生,停住的言谈与姿势从它们被中断处重新拾起,意识之时间自动重新黏合,且组成连续、表面上无断裂之时间。分神之时能为数极多,每天数百回,且常完全不令周遭知觉得经过,因之以“失神癫”一词称之(来自希腊文picnos,频繁的)。然而,对失神癫患者来说却什么也未发生,分神的空档并不曾存在;每次发作都仅有一小段连他都感受不到的时间逃逸无踪。(维利里奥79—80)
维利里奥认为分神状况是一种集体现象,我们每个人都对此有所体验,尤其是在童年时期。作为一种无关紧要的小疾患,分神造成了一种我对所目睹的事件的“迟到”,因为尽管事件就在我的眼前发生,我却对它毫无察觉,形成了一种身体“在场”,但是意识却“不在”的怪异场面。就拿那个早餐时被打翻的杯子来说,我意识的前后衔接的是桌上完整的杯子和地上破碎的杯子,而我对这之间的状况是分神的,我(身体)明明在事件发生时在场,但我(意识)却好像不在一样,对被子掉落这一事件的发生一无所知。
现代科技重建了这种分神技能,最初表现在电影拍摄的“停格技巧”上。在电影拍摄更换胶卷时,发生了一段空隙,电影的上一幅画格和下一幅画格之间,“公共汽车突然变成了灵车,而男人变成女人”(维利里奥89),但电影黏合了这段空隙,我们在看观看时对这一时间上的断裂毫无察觉。电影成了我们的视觉义肢,延展了我们感官和身体的能力,也构筑了一种新的感受世界的方式。世界成了被剪贴排序的世界,我们也不再能够“直接”抵达世界,而是必须透过电影、屏幕,才能对这一世界进行观看。
如果说电影的分神是对时间断裂的无知觉,那么在电子游戏的体验里,我们将同时在时间和空间上全面进入分神状态。在类似《魔兽世界》(WorldofWarcraft)或《第二人生》这样的MMOG(“Massive Multiplayer Online Game”,大型多人在线游戏)中,高速传输的数据征服了空间距离,取消了时间的延续,毫无间隙、毫无衰退地粘住全速而来的数据、事件、人物,生产出一个虚拟世界,一切都是此时此地:和你同时玩游戏的玩家,是在场的,却又是不在的;玩家们共处的那个游戏世界,是在场的,却也是不在的。技术义肢帮助我们知觉并适应了这种“无所不在的不在”(absence ubiquitaire)(维利里奥103),使我们得以平滑地生活在数字世界中。
饶有意味的是,当我们在等待游戏数据登陆或资料加载时,我们其实是感知得到这一段“放空”的分神的,在这几秒至几分钟的意识停格中,我们被技术阻滞在分神地带,但我们的身体却保持不动,手指不会移开屏幕,眼睛也不会抬起来,我们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想,即使我们可以动作、可以思考。而一旦加载完成,我们又即刻能够滑入游戏里,仿佛刚才的阻滞全然不在。这样的小卡顿成了我们身体的节奏,也即,技术的节奏成了身体的节奏。
可以看到,分神是断裂的、阻滞的,同时也是平滑的、连贯的。强调分神是一种断裂,因为它首先是一种时间和空间上的“不在”,沿着这种否定性的、断裂性的思路,我们能够发现这里其实存在着先天的敞口,我们对“不在”的无所知,是因为它奠基于目前的感知系统,因为这一套感知系统限制了我们的感知语境。而一旦感知系统某个元素发生了变化,导致整个感知系统也随之调整,那么这个曾经被掩盖起来的断裂就会发挥巨大的威力,将我们引入某种晦暗的深处或全然不同的境地。
将这种中断性的“不在”得以连贯起来的分神技术,把世界从海德格尔意义上的那种“世界图像时代”转变为弗卢塞尔意义上的“技术图像的宇宙”。前者作为技术主体依凭技术意志将世界作为图像进行计算和征服,后者则从图像(世界)的可能性角度来思考未来的方向,放弃了某种抽象概念或稳固实体的“我”,“在创造性游戏中,游戏的人通过他者而发现自己。在这场对话、这场相互指认对方的创造性游戏中,众人都处在平等共生、相互熟识的环境之中。这就是游戏、创造与远程通信的意义”(弗卢塞尔74)。这将颠覆我们对既往形而上学的那种表层/深层或能指/所指的偏好,我们感知到的在场,或许被诟病为一种无深度的表面,但其实它并不需要所谓内面,如果必须要求一种所谓内面的话,那么它的内面也并不在别处,因为这个表面也正是它的内面。
只有在封闭的身体那里,分神才构成先天敞口,发生阻滞,而在开放身体这里,却能发现一种连贯性,这不仅是观念上的不同,还涉及实质的不同:技术对身体的融入。现代技术的分神状态,其实是技术义肢重塑了我们的身体感知,剪贴缝合了虚拟和现实。我们的身体和世界,从观念到实践上都从封闭走向了开放。等待的身体和悬搁的意识,是一组技术世界中身体现象的一体两面,在第一个层次上,它是跨身体的(trans-body),因为它能够在融合世界中同时作用,在第二个层次上,它是“准备着”向世界扑去的可能状态。由此我们发现了一种数字身体现象,和一种新的技术知觉与人的身体知觉相适配的技术身体现象学。
经典现象学研究的是我们对世界的体验,那么所谓后现象学则是研究我们的体验是如何被技术所中介的(Wellner209),也被称为中介理论(Mediation Theory),在“我-技术-世界”(I-technology-world)的框架中理解世界,放弃笛卡尔以来的主体概念,将身体概念恢复到生活着的具身实践中,构建了一个非主体性的具身现象学。
海勒(N. Katherine Hayles)对此持相同的理解,她认为,具身从未与身体相吻合。身体“是一种理想化的形式,暗示某种柏拉图式的现实”,与身体相反,具身是“处于语境中的,被卷入特定的地点、时间、生理和文化之中,这些地点、时间、生理和文化因素共同构成了规定性,……是他者或者别处,是处于无限的变化、特性和异常之中的过度与不足”(海勒264)。电子游戏的环境其实就是我们的技术具身训练,我们穿戴VR设备、适应键盘和手势操作,身体被数字技术重组,我们借由技术才能知觉(比如通过眼镜和手持设备,我们才能捕捉到宝可梦精灵),并在这样的具身体验中感知世界,构成“(我-技术)→世界”的模式。
芬伯格(Andrew Feenberg)则提出了“我→(技术-世界)”的模式,他认为技术与世界并不是一组组合的两个部分,而是作为一个共同实体(co-entity)(Feenberg194),是不能够被拆分的。这尤其体现在我们在游戏世界中的状态,因为这个“世界”本身就是由技术搭建的。如果说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的身体现象学是为了恢复我们对“生活世界”的感知,那么,芬伯格扫清的是我们通向“技术-世界”的道路。
在前两种模式中,似乎技术都作为一种中立的中间物,或卷入具身的过程,或参与世界的形塑。维贝克(Peter-Paul Verbeek)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因为技术其实是具有意向性的,他用“赛博格意向性”(cyborg intentionality)来说明技术物在被编程时就已经有了预设,而人与技术物的实际互动和分配中,又构成了“复合意向性”(composite intentionality)(Verbeek388)。正如不同的电子游戏所设定的玩法和体验都有其边界和指向,我们不可能要求在《愤怒的小鸟》(AngryBirds)中体验《动物森友会》(AnimalCrossing)的自由度,反之,我们也不会期待在《动物森友会》中体验射程、力度与节奏;需要注意的是,我在玩不同的游戏时,可以和游戏本身所铺设的玩法轨道完全不同,这就形成了我和技术物意向的涌现。因此,“我-技术-世界”的框架被重新调整为“我→(技术→世界)”。
经由对分神的身体现象的思考,我们得以进入被剪贴缝合的分神的技术世界。电子游戏的世界无疑是最基础也最典型的范例。如果说身体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对身体的超越,我们对身体的理解也更新为一种元身体的跨越性、具身化的状态,那么相对应地,让这个元身体得以生成的世界,以及关于这个世界的观念,将会如何更新,走向何处,是需要我们继续思考的。
结 语
伊丽莎白·格罗茨(Elizabeth Grosz)在《易变的身体》(VolatileBodies:TowardaCorporealFeminism)里,描述了一个“莫比乌斯环”态的身体,在这个形态中,身体的外部变成内部变成外部,瓦解了身体稳固的边界,展开一个开放的姿态。在电子游戏中,我们观看到、体验到数字身体的易变性,也折射出了从封闭走向融合的数字世界。重新解读沉浸的意义,将理想的、甚至是幻想的数字身体状态,转变为对数字身体“分神”日常态的思考,从这种人-技术-世界相融合的最初雏形里,探索未来元宇宙的可能性,这也是理论思考的应有之义。
元宇宙是对我们关于虚拟与现实的固有观念的颠覆。《雪崩》的主人公在现实里是个毫不起眼的披萨速递员,但在虚拟世界里,他却拥有无上的声名、至高的力量。类似地,在《黑客帝国》(TheMatrix)里那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经典抉择场景中,蓝色药丸意味着进入虚拟世界,红色药丸则能够回到现实世界,你会作何选择?在这类科幻场面中,梦幻幸福的虚拟和平庸晦暗的现实总是形成对照,仿佛选择红色药丸就是更清醒高贵地面对,而选择蓝色药丸便是选择自欺欺人地逃避。关于元宇宙的想象,总是环绕着矛盾和犹豫的爱与怕,也许问题的基础一开始便被错误假设了,因为虚拟和现实的关系并不是非此即彼的,更不是谎言与真实的象征,元宇宙完全可以是一种“双开”状态,同时保持现实和虚拟的在线和切换,并对不同信息和内容进行选择、处理。
新冠疫情让远程办公和远程教育成了常态,这种情况一方面加速了元宇宙技术的推进,一方面也培养了我们线上生活的习惯。元宇宙的落成可能还目不可及,但它正搭建在我们每天的工作、学习、社交、娱乐、消费等场景中。在前疫情时代的2008年5月,由记者约翰·博安农(John Bohannon)发起的一场主题为“现实与虚拟的融合”(Convergence of the Real and the Virtual)的学术会议在《魔兽世界》中举行,与会的百余名专家学者,以游戏化身的形式在“大地之环”(The Earthen Ring)中行动、讨论,每个与会者都会收到一个“公会背包”(guild starter packs),包含着虚拟世界中可通行的徽章、望远镜,甚至包括购买武器和盔甲的黄金。一路上,等级高的与会者会保护等级低的与会者。这与我们对一般学术会议的严肃印象相距甚远,那些在会议厅、走廊茶歇交流的内容,发生在了虚拟丛林中。随着技术的发展,数百万玩家进入了一种持续在线的状态,他们在游戏世界中生活、战斗、交易、死亡,为游戏投入金钱,也从游戏中赚取金钱。远距离的情侣们,相约在《动物森友会》的海岛上看夕阳;地北天南的网友,在Clubhouse(即时性的音频社交软件,网称“聊斋”)主题房进行辩论或者是即兴的提问和对话。我们在不同的游戏世界和在线软件中习得的是未来元宇宙的融合世界里所需要的技能,而我们所形成的新常态也反过来催生了我们对更大体量的元宇宙的渴望。
自扎克伯格宣布Facebook(脸谱网)更名Meta(元)以来,除开那些美好的设想,关于元宇宙的担忧与批判也随之而来。如果真的有一个元宇宙,谁来为它立法呢?是资本、政权,还是自动技术本身对我们的数据化控制?当被问到什么是元宇宙时,扎克伯格的答案是,它是一组虚拟空间,允许不在同一物理空间的人们一同创造和探索。用户创造,这正是元宇宙能够让我们在控制与反制之间实现自由的方向。元宇宙的巨量意味着它不可能由单一力量、单一技术所主导和把控,这种去中心化的世界也激励着个体创造的发生。在《塞尔达:荒野之息》(TheLegendofZelda:Breathofthewild)中,玩家在掌握游戏世界的基本元素和法则后,能够生火、配比出不同的食物、发现各种“隐藏款”过河方式(让河面结冰、砍树为桥、乘风起飞等);在《动物森友会》中,玩家可以自己设计服装、家具,甚至会成为全网流行的爆款;在《我的世界》(Minecraft)这款沙盒游戏里,玩家可以自制地图,有的地图下载量高达数百万。在这个意义上,元宇宙建立了真正的“世界性”,它不单指一种存在感,更意味着人与人、人与技术、人与非人之间的亲密交互,我们关心世界,同时创造世界。
注释[Notes]
① 具体讨论可参考韦施伊:《电玩游戏的后人类情感——以〈集合啦!动物森友会〉为例》,《文艺争鸣》8(2021):80—87。
② 杨凯麟在《消失的美学》中译本中将“absence”译为“失神”,本文译为“分神”,区别前译侧重于一种病症性,“分神”可以更直接地描述出人在虚实融合的新现实中所展现出的状态。
③ 罗布乐思(Roblox)的CEO大卫·巴斯祖奇(David Baszucki)提出“元宇宙”的八个基本特征:身份(Identity)、朋友(Friends)、沉浸感(Immersive)、低延迟(Low Friction)、多元化(Variety)、随地(Anywhere)、经济系统(Economy)和文明(Civility)。
④ 心流,有时也被直接译为“沉浸”,比如沉浸理论(Flow Theory)。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Biocca, Frank. “Virtual Reality Technology: A Tutorial.”JournalofCommunication42.4(1992):23-72.
乔纳森·克拉里:《知觉的悬置:注意力、景观与现代文化》,沈语冰、贺玉高译。南京: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7年。
[Crary, Jonathan.SuspensionsofPerception:Attention,Spectacle,andModernCulture. Trans. Shen Yubing and He Yugao. Nanjing: Jiangsu Phoenix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2017.]
Daassi, Mohamed, and Sana Debbabi. “Intention to Reuse AR-Based Apps: The Combined Role of the Sense of Immersion, Product Presence and Perceived Realism.”Information&Management58.4(2021):103453.
Dionisio, John, William G. Burns, and Richard Gilbert. “3D Virtual Worlds and the Metaverse: 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Possibilities.”ACMComputingSurveys45.3(2013):1-38.
Feenberg, Andrew. “Active and Passive Bodies: Don Ihde’s Phenomenology of the Body.”Postphenomenology:ACriticalCompaniontoIhde. Ed. Evan Selinger.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6.189-196.
威廉·弗卢塞尔:《技术图像的宇宙》,李一君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年。
[Flusser, Vilém.IntotheUniverseofTechnicalImage. Trans. Li Yijun.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2021.]
N.凯瑟琳·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刘宇清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
[Hayles, N. Katherine.HowWeBecamePosthuman:VirtualBodiesinCybernetics,Literature,andInformatics. Trans. Liu Yuqing.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7.]
约翰·赫伊津哈:《游戏的人:文化中游戏成分的研究》,何道宽译。广州:花城出版社,2007年。
[Huizinga, Johan.HomoLudens:AStudyofthePlay-ElementinCulture.Trans. He Daokuan. Guangzhou: Flower City Publishing House, 2007.]
Juul, Jesper.Half-Real:VideoGamesBetweenRealRulesandFictionalWorlds.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2005.
Keogh, Brendan.APlayofBodies:HowWePerceiveVideogames.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2018.
Kirkpatrick, Graeme. “Controller, Hand, Screen: Aesthetic Form in the Computer Game.”GamesandCulture4.2(2009):127-143.
Lombard, Matthew. “Resources for the Study of Presence: Presence Explication.” 29 Apr.2000.7 Oct.2021.
Murray, Janet Horowitz.HamletontheHolodeck:TheFutureofNarrativeinCyberspace. New York: Free Press, 1997.
Salen, Katie, and Eric Zimmerman.RulesofPlay:GameDesignFundamentals.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2003.
Steuer, Jonathan S. “Defining Virtual Reality: Dimensions Determining Telepresence.”JournalofCommunication42.4(1992):72-92.
Verbeek, Peter-Paul. “Cyborg Intentionality: Rethinking the Phenomenology of Human-Technology Relations.”PhenomenologyandtheCognitiveSciences7.3(2008):387-395.
保罗·维利里奥:《消失的美学》,杨凯麟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
[Virilio, Paul.TheAestheticsofDisappearance. Trans. Yang Kailin. Zhengzhou: Henan University Press, 2018.]
Wellner, Galit. “From Cellphones to Machine Learning: A Shift in the Role of the User in Algorithmic Writing.”TowardsaPhilosophyofDigitalMedia. Eds. Alberto Romele and Enrico Terron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8.205-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