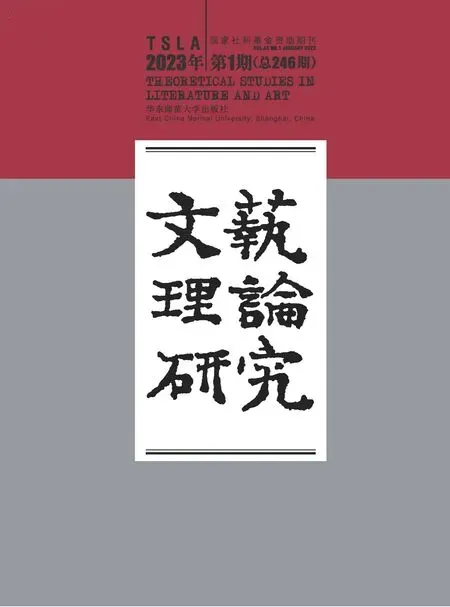裕情
——王夫之《诗广传》中的修养处世论
高 阳
情是王夫之诗学思想中的重要范畴,具有诗歌本质的意味,所谓“情之所至,诗无不至;诗之所至,情以之至”(《古诗评选》654),《诗广传》的重点亦在于对情的讨论。然而,与《姜斋诗话》①及三本诗评选②不同,从诗美鉴赏、诗艺剖析的角度论情不再是王夫之的着力点,即兴发挥对《诗经》篇目的义理思考、广衍诗歌而申发的情之哲学义理亦具有重要价值。王夫之表示,情作为“性之端也。循情而可以定性也”(《诗广传》353),循情以定性既表明情是人性结构的关键一环,也意味着情系乎人的修养处世之道。因此,《诗广传》的内容不仅在于诗歌背后的美刺意蕴、诗学理论,还包括诗歌所展现的内圣修为之道。这样,王夫之诠释诗歌以探讨情对于修养处世的意义成为《诗广传》的重点之一。本文从王夫之广衍《诗经》义理出发,探讨情之于修养处世的作用,进而揭示其所标榜的“裕情”修养处世论及其意义。
一、 情的对治与修养处世
情成为王夫之阐发修养处世的关键,最直接原因在于其自身的出入行藏。作为亡国遗老,王夫之自青年时代起就身历起伏,如何在天崩地解、宗社沉沦中安顿行藏,他在晚年重订《诗广传》时体悟渐深,在诠释《诗经》的过程中探索到了自我修为、泰然处世的修养境界,即“裕”。王夫之表示,“裕者,忧乐之度也”(《诗广传》338),忧乐就是人之喜怒等七情,“裕”意味着把握、调控情的起伏,以达到泰然从容、忧喜合宜的理想状态。不仅如此,安顿情而裕于情也是修养处世之德的表现,“夫能裕其德者,约如泰,穷如通,险如夷,亦岂因履变而加厉哉”(320)。能裕于情者,其境遇遭际不会因变化无常而更加棘手,即使身历窘境也能泰然,遭遇困顿也能通变,险阻重重亦能等闲视之。这种于乱世实现自我修养的贞定、从容处世的修养工夫本质上就是善用其情,即通过情的对治以安顿情志,从容面对家国、人生失意,故而修养处世成为一个如何安置情的问题。
当然,修养处世成为情之安置的根本原因在于情之于天人往来的独特地位,或者说是情自身的独立性与实践性。观王夫之思想,情是其探寻诗意审美的必经之路,即诗学思想中的情更多是作为审美之情而存在,但这种情况在诠释《诗经》的过程中发生了改变。王夫之在《诗广传》中辟出一条以审美活动寻求修养处世智慧的新进路,所谓“《诗》之教,导人于清贞而蠲其顽鄙”(《诗广传》326),《诗经》可以指导人们克服愚钝鄙陋以清正坚贞。进一步讲,王夫之希冀通过审美之情探寻道德修养的智慧。他一方面强调人继善成性,③性善关乎人之修养处世的底色;另一方面又于《诗广传》中提出“循情定性”,性善需通过情以贞定,故而情在天人接续往来中的关键地位决定了情之于修养工夫的意义。
王夫之认为情产生于人心与天地之产互动相应之几:“情者,阴阳之几也;物者,天地之产也。阴阳之几动于心,天地之产应于外。故外有其物,内可有其情矣;内有其情,外必有其物矣。”(《诗广传》323)相对于外物,心处于内,情的产生必有外物与之相应,“内有其情,外必有其物”;但如果仅有外物,则有情的生成与不生成两种可能,“外有其物,内可有其情”。换言之,情物不离,情是内外交成、互动相取④的结果。王夫之又指出:“盖吾心之动几,与物相取,物欲之足相引者,与吾之动几交,而情以生。然则情者,不纯在外,不纯在内,或往或来,一来一往,吾之动几与天地之动几相合而成者也。”(《读四书大全说》1069)“吾心”即人心,人心属内,但情的生发却“不纯在内”。虽有外在相引,情的产生也并非“纯在外”,而是成于内外往来相取,此即王夫之所谓“有识之心而推诸物者焉,有不谋之物相值而生其心者焉。知斯二者,可与言情矣”(《诗广传》383)。
情成于内外往来、心物互动相取,不同生命个体对心物互动的体验相异,这意味着人之处世交往的关键在于情。王夫之指出:“絜天下之物,与吾情相当者不乏矣[……]均是物也,均是情也,君子得甘焉,细人得苦焉;君子得涉焉,细人得濡焉。无他,择与不择而已矣。”(《诗广传》323—324)衡量天下之物,与人之情相值相取者众多,故而情物不离。然而,在同样的情物不离状态下,不同的人情之体验相异,就好比君子得甘味而浅薄之人得苦味。王夫之表示,造成体验不同的关键就在于情“择与不择”的分寸,情或“择”以贞定,或“不择”而漫荡。这种分寸的把握表明情具有实践性的特点,而这种实践性的重要意义在于情之定性、尽性的修养之用,即王夫之所谓的“循情而可以定性也”(353)。
王夫之强调循情以定性,原因在于性情的和合关系。性与情是两种不同的范畴,“性,道心也;情,人心也。恻隐、羞恶、辞让、是非,道心也;喜、怒、哀、乐,人心也”(《读四书大全说》966),“人生而有性,感而在,不感而亦在者也。其感于物而同异得失之不齐,心为之动,而喜怒哀乐之几通焉,则谓之情”(《四书训义》下698)。性不因物之来感与否固存,“性只是一阴一阳之实”(《读四书大全说》 1068)而情具有已发性,“发而始有,未发则无者谓之情,乃心之动几与物相往来者”(966)唯有人心之动几与物相取才能生情。然而,性与情关系密切:
斯二者,互藏其宅而交发其用[……]于恻隐而有其喜,于恻隐而有其怒,于恻隐而有其哀,于恻隐而有其乐,羞恶、恭敬、是非之交有四情也。于喜而有其恻隐,于喜而有其羞恶,于喜而有其恭敬,于喜而有其是非,怒、哀、乐之交有四端也。故曰互藏其宅。(王夫之,《尚书引义》262)
王夫之认为性情既分际甚严又彼此相需,于四端(性)之发而见喜怒哀乐(情),于喜怒哀乐而见四端,性情相需而交发其用,“互藏其宅”就是性情和合的状态。鉴于性情和合,情之所以为善就在于性能够规范与约束情,“以性固行于情之中也。情以性为干,则亦无不善”(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967)。性行于情中且能导情为善,即情以性为导向,故而促使情之所发能够尽性,此即王夫之所谓情之为善“专就尽性者言之”(1072)。
在此基础上,王夫之一方面强调性对情的规范与引导,提出“尽其性,行乎情而贞,以性正情也”(《诗广传》429),诗歌应当抒发贞正之情,唯有性的约束、引导,情方称得上是性之情,而性之情就是为善之情;另一方面,王夫之也强调情可以为性之用,“情如风然,寒便带得寒气来,暄便带得暄气来,和便带得和气来。恻隐等心行于情中者,如和气之在风中,可云和风”(《读四书大全说》1072),情如同风,性之四端于情而显发犹如和风承载和气。此又如王夫之所言,“性隐而无从以贞,必绥其情。情之已荡,未有能定其性者也。情者安危之枢,情安之而性乃不迁”(《尚书引义》366),情关乎善性德行之安危,成为滋养道德的沃土。因此,只有情和谐、宁静而安,人的善性德行才能稳固不迁。
诚然,定性所循之情必然落脚于人,即通过人之情的践履工夫以贞定人性。人之情的实践工夫集中体现在人的修养处世之为,“以是知忧乐之固无蔽而可为性用,故曰:情者,性之情也”(《诗广传》384),忧乐即人修养处世过程中的情之发用,而善于对治处世之忧乐才能从容处世,进而实现尽性之用。那么,人如何修为才能从容处世,或者说人应当循何种境界之情来贞定其性?对此,王夫之提出以裕于忧乐、旁通无蔽来超越生命个体之忧乐,“忧之切,乐之大,而不废天下不屑尔之忧乐,于以见公裕于忧乐而旁通无蔽也”(384),以“裕于死生之际”(302)的裕情境界来应对人生失意起伏,完善人格修行。王夫之表示,裕情境界的实现首先在于人能够做到“白情”,即充分表达、告白自我之情而不自匿其情,进而以“同情”之心而“取天下之情”,最终导之以“广心”来实现“人心和平”的余裕之境。这样,王夫之通过情的对治探索出修养处世的工夫。
二、 白情:修养处世工夫的起始
王夫之在《诗广传》中提出一种“达情”之论,“达情”与其“诗以道情”有相通之处,二者都强调诗歌的抒情性。然而,王夫之广衍《诗经》并不囿于阐发诗论,其“达情”思想也蕴蓄着对人与人之间交流处世的思考。
王夫之表示:
君子与君子言,情无嫌于相示也;君子与小人言,非情而无以感之也。小人与君子言,不能自匿其情者也。将欲与之言,因其情而尽之,不得其情,不可尽也[……]言之而欲其听,不以其情,嫌于不相知而置之也[……]故曰“《诗》达情”。(《诗广传》353)
诗歌作为诗人与读者之间交流的媒介,“诗达情”的意义不仅在于传递诗人情感,也在于读者透过诗情与诗人进行交流。故而“达情”指传递、表达其情,旨在强调情不仅不可或缺,而且也必须有所告白与表达。在这里,王夫之通过君子、小人之交等问题说明人在修养处世中自达其情的重要意义。君子与君子之交无嫌、相通全因彼此间情意的流露与表达,而君子与小人的交往不仅需要君子以情感化之,而且需要小人对君子之情的表露有所接纳,不能自匿其情。具体而言,倘若人想要与他人互动,唯有表达其真情实意才能实现交流的目的,反之则无法充分表达自我。同时,面对他人的言说告白,如果不以设身处地之情来体会,将无法体谅他人而陷于“不相知”。
除了主张“达情”,《诗广传》中亦有“白情”之论。与“达情”相比,“白情”更加直接地体现了王夫之为人处世应显露其情的主张。所谓“文者,白也,圣人之以自白而白天下也。匿天下之情,则将劝天下以匿情矣”(《诗广传》299),“白”即表达,“白情”就是将自我内心的真情实感表达出来。在王夫之看来,诗文之用在于畅达其情,圣人通过诗文而使其善而正之情通达于天下,故而天下可知圣人之情。相反,如果废诗禁文,将导致天下人皆隐匿其情,而这也再度肯定了诗歌的抒情性。
王夫之主张“白情”,反对“匿情”。“匿情”指严格控制、压抑情的表露,甚至使情不得显现。虽然一味地表达、宣泄情并非合理样态,但严格把控情以至于让情陷入秘而不发的状态,则会对人之心性产生严重的不良后果,即王夫之所谓的“迁心移性”。他广衍《诗经·关雎》时表示:
忠有实,情有止,文有函,然而非其匿之谓也。“悠哉悠哉,辗转反侧”,不匿其哀也。“琴瑟有之”,“钟鼓乐之”,不匿其乐也。非其情之不止,而文之不函也。匿其哀,哀隐而结;匿其乐,乐幽而耽。耽乐结哀,势不能久,而必于旁流。旁流之哀,懰栗惨淡以终乎怨;怨之不恤,以旁流于乐,迁心移性而不自知。(《诗广传》299)
在这里,王夫之借评《关雎》为例,褒扬人之修为处世能秉真挚之情,既不匿不得之哀(“辗转反侧”),也不匿求得之乐(“钟鼓乐之”)。相反,匿其哀乐则将陷哀乐于隐幽,甚至旁流而“懰栗惨淡以终乎怨”。进一步讲,自白其情而不匿哀乐,这种坦然的表白不仅是一种无邪的情思,更是一种情感疏导的良方。换言之,如若情感无法得以表达、获得疏导,反而处处压抑以致未能有所抒发,随着时间的推移将导致人本性的改变,人也将难以从容、余裕处世。
值得注意的是王夫之所谓的“忠有实,情有止,文有函”,在他看来,人之忠既能强烈激进又能和缓踏实,情既能有所发又能有所敛,情之文既能有所显豁又能有所隐微,以上三者都不属于“匿”的范畴。“情有止”属于“白情”而非“匿情”的观点,与其诗学所主张的“忍”之审美建构一脉相通。从王夫之诗学的角度讲,“情有止”仍然是一种诗歌抒情的方式,是诗歌抒情有所敛忍而非隐匿的表现,“‘忍’体现了王夫之对‘情有止’抒情方式的坚守,‘情有止’并非情有匿,而是对不加节制抒情方式的反拨[……]虽然情感涌动如‘射者引弓极满’,欲倾泻而下,但秉持‘情有止’可以让情感宛转绵长”(高阳181)。正如王夫之所褒扬的《关雎》这种不匿其情的作品,虽然诗歌没有直接书写哀乐,但借“辗转反侧”“钟鼓乐之”的侧面烘托将哀乐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因此,“忠有实,情有止,文有函”本质上仍属于“白”而非“匿”的范畴。
王夫之继而表示,“周道因人情而礼行,夺人之情而不得伸,而后道之丧也无余”(《诗广传》377),人之情有所白也是礼制推行的前提,强行改变人的情志、压抑人之情的表达将导致国之衰、道之弛,即“周衰道弛,人无白情”(299)。换言之,“白情”而不“匿情”不仅对个体自我有良好的平衡身心之功,对社会亦有治国之效,缺乏情之白将导致严重的后果。王夫之指出:
上不知下,下怨其上;下不知上,上怒其下。怒以报怨,怨以益怒,始于不相知,而上下之交绝矣。夫诗以言情也,胥天下之情于怨怒之中,而流不可反矣,奚其情哉!且唯其相知也,是以虽怨怒而当其情实。如其不相知也,则怨不知所怨,怒不知所怒,无已而被之以恶名。(《诗广传》341—342)
倘若整个社会处于“匿情”的状态,则易滋生君王与白姓彼此间的怨怒,甚至引发社会的动荡。王夫之继而以周之兴亡来说明白情的社会意义,“周以情王,以情亡,情之不可恃久矣。是以君子莫慎乎治情”(342)。因此,“诗以言情”是诗的正常状态,而人之“白情”处世亦是社会的常态,君子更应审慎对治情。
除反对“匿情”之外,王夫之也对佛教所主张的“窒情”提出了批判。“窒情”意味着阻滞情的表露与抒发以不被情所牵绊,与“匿情”有相似之处。实际上,不执着于情的“窒情”观念否定了情的实践性。王夫之认为,“见情者,无匿情者也。是故情者,性之端也。循情而可以定性也。释氏窒情而天下贼恩,狺狺以果报怖天下,天下怖而不知善之乐,徒贼也,而奚救乎”(《诗广传》353),人之在世处世应当白其情而使情有所见,然而,佛教主张阻拒情,甚至喋喋不休地向世人宣扬因果业报并以此诈怖愚民,使得人莫名惧怕而不明真正的为善之乐。在王夫之看来,佛教这种主张泯灭了循情定性的价值,最终将戕害天下。
王夫之肯定“达情”“白情”而反对“匿情”“窒情”的主张,反映了情之存在与情之发用的必然性。不同于前人“去情”,⑤王夫之不仅肯定情之存在的必然,而且主张“白情”以发挥情之用。由于情之存在是必然的,故而不能压抑、隐匿情。唯有充分表达情,发挥情的实践意义,让情有所白、有所达,才能避免情被束缚以致无法实现情的余裕、发挥循情定性之用。然而,人之修养处世的余裕泰然并不仅仅在于表白其情,倘若人仅表达自我之情而忽视他人之情、不能与他人有所共鸣,其亦无法应对变幻的人生遭际、实现从容处世。因此,王夫之在“白情”的基础上主张以“同情”之心关照他人与社会。
三、 同情:修养处世工夫的展开
王夫之所谓的“同情”是一种设身处地的修养工夫,即以自我之情关照他者以体会他者之情,进而实现通天下之情的余裕境界。王夫之广衍《诗经·东山》时指出:
圣人者,耳目启而性情贞,情挚而不滞,己与物交存而不忘,一无蔽焉,《东山》之所以通人之情也。周公之徂东山也,其忧也切矣;自东而归,其乐也大矣。忧之切则专以忧,乐之大则湛於乐。夫苟忧之专,乐之湛,所忧之外,举不见忧,而矧其见乐?所乐之外,举不见乐,而矧其见忧?独宿之悲,结褵之喜,夫何足以当公之忧乐,而为尔不忘邪?忧之切,乐之大,而不废天下不屑尔之忧乐,于以见公裕于忧乐而旁通无蔽也。(《诗广传》384)
《东山》是反映周公东征归来的作品,诗歌表现了战士征战胜利、返归家乡的复杂心情。《诗序》言,“《东山》[……]君子之于人,序其情而闵其劳”(李学勤518),王夫之顺《诗序》衍《东山》,在他看来,圣人耳目清明且情之真挚,其能与物交而不忘物,能做到感同身受而通他人之情。圣人即如周公,他能以清明耳目观照所闻所见之人与物,故而能真切感受东征兵卒的悲喜之情。周公之徂东山及胜利而归乃大忧大乐之事,然而周公不因徂东山之忧而忘却兵卒“独宿之悲”,亦不因东征凯旋而忽视兵卒“结褵之喜”。换言之,周公不以己之忧乐而废天下之忧乐,能以一己之情通他人之情。这样,个人之情与天下人之情互通相融,其所达到的状态即旁通无蔽之裕。
圣人“通人之情”而裕于忧乐为王夫之所赞赏,然而,并非所有人都能够成圣。鉴于此,王夫之认为作为儒家人格修养目标的君子亦能以“同情”之心而裕于忧乐,即君子因通天下之情而洞悉万物:“君子之心,有与天地同情者,有与禽鱼草木同情者,有与女子小人同情者,有与道同情者,唯君子悉知之。悉知之则辨用之,辨用之尤必裁成之,是以取天下之情而宅天下之正。”(《诗广传》310)君子能够以“同情”观照天地、禽鱼草木、女子小人乃至道,表明君子能够在洞悉情的基础上,以缜密思辨的工夫分辨其情,善用其情,同时合理取舍调节其情,从而实现通天下之情而使之向正。王夫之继而指出:“与天地同情者,化行于不自已,用其不自已而裁之以忧[……]与禽鱼草木同情者,天下之莫不贵者,生也,贵其生尤不贱其死,是以贞其死而重用万物之死也。”(310)君子能够将天地流行不息而化行于己,而面对“化行于不自已”者能予以和宜的取舍节制以产生相应的情感,故而君子能“与天地同情”;君子又能以“同情”之心观照禽鱼草木,以人之情感通草木禽鱼的死生,从而珍其生而重其死。君子基于同情达到了感通万物的境界。
值得注意的是君子之“与女子小人同情”,王夫之将同他者之情的重点落脚于普通人:
与女子小人同情者,均是人矣,情同而取,取斯好,好不即得斯忧;情异而攻,攻斯恶,所恶乍释斯乐;同异接于耳目,忧乐之应,如目击耳受之无须臾留也。用其须臾之不留者以为勇,而裁之以智;用耳目之旋相应者以不拒天下,而裁之以不訢。(《诗广传》310)
人际交往依情而推进,而人之耳目感官是情之产生的前提,故而人以感官体验来判断他者与自我的同与异。君子之所以能“与女子小人同情”,原因在于君子非常了解女子、小人面对同与异的忧乐情感体验。君子的超越在于他不仅能深入体会其情,而且能够以理智裁夺取舍、以严肃的方式节制其情,从而弥补其不足、调节其过度。所以,面对天地大化、草木虫鱼,君子能以“同情”之心而知之、裁之、用之,从而感通大化流行、明察几希之微,“悉知其情而皆有以裁用之,大以体天地之化,微以备禽鱼草木之几”(310)。需要注意的是,君子同天地、禽鱼草木及女子小人之情并不意味着君子无有自我之情,相反,这表明君子能通天下之道,即君子因通天下之道而能以一己之情通他者之情,故而王夫之表示,“君子匪无情,而与道同情者,此之谓也”(310)。
与通天下之情相对的是囿于一己忧乐的狭隘之情,这种情因己之困顿而忧、己之所得而乐,即“私情”。王夫之评《诗经·北山》指出:“为《北山》之诗者,其音复以哀,其节促以乱,其词诬,其情私矣。故音哀者节必乱,节乱者诬上行私而不可止。是以君子甚恶夫音之遽哀而不为之节也。”(《诗广传》422)《诗序》言“《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己劳于从事,而不得养其父母焉”(李学勤796),可知《北山》以周朝士人的口吻,表达了对上层统治者分配工作劳逸不均的不满。在王夫之看来,一味表达抱怨与不满只会滋生“音哀、节乱、词诬”等现象,而造成诗歌流弊的原因就在于作者拘泥于一己得失,只知己之不满,不通他人之情。
对比王夫之评《诗经·东山》,周公自东征归来“忧之切,乐之大”,但他“不废天下不屑尔之忧乐”,足见周公“裕于忧乐而旁通无蔽”。相较之下,《北山》中士人目之所见唯有自己劳作之辛苦,忽视了他人的处境甚至社会大局。简言之,《北山》的主人公未能以“同情”而以“私情”处世。王夫之对《北山》所表现出的局限于一己之私的“私情”颇多指斥:
为《北山》之诗者:知己之劳,而不恤人之情;知人之安而妒之,而不顾事之可;诬上行私而不可止,西周之亡不可挽矣。故节其哀者戒其复,饬其乱者惩其促,治其诬者穷其连累之词,革其私者禁其迫切之响。王者以之化民,君子以之自淑,保天下于和平,此物此志焉耳。(《诗广传》422)
既然作为周之臣民,理应承担相应责任,而不可拘一己之私,倘若人人怀有自私、狭隘,国家不可避免地发生动荡。面对《北山》这种“私情”泛滥的诗歌,王夫之认为应通过“同情”的工夫来对治,诗歌的书写应收敛一己之哀以摒除反复增长的负面情绪,规整紊乱的诗歌节奏以改变抒情之急促,整治夸张虚假言辞以减少赘语,革除诗中的私情以杜绝迫切之风。诗歌尚且如此,人之修养处世亦应克服“私情”,以同情处世而自淑其身,从而营造天下和平的氛围。
值得注意的是,王夫之对同情民生疾苦、以忧国忧民著称的杜甫提出了质疑:
果有情者,亦称其所触而已矣[……]无大故而激,不相及而忧,私愤而以公理为之辞,可以有待而早自困,耳食鲍焦、申徒狄、屈平之风而呻吟不以其病,凡此者,又恶足以言性情哉!匹夫之婞婞而已矣[……]是故杜甫之忧国,忧之以眉,吾不知其果忧否也。(《诗广传》338)
虽然所白之情由所触而发,有的人却以天下公理之辞表达一己私愤,但王夫之认为这种“无大故而激,不相及而忧”的张狂之态无异于匹夫婞婞的“私情”表露。因此,王夫之对杜诗所展现的忧国之心表示怀疑,认为其诗中所抒之情囿于“私愤”,这不过是为自己谋得官职提携的“私情”。此外,王夫之如此评判杜甫还有一部分原因在于部分杜诗遣词用句不够敛约,致使情之所发未能有所节制而沦为直白的匹夫婞婞。
诚然,王夫之对杜甫的质疑存在偏颇。不可否认,杜诗中有关百姓疾苦的描写、对民生多艰的哀叹无不是有感而发,并非不恤他人的自我“私情”。然而,抛开这种偏颇,对杜诗的质疑反映了王夫之希冀将自我之情融入家国巨变的愿望,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其强烈的家国意识。王夫之历经生活颠沛,以“乞活埋”的心情终其一生,但其将孤臣孽子之情融入家国忧患,希望以“同情”替代一己“私情”,无疑是在天崩地解的巨变中升华了修养处世之道。
四、 广心:修养处世工夫的升华
诚如王夫之所言,裕于情的境界应当是“旁通无蔽”的,即达到一种无有蔽障、广大深远的境界。由前之所述,人以“同情”之心关照他者通常需要“悉知其情而皆有以裁用之”,而“裁用”似乎意味着要有所舍弃,有所舍则有损于“旁通无蔽”。实际上,“裁用”并不是忽视、舍弃情,而是“情已盈而姑戢之以不损其度”(《诗广传》302),即对超过限度的情有所收敛而不舍其必要之度,达到不舍此而通彼的余裕境界。无论是“戢之以不损其度”还是“不舍此而通彼”,二者皆蕴蓄着“广”的意趣。换言之,王夫之为裕情境界着上了广远的底色,“不舍此而通彼”旨在实现“旁通无蔽”之广远。
何以称“广”?王夫之表示:“广之云者,非中枵而旁大之谓也,不舍此而通彼之谓也,方遽而能以暇之谓也,故曰广也。”(《诗广传》302)“广”并不是徒有庞大外表而内中空虚,而是面对意外骤变亦能以暇豫而应,不舍弃已存而又能接纳现成。换言之,“广”并非由自我虚张强撑而成,而是一种通此贯彼、以暇调遽的心态。正如王夫之广衍《诗经·采薇》所言:
往戍,悲也;来归,愉也。往而咏杨柳之依依,来而叹雨雪之霏霏。善用其情者,不敛天物之荣凋,以益己之悲愉而已矣。天物其何定哉!当吾之悲,有迎吾以悲者焉;当吾之愉,有迎吾以愉者焉;浅人以其褊衷而捷于相取也。当吾之悲,有未尝不可愉者焉;当吾之愉,有未尝不可悲者焉;目营于一方者之所不见也。(392)
人生在世,无论面对悲伤还是喜悦,人应当广其心而“善用其情”,而不以外物之荣凋来倍增自我悲愉。可以说,王夫之希冀人摒除内心褊狭,克服囿于一方的狭隘情感。
“褊衷而捷于相取”“目营于一方”是人毗于忧乐的表现,王夫之指出:“惟毗于忧,则不通天下之乐;毗于其所忧,则不通天下之所忧。毗于忧,而所忧者乍释,则必毗于乐;毗于乐,亦将不通天下之忧;毗于其所乐,抑将不通天下之所乐。故曰:‘一叶蔽目,不见泰岱;两豆塞耳,不闻雷霆。’言毗也。”(《诗广传》384)“毗”与“广”相对,意在说明人囿于局部的、暂时的、眼前的物事则无有广远的眼界。王夫之此番言论明确了毗于忧乐之弊,从而肯定了广其心以通天下之忧乐的意义。
毗于忧乐与“私情”相近,“私情”指囿于人忧乐的狭隘之情,与“毗于其所忧”“毗于其所乐”相一致。然而,毗于忧乐不仅在于只关注一己之情,而且在于局限于忧而不通乐、局限于当下之情而未能有所升华。针对“私情”与“毗于忧乐”之弊,王夫之认为人若能正视其情,合宜接纳感遇而来的忧乐而不执着于一时、一己之忧乐,则能够通天下之情,“不毗于忧乐者,可与通天下之忧乐矣。忧乐之不毗,非其忘忧乐也,然而通天下之志而无蔽。以是知忧乐之固无蔽而可为性用,故曰:情者,性之情也”(《诗广传》384)。不毗于忧乐并不是忘却忧乐,而是不执着于忧乐、不为忧乐所蔽,体现了“情已盈而姑戢之以不损其度”(302)的修为处世态度。“戢”有收敛、停止之意,故而不毗于忧乐即收敛过度的忧乐之情。收敛的同时不能损其度,唯此敛而有度方能不忘忧乐、不为忧乐所蔽。
裕情以广除了在于不毗忧乐,王夫之还认为应荡涤惉滞之情。他在评析《诗经·葛覃》时指出:
道生于余心,心生于余力,力生于余情。故于道而求有余,不如其有余情也。古之知道者,涵天下而余于己,乃以乐天下而不匮于道;奚事一束其心力,画于所事之中,敝敝以昕夕哉?画焉则无余情矣,无余者,惉滞之情也。惉滞之情,生夫愁苦;愁苦之情,生夫攰倦;攰倦者,不自理者也,生夫愒佚;乍愒佚而甘之,生夫傲侈。力趋以供傲侈之为,心注之,力营之,弗恤道矣。故安而行焉之谓圣,非必圣也,天下未有不安而能行者也。安于所事之中,则余于所事之外;余于所事之外,则益安于所事之中。见其有余,知其能安。人不必有圣人之才,而有圣人之情。(《诗广传》301)
《葛覃》描写了已嫁女子准备回家探望父母时喜悦而急切的企盼之情,王夫之从中引申出烦乱混沌的惉滞之情,并着重分析了其所产生的弊端。人之所以能体会道在于有余裕之心,而余裕之心源于人的余力,余力的产生又源于余裕之情。换言之,与其于道来追求余裕,不如说余裕源于余情。王夫之表示,得道的古人往往通过内心之有余来体悟道之无穷,他们乐天知道而不匮于道。然而,今人却“奚事一束其心力”,于一事竭尽心机导致其无法成为有余情、余心、余力的有余者,故而产生惉滞之情。
王夫之将惉滞之情作为余情的对立面提出,“余情无惉滞”,惉滞之情反映了人缺乏余裕、繁乱局促的状态。惉滞之情将导致连锁反应,其易生愁苦,愁苦之情将导致人疲惫困倦,而人的疲倦又将滋生安逸懈怠,习惯于安逸懈怠将导致奢侈傲娇。当人之心力为这种傲侈之情所充斥时,则无法体悟道。鉴于此,王夫之认为,即使普通人没有圣人之才,但其仍可以“安于所事之中,余于所事之外”,以余情来荡涤惉滞之情,从而拥有如同圣人一般的情之体验。可以说,《诗经》是古人畅达其情以求有余而生成的文本,即王夫之所谓“荡涤惉滞而安天下于有余者也”(《诗广传》302),以余情荡涤惉滞是《诗经》所闪耀的处世智慧。
王夫之倡导不毗于忧乐、荡涤惉滞之情,通过心之广以如素而行反映了儒家平和、中正的人格修养诉求:“其悲也,不失物之可愉者焉,虽然,不失悲也;其愉也,不失物之可悲者焉,虽然,不失愉也。导天下以广心,而不奔注于一情之发,是以其思不困,其言不穷,而天下之人心和平矣。”(《诗广传》392)在王夫之看来,倘若人皆以广远的心境与大化流行之几从容相应、与世人观面而不违,则能不失悲愉且亦不陷于悲愉,如此便能不毗于忧乐、无有惉滞之情,从而实现“思不困、言不穷”的和合平顺之境。王夫之继而表示:“广则可以裕于死生之际矣。”(《诗广传》302)“死生”并非仅表示生命的消亡与存在,而是象征着一系列对立范畴,即人生的起伏、聚散、穷通。进一步讲,若人在自白其情、同他者之情的基础上,以“广心”面对人生在世的起伏夭寿、穷通转换,则能消解“奔注于一情之发”的弊端,将情的负面转向正面,复其“性之情”,从而以余裕之态坦然处世。
五、 志士兼仁人:修养处世之裕的内圣境界
通过广衍《诗经》而探寻从容旷达的裕情境界,是一种通过情的审美实践寻求道德修养的进路。从诗歌审美的角度讲,王夫之主张诗人应自白其情而不“匿情”以维护诗歌的抒情性,感通他者而非宣泄“私情”以抒发具有普遍价值、关怀天下之情,广其心而不述褊衷混沌以营造余裕泰然的审美诗境。无疑,王夫之在《诗经》中所体悟到的审美经验表现出伦理化的特点,审美实践与道德修养已然相融相通。进一步讲,“白情”以展现自我而与他人良性互动,“同情”以与他人共鸣而通天下之情,以广心而导天下于和平彰显了情之于修为处世的社会责任感。这样,裕于情的审美经验成为道德修养的体证,既具有指导人修为处世的现实意义,又昭示着道德修养的内圣旨归。
从王夫之个人经历与现实意义的层面讲,裕于情的修养工夫能教人于颠沛挫败的人生遭际而有所余裕。作为亡国遗民,王夫之身历颠沛起伏,如何于天崩地解的动荡中从容处世成为其思虑的重要内容。纵然身经流离,但通过“白情”“同情”与“广心”的渐进式的修养工夫,王夫之于乱世中探寻到了余裕,达到了不毗于忧乐而能裕于情的境界。诚如王夫之所言,其虽为遗民孤臣却主张如其未为孤臣:
夫能裕其德者,约如泰,穷如通,险如夷,亦岂因履变而加厉哉?如其素而已矣。弗可以为孤臣嫠妇而诡于同,亦弗可以为孤臣嫠妇而矜为异。非无异也,异但以孤臣嫠妇之孤行,而勿以其余也[……]当其为嫠,如其未为嫠也,而后可以嫠矣。当其未为嫠,温且惠也。如其未为嫠者以嫠,而何弗终之邪[……]广以其道于天下,不见有矜己厉物之地;守以其恒于后世,斯必无转石卷席之心。(《诗广传》320)
面对遭际骤变,作为一种美好德行的修为,处世之裕让人身历动荡而能不改本色,始终保持温厚和顺,即使身有所束亦能泰然,生活困顿亦能心胸阔达,险阻重重亦能等闲视之,避免一心想要逃避“孤臣嫠妇”身份以回到从前,摆脱刻意标记“孤臣嫠妇”矜异身份的失裕之举。可以说,王夫之“裕情”修养处世论是其遭逢改朝易代、颠沛起伏的践履心得,若无此番修养处世境界及其践履工夫,孤臣之忧不免陷于矜己厉物之狂妄,心态不免发生转石卷席般的动荡。
从更深的层面来看,裕于情所达到的从容泰然也昭示着王夫之内圣之学的境界,即修养处世之裕反映出“志士、仁人”合一的内圣追求:
时当其不得从容,则仁人亦须索性着。若时合从容,志士亦岂必决裂哉?刘越石、颜清臣,皆志士也,到死时却尽暇豫不迫。夫子直于此处看得志士、仁人合一,不当更为分别。近瞿、张二公殉难桂林,别山义形于色,稼轩言动音容不改其素,此又气质之高明、沉潜固别,非二公之一为志士,一为仁人,可分优劣也。(《读四书大全说》829—830)
修养处世之裕所展现出的临危不乱、游刃有余、从容不迫等特质,与王夫之所推崇的“志士兼仁人”内圣观相通。王夫之历经天崩地解的家国巨变,以“乞活埋”之心终其一生,足见其奋不顾身、英勇慷慨的志士之气。然而,在身之所历颠沛、心之所感忧愤的同时,王夫之指出,“孤臣嫠妇,孤行也,而德不可孤[……]夫能裕其德者[……]亦岂因履变而加厉哉?如其素而已矣”(《诗广传》319—320)。虽然孤臣嫠妇胸怀忧愤,但其德不可走向一意孤行的极端,而应以仁人“言动音容不改其素”“如其素”的特质来中和。换言之,“志士、仁人”合一才是身处多舛之世的理想境界,唯有“志士兼仁人”者才能于人世纷乱求得所安,裕于人生忧乐。在王夫之看来,“志士兼仁人”拥有壁立千仞、刚健奋进的品质,能“历乎无穷之险阻而皆不丧其所依,则不为世所颠倒而可与立矣”(《俟解》486),同时又能守静稳重、暇豫不迫,即“忠孝深远人游刃有余,不甚张皇将作惊天动地事”(《唐诗评选》1025)。诸如刘越石、颜清臣等怀有满腔家国情怀的志士,“到死时却尽暇豫不迫”,其蕴蓄着仁人终温且惠的特质;而通情达理的仁人“言动音容不改其素”,闪耀着志士坚定顽强的光辉。可以说,“志士兼仁人”成为裕于人生忧乐、从容泰然处世的人格代言。因此,修养处世之裕彰显了王夫之“志士、仁人”合一的内圣境界。
王夫之身兼儒者与诗论家的双重身份,《诗广传》“裕情”兼具道德境界与审美意蕴,体现了哲学情范畴在诗学领域的美学实践。总之,通过情的诗美实践探索道德修养,处世修为之裕在王夫之诗学中展现为诗歌的审美情调,而内圣境界则成为其诗学伦理化的理据。
注释[Notes]
① 《姜斋诗话》是王夫之的诗论合辑,《诗译》论《诗经》艺术及影响,《夕堂永日绪论》泛论诗艺,《南窗漫记》评点时人诗作。
② 三本诗评选包括《古诗评选》《唐诗评选》与《明诗评选》,王夫之此系列论著选辑汉至明众多诗人的诗歌作品分别加以评点,所评或简或详,皆能不袭陈言而自出机杼。
③ 王夫之指出,“性者,天人授受之总名也”(《读四书大全说》397),继善成性的含义在于,人于天人互动之际绍续自然流行的天道之善,终始如一凝成为自己的本然之性,将天道的道德价值内化为自身的道德本质。按照王夫之“道—善—性”的逻辑理路,可知人性因天道继善而成,性必然为善,且只能是善,即“性者善之藏”(《思问录》428)。
④ “相取”可借鉴戴鸿森《姜斋诗话笺注》的说法:“二者交互为用,水乳相投,就叫做‘神理相取’‘远近之间’。”(王夫之,《姜斋诗话笺注》65)“相取”即两者交互为用、水乳相投,意在强调彼此间相互因依的密切关系。
⑤ 在王夫之以前,去情、灭情的主张并不少见,李翱“去情复性”是典型代表。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高阳:《论王夫之诗学中的“忍”范畴——以其批评实践与审美建构为中心》,《浙江学刊》4(2020):178—186。
[Gao, Yang. “The Category of Tolerance in Wang Fuzhi’s Poetics: Focusing on His Critical Practice and Aesthetic Construction.”ZhejiangAcademicJournal4(2020):178-186.]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Li, Xueqin, ed.ThirteenConfucianClassicswithAnnotationsandCommentaries:ACriticalInterpretationofMao’sEditionofThe Book of Songs.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99.]
王夫之:《尚书引义》,《船山全书》第2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237—449。
[Wang, Fuzhi.IntroductiontoThe Book of Documents.TheCompleteWorksofWangFuzhi.Vol.2. Changsha: Yuelu Press, 2011.237-449.]
——:《诗广传》,《船山全书》第3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299—523。
[- - -.CommentariesonThe Book of Songs.TheCompleteWorksofWangFuzhi.Vol.3. Changsha: Yuelu Press, 2011.299-523.]
——:《读四书大全说》,《船山全书》第6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395—1151。
[- - -.ReadingtheFourBooks.TheCompleteWorksofWangFuzhi.Vol.6. Changsha: Yuelu Press, 2011.395-1151.]
——:《四书训义》下,《船山全书》第8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
[- - -.AnInterpretationoftheFourBooks.Vol.2.TheCompleteWorksofWangFuzhi.Vol.8. Changsha: Yuelu Press, 2011.]
——:《思问录》,《船山全书》第12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401—472。
[- - -.ThinkingNotes.TheCompleteWorksofWangFuzhi.Vol.12. Changsha: Yuelu Press, 2011.401-472.]
——:《俟解》,《船山全书》第12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475—498。
[- - -.WaitingforUnderstanding.TheCompleteWorksofWangFuzhi.Vol.12. Changsha: Yuelu Press, 2011.475-498.]
——:《古诗评选》,《船山全书》第14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483—881。
[- - -.CommentaryandSelectedWorksofAncientPoems.TheCompleteWorksofWangFuzhi.Vol.14. Changsha: Yuelu Press, 2011.483-881.]
——:《唐诗评选》,《船山全书》第14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885—1142。
[- - -.CommentaryandSelectedWorksofTangPoems.TheCompleteWorksofWangFuzhi.Vol.14. Changsha: Yuelu Press, 2011.885-1142.]
——:《姜斋诗话笺注》,戴鸿森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 - -. AnnotatedJiangzhai’sRemarksonPoetry. Ed. Dai Hongsen. Shanghai: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