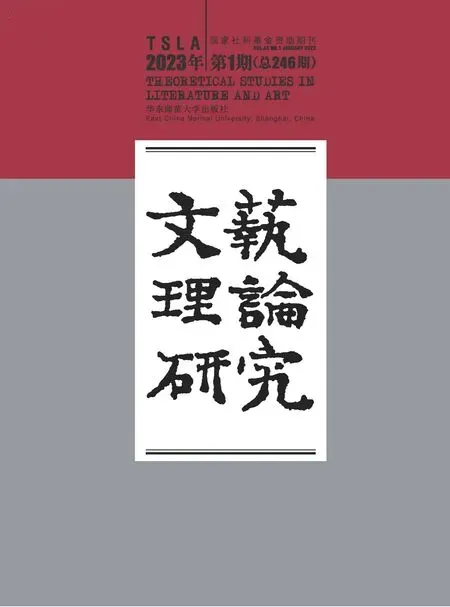时间的他者
——元宇宙及其慢速时间的潜能
熊亦冉
元宇宙(Metaverse)并非关于地方的具象描述,而是更多意味着某个即将来临的“奇点”(Singularity)时刻,这种强调临界状态的时间节点将标志着数字算法在这一刻超越人类智能,时空折叠由此成为数字生产的一部分。但这种生产形式却催生了新的悖论,即如何经由算法理论构造出具有内在一致性的时间模式,并在此基础上依然保留时间的异质性,进而构建主体秩序的问题。因为如果回归小说《雪崩》(SnowCrash)的原初语境就会发现,元宇宙并非脱离现实世界的平行宇宙,而是“悬在阿弘的双眼和他所看到的现实世界之间”(斯蒂芬森28)的世界,其本质是肉身与算法、主体与媒介、虚拟与现实的并置,并以此分解出自我的多重性与时间结构的断裂性。因此,对元宇宙时间逻辑的反思既承载了现代性的镜像问题,又呈现出了一定的自反性(reflexivity)特征,以此撑开了重审现实问题、解构原始权威的裂隙。
一、 发明未来:元宇宙及其当代性
“元宇宙首先是一个当代(contemporary)事件”,而“当代性的一个显著性质是‘未来提前到来’”(赵汀阳31)。对于这种“保持距离”,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曾以“不合时宜”(untimely)来概括主体与同时代的错位关系,并以此强调时间的断裂与脱节(out-of-jointness)(阿甘本20)。换言之,对未来的瞻望恰恰需要以回溯的姿态予以完成,它需要更多未知经验的敞开,需要打开时间的褶皱去与之相遇。因此,元宇宙的当代性脱离了古典时间机制,并预先实现了对未来的殖民。但这种历经筹划的当下化未来并非真正的未来,后者只是作为前者的绝对可能性而存在。作为朝向未来的“事件”(event),对“元宇宙”的命名已然构成了一种例外状态,即对日常生活惯常节奏的打破,以及对既有知识体系和话语方式的颠覆。然而,在作为命名的原初性事件之外,更应注意的是由此引发的意义与效果的关联,因为“事件,就是意义本身。事件本质上属于语言,它与语言之间有一种本质性关系;但语言是对事物的陈说”(德勒兹11)。元宇宙由此更为突出地体现为对语言的位置占有以及对未来向度的指涉,而理想性事件的典型特征就是特异性(singularity)(德勒兹12)。在元宇宙的语境中,这样的特异性或奇点更为突出地体现为一种技术变革的节奏,它是“未来的一个时期”,能够“将事物模式本身转变为人类生命的循环”(库兹韦尔1)。
因此,对元宇宙作为“事件”的关注,一方面注定了对于朝向未来的“奇点”式锚定,另一方面也凸显了事件背后的断裂时间观。慢速(Slowness)的时间特质旨在强调放缓(slow down)和减速(deceleration),它试图抵抗加速(acceleration)的现代性时间机制,并在速度的中心撑开一个空间,以呈现生命经验在共时状态下的协调、对抗与缓冲。①如今,维利里奥(Paul Virilio)的推论或许正在悄然实现,“当代社会正在到达一个临界点,在这个临界点上,进一步的加速或许不再可能”,这毋宁说是现代时间机制借助奇点临近而撞向“加速之墙”(wall of acceleration)的反弹(詹姆斯40)。慢速即以凝视的方式重新审视当代性,并恢复主体异质性的生命经验,其本质是断裂时间观念的一种叙事。它聚焦于共时性,但这种共时状态的核心在于多维辩证法(multi-layered dialectic),只有将当下视作多样性的时间场域,对于历史辩证法的逃逸才得以可能。
作为一种时间体验的现象学维度旨在实现对主体数字分身的悬置,以使其体验时间的绵延本身,进而生成一种叠合过去与未来的同时性。换言之,慢速并非强调静态或缓慢,而是意在呈现时间的多样性及其空间特性,以构成对当下时间体制的认知与反思。此外,对于元宇宙时间架构及其总体性的考察,彼得·奥斯本(Peter Osborn)对“时间的政治”的研究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参照,他指出现代性的时间逻辑与历史观念的总体化特征密切相关,而“当代性”实则是一种建构的虚拟叙事,它的产生基于主体对总体时间机制的共识与认同,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对自我的虚拟化。更为重要的是,它向我们展现了时间结构内部异质性与外部统一性同时“在场”的可能(奥斯本30—33)。如今,奥斯本所言及的断裂时间观及其异质共存的情境仍然构成了元宇宙时间议题的核心。
与之相关的另一个关键议题在于,如何在对全球时间的虚拟想象中重构主体性的根基。启蒙时代以来的主体是基于笛卡尔和康德哲学的理性内在主体,其特征在于对象的客体化。对于这样的主体而言,时间意味着秩序,而秩序则生成位置和意义,从而使事件处于有意义的联结之中,永恒轮回的时间意义源自对过往之物和永恒真理的再生产。主体与时间的关系意味着主体将委身于对过去的返归,时间被自然常量打上了印记。因此,时间是事实性。现代性的时间规定了主体的位置和界限,并以此构成了主体作为共同体的根基及确切意义。正如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指出的那样,主体的存在价值及意义是通过对时间的思考予以完成的,对主体生命经验的把握就是对时间本身的把握(海德格尔375—376)。
而在元宇宙中,作为“现在”的时间将颠覆传统时间对于绝对的“无延伸性”(unextendedness)的强调,因为这种确定的此时此地性将在其中予以无限放大。元宇宙的全息投影技术为主体提供了即时性和当下感,处在“实时”影像中的“当下”特性被划分为多重维度(如多个数字分身),并同时聚焦于瞬间及其强度本身。作为限定的“现在”实现了对生命流变与界限超越的殖民,而多维共存的现实形式——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VR)、增强现实(Augmented Reality/AR)与混合现实(Mixed Reality/MR)则进一步将现实世界中的虚拟内核以超现实的形式呈现出来。此时康德所谓的主体先验统觉,即通过纯粹理性批判所形成的“现实感”判断将进一步被颠覆,因为此时虚拟支配了现实,密集曝光时间(time of exposure)取代了具身绵延(duration)时间。
从根本上说,元宇宙是数字媒介对主体现实的再造,它以更为虚拟的形式强化了主体的现实感。因此,在笛卡尔意义上的理性主体之外,还存在着另一种分裂的主体观念,它冲破了传统的单一主体,并同时强化了偶然的生命经验和断裂的时间观念。这种基于无意识的力比多主体以游牧的方式逃逸了原有的主体设定。而在元宇宙中,这类“逃逸”的痕迹并未被抹除,而是以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所谓的“第三持存”(Tertiary Retention)的方式予以呈现和保留,它不同于以在场为特征的“第一持存”和以回溯为特征的“第二持存”,而是以中立和客观的方式记录了外在于主体的数据,进而“将过去时刻以及正在流逝的意识的时间空间化了”(斯蒂格勒74)。这样的人为性和虚拟性使得身体经验被进一步压缩为抽象的算法,滞留在“第三持存”中的数字客体正以代具(prostheses)的方式再现了时间与意识的物质实在性,并以具象化的形式确证了主体及历史的镜像本质。这种由攫取主体无意识溢出的数字痕迹而生成的数字绘像(Digital Profiling)构成了以“第三持存”为本质的“外主体”(external-subject)。②
以元宇宙中的数字孪生(Digital Twin)技术为例,它构建了基于生命周期与身体指数的数字虚拟模型,并形成了所谓的数字孪生体。通过主体与数字模型之间的信息还原、交互与反馈,它实现了人类对信息镜像阶段的想象与投射,并使得算法对主体的预测部分地成为可能。尽管这一技术的核心是与主体的共生性,实则仍然面临着同一性的认同危机,并旨在反向实现和确证自我经验的想象性构成。因此,对数字分身的选择将直接投射出主体最想实现的身份认同,这种屏幕与主体的关系在本质上仍然需要基于镜像阶段的自我指认,但当重返现实的时候,主体却只能再次陷入实在界(the Real)的创伤之中。看似自由与多元的虚拟空间实则强化了实在界与想象界(the Imaginary)的裂隙,并直指主体的存在性困境——即便元宇宙实现了虚拟化从自在到自为的过渡,但作为“想象的实在界”的赛博空间实则无力承担象征界(the Symbolic)消隐的失落,这也是主体本源性的裂缝所在。
而主体更为严峻的情境在于,既然元宇宙已对现实感进行了重构,那么一旦构建秩序的虚拟性结构不再具备原有的权威,虚拟空间中的主体行动就难以实现对大他者规训的逃逸,抑或原本由大他者所承载的重担将随之让渡于主体自身,造成主体无法承受自由之重而陷入克尔凯郭尔所言的“眩晕”之中,这也正是存在主义的选择悖论所在。因此,如果元宇宙缺乏时间作为界限,那么主体将被无限的虚拟空间淹没而失去定向方式,因为界限的使命就是规定意义。此处的“规定”具备两层含义:一方面,时间作为坐标体系规定着元宇宙的社会交往层面,并蔓延至个体的自我规定与筹划;另一方面,只有发挥时间的界限属性,主体行动者才能确立位置,进而提供安全感与确定性以生成元宇宙世界的可理解性。形式实现了对生命的规定,只有这样的生命才是自足的、自我规定的,否则生命将遭遇脱域的危机而沦为盲目。时间作为界限构成了主体身处其中的既定位置,而界限的持恒性又由此确立了作为形式的文化与作为活动的生命之间的辩证性。因为生命的本质是一种过程,而时间则维持了限定(fixation)与流动(fluidity)之间的张力关系,这一矛盾既是现代文化冲突的实质,也是元宇宙多元价值体系的复杂内核。
二、 抵抗加速:慢速时间的生成机制
速度是时间的次级概念,它基于时间产生并呈现其内部动态关系的综合。早在文艺复兴时期,线性时间观念就经由人文主义研究而得以强化。而关于速度的理论叙事则肇始于启蒙时代,这种对理性赋予绝对权威的时间表象以去事实化的时间为基础,它从神学压制中解脱并以未来为旨归。因此,时间是筹划,加速借助时间的未来向度而具备了意义。正如1909年,马里内蒂(Filippo Tommaso Marinetti)在《未来主义的创立和宣言》中声称的那样——“宏伟的世界获得了一种新的美——速度之美,从而变得丰富多姿”(马里内蒂46)。速度的叙事话语由此逐渐在现代性的时间框架中占据了主导,它既是集体经验得以展开的媒介,又是支撑这一经验及其历史性的核心内驱力。现代性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一种带有目标指向的投射,并显现为朝向未来的行进姿态。与前现代不同的是,现代人是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意义上的朝圣者抑或异乡人,他已不再是预定的被抛状态,而是将自身确立为历史的主体进而踏上了不确定且不可靠的远方征途。因此,这种进步的自由叙事使得未来永远处于期待之中,加速充当了介入世界的方式并构成了它的本质特征。
具体而言,对“加速”的定义呈现为双重视角,其一是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基于社会时间结构而提出的加速概念,这一视角更倾向于对客体的时间机制及其特征展开分析;其二是韩炳哲(Byung-Chul Han)基于主体及其本真性提出的时间消散问题,这一视角更为关注主体的时间经验及其变化本质。对于前者而言,“现代化的经历就是加速的经历”(罗萨28),速度由客观抽象的物理概念转变为代表当下的现代性体验。而以技术、社会变化、生活节奏为主要维度的“加速”在借助加速度(speeding-up)实现自身的同时,又促使个体与社会从“共鸣”(resonant)走向了“异化”(alienation),主体沉浸其中的当下被抽空。因此,线性时间在一定程度上拉平了主体经验的内在丰富性,最终导致了生命经验的均质化以及感知方式的稀薄与趋同。
这一事实产生的前提可追溯至新教伦理对速度价值的强化,工具理性逐渐发展为以竞速为特征的时间经济,因为对资本和个体的控制是以时间榨取的形式实现的。在这一意义上,资本是一种时间的技术,它通过将未来编入当下的形式填满了所有意外事件之间的裂隙,以表面的预知和筹划消除了对时间的“焦虑”。它进而作出了这样的预设——只有将时间性能化,不断增强对信息的抓取和量化能力,才能实现对时间的精准计算和处理。因此,尼克·兰德(Nick Land)将“加速”视作描述资本积累的时间结构,并认为“加速主义”(accelerationism)展现的是一种“目的螺旋”(teleoplexy)的资本化控制过程(Land514-516)。资本的复杂性体现在它对时间的分解,随着“目的螺旋”裹挟着现代历史向虚拟化方向倾斜,这一时间结构越来越多地将科幻场景作为生产系统的组成部分予以操作。“尚未”(not-yet)存在的价值观获得了对经济和社会进程的绝对控制权,也就必然会导致现实本身的贬值,旨在“抢占”未来的元宇宙经济无疑为这一论断提供了更为鲜明的注脚。
但罗萨所谓的“加速”概念并非只强调速度的提升,它实则还隐含着对速度“失调”的考察,这将由此关联到韩炳哲对主体时间经验及其“失重”的讨论。对于后者而言,加速的产生是由于时间内部丧失了自身支撑之物。缺乏方向的加速并非真正的加速,因为加速在原本意义上是以定向的流动轨迹为前提的(韩炳哲15)。“上帝之死”使得现时成为某个转瞬即逝的时间点,亦即时间的原子化。它不再与过去和将来相连接,时间的重力消失了,点状时间导致了时间本身的最终崩塌。不过,但韩炳哲并不赞成将意义的流失单纯地归因于速度本身,而是认为诸事物持续得以加快,其根本原因在于没什么东西能将其保持在稳定的运转轨道上,轨道的消失使得“一切就都拥挤到现时之中”(韩炳哲53),从而形成了事件和信息的大众化。同时,这种去时间化还将引发叙事危机,使主体无法实现对事件的筹划与聚合。更为典型的去叙事化症候则是一种疲于奔命的感觉,仿佛生活在持续加速,然而意义却并未随之提升。因为真实的加速意味着一种确定性的定向进程,而去叙事化却导致了无方向的紊乱,这些均源自叙事轨道和时间重力的消失。突然停顿的恐惧(如闭关休假或向虚拟空间逃逸)会反向强化加速的许诺,这更加印证了朱迪·瓦克曼(Judy Wajcman)所谓的“时间紧迫悖论”(time pressure paradox)(Wajcman5)。
然而,当现代性的加速机制被推向极致的同时,它也将在临界状态为主体提供断裂与颠覆的可能。而这一“断裂”的时间潜能早在波德莱尔对现代性的定义中就已形成了,即现代性的时间机制所予以参照的正是短暂的“偶然”与稍纵即逝的“此刻”(波德莱尔431)。在这一前提之下,“游荡者”才成了反抗加速现代性的“英雄”,因为它赋予了行走的主体以时间和空间的连续感,进而以此调整异化感并悬置速度体验与同质化空间。因此,从波德莱尔和本雅明的“闲逛者”到齐美尔的“距离”说,从列斐伏尔对日常生活审美性的强调,到阿甘本对“不合时宜”的旁观者与局外人的言说,都无一例外地构成了一种审美叙事的立场,旨在以救赎的方式抵抗被异化了的现代困境,其本质是以时间感知与生命体验对抗启蒙的现代性困境,这也构成了慢速时间机制真正得以生成的起点。
本雅明曾以“背对着未来”的“历史天使”形象探讨历史观及其时间本质,基于现代速度的历史时间捕获了天使,使其无法合拢翅膀,但他的目光却依旧凝视过往的残骸,拒绝朝向未来(本雅明270)。他对时间性的考察颠覆了既有的线性时间观念,进而在废墟的意象中捕获了时间本质和感知模式的历史性变迁。本雅明对救赎的希冀承载着变化、偶然与开放的可能,而总体性的历史叙述却总会跳过历史事件的不连贯性和非因果性,同时以进步的期许作为它的终极目标。因此,这种历史观并未将目光瞄准主体身处其中的当下,而是只有具备回溯的视角才能打破指向进步的线性时间观。既然时间是原子化的存在,那么每一个节点都有可能实现本雅明意义上的“虎跃”。这种速度的中断无疑构成了审美叙事及其体验的基础,以此呼唤着本真性的来临。
与之相关的是,作为本雅明好友的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同时提出了“异步性”(asynchronicity)的概念,以阐释作为复数而非单一的现代性。因此,他与布洛赫、本雅明一道被视为描述现代性之时间体验的首批作家(弗里斯比144)。面对启蒙理性及其引发的意义真空,克拉考尔主张以“等待”的姿态维持一种“犹疑的开放性”(hesitant openness):“等待就是一种犹疑中的开放性存在,虽然这是很难解释的一类存在。[……]由于他们是自愿在等待的,所以他们就是此时此地在等待的人。”(克拉考尔113)这里的“此时此地”无疑是对本真性的一种开启,这是对原子化个体的解放,而“等待”则意味着保有彷徨的希冀,并力图实现对现实的重返。这也是克拉考尔以“心理的显微透视”方式从“街头”和社会“表层”实现对历史体验重新感知的可能,而那些等待现代速度接近并将其视为异质场域的才是真正的当代人。概言之,元宇宙得以开放的慢速时间机制无疑可以帮助本雅明的“天使”走出朝向未来的“风暴”。因为主体对时间流的反转将重新捕捉过去和当下未曾被察觉的细节,从而恢复对“例外状态”和“事件”的重新关注。这种慢速机制也终将使主体从定向的速度决定论中解放出来,让元宇宙分分秒秒都得以开启主体侧身步入的门洞。③
三、 媒介考古视野中的时间自反性
“媒介的概念既是对现代理性祛魅规则的体现,也是一种对此的纠正”(科普尼克47),这正是媒介考古学的基本立场。因此,它展现了早期媒介对断裂和速度的双重压力,以及后期媒介对时间自反性的重新考察。从基于文字的媒介到基于沉浸与交互的数字媒介的演变,其实质是认知诉求向体验诉求的转型。而后者与主体的在场密切关联,并通过虚拟数字媒介再现了主体具身体验的重构与再造。元宇宙作为新媒介的特性在于,它在移动图像的基础上将其转换为互动、操作、传输和反馈的多元体系,进而重新改写了传统电影实践与新兴数字媒介之间的连续性。如果说电影已形成了观看、触摸、感觉等媒介形式及其融合的话,那么如今以游戏和数字影像为表征的元宇宙实则进一步重建了自身与媒介装置的关联。其中,电子游戏的特性恰恰在与它将时间性溶解于节奏与操作的偶然性之中,并将暂时性转换为视觉、触觉、听觉等感知形式,从而在用户与系统之间构建起了统一的时间框架和度量标准。
在本质上,影像以加速、浓缩、颠倒时间流的形式实现了主体对时间感知的聚合、凝固和延展。而在元宇宙中,交互界面的本质仍然是数字图像,它在一定程度上与影像共享同一个数字基底,因为计算机及其数字代码作为元媒介的属性并未改变。正如马诺维奇(Lev Manovich)所言:“计算机时代的视觉文化在外观上是电影式的,在材料上是数字的,在逻辑上是与计算机有关的。”(马诺维奇182)因此,元宇宙对影像潜能的开启已毋庸置疑,它甚至将以数字动态影像的方式进一步强化电影、游戏得以重构的视频时间。以电影及其时间逻辑为例,多恩(Mary Ann Doane)曾指出:“电影被视作时间本身的印记,即脱离了理性化的时间、非逻辑的时间,在这样的时间里,每一个瞬间都可以产生意想不到的、不可预测的、暂时性的不确定性。”(Doane22)换言之,电影的时间绵延就是正在发生抑或正在消失的绵延,它实现了对空间图像的时间化表达。
在元宇宙的影像生成中,慢速将作为电影和游戏时间的突出形式予以展现,因为主体能够借助闪回(flash back)和闪进(flash-forward)的形式打破原有的时间顺序,从而构成对叙事速度的再创作。以电影为例,这种主导时间的潜力突出体现在劳拉·穆尔维(Laura Mulvey)以“延迟”(delay)为例的分析中:“首先,它指的是减缓胶片运动的实际动作。其次,它指的是时间上的延迟,在这段时间里,一些细节处于休眠状态,等待被注意到。这与弗洛伊德的‘事后性’(nachtraglich-keit)概念有着大致相似之处,即潜意识保留了一种特定的经历,而它的创伤效应可能只会被另一个稍后但相关的事件实现。”(Mulvey8)尽管其效果和机制来自数字算法的合成,但它实则暂停了总体叙事进而使得不同时间流的差异性保持可见。因此,元宇宙基于电影或视频形式的慢速时间能够以此反转主体既有的知觉结构,并以细部呈现的方式捕捉时间动态本身。
而数字游戏时间则在界面与主体之间建立了即时性的互动关系以感知不同维度的时空重叠,并以特殊的时间性重新书写了主体对时间的体验和理解。基于即时性和临场感的游戏时间是一种递归的(recursive)时间机制,它以对时间的操纵和重置为核心,因此在本质上仍是反身性的时间结构映射,即游戏需要玩家不断介入以维持互动性及其与游戏机制之间的持续反馈循环(Hanson194)。在这一意义上,游戏实现了一种独特的时间流动,它在过去、现在和各种潜在的未来事件之间建构起了连续的统一体,并通过对时间操控、重置、互动和递归等方式创造了新的时间体验。此外,游戏还同时体现了用户时间、游戏中的事件时间(玩家生成的时间线)以及话语时间(游戏设定的时间线)之间的分裂、重合与倒置。玩家在游戏过程中主动编排并缝合了事件时间,这正是游戏研究中所谓的突发性(emergent)特征,以此对抗既定的嵌入式叙事(游戏的情节设定)。
元宇宙与电影、游戏或视频的亲缘性联结,使其更为典型地实现了“电影眼”(Kino-Eye)对时间和空间界线的打破。这一过程将借助新媒体的“可编程性”(Programmable)实现更为本质的计算机化(Computerization),即通过对数据的存储、检索、分类以实现对不同媒介和不同主体的算法统筹与归并。基于算法感知的数字影像一方面呈现了计算机的工具属性,另一方面又仍然构成了对电影效果的存续与延伸,其本质上是新媒体的新奇性(newness)及其文化史之间的悖论关系。因此,媒介考古的根本任务在于发现媒介背后的时间逻辑,该逻辑展现了媒介形式特征所经历的“再媒介化”(remediation)过程,并由此彰显了媒介内部的时间性及其连结和转化。马诺维奇进而指出,作为控制结构的循环语句奠定了媒介时间的基本架构,即循环语句与顺序进程这两种时间形式的协同工作——“循环不仅催生了电影,也催生了计算机编程。编程通过一系列控制结构,例如‘if/then’‘repeat/while’,来改变数据的线性流动,而循环语句是最基本的一种控制结构”(马诺维奇321)。此外,“循环”还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媒介叙述和交互控制的结合。
因此,“循环”真正的媒介考古意义在于:“循环的使用不是陈旧的历史残余物,也不是对电影发展的抵抗,而是为基于计算机的电影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时间美学。”(马诺维奇323)而在这种控制论的循环语句之外,数字媒介的时间架构还会以图像和页面嵌套的形式予以呈现。安妮·弗雷伯格(Anne Friedberg)指出,对于如今的数字页面和视频窗口而言,其深层的演变线索恰恰在于一种新的视觉逻辑的生成,它通过对窗口的框架化和虚拟化处理,实现了对空间装置的时间转换(Friedberg240-244)。因此,这与其说是现代性视觉政体的演进与变迁,毋宁说是一种历时性的重屏显现,即交互界面在时间性的层面连接了时间与空间、暂时性与总体性,进而生成了主体与对象共时交互的新形式。
从根本上说,元宇宙借助交互页面的媒介特性实现了时空折叠以及空间开放的潜能。西方哲学传统对空间的认知大概分为两条进路,一是以笛卡尔为代表的基于实体的物质广延观念,二是以洛克和柏格森等为代表的基于精神实体的心理绵延观念,后者将绵延视为真正的时间,其内部诸多瞬间的渗透、连结共同构成了由过去通向未来的动态时间流,以此区别于传统的静态均质化时间。胡塞尔进而提出了基于现象学维度的空间知觉观念,这一内在时间观念可溯源至奥古斯丁对时间意识的界定以及康德对时间形式及感性直观的阐释。胡塞尔认为,正是由于时间流的介入,从二维到三维空间的感知才得以可能。而时间流的本质是具有持续时间意识的心理机制,延续的感知是以感知的延续为前提的,它通过对幻相(phantom)及其二维呈现的延伸,弥合了空间的同一性与差异性,而视域(horizon)则是主体感知的结果(胡塞尔60)。
然而,现代性的时间机制却展现出了动态变化的时间观念与静态共时的空间观念的失衡,其根本原因在于速度导致了时间对空间的压缩,即技术速度阻碍了主体对空间经验的生成并使之虚拟化(如坐飞机虚拟化了主体对风景的亲身体验),空间的广延性让位于瞬间的密集性,“当下”支配了“这里”:“时间的观点可以归结为一种透视观……由不具时间长度的瞬间构成的时延就如直线是由不具向度的点所构成一般。”(维利里奥212)至此,基于速度的时间取代了绵延秩序而成为了虚拟现实的视觉机器。这种由技术现代性及其不断递增的传递速度所造成的实时伪像(real-time simulacra)对真实展相(real presence)的全面接管,以及主体知觉时间性和历史性的变形,正是维利里奥借助“竞速学”(dromology)所道出的言外之意(詹姆斯xiv)。速度改变了现象向主体涌现的形式,竞速复制构成了伪像的短暂本质。
因此,需要重新考察空间及其叙事变革的可能性。作为赛博空间的全新形式,元宇宙无限多元的空间与反向回溯的时间构成了时空连续性的断裂。这反而在另一种程度上开启了空间的开放式动态和异质性过程,并同时显示出多重速度和持续时间的活跃共存。元宇宙在空间不在场的前提下实现了主体的在场,但这种在场性并不仅仅是主体自身的沉浸体验,它还意味着与他人在虚拟空间中的共在。因此,以交往的主体为核心,元宇宙空间将进一步彰显以人与人、人与物的关系为核心特征的空间范畴。此处的“空间”呈现为列斐伏尔意义上的关系场域,基于差异与重复的主体介入元宇宙的过程近似于从光滑空间(Smooth space)到纹理空间(Striated space)的逆转与折返,由此更为凸显其逃逸的可能性路径。
对于元宇宙中的个体而言,时间从来都不是中立的,相反,经由“时间化”的事件才能更加强烈地标识出等级与权力的博弈,并以此呈现世界本身的异质性以及时间观念的流动与变形。以个体记忆和集体怀旧为例,对当下时间的执着反而会导致主体以回溯的方式重温本真性的时间体验,因为“过去完全是在我们对它进行指涉时才得以产生的”(阿斯曼23),即记忆只有经历重构才能予以保留。死亡是时间断裂的最原始经验,而元宇宙则通过全息投影的“隔空对话”恢复了不同于交往记忆的文化记忆,并在激活原始场景的同时,突出了集体记忆特有的文化成分。与此同时,元宇宙记忆机制的核心还与接纳未来及重返过去密切相关。托夫勒(Alvin Toffler)曾预言,人类将有可能成为未来超载的受害者,即过于疾速的“变化”将导致主体时间感知的骤变及其对过往的决裂,而这种决裂正是怀旧产生的先决条件(Toffler449)。在这一意义上,元宇宙中的慢速时间机制将作为缓和未来冲击的“过往的飞地”而存在,其功能在于逃离未来的疾速时间流。正是这种趋向过往“飞地”的重返才最终在增值的复归中再造了意义和历史。
元宇宙中的主体在让渡个体记忆的同时,也意味着“非人”(inhuman)化的生成,因为去事件化的记忆将以技术单子的模式占据元宇宙的时间架构(利奥塔61)。这种非人化的特性在根本上源于算法自身的物质性,并导致了以抽象逻辑符号为基础的“算法信任”。尽管区块链技术意在通过数字加密实现对网络秩序的规约,但它仍在很大程度上存有隐患。从本质上看,数字算法构成了对个体生命记忆的代理、殖民和架构。数字记忆将永久转变为不断持续的现在与当下,而人造记忆库则以存档的“同步性”消解了时间的异质性,对记忆的数码生成同时伴随着个体的失忆及原子化。这将在根本上冲击到“体验”这一核心范畴,因为“元宇宙的核心是体验,它的起因正是VR所肇始和营造的沉浸性对于互动性的遮蔽、压制、乃至扼杀”(姜宇辉24),这无疑将引发个体时间与记忆感知的困境。
因此,元宇宙中的算法意识形态有可能在披上实证主义外衣的同时隐匿了其背后的真实立场——“赛博演化主义”(cyberevolutionism),并由此强化了自我演进的逻辑自洽。④基于数字达尔文的历史观实则重新论证了线性时间观的内在逻辑,并强化了它殖民未来的合法性。我们无法想象元宇宙的中断以及偶然事件对它的扰乱,正如我们深信进化链条的坚不可摧一样。这在强调数字化生存的持续性与常态化的同时,也在无形中模糊了元宇宙内部的权力话语及其内在复杂性。在齐泽克看来,赛博空间在本质上是赛博资本家(cyber-capitalists)所主导的“无摩擦资本主义”(friction-free capitalism),因为它可能正在以“彻底透明、虚幻的交换媒介的幻想”擦除创伤性的社会对抗及权力关系(齐泽克196),或许这正是元宇宙数字图景背后的隐忧所在。
结论:慢速与重审当代性的可能
元宇宙及其技术仍然活跃于现代性的内部,对于嵌入其中的主体经验而言,虚拟空间的交互性与沉浸性将得到最大限度的彰显。它进而以新异的方式实现了对主体的定位并重塑了时间体验,其中的慢速时间在本质上是新历史主义、非线性时间以及新游牧哲学的混合体,并由此暗含了一种加速批判的现象学视角以实现对时间知觉的聚焦。而速度则展现了诸现象之间的关联性,并决定了现象向主体涌现的方式。元宇宙以拟像的形式重建了主体与可感世界的关联,而长期以来,物理时间对线性和进步的指向使其规避了对递归、非线性及多样性的关注。在这一意义上,慢速时间构成了对这一事实的抵抗,其本质在于恢复数字技术与身体情境的关联,即时间体验如何经由技术环境而实现自身的定向结构。
在元宇宙的虚拟场域中,远程在场取代了真实在场,原本具身化的时间体验被抽象为单一原子化的数字时间,算法与生命情境的冲突由此产生。对这一时间架构的逃逸则需要打开现代时间机制的褶皱,并从慢速美学中重新恢复对生命异质性的关注。概言之,尽管元宇宙到来之日就是算法成熟之时,但算法确定性却仍然取决于主体的不确定性,即主体的边界在本质上决定了元宇宙的边界。但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实现文明演进的非线性路径才得以成为可能。借助元宇宙数字媒介,基于回忆、怀旧、凝视的慢速时间最终使主体获得了对他者的时间经验,以此构成了对线性时间观的颠覆。因此,慢速始终显现为对历史总体性及其压力的对抗,这种压力还同时包含了时序霸权对个体本真性的压力以及时间对空间的压力。对于容纳了多重时间流的元宇宙而言,慢速时间机制在更大程度上意味着重新发掘当下,以开启通往未来的可能性,由此完成对当代性的另一种体察和认知。
注释[Notes]
① 对“慢速”一词的引用源自德国学者卢茨·科普尼克(Lutz Koepnick)的著作《慢下来:走向当代美学》。他在书中对“慢速美学”作了如下界定:“当代慢速美学,是我们有能力去感知和再现,当下的空间中不同时间性的同时性;它提高我们对新旧、快慢、连续与破坏共存的感知,无须要求我们优先考虑其中一个,或概念化不同的时间和连续性,作为整体之一(或者就此而言,辩证)的动态。”(270)
② 学者蓝江指出,“‘外主体’依然是主体,因为它仍然与我们的意识和无意识行为密切相关,它仍然是被我们生产出来的,但是这个主体已经从内部的主体结构中逃逸,成为一个外在并制约着我们行为的主体”(44)。
③ 此处化用了本雅明的说法,他曾指出“时间的分分秒秒都可能是弥赛亚侧身步入的门洞”(本雅明276)。
④ 齐泽克在《幻想的瘟疫》中指出,这一概念他参考了蒂齐亚纳·特拉诺瓦(Tiziana Terranova)对“数字达尔文”(Digital Darwin)的定义(196)。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吉奥乔·阿甘本:《裸体》,黄晓武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
[Agamben, Giorgio.Nudities. Trans. Huang Xiaowu.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7.]
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Assmann, Jan.CulturalMemoryandEarlyCivilization:Writing,Remembrance,andPoliticalImagination. Trans. Jin Shoufu and Huang Xiaochen.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5.]
夏尔·波德莱尔:《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郭宏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
[Baudelaire, Charles.SelectedEssaysofBaudelaireonAesthetics. Trans. Guo Hong’an.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Press, 2008.]
瓦尔特·本雅明:《历史哲学论纲》,《启迪:本雅明文选》,汉娜·阿伦特编,张旭东、王斑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265—276。
[Benjamin, Walter. “On the Concept of History.”Illuminations:EssaysandReflections. Ed. Hannah Arendt. Trans. Zhang Xudong and Wang Ban.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8.265-276.]
吉尔·德勒兹:《〈意义的逻辑〉节选》,《生产》第12辑,汪民安、郭晓彦主编,姜宇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3—24。
[Deleuze, Gilles. “The Logic of Sense (Excerpt).”Producing. Vol.12. Eds. Wang Min’an and Guo Xiaoyan. Trans. Jiang Yuhui. Nanjing: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7.3-24.]
Doane, Mary Ann.TheEmergenceofCinematicTim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Friedberg, Anne.TheVirtualWindow:FromAlbertitoMicrosoft.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2006.
戴维·弗里斯比:《现代性的碎片:齐美尔、克拉考尔和本雅明作品中的现代性理论》,卢晖临、周怡、李林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
[Frisby, David.FragmentsofModernity:TheoriesofModernityintheWorkofSimmel,KracauerandBenjamin. Trans. Lu Huilin, Zhou Yi and Li Linyan.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3.]
韩炳哲:《时间的味道》,包向飞、徐基太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7年。
[Han, Byung-Chul.ScentofTime. Trans. Bao Xiangfei and Xu Jitai. Chongqing: Chongqing University Press, 2017.]
Hanson, Christopher.GameTime:UnderstandingTemporalityinVideoGame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8.
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
[Heidegger, Martin.BeingandTime. Trans. Chen Jiaying and Wang Qingjie.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8.]
埃德蒙德·胡塞尔:《内时间意识现象学》,倪梁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
[Husserl, Edmund.OnthePhenomenologyoftheConsciousnessofInternalTime. Trans. Ni Liangka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7.]
伊恩·詹姆斯:《导读维利里奥》,清宁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9年。
[James, Ian.PaulVirilio. Trans. Qing Ning. Chongqing: Chongqing University Press, 2019.]
姜宇辉:《元宇宙作为未来之“体验”——一个基于媒介考古学的批判性视角》,《当代电影》12(2021):20—26。
[Jiang, Yuhui. “Metaverse as Future ‘Experience’: A Critical Perspective from Media Archeology.”FilmStudiesinChina12(2021):20-26.]
卢茨·科普尼克:《慢下来:走向当代美学》,石甜、王大桥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20年。
[Koepnick, Lutz.OnSlowness:TowardanAestheticoftheContemporary. Trans. Shi Tian and Wang Daqiao. Shanghai: Orient Publishing Center, 2020.]
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大众装饰——魏玛时期文论》,孙柏、薄一荻、郑家欣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21年。
[Kracauer, Siegfried.TheMassOrnament:WeimarEssays. Trans. Sun Bai, et al. Beijing: Law Press, 2021.]
雷·库兹韦尔:《奇点临近:当计算机智能超越人类》,董振华、李庆成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年。
[Kurzweil, Ray.TheSingularityIsNear:WhenHumansTranscendBiology. Trans. Dong Zhenhua and Li Qingcheng. Beijing: China Machine Press, 2011.]
蓝江:《外主体的诞生——数字时代下主体形态的流变》,《求索》3(2021):37—45。
[Lan, Jiang. “Birth of External Subject: Change of Subject Form in the Digital Age.”Seeker3(2021):37-45.]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非人:漫谈时间》,夏小燕译。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
[Lyotard, Jean-François.TheInhuman:TalksaboutTime. Trans. Xia Xiaoyan. Chongqing: Sou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19.]
菲利波·托马索·马里内蒂:《未来主义的创立和宣言》,《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柳鸣九编,吴正仪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44—60。
[Marinetti, Filippo Tommaso. “Foundation and Manifesto of Futurism.”Futurism,SurrealismandMagicRealism. Ed. Liu Mingjiu. Trans. Wu Zhengyi.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1987.44-60.]
Mulvey, Laura.Death24xaSecond:StillnessandtheMovingImage. London: Reaktion Books, 2006.
Land, Nick. “Teleoplexy: Notes on Acceleration.” Ed. Robin Mackay.#Accelerate:TheAccelerationistReader. Falmouth: Urbanomic, 2014.509-520.
彼得·奥斯本:《时间的政治》,王志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
[Osborne, Peter.ThePoliticsofTime. Trans. Wang Zhiho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4.]
哈尔特穆特·罗萨:《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董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Rosa, Hartmut.Acceleration:TheChangeofTimeStructuresinModernity. Trans. Dong Lu.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5.]
尼尔·斯蒂芬森:《雪崩》,郭泽译。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年。
[Stephenson, Neal.SnowCrash. Trans. Guo Ze. Chengdu: Sichu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2009.]
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3:电影的时间与存在之痛的问题》,方尔平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
[Stiegler, Bernard.TechnicsandTime,3:CinematicTimeandtheQuestionofMalaise. Trans. Fang Erping. Nanjing: Yilin Press, 2012.]
Toffler, Alvin.FutureShock.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71.
保罗·维利里奥:《消失的美学》,杨凯麟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
[Virilio, Paul.TheAestheticsofDisappearance. Trans. Yang Kailin. Zhengzhou: Henan University Press, 2018.]
Wajcman, Judy.PressedforTime:TheAccelerationofLifeinDigitalCapital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4.
赵汀阳:《假如元宇宙成为一个存在论事件》,《江海学刊》1(2022):27—37。
[Zhao, Tingyang. “If the Metaverse Becomes an Ontological Event.”JianghaiAcademicJournal1(2022):27-37.]
斯拉沃热·齐泽克:《幻想的瘟疫》,胡雨谭、叶肖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
[Žižek, Slavoj.ThePlagueofFantasies. Trans. Hu Yutan and Ye Xiao. Nanjing: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