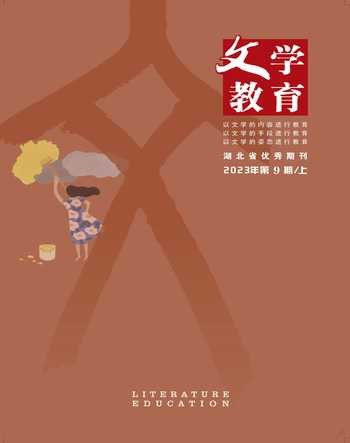三岛由纪夫《金阁寺》主体建构的拉康式解读
徐杨 嵇菁青
内容摘要:《金阁寺》讲述了主人公沟口在混乱无序的战后现实中想要融入社会,却经历亲情、友情、爱情的接连无望,最终火烧金阁的故事,沟口的一生是在他者身上构筑幻想,并因此毁灭的一生。本文以拉康的镜像理论与主体三界说为基础,探讨沟口的成长轨迹与心路历程,阐明沟口从无意识的实在界凭需要行事,至想象界在他者中建构主体,最终在象征界走向毁灭的主体建构失败的过程并进一步分析其失败原因,沟口的经历不仅折射出战后普遍的存在焦虑,更反映出创作者三岛由纪夫的文学观念。
关键词:三岛由纪夫 《金阁寺》 镜像理论 主体性建构 他者
《金阁寺》被普遍认为代表了三岛由纪夫文学的最高水平,是三岛美学的集大成者。该作品以1950年发生于京都鹿苑寺的一起纵火案为原型,讲述了主人公沟口在永恒之美的金阁与现实世界的人生中抉择不定,最终火烧金阁的故事。《金阁寺》延续了三岛美学的一贯态度,游离于主流社会生活和审美趣味之外,文字间张扬着作者对于主体与他者,存在与毁灭,战争与和平等矛盾冲突的思考,这些矛盾相互依赖又相互排斥,形成了势均力敌的竞争关系。其中主人公与金阁的矛盾参与了其自我主体建构的全过程,也体现在与其他人物的交往之中。因此,对金阁之于沟口的意义以及沟口与他者间的动态关系的解读,正是研究《金阁寺》这部小说的关键。从偏远乡村的青年到火烧金阁的罪犯,沟口主体确立的过程纷杂难解,本文將从拉康的主体三界理论入手,分析沟口在不同阶段自我认同的困境。他在自己的
一.无意识的竞争关系
三界说是拉康针对弗洛伊德的三重人格结构学说所提出的关于主体理论的核心概念,分别为实在界、想象界、象征界,这三界相互连结,构成了主体心理结构的认同过程。拉康对于实在界的论述经过多次变化,最早在发表于20世纪30年代的那些论文里,他就曾经使用过“实在”这一术语,作为“自在存在”,实在界指的是从出生到镜像前期,婴儿无法识别自己和他人之间的区别,自我是边界暧昧、不明确、缺乏完整性的事物,只凭需要行事。
《金阁寺》的主人公是一个名叫沟口的年轻僧侣,因为天生的口吃、体弱而遭到周围人的排斥,其主体建构和自我认同的过程是曲折的。沟口幼年时期便自觉不被世界所接受,受人嘲弄的灰暗现实使其对美的需要更加强烈,得到美的认同成为了他主体建构的关键,因而从小美的存在就占据了他的头脑。在父亲的影响下,他对金阁产生了强烈的兴趣,认为“人世间再没有比金阁更美的东西”。沟口对金阁有了无穷的想象和期待,沉醉于内心世界对幻想中金阁的崇拜。然而,在其未知的地方存在着美,对于沟口来说是对其自我的价值的否定。自此,沟口与金阁便隐约形成了一种竞争关系,沟口需要得到金阁的认同,方能完成自我的确认,但在实在界这种矛盾竞争关系并不激烈,也尚未威胁到他存在,因此并不能被沟口察觉。尽管竞争关系并不凸显,但确实影响着沟口对待世界的方式。没有完整的自我的概念的沟口,如婴儿满足自己需要般支配意念,推动他处理与他人关系的动力是生存需要。
在接触到实在的金阁之前,沟口在所能接触到的一切风景和事物中寻找美的替代来满足自我需要,对医院护士有为子的爱慕是他第一次接触现实美的尝试。凭借着对美的强烈需要,当沟口沿着内心世界的轨迹在夜晚拦住有为子对她表达爱意时,却因为口吃遭到了拒绝和嘲笑,并在事后遭到了叔父严厉的叱责。可以说,有为子所代表的的美的世界拒绝了沟口,并映衬出他口吃的丑陋。这种拒绝是对沟口主体建构需要的否定,面对无法满足的需求,沟口采取的方式是诅咒和怨恨。这种诅咒是日后沟口火烧金阁在认识层面的先兆,诅咒的背后暗示的是人生的另一条道路——灭绝他人和世界。《临济录》中讲“逢佛杀佛,逢祖杀祖”,苦恼的根源在于杀得还不够多,只要灭绝了他人,那么就没有任何人可以证明沟口的“丑”,便能够得到美的认同了。
当沟口越过语言和文字,第一次在现实中看到梦寐已久的金阁时,与想象相距甚远的金阁没有能引起沟口任何的感动,它只是一个破败、古老、没有任何美感,甚至不协调的建筑物。但在远离金阁后,那样令其失望的金阁,又渐渐复苏了他的美。在幻象中孕育的事物,一旦经过现实的修正,反而更加刺激欲望了。现实中对美的幻想的破灭又形成观念上的美,在这样观念与现实的相违背的情况下,沟口受父亲的遗愿的嘱托成为了金阁寺的一名弟子,与金阁亲密接触,沟口对于金阁的认同需求也愈加迫切。
与代表着美的特质的有为子不同,在沟口少年时期,母亲这一角色充当的美的对立面,她“天生就同美丽的金阁无缘,却拥有着我所不知道的现实感觉”。因为初中暑假目睹了母亲与亲戚的乱伦,沟口心中一直怨恨母亲。然而,正是代表着贫困寒碜、欲望背叛,与金阁美丽无缘的母亲激化了沟口与金阁之间的矛盾关系。父亲过世一年的忌日,母亲上京都想请老师为父亲诵读经书超度,并且告诉沟口家乡的寺庙已经转手给了其他人,沟口只有成为鹿苑寺住持这一条路可走。母亲对沟口一再灌输希望他成为住持的心愿,“要亲眼一睹你当上鹿苑寺住持的风采,我死才瞑目。”在此之前,尽管沟口渴望得到金阁的认同,但这种渴望是仰视的,母亲要求沟口成为住持的执念引出了拥有金阁寺的一种可能性,实际上拉近了沟口与金阁寺的距离,使得二者的矛盾激化开来。
在实在界,沟口与金阁之间的矛盾,即沟口自身的丑陋与金阁的绝对美之间的矛盾因主体的无意识存在但并不被察觉。沟口想要获得自我认同,要么毁灭美,要么得到美的认可。作为主体的沟口受到金阁绝对美的形象召唤的同时,却在现实中感知到被排斥的矛盾的灰暗的现实。根据拉康的观点,从统一的形象相对于破碎的经验而形成的那一时刻开始,主体即被建立成了其自身的一个竞争者。在沟口破碎的自体感及其想象的自主性之间产生了某种冲突,自我由此而产生。为了存在,沟口必得到金阁的承认。然而,这就意味着其主体的形象是由他者来中介的。于是,金阁就成为了他存在的保证人。沟口既依赖于金阁作为其自身存在的保证人,同时又是这个他者竞争者,凭借着这种模糊的主体建构的需要进入到想象界。
二.在他者中建构的主体
想象界是虚幻的世界,源自镜像阶段,即当婴儿第一次看到自己的镜中之像的时候,他将镜中之像等同于自己,建立起虚幻的想象自我。想象界不是一个阶段,为了保持自我认同,主体终生都会与想象界有所交集。拉康认为,自我是被建立在整体性与主人性的虚幻形象基础之上的,而且正是自我的功能在维持着这种一致性与主人性的幻象。换句话说,自我的功能即是一种误认的功能:它拒絕接受破碎与异化的真相。
在沟口成为金阁寺僧侣的不久之后,太平洋战争爆发了,美军对东京的轰炸使得日本人人自危,一时之间金阁寺所在的京都遭受空袭成了必将发生之事。空袭如一把达摩克里斯之剑煽动着沟口将个人的命运与金阁的命运息息相关。“在这人世间,我和金阁有着共同的危难,这激励了我。因为我找到了把美同我联系在一起的媒介。我感到在我和拒绝我、疏远我的某种东西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沟口想象着金阁毁灭的悲剧场面,感觉与金阁生活在了同一纬度的世界里,彼此亲近,已然成为一种完美的状态。然而,这种完美的自我是想象界前期的误认,婴儿满足于镜中之像,与之认同并认为其是完整的自我,这种完美的幻觉不能构成主体本身,也注定无法久存。战争结束后,现实中的金阁依然故我,它超越了战败的冲击和民族的悲哀,沟口与金阁在战争中建立起的平等关系立即崩溃了。战争的结束斩断了沟口想通过与金阁寺一同毁灭来实现人生价值的妄念,主体再次返回到由镜像造成的疏离和主体化、相互争夺存在的场面,便又推开了更多的不均衡的门。
自恋的镜中之像破灭后,矛盾关系凸显出来被主体觉察,沟口与金阁之间涉及承认的相互关系可以以黑格尔的主奴(Master/Slave)辩证法来解读。在这场关系中,沟口为主,金阁为奴,沟口想要获得自我主体,必须获得金阁的认同;反过来,金阁至上的绝对美的地位依赖于沟口的承认。这种辩证法的悖论在于作为主人的沟口看似可以随心所欲去做一切事情,但他的主体依赖于金阁对其身体缺陷的承认,所以沟口永远不可能是真正“自由”的,而金阁却不是以相同的方式依赖于作为主人的沟口,因为它具有存在的实体,且不被任何人所拥有,这样看来真正自由的不是沟口,而是不以人意志所转移,不属于任何人的金阁。沟口与金阁的关系根本上是一场欲望与承认的博弈,是一场殊死搏斗。在这场搏斗中,沟口在他者身上关照自我,希望从中获得将分散零乱的自我整合的契机。
进入金阁寺后,沟口与众人都是寺庙弟子而不再被他人另眼相待,也结识了人生中的两个重要的朋友——鹤川与柏木。鹤川是一个乐观单纯的少年,有着健全身体、伶俐的口齿的他却从未嘲笑过口吃的沟口,鹤川的出现为沟口打开一条与世界交流的通道,他一次又一次地将沟口阴暗的感情转变为温暖光明的语言。鹤川并不在乎沟口的口吃,他观察的是作为整体的沟口,他认为丑陋缺陷并不是决定沟口存在的关键。而柏木给予沟口的是一种与世界对立的,主体建构的新方式。天生X型腿的柏木承认自己的丑陋,并将这种丑陋确认为自己存在的证明和条件,毫不避讳地展露自我的欲望和卑鄙,他在沟口面前炫耀式地故意摔倒以博取一个美丽高贵女性的同情,在极度丑化自己后达成一种自我的神圣化。不同于沟口自卑于口吃而期望得到美的认同,柏木展示给沟口的是人生的恶意。鹤川与柏木映射出的是两种建构主体的方式,随着情节的发展,鹤川的突然死亡暗示了沟口对于毁灭性方式的选择。作为“恶”的代表的柏木为沟口引出了两位女性,在交往中沟口与他人、与金阁的矛盾越来越深化,生与美的对立越来越激烈,沟口的行恶及破坏的本质也越来越显露出来。
正如伏波娃在《第二性》中指出的那样,女性是永恒的他者,女性的身体代表了沟口对人生的向往、欲望。然而,沟口与女性之间的恋爱是徒劳的,他追求的是与女性的结合中看见充满幸福的自我的内心景象,对她们性的征服成为沟口自我认同的关键。近代日本文学中的男人们,善于向“女性”寻求解救自身的内心世界的方法。他们若不与女性结为一体,就无法看到自己的内心世界,将女性试作逃离现实的良药,是一种普遍的倾向。沟口对于女性的追求,不是恋爱,而是在女性身上实现自我主体建构的想象憧憬。沟口与公寓房东姑娘、插花师傅这两位女性都即将发生关系,但金阁寺每一次都会出现阻止性爱的发生,金阁作为一种绝对的静态的观念一次次妨碍着沟口进入那动态的、享乐的、作恶的王国。沟口被女性所拒绝,无法与女性发生性关系,如此一来,便无法处理自我主体与对象之间的想象关系,自我存在因欲望对象的拒绝而消耗殆尽。根据拉康对哈姆雷特困境的解释,可以得知沟口的困境就在于无法把自己从对金阁的欲望要求之中分离出来并实现自己的欲望。身为旁观者的读者清楚,并不是金阁纯粹的美阻止了沟口的欲望,而是沟口固着在金阁的欲望之中。沟口渴望与女性发生关系从而确认自我的存在,实际上表明沟口自体的位置已经丧失,即使最后沟口与妓女鞠子身上发生了性关系获得了这样一种认同,但这种认同是以自体成为他者为代价而获得的,沟口在追逐纯粹美的道路上最终成为了美的可悲的镜像。
想象界中的镜子不会显现主体的本质,在虚幻的影像中,沟口从他者身上得到的是关于自我虚构的形象,主体建构始终没有实现的可能。想象界要求作为“父亲”的第三者的介入,从而终结主体与对象的欲望闭环,迫使主体离开在他者身上寻找认同的想象界进入到象征界。
三.主体建构的失败
象征界即符号的世界,它是一种秩序,支配着个体的生命活动的规律。主体需要经由象征化的过程,从镜像中区分出作为主体的自己。在象征界,主体心理发展的关键是经历俄狄浦斯情节的阶段,进入到象征秩序之中。这里的俄狄浦斯情节是拉康对弗洛伊德学说的发展,它脱离了两性关系的局限,具有了更有开阔的文化视野。在俄狄浦斯阶段,自我与母亲是一个二元欲望闭环,只有象征着的第三者父亲出现,主体意识到自我缺失父亲所有的“阳具”,才能够从与自己镜像争夺主人性的决斗中脱身,在象征秩序下,进入稳定的交换关系支配下的社会关系的环中,对于这种缺失的承认便是象征界的过程。这个父亲名义的第三者并不需要一个真实的父亲或男性,其意义在于禁止孩子的欲望,使孩子意识到母亲还有其他的欲望指向,孩子也因此开始把自己作为和母亲相分离的存在而认同。对于沟口而言,禁止其欲望的第三者始终没有出现,沟口与金阁处于欲望的封闭结构之中,无法脱离开竞争关系,自我与他人的严重失衡,最终只能走向毁灭的道路——火烧金阁。
在沟口决意烧毁金阁的当晚,福井县龙法寺住持桑井禅海和尚来到金阁寺讲学。沟口在禅海和尚身上沟口体会到“一股老师所没有的朴素,父亲所没有的力量”,他担心着自己火烧金阁的勇气被禅海和尚的慈祥磨平。他向禅海和尚发问道:“您不觉得我是个平凡的学生吗?”“看来平凡,这是最好不过的了。平凡才好呢。”在禅海和尚看来,沟口与其他人并无区别,都是众生中一個平凡的存在。沟口对于美与恶的执着、对口吃这一缺陷的执着,最终都需归咎于自我认同的的焦虑。禅海和尚认为平凡存在的本身即是自我存在的证明,他令沟口放弃焦虑,归于平凡求得生存。这种教诲对于沟口来说无疑是巨大冲击,是对其想象界一切行为的否定,“我觉得我完全地毫无保留地获得了理解。我开始感到空白。”这种空白即是焦虑的空白,沟口以为自己在寻觅欲望,在自我认同上犹豫不决,其实寻觅欲望和犹豫不决这个普遍的平凡的行为,本身就构成了自我主体的建构。
尽管禅海和尚的教导振聋发聩,但此时的沟口已经无法回头,这种焦虑在更早阶段已经注定。正如拉康所言,不能以自己本身来度过自己一生的人类的悲剧在主体构成自己原型的那个初始的地方就注定了。沟口的悲剧是一个无法建立起自我认同的主体的悲剧,哈姆雷特行动延宕,在对存在的不断追问中错过了复仇的机会,但在戏剧的结尾他承担起了自己主体的责任,向国王刺出最后一剑完成了使命,但沟口却永远丧失了自我,这背后存在着战后日本社会的普遍原因。
在沟口的世界中,人物出场顺序看似杂乱、分散,实则遵循了严格的顺序性和逻辑性,其目的在于将沟口推入一种孤立无援的境地。第一次为他树立起美的概念的父亲早早离世,作为沟口与世界的译者的鹤川因为爱情的失败而自杀,他们的退场是沟口主体建构失败的预告。最后在沟口周围不断徘徊的是代表着野性与欲望的母亲,肆意玩弄他人感情的柏木,虚伪懦弱的寺庙老师以及任人欺辱的女性。他们在战后日本混乱、无序的社会现实下依次登场,表演着面对生活的无力感。战后的日本“没有钱,没有自由,也没有解放”,寺庙生活忙煞人累煞人。对于这种现实,沟口也有过反抗。当他第一次看到柏木自得于X型腿的缺陷,并用它来骗取女性同情时,他无法忍受并发出了祈祷:“我的人生要是像柏木那样,请务必保护我把。他那副情景,我是忍受不了的。”沟口无意发现了老师与妓女私会,在老师的抽屉中塞入妓女的照片以作威胁,希望以此得到老师的注意或批评,但为了维护高僧形象的老师一面对照片事件只字不提,一面将沟口驱逐出寺庙,切断了沟口生存来源。在此之下,尽管沟口能够意识到柏木的恶,认识到老师的虚伪,意识到想象界以他者为镜的虚幻和不切实际,但无法找不到解救的办法,只得挣扎与茫然,终于,在一个月明风急的夜晚,沟口点燃了金阁。沟口不再是顶着草鞋的赵州,而是成了挥刀斩猫的南泉。这变化的过程痛苦漫长,在与金阁、与他者的对峙交手中可以看见每一步的变化,金阁纵火最终成了沟口自己的公案。
沟口主体性建构的失败不止关乎个人,更关乎战后幸存的所有人。作者三岛在沟口身上寄予人性的思考是不难预测的。小说中小到对草叶末端锐角的思考,大到对自我认同的焦虑,沟口的主体建构的过程即是三岛对战后生还者建立真实自我的尝试与劝告——想象界至象征界的过渡,自我与他者共同发挥作用,才能不沉溺于虚幻的自我,进入到稳定的社会关系之中。
在三岛由纪夫的怪异文学中,主人公大多是沟口一样边缘化的人物,他们在日本战后的混乱和无序中游移不定,想要建立起完整的自我,却无可行之径。从完美的想象到毁灭的冲动再到自我的彻底丧失,沟口的主体建构之路见证了以他为代表的幸存者的痛苦挣扎。在小说结尾,烧毁了金阁寺的沟口仍然是那个充满矛盾的青年,他只顾拼命奔跑,却不知道自己该向哪里去。三岛没有对沟口进行任何的道德批判,他将这种自我与他者的对峙抛掷在时间的长河中,通过文学创作使人物具有了普遍性。
参考文献
[1][日]三岛由纪夫.金阁寺[M].陈德文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21.
[2][法]拉康.拉康选集.[M].褚孝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
[3][日]福原泰平.拉康——镜像阶段.[M].王小峰,李濯凡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4][英]肖恩·霍默.导读拉康[M].李新雨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
[5][英]亨利·斯各特·斯托克斯.美与暴烈:三岛由纪夫传[M].于是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0.
[6][日]水田宗子.女性的自我与表现:近代女性文学的历程[M].叶渭渠主编.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
[7]吴琼.他者的凝视——拉康的“凝视”理论[J].文艺研究,2010,(04):33-42.
[8]刘文.拉康的镜像理论与自我的建构[J].学术交流,2006,(07):24-27.
[9]崔健,舒练.拉康“三界学说”对意识形态理论的启示及其局限[J].世界哲学,2021,(01):102-109.
[10]黄丽娟.从拉康“镜像说”解读“他者”的含义[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2(06):86-87.
[11]郭勇.美与恶的辩证法:重读三岛由纪夫《金阁寺》[J].外国文学评论,2007,(02):64-70
[12]张文举.《金阁寺》本事、结构及意义阐释[J].外国文学评论,2003,(03):52-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