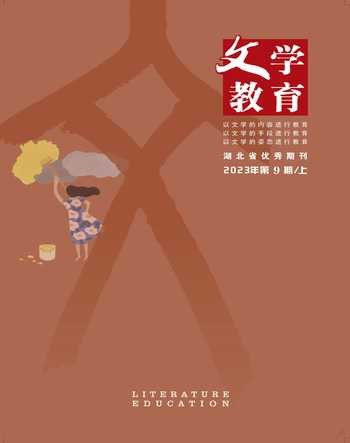杜甫诗歌中灯烛意象的内转性
郑丽慧
内容摘要:杜甫自宋朝中后期以来就负有“诗圣”的美名。古往今来,世人为他忠君报国的政治理想和忧国忧民的道德情操所动容。天宝六年至宝应二年,杜甫困居长安,后又遭遇陷贼为官。这十四年是他的关注点从上到下的时期,是他的思想从“致君尧舜上”到“穷年忧黎元”变化的时期。本文不将目光聚焦到他这一时期思想表现的人民性上,而是通过“灯烛”这一意象看到他这一时期思想的内转性。这一时期,杜甫的思想表现出崇高的特点也体现出普通人对人情温暖的向往,这绝不是杜甫这一时期思想的割裂,而是他的儒家意识形态和诗歌的审美话语融合影响下对人性美的希冀。
关键词:杜甫诗歌 灯烛 意象 内转
天宝六年到宝应二年,是杜甫困居长安求仕至安史之乱初期的一直以来被学者认为是杜甫思想转变的关键时期,大多数学者通常认为在这一时期,杜甫的思想从个体走向群体,融合个体生命与历史生命,他在政治失意中走向更为开阔的精神世界。并且杜诗的时间融合了历史,杜诗的空间从狭隘的朝堂走向广阔的底层社会。不过在这一时期,杜甫仍有一部分作品表现出不同于这一时期整体上的特点,如《羌村三首》、《赠卫八处士》等作品表现出杜甫这一阶段思想的内转性,他在诗作中流露出对自己年华流失命运坎坷的感伤、与友人相遇的相惜、家人相聚的珍惜、人间温暖的感激等细小的个人情感。从困居长安大量的干谒诗到战乱逃亡、陷贼为官的部分抒发个人情感的诗作中都出现了“灯烛”的意象,在“灯烛”意象的观照下,我们看到了杜甫不只有“圣人”的一面也有一个生活在安史之乱时期困窘的普通人的一面。本文将以“灯烛”意象来参照自天宝六年到宝应二年时期杜甫部分诗歌具有的普通人情感的共鸣性特点和其中表现对人性美的希冀情感。
一.灯烛意象的特点
中国较为成熟的灯具最早出现在春秋时期,先民们把蜡与脂肪一类的东西涂抹在树叶上,把涂抹好的树叶捆扎在一起,做成照明用的火把。[1]《楚辞·招魂·第九》中记载“兰膏明烛,华镫错些”,《说文解字》也记载:“烛,庭燎火也”,这些无不说明灯烛的诞生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在汉魏时期前,灯烛只是作为物象而不是意象出现在前代的文学作品中。汉魏时期是文学走向自觉的时期,灯烛物象在这一时期和诗人的主观情感融合,渐渐地从物象走向意象。《古诗十九首·生年不满百》“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中“烛”就不仅仅是物象,秉烛游有及时行乐之意。
隋唐时期,生产力快速发展,灯烛也逐渐进入普通人的家中,灯烛意象开始被诗人们大量使用,在全唐诗中共有1255处写灯烛。孟浩然的“就枕灭明烛”的渔船明灯,李商隐的“何当共剪西窗烛”的夜雨残灯,杜牧“银烛秋光冷画屏”的孤清宫烛等,以上所举例的灯烛意象很明显和诗人的主观情绪向融合,在一定程度上灯烛意象总能使诗人们抒发个人的情感,黑夜、单人、灯烛,这些要素的汇聚,总会使诗人们想到在外漂泊的自己、远方的家人、难酬的壮志、难见的朋友。黑夜,诗人与灯距离越近,越靠近光,就会愈发思念遥远的人和事,物理距离的靠近缓解不了诗人内心的孤独,心理距离在不断被诗人放大,诗人的思绪也会从宏伟壮大的外物感观走向个人私密的体验感受。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篇记载:“是以陶鈞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积学以储 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然后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意象在文章中有重要的作用,在心中得见意象后而运斤,胸有成竹才能文质俱出。美国诗人庞德在《兆牛辣意象主义者的几个“不”》中认为:“意象是一刹那间思想和感情的复合体。”同时,物象能较好地适应辞令表达的需要[2],灯烛物象具有隐喻的特点,提起灯烛物象,读者在潜意识中会将想到烛花时联想到泪珠。P·E·威尔赖特在《原型性的象征》中指出:“在所有的原型性象征中,也许没有一个会比作为心理和精神品质的‘光更为普及。”人类本就有趋光的意识,灯烛会被诗人有意识地运用表达心理流露。故意象本就有抒发诗人内心个人情感的倾向,灯烛这一意象具有隐喻特点使诗歌有从外物走向私密个人的倾向无疑能更好地观照诗作中所流露诗人的情感流露和文人思深。杜甫《酬孟云卿》:“乐极伤头白,更深爱烛红”,也说明漫漫黑夜,游子独坐,白头烛影,人心中无法不有一点私人情绪,故本文选用“灯烛”意象观照杜甫诗在天宝六年至宝应二年表现的杜甫思绪的内转特点。
二.困居长安期间灯烛意象中内转变化
天宝六年,正直壮年的杜甫并没有听从李白的劝告,抱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奉儒守官的理想抱负到了长安,李林甫“野无遗贤”的权谋一下子击垮了他通过科举为官的道路信念,“葵霍倾太阳,物性固难夺”的政治理想使他走向了干谒从官的道路,在这一时期他创作了大量的干谒诗,干谒诗自天宝六年到天宝十六年则现颂美到自诉的变化,这种变化是杜甫的儒家理想的变化和视野的下沉的体现。
诗人在干谒时不免进入长安高门大族的宴会中,夜宴是长安文化中不可或缺的,有夜宴就有烛光,有灯。这里的灯光既表现了高门大户的财力又表现了时间的不断的流逝,多是外指性的,诗人的情感我们始终是隔了一层并不看得清楚。公元746年至公元751年,诗人的重心多在歌颂豪门大族,而把抒发自己的情感部分压缩,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诗人逐渐认清的腐朽的长安社会,找到了真正的自己,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夜宴左氏庄》“检书烧烛短,看剑引杯长”中的烛短,暗示了检书的时间之长和时间的不断流逝。《杜位宅守岁》“盍簪喧枥马,列炬散林鸦。”宾客友人马儿喧嚣,灯火惊散了寒鸦,诗人不由得想到自己已经四十岁了,却功业未就。灯惊了乌鸦,也引发了诗人对自己身世前途是思考。这一特点在《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其十》“自笑灯前舞,谁怜醉后歌?”中也表现出一定的相似性,灯光照亮了宴会上舞女的窈窕身姿,但也映衬了灯光熄灭后的“残杯与冷炙”,诗人明明以干谒为耻,却不得不为的“到处潜心悲”私人情绪也愈加凸显。灯前越是辉煌,灯后也是悲凉,灯分割出来两个世界,这里已经隐隐暗含诗人的批判。这与他之前的《赠特进汝阳王二十二韵》“樽晷临极浦,凫雁宿张灯”中灯只为表达汝阳王家宅之豪完全不同。《今夕行》中“今夕何夕岁云徂,更长烛明不可孤”中烛火越漫长,诗人就越孤独,诗人不再同质化地写干谒对象的烛写其家宅写其家世传承,而是真正我手写我情。[3]《醉时歌》“清夜沉沉动春酌,灯前细雨檐花落”,夜沉烛花落暗示诗人的孤独、苦闷,联系下句“但觉高歌有鬼神,焉知饿死填沟壑?”诗人不顾其他只管抒发自己的苦闷,诗情再也无法被抑制了。
这种从颂美到自诉的变化在《赠韦左丞丈济》、《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也有体现,前者诗人把重心都放到颂美,先是歌颂干谒对象的才华品德,然后说明自己现在困窘的处境,最后才点明希望援引的希冀,四联都在歌颂韦济,后四联表明自己的落魄,失去了刚开始在《河南韦尹》将自己自比扬雄等人的自信,不过这种自信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找了回来,诗人改用五古,请丈人静听自己的比肩扬雄、曹植的才华、尝尽残杯冷炙的悲凉和一腔热血抱负,只在末尾向韦丈人表示真挚的感谢,“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训?”的末句一扫沉疴,盛唐自信高扬的精神面貌令人精神一震。
从干谒诗中灯烛意象的转变,我们看到杜甫个人精神的自诉,“致君尧舜上”的政治抱负使他不得不干谒求官来实现自己的儒家理想,困居长安的几年现实经历告诉他在黑暗的长安社会,他能做的不过是一个小吏,连独善其身都做不到,如何挽救不了大厦将倾的盛唐,但杜甫的伟大就在与儒家权利形态的似连非连,他清楚明白自己仕既不成的现实,却无法割舍,故“隐又不遂,百折千回”,而就在曲折中缝隙中高歌已悲,独有一番魅力。[4]
三.安史之乱初期灯烛意象的个人内转
公元755年十一月,安禄山起兵范阳,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暴发了,杜甫的逃亡和被掳生涯正式开始。公元755年十二月,此时的杜甫正在归家探亲,但突如其来的人祸打乱了他的计划,叛军此时已经攻陷洛阳、潼关,叛军即将进攻长安,杜甫只好暂且投奔在白水县的舅舅,白水县沦陷后,杜甫携家眷随从洛阳向西北方向逃亡数万难民开始向西方奔逃,杜甫一家经历千难万险来到了漉州城北的羌村,在这里暂且安顿下来。这一时期是杜甫思想和诗风变化的关键时期,之前将目光投向君王朝堂的杜甫真真切切地和数万难民有了相同的经历。文学史上关注到杜甫这一时期诗风的人民性特点和杜甫诗的史诗品格,但在这一时期,杜甫在将目光向下的同时也在向内,杜甫流露出对人情温暖的衷心赞美和感动。
《羌村三首》其一中“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的烛是沟通男女主人公的媒介,由于兩人长时间分离,一时相见,激动欢喜都化成沉默,只有情思在双方眼神之间流转。“灯烛”在黑夜中将对方的容颜照得愈加清楚,诗人反而会因长久分离还以为与妻子在梦中相见,等到认识到一切不是梦,才感受到与妻子团聚的欢喜。诗人的情感此时和“灯烛”融合在一起,情景相融,“灯烛”温暖的烛光在黑夜中照亮彼此,诗人的思念越深刻,与家人相见,反而越感到如梦寐一般。“灯烛”在整首诗中成了诗人思绪内转的导向物,诗人秉烛相对,灯烛提供了一个温馨的氛围,杜甫抒发普通夫妻在乱世中再次相见的儿女情思。
《赠卫八处士》中杜甫向内转的趋势更加凸显,“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杜甫与友人再次相见,如同“参与商”相遇,已是极大的幸运。乱世相逢的两个人在夜中灯烛下回忆往昔,他们的回忆勾连两个时期,两人初相识和两人今相逢,杜甫在回忆中抒发人生中的好友一旦道别也不知何时再见的伤感,发出感慨:“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这一份深厚友谊相聚的时间是短暂的,而那份情感却会在一生中温暖诗人的内心。“灯烛”在两人的谈话中越烧越短,预示着留给二人相聚的时间越来也短,此时“灯烛”在隐隐之中传递给诗人一种友人之间难以相逢的伤感,也说明了乱世之中一份真挚的友情的不易和杜甫对友谊的珍视。
《冬末以事之东都湖城东遇孟云卿复归刘颢宅宿宴饮散因为醉歌》中,诗人表露对友人的感谢和赞美。“刘侯叹我携客来,置酒张灯促华馔”一句以白描的手法,点出刘侯的动作“置酒”、“张灯”、“促华馔”,这些动作表现刘侯对杜甫的到来,非但没有表现不愿,反而真心地为杜甫接风洗尘,这一点人情温暖在安史之乱时期是极其可贵的。这里的“置灯”不同于困居长安时期的“灯”,同样是高门大户,杜甫感到却是人与人之间温暖的人情美,而不是自己不得意的落魄,同样的意象在不同时期带给杜甫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
这一时期杜甫在向下看的同时,也在向内转,他用细笔描绘与妻子相遇、与友人重逢、受到他人帮助的场景的诗句,传递给我们的是一个普通人在乱世遭遇不幸之后所感受到的人情温暖的美,这种美虽然没有“三吏三别”历史感和鞭笞上层权贵的《丽人行》的深刻性,却具有共鸣性和普世性的。
杜甫在文学史上总是被当做圣人对待,不少研究者会忽略他诗中的平常人的感情抒发。杜甫此时是一个身居卑位的普通人,他真真切切地和数万难民一起逃亡,所以他懂得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民相聚不易、温暖难寻,他这一时期向内转趋势的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他追求人性之美,而这种美实际上是一种大爱,若所有逃亡的难民都如杜甫一般得到他人的帮助、与朋友、妻子相逢,人人之间守望相助,就不会有人与人之间在动乱下的易子而食、互相杀掠等行为。
所以杜甫这一时期的诗歌在向下同时也在向内转并不意味杜甫思想的割裂,在本质上还是儒家权力话语体系下困顿小我的忧国忧民的情结导致的结果。这一向内转的特点又和杜甫诗歌“诗而入神”的境界分不开[5],他不是有意为此而是他心中忧国忧民的儒家意识形态已经和诗歌的审美话语相融合。
以“灯烛”意象参照杜甫困居长安至安史之乱初部分诗作出现的内转性特征,我们看到这一时期杜甫作为诗圣思想的崇高的同时,也应关注到他自身对年华已逝、志向未成的苦闷、友人相遇的相惜、家人相聚的珍惜、对人情温暖的衷心赞美和感动等私人情感流露。这些私人情感流露与他这一时期思想崇高并不矛盾,这不是杜甫思想的割裂,而是他的儒家意识形态和诗歌的审美话语相融合下“诗而入神”的境界的表现,能帮助我们从新的角度发现杜甫困居长安至安史之乱初诗歌中的思想新质。
参考文献
[1]熊月之.照明与文化:从油灯、蜡烛到电灯[J].社会科学,2003(3):94-103.
[2]段宗社.李梦阳“重情”诗观评议——兼论七子派评价中的一个缺失[J]. 学术论坛,2016,38(1):119-124.
[3]冯臻远.从赠韦左丞丈济看杜甫长安十年的干谒[J].古典文学知识,2020(3):31—36.
[4]傅其林.论杜诗“沉郁顿挫”的审美意识形态张力·当代文坛·2010.6.
[5]莫砺锋.杜甫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