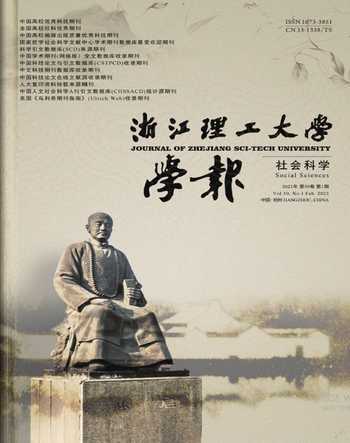马克思主义异化论视域下人工智能的“人文困境”与反思
张海涛 周桃顺
摘 要: 人工智能技術的资本主义应用,既造成了人机边界的模糊、算法偏见的盛行、价值鸿沟的扩大和权责归属的争议等问题,又造成了人的主体性困境,即技术物化对人能力的“殖民化”和对人本质的异化,工具理性对人理性完整性的解构,以及主体信息的去隐私化抑或透明化。从马克思主义异化论视域来剖析人工智能引发“人文困境”的根源,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从演化到进化的视角,揭示人们对人工智能这一新事物认识的矛盾;二,通过对技术理性“合理化”的批判和数字资本剥削本性的揭露,阐明人的种种异化归根结底摆脱不了资本主义的束缚和羁绊。总之,意欲消解人工智能引发的“人文困境”,既要坚持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构建完备的伦理准则和道德规范,又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坚持技术向善和技术求真。在人同智能技术的共处中,自觉塑造自我主体地位,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牢牢将人工智能掌握在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手中。
关键词: 人工智能;主体性;异化;技术理性;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 B03;TP1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2023) 02-0096-07
The "Humanistic Dilemma" and reflec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theory of alienation
ZHANG Haitao, ZHOU Taoshun
(School of Marxism, Xi′an Shiyou University, Xi′an 710065, China)
Abstract: The capitalist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has not only caused problems such as the blurring of human-machine boundaries, the prevalence of algorithmic bias, the expansion of the value gap and the controversy over the ownership of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but also caused the dilemma of human subjectivity, that is, the "colonization" of human ability and the alienation of human essence by technological materialization, the deconstruction of human rationality by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nd the de-privacy or transparency of subject information. To analyze the root caus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alienation theory, we can start from two aspects: Firs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volvement to evolution, the contradiction of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s a new thing can be revealed; second, through the criticism of the "rationalization" of technological rationality and the exposure of the exploitative nature of digital capital, it is clarified that the alienation of human beings cannot be freed from the shackles of capitalism in the final analysis. In short, to dissolve the "humanistic dilemma" caused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e should not only adhere to the unity of technical rationality and value rationality and build a complete ethical code and moral norm, but also give play to people′s subjective initiative and adhere to technology for good and technology to seek truth. In the coexistence of people and intelligent technology, we should consciously shape the status of self-subjectivity, give play to the subjective initiative of people, and firmly grasp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the hands of the proletariat and the masses of the people.
Key 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ubjectivity; alienation; technical rationality; Marxism
作为人类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标志性产物,人工智能技术正在以颠覆性、革命性、指数级飞跃式发展,在大数据处理、生物医药、智能机器人、无人驾驶等领域[1]取得令人叹为观止的成就,解构和重塑着人们的生产生活。人工智能在给人类带来智慧生活的同时,也带来了现代性智能危机,引发了诸多“人文困境”。这种困境是围绕核心的人这一主体引发的多方面危机,不仅表现在交往行为中人的话语权、隐私权被剥夺,消费生活中人的主导性丧失,技术异化致使人的道德沦丧,而且人的情感和理性也被瓦解,使得主体性的人深陷于算法设计的虚拟演绎和桎梏偏见之中。尤其是当下人工智能“超越论”和“本体论”的兴起,更强调人工智能的功效,忽视了把现实的人作为主体尺度去评价这种功效,人反而被奴役和物化。
目前,学界大多数学者从认识论、价值论和本体论的视角探讨人工智能同人的关系问题,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例如,欧阳英[2]认识到,人工智能是人脑的智能异化物,会造成人脑同自己脑力劳动、智力成果和类本质的异化。孙伟平[3]指出,人工智能对社会发挥着积极的效应,同时必然会挑战既有的人的价值,引起人们的担忧。余乃忠[4]则认为,机器在剥夺了人的劳动权和隐私权的同时,在思想根基上动摇了人类对自身的信念,等等。大多数学者从人工智能外在的社会和科技、内在的认识论和本体论的角度,聚焦于人工智能的起源、发展及人工智能同人的智能相比较层面的研究,很少有学者从人的主体性异化角度对人工智能展开系统研究。本文在马克思主义异化论视域下分析人工智能引发的人的主体性危机,探讨和揭示这种人文危机的根源,并提出治理危机的理路与方法,旨在通过对资本逻辑的批判,解蔽人被智能体异化的事实,构建科学合理的伦理机制,促进人机和谐发展,降低人的物化程度。
一、人工智能发展导致人的主体性缺失
人工智能作为技术进步呈现的新形式,依然没有离开马克思对于技术异化的批判。马克思在谈及科学技术对人的异化时,提到统摄生产的技术不断凸显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存在和意义被削弱,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5]580。人们出于物质利益和感官享乐的需要进行无限度的技术实践活动,致使工具理性与人文价值割裂,造成了人的主体性意义被忽略,而对最终价值标准的放弃,使得人工智能技术存在的“隐忧”逐渐显现。
(一)物的人格化对人本质的异化
人工智能技术作为人的对象性社会知识的展开力量,是人的物化本质确证的基本依据。技术诞生伊始,人类由最初直接意义上的生存活动,很快被卷入社会分工生产之中,机器和资本的结合使得机器具有了资本的属性。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人工智能技术是生产剩余价值的关键手段,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高强度的工作使工人感到疲惫,找不到劳动带给他的自由和富裕,反而“我们看到,(机器)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6]776。主体的人和客体的机器不但没能统一,反而走向对立面,客体的机器转变为外在的力量控制、奴役和驱使着主体,使得主体不断被物化和外化。异化的技术日趋自主化,它侵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部分,使人类日益在技术的淫威之下无所作为[7]。人的价值世界和意义世界受到无情的挤压,人自由自在的追求受到巨大的威胁。
人工智能正在实质性地改变着“人”。通过产品功能实现特定虚拟主体的表达,设计者按照人的智能和功能模型,仿制和打造出具有高度自主性和可感知性的智能机器,并赋予它自我设定的某种身份和角色。试想未来强人工智能时代,智能机器虽不具备客观存在的实体生命,但在外形上似人,声音上动听如人,行为和智能水平都和自己一样,令“自己不朽”,甚至可以“编辑人”“控制人”如此种种。人和智能机器的生命界限在哪里,究竟如何定义“人”和人的本质,如何处理人机关系的价值准则,都要重新认识。2016年,欧盟委员会鉴于人工智能特殊的拟人格性,赋予其劳动权、著作权等相关权利和义务;2017年,机器人Sophia(索菲亚)成为沙特阿拉伯历史上首位获得公民身份的机器人。如果获得公民身份的机器人出现破坏公序良俗、伤害他人、触犯法律等问题,该如何判定责任主体呢,这都需要重新认识。人工智能虽然不具有完整的社会历史性和主观能动性,但是会造成人实质性的削弱,对于属人的责任与义务、道德与伦理等价值理性的判定构成挑战。
(二)技术物化對人能力的“殖民化”
人工智能技术是对人的眼睛、皮肤,特别是大脑器官的延伸,使人的结构不断完善和能力获得跃迁式发展,促进了人的生命意志的拓展。然而,“科技让生活的时空被压缩,它承载了人类太多的欲望,它让人类对周遭的现实钝化麻木而沉浸在虚空的幻想的世界”[8]。智能技术的不断迭代升级,致使作为谋生手段的劳动也被机器取代,去技能化使得工人的劳动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劳动,会加剧社会失业风险。尤其是简单、重复、机械的工作,不需要太多情感交流的工作,以及不需要太多人类灵感、智慧做出综合判断的工作[9]。像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公司普通的职员、评估工作的评估师等等,面临可取代的趋势和风险。Kuhn[10]指出,科学的学习是通过教科书为基础的严格训练实现的,目的在于让学生掌握一套通用的科学知识体系,是一种汇聚的思维方式或创造性的思维模式,而非发散性的。人工智能教育产品的广泛应用,虽然告别了死记硬背的非创造性学习,但是技术的排他性使人的基本技能退化,以至于人们出现提笔忘字、不会找“度娘”的困境和焦虑。技术的进步不是塑造和发展人的技能,而是使人沦为“多余的人”。
此外,人对智能产品的依赖过度,容易产生惰性。人工智能虚拟技术的发展,模糊了虚拟和现实的界限,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冰冷的技术系统同各种终端打交道,淡化了真实世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对话,使得一些人认为虚拟的世界才是真实的、可信的。长期沉浸在这种虚拟感官的演绎下,人感性器官的社会性会逐渐退化,人的天赋秉性、主动意识和自觉担当会消失于无形[8],呈现出异化和畸形的样态,人成为“单向度的人”,社会也成为“单向度的社会”。人工智能引发了阅读方式的变革,拓宽了阅读场景,丰富了阅读体验,使得碎片化阅读成为学习和休闲的重要方式。诚然,碎片化阅读往往给人以服从和暗示的作用,容易让人产生心理依赖和精神焦虑。用户每天要从数亿级的信息中筛选出符合兴趣,思想深刻的高质量信息。眼花缭乱的讯息令人身心疲惫,对阅读产生厌恶和抵触,导致人的创造性、想象力和审美力的退化以及自身感性经验积累的贫乏。碎片化的信息支离破碎使人无法专注,消解了人的求知欲望和热情,阻碍了人对自由的真实追求。
(三)工具理性对理性完整性的解构
所谓的工具理性,就是通过实践的途径确证工具(手段)的有效性,其核心是对效益的最大化追求。工具理性的膨胀致使理性由最初人的解放工具退化为统治人和自然的工具。
在工具理性的支配下人工智能技术发生异化,导致人的理性判断力和情感被解构。一方面,在当前新媒体话语公共空间下,各种话语权涤荡博弈,鱼龙混杂的信息不断被价值化,使得群体的价值观和自我的价值观被迫分离,自我的价值的实现被削弱和同质化。在混杂的信息辨识上,主体的自我愈来愈急功近利,看重结果而忽视过程,造成问题辨识的错位,思考的方法简单狭隘。此外,科技利己主义者的伪善造成了审丑文化的盛行,人们对于何为真善美的判断标准逐渐丧失,畸形、怪诞和丧,从来都不是文化的主流,却无形中让很多人欣然接受。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使得人们的真情实感反而被异化了,“虚假的需要”取代了“真实的需要”,资本家蓄意营造出消费和幸福等同起来的假象,暗示只有不断消费才能获得幸福和快乐,而提倡节俭和忍耐是反人性的[11]。致使人失去了对于“物”原有尺度的把握,传统美德也不再从情感上被需要。
此外,人的认知偏差导致人理性完整的消解。工具理性造成技术主义的极端,对人自身的崇拜转化为对技术的崇拜,人沦为现代机器的附庸,人的精神价值被解构和物化。技术的无限增殖刺激着资本家贪婪的欲望,致使工具理性割裂了人与自然的生命联系。人们盲目地开采和攫取地球资源,使得有限的资源和无限的技术进步之间矛盾的张裂,打破了人与自然之间脆弱的平衡,导致了20世纪以来肆虐全球的生态破坏、环境污染、核辐射等问题,直接危害着人类的生命和健康。
(四)主体信息的去隐私化抑或透明化
人工智能技术高度依赖丰富的计算资源和海量的数据,学习的过程仍然是个“黑盒子”,由此引发信息主体自主权不足、个人信息权利边界模糊、信息隐私被侵害、信息霸权等问题。隐私权作为人的一项基本权利,在智能时代用户的一切信息都可被记录、可追踪,呈现出主体信息的去隐私化抑或透明化。各种数据采集设备和系统无时无刻地获取着个体详细的信息。当用户使用智能产品,系统会根据用户的兴趣爱好,全面掌握用户的身份信息、行为习惯、消费心理等,精准把控用户的动态,及时推送相关服务。这不仅导致处理私人事情的自由和时间被干预,而且还会泄露用户的秘密,例如生理缺陷、征信失信、既往病史等。
根据墨菲定律,凡是可能出错的事总会出错。人工智能技术的算法程度越高,意味着构建数据算法的逻辑越复杂,从而出错的概率就越大。智能产品之所以能够进行复杂的判断和抉择,其核心是依赖海量的数据资源进行精密的智能运算,但在这种算法的逻辑语析下,会导致用户信息的透明化和泄露,使得私人的领域被打开,个人的隐私随时有被公之于众的风险。2020年1月,全球最大的视频会议应用Zoom被爆1.5万用户视频被泄露;2020年6月,加拿大写作博客平台Wattpad数据库被入侵,导致2.68亿条用户敏感信息泄露;2020年10月,美国VoIP服务供应商Broadvoice泄露超过3.5亿条客户隐私记录,等等。这些问题的出现,一方面源于系统存在的漏洞,将掌握的个人信息泄露出去;另一方面,不法分子的利欲熏心,利用系统漏洞或黑客技术非法获取用户隐私以牟利。
二、人工智能“人文困境”根源的科学揭示
人工智能技术作为科技创新的产物,在资本逻辑统摄下带来了诸多的智能危机,使人的主体性遭受到不确定的风险和挑战。不管是当前流行的技术悲观主义的“终结论”,还是乐观主义的“人本论”,二者争论的交锋都畅谈在未来人工智能是否具有“人属性”的喧嚣,却忽视了从现实的基本问题中去揭示和阐发人工智能技术的本质和“人文困境”产生的根源,以此回应现实的困顿和需要。
(一)从演化到进化的突围
纵观人类发展的历史,无论人类的文明演进史,还是科技发展史,归根结底是人类能力不断外化的历史。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各种技术的发明本质上是人类自己器官的延伸,也就是用外物来强化自己的功能[12]。人的手脚等器官是最原始的劳动工具,有着诸多的天然局限性,为了克服先天的局限,人类不断寻求外物来弥补局限。于是机器的发明,大大节省了体力和提升了效率,克服了人體能的局限。然而,以往技术的出现仅仅替代人的肢体,而人工智能技术则试图取代人的大脑。人工智技术能够精通连人类一直引以为傲的琴棋书画,甚至可以模拟人的表情,同人们风趣幽默地交流,彻底颠覆了人们的认知。可以说,以往人类生物意义上适应环境的变化,只能称之为演化,而人工智能时代人的发展才算得上真正意义上的进化。
人们对于发展着的新事物,往往难以把握其发展方向或难以预料其发展结果,难免会产生抵触的情绪和怀疑的态度。虽然智能技术不会像霍金的“替代论”、赫拉利的“无用阶级论”以及库茨韦尔的“奇点论”等为代表的悲观主义者们宣扬的那样——人工智能未来终将进化到超越人类智能,成为人类的终结者。然而,由于他们的忧虑和恐惧源于把人的价值实现限定在资本主义制度及其观念框架内,因此他们对于人工智能这一新事物的认识明显不足。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选择和创构的过程,是一个新技术持续广泛延展和强化人能力和智力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技术的进步是人特有的进步方式,技术是人本质力量的昭示。技术异化这一历史事实必须从历史的合理性和暂时性上加以理解。一方面对技术过度的依赖,使人遗忘自身的存在,甚至丧失人性的坐标和尺度,要警惕技术的隐性风险。另一方面,通过技术更好地反观自身,利用技术不断创造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条件。
(二)从技术理性到技术异化的“合理化”
技术理性的本质是理性统治人的过程。技术理性由著名学者哈贝马斯[13]提出,他认为技术规则是一种合乎目的和理性的实践性活动,把人的劳动或理性活动也视为工具的活动。霍克海默也认为技术理性会带来物化,技术不仅仅是统治社会的工具,更是统治人的工具,表现为技术理性同化了劳动者的革命意识和斗争精神、同化了文学艺术的多元化以及同化了社会的意识形态[14]。随着人力支配自然能力的增长,社会对人的支配也愈发严重。短视频、网络游戏等娱乐形式不断入侵着人们的闲暇时间,太多的感官刺激造成了人们精神的贫乏与情感的空虚,人们的精力被分散,人的感觉、语言和思维不断被物化和异化。
技术理性只问事实、不讲价值的实用功效观是技术理性的深层思想根源。技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打上异化的烙印,在技术理性的统治下,人的异化成为合理的“存在”,个人为了实现眼前的物质利益而喧囂尘上,甚至枉顾道德和伦理观的约束。技术的异化也促成了人本身及人与人关系的异化,马克思指出:“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6]51机器的生产改变了人类劳动自身的基础秩序,人沦为资本增值的工具,技术不再是征服和改造自然的工具,而成了支配和奴役人的外在力量以及资产阶级统治合理性的辩护工具。同样,人工智能技术在资本逻辑控制的社会下,人的种种异化归根结底摆脱不了资本的束缚和羁绊。
(三)从资本的重技走向资本的“尚艺”
技术的异化是在工业大生产中诞生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机器的资本主义运用是造成劳动者困境的根源。19世纪的工业革命是机器对人肢体的肢解,人的体力劳动过程被拆分成了若干个独立的动作,人成为机器的附庸,机器及其整个生产过程成了剥削和排斥劳动者的异化力量。人工智能时代是智能技术对人大脑的解构,机器善于把控人的情绪和心理,模拟人的语言和智能。资本的剥削手段也从传统暴力范式转向个性协作,剥削的手段越来越隐蔽和巧妙了。智能革命催生出了数字平台经济的兴起。平台资本家建立全球数字工厂,用户的智能设备即机器,资本家提供的交互平台即工厂,用户扮演着工人和消费者的角色,用户使用网络产生的数据过程即为工人的劳动过程。本该网络数据归用户个人所有,实则被利益驱使的平台资本家无偿占有。用户(被剥削者)沉浸在资本家所营造出的个性化多样性消费的行为和思想形式的快乐幻想之中,陷入一种心理上的“心甘情愿”和主动接受“剥削”的状态。
数字经济利润逻辑统摄下的智能化资本的突出特征是:人的精神被物化,人的自由意志被束缚,人的心智和能力被资本吞噬,人的主体性和独立性被消解沦为新型异化的工具。相应的新型劳资关系亦呈现隐匿化,使得剥削行为无形化,凭借用户感官很难察觉,造就了一种更加隐蔽和无感化的剥削,实质上是资本家剥削的手段更高明,相比传统的剥削程度有过之而不及。这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只要资本统摄劳动的私有制还未消亡,“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15]的现象就不会消失,劳动价值论这一批判武器就不会过时。
三、人工智能“人文困境”的人文反思
人工智能也存在克林格里奇困境(Collingridge′s dilemma),即每一项技术创新都必然给社会带来二重性矛盾。但人是科技的掌控者,有着天使和魔鬼的区别,当人的价值观天平倾向于自私自利,把自我和他人的关系对立和割裂开来,就会导致技术产生负面影响。因此,人工智能作为科技创新的产物,要保持技术理性,趋利避害,构建完备的伦理准则和道德规范,将这推动社会变革和历史进步的力量,掌握在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手中。诚如马克思所言:“科学是历史有力的杠杆,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16]
(一)坚持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
理性世界打造的现代工业化社会的“铁笼”,使人丧失了完整性和丰富性,工业规律支配的世界,成就了人,也异化了人。工具理性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工业化繁荣和巨大财富,也使人们逐渐产生了重工具性和功效性的普遍拜物的行为和心态。价值理性在工具理性的膨胀和僭越下日益衰落,造成的后果就是人性的贫乏和人的物化,究其根源就在于技术手段的目的化[17]。爱因斯坦曾告诫人类:“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目标。”[18]他也意识到了工具理性支配下人被物化的问题,始终强调要重视人的主体性和人本性的复归,只有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二者获得相对平衡的时候才能缓解这种矛盾。黑格尔也曾说过“熟知”并非“真知”。人类所追求的东西一旦缺乏理性和价值关怀,就会变成一种盲目的、危险的东西,会造成难以预料的后果。当前人工智能技术时代,工具理性的蔓延虽然给社会带来了丰硕的成果,但社会缺失的却是责任与义务的承担、道德与伦理的价值关怀。马克思也指出,在利己的需要统治下,“外化的人、外化了的自然界,变成可让渡的、可出售的、屈从于利己需要的、听任买卖的对象”[6]54。人们把需要理解为资本家主观的欲求,忽视了劳动者主体的价值本真,导致异化的人遗忘对自身生命意义和价值的追问与观照。因此,必须要从价值尺度和人的主体性去呼唤价值理性的复归。
重构价值理性的本质是重建人文精神。人文精神的内核则是强调人的主体性,注重人同自身、人与人和人与自然关系的调和。人工智能负效应的显现就在于发展着的现代科技缺少人文精神的注入。工具理性片面强调人的自身利益,在资本增值效用的驱使下,人文精神难免失语和缺位。这就要求人类从工具理性的“经济人”转向价值理性的“伦理人”,把人的价值实现从资本主义制度及其观念框架中解放出来。消除人工智能技术的异化,必须坚持人文精神的正确指引,冲破西方社会将个性自由视为人的解放的观念。因此,既要防止个性自由成为人异化的通道,又要坚持真善美的价值原则和遵循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准则,实现人与技术的协同进步和共同提升。
(二)坚持科技伦理与道德规范相结合
人工智能技术造成了人机边界的模糊、算法的偏见、价值观的错位等问题,带来了一系列的科技伦理风险和道德冲突。这就需要构建科学合理的伦理机制和道德准则,保障人工智能技术的良性发展。首先,优化人工智能的伦理设计,注重前瞻研判人工智能带来的伦理挑战。从人道主义的角度设定人工智能的权限,具体而言,就是将人的主体伦理价值观(例如,法律、道德、人文关怀等规范和价值信念)嵌入人工智能伦理系统中去,明确和完善人工智能的伦理道德权限与责任,使人工智能产品成为具有自主伦理选择和道德规范的智能体。
其次,制定人工智能行业道德规范,建立科技人员自律制度。责任是人工智能研发和应用过程中基本的伦理原则。人工智能作为被研发的产品,其生成过程隐藏着复杂的人际关系网。智能产品是否安全可靠、高效和人性化,离不开研发人员的所思所想和所作所为,研发人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产品对个人和社会造成的影响。为避免人工智能体带来的负面效应,人工智能研发人员必须具备高度的伦理价值观和道德修养,本着对人类负责和服务的态度,主动承担起尊重和维护生命的道德责任和使命,克服技术盲动和技术滥用造成的伦理问题。
最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是多源聚集的结果,离不开社科、人文、自然等学科的交叉融合。人工智能的自反性治理不足以为伦理构建提供原则基础,因此,技术伦理治理的跨学科研究尤为必要。人工智能的伦理道德构建需要借鑒一系列学科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更需要各学科研究人员的通力合作。此外,还需要扩大人工智能治理的公众参与度,广泛听取不同领域、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专家和公众的意见,建立科学的预警监管机制,划出人工智能技术不可逾越的红线,最大限度地防范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伦理冲突,实现人工智能可持续发展和服务于人类的根本目的。
(三)科技向善是人类解放的必由之路
科技向善是指科技要合乎某种善的观念和行为,以人的主体性需要为价值尺度。向善是科技伦理尺度和标准的根本依据之一。亚里士多德[19]也曾言“一切技术,一切研究以及一切实践和选择,都应以某种善为目标”。但是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造成了技术和人的异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偏见、贫富差距、环境污染等“恶”的问题。要想破除人工智能异化带来的困境,就要求人类必须树立人本主义技术观和遵循向善的价值原则。
首先,分配正义是科技向善的内容。智能时代以数据为核心的资源分布不均衡,加上功利主义分配原则忽视个体的基本权利,仅把个体当成牟利的工具,致使分配不公正和数字鸿沟不断加剧。人们已经意识到数字鸿沟背后遮蔽的是科技的滥用,损害着人们的基本权利,侵蚀了社会治理系统的公正性,加剧着社会的偏见和贫富差距,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因此克服数字化生产力造成的困境,就要坚持科技向善的正义分配原则,不断开放和共享技术成果,弥合数字鸿沟,真正让科技造福于人类。
其次,共同价值是科技向善的手段。技术的发展使全人类面临着普遍的价值冲突、环境污染、核威胁等不确定因素和风险。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武器的研发和运用,给世界安全和稳定埋下了严重的隐患。避免技术趋“恶”,就要倡导世界各国共守人类价值之“善”意,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善”举,遵循人工智能技术向善的价值原则,实现人工智能向善的发展。
最后,人的解放是科技向善的目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唯物史观出发,把技术看成人类认识与改造世界的中介和桥梁,并指出,技术可以通过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缓和阶级矛盾,却改变不了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取代的历史必然性。技术的进步使人更加自由、独立,给人创造了更多的发展空间。但技术扩张却重构着人的身体感知,消解了人的主体性,致使人的生理身体被物化为技术中的身体。要使科技真正造福于人类,就要降低其负面影响,就必须坚持以人为中心,兼顾身心的需要,促进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此外,智能经济、智能革命愈深入发展愈要求整个社会接受科学社会主义原则,智能社会、智能共同体的广泛共建愈趋同于对社会主义的认可。未来人工智能技术的社会主义应用必将使人工智能技术的本真意义得以彰显,使人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解放。
四、结 语
正如马克思所言:“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件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5]606人工智能的负效应造成了人的主体性缺失、判断力衰退、生存价值迷失等困境,使人的身心受到无情的摧残和异化。走出人工智能异化的梦魇,首先要认清人工智能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这一异化根源;其次,要求人工智能的创造者坚持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制定完善的道德伦理规则与法律制度;最后,要在同人工智能产品的交互中,积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自觉塑造人的主体地位,降低异化程度。
人工智能技术视域下人的主体性问题研究依然是一个宏大的时代课题。对于未来不断加剧的人工智能异化现象,如何应对异化风险,拓展异化理论新视野,重构和谐共生的人机关系等问题,仍值得深入研究。相信我们定能不断突破对智能技术和人本身认知的局限,创造出以人为本、人机共生的新型文明社会。
参考文献:
[1]黎常,金杨华.科技伦理视角下的人工智能研究[J].科研管理,2021,42(8):9-16.
[2]欧阳英.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看人工智能的意义[J].世界哲学,2019(2):5-12.
[3]孙伟平.关于人工智能的价值反思[J].哲学研究,2017(10):120-126.
[4]余乃忠.积极的“异化”:人工智能时代的“人的本质力量”[J].南京社会科学,2018(5):53-57.
[5]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黄欣荣.现代西方技术哲学[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133.
[8]赵青新.抵制科技的“平庸之恶”[N].中国证券报,2015-12-19(2).
[9]黄欣荣.人工智能对人类劳动的挑战及其应对[J].理论探索,2008(5):15-21.
[10]Kuhn T. The Essential Tension[M]. Universily of Utah Press, 1959:162-174.
[11]任剑涛.人工智能与“人的政治”重生[J].探索,2020(5):52-65.
[12]刘则渊.马克思和卡普:工程学传统技术哲学比较[J].哲学研究,2002(2):21-27.
[13]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M].李黎,郭官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49.
[14]贾凯芳.霍克海默的技术理性批判理论及对当代中国的启示[J].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2019(12):24-25.
[15]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51.
[16]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72.
[17]王立新.休闲异化的技术审视[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7:158.
[18]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M].徐良英,李宝恒,赵中立,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89.
[19]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克伦理学[M].廖申白,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74.
(责任编辑:雷彩虹)
收稿日期:2022-05-24网络出版日期:2022-11-11
基金项目: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2022A013);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项目(20022ND0204);西安石油大学研究生创新与实践能力培养计划资助项目(YCS21213265)
作者简介:张海涛(1982- ),男,山东泰安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国外马克思主义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