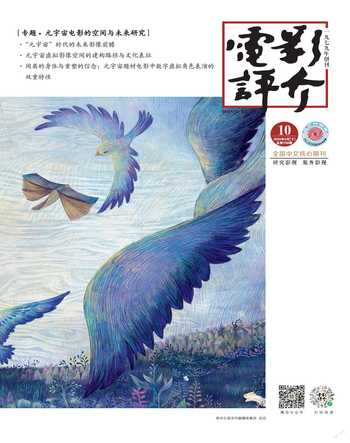经典建构:中国电影编剧理论探索
王梅
电影编剧对电影创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构建中国电影学派理论体系背景下,中国电影编剧理论体系值得梳理和研究。继承与创新中国电影编剧理论,也是十分迫切的。回望早期的中国电影,已出现具有代表性的电影编剧理论专著,如侯曜的《影戏剧作法》(1926年)、谷剑尘的《电影剧本作法》(1936年)、洪深的《电影戏剧的编剧方法》(1946年)等。新中国成立后,电影编剧受到了格外重视。电影界多次进行剧本创作研讨会议、讲座或专题学习,电影编剧理论专著、文章、发言稿丰富,具有强烈的实践指导作用。夏衍、史东山、张骏祥、陈荒煤、袁文殊等一批电影艺术家、理论家积极探索电影编剧理论,指导实践,对编剧重要理论问题展开热烈讨论,并建构起经典的电影编剧理论体系。从已有的相关研究来看,一是集中于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经典电影理论的研究,较少专门研究电影编剧理论;二是研究电影编剧理论也主要聚焦于夏衍的编剧理论,鲜少对电影艺术家、理论家的主要编剧理论探索进行系统梳理。因此,研究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经典电影编剧理论不仅对中国电影编剧理论体系的建构有重要意义,亦对当下编剧理论与实践有启发。
一、电影艺术家、理论家的主要编剧理论探索
(一)电影编剧视听思维的建立
电影编剧理论特别强调视觉特性,这是在早期电影编剧的“蒙太奇思维”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电影艺术家从电影自身的独特性出发,反复强调电影的视觉形象表达特点,反对仅仅依靠人物对话进行叙事。此外,声音的运用及其独立性也受到了编剧理论家的重视。在视听思维理论方面,有着丰富的编剧与导演经验的电影艺术家史东山和张骏祥的理论较有代表性。
1.依靠视觉形象而非冗長对话
史东山在《电影艺术在表现形式上的几个特点》①一书中特别强调电影的视觉形式,认为电影可以真实地呈现人物在现实生活中细微的动作和表情,据此可以表达丰富而隐秘的内涵,这是电影的特长;可是有些电影放弃了这种特长,“电影剧本依照话剧的形式来写,只有对话,缺乏动作表情的细致描写”[1]。在《谈谈电影文学剧本艺术形式的要求》一文中,他再次强调“电影的艺术表现的力量和明确性,应该在于较多地利用动作和表情——视觉的东西”,反对冗长对话。[2]值得一提的是,史东山从两个方面探索艺术形式,一是这种艺术所具有的独特的性能,二是欣赏者的心理和习惯,两者不可分割。这是史东山对艺术形式独特的理论阐述,将艺术形式与接受者心理和习惯结合进行研究,拓宽了艺术形式的研究思路,同时也为夏衍的“大众化”编剧理论奠定了基础。
与史东山的观点一致,张骏祥也反对“滔滔不绝的冗长的对话”,认为依靠形体动作表现人物的思想情感,远比依靠台词对话表现生动有力。他对有声电影时代的到来对话的呈现保持警惕,认为“没有任何理由把电影退回到舞台形式去”。[3]即使在舞台上,也主要依赖动作,而不是台词。张骏祥认为真正将戏剧与电影进行区分的是“镜头动作”,即拍摄的景别、角度、剪辑的节奏等镜头语言。他反对将蒙太奇视为万能手段。他甚至认为库里肖夫实验是“愚蠢的试验”,“将演员降低到与一件道具相等的傀儡的地位”[4],将蒙太奇变成了一种杂耍。形象的语言与蒙太奇语言是电影艺术的两个重要方面,任何一方都不可偏废。
2.在声画关系中合理运用声音
史东山探讨了声音的独立表现,尤其是“画外音”的运用。电影表现人物内心活动的声音与舞台上的“心理独白”产生完全不同的效果。电影的声音运用可以独立表现,声音和画面可以不同步。画外音可以表现人物内心活动,而不会破坏电影的逼真性;但画外音不能采用过长的台词,而应主要通过人物的动作去表现内心活动。
张骏祥认为蒙太奇的概念不止局限于画面,还包括音响、音乐与画面的组合关系。他批评“我们的编剧尤其在这方面放弃了自己的责任”[5],把这些全部交给了导演。在剧本写作阶段就应该合理运用声音,使之与画面产生配合,能产生较大的感染力。声音与画面的矛盾可以产生特殊效果,声音与画面一致,又可以产生强调作用。他认可主观镜头的运用,尽管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运用了这种方式,但运用合理可以成为表达人物内心的直接手段。张骏祥真正具备了“声画蒙太奇”思维,并将这种思维方式带入编剧理论,发展和丰富了有声电影以来的编剧理论。
(二)电影编剧的民族化、大众化
1958年,电影艺术家夏衍在北京电影学院举行讲座,其讲稿整理后以《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为题陆续在《中国电影》杂志上发表,后来加上其他理论文章以专著形式出版并多次再版。学者戴锦华曾专文分析过夏衍《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的重要性,认为它“标志着新中国电影史的整整一个时代”,是“认识了解新中国诸多艺术现象的一把钥匙”。[6]
夏衍在《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中首先强调的是“群众观点”,因为“电影的特点是大众化”[7]。夏衍在此提到的受众观点明确,剧作家写作的对象是千千万万的劳动人民。以此观点为前提,夏衍提出了民族形式的问题。其民族化的思想与大众化的要求密不可分。无论是电影的开场、人物的设计,剧情的起、承、转、合等,都要符合观众的审美习惯,符合传统的叙事特点。哪怕是“蒙太奇”的运用,也要符合中国观众的心理,也要注意中国的民族特点。
夏衍从电影的“第一本”谈起,认为“一部影片的开端,首先要接触到民族形式的问题”[8],在叙事方法上要充分考虑民族形式和观众的欣赏习惯。他从戏曲“有头有尾”的特点进行分析,要求电影的开头要交代清楚时间、地点、社会背景、人物及其关系;谈到人物出场时,他结合清代剧作家李渔的理论著作《李笠翁一家言》阐述人物登场的特点;分析剧本结构时,夏衍再次引用李渔的戏曲结构观点,认为结构就像造房子,动笔之前,先设计结构,其次再考虑材料和细节。在阐述人物、结构特点时,夏衍多次结合戏曲《西厢记》《琵琶记》、文学名著《红楼梦》等进行分析。夏衍的民族化探索受到关注,也影响深远。
(三)人物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塑造新时代典型人物形象,成为电影编剧的重要任务。艺术家、理论家们表达了对定型化、脸谱化人物的不满,认为剧作家应从人物的精神世界出发,结合人物的典型环境,描写“动作中的人物”。剧作家应“设身处地”为每个角色着想,而不能让角色沦为工具。人物形象与时代环境、性格冲突、情节、主题的表达是不可分割的,其对人物塑造的探讨始终置于整个编剧理论体系及各元素关系中。
蔡楚生“反对那种从概念中臆造出英雄来的创作方法”[9],他认为英雄不是从天而降的,应该展现人物的发展与变化。他认为“真实”来源于对事物内在和本质规律的揭示,而不仅仅是生活的真实,强调艺术的提炼与加工。陈荒煤针对正面人物缺乏个性、缺乏血肉的问题,主张运用人物的性格冲突来反映社会现实。他认为有些电影虽然表现的规模和场景都比较大,但没有表现人物的性格冲突,无法真正打动人心。他强调创造“正面人物的典型形象”的重要性,应“真实地、生动地创造典型环境里的典型性格”[10]。袁文殊也认为电影剧作家的根本任务就是创造完整的人物形象及其性格,性格是通过冲突展现的,但冲突若只展现一时的现象,没有展现“社会现象的本质的冲突”[11],艺术效果将大打折扣,也不可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
夏衍在讨论人物塑造时更集中阐述了典型环境与典型性格之间的关系。人物行为、动作、语言表现人物性格,而人物性格又体现时代背景。夏衍认为影片的开端应该很好地介绍时代氛围和地方色彩,“在影片一开始就在人物身上反映出时代脉搏”[12]。有了时代背景,人物才有根据和基础。夏衍强调描写时代氛围是为了烘托人物,人物才是观众最关心的,通过人物才能表达剧本的主题思想。在性格刻画方面,他反对为情节而情节,为性格而性格。在表现正面人物方面,他反对“一出场就写成‘天生的英雄”[13];他主张从唯物辩证法、真实的生活逻辑来处理人物性格,弄清楚人物的“来龙去脉”。
(四)叙事节奏与情节结构
1.史东山的叙事节奏理论
史东山从电影艺术的节奏入手,批评了不讲究节奏的剧本。他对节奏的定义有完整的阐述:其依据是典型的生活本身,根据事物的运动规律,表现剧情中大小矛盾的激化,到更激化,最后汇总成“最高潮”,再到主要矛盾解决,次要矛盾随之解决,从而展现了一种新现象,最终给予观众深刻的刺激和教育。节奏“不但存在于电影的故事情节的结构上、总的骨架上,也存在于形象表现进展中的大小各处,存在于一切表现的形式上”[14]。他结合当时的电影剧本进行节奏特点分析,进一步阐述剧本节奏理论。他的节奏理论并不限于剧本创作,但在谈及剧本创作时,其对剧本节奏的理論阐述尤为宝贵。
2.夏衍的结构、脉络与针线理论
关于结构,夏衍也分析了叙事节奏问题。“呼与吸,起与伏,断与续,紧张与松弛,连续与顿宕,这都是一件事的对立而又统一的两面”[15],分场分段与节奏感息息相关。剧作家应该考虑结构上的松紧,在分场分段之后,应对每一个段落中的情节、人物等做出适当的安排。在每个段落之间,场次不宜过多。电影场景可以自由变换,但不能滥用,需要有目的性。夏衍分析了传统叙事中起、承、转、合的特点,将情节结构分成四个部分:开端、预示可发展的矛盾;积累、发展矛盾;斗争及其转化;结尾、矛盾解决。
电影结构内容的另一个问题,是贯穿故事情节与人物性格的脉络与针线。脉络要清楚,针线要紧密。脉络包括故事情节脉络和人物性格脉络,而针线正有将两者贯穿起来之意。脉络和针线的设计要有目的性,人物与故事情节相互贯穿,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3.张骏祥的悬念与冲突理论
张骏祥指出剧作者不能较好地展现冲突的根本原因是情节与人物性格的脱节,“冲突只有以性格的发展为依据才能得到真正的发展”[16]。他认为塑造人物形象与开展戏剧冲突本质上是一回事,强调其密切关系。矛盾和冲突产生戏剧,但戏剧实际上“产生于冲突的错综复杂的发展过程”[17],这种过程产生悬念。悬念产生于冲突的过程,但实际是人物性格的矛盾。其关于矛盾和冲突的观点一方面侧重于矛盾的发展过程,一方面更强调人物性格与悬念的密切关系。
张骏祥直指电影剧本被无意义的动作所充斥的现象,也指出剧作者对惊险场面、大场面过度追求而忽视人物性格逻辑的问题。戏剧性不止存在于高潮场面之中,也存在于引向高潮的场面之中。在关于结构的论述中,他强调了“立主线”的重要性,同时认为应多方面烘托主要剧情线索。在探讨先有主题还是先有人物的问题中,他认为“人物形象与人物的斗争以及这个斗争所显示的意义,往往是几乎同时成熟的”[18]。
(五)电影剧本改编理论
电影剧本改编理论的主要代表是有着丰富改编经验的夏衍。夏衍曾改编过《春蚕》《祝福》《林家铺子》等电影剧本,并多次撰写文章或参加电影剧作座谈会发言,专题讨论改编问题,如《杂谈改编》《对改编问题答客问——在改编训练班的讲话》等。其改编理论多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进行总结,有较强的问题针对性,多是对现存改编问题的直接回应。
夏衍认为改编是一种创造性劳动,并结合自己的改编实践阐述了这一观点。另外,他特别强调剧本的实际运用,“我历来所写的所谓电影剧本,都只是供导演写分镜头台本时‘使用的提纲和概略,而并没有把它看作可供读者‘阅读的‘文学剧本”[19]。
改编不只是一个技巧问题,夏衍认为“最根本的还是一个改编者的世界观的问题”[20]。改编者从什么立场、什么观点,基于什么目的来改编,以什么样艺术形式来表达主题,是改编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他认为改编者的世界观决定了作品最终呈现出来的思想性。除了世界观的问题,另一个是艺术形式的问题。谈及艺术形式,夏衍仍然强调大众化、通俗化,希望改编者在叙事方法上注重民族传统,注意中华民族的欣赏习惯。
二、外在影响与传统延续
(一)外来思想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至1960年,电影编剧理论深受苏联影响。苏联电影剧本成为电影理论家要求学习的模范剧本,其中《乡村教师》《夏伯阳》等电影剧本备受推崇,被视为艺术标杆式剧本。苏联的编剧思想也深刻影响中国电影艺术家的思想,他们经常在阐述编剧理论时对其观点进行引用。在电影艺术家为阐明编剧观点引用的案例中,虽绝大部分是苏联电影剧本,但仍少量引用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左翼电影,尤其对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赞赏有加。如夏衍在《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中提到了美国进步影片《告密者》、刘别谦《春闺梦里人》,陈荒煤感慨“‘偷自行车的人影片的结尾……是多么令人回味、激动的场景啊”[21]。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理论者以《电影艺术译丛》为阵地,在这一时期译介了大量国外电影理论,他们被后来的学者称之为“洋务派”。这一理论群体在建国后至1956年,大量译介苏联电影理论、电影剧本;1957-1958年,译介了西方先锋电影理论;1961-1963年对当代西方电影思潮进行译介。[22]“洋务派”对国外电影理论的译介,为中国电影界打开了一个观察世界的窗口。
(二)传统的延续
新中国成立后,电影编剧观点出现变化,与旧时代、旧思想形成鲜明对比,但编剧理论体系并不是割裂式存在的。一方面,电影界开始民族化探索,从古典文艺中汲取养分,充分滋养新中国电影编剧理论;另一方面,电影编剧理论延续了左翼文化思想,总结了左翼电影运动的经验。民族化探索在夏衍的电影编剧思想中体现最为鲜明,同时,夏衍的电影民族化观点影响亦广泛而深远。《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这本专著“直接带动了60年代初关于中国电影民族化问题的讨论”[23]。电影界专门开展了向古典文艺学习的课程,民族化探索一度在新中国电影理论探索中形成一种理论气候。电影艺术家也充分总结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左翼电影人的实践经验。
三、经典电影编剧理论的建构
(一)理论与实践的高度互动
这一时期电影编剧理论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紧密性。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电影编剧理论也呈现出理论与实践互动性强的特点。新中国成立后,史东山、张骏祥、蔡楚生、夏衍等电影艺术家拥有丰富的创作实践经验,他们积极将创作经验进行理论总结,其理论往往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又因夏衍、陈荒煤、袁文殊等电影艺术家在电影界领导者的身份,他们的理论又对实践产生较大影响。这一时期的理论专著、论文多是电影艺术家、理论家的剧本创作座谈会发言稿、学习笔记等,文风质朴平实,问题意识特别突出。在编剧理论方面其讨论的问题既有宏观层面,也有微观层面。宏观层面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如何看待政治性和艺术性之间的关系;二是如何认识电影特性的问题;三是如何解决剧本公式化、概念化的问题;四是如何做到民族化、大众化的问题等。微观层面主要体现在:一是如何解决剧本长度过长的问题;二是如何克服人物形象的定型化、脸谱化,如何塑造正面人物的问题;三是如何解决人物对话过多的问题等。
(二)经典电影编剧理论的形成
现实的社会政治环境、传统的延续、外来思想的影响,共同构成了这一时期电影编剧理论的环境,经由电影艺术家、理论家的建构,形成一种较为成熟的电影编剧理论体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为电影编剧的创作原则,民族化、大众化成为创作要求,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成为创作理论依据。这一时期电影编剧理论在电影编剧的视觉形象表达、声音设计、人物塑造、情节结构、改编等诸多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并形成主流电影編剧理论。此外,电影编剧理论家在电影题材、类型多元化等方面也有积极探索。尽管有些理论阐述呈现出重复性、趋同性的特点,但电影编剧理论在反复论证中不断被深化,尤其是电影艺术家在问题意识导向下产生了很多具有真知灼见的理论观点,从而形成了经典理论范式。在电影编剧视听思维的建立方面,这一时期的理论探索很好地弥补了有声电影产生以来理论上的不足,具有较强的创新性。民族化、大众化的理论探索对新时期以来中国电影发展有着重要意义,虽然时代环境发生了变化,观众发生了变化,有些具体技巧可能已不适用,但民族化、大众化的要求一直存在。
结语
新中国成立后,电影编剧理论探索是艰辛的,艺术家、理论家们在面对、解决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建构起经典电影编剧理论体系。这种问题导向意识,实践与理论的密切联系,对当代电影编剧理论与实践具有启发意义。艺术家、理论家们在各个方面进行了一次全面的编剧艺术理论探索,在电影编剧视听思维的建立、民族化与大众化、人物塑造、叙事节奏与情节结构、电影改编等方面均有理论探索,很多理论观点至今仍然闪光,其建构的经典理论范式影响深远。如何继承与创新中国电影编剧理论,汲取其理论精华,促进新时代电影创作实践,都是值得探索的问题。
参考文献:
[1][14]史东山.电影艺术在表现形式上的几个特点[M].北京:艺术出版社,1954:22,27.
[2]史东山.谈谈电影文学剧本艺术形式的要求[C]//蔡楚生.论电影剧本创作的特征.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56:76.
[3]张骏祥.关于电影的特殊表现手段——根据在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座谈会上的发言整理[ J ].中国电影,1956(S1):49-54.
[4][5]张骏祥.关于电影的特殊表现手段(续)——根据在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座谈会上的发言整理[ J ].中国电影,1956(S2):33-40.
[6]戴锦华.读夏衍同志《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 J ].当代电影,1987(01):138-143.
[7][8][12][13][15]夏衍.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C]//夏衍.夏衍电影论文集.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1:83,89,100,131,119.
[9]蔡楚生.对分镜头剧本和文学剧本的一些看法[C]//蔡楚生.论电影剧本创作的特征.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56:65.
[10][21]陈荒煤.关于电影文学剧本创作的特征[C]//长春电影制片厂总编辑室编.电影剧作论文选集(内部学习资料).长春:长春电影制片厂,1959:62,68.
[11]袁文殊.电影中的人物、性格和情节[C]//长春电影制片厂总编辑室编.电影剧作论文选集(内部学习资料).长春:长春电影制片厂,1959:137.
[16]张骏祥.关于展开戏剧冲突的一些问题[C]//长春电影制片厂总编辑室编.电影剧作论文选集(内部学习资料).长春:长春电影制片厂,1959:149.
[17]张骏祥.谈悬念[ J ].中国电影,1958(04):12-17.
[18]张骏祥.谈电影剧本创作中的三个问题[C]//中国电影出版社编辑.电影剧作探索.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61:19.
[19][20]夏衍.杂谈改编[C]//夏衍.夏衍电影论文集.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1:193-194,198.
[22]陈山.经典的建构:五六十年代中国电影理论的成熟[ J ].当代电影,1999(05):24-33.
[23]俪苏元.在传统与现实之间构筑完美——夏衍《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的理论意义[ J ].当代电影,2000(06):18-21.
①史东山在《电影艺术在表现形式上的几个特点》一书的前言中提到写作此书的目的首先是为电影编剧提供理论参考,尤其第一部分“是与电影编剧工作直接有关的”,因此本书也被纳入编剧理论范畴讨论。
【作者简介】 王 梅,女,湖北荆门人,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影视编导与创作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