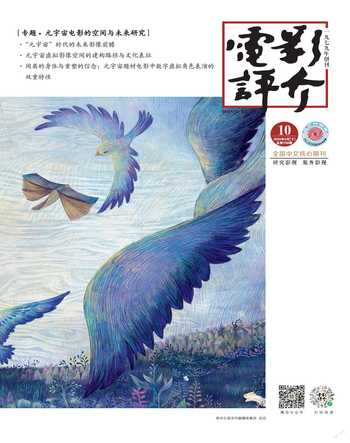《四个春天》: “纪录式”与“写意化”的乡土镜像融合
许河 耿小博

电影《四个春天》是陆庆屹执导的纪录片,记录了父亲陆运坤和母亲李桂贤老两口四年来的日常生活。本片以父母两人平凡真诚的生活故事为叙事主线,将个性鲜明的乡村故事浓缩、融入其中,既讲述了父母干农活、打野菜的日常劳作,也讲述了他们充满诗意的生活,诠释了独特的底层人文关怀,构建了地域特色鲜明的乡土话语空间。该片采用时空对话的方式,在相对平和的故事情节中,用简约的叙事语言,平缓的叙事结构,勾勒了充满温馨的真实乡村生活图景,回应了大众对乡村生活的丰富想象,折射了乡土文化与集体记忆的时代变迁。
一、细节呈现:乡村生活图景的真实表达
学者汤祯兆在《香港电影血与骨》一书中提出,“类型研究的最大特色,是类型本身有强烈的重复本质。在同一类型电影中,不同年代的作品往往只会在细节上加以修正。”①影视作品的细节不仅能够承载主流价值观念,也能通过设置丰富、生活的故事情节来塑造立体、鲜活的人物形象,从而借助影像景观取得了良好的叙事效果。电影《四个春天》用近乎白描的叙事手法,诠释了充满现实质感的叙事风格,构建了真实的乡村生活面貌。
(一)主体人物形象的生动建构与现实表达
语言学家索绪尔提出,语言符号是能指和所指的结合体,能指、所指通过意指成为符号,意指有象征功能,通过意象符号隐喻作者的理念。②电影艺术在叙事过程中,通过展示主要人物的语言风格、动作姿势以及衣着服饰,从而塑造了风格鲜明、特色突出的人物形象。[1]电影《四个春天》的人物形象设置相对简单,通过讲述父母二人完整的生活故事,以更自然生动的叙事方式来推进故事情节,也使观众对乡土故事形成了更加鲜活、立体的认识。作者从反思的角度记录了父母二人的生活,其中既有家庭情节的故事内容,也有父母的淳朴爱情、父母对子女的纯正感情等。本片借助有机衔接的人物故事情节,赋予本片深厚的人文内涵与深刻的现实反思,彰显了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虽然本片在叙事过程中使用了较为简单的视听语言,充满象征隐喻的视听符号,但是其中所蕴含的细腻情感却能够使观众充分体会到改变生活的热情和希望,也让原本平淡的生活充满了动人情懷。
(二)乡村生活图景的有序递进与无序翻转
《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一书中提到小说戏剧化的倡导者亨利·詹姆斯认为:“最大限度地降低作家的叙述声音,将作为完整有序的‘有机体的小说直接呈现在读者面前,使阅读的过程与观看戏剧一样,具有直接的戏剧效果。”①电影作品在描摹、呈现叙事场景时,为使观众获得直观、生动的体验,增强电影的艺术感染力和戏剧效果,需要尽可能采用自然、流畅的叙事手法,具象呈现真实的生活状态。[2]电影《四个春天》塑造的空间是乡村生活、生产空间的无缝衔接和有机切换。无论是陆庆屹父母两人在生产种植空间的流动、变化,还是日常生活空间的单一、清贫,都向观众自然再现了鲜活、客观的生活场景,并在无意识间传递了具有特殊性的精神空间。该片始终坚持全面、真实的叙事态度,完全依据乡村生活的发展规律进行拍摄创作。例如影片用四个春天的生活场景象征四年的影像记载,真实呈现了平凡琐碎、幽默欢乐、走心感触等生活场景,通过设置转折性生活图景,回应了影片“四个春天”的叙事主题,在前半段递进性、后半段转折性的生活图景中,形成了动态变化、持续流动的生活空间。
(三)人物性格的持续凝练与生动传递
意大利符号学家艾柯认为,文本存在一种连贯性及其原初意义生成系统,而诠释只能是对文本意义的诠释。②电影是视听叙事艺术,从人物形象塑造、情节变化到精神诠释,都达到了相应的审美水平。在电影文本叙事过程中,即使其叙事内容、叙事主题一致,但是从不同视角出发,所获得的观赏体验完全不同。乡村生活图景的艺术呈现,既是跨越时空的对话,也是人物精神风貌的生动展现。[3]影片《四个春天》以近乎纪实的创作手法,讲述了父母日常耕耘的生活故事,其中既记录了父母熏腊肉、列菜单、准备年夜饭等节俗场景,也讲述了热情开朗的姐姐患肺癌去世,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痛。但是,父母明白生活还要继续,所以又重新响起了歌声,生动展现了基层农民坚韧、乐观、真诚的精神。影片既展示了真实、具象且充满感染力的底层群众生活,也围绕逐渐被遗忘的乡土生活进行了一一描述。该片借助影像艺术来折射乡村生活的现实图景,用典型的乡村美学将贵州省独山县的家庭生活与乡土农村相融合,并巧妙借助影像手段淡化了城乡二元关系,以“象外之象”的表现方式,实现了乡村文化、乡村故事、乡村空间的真实表达。
二、诗性表达:乡土生活意境的合理创造
郑大群在《论传播形态中的身体叙事》一文中提出,“身体叙事,是将身体作为一种叙事符号,并由此形成话语的叙事流程,从而达到表述、交流和传播等目的。”③语言、动作、服饰等作为重要的身体叙事符号,通过尽可能原本、自然地呈现叙事图景,生动反映了叙事主体的内心情感和心态。电影《四个春天》采用视听剪辑手段,以“影像回声”的方式,将跨越时空、地域的虚实线捏合在一起,其中所使用的语言、熟悉的土地种植动作以及真实的衣着服饰,诠释了一个基于真实乡村生活图景的艺术意境。
(一)关注现实与人文语境的柔性表达
语言是电影艺术最突出、最明显的身体叙事方式,其中使用的语言既有人物对话交流,也包含了影片人物内心的独白、面对镜头的倾诉等。[4]影片展现了独特的导演意识,导演既是创作者,又是叙事内容的观察者,其通过从“参与者”的身份抽离,以旁观者的视角进行记录,在关注现实的同时,实现人文语境的柔性表达。电影《四个春天》基本以贵州南部方言为主,形成了质朴、鲜活的乡土文化景观,在彰显语言差异性的基础上,赋予观众独特的听觉感受。父母二人是传统乡村生活的代表,他们用纯正的方言“艺术化”地再现了自然、生态化的乡村生活图景,更加生动、真实地展现了农耕生活、情感生活场景。影片从最普通的鸡鸣狗吠开始,从父亲熏好腊肉香肠到母亲歌唱《故乡的云》,让观众在关注现实的同时迅速进入剧情。本片故事设计既紧凑,又环环相扣,在叙事过程中真实还原了农民的生活状态,尽可能地记录父母日常化的对话、交流,以简约的语言内容、平缓的叙事结构,以及相对平和的情节冲突,完成了真实乡土故事的生动叙述。
(二)聚焦现实与人物特质的诗意表达
美国学者格里高利·赛格沃斯在《情动理论导引》中提出,“情动的承诺有行动力的增加、开始‘变得有能力、身体与世界亲和性的共鸣,以及对更多生命或生命本身的敞开。”①在“情绪叙事”中,通过聚焦现实、传递情感,形成了现实与人物特质的有机联动。作为现实主义题材影片,影片《四个春天》用平实且充满诗意的叙事镜头,细腻呈现了乡村生活图景,通过真实、自然地展现底层农民夫妇从陌生走向熟悉,从相亲、相伴到相守,在质朴浪漫、朴素绵长中,唤醒了大众对乡土生活的认识,艺术化地再现了特殊的乡村场景,实现了有效叙事目标。动作是重要的身体叙事语言,也是身体叙事的重要外在。虽然自己的父母都是农民,但是两人都热爱娱乐、热爱生活。两人不仅喜欢栽花种树、养蜂练字,更让观众印象深刻的是,两人都喜欢音乐。比如母亲在做针线时,会唱“妹呀,在的房呀中的绣呀罗裙呀。”在上山打野菜时,唱起山歌“打菜莫打那边坡,那边打菜不满箩。”歌词内容虽然简单,但是却生动展现了人物内心的情感变化,也诠释了质朴、真诚的人物特质。影片中,母亲的动作语言、演唱歌曲虽然相对简单,但却极为真诚,其个人身上所散发、诠释的是纯正的农业文明,她对生命的尊重,诠释的诚信品格,既是农民的生活态度,也是乡村文化的生动传承。
(三)反映现实与人物个性的合理表达
乡村叙事素材的合理挖掘与充分应用,成就了具有思想深度、艺术个性的叙事空间。在电影艺术创作过程中,不仅需要有效使用叙事语言、视觉表现等艺术手段,还要立足情感共鸣和情绪共振,从多维视角出发,传递真实情感,以实现情绪共振的理想成效。[5]在电影《四个春天》中,父亲对乐器的喜爱是叙事的重要形式,尽管乐器本身并不表达和传递任何情感,但是通过将制作各类乐器与人物形象、故事情节相融合,能够营造极为鲜明、更加个性的视听景观。母亲喜欢歌唱、父亲喜欢制作乐器,两人完美的配合不仅是令人感动的真情,也是本片理想化表达的重要体现。与母亲喜欢唱歌不同,在父亲看来,“音乐是他唯一的精神出口”,这其中诠释了乡村教師、知识分子对精神生活的热爱与追求。而制作乐器、品读音乐,更是他的精神趣味。但是,这不仅反映了父亲的人物性格,也间接阐释了父亲的孤独。片中父亲对乐器的态度,既是现实生活与理想期待矛盾的体现,也是人物个性的生动写照。乐器不仅是父亲情绪的表达,也是父亲面向自我的内部深思,更是其个人生活态度的彰显。
三、情怀书写:乡村生活题材的多元意蕴
人性叙事以人性为基础,融合多种元素于一体,几乎全篇都在描述日常生活叙事,是对人性真善美的全面刻画。影片《四个春天》上映后获得了良好的市场口碑,无论是故事题材的选择,还是故事情节的设计,都是成功的。一方面,本片立足真实、质朴的乡土空间,观众化身村民,与导演父母共同体验乡村文化,并借助语言、服饰和动作等身体叙事,推动故事情节发展,在讲述生动感人故事的同时,生成极具乡土气质的叙事景观;另一方面,本片借助“时空对话”的叙事方式,关注乡村风貌,传递了真诚、感人的情怀,并借助一家人相伴的故事,进一步深化大众对乡村文化的精神记忆与文化隐喻,形成“讲好乡村故事”的全新范式。
(一)多元情感的容器承载
法国电影理论家安德烈·巴赞在《摄影影像的本体论》一文中提出了“影像本体论”,强调了影像艺术具备的客观性、纯粹性,其认为电影艺术能够再现事物原貌。②电影作品在叙事过程中融入多元情感,有助于实现精神书写的效果。[6]电影《四个春天》采用“生活流式”的叙事结构,以合理的故事情节来象征和隐喻叙事主题,借助充满想象的开放式叙事结构,成功记录了自己一家平凡而又动人的故事,并生动展现了乡土美学的叙事风格与多元象征。在第三个春天的时候,对于陆家一家人来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冷清一些。在医院里,平常开朗、外向的母亲再也没有了日常的笑容,只有不停地为自己的女儿祝福祈祷,而自己的父亲更是沉默不言。最终,陆庆伟去世了。原本导演想记录父母的十年生活,但是受“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影响,只能接受现状。在第三个春天后,父亲再也没有摸过乐器,而母亲也不再跳舞。通过将镜头对准送葬队伍,记录寂静的坟地、家人久久不能停息的哭泣声,使观众对父母的情绪产生了深刻共鸣。本片通过讲述真实、接地气的乡土生活,生动表现了亲情的真实厚重力量,在与观众之间建立情感共鸣、情绪共振的同时,也使影片内容及创作主题获得了大众的广泛认可。
(二)乡村生活的精神想象
麦茨指出,不同于约定俗成的自然语言——电影语言,是一种能指与所指高度重合的理据性符号,外延与内涵由此区分开来,外延的所指就是拍摄对象,能指就是电影化手段,两者相结合构成了内涵的能指,进而指向了情感与意义的内涵所指,即组成电影的语言符号。①
电影是情绪表达的工具,也是情感交流的重要媒介。电影《四个春天》以纪录风格为基础,融入戏剧性,在增添叙事张力的同时讲述动人故事,使观众获得了独特的观赏体验。该片以真实再现乡村生活图景为前提,将意象营造、意境表达与美学风格相结合,通过细致描摹乡村生活图景,呈现出独特的乡土记忆,不仅彰显了质朴的人文关怀,也形成了充满温情的乡土故事叙事范式。[7]不可否认,随着城镇化建设的不断加速,乡村文化逐渐消散,甚至已蜕变成大众的集体记忆符号。影片所讲述的故事是家乡故事,其借助时空对话,以一种怀旧潮的叙事方式,生动恰当地展现了基于乡村文化的媒介记忆景观。该片所讲述的主体故事,既是生产与生活叙事空间的连接,也是城市与乡土空间的连接。相对于乡土空间的直白、大幅描写,城市空间仅仅以隐性方式出现,并借助富豪的生活、外出打工村民的行为等零散性呈现,在相对分散的空间中引发观众充分想象,并期待能有一种团圆、幸福的生活图景。这种图景既是符合观众内心期待的有序呈现,也是观众对真实乡村生活的心灵想象。虽然影片具有一定文艺气息,但是并没有弱化乡土生活的再现功能与写实风格,其通过“立象尽意”的叙事策略,不仅高度契合了影片的叙事主题,也丰富了电影的叙事意境,更形成了有意义、有生命的意象文本。
(三)乡村文化的时代变迁
苏珊·朗格在《情感与形式》中提出,“电影作品就是一个梦境的外现,一个统一的、连续发展的、有意味的幻象的显现,银幕上的画面不受实际情感压力支配,而为一种明确意识到的情感所左右”。②与文字、音乐和绘画艺术的模糊表现相比,电影艺术具有更为具象、立体的表达效果。电影《四个春天》生动呈现了乡村生活的善良、温馨与真诚,直击观众内心。四个春天,是一种递进式的生活图景。一家人相互珍惜、互相陪伴,一直向过上美好的生活而努力。然而,接下来极具转折特征的生活图景,不仅为观众带来了极为强烈的视觉差异,还在强烈的情感反差中鲜明地传递了真实的人物情感与精神理念。原本一家人是相伴相依的幸福生活,但是姐姐因肺癌离世,让一家人陷入痛苦之中。这一段特殊的经历,不仅让一家人产生了消极情绪,也使观众在家人的沉思中感受到真挚情感,甚至使其反思应该如何做父母、如何做子女。又一个春天来临后,燕子回来了,父亲来到房子里,拿起短笛、擦擦灰,说“好久没有吹了”,而母亲正在厨房做饭,听到楼上传来的乐器声,高兴地掉了眼泪,说道:“你爸终于玩乐器了,这一年不知道怎么过的。”该片描述了现代生活视野下,一家人最普通的日常生活及劳作场景,这不仅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碰撞后的不稳定因素,也是以时空对话的方式实现了乡村生活图景的复杂表述。因此,观众可以感受到影片对乡村生活的真挚表达,也能够从中发现乡村文化的时代变迁。
结语
电影《四个春天》聚焦真实、自然的乡村生活,从故事设计到人物形象、主题表达,所有的创作灵感都来源于生活本身,其通过构建流动、变化的乡村生活图景,承载了亲情、爱情等相互共鸣的丰富情感,生动描述了具有象征性的乡村场景,从而实现乡村人物、乡土生活与乡村文化之间的有机关联,也构成了影片叙事主题的隐喻表达。与此同时,作为现实主义题材电影,影片以乡土生活为创作基础,通过时空对话的叙事方式,以纪录片的创作手法,鲜活地记录了亲人的日常生活,不仅生动彰显了深厚的人文价值意蕴,而且在构建全新叙事范式的同时书写了更多心灵思考。
参考文献:
[1]袁道武,程波.身体、叙事与悖论:当代中国电影底层形象的性别转向(1992—2019)[ J ].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20(01):39-46.
[2]江腊生,张振强.乡村伦理与现代气息——浅析电视剧《一个都不能少》的脱贫攻坚书写[ J ].中国电视,2020(07):32-35.
[3]宋珮暄.电影媒介景观中女性身体叙事的流变与演化——基于米歇尔·福柯身体哲学观认知分析[ J ].学习与探索,2021(04):143-148.
[4]杨彪,郭昊天.农民的“出场”:短视频中的乡村振兴图景与话语表征[ J ].新闻爱好者,2021(02):48-50.
[5]杨岱,张翔.纪录片《书简阅中国》:双重抒写、叙述话语与视听图景[ J ].电影评介,2022(01):40-43.
[6]朱飞虎,钱帆帆,张晓锋.乡村文化振兴视域下三农短视频的媒介图景、核心价值与提升路径[ J ].当代电视,2022(09):81-85.
[7]柴冬冬.话语生产、视觉建构与再媒介化——当代中国短视频文化的乡村叙事实践[ J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06):56-65.
①参见:汤祯兆.香港电影血与骨[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215.
②参见:[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33.
①参见:申丹,韩加明,王丽亚.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7.
②参见:[意]安贝托·艾柯,等著.[英]斯特凡·柯里尼,编.诠释与过度诠释:文化生活译丛[M].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62.
③参见:郑大群.论传播形态中的身体叙事[J].学术界,2005(05).
①参见:[美]格里高利·赛格沃斯,梅利莎·格雷格.情动理论导引[EB/OL].李婷文,译.(2019-09-04)[2023-03-15].https://www.doc88.com/p-6488789328827.html.
②参见:肖永亮,许飘,张义华.数字技术语境中电影的真实性美学——从巴赞摄影影像本体论谈起[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2):149-154.
①参见:[法]克里斯蒂安·麦茨.想象的能指:精神分析与电影[M].王志敏,赵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24.
②参见:[美]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M].刘大基,傅志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82.
【作者简介】 许 河,女,河北石家庄人,河北美术学院影视艺术学院讲师;
耿小博,女,河北保定人,河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影视学理论与影视创作研究。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20年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河北省人文類乡村纪录片的创作与传播”(编号:HB20YS018)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