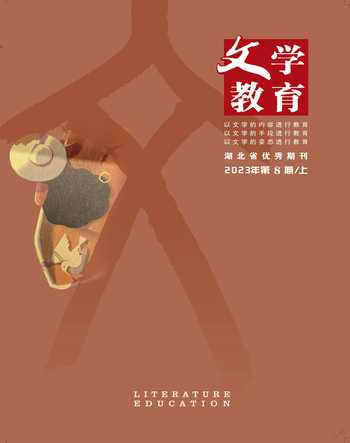论语言的虚构性
石舞潮 胡青宇
内容摘要:语言是存在的家。万物在语言的世界里存在、展开;人类在语言的世界里生活、思考。作为一个人工创造的符号系统,语言自身具有明显的、系统的虚构性——正是语言自身的虚构性,为人类的语用实践提供了虚构的便利,让人类得以在语言虚构的世界里诗意地栖居。
关键词:语言符号 能指 所指 语法系统 虚构性
J.G赫尔德说:“当人类还是动物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语言。”[1](P-5)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那么,人类最初的语言必定是根于自然的语言。这种语言是声音、表情、肢体动作与人类情感的自然结合,与人类心理、情感表达的需要直接相关,就像卢梭所说,“语言虽然是社会的第一个人为的产物,但它的形式则完全是由自然的原因形成的。”[2](P-6)这根种于自然的“语言”,不仅在人类世界是处处相通的,与自然界高等动物的“语言”也是大略相通的:高兴时眉飞色舞;愤怒时横眉立目;悲伤时垂头丧气……概而言之,它可能只是一些简单的声音与肢体动作的结合,仅限于用来传递简单的信息、模糊的情感。因为这种“语言”的自我繁殖能力极低——不仅“词汇”量少,而且缺乏一套能够对这些“词汇”进行灵活编码的语法规则,其效用范围也因而大打折扣。要传达更为丰富更为复杂的信息或情感,人们必须借助语言符号。
一.语言符号的虚构性
语言符号的发明,是人类文明史上最重大的事件,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分水岭。只有当人类用语音符号或文字符号来指称世界万物,表达其对世界的认知与感受,并把这种符号作为相互交流的工具时,人类才真正拥有了自己的语言。这种语言,与赫尔德或卢梭所说的“自然语言”有着本质的区别:首先,“智人的语言最为灵活。虽然我们只能发出有限的声音,但组合起来却能产生无限多的句子,这些句子各有不同的含义。于是,我们能够吸收、储存和沟通的信息量巨大惊人。”[3](P-21)其次,与“自然语言”根于自然需要的发声不同,语言符号是根于社会需要的纯粹的人工建构——人工建构与自然产物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它具有主观性、创造性,并因之具有虚构性。这也是语言符号与自然发声的根本区别。
荀子曰:“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实辨,道行而志通,则慎率民而一焉。……故壹于道法,而谨于循令矣。如是则其迹长矣。迹长功成,治之极也。”[4](P-131)这是从起源角度探讨古之王者为什么要创造语言。一言蔽之:有利于社会的发展进步,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强大。古之王者又是如何创造语言的呢?荀子曰:“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5](P-132)即,万物本来没有确定的名称,也没有所谓合不合适的名称;名称是社会约定俗成的通用符号——符合约定俗成的规矩(即社会公约)的就是合适的名称,在社会公约之外标新立异,“托为奇辞以乱正名”[6](P-132)的就是不合适的名称;名称(即词语)作为符号是不具有它所指称的实体性事物的实际内涵的;但是,如果我们共同约定以某个词语来命名某个实体,而且这种约定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并在语用实践被广泛应用,那么,这个词语就成了某个实体性事物的专名,在语用实践中可充当实体性事物的代理。当然,它只能指示而不能显示它所指称的实体性事物。由此观之,在语言体系中,词语的生产过程也即“名”与“实”的关联是具有明显的虚构性的。
索绪尔说,语言符号是“概念和音响形象的结合”,“能指(音响)和所指(概念)的联系是任意的……即对在现实中与它没有任何自然关联的所指来说是任意的”。[7](P-107)能指和所指之间联系的这种任意性,从根本上揭示了语言符号的虚构性——把既无自然关系,也无逻辑关联的二者撮合在一起。只是这种由人们主观创造并强加于二者的关联,经由社会约定俗成,具有了社会契约性,因而能够在特定社会内部通行而已。在此意义上,它与纸币无异——自身没有价值却可以代表价值而流通。语言符号的这种虚构性本质,赋予了人们在符号的能指和所指的关系之间任意虚构的权利——不同的语言用不同的声音、文字符号来指称同样的事物,就是明证。比如:作为能指,树shù和tree[tri:]所指的是同一事物,但不同民族的语言用以标识这个概念的语音、文字符号形象却大相径庭。这种情况,在同一语种内部不同的方言之间也司空见惯。这种差别,显然与人们的心理、情感无关,而是源于语言符号的能指与所指的关联的任意性——即虚构性。
二.能指的虚构性
语言符号的能指,不论是语音还是文字,都只是其所指的代理——它只能指示而不可能显示其所指。形而上学的观念认为:在理想的情况下,能指就是其所指概念的天然的表象,其声音形象与其所指概念的内涵是高度统一的——符合自然的普遍的指称秩序,能够把其所指完整或部分地带入在场。卢梭说:“上帝将字写在人的心中”(致维尔纳的信),“自然律,以不可磨灭的文字刻在人的内心深处……它在那里向人呼唤。”[8](P-21)黑格尔说:“理智通过言说直接地无条件地表现自身”。[9](P-34)索绪尔亦认为:意义与感官之间有一种自然纽带,并且正是这种纽带将意义传递给声音——“唯一正真的自然纽带,声音的纽带”。[10](P-48)而事实上,在成熟的语言系统中,这种所谓能指与所指高度统一的语言符号仅限于为数极少的拟声词;越是发达成熟的语言,其语言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这种“统一性”就越低。因为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联的虚构性,语言符号内部的这种所谓统一性早在其诞生之时就已经分崩离析了。指望象诗人所说的那样“期待远古女神的降临,在她的渊源处发现名称”[11](P-129),只能是形而上学的幻想。
语言符号通过虚构能指与其所指的關联,让能指替代了所指并在各种语用场合充当了所指的代理,从而在各种语用场景使不在场的所指“到场”。而事实上,能指作为其所指的代理,其在场仅仅只是符号的在场——它只是指示而非显示其所指,因而它不可能完全替代其所指并履行其功能;恰恰相反,能指(代理)的在场只是昭告了其所指(被代理)的缺席,提醒了人们关注缺席的所指,并由此把人们对所指的经验(记忆、想象)部分地带入在场,从而引导人们对所指进行虚构——所指就在这虚构中到临现场。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命名)它召唤物,令物到来。令物到何方?并非令物作为在场者置身于在场者中,并非令诗中所说的桌子到诸位现在的座位之间。在召唤中被召唤的到达之位置是一种隐蔽入不在场的在场。命名着的召唤令物进入这种到达。这种令乃是邀请。它邀请物,使物之为物与人相关涉。”[12](P-11)因此,能指充其量只能营造其所指在场的幻象。
当文字出现之后,特别是当文字在特定场合取代了语音形象成为了语言符号的能指时,能指的虚构性就显得更加凸出。
从语言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文字应该是为标识语音而创造的符号。正如索绪尔所说,“言语与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再现前者是后者存在的唯一理由。”[13](P-47)字母文字直接就是为了标识语音而创造的;被认为是表意典型代表文字的汉字,虽然部分文字具备独立的表意功能,比如象形文与会意字,但在语用实践中,每一个表意文字都是与特定的语音相对应的,而且可以十分肯定的是,这些文字必定是为标识语音而创造的;同时,汉字中存量最大的文字也不是象形字和会意字,而是表音、表意相结合的形声字。因此,亚里士多德也曾说,“言语是心境的符号,文字是言语的符号。”[14](P-14)即文字符号是语音符号的形象化。如果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语音作为能够直接传达心境的能指,是心灵与逻各斯之间最初的神性的约定,是语言的天然符号;那么,作为语音之代理的文字就是符号的符号,是代理的代理;因而,如果说作为能指的语音是其所指的在场的虚构,那么,文字则是其所指的在场的虚构的虚构,或者说文字与其所指之间的关系是虚构的虚构。
文字作为能指的虚构性,不仅体现为它以所指的再代理的身份虚构了其所指的在场,它还以语音代理的身份,虚构了发言人与听众的在场。众所周知,语音作为能指,如果要虚构其所指的在场,必须以发言人与听众的在场为前提。而文字作为能指,它虚构其所指的在场,则不需要发言人与听众在场——它以再代理的身份,假装发言人与听众就在现场,以文字代替了发言人发言。索绪尔说,“音响形象不是物质的声音,纯粹物理的东西,而是这种声音的心理印迹,我们的感觉给我们证明的声音的表象。”[15](P-106)的确,语音是有温度、有情感、有个性、有生命气息的,它是发言人的在场的直接表现与生动见证;与之相比,文字则因为发言人的不在场而成为了“纯粹物理的东西”,它以空间形象呈现在我们面前,冰冷而坚硬,我们无法像聆听语音一样通过文字形象去感受发言人的心理印迹;我们的感觉无法通过现场的印迹来证明文字的表象传达的是否是发言人的心声,抑或仅仅只是文字的表演。因此,文字代理语音形象作为语言符号的能指,大大洞开了虚构的方便之门:一方面,发言人不在现场,他无须面对现场听众,没有来自现场听众审视、质问的压力;另一方面,他没有现场即时发言的时间限制,他有充足的时间和自由的空间去精心编造他的故事,反复斟酌他的说辞,遣用最花哨的形式和最华丽的辞藻,来打动读者(不是听众)或者为自己辩护。所以,文字表达的可信度远低于语音表达——即使是最动人的文字表达,也更加可能不是发言人真实内心的展现,而是花言巧语的虚构,因为这不用冒任何留下现场的印迹危险。苏格拉底就曾对文字深表不信任:“我们会认为那些拥有正义、荣耀、善良一类知识的人……不会看重那些用墨水写下来的东西,也不会认真用笔去写下那些既不能为自己辩护,又不能恰当地体现真理的话语”。[16](P-200)索绪尔则干脆直截了当地贬低文字:“文字遮掩了语言的面貌,文字不是一件衣服,而是一种假装。”[17](P-55)
三.所指的虚构性
因为能指与所指关联的虚构性以及能指自身的虚构性,我们根本不能指望能指把所指带入在场——我们能接触的只是能指,它仅是其所指的代理,它不但无法替代所指,甚至不能描述所指的表象(如果所指果真是某种实体性的本原的存在的话)。如果我们愿意接受其次的话,或许可以把能指当作一个有效的路标,沿着它的指引,到达所指的栖息地。然而,即使是这样一个退而求其次的愿望也不可能实现。因为在语言系统中,所指本身也具有虚构性。
语言符号的所指(概念)都是高度概括的、抽象的。在本体论的哲学框架内,所指(概念)所标识的是事物的类的存在,即同类事物的普遍的一般的存在。逻各斯中心主义支持将它(所指)规定为在者,并将其存在形式规定为在场:它是朴素而丰富的存在——它概括了所有同类事物的共同本质,却又超越了个体而不具备任何个体的具体特征;那些具体的个体之所以千姿百态异彩纷呈,都是因为分有并突出表现了它所分享的某些个性化元素;它是先验的存在——它存在于人们的经验之外,任何人都不曾具体经验过它,任何人都不可能具体经验它;因为它虽然确实存在,但却是不具备任何实体性形式的存在,因而不是人的具体经验能够感知的。这个普遍的一般的先验的存在,是同类事物中的所有个体存在的终极本源——它就像大能的神,无处不在,随时显灵,但永远不会现出真身。套用柏拉图的话来说:现实中的具体的个体都只是所指(概念)的影子,所指(概念)自身才是终极的真实的存在。柏拉图的终极理念最终来到了万能的神那里。逻各斯中心主义语言观所谓的终极能指,几乎是柏拉图终极理念的翻版。“即便事物、‘所指对象并不与造物主上帝的逻各斯发生直接关系(在那里逻各斯开始具有言语/思想的意义),所指无论如何与一般逻各斯(有限或无限的逻各斯)直接相关。”[18](P-19)但是,为使所指与能指的区分在某个方面具有绝对意义和不可还原性,就必须有一种先验所指,即存在的逻各斯——它乃是符号的第一源泉和最终源泉,也是区分能指与所指的第一源泉和最终源泉。在此,思想听从存在的召唤,就像万物服从上帝的命令。“这一关系如此不可抗拒地侵袭着思,以致于它以一个独一无二的词语道出自身,这个词语就是逻各斯。”[19](P-152)至此,先于能指而存在的语言符号的所指作为终极的先验的本原的存在的虚构性也就暴露无遗了——这个终极所指,只不过是逻各斯中心主义存在-神学论的语言学表达,是一个形而上学虚构的幻象。因而,德里达批评说:“在这种形而上学-神学之根上依附着许多其他隐藏的淤积物。……作为纯粹的可知方面,它反映它与之直接统一的逻各斯。这种绝对的逻各斯在中世纪神学中是无限创造的主体:符号的可知方面转向上帝的言语和外表。”[20](P-17)
西方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索绪尔承认:“在同一语言内部,所有表达相邻近的观念的词都是互相限制着的:由于它们的对立才各有自己的價值;也有一些要素因为同其他要素发生接触而丰富起来……任何要素的价值都是由围绕着它的要素决定的。”[21](P-168)也就是说:在语言系统中,没有一个所指(概念)能够单独、完整地存;不同的概念之间经常相互交叉、相互包含,甚至难以分辨你我;因而,所有的所指(概念)都必须依赖其他的所指(概念)来说明、指认自身。它们就是依靠这种相互指认、说明来相互证明彼此的存在;最重要的是,这种相互指认依靠的不是所指自身,而是作为所指之代理的能指,并由此构造了一个巨大的能指互文的迷宫。如此一来,所指就深陷能指的迷宫而无法脱身了。“意义并非直接存在于符号之内……意义分布在整条能指的链条上,它无法被轻易地确定,它从未完全存在于一个单独的符号之内,它总是不断地忽隐忽现……我们绝不可能抓住意义,因为语言是一个时间过程。语言的意义始终悬浮着,是某种延迟的或将来的东西,后来的意义改变着前面的意义。”[22](P-143)
德里达接着索绪尔的主张进一步发挥道:“差别的显现并发挥作用取决于不以任何绝对的简单性为先导的原始综合……没有将对立作为对方而保留在同一物中的痕迹,差别就不可能发挥作用,意义就不可能产生。”[23](P-87)一旦我们试图沿着形而上学的道路去寻找某个所指的本原的存在,我们就被卷入了能指的永无休止的延异运动中;所指(概念)的内涵就在这一运动中被不断地“播散”着、延异着,最终只留下了一连串没有终点的“痕迹”的运动与运动的“痕迹”,而无法确定其本原的存在。“这无异于说,不存在一般意义的绝对的起源。痕迹乃是分延,这种分延展开了显像和意指活动。”[24](P-90)因此,所指之确定的本原的存在,也就成为了臆想的存在,成为了一个形而上学虚构的幻象。
正因为所指自身具有虚构性,所以,任何时候,听众或读者都不可能借助于能指的指引去接近所指的栖息地,抓住所指的本原——本原根本就不存在,所指根本就没有固定的栖息地,它在语言系统中四处漂泊,我们有可能捕捉到所指存在的痕迹,但却永远不可能遇见它完整的存在。用德里达的话来说:在语言符号中,能指与所指是不可分的,所指不可能脱离能指而独立存在——根本就不存在先于能指存在的先验的所指。“符号始终在自身中包含能指与所指的区别,即便它们像索绪尔论证的那样只是一片树叶的两面。这一概念属于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派生生物。”[25](P-14)所指,始终扎根于语言系统并依附于能指而存在,离开了语言系统,它就无家可归。“没有所指可以逃脱构成语言的指称对象的游戏,所指最终将陷入能指之手。”[26](P14;P-6)“词语破碎处,无物存在”。[27](P-129)
所指的最明火执仗的虚构,凸兀地表现在语言系统中那一类纯属虚构的所指(概念)上,它们在现实中连“痕迹”都没有。比如神、仙、鬼、怪、妖、魔等概念。它们纯属虚构,但它们却在我们的语言系统中大摇大摆地四处游荡、互相指认、相互证明它们子虚乌有的存在。与之相似的是文学家们创造的那些所指(概念、形象),比如孙悟空、林黛玉、唐吉坷德等,他们也是明火执仗的虚构的所指——他们的名字连同他们的出身、事迹都是无稽之谈。他们只存在于语言系统中,离开了语言系统,他们就无迹可寻。“如此,在渊源深处一无所有”。[28](P-129)正是有感于此,所以尤瓦尔·赫拉利说,“讨论虚构的事物,正是智人语言最独特的功能。”[29](P-23)
所指(概念)自身的虚构性,具有某种神奇的魔力——召唤人们参与它的虚构过程。因为所指(概念)自身并非实体性的存在,所以,人们对它的认知在一定程度上都是通过想象来进行的:对熟悉的概念,人们会努力联系其所熟悉的某些具体个体的特征来想象它;对陌生的概念,人们会尽力联系与之相邻的概念的某些个体的具体特征来想象它——神仙鬼怪之所以具有与人相近的面目,有着与人相近的情感与欲望,就是这个原因。无论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这种想象加工的过程都必然会产生一个具有虚构性的结果。人们与世界的隔膜,人们对世界认知的差异,就是源于所指自身的虚构性以及人们对所指的虚构,因为人们是依靠语言来认识认知世界的。
四.语法系统的虚构性
逻辑和修辞是语言结构的两种基本方式。语法系统正是以纯逻辑的形式存在的语言编码程序。这套程序具有高度的抽象性。理论上,只要依据这套程序来编码,就可以用有限的语素制造出无限量的词、句。正是在此,语法系统为语言的虚构提供了生产工具,赋予了语言无限虚构的便利。虽然人们通常要求语言表达不仅要符合语法的形式逻辑而且要符合现实的事理逻辑,但在以纯逻辑形式存在的语法程序中,编码只要符合形式逻辑就能生成词、句;因此,在语言的世界里,以形式逻辑压制事理逻辑而制造虚构的语言事件不是偶发的,而是经常的——语言虚构的判断依据不是形式逻辑而是事理逻辑,只要成分搭配越过了现实的边界,与事理逻辑违和,词、句就具有了虚构性。当然,这种虚构也不是只要越界就能完成的,还必须结合恰当的修辞手段才能实现。而语法系统,恰恰又为修辞留下了广阔的空间。
以汉语为例:在词法层面上,汉语中的偏正式、主谓式、动宾式、动补式等几种构词法是最常见的、构词量最多的。而这几种构词法,也恰恰是最方便虚構的编码程序——汉语中存量最大的修辞性虚构的词汇就是这几个结构类型的。例如:偏正结构的词汇:新鲜事、丑事、臭事等,这些词汇人们早已习以为常,但人们却极少注意到这些词汇之中隐藏着的一个个虚构的事件。《词源》释义:“新鲜”,鸟兽等新杀曰鲜。仪礼士昏礼:腊必用鲜。很显然,“新鲜”当初是用来形容刚刚宰杀的禽畜之肉的,后来被用于形容刚刚采摘的蔬菜、水果,已经有了些许比附虚构的意味;至于被用来形容某个事件,其修辞的意图与虚构之事实就更加明显了——似乎某个事件也像刚刚宰杀的禽畜之肉或刚刚采摘的蔬菜一样色泽光鲜,甚至散发着“新鲜”的气味,可以用作美食,给人带来口腹之欲的满足和味觉上的快感。“事件”本身只是一种时间的存在,它无形无相无色无味,是无法凭借感官而感知的,如果用“丑”或“臭”来形容,就赋予了“事件”以生动的视觉形象和强烈的感官形象,这显然是与事理逻辑违和的修辞性虚构。又如主谓结构的词汇:思想浅薄、情感热烈、声音响亮、阳光明媚等,似乎“思想”就像水或木一样有着物理的深度和厚度,是可以用仪器来测量的;似乎情感是有形有声有色有热力温度的,如同一团或正在熊熊燃烧;似乎声音不但是响的,可以听到的,而且是明亮耀眼的,可以看见的;似乎阳光可以像温柔美丽的女子一样,不仅惹人怜爱,而且善于讨人欢心。再如动宾结构的词汇:吃亏、上当、抓狂、贴心、喝西北风等,这些词汇从语法结构上看完全符合形式逻辑,但却与事理逻辑违和:亏,有形有味,可以吃吗?当,真的上得去吗?狂,可以被抓住吗?心可以贴在一起吗?西北风可以喝吗?这些词汇在结构过程中显然糅进了某种特殊的修辞手法,正是修辞让这些词汇有了虚构性。而这些修辞手法之所以能够进入词汇的结构之中,也正是因为这些构词法本身为修辞留了方便之门——它默许、纵容、鼓励形式逻辑压制事理逻辑的事件在语言中发生。
汉语的句法结构与合成词的成分之间的结构关系基本上是平行的。构词法已经给虚构留下了足够的空间,让语言的虚构成为了经常性事件;而句子还更进一步允许在各个语法成分前后添加定语、状语、补语等修饰成分。就像構词法中语素之间的搭配经常越界一样,句子中的附加成分的修饰,极容易越过现实的边界而成为修辞——修辞即是为了表达的艺术效果而超越现实的边界,以形式逻辑压制事理逻辑来进行编码,即是虚构。这一点,在日常语用中已经屡见不鲜,如刀子嘴,豆腐心(定语与中心词之间构成了比喻关系),狼奔豕突(状语与中心词之间构成了比喻关系),扯开嗓子喊(状语夸张了中心词的情状)等,虚构性已经跃然纸上。而这在文学作品中,修辞性虚构更是司空见惯。文学作品为了实现辞采美,刻意追求语言陌生化,语不惊人死不休,充分利用了句法结构提供的修饰空间,经常主动地、努力地越过现实的边界,把修饰转换为修辞,制造了无以数计的具有虚构性的语言事件。诸如: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虚构了主谓、动宾关系),蛙声在故乡的田野里长势良好(虚构了主谓关系),凄凉的胡琴,拉长了下午(虚构了动宾关系),粗野的山风爬进古老的夜里,传说围着火塘繁衍(虚构了修饰关系+虚构了主谓、动宾关系),金色的钟声,将夕阳击落,野草丛中(虚构了修饰关系+虚构了主谓、动宾关系)……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大量修辞性虚构的语言事件表明:语法系统即是语言虚构的生产程序。
由此看来,语法系统虽在形式上是逻辑的,而本质上却是修辞的——它在词、句上所留下的修饰空间,鼓励了修辞性虚构。当然,修辞在虚构的同时也激活了语言的灵性,凸显了语言的美感,丰富了人们对自身与世界之间的关系的想象,丰富了人自身的精神世界,让人得以从中领悟世界万物的秘密玄机。因此,语法系统所鼓励的修辞性虚构不是把人带到了物的面前,而是把人带进了人与物的想象性关系之中,把人引向了诗——在一个个活色生香的词语里,在一首首熟悉又陌生的诗词里,在语法系统所留下的修辞空间里,人的灵魂深处蛰伏的神话倾向和图腾冲动得到了朝圣般的满足;在语言的神秘的狂欢中,人走进万物的奥秘,万物向人欣然展开,与人发生了灵与肉的激情互动,实现了令人心醉神迷的天人合一。恰如海德格尔所说:普通语言只不过是诗化语言的特殊表现,即一首被遗忘、磨损了的用竭了的诗。[30](P-123)也就是说,虚构不只是诗的特权,虚构之于日常语言也是无处不在的。我们或者可以因之断言:最初的语言都是诗性的,语言就是最初的诗——语言的世界就是虚构的世界。
语言的虚构是系统性的:从语言符号的结构,到能指与所指自身,直至语言符号的编码程序(语法),都具有虚构性。因而,我们可以说虚构性是语言的本质特征,或者说语言就是一个虚构的系统——正是语言,向人类打开了虚构世界的大门,让人类得以在语言虚构的世界里诗意地栖居。
参考文献
[1]J.G赫尔德:论语言的起源[M],姚小平译,商务印书馆,北京:2019。
[2]卢梭:论语言的起源[M],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北京:2021。
[3][29]赫拉利:人类简史[M],林俊宏译,中信出版集团,北京:2017。
[4][5][6]荀况:荀子[M],方勇,李波译注,中华书局,北京:2015。
[7][9][10][13][15][17][21]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明凯译,商务印书馆,北京,1980。
[8][14][18][20][23][24][25][26]德里达:论文字学[M],汪堂家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11][12][19][27][28][30]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16]柏拉图全集:第2卷[M].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22]伊戈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艺理论[M],伍晓明译,陕西师大出版社,西安:1987。
本文为2020年度江西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规划项目《文学修辞的虚构性研究》(ZGW20107)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