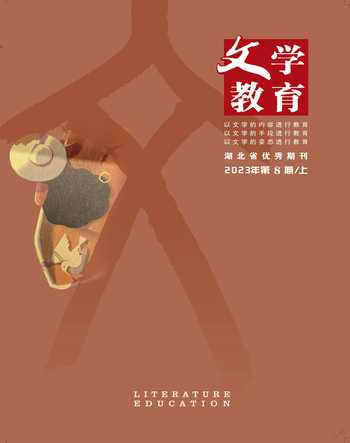鲁迅《铸剑》中的暴力叙事分析
陈立得
内容摘要:《铸剑》中鲁迅自觉或不自觉的暴力叙事,背后有其特殊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思想因素,暴力叙事中复调、荒诞的特征使得文本有了多义的可能,解构和创作主体的介入使得“复仇”的主题得以重建。暴力叙事其实是“复仇”外衣之下“反抗绝望”的暴力表达,同时展示的暴力也达到了对人性深处良善和恶意的挖掘。
关键词:暴力叙事 《铸剑》 鲁迅
将暴力与叙事结合并非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才有的现象,在三十年代它伴随着“救亡图存”的民族情绪也在作家作品中广泛存在,将“暴力”作为研究视角深入鲁迅的《铸剑》也有相关的研究。刘青汉的《希伯来文化关联中论鲁迅在暴力面前的困境》有探讨鲁迅在面对暴力的基本态度、精神质地,其中也单独论述了鲁迅在《铸剑》故事中面对刺客和复仇的否定和揭穿态度。在黎保荣的《暴力与启蒙:晚清至20世纪40年代文学“暴力叙事”现象研究》中有对国内外现代文学暴力叙事的研究进行过综述,认为对单个作家作品的暴力阐述不够集中厚重。黎保荣还认为刘青汉除了偏离对鲁迅的集中视角外,还过于注重鲁迅的“非暴力”思想,对“暴力复仇”思想缺乏认识,是基本符合实情的评述。他在论文里也论述了鲁迅在《铸剑》中主张“暴力复仇”的思想,却没有分析其中暴力叙事的特征和形成的模式,缺少这方面的文学性关照。在发生论中将鲁迅思想的“暴力”倾向来源归结为日本的“尚武”文化,也缺少一些对其他因素的分析。
暴力和作为文学作品中的暴力叙事是有距离的,不能将两者混同一谈。即使作家对现实的暴力是否定的,也不意味着要对暴力叙事持否定态度,更不意味着暴力叙事缺乏文学价值和现实意义。周华健的《新时期以来小说暴力叙事研究》论述了在“文革”结束以后三十年来小说创作中暴力叙事作为现象的存在,其中界定了暴力叙事的概念,他认为暴力叙事主要是指文学创作中推崇使用语言“暴力手段”的文学创作倾向,或者以暴力事件为叙述核心的文学创作现象。他认为新时期作家已经将暴力事件单独作为对象进行书写,形成了不同叙事的模式和美学风格,在独立的艺术世界中有其独特的价值。同时也是对现代化社会的一种“艺术”回应,不仅具有文学价值,也具有现实意义。
本文采取周华建对暴力叙事概念的界定,在《铸剑》的暴力叙事发生论中补充其他见解,通过对《铸剑》的文本细读来分析鲁迅的暴力叙事特征,最后探讨《铸剑》的价值取向。
一.《铸剑》的暴力叙事原因
《铸剑》的创作时间和地点有三种不同看法,于1926年10月厦门,或于1927年4月3日广州,或者认为前一二节创作于彼时厦门,后三、四节创作于彼时广州。①将《铸剑》创作的时间坐标设置为1926年到1927年4月3日,分析历史传统、时代背景、文本出典和作家自身因素,就可以粗略地分析鲁迅创作中暴力叙事产生的原因。
1.社会与历史因素
1926年在段祺瑞执政府的统治之下发生三·一八惨案,再次证明了政府的昏聩和外患的严峻。启蒙的叙事话语伴随着强烈的“救亡图存”的情感成为了社会的主导型叙事样式。一方面是政府、战争和列强中实际的暴力行为带来了“显性”的暴力事件,催生了民众的苦难记忆和暴力想象。一方面是对段祺瑞执政府的愤怒和“救亡图存”强烈的情感欲望需要得到宣泄和表达。这样就不难理解启蒙代表着人性、理性的神圣话语中存在着大量的暴力叙事。
民众对于统治阶层压迫而产生的苦难记忆是有着很久远的渊源的,且是伴随着统治者的残酷、暴力而来的。《铸剑》的故事起因是统治阶层的王对于眉间尺父亲的剥削压迫,实则如此的事件在古代文学中不在少数。杜甫的《石壕吏》中写道“吏呼一何怒! 妇啼一何苦!”“一何怒”“一何苦”便是统治者和受压迫的民众之间最真实的写照。《铸剑》中对于王的形象塑造“他常常要发怒;一发怒,便按着青剑,总想寻点小错处,杀掉几个人。”在鲁迅的笔下,王不仅仅是为了怕眉间尺父亲再给他人炼剑而杀害他,而是王本身就是嗜血、残暴、乐意去杀人的。
暴力想象来源于现实的暴力事件和对现实的愤怒。近现代的战争加重了人民的苦难,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和各种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一步步使得清政府陷入了列强的殖民控制之中。伴随着国内的农民起义、镇压运动、军阀混战,不难想象此刻人民陷入的悲惨处境。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刊发在《人民报》中“匈奴来信”记录了当时的惨象“随处可见逃亡的饥民,妇女,老人与躺着尸体的瓦砾堆。”②《辛丑条约》中要求拆毁天津大沽口到北京沿线设防的炮台,而三·一八惨案也缘起于此条款。在深重的民族危机下,“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被清政府围剿,爱国学生的运动被段祺瑞执政府镇压,民众的愤怒情绪一次次被压制又爆发,得不到很好的表达,于是宣泄于文学创作之中,变成一种文学现象。鲁迅身处时代之中,在创作和接受的两端都不免受愤怒情绪的影响。但是暴力“复仇”的失败的结局也引得鲁迅的反思,于是《铸剑》最后结局变得荒诞、虚妄,“几个义民很忠愤,咽着泪,怕那两个大逆不道的逆贼的魂灵,此时也和王一同享受祭礼,然而也无法可施。”
晚清开始的一系列“救亡图存”的“排满”运动中就弥散着激进和焦躁的情绪,“救亡图存”是常伴随着激烈情绪同行的。章太炎的《逐满歌》中有“他的老祖奴尔哈,带领兵丁到我家。龙虎将军曾归化,却被汉人骑跨下。后来叛逆称皇帝,天命天聪放狗屁。”诗歌中有通俗的民间风味,但也不难读出其语言暴力的趋向。陈天华的《猛回头》在悲愤之中还有“看起来,留得命,有何好处?倒不如,做雄鬼,为国之光!”舍生取义的英雄传统,也植根于民族记忆之中的,而在列强环伺,国家将亡的处境下得以激发。伴随着暴力的舍生取义情节在《铸剑》中得以保留,而且与其他暴力事件的荒诞的细节处理不同,眉间尺杀老鼠时的优柔寡断就和后来舍生取义时的果决形成鲜明对比,产生一种的斩钉截铁的、清脱的美。
2.文学与思想因素
出典文本本身就包含着“暴力”因素。《铸剑》中情节的铺排演绎得力于鲁迅对《列异传》或《列士传》及《搜神记》等不同文本的辑录工作,而镬中三头相咬的场面来自于《吴越春秋》的逸文。③《铸剑》故事的叙事核心是展现孝和俠义,这是中国古代常见的道德化叙事,长期占据主导叙事的地位。鲁迅写《铸剑》时保留了故事中的大部分暴力事件,王杀父,眉间尺自刎,宴之敖砍下王和自己的头,三头相咬。暴力叙事是依靠道德化而获得其合法性的。鲁迅虽然指出:“孔孟的书我读的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干,”但他不可避免地受到了道德化叙事传统的影响,展现极端的暴力,以塑造出在暴力、毁灭之中光辉的英雄人物形象。但同时鲁迅也不限于道德化的叙事传统,在最后对复仇行为的解构可以看作他对道德化叙事的自反。
鲁迅承认世界冲突、对抗的真实性。在叔本华和尼采唯意志主义里,他们强调不同事物之间存在着冲突、对抗,且认为世界是不断运动的。1902年鲁迅东渡日本,早期对进化论之下的理性主义的信奉,逐渐转变为对尼采的非理性主义的接受,兴趣进而扩大到德国文化。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说“意志客体化的每一级别都在和另一级别争夺着物质、空间、时间……生命意志就始终一贯是自己在哨着自己,在不同形态中自己为自己的食品,一直到了人类为止……人把那种斗争,那种意志的自我分裂暴露到最可怕的明显程度,而‘人对人,都成了狼了。”④揭示了事物和生命斗争的本质。鲁迅的《摩罗诗力说》也指出“平和为物,不见人间。其强谓之平和者,不过展示方已或未始之时,外状若宁,暗流仍伏,时劫一会,动作始矣”。《铸剑》中王意志表出的暴力欲望战胜眉间尺父亲安稳生活的欲望,王在意志表出的欲望匮乏后衍生内心和行为上的残暴,眉间尺意志表出的暴力复仇欲望最后又杀死了王。在唯意志论影响之下,也不难理解鲁迅在了解冲突、对抗真实存在下对的未来怀疑、绝望的看法,以及衍生的对暴力否定又不可排拒的犹疑态度。
鲁迅的这种思想和态度还在1926年到1927年得到加强。1926年鲁迅发表评论揭示段祺瑞在三·一八的暴行,后来遭到政府的下令逮捕,他只得四处避难。在1926年8月到厦门任国文教师,12月辞职。怀着“造成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愿望的鲁迅,又在1927年1月来到 “革命策源地”广州,但在中山大学,一切并不如他所愿。他受到国民党右翼的包围,无法开展工作,不久便辞去中山大学文学系教授、主任和校教务主任之职。紧接着1927年发生四·一二政變,但其实国民党的“反共”早已开始。三·一八惨案发生后,鲁迅写道“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给人暂的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鲁迅选取《铸剑》中复仇的故事,是针对在政权和社会场域对自己和人民进行压迫时,对暴力作为本能的一种反思,以及用暴力叙事进行愤怒的情感宣泄。
二.《铸剑》的暴力叙事特点
暴力叙事的考察,有内容和形式两方面,一方面是作为叙述内容的暴力事件,一方面是对事件采用的象征性暴力的叙述话语和叙述行为。同时暴力叙事作为现象出现在作家的文学创作中后也不免会沾染上作家的作风,在创作过程中作家叙述的风格、技巧的运用、情节的安排都会有一定的特征。这些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作家的创作个性和对暴力的态度。鲁迅在《铸剑》中的暴力叙事呈现出复调、荒诞的特征,这样的特征扩大了小说文本叙述的张力,文本的含义和文本之间有了多重解释的可能,包含更丰富的含义。同时鲁迅对于暴力意义的消解和创作主体的介入,又重建了新的秩序和价值。
1.复调、荒诞与多义
暴力叙事的复调特征首先表现为眉间尺杀鼠时矛盾的心理。眉间尺反复逗弄老鼠,觉得老鼠可恨,看到落入水瓮的老鼠:“‘活该!他一想到夜夜咬家具,闹得他不能安稳睡觉的便是他们,很觉得畅快。”后来“却忽然觉得它可怜了,就又用那芦柴”使老鼠爬上来,“待到他看见全身,——湿淋淋的黑毛,大的肚子,蚯蚓似的尾巴——便又觉得可恨可憎得很,”但杀死它之后“又觉得很可怜,仿佛自己作了大恶似的,非常难受。”眉间尺在此处有两种意识在进行斗争,一种是对鼠的怨愤,一种是对鼠的同情,虽然最终以暴力行为踩死了老鼠,看似是呼应了后来眉间尺“暴力复仇”的主题,但不可忽视的是他结尾对老鼠的同情。
复调特征还表现为复仇前后不同的叙述视角下的声音。首先是眉间尺为父亲复仇,在他进城之后虽然遭遇了一些挫折,但是他心中的悲愤、对于复仇态度的坚定是明显的,以至于在遇见宴之敖时舍生取义。宴之敖对于复仇的态度虽然坚定,但是却多了一种洒脱、清逸,“提起眉间尺的头来,对着那热的死掉的嘴唇,接吻两次,并且冷冷地尖利地笑。”再到最后二人都死去,王后、弄臣等对待大王死去的表现,“约略费去了煮熟三锅小米的功夫,总算得到一种结果,是:到大厨房去调集了铁丝勺子,命武士协力捞起来。”暴力“复仇”由坚定到不置可否,再到最后的消解,可以看出鲁迅对于暴力的犹疑态度。通常将结局解释为宴之敖最后是对看客进行“复仇”,但眉间尺杀鼠的犹疑、大臣们滑稽的举措都可以有更加多元的理解。各人物的意识和人物自身矛盾的意识并没有明显的不平等对话,在多声部共同演唱“复仇”主题的同时,这些话语之间也具有丰富解释的可能性。
鲁迅在写《铸剑》时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了荒诞的手法表现暴力事件。小说一开始就以具有暗喻手法的杀鼠情节入手,后来宴之敖在王面前的狂欢化表演,三头相逐的荒诞情节,复仇的行为本身就变得非理智。细节中也有令人费解的怪异书写,眉间尺自刎后宴之敖亲吻其头颅,表征中似乎有嗜血和残酷的因素,更令人费解的是他“冷冷地尖利的笑”,给人一种诡异的感觉。复仇成功之后,大臣们滑稽的举动,辨认不出大王头颅的喜剧意味,使本身应该严肃的复仇行为变得荒诞滑稽,最后甚至还有义民义愤填膺在心中怒骂逆贼。伴随着暴力叙事中荒诞手法的运用,文本表征的暴力事件游离于“复仇”的主题,故事的冲突遭到毁坏,“复仇”变得没有意义,似乎有又具更多层的意义。
2.解构、介入与重建
德里达对解构主义的阐释是通过对二元对立思维的一种质疑来完成的,他引入了延异的想法,认为概念是通过差异、互相定义形成的。首先,“复仇”的主题含义从最开始眉间尺的杀父之仇,消解为向残暴的统治者反抗,以及向给个体施加精神暴力的社会反抗。这种含义是通过书写王的压迫统治和民众愚昧的行为来达成的。眉间尺入城之后怕剑伤人,却遭到干瘪少年的拳击,他却“遇到了这样的敌人,真是怒不得,笑不得,只觉得无聊,却又脱身不得。”此时的眉间尺心中的复仇逐渐变为了唤醒民众意识、反抗暴君的义行。“眉间尺预觉到将有巨变降临,他们便都是焦躁而忍耐地等候着这巨变的。”鲁迅是借暴力叙事来消解了眉间尺个人的复仇的,暴力在此表现为一种民智缺乏而产生的无聊中的本能。
再次的解构则是宴之敖对于反抗和复仇行为中的侠义的消解,“你还不知道么,我怎么地善于报仇。你的就是我的;他也就是我。我的魂灵上是有这么多的,人我所加的伤,我已经憎恶了我自己!”《列士传》中“赤鼻”和“客”之间的生死交付,是复仇者的孝行向义行的转变,而在鲁迅的笔下这种义行被消解了,“仗义,同情,哪些东西,先前曾经干净过,现在却都成了放鬼债的资本。我的心里全没有你所谓的那些。我只不过要给你报仇!”眉间尺轻易地自刎,将自己的复仇大业交给了单纯只想报仇的宴之敖。宴之敖仿佛就是暴力“复仇”的化身,因为暴力而来,为了以暴力反暴而行。
《铸剑》三头相逐的描寫又是对反抗、复仇行为本身的消解,复仇经过狂欢化的暴力叙事本身的意义仿佛消失了,变为了一种可供观赏的行为。原本的三头相咬表现的仇恨之深,侠义之盛被消解,“于是他们就如饿鸡啄米一般,一顿乱咬,咬得王头眼歪鼻塌,满脸鳞伤。”最后大臣们捞头辨尸的滑稽行为更加消解了“复仇”的意义,在暴力之下诞生对暴力反抗的暴力。这种暴力被“看客”当成观赏的对象,“暴力”过后愚昧的民众依旧愚昧,“假装”的大臣依旧“假装”。
《故事新编》似乎与“油滑”分不开,鲁迅将杂文的书写方式融入小说写作,现实的事迹、语汇安置于“故事”之内,形成一种文体风格。“除《铸剑》外,都不免油滑。”给增田涉的信中也说“《故事新编》中的《铸剑》,确是写得较为认真。”⑤“油滑”其实暗含了他杂文本身投枪匕首的愤怒情绪,“鲁迅的文体简练得像一把匕首,能以寸铁杀人,一刀见血。”⑥《铸剑》中却也并非毫无“油滑”之处,“那头即随水上上下下,转着圈子,一面又滴溜自己翻跟头,人们还可以隐约看见他玩得高兴的笑容。”这种“油滑”是鲁迅创作主体对文章的介入,以“油滑”来消解血腥、残酷的暴力叙事,让人在轻松的喜剧之中触摸到一抹悲凉。后来通过分辨“瘢痕”“准骨”“胡子颜色”来辨别国王头骸的情形,充满滑稽与调侃,在消解了复仇严肃性时又给人以更深层的反思。
暴力叙事的解构和介入书写其实是为了一步步重建“复仇”的主题,“复仇”经过三次自反最后又变为向“看客”的“复仇”,向绝望的真实性复仇。“油滑”风格的介入也为暴力叙事除去了残忍、痛苦、血腥的书写,使得暴力叙事获得合法性,更让人在悲情的狂欢化情节中反思“复仇”行为的本身。重新建构和对暴力“复仇”反思后,“复仇”的主题可以理解为在“复仇”都变得“绝望”、无意义之后,仍旧要向“绝望”复仇,向启蒙无效、个人孤独感等造成的绝望反抗。
三.《铸剑》的暴力叙事意指
西方思潮的引进和“救亡图存”的迫切企图,使得暴力叙事在伴随着启蒙话语时获得了合法地位,即使段祺瑞执政府和军阀对作家文学创作会有压迫和要求,但是还是有很多作家书写着暴力的同时扛着重压进行社会挖掘。鲁讯在《铸剑》中自觉或不自觉的暴力叙事,也有其深刻价值取向,在社会和人性中挖掘出了更深的主题。
1.反抗与绝望
“反抗”和“绝望”作为研究鲁迅思想的概念通常在短语搭配中呈现组合关系,“反抗绝望”被汪晖提出后,被大多数学者承认并理解为鲁迅思想的一种哲学主题。汪晖对“反抗绝望”的论述其实是通过解释“绝望”真实性后,确认生命意义存在于选择、反抗之中,从而对颓丧的精神状态否定的一种独特的思维逻辑。在《铸剑》中拆开两词,用“复仇”来作为进行聚合关系词语或者概念的替换,分别与“反抗”“绝望”两词词组合,将会发现“复仇”主题其实也是在暴力叙事中的一种“反抗绝望”。
“复仇反抗”是连动的关系,“复仇”是一种“反抗”,在《铸剑》当中“复仇”的主题是逐步过渡到反抗精神上的。“复仇”与“反抗”中都包含了暴力的倾向,但“复仇”的情绪明显激烈于“反抗”。眉间尺对王的复仇、宴之敖相助复仇,最后对看客的“复仇”都是显性的,它们作为暴力叙事的表征呈现出残酷的同时,可以察觉到愤怒的情绪表述下其实是对抗的意识。“复仇”到“反抗”的受动者也从单一变为了泛化的,甚至转变为一种无对象的暴力行为本身。《铸剑》“仇”的因素其实是被淡化处理的,在细节描写和画面展开时完全略去了眉间尺父亲献剑时遭到的迫害,其后眉间尺的杀父之仇也逐渐演变为对统治者的一种对抗。宴之敖在接过“复仇”大旗后也宣称自己就是为了报仇,“仇”在此泛化了。在泛化的“仇”中,可以将“复仇”理解为一种悲愤的“反抗”。《铸剑》实际上是在用“复仇”来抒发一种反抗精神,“仇敌”不仅仅是统治者和“看客”。应该成为“反抗”的本身,反抗传统礼教的束缚,反抗执政府的压迫,反抗社会的不公和列强的殖民控制。将“反抗”包裹成“复仇”也是为了宣泄心中的愤怒、抒发暴力的本能。
“绝望复仇”“复仇绝望”分别是状中和动宾关系,“绝望”地“复仇”或向“绝望”“复仇”。一方面是指“复仇”主题实际来源于对“绝望”真实性的察觉,一方面又是指对“绝望”真实性“反抗”的暴力性书写。《铸剑》中的“绝望”意识是明显的,老鼠陷入水瓮的挣扎,眉间尺杀鼠后的悔恨、进城后见到的愚昧民众,宴之敖对自我的否定,这些都是“绝望”的根源,这种弥散的“绝望”意识可以在背后看见鲁迅创作主体介入后所展现的孤独个体意识,在处于剧烈变迁、社会压迫中内心的纠结和分裂状态。正因为这种绝望感无法排遣,才会以“复仇”的暴力、激愤倾向书写《铸剑》。结局愚昧的民众依旧是“无聊”的“看客”,但眉间尺和宴之敖已经化为了被跪拜尊崇的本身。看客”的形象是鲁迅在《铸剑》中着重的改写,是明显有现实所指的,是鲁迅向这种透视社会后的绝望感“复仇”。
《铸剑》的复仇情节其实是暴力外衣下的“反抗绝望”,除了对统治者的“仇”,还有泛化、虚无的“仇”,这种“仇”其实只是暴力叙事现象造成的。《铸剑》的暴力叙事是在借“复仇”的反抗精神来呼吁个性舒张、民族独立,也是对新文化运动落潮、启蒙无效的寂寞悲凉状态和愚昧民众采取的刺激性暴力表达。⑦
2.人性善与恶
鲁迅笔下的《铸剑》其实也是“鬼世界”,是一种“向下超越”,暴力意象作为这个世界呈现出的泛化因素,表现于眉间尺杀鼠时的残酷手法、干瘪少年的拳击、无聊的民众对暴力的围观以及王的残暴嗜血等。鲁迅对“暴力”并非是明显的否定态度,“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杀出一条生存血路的东西”,他对于“暴力”也并非提倡,不然眉间尺也不会因杀鼠而后悔,也不会觉得干瘪少年的暴力无趣。鲁迅对“暴力”的态度是犹疑的,这种犹疑来自于鲁迅的个人精神品质,也是他对人性挖掘的结果。
在人性的審视下,《铸剑》中展现的暴力存在着善的成分。它是在受到暴力压迫时眉间尺的反抗,是为了“复仇”而殉道的大义,也是宴之敖在接过“复仇”大旗后自刎时的洒脱和果决。这些人物品质的情节展现很多也来自于出典文本,鲁迅并没有用“油滑”的风格来处理和展现这些画面,更好地保存了暴力叙事在道德化叙事中清洁的特征,才使得文本在叙事断裂时产生一种侠义之气和清逸之美。
对于人性恶的挖掘,鲁迅也不止步于展现残暴的统治者和无聊焦躁的“看客”。眉间尺反复对鼠的折磨,心中的嗜血因子,以及对宴之敖人物形象的改写:从义士变为了对义否定的复仇者,使得读者可以更立体地去观察这些人物形象:他们的道德正义感背后也潜藏着暴力的因子。所以清醒的宴之敖会说“你的就是我的;他也就是我。我的魂灵上是有这么多的,人我所加的伤,我已经憎恶了我自己!”正是通过暴力书写,观察人心中潜藏的暴力倾向,将对暴力行为的“看客”心理公开在大众读者面前,读者才会注意到人的本能中的残暴和奴性的匪夷所思,在暴力叙事中关怀自身。
通过对《铸剑》暴力叙事的研究分析,能注意到鲁迅对于暴力是呈犹疑态度的。但是他创作中自觉或不自觉的暴力叙事现象,是暴力事件催生的,也是民族、民间情绪的表达,同样也受到出典文本和作家自身思想的影响。鲁迅的暴力叙事也有异于其他作家的暴力叙事的特征,复调和荒诞的特征使得文本具有多义解释的可能,解构和创作主体的介入使得文本对“复仇”主题得以重建。《铸剑》的暴力叙事,其实是“复仇”外衣之下的“反抗绝望”的暴力表达,同时展示的暴力也是为了“向下超越”,是对人性深处的良善和恶意的挖掘。
参考文献
[1]黎保荣.暴力与启蒙——晚清至20世纪40年代文学“暴力叙事”现象研究[D]. 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
[2]刘汉青.希伯来文化关联中论鲁迅在暴力面前的困境[D].兰州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2005.
[3]周建华.新时期以来小说暴力叙事研究[D].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
[4]刘晓航.试论〈铸剑〉的故事策略及其不“油滑”——从莫言的感受谈起[J].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20(6).
[5]周楠本.关于眉间尺故事的出典及文本[J].鲁迅研究月刊,2003(5).
[6]朱岩.浅论鲁迅思想发展的历程——兼与王富仁先生商榷[J].文教资料,2009(6).
[7]海力洪.暴力叙事的合法性[J].南方文坛,2005(3).
[8]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68页,第68页,第301页。
[9]鲁迅:《纪念刘和珍君》,《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90-292页。
[10]邓剑歌.《殖民心态,民族狂热与自我省思——1900年德国媒体中的义和团镜像[J].全球传媒学刊,2020,7(2).
[11]王瑶.从“反抗绝望”到“向下超越”——汪晖鲁迅研究述略[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2).
注 释
①席思宇:《铸剑》研究综述(1978-2019)》,《文教资料》2019年第36期,第131页。
②邓剑歌:《殖民心态,民族狂热与自我省思——1900年德国媒体中的义和团镜像》,《全球传媒学刊》2020年6月第7卷第2期,第156页。
③周楠本:《关于眉间尺故事的出典及文本》,《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5期,第62页。
④叔本华:《世界作为意志初论(27)》,《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211-212页。
⑤刘晓航:《试论〈铸剑〉的故事策略及其不“油滑”——从莫言的感受谈起》,《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20年11月第6期,第107页。
⑥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影印版,第14页。
⑦龙永干:《〈铸剑〉:鲁迅“复仇”话语的创造性书写》,《鲁迅研究月刊》2013年第7期,第5页。
——广西警察学院侦查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