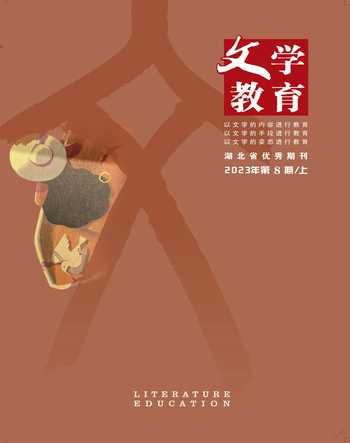《黄雀记》:“失魂”的时代镜像书写与反思
陈巧 胡洪强
内容摘要:苏童的《黄雀记》以“香椿树街”为叙事背景,以祖父灵魂的丧失为开端,描写了“香椿树街”上众多人物的“失魂”。几个主要人物如祖父、保润、柳生、仙女的“失魂”各有其个性化的原因,通过其“失去的灵魂”揭示了社会转型期国民精神紊乱的整体特征以及当下荒谬残酷的社会现实,生动地展现了人性的张扬、堕落与毁灭,背后又是时代的变迁、罪与罚、自我救赎、绝望和希望。作者的最终目的是引入对当下社会的思考,以及对时代和社会强烈的使命感和人文关怀。
关键词:苏童 《黄雀记》 失魂 香椿树街 自我救赎
《黄雀记》是苏童所作的一部具有写实性的长篇小说,讲述了香椿树街上保润、柳生与仙女三人的年少纠葛以及长达十余年的爱恨情仇。故事以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社会变迁为时代背景,以“失魂”这一核心线索为全文基调,描写了三个少年交织错杂的的命运悲剧,淋漓尽致地展现香椿树街上人们所遭遇的巨大的精神逼仄,来审视背后反映出的时代镜像——在这样一个变动不羁、焦虑浮躁的时代,当代人灵魂的“轻与重”,人性的变异、堕落或重生,惶惑与脆弱。
一.香椿街:现代性社会的时代镜像
《黄雀记》以祖父的丢魂为开端,并描绘了香椿树街的一番景象。但小说中仙女被捆绑在水塔强奸、保润刑满释放后遇见柳生这几个情节转折的地方并没有香椿街这个背景的介入,仿佛它只是存在于这个故事中一个特殊的地域标志。当然,苏童是先锋派的代表作家之一,对小说中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描写的淡化,是符合现代先锋派文学的美学范畴。可是不难发现,苏童不少文学作品视线从未离开过这条香椿树街。他对香椿树街的执着也为中国文学提供了许多市井生活的新文化形态。苏童说:“从物理的意义上说,它就是一条狭窄的小街,从化学意义上说,它很大。我写它倒不是说要让这条小街走向世界,对我来说,我是把全世界搬到这条小街上来。它是我一生的写作地图。”[1]事实上,苏童看到了一条晦暗甚至坍塌的香椿树街。这是一条难以抗拒现代化、已经失去美感意义的老街。这也是苏童在现代性社会中对传统社会反思的结果。这条空洞而幽暗的香椿街没有办法再去召唤那些丢失的灵魂,柳生最终还是丧生在保润的刀下,保润再次受到了法律的审判;而仙女原本不该归属于香椿树街的,但她在小说最后结尾被邻居围困在租来的房子里,无奈之下跳进了旁边的河里,再次以出逃实现救赎。因此,只有他们自己才能承担起人性救赎的重担,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小河里的河水不再澄澈,并且堆满了垃圾,一个貌似刚用过的避孕套在水中不紧不慢地跟随着仙女,象征着她的堕落以及性的放纵。她曾肆无忌惮地纵情狂欢,将自己的罪恶过往交给历史审判,所带来的恶果与代价早已侵入了香椿树街。好比波德莱尔《恶之花》中所描绘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下现实的冲突与逃亡以及破败与污浊的社会现象,同样,这片土地不仅无法被虚构、无法被拾起,也无法再承载起一段往事,在现代性侵染下早已是一片废墟、荒芜之地,但苏童仍然把它放在寓言之上,这依然是一个令世人警醒、反思的终极之地。马克思韦伯说“现代性的根本问题就在于传统与现代的张力,所以只有理性、自由、解放才能走向最终的理想社会。”现代性的典型特征就是“时间的纬线每时每刻在断裂,一代代人的踪迹被就此抹去。”[2]我们对传统社会进行反思并不意味着全盘否定,也不是漠视他对人类文明进步和人的自由解放所发挥的作用。而是为了矫正以前社会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用理性、清醒的眼光来审视现代人所面临的问题和困境,为更美好和谐幸福的生活提供方向。
二.时代镜像中灵魂与精神的追寻
《黄雀记》中一个最为关键的意象就是“魂”。魂是一种精神归属和一方栖息地,是道德的坚守和伦理的追寻,是历时的虚无和共时的存在……[3]小說中的“失魂”反映了二十世纪80年代人们普遍的精神存在境况。通过对“魂”的丢失的描写以及寻找“失魂”过程的用心良苦,苏童为我们展现出灵与肉的结合和分离轨迹。小说不仅试图还原被宏大历史所遮蔽的一部分人的社会真实生活,还尝试从中探索人性以及人生存状态的可能性。《黄雀记》中的人物在追寻生存空间和精神空间时作出的努力——在挣扎与反抗里前行,是那个时代下的芸芸众生的鲜活写照。
祖父精神逃亡的一个外在表象就是“失魂”。自称在照相馆丢了魂魄的祖父,从此便开启了他寻根式的挖掘——到处挖别人家的树根。监狱的门卫带的枪让祖父不敢上前,跟着柳生去洗头他也说是犯法的。这表明祖父对自己所经历的创伤仍然耿耿于怀。当祖父被送进井亭医院后,晚辈们变卖了老宅的雕花大床,还高价将房屋租赁给马师母家开服装店,俨然已经把带有传统色彩的祖父逐出家门。面临着身体和精神双重逃亡的祖父,尝试叫绍兴奶奶为他出谋献策,帮助他找回灵魂。她提议祖父到祖先的坟上“热热闹闹地把魂喊回来”,但早在文革时期红卫兵就把祖父的祖坟强行刨了,现在是塑料加工厂,祖上家产也早已充公。这些看上去是小说中可有可无的情节,背后则暗喻了革命对一个家族伦理的破坏和摧残。事实上,祖父的失魂落魄不单是文革精神创伤的后遗症,也是个人不想从历史中解放出来。随着近代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人们内心的精神世界也越发空虚和无助,很多人出现不能自我消解的精神上的苦闷。因此,如何反思乌托邦精神,对当下的文学以及人类的生存是至关重要的。
保润第一次感受到“失魂”是他将一张少女的照片撕碎后放入祖父房间的“黑洞”中。第二次,他听到了自己灵魂破碎的声音,是他的魂魄被仙女搞丢了。保润迷恋仙女,但他感到不由来的恼怒,因为仙女打心底里就瞧不起他,骂他“脑子里长满了细菌,要打开来,用消毒水、钢丝刷子刷一刷”。这严重伤害了一个少年的自尊,于是他出现了变态的行为——逼迫仙女和他一起跳小拉,最终以捆绑的方式造成了无法挽回的伤害。其实保润本性善良,对祖父也很孝顺,然而他出狱后体会到的只有人性的冷漠,最后被现实一步步逼入绝境。保润对仙女的变态行为是他固执地追求自我认同感来弥补他精神上的个体完整性的不足。但最终仙女并无法安抚他内心的紧张和恐惧,导致在这个时代的创伤下引起了无法宣泄的愤怒。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大多数人都缺少心底的那份生存根基,所以人们都渴望“寻根”。但不管寻求的“根”是绝对的价值真实,还是历史文化原始的初形态的事实,我们都无法得出准确的结论。小说在阴翳的社会背景下,透视了人们精神层面的凋敝和无处救赎、皈依的灵魂,将个人从被压抑的状态中解放出来,获得本质意义上的自由是那个时代人们的精神追求。
小说开头对柳生的描述“他夹着尾巴做人,已经很多年了。”[4]这句话说明了柳生本质上并非恶人。强奸了仙女后,他逃脱了牢狱之灾,但他并没有忘记好友替其所承受的罪过和自己的罪孽。相反,他背负着深深的内疚感,他觉得是自己让家人都活在他错误的阴影下,遭受世人指责,大有“不可承受之轻”。这种强烈的负罪感抹杀了他年少时期的快乐,使他变得谦卑而世故。对于保润,他内心充满了“巨大的愧疚”。于是他接替起了照顾保润祖父的责任。对于陷入困境的仙女,他也真心实意地帮助她。柳生在用自己的方式减轻负罪感。他也是整部小说中唯一一个有着特殊的自我救赎方式的人。然而,他的救赎是有限制的——即不毁掉他现在拥有的生活。小说中多个地方提到他暗示保润,过去的事就让他过去吧。他承担过错都是从个人生存角度加以考量的,并没有摆脱成长的那片土地给他带来的枷锁,只能受困于“现实的生活”这个巨大的阴影中,在挣扎中失去了自我的“可怜”形象。苏童将眼光贴近现实社会底层来窥探隐匿在人们内心深处的痛苦。他不仅刻画了现实社会的黑暗与残酷,还表达出了对现实和人性的关怀和思考。
小说中的仙女,她不仅是这个时代的狂欢者,还是这个时代的迫害者。仙女从出身以来就生长在一个凌乱无章的世界中,这隐喻了资本神话的时代社会秩序的杂乱以及文明发展重建前的状态。而她就是这个时代下最直接、无辜的迫害者:保润变态要求,柳生的强奸,使她的人生彻底改写,并以一种毁灭性的姿态走向了社会的边缘地带。成年之后的她成为当下社会的出卖肉体的高级妓女,采取无原则的方式挣钱。她做过井亭医院特二床郑先生的公关小姐。被解雇后,她回到酒店当歌女。随后还想用肚子里的婴儿敲诈庞先生,试图从富商那里取得巨额财富。小说中的仙女便是以“失魂”的方式一步步陷入信仰缺失的困境而永远无法摆脱命运的桎梏。苏童在这里向我们呈现了在这个金钱至上、物欲横流的时代,女性的身体是如何变成商品,怎样一步步走向毁灭堕落的。在现代性思潮的消费主义、金钱主义肆意解构之下,这样的人物已经已经支离破碎、伤痕累累。
小说上演了少年懵懂的青春到中年残酷的鲜血淋漓的社会现实,折射出了剧烈变革年代中人们的奋进、彷徨和沉沦。他们是时代的施害者,也是受害者,无法摆脱灵肉分离的精神枷锁。这里寄寓了苏童对待当下精神伤痛与历史关联的思考和审视。现如今,当下的大多数人依然处在进退两难的双重境地:一方面没有太强的社会自我意识,另一方面也不重视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苏童绘声绘色地叙说了那个时代的城南旧事,以及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的惶恐与不安。不仅展示了道德、精神的整体性紊乱,还揭示了失魂的人物命运这一永恒问题。
三.时代镜像背后的人文关怀
在苦难面前,香椿树街上的人的灵魂救赎不过是无望的垂死挣扎。在那个物欲横流的时代背景下,保润、柳生和仙女的命运注定逃不出悲剧的结局,他们身上印着那个时代里,千千万万小人物的悲剧。每当困难来临之际,他们不是面对而是逃跑;每当到了面临罪恶的时候,他们又选择了自我赎救。无论最终是选择逃避还是自我赎救,他们都充分表现了人性的悖论。这也是《黄雀记》这篇小说带给我们的现实价值和意义。恰如苏童在2011年获茅奖感言中所说“一个优秀作家的使命就是审视社会与时代,挖掘人性这一永恒主题。”[5]保润、柳生和仙女他们自身的欲望所呈现的复杂人性,交叉着一种绝望与希望的自相矛盾状态。在那个社会环境的逼仄下,他们所遭受的摧残以及欺凌、所欠下的罪与罚,就在这种矛盾状态中走向了渺茫。
苏童在《黄雀记》中这样写道“风一吹,旧社会的桂花与竹子在摇曳,新社会的花草和蔬菜在摇曳,他们在一齐,正好是历史在摇曳。”[6]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我国重要的社会转型期,也是推进现代化进程的发展期。社会生活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的思想也开始遽变。小说中,许多人物对金钱的疯狂追求和道德意识的丧失可以称作为一种“集体的无意识”状态。这是在当时社会下许多人的普遍精神状态。功利、 攀比等不良思想风气逐渐盘踞了人们的大脑,他们逐渐迷失了自己,在汹涌澎湃的时代洪流裹挟下,火急火燎地向前冲。同时,这些不良风气也诱发了许多荒谬的离奇事件,使得社会出现了一连串问题。传统的社会道德伦理秩序在私欲的过分膨胀下逐渐被损坏,首当其冲的就是个人灵魂的丧失和无处安放。犹如小说中的祖父,他一生都在精神式地逃亡,寻找自己丢失的灵魂。他的“灵魂”不只是代表装着祖先尸骨的手电筒,也是个人道德伦理底线的借指和传统美德信仰的标志。保润的母亲,胸狭隘又刻薄自私,她既不符合“贤妻良母”的传统道德标准,也沾染了许多“庸俗化”的小市民习气。人类灵魂深处的美好的丢失已经成为了一种普遍化的现象,这是现代社會转型期裂变的必然结果。拜金主义、信任危机下所掩藏着的空虚的烦恼,正是这种信仰缺失的现实写照。因此,《黄雀记》的真正价值体现在它试图探索一种中国式的灵魂叙事,“呈现出这个时代在发生巨大转型和变化时,所遭遇到的最大窘境——道德、 精神系统的整体性紊乱,这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最大难题。”[7]作者借用“失魂”讽刺当下社会人的普遍状态,轻快诙谐的笔调下蕴藏了对现实、人的生存状态深刻的思考以及强有力的批判。最后保润在婚礼上连捅柳生三刀“复仇”的背后是社会转型期的矛盾的体现。犯了罪的人非但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相反却发家致富、结婚生子。尽管十年来“夹着尾巴做人”也不能够抵消其犯下不可饶恕罪恶的本质。平白无辜的保润却要遭受牢狱之灾,赔上所有的一切,甚至连自己的老父亲去世、母亲离家出走也无人告知,着实凄凉。此处作者的“荒原”意识也开始浮现——也就是说在这个肮脏黑暗的世界里,唯有金钱是行走的唯一标准。所谓的正义、道德都被淹没在嘈杂的人海中,逐渐黯然失色。因此,作者开始对这样焦躁低迷、萎靡不振的世道进行无情的抨击。在驳杂荒芜的社会环境下,香椿树街上的人们已然是看不到生活的希望,一群如保润一般的社会底层民众,深陷命运的泥潭而无力自拔,犹如困兽一般,不断被压抑、被欺侮,直至无望亦无声。
二十世纪后期的中国,现代化已经成为了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在这新旧政治、文化交替之际,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发生了转型与重构,反抗叛逆的矛盾心理和人性的迷惘已逐渐成为笼罩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理写照。荒芜也变成了现代社会变革下人类精神困厄的真实写照。现代化作为一种合乎历史发展趋势的目的而存在,不单单指引着文明向前发展的新趋势,背后也潜藏着种种未知的危机。错综复杂、令人捉摸不透的社会现象仿佛冥冥之中的无形怪手,将人们任意玩弄与弃绝,使每个人都无法逃离精神的困厄,使每个生命所期待的自由呼吸成了现世的奢望。这是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西方的价值失落、生活无意义的现代性问题有着本质的区别。《黄雀记》体现了苏童对人性、社会深刻的思考和强烈的批判,以及他对时代和社会强烈的使命感和人文关怀,这种关怀人类命运、社会现实的使命感,是时代变革中人的精神境界提升的推动剂。
参考文献
[1]涂桂林:《苏童:这条小街是我一生的写作地图》[N].《中国新闻出版报》,2013 年12月27日.
[2]张琳:《现代性的信仰困境与信仰塑造》[D].复旦大学,2012年,第88页.
[3]李欢:《凌乱人生与精神荒漠》[N].《东莞理工学院学报》,2015年04月27日(第22卷第6期).
[4]苏童:《黄雀记》[M].浙江人民出版社:苏童,2013年版,第165页.
[5]苏童:《茅盾文学奖得主苏童:作家的使命是审视社会与时代》[J].南报网,2015年8月7日.
[6]苏童:《黄雀记》[M].浙江人民出版社:苏童,2013年版,第123页.
[7]张学昕:《苏童长篇小说<黄雀记>变动时代的精神逼仄》[J].中国作家网,2013年7月10日.
本文系江西省社会科学“十四五”(2021年)基金项目:新时代小学教科书中文学意象的多模态话语研究(课题批准号:21JY42D)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