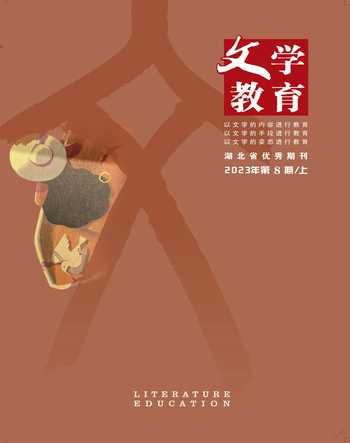心灵的风景:从《复活》看托尔斯泰的自然书写
田雨冬
内容摘要:大自然(也叫风景描写)是指文学作品中对大自然的一切有生命和无生命的事物的描写,它作为文学所构建的艺术世界的形象之一,往往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俄罗斯文学自诞生起,就蕴含着无数对大自然饱含深情的描绘,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创作更是其中的代表。在小说《复活》中,自然界的事物、季节和天气都具有象征性意义,自然作为独立存在的“天然启示者”将上帝的真理带到人的心中。作为聚焦人物精神世界的作品,《复活》体现了作家将自然风景同人物心理描写相结合的高超技巧。大自然对于展现小说主人聂赫留朵夫和马斯洛娃的心理活动和他们精神“复活”的过程,塑造更为生动的人物形象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俄罗斯文学 《复活》 大自然 心理平行主义
大自然是俄罗斯文学永恒的主题,对其饱含深情的描绘存在于文学进程的各个阶段。正如哈利泽夫所言,“十九到二十世纪的每一位作家笔下都有着一个特别的,专属于他自己的自然世界。大自然不仅以它的魅力俘获了作家们,也在他们笔下的人物心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5]242—243无论是赋予大自然以无限哲理性的丘特切夫,还是将浪漫的激情寓于写景之中的茹科夫斯基,亦或是令池塘和树木都充满象征意义的卡拉姆津,秀美的自然美景在俄国古典主义文学中熠熠生辉。近代以来,风景描写开始在与人物的相互作用中体现其价值,人与自然的交流、融合与对立逐渐成为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主题,列夫·托尔斯泰的创作就是典型体现。托尔斯泰将自然视作“净化人类心灵的天然启示者和永不枯竭的道德源泉”。[2]158从《哥萨克》、《高加索》、《战争与和平》到《安娜·卡列尼娜》,主张顺应自然和回归自然的生态主义觀念一直贯彻在作家的创作中,并在长篇小说《复活》中得到了最为集中的体现。托尔斯泰强调,自然作为独立存在的“天然启示者”将上帝的真理带到人的心中,而人只有尊重自然,才能拥有独立的人格和完整的自我。
俄国19世纪文论家维谢洛夫斯基在诗人瓦·亚·茹科夫斯基的抒情诗中最先发现了“心灵的风景”这一现象,其作为俄国抒情诗歌乃至小说传统中广泛存在的艺术表现形式,体现了俄国作家对自我与外在、主体与客体关系所采取的一种独到的宇宙人类论立场。维谢洛夫斯基指出,作为文学创作手段的“心理平行法”旨在进行人之形象与自然形象在行动或者状态上的比较,它“并非将人类生命与自然生命相等同,也不是基于对象分隔性的比较,而是根据行为和运动的特征将对象并置。”[7]101作为一种综合性的文学情境,心理平行手法兼具主题阐释、人物塑造、结构建立和情节推进的功能,这一手法贯穿了《复活》的自然书写,对塑造主人聂赫留朵夫和马斯洛娃的形象,完善人格复活的叙述构建,展现作品的哲理意涵起到重要作用。
一.感官与情节并置
感官细节作为塑造动态的内在生活的手段,能够非常直观地将“人物情绪、体验、意识和无意识活动的产生和变换”[6]183传递给读者。在小说《复活》中,“心灵的风景”首先体现为灵动可感的大自然形象。小说的风景描写对象丰富,涵盖自然与社会诸多方面,包括不同种类的植物、动物、天气现象和城市风光,等等。托尔斯泰不仅擅于传达“自然本身所具有的包容而稳定的本性”[5]243,还注重不同时节中感官细节的差异,通过意象衬托传递殊异的情感色彩。例如,小说开篇的景物描写突出了太阳为生命提供能量的特质,以万物的生机烘托平静而充满希望的氛围:“太阳照暖大地,青草在一切没有除根的地方死而复生,不但在林荫路的草地上长出来,甚至从石板的夹缝里往外钻,到处绿油油的。桦树、杨树、稠李树生出发黏的清香树叶,椴树上鼓起一个个正在绽开的花蕾。寒鸦、麻雀、鸽子像每年春天那样已经在欢乐地搭窝,苍蝇让阳光晒暖,沿着墙边嗡嗡地飞。植物也罢,鸟雀也罢,昆虫也罢,儿童也罢,一律兴高采烈。”(1,5)然而在小说中段,同样是以太阳为核心描写秋日图景,衬托的形象换为白桦树和落叶松这种高大、苍劲的植物,凸显出太阳的高度,这是为了抒发真理昭昭,造物主审度世间的感受:“(太阳)高悬在树林之上……树木、水塘、教堂的拱顶和十字架都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天气放晴,雾消云散,广阔的田野远处现出影影绰绰的群山”。(1,572)
除视觉画面的勾勒外,托尔斯泰还擅长凸显景物的声音、气味和光线细节,塑造立体可感的大自然形象。例如,在描写以聂赫留朵夫视角出发的街景时,读者的听觉、嗅觉、视觉都活跃了起来,在头脑中形成以主人公视角出发的大自然的四维影像,从而能够最大限度地体会主人公的心情:“这是清新无风的月夜,街上隆隆滚过车轮,过后一切又归沉寂。紧靠窗口的地上呈现着一棵高大光秃的白杨树枝杈的影子,纵横交错的树影清晰地印在一块空旷的沙地上。左边是一个仓房,房顶在明亮的月光下显得发白。再往前是枝杈交织的树丛,透过树丛隐约可见栅栏的黑影。聂赫留朵夫望着被月光照亮的花园、房顶,望着白杨树影,呼吸着令人兴奋的清新空气。”喧闹与寂静,月光与树影,仓房与树丛等形象的矛盾关系与聂赫留朵夫心受到压抑的情欲相得益彰。
二.心理与空间互动
别尔嘉耶夫曾说,“‘对大自然之同情的观照还在语言床的阶段,还在远古神话时代,就已然与人相伴随”。[3]2人自诞生之日起,就与自然空间有非同一般的紧密联系,而这种联系在俄罗斯人的民族意识中体现的尤为明显。无论是《战争与和平》中的鲍里斯,还是《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列文,托尔斯泰笔下的人物都是在对自然全身心的热爱与亲密无间的交接中找到了最终的精神归属。长篇小说《复活》作为聚焦人物精神世界的作品,更加体现了作家将自然风景同人物心理描写相结合的高超技巧。
小说《复活》中的主要人物都有对环境高度敏锐的感知力,她们对自然的体验往往境随心转。在马斯洛娃出场的片段,作家以近乎自然主义的笔法详细地描写了马斯洛娃在监狱中的生活环境:“就连监狱的院子里也有新鲜的郊外空气,令人精神爽快……然而长廊上的空气却饱含着伤寒病菌,充满粪便、焦油、腐物的臭气,凡是新来的人立刻感到萎靡不振,心境郁闷。”这种环境,就连“闻惯恶劣空气”的女看守也依然不能适应。然而,长期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马斯洛娃却安之若素。这是由于她此时尚未意识到真理,甚至为自己的一套人生观点而感到得意,这从她的步态和打扮上都看的出来。马斯洛娃“分明故意让几绺鬈曲的黑发从投进里滑下来”,在面对看守长时“把身子站的笔直,挺起丰满的胸脯……走到长廊上,微微仰起头,照直瞧着看守长的眼睛,停住脚,准备着不管要求她做什么,她一律照办”。(1,7)我们知道,“监狱”的意象对监狱之外的人们来说代表对罪恶的禁锢,对监狱之内的人来说也是对善之世界的隔绝。处在与自然隔绝程度最高的监狱环境中的马斯洛娃,其精神是完全没有得到救赎的。
尽管如此,作家在自然描写中埋下了人物新生的伏笔。当马斯洛娃经过走廊去接受提审的过程中,她感受到了清爽的春天的空气,这使她感到高兴。当马斯洛娃的脚差点碰到一只蓝灰色的鸽子时,鸽子飞起来将一股风送到她的耳边,这使得她“微微一笑,然后想起她的境况,就沉重地叹一口气”。(1,8)处在人工环境的禁锢中的人物无法与自然亲密接触,就极易忽视真理而导致心灵蒙昧,而感受自然则成了他们倾听内心上帝的召唤,寻回真理的途径。这时,一个乡下人对马斯洛娃画了一个十字,使她脸红了起来。在托尔斯泰笔下,乡下人是更加接近上帝和自然的,这一细节同样寓指马斯洛娃的自我觉醒。鸽子、乡下人、清风的意象所象征的上帝的真理已来到马斯洛娃身边,只是尚未被她所接受。
在小说中,空间背景的转换同样具有心理功能。处在人工环境中的人物更倾向于利己和闭塞的状态,无法聆听到内在自我的声音,而身处大自然之中则会让人物更坚定的找寻自我。聂赫留朵夫最初的堕落就是源于身处的环境从乡村转换到军队。他与马斯洛娃最初的纯恋萌发于自然的环抱,在丁香树丛的掩映之下他们有了第一次亲吻,却彼此都不明白自己正经历着何种感情。托尔斯泰借此表明,人最本真对自然之美的感受力是平等的人格之爱的源泉,它可以保证爱情的纯洁性,而纯洁的、利他主义的爱情观正是精神之人的特质。来到军队后,聂赫留朵夫停止了倾听自己的心灵:“原先,同大自然的交接,同在他以前生活过、思索过、感觉过的人(哲学和诗歌)的交接,才是重大而必要的,如今重大而必要的却是各种人为的制度以及跟同伴们的交接。”(1,62)从制度之外进入到制度之內的转换对应着忠于自我到关注他者的转变,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人物纯洁的道德信仰彻底遗失了。
在小说第二部中,聂赫留朵夫回到库兹明斯克耶庄园,见证田间忙碌的春播,其精神开始向自我复归,这首先表现在重拾青年时代的心愿——为农民争取更多的权益。然而在实践的过程中,聂赫留朵夫遭遇到来自多方面的阻碍,他想将自家田地低价租给农民,这样的事情在农奴制的社会不仅不被贵族阶级所理解,更不能为农民所接受,聂赫留朵夫的善意遭到的尽是农民的怀疑与嘲讽。面对困难,他的内心难免对精神复活的意义产生动摇,但美丽的俄罗斯大自然时刻提醒着主人公精神复活的重要意义,坚定他的决心。在库兹明斯克耶的一个雷雨夜,聂赫留朵夫思索着如何能够让农民接受自己的善意,天气仿佛是主人公心情的一面镜子,真实地反映了其逐渐认清自己内心的过程。当聂赫留朵夫的思想活动由童年的美好回忆转到在库兹明斯克耶经受的考验,发现自己并不再留恋自己的财产,意识到自己帮助囚犯的信念和意愿时,本来只是“从远处响起”的雷声由远及近,“黑压压的乌云堆满了天空”,鸟儿的歌声停止了,“一道闪电照亮了整个夜空。万籁俱寂。聂赫留朵夫还没来得及数到三,突然头顶上响起一声不及掩耳的霹雳,紧接着整个天空都滚动着隆隆的雷声。”(1,422)此时,主人公的心情也随之激昂起来:“‘对,对他想,‘我们生活中的一切事情的全部意义,我是不可能理解的……然而,去执行铭刻在我良心上的上帝的意志,我却是能够做到的,这一点毫无疑问。我去做了,我毫无疑问会心安理得。”(1,423)在叙述平稳的切换中,主体心理活动经客体的映照而愈见明朗。同时,象征“上帝的意志”的雷声改变了主体的心境,随着一场雷雨从酝酿到瓢泼而至,主人公的信念也从朦胧转为坚定。大自然在这里作为一个与人物积极互动的形象,使我们更充分地体会到聂赫留朵夫心理活动的过程,明白他是如何最终认识到道德自我完善的意义。
随着小说临近尾声,聂赫留朵夫漫长而艰辛的自我救赎之路已临近终点,此时作者再次安排大自然出场,为主人公带来至关重要的心灵启迪:“正是闷热的七月天气。街道上的石头、房屋、铁皮房顶经过闷热的一夜以后,还没有冷却,把它们的余热送到炎热而停滞的空气里。这时候没有风,不过即使起风,也只能刮来一股又臭又热的空气,包含着灰尘和恶臭的油漆味。”(1,431)闷热恼人的天气,狱长和押解官粗暴的态度,犯人的死亡都使得气氛异常压抑,处在这种环境中的聂赫留朵夫在火车上思索着当权者的恶劣行径,失望的情绪越来越强烈。就在此时,天气剧变,下起了瓢泼大雨。呼吸着新鲜的空气,看着蓦然变得明澈鲜艳的庄稼和植物,主人公的思维随着情绪的高扬而变得活跃,他联想到担任官职的人的心就好比“土地铺了石头,雨水就渗不进去”,意识到自己同这些人的区别正在于后者“不承认由上帝自己印在人们心灵上的那种永恒的、不可改变的、不能背弃的戒律才是法律”。(1,468)大自然再次充当了上帝真理的传播者,主人公认识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种种变化的本质所在,明白使自己获得“新生”的正是上帝的救赎:“一方面在难熬的炎热之后阵阵凉风使他周身舒畅,另一方面他体会到在他心中盘踞很久的那个问题这时候在他已经彻底澄清了。”(1,465)至此,聂赫留朵夫精神的复活彻底完成。
三.自然的象征性
“复活”是小说的核心性的隐喻,它既是聂赫留朵夫对马斯洛娃爱情的“死而复生”,也是男女主人公在对彼此和上帝纯洁的爱情中灵魂相交融的那个复活节夜晚,但它最重要的含义,还是指自我救赎。值得注意的是,大自然在小说中是人精神的拯救者,是小说人物领悟真理的重要途径。在小说开篇的一段景物描写中,作者运用了一连串的让步句式表现大自然万物顽强的生命力,暗示自然规律不以人的作用为转移。“尽管好几十万人聚集在一块不大地方千方百计把他们居住的那块土地毁坏的面目全非,尽管他们把石头砸进地里,害得任什么植物都休想长出地面,尽管出土的小草一概清楚干净,尽管煤炭和石油燃烧得烟雾弥漫,尽管树木伐光,鸟兽赶尽,可是甚至在这样的城市,春天也仍然是春天。”(1,5)作者在小说开篇就申明了自然本位的道德立场,指出未经人类改造的自然世界才是上帝真理之所在:“人们认为神圣而重要的并不是这个春天的早晨,也不是上帝为造福众生而赐下的这个世界的美丽,那种使人趋于和平、协调、相爱的美丽;人们认为神圣而重要的却是他们硬想出来借以统治别人的种种办法。”(1,5)在托尔斯泰看来,信奉上帝就等同于信奉自然,得到人与人之间“和平、协调、相爱”的世界;忽视上帝,转而相信人“硬想出来”的办法,就会导致互相欺骗和互相折磨。等待救赎的降临就仿佛亘古不变的自然规律一样,是不以个人的努力为转移的,救赎永远是来自外部的力量,人只能被动地接受它。
在《复活》中,自我救赎与爱情的联系也是非常紧密的,但这种爱情只能是纯洁的精神之爱和灵魂之爱。当爱情受到了欲念的支配,就会由利他的、善的变为利己的、恶的,进而成为毁坏人内在世界的力量,引人走向堕落的深渊。男女主人公第一次见面时彼此所体验到的那种感情本是神圣的,然而由于在聂赫留朵夫的身上同时存在利他的精神的人和利己的兽欲的人,所以他们爱情的本质逐渐腐化。在聂赫留朵夫强行占有马斯洛娃的那个夜晚,作家利用月亮、河流和雾等自然界中的事物营造出阴森可怖的氛围,这些具有象征意义的形象暗示着人物受到邪恶欲望支配的内心。作者写道,虽然那是一个“天已经很亮了,但太阳还没有升起来”的清晨,但象征着堕落的黑夜很快就再度来临。聂赫留朵夫走出房门,向马斯洛娃的小屋潜去,此时“门外漆黑,潮湿,温暖。整个空中弥漫着白茫茫的大雾,在春天,这样的雾消融着残雪,或者正是因为残雪在融化,才升起了这样的雾。正房前边,百步开外,在陡坡底下有一条河,传来一种奇怪的响声:那是冰层在碎裂。”(1,239)聂赫留朵夫与喀秋莎第二次见面时,他全身被雨淋湿,披着一件潮湿的军大衣,“潮湿”意象与春水意象正是人物早已突破理性“冰封”的情欲的象征。作者不止一次地描写从河流那边传过来的奇怪声响,并暗示这种声响是由某种未知的、邪恶的事物所发出的:“不知是一个什么东西时而呼哧呼哧地喘气,时而咔嚓一声裂开,时而哗啦一声倒下来,时而薄冰像玻璃似的碰得叮铃叮铃地响。”(1,80)大雾和黑暗中的野兽一样的东西隐喻着聂赫留朵夫的欲念。因此,在聂赫留朵夫最终占有喀秋莎之后,自然的场面形象地喻示出人物潜意识之恶的甚嚣尘上:“冰块的崩裂声、磕碰声、喘息声越发响起来,而且在原有的各种响声之外,还添上了流水的潺潺声。”(1,83)与明亮的圆月相对,“弯弯的下弦月”所代表的邪恶意味不言自明。
在小说《复活》的艺术世界中,月光是一个善恶交织的意象。它既有蒙蔽人双眼的能力,也可以使人看清自己最真实的内心。明亮的圆月使主人公与自身的心灵链接,而大雾中“朦胧地照着一个乌黑而可怕的什么东西”(1,83)的下弦月却象征堕落的诱惑。当聂赫留朵夫身上的“精神之人”开始觉醒之后,他的眼睛也开始看得到原本被他刻意忽视了的生活中的丑恶和虚伪。在描写聂赫留朵夫对米西的看法时,作者用了这样的比喻:“有的时候他仿佛在月光下瞧着她,在她身上看见了一切优美的东西……有的时候他好像在明亮的阳光下似的,却忽然看见了她的缺陷,而且也不能不看见。”(1,121)同样的,在聂赫留朵夫感觉到上帝的存在和自己灵魂里所起的变化的那个夜晚,他看到这样一幅自然与人工和谐共存的图景:“窗外是花园。那是月夜,没有风,空气清新。在窗子紧跟前,现出一棵高大的杨树的阴影,光秃的树枝的影子犬牙交错,清楚地印在一块打扫干净的小空场的沙土地上。左边是堆房的房顶,在明亮的月光下显得发白。正面,树木的枝丫交织在一起,后边现出一道围墙的黑影。聂赫留朵夫瞧着被月光照亮的花园和房顶,瞧着杨树的阴影,吸进清爽新鲜的空气。”(1,136)与之前象征邪恶的下弦月不同,明亮的月光使地面上的一切无所遁形,每一件事物都清晰地出现在人物的视线里,拥有属于自己的阴影,这种明暗交织的状态不同于青天白日下绝对的光明,却暗合着聂赫留朵夫当时的状态——精神的人开始觉醒,理性如同人类文明一般开始尝試着驯服自然力。与马斯洛娃所感受到的清新的风一样,干燥、清爽的空气同样也为对聂赫留朵夫来说带来了心灵的改变。聂赫留朵夫在库兹明斯科耶庄园里同自我对话时,天空中同样是一轮“滚圆的明月,乌黑的阴影铺开,盖满了整个院子。破败的铁皮房顶开始闪闪发光”。(1,299)满月的明亮光芒总是给予人物心灵的启迪,引导他走出困顿与迷惘的境况。
常言道,一切景语皆情语,文学作品中的情与景自古密不可分。在《复活》这篇作品里,作者笔下的大自然具有丰富的象征性意义,它承载着传递真理、救赎心灵的使命。《复活》中的大自然不仅为人物倾听和回归自我提供环境,也参与着人物的情绪和内心活动变化的进程,成为映照“心灵的风景”的一面镜子。诚如维谢罗夫斯基所言,“作家总是能够抓住那些充满诗意和幻想的元素,那些将人类生活同周遭鲜活而生动的现实紧密结合起来的那些捉摸不定的联想”。[4]471对于托尔斯泰来说,大自然就是开启心灵之门的钥匙,作家笔下自然世界解读不尽的魅力有待继续发掘探索。
参考文献
[1]托尔斯泰著:《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十一卷,汝龙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
[2]易宋江:《从托尔斯泰的自然观看其文艺观中的浪漫主义因素》,《湖南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第158页。
[3]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的宗教阐释》,邱运华、吴学金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2页。
[4]亚·瓦·维谢洛夫斯基:《情感书写与“心灵的想象“》,圣彼得堡:皇家科学研究院印刷处,1904年。
[5]瓦·叶·哈利泽夫:《文学理论》,莫斯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
[6]尼·季·塔玛尔琴科:《诗学:实用术语和概念词典》,莫斯科:库拉金诺出版社,2008年。
[7]亚·瓦·维谢洛夫斯基:《历史诗学》,莫斯科: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
本文系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KYCX17_0014)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