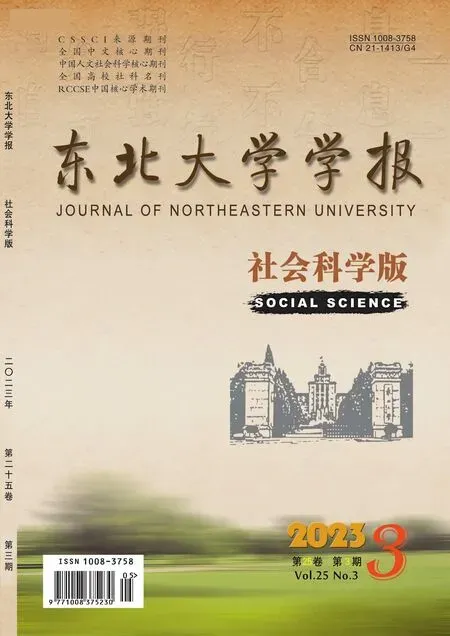从主体性到客体性:卡尔森环境美学对传统自然美学的批判与突破
刘 希 言
(南开大学 哲学院, 天津 300350)
自然美的主客体性问题既是自然美学研究的基础性问题,也是一般美学研究的基础性问题,甚至可以说,解决“美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何回答“自然美是什么”这一问题。对此,朱光潜早有论断,他在总结我国20世纪50年代美学大讨论时指出:“最近一年的美学讨论证明了‘自然美’对于许多人是一大块绊脚石,‘美究竟是什么’的问题之所以难以解决,也就是由于这块绊脚石的存在,解决的办法只有两种:一种是否定美的意识形态性,肯定艺术美就是自然中原已有之的美,也就是肯定美的客观存在;另一种是否定美的客观存在,肯定艺术美和自然美都是意识形态性的,即第二性。第一种就是蔡仪、李(泽厚)、洪(毅然)和一般参加美学讨论者所采取的办法,第二种就是我所采取的办法”[1]。
然而,彭锋认为,朱光潜“所列举的两种解决办法都没有触及到问题的要害,因为这两种解决办法可以适用于一切审美对象,自然作为审美对象的独特性并没有突显出来”[2]。除此之外,囿于时代的局限性,各位前辈学者在关于这一问题的认识上可能不够全面。换言之,在当今自然美学逐渐没落与生态危机愈演愈烈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对自然美学的主客体性问题也许会有新的思考。我们知道,西方环境美学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并且“自然区别于艺术的本质特性”是其探讨的中心议题,那么我们能否从其中探寻到某些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加拿大学者艾伦·卡尔森(Allen Carlson)的“以客体为导向”的审美欣赏理论值得我们重点关注与详细考察。本文试图以卡尔森的环境美学思想为考察对象,通过梳理与总结他关于自然美学主客体性问题的观点与看法,分析并揭示其对传统自然美学理论的反思与突破之处,以期对自然美学乃至美学基础理论建设提供些许助益。
一、 “以客体为导向”的审美欣赏理论
“美学观”是美学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深谙此道的卡尔森在详述自己的环境美学思想之前首先提出了自己的美学观:“美学是哲学的这样一个领域,它关注的是当事物影响我们,尤其是以一种令人愉悦的方式影响我们的各种感官时,我们对这些事物的欣赏。”[3]ⅹⅶ简言之,在他看来,美学就是“审美欣赏理论”。作为一名深受分析美学影响的研究者,卡尔森深知,为了避免歧义,我们在使用一个概念或术语的时候必须对之进行明确界定。正因如此,他在《艺术欣赏与自然欣赏》一文中特意用一节考察了“审美欣赏”这个概念,但在梳理美学史的过程中他遗憾地发现:对于“审美欣赏”,美学家往往只关注前者——审美——的性质,却忽视了对后者——欣赏——的考察,尽管“欣赏这个概念无论对哲学美学还是对日常事物而言都是关键的”[3]103。不过值得庆幸的是,“虽然哲学美学对此概念表述甚少,但仍可以从它对审美的考察中得到一些有益的结论”[3]107,换言之,通过反思传统审美理论的洞见与缺陷,我们可以获得关于欣赏的准确认识。
诚如卡尔森所言,对“审美的性质”的探讨总是离不开一个关键概念——无利害性(disinterestedness)。作为一个美学术语,“无利害性”最先由夏夫兹波里引入,经过哈奇森、艾里生等人的进一步阐发,最后在康德那里发展成为“审美”的标志。据康德自己的解释:“被称之为利害的那种愉悦,我们是把它与一个对象的实存的表象结合着的。所以一个这样的愉悦又总是同时具有与欲求能力的关系,要么它就是这种能力的规定根据,要么就是与这种能力的规定根据必然相连系的。”[4]可见,所谓“无利害”就是不关心“对象的实存”(existence of object),只关心对象“呈现”于人类心灵上的“表象”(representation),仅根据表象能否引起主体的愉悦之感来判断一个事物是“美的”还是“不美”。之所以有此规定,一是因为在康德看来,实存与欲念相连,会使得愉悦不再纯粹;二是因为康德认为,人类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只能认识到“物的表象”而不能洞悉“物自身”,换言之,在康德看来,一切认识对象,既然能被认识到,就必然经过了人类心灵的加工与建构。由此可见,康德美学本质上是一种“忽视事物自身的表象美学”,而这正是“以康德为代表的现代美学的根本缺陷”[5]。
不可否认,无利害观念之于美学基础理论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保证了审美欣赏的客观性,使得欣赏者从个人的实用性的、功利性的欲求或目的中跳脱出来,集中注意力于对象本身;使得审美活动从其他经济的、政治的日常活动中区分出来,获得了独立的身份。然而,由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学家们的过度诠释,这种观念逐渐变成制约美学理论发展的枷锁。这一枷锁体现为三大教条:一是审美欣赏总是关于某个具体“对象”的欣赏。为了减少外界的干扰,将注意力集中于欣赏对象本身,欣赏者往往借助框架、基座、舞台等形式人为地将审美对象与其周围环境分隔开来。这种做法虽有利于划定欣赏的边界、明确欣赏的焦点,但却使欣赏对象沦为一种孤立的、静止的存在,失去了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二是审美的焦点局限在对象的“形式特性”上。作为一个独立的存在,审美对象既然能与周围环境区分开来,说明该对象本身具有某种突出的、醒目的特性。这种特性只能是线条、色彩等形式要素的组合或安排,因为根据无利害观念,审美欣赏关切的只是事物呈现在人类心灵上的表象。三是审美的方式规定为远距离的静观。这一点同样是由“对象性”决定的。欣赏者与欣赏对象之间的距离不仅是物理上的,且是心理上的——只要不是呈现于欣赏者感官上的,都与审美欣赏无关。总而言之,如卡尔森所言,对无利害观念的过度阐释使得曾经丰富、广阔的欣赏传统彻底沦为一种有限的、分离的状态,成为“呆牛般的凝视”(blank cow-like stare)[6]35。
不难预料,这种逐渐僵化的审美理论必然会遭到时代的厌弃,而在所有反对声中,当以美国分析美学家乔治·迪基(George Dickie)最为强烈。在《审美态度的神话》一文中,迪基一一分析了使“审美态度”得以可能的三个基本概念:“距离”、“无利害性”和“不及物”。通过批判这三个概念,迪基揭示出“审美态度”理论的空洞性,即并不存在这样一种特殊的心理状态,它只是美学家主观臆造的产物。不仅如此,“审美态度”理论的缺陷还在于“在根本上误导审美理论”,因为它对“审美关联性因素”设置了界限[7]。有鉴于此,迪基尝试打破这条界限,将其他因素都纳进审美欣赏的范围。在《艺术与审美》一书中,他在丹托的“艺术界”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艺术惯例论”。在他看来,一件艺术品之所以能成为艺术品,不是因为它本身具有某种客观的属性,而是因为它被某种“社会体制”所认可。这就将审美判断的标准从艺术品自身的“小语境”扩展到外部的“大语境”,这种外部语境包括艺术家的意图、公众的理解以及艺术品所处的历史、文化、社会传统,等等。
其实,不止是迪基,20世纪中期有很多美学家在“审美”的理解上都发生了这样一种范式性的转变:审美对象不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而是一个与审美主体密不可分,受其影响并由其塑造的整体性存在。正因如此,审美的焦点不再局限于“形式”这一种,而是包含所有未出现在客体本身内的思想、形象或知识。这就意味着审美模式不再是远距离的静观,而是主体的全面参与。不可否认,通过对无利害观念的反思,美学又恢复了曾经的丰富性与积极性,但是,审美边界的无限拓宽也使得它不得不面临这样一个诘问:审美对象区别于其他日常物,审美活动区别于其他日常活动的独特性又在哪里呢?正因如此,卡尔森认为,迪基对“审美态度”的消解其实是一种过度的反应,就像泼洗澡水时将盆里的孩子一道泼掉了。在他看来,“审美态度理论”是区分“审美”与“非审美”的基本要求。如果没有这些原则的限制,我们就无法对“审美的性质”作出解释,最终可能面临“美学的终结”[8]。
在卡尔森看来,新旧模式之间的分歧在于如何处理“审美相关性问题”(problems with aesthetic relevance)。这一问题,借用杰洛姆·斯托尼茨(Jerome Stolnitz)的经典表述,就是“未出现在客体自身之中的思想、形象、知识,是否与审美体验相关?如果是,那么什么条件下才是相关的?”[6]53由前文可知,对于这一问题,新旧范式给出了两种极端的答案:前者认为“除了‘呈现在欣赏者感官上’的东西,任何东西都与审美欣赏没有关联”,而后者认为“任何未呈现在感官上的思想、形象或知识都可以与审美欣赏相关”[3]129-131。在卡尔森看来,二者之所以会走向两种极端,是因为他们都将审美判断的标准建立在主体之上,也就是说都通过关注“欣赏者的状态”来解决审美相关性这一问题——对前者而言,欣赏需要主体的一种特殊的审美态度,而对后者而言,这种特殊的审美态度并不存在,因此任何状态下的欣赏都可以看做是“审美的”。如此一来,对审美相关性问题的回答便走向两个极端:“要么什么都不需要,要么什么都可以”[3]131。有鉴于此,卡尔森认为在这两种极端之间必然存在着一个“稳定的中间地带”,而到达这一地带的最佳方式是“不把答案与欣赏主体联系起来,而是与欣赏客体联系起来”,即建立一种“对于审美关联性问题的‘以客体为中心’的立场”(the object-focused approach to the question of aesthetic relevance)[3]132。这种立场之所以能避免走向极端,是因为对于一个特定的客体而言,必然存在一些外部信息与欣赏它有关,但同时也存在一些信息与它无关。换言之,“客体本身及其特性”一方面对欣赏者作出要求,另一方面也对其进行了限制。
正是通过从主体转向客体,卡尔森提出了一种新型美学观——“以客体为导向”(object-orientated)的审美欣赏理论。如其所言:
跟随客体的引导,也就是被“客体地”引导。这种客体的意义是最基本的:它是关于客体及其特性的,与那种关于主体及其属性的主体的正相反。在这个意义上,客观地欣赏,就是欣赏事物本身及其所具有的属性。它与主观地欣赏是相反的:在这个意义上,主体(欣赏者)及其特性在某种程度上是强加于客体的,或者,更普遍地说,将不属于客体的一些东西强加给它。[3]107
正如卡尔森所言,这种“以客体为导向”的审美理论并非他个人首创,早在斯托尼茨与保罗·齐夫(Paul Ziff)那里就已见端倪。
与传统一样,斯托尼茨也是通过“审美态度”来界定“审美欣赏”的,但是,在他看来,“审美态度”并非是一种“消极被动的静观”,而是一种“警示和充满活力的行为”[6]37,因为“态度”本身蕴含着一种“导向性”,而这种“导向性”会“使我们作出反应”[6]33。然而,斯托尼茨同时指出,这种“反应”并非是一种主观臆断的行为,而是一种“同情式”的反应。所谓“同情”就是“从客体自身角度接受它,遵从客体自身之引导,并与客体相呼应”[6]36。这种意识从斯托尼茨对于“审美相关性问题”的回答可见一斑。在他看来,判断一种知识是否与审美相关,必须符合三个条件:“当它不削弱或破坏对客体的审美关注时;当它适合于客体的意义和表现力时;当它提高了对客体直接审美反应的质量和意义时”[6]58,简而言之,当这种思想、知识是关于“客体”的,他们才与审美欣赏相关。
齐夫也强调了“以客体为导向”的知识之于审美欣赏的重要性:“欣赏”一词尽管经常用于表示“感激之情”,但其首要内涵则是“判断或评估”[9]101。正因如此,作为一种评价性活动,审美欣赏必然包含着一定的认知因素。不过,齐夫同样指出:这种认知因素只有关乎对象本身及其特性时才能构成恰当的审美欣赏。基于这一观点,齐夫提出了“观赏的行为”(act of aspection)这一理论。在他看来,万物皆可欣赏,但由于不同的对象具有不同的特征,所以“观赏行为的特点、条件以及必需的性质、技巧和欣赏者的能力也需要随之不断变化”[9]135。换言之,只有具备了与欣赏对象及其特性相关的知识,审美欣赏才可能是恰当的。
综上可见,在卡尔森看来,审美欣赏应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作为欣赏者,我们首先需要一种“审美态度”,使自己摆脱功利性的目的或欲望的束缚,集中注意力于客体本身。随后在客体的引导下,充分调动起自身的认知或情感能力对该客体作出“反应”。最后,在欣赏者与欣赏对象的平等交流与积极对话中,审美欣赏移向一种更加“交融”且“完整”的体验。由此可见,“审美欣赏”的性质共有三点:“客体导向性”“回应性”与“交融性”。其中,“客体导向性”是“审美欣赏”可以称之为“审美”的保证,“回应性”是“审美欣赏”区别于传统“审美”的关键,二者结合,最终使审美欣赏移向一种更加亲密的、整体的且无所不包的体验。诚如卡尔森的总结:“欣赏呈现为一种交融的精神和肉体的活动(engaged mental and physical activity)——可应用于任何客体,对该客体有强烈的反应,几乎排他性地只接受该客体之性质的引导。”[3]107
二、 “自然本身及其事实特性”与“如其本然地欣赏”
根据“以客体为导向”的审美欣赏理论,恰当的自然审美欣赏就是“按照自然的本然面貌及其所具有的特性”去欣赏,简言之,如其本然地欣赏。那么问题便是,什么样的面貌才是自然的本然面貌?什么样的特性才是自然本有的特性呢?在《景观与文学》一节中,卡尔森将与自然审美相关的信息分成了三类:形式的(the formal)、事实的(the factual)和文化的(the cultural)[3]219-240。
如卡尔森所言,对自然环境之形式特性的排他性关注与艺术中的形式主义传统有关。作为形式主义的代表,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认为,“要欣赏一件艺术品,我们不需要从生活中获得任何观念或知识,我们唯一需要的是对形式和颜色的感觉以及对三维空间的认识”[10]30。自然环境具有审美价值,当且仅当其被视为“各种各样交织在一起的线条、色彩的纯形式的组合。……谁没有,至少在其一生中有一次,偶尔以纯形式的眼光欣赏某种景观呢?就在某一时刻,不是把它们看成一片田野和村舍,而只当作线条与色彩来欣赏”[10]45。除了形式主义,如画模式也将焦点放在形式特性上。为了获得“如观画作”般的审美体验,18世纪的人们发明出一种新型的观赏工具——克劳德镜。这种镜子可以帮助人们实现操控自然的愿望:通过为自然添加一个边框,人们可以避免外界的干扰,将注意力集中于自然对象本身;通过将风景移到适当的距离,人们可以找到呈现出自然的柔和色彩以及眼睛所能感知到的最规范视角;通过将镜片设计为曲面,人们可以在一个镜像中看到超过180度的风景;通过在镜片上涂抹颜料,人们可以随意改变风景的明暗、色泽,等等。
在卡尔森看来,对形式特性的排他性关注“不仅是‘不恰当’的,而且是一种严重的‘误导’”[3]38。他给出的理由有二:一是相较于决定自然之为自然的本质“特征”(character),形式特性是一种肤浅的、表面的特性,因为这种特性不够有“解释力”,即只能表明某一对象或某一人具有某种特性这一事实,而无法对这一事实——为什么和如何具有这一特性——作出充分解释,因而它只能处于审美欣赏的边缘地带[11]。二是因为形式特性并非是自然环境本有的特性,而是欣赏者主观建构出来的。这一结论出自对自然对象与艺术对象之差异的考察。卡尔森指出:艺术品大都具有“框架”或“基座”,这些框架或基座通过将他们与其所处的环境显著地区分开来划定了审美欣赏的范围与边界。换言之,“艺术品的审美特征取决于它们的内在结构,取决于它们各种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12]45-46。然而,自然是无框架的,自然物与自然物之间,自然物与其周围环境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自然环境是一个环境”[3]47,它的审美特性是其与所处的环境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结果。正因如此,我们不能再像欣赏艺术那样,站在对象的对面,对自然进行无利害的审美静观,而是要“深深地浸入”(be immersed in)我们的欣赏对象之中,与自然环境建立“亲密的、全面的、没入性的”(intimate、 total、 engulfing)动态关系。正因如此,卡尔森认为自然环境本身没有形式特性,如果有,那一定是人类“强行构图”的结果,因为人类如果想要对环境作构图式处理,就必然需要“变成一个静态的观察者,与自己正在构图的那部分环境相分离”[3]37,而这显然不符合欣赏自然的实际情况。
正是鉴于人与环境之间的连续性,一些学者认为,自然本身无所谓美丑,我们之所以觉得某一自然物是美的,是因为它的某种自然属性能够引发我们某种美好的联想。这种联想可能是某个神话传说,或者是某种艺术创造,还可能是某种精神象征,甚至是一段仅属于个人的生活记忆。以卡尔森所举的三处山地景观为例:魔鬼塔(Devils Dower)的神圣性是印第安神话赋予的,在印第安神话中,这座塔是“熊出没的地方”,是“天地创造的象征”;拉斯摩尔山(Mount Rushmore)之所以能成为闻名遐迩的旅游胜地,无疑是借了其上四位美国总统雕像的光;而富士山(Mount Fuji)显然也不是一处单纯的自然景观,作为日本精神文化的象征,其文化价值远远超过了山峰本身[13]229-230。如果说这些联想尚有某种客观物性作为基础,尚有某个文化语境作为限制,那么到了托马斯·海德(Thomas Heyd)这里,则是完全的放开、绝对的自由。他认为:“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来自各行各业和文化背景的人们所汇集的许许多多不同的故事,都确实对自然审美欣赏有益。”[12]269在海德看来,任何故事,无论它是否以自然客体本身为依据,只要它能丰富我们对自然环境的体验,提升我们欣赏自然的能力,那么它就是与自然审美相关的。如卡尔森所言,这显然是一种极端的主观主义立场。
卡尔森对这些文化特性与恰当自然审美的相关性同样持怀疑态度。他指出:相较于自然史、自然科学等其他信息,“神话、象征和艺术的应用似乎与景观的生长史并无关联,这些因素的应用并不会真正地影响景观的造型与重铸”[13]231。也就是说,联想主义的欣赏模式并没有做到“如其本然地欣赏自然”,所谓文化特性并不是自然本身的特性,而是主观强加的。如斋藤百合子(Yuriko Saito)所说,这种模式暗藏着一种假设——“自然如果不是被实践的或想象的人类行为‘人化’或‘神圣化’就不能被欣赏”,或者说“未经开发的自然本身缺乏美学意义”[12]144-145。有鉴于此,在“自然环境是一个环境”之外,卡尔森又提出了“自然环境是自然的”[3]47这一观点。这里,“自然”与“人造”相对。卡尔森指出,艺术品是由艺术家创造的,它的身上或多或少承载着艺术家的设计理念,体现出艺术家的设计技巧。因此我们可以从设计者那里找到艺术品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并据此作出恰当的审美判断。然而,自然既不是人类创造的产物,也不是文化塑造的结果,它是自然而然产生的,因此我们无法从设计者那里找到审美意义的焦点,也不能根据设计的好坏来判断自然的审美价值。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一些学者认为对自然的审美判断必然是个人的、相对的、主观的,更有甚者认为对自然的欣赏是“非审美”(nonaesthetic)的。如卡尔森所言,持这一立场的代表是美国学者肯德尔·沃尔顿(Kendall L. Walton)。在沃尔顿看来,对艺术的审美判断存在正确与错误、真实与虚假、恰当与不恰当之分,而区分的标准在于是否在正确的“艺术范畴”(categories of art)的指导下感知进而作出判断。关于如何确定艺术作品所属的“正确范畴”,沃尔顿给出了四条判断标准,这四个条件分别指向作品、欣赏者、设计者与作品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对艺术审美判断而言,这应该算是一个较为完善的评价体系,但是对自然审美判断而言,这一体系似乎并没有用武之地。正因如此,沃尔顿才否认感知自然的正确范畴的存在,进而否认自然审美判断具有客观性[3]56-58。
对此,卡尔森提出了反对意见,以上问题只能说明确定艺术范畴的条件不适用于自然对象,而不能说明自然对象所属的正确范畴不存在。换言之,自然虽然不是人造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它一无所知。既然依靠设计者的想法无法成立,那么我们何不转变思路,寻求自然本身的帮助呢?在“以客体为导向”基本纲领的指引下,卡尔森提出,在自然环境欣赏中,设计师和设计的空缺可以由欣赏者和被欣赏者(即自然本身)来填补。也就是说,对于一处自然环境,欣赏者可以为其设置“框架”,即确定“欣赏什么”与“如何欣赏”,这点在卡尔森看来十分必要,因为如果不作限制与强调,我们对自然环境的体验将只是“一种没有任何内涵与意义的生理感觉的混合”[3]49,无法担得起“审美的”这一称谓。既然十分必要,那么这种确定性的可能又何在呢?卡尔森指出“自然环境自己给自己提供了设计”,为欣赏者“提供了必要的指导”[3]xiv。换言之,指导自然审美的自然范畴应该从自然本身去寻找,应该从地质学、生物学、生态学等提供的博物学或自然科学知识中去寻找。
那么,这样的知识(即所谓“事实特性”)具体有哪些呢?从卡尔森的相关叙述中,我们可以总结出至少三类知识。
一是关于“欣赏对象是什么”的知识,包括自然万物的名称、类别、生理、生境等。尤其是“类别”,如卡尔森所举之例:我们普遍认同“大提顿山是宏伟的”这一审美判断,而否认其是矮小的这一判断,就是因为在我们的脑海中存在一个关于山峰之标准特征的认知;对马的欣赏也是如此,如果我们对马这个物种毫无概念,那么当我们面对设得兰群岛马时,就不会作出精致、伶俐这样的判断,也不会认为苏格兰克莱迪马是雄健、笨重的。如卡尔森所言,这些认知很多都是常识,仅凭直觉便可获得,但有些物种,例如“鲸”,仅凭其感性特征无法确定其正确范畴(属于哺乳类而非鱼类),所以此时就需要借助更专业的手段——自然科学[3]60-68。
二是关于“欣赏对象如何生成”的知识,即自然万物生长、演变的历史。仍以对山景的欣赏为例,如卡尔森所言:如果一个人仅仅具有感知方面的敏感性,而没有关于这一景观的任何知识,那么他也许能够发现这幅画面中的平衡感、稳定性,但也仅此而已;如果他有了关于此山到底存在了多长时间以及有关创造了这座山的力量方面的知识,认识到其上的鸟兽草木为了赢得生存斗争付出了多么艰辛的努力,那么他对这座山峰所展现出的雄伟和力量也许会有更全面、更深入的感受[13]20。“在对自然世界的解释与拓展中,崇高概念在审美欣赏中有了一席之地。惊奇与敬畏以前被认为只对神圣事物才合适,现在似乎变成对看似无限的自然界的审美反应。”[13]100
三是关于“欣赏对象为什么以这种方式生成”的知识,即自然万物的目的、功能、价值。此处所言的“价值”不是指旨在满足人类需求的“工具价值”(instrumental value),而是指服务于自身生存和发展利益的“内在价值”(intrinsic value),换言之,不是合于主体的目的、功能,而是合于“自身之善”。对此,卡尔森举出的例子是对湿地或沼泽环境的体验:“肮脏的死水”“大块的苔藓”“无数的杂草”“随处可见的昆虫和鸟类”等,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沼泽是令人感到恶心和恐惧的,然而,如果我们具备生态学的眼光,即认识到这里的每一种元素对于维持该地生态平衡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么我们也许会改变对它的态度,会发现“这些环境即便不美,至少在审美上更少地令人不悦”[14]127。
总而言之,在卡尔森看来,科学知识的参与不仅能够提升自然审美欣赏的丰富性(包括扩大欣赏的范围、提升欣赏的深度和增强欣赏的活力),同时还能保证自然审美欣赏的客观性(即还原自然的本真样貌,避免主观意志的强加),因而能为恰当自然审美提供最有效的帮助。
三、 承认并尊重自然的内在价值
从主体性转向客体性,重建的不只是美学基础理论,还有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不高,人在自然面前处于明显的劣势。因此,敬畏自然、崇拜自然甚至迷信自然在各个民族历史上都不鲜见。然而,文艺复兴吹起了“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的号角,启蒙运动奏响了“我思故我在”的乐章,18世纪开启的工业革命,更是将“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扎根深处。控制自然、改造自然甚至主宰自然成为彰显人之力量的不二选择。然而,历史证明,人与自然的对立给整个世界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气候异常、资源枯竭、生态系统紊乱……愈演愈烈的生态危机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重新审视人在自然中的位置,而这正是环境美学诞生的背景与肩负的重任。对一些环境美学家来说,要紧的工作是如何从“自然环境具有审美价值”这个“事实判断”推出“我们应该采取行动保护它”这个价值判断,如何从“美”生发出“责任”。如果这种推论本身没有问题,那么“如何评价自然环境的审美价值”就成为我们制定环保政策的中心问题,而关于这一问题,如前所述,传统自然美学提供了两种方案。
一种是将审美判断的标准建立在自然环境内部的形式特性之上。在万千自然景象中,只有那些形式优美、如画、能够带给人感官上愉悦的部分才是值得欣赏的,其他部分则被视为是缺乏审美价值的。诚如卡尔森所言,这种评价方案“极大地限制并因此扭曲了我们对自然界审美欣赏的范围”,它造成我们对“风景的迷恋”和对其他众多环境类型(如平原、荒地、沼泽等)的忽视甚至厌弃[15]。显然,这种偏好会影响自然管理者作出正确的决策。以斋藤百合子在《如其本然地欣赏自然》一文中所举的美国国家公园的设计为例:这项保护举措最初仅仅针对那些具有“壮丽”属性的风光,而那些并不壮丽的部分则被划分在外,最终导致它们遭到农耕与矿采的破坏[12]143-144。这种破坏可能会引发两点恶果:首先是生态系统之多样性与复杂性的减少,“如果以这种模式为指导,结果可能会是符合审美偏好的景观的重复呈现——无尽的山水”[13]16,进而造成生态系统之稳定性的降低。如前所述,生态系统具有整体性,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任何一个要素的改变都会打破原有的平衡状态,最终导致整个系统的紊乱。
另一种是将审美价值建基于自然环境所引发的一系列个人的或文化的联想上。任何自然环境类型,只要它能带给人美好的联想,它就具有审美价值,反之,则不值得被欣赏。在卡尔森看来,在制定环保政策时,这种价值判断标准同样存在一定的风险。以玛西亚·伊顿 (Marcia Muelder Eaton) 在《自然审美欣赏中的事实与虚构》一文中所举的“小鹿斑比”与“沼泽怪物”为例:广受赞誉的《小鹿斑比》一书与随后迪士尼改编的动画使得人们一看到鹿这个物种就自然联想起善良纯洁的斑比。正是由于这一联想,鹿种获得了人类的偏爱并由此得到更多的保护。然而鹿的总量的激增严重地威胁到了其他物种的生存,尤其是一些树木和鸟类,由此破坏了整个生态系统的和谐与稳定。与之相对,人们之所以厌恶、畏惧沼泽这种自然环境类型,是因为有太多的艺术,尤其是文学作品将这些地方描绘为怪兽频出、毒物遍布的场所。其实,这些环境类型同样具有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同样在生态系统种扮演着重要的角色[12]175-176。
通过上述考察可以看出,无论是形式特性还是文化特性,似乎都不能给伦理判断以强有力的支撑,在卡尔森看来,二者都严重削弱了“我们审美欣赏的对象与我们相信应保护的东西之间、审美价值与道德义务之间、美与责任之间”[15]的联系。那么,为什么会造成如此结果呢?根源还在于审美价值的“主体性”上,即认为自然本身没有审美价值,之所以将其判断为“美的”,是因为它的某种特性符合我们人类的审美需要。对于前者而言,这种需要是感官层面的,而对后者而言,这种需要是精神层面的。在卡尔森看来,这种主体性的审美价值论对于制定环保政策效用不大,因为它不能为其提供一个客观的判断标准。抉择者们会认为这种审美判断“要么是单纯基于一时兴起的主观兴致,要么仅仅是相对的、短暂的、糊涂不明的文化或艺术理想”[16]。而如果是这样,我们又有什么理由“要求”大家同意这一判断,听从这一裁决呢?正如环境哲学家詹娜·托普森所指出的那样:“如果自然界或艺术中的美仅仅存在于观赏者的眼中,那么审美判断就不会产生普遍的道德责任……仅仅是个人的和主观的价值判断使我们无法论证每个人都应该学会欣赏某些东西,或至少认为它值得保存。”[17]
有鉴于此,卡尔森认为,要想使审美价值成为环境保护的正确起点,使自然环境美学成为环境伦理学的坚实基础,我们就必须将价值判断的标准从主体转向客体,即认识到自然环境不仅具有旨在满足人类需求的“工具价值”,而且具有旨在满足自身的“内在价值”。在他看来,如果我们能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会发现自然环境之间只有类型之别,而没有高下之分。换言之,那些被人们忽视或者厌弃的自然环境类型只是没有符合人类的意愿,并不代表它没有审美价值,并不意味着它不值得被欣赏,进而被保护。卡尔森据此提出他的“肯定美学”观:
尚未被人类所染指的自然环境主要具有积极的审美特性(positive aesthetic equalities),它们主要体现为优雅的、精致的、强烈的、统一的或有序的;而不是乏味的、迟钝的、平淡的、混乱的或无序的。简言之,所有野生自然(virgin nature)本质上都有审美之善(aesthetically good)。对于自然世界恰当的或正确的审美欣赏(appropriate aesthetic appreciation)基本上是积极的,消极的审美判断在此无立锥之地。[3]73
从上述这段话中我们可以得到关于“肯定美学”的四点信息:一是与传统美学相比,肯定美学最明显的变化在于把“积极/消极的审美特性”而不是“美/丑”作为美学研究的第一关键词。显然,这种转变拓宽了审美欣赏的范围,使其不再限于“优美”这一种标准,而将“统一的”“有序的”等也包括在内。二是与“人化自然”相对,肯定美学提出了“没有被人类有意图的行为所染指或影响”的“野生自然”这一概念。我们知道,伯林特等环境美学家从人与自然息息相关的角度否认了野生自然的存在。但是我们应该理解,肯定美学所看重的原生自然,与其说是一种现象,不如说是一种期盼,期盼我们在欣赏自然的时候,不要受到个人经验的摆布,而要直面最本真的自然。三是通过转变视角,肯定美学得出了“所有野生自然在本质上具有审美之善”这一结论。我们注意到,这里卡尔森使用的是“善”而不是“美”,二者的区别正是我们理解其肯定美学理论的关键。也就是说,我们之所以对一切原生自然都给予肯定,不仅仅是基于审美层面的考量,更是基于道德层面的考量,即一切自然物都具有内在价值,都合于自身生存、发展之目的。由此可见,卡尔森眼中的自然美不是“人的本质对象化的结果”,而是自然之真与自然之善的感性显现。我们对自然的审美体验,与其说是一种愉悦,不如说是一种震撼,震撼于其旺盛的生命力、其顽强的适应力、其生生不息的创造力。至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最后的“恰当自然审美”的含义,卡尔森意在借此提醒我们:克服人类不良的审美偏好,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判断标准,承认与尊重自然对象及环境的内在价值。在他看来,唯有如此(将审美问题转化为伦理问题),我们才能恢复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同情之心、感恩之心,提升自我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责任意识。
简而言之,卡尔森的论证思路是:①将自然审美评价的标准从人类主体转向自然客体的本身;②通过发现自然万物的内在价值扩大审美欣赏的范围;③由此拓展人类对自然的伦理责任,为保护自然提供支持。其中,客体性转向是推论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没有这种意识也就没有随后的推论。如此,便只剩下一个问题:我们如何才能认识到这种“内在价值”呢?或者说我们如何才能确立关于自然的正确的伦理观念呢?如前所述,卡尔森把这项重任交给了“科学知识”。科学知识可以帮助我们“发现、揭示或者创造”自然界的诸如“秩序、规律、和谐、平衡、张力、稳定”等特性,这些特性“不仅让世界变得对我们而言是可理解的,而且会让我们觉得世界在审美上是好的”,因为这些特性“正是我们在艺术中所发现的在审美上是好的特性”。换言之,在卡尔森看来,科学知识对自然的解释本身包含着对“自然之善”的考虑,正因如此,当我们按照科学知识所提供的正确范畴欣赏自然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自然在审美上是好的[3]93。
综上可见,卡尔森实际上提出了一种“二元交融”的自然环境美学观:一方面承认自然具有不同于人类的生命样式和发展轨迹,具有独立于人的意识而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属性与内在价值;另一方面又强调这些客观属性与内在价值要想“显现”出来,就必须借助主体的审美能力,尤其是科学认知能力。换言之,只有具备一定的审美能力,我们才能超越肤浅的表象,深入到自然客体内部,揭示出那些隐藏的丰富性,才能超越个别的、瞬间的“丑”,获得永恒的、整体的“美”。但是必须强调的是,审美能力只是审美价值得以“显现”的条件,并不是其存在的条件,真正决定它是否存在的还是自然本身。因为与漫长的地质演变与生物进化的过程相比,人类只不过是一个后来者。换言之,生态系统的属性及其所承载的价值在人类出现之前就已存在,所以并不是人类所赋予的。正因如此,我们才更应该摆正自己的位置,以一颗谦卑之心面对自然。
四、 结 语
与传统自然美学相比,卡尔森的环境欣赏理论将研究的重心从人类主体转向自然客体,这种“客体性”转向之于“美学基础理论之重建”与“人与自然关系之重建”的意义表现为如下几点:首先,就哲学基础而言,“以客体为导向”的审美欣赏理论既打破了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的对立,又保留了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的区分,在平等交流与积极对话的过程中重建了“二元交融”的审美关系;其次,就审美对象而言,“以客体为导向”的审美欣赏理论既突破了“形式特性”的狭隘边界,又防止了“文化特性”的恣意妄为,在承认与尊重自然环境的客观属性与内在价值的基础上肯定了主体的审美能力(尤其是科学认知能力)在揭示这些属性与价值时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最后,就审美模式而言,“以客体为导向”的审美欣赏理论既提升了自然审美欣赏的丰富性(因为有来自审美主体及其审美能力的参与),又保证了自然审美欣赏的客观性(因为有来自自然客体本身及其真实特性的限制),真正做到了如其本然地欣赏。不过,客观而言,卡尔森所完成的“客体性”转向只是初步的,他所提倡的“科学认知主义”也只是实现“如其本然欣赏”的途径之一,且这条途径还存在诸多有待回答的难题,这就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充足的理论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