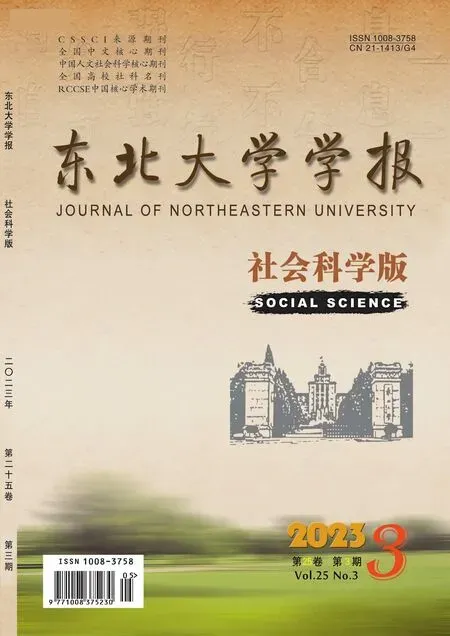何谓城市文学跨学科研究?
王桃花, 黄美琪
(1. 中山大学 外国语学院, 广东 广州 510275;2. 华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1)
现代城市的发展与西方小说的兴起时间大致相当,两者相伴相生,甚至可以说,西方小说史就是一部现代城市(文学)史。英国文学批评家马尔科姆·布拉德伯里(Malcolm Bradbury)指出:“现代城市无法言喻的偶然性与最现实、最松散、最实用的文学形式——小说的兴起有着莫大关联。”[1]英国小说理论家伊恩·瓦特(Ian Watt)则总结道:“小说的世界本质上就是现代城市的世界。”[2]
然而,正由于城市文学与文学本身密不可分的关系,长久以来城市文学并不被视为独立的研究领域。比利时城市文学批评家列文·埃米尔(Lieven Ameel)指出:“虽然学界对单个作家作品中的城市形象和经验以及关于特定城市的文学进行了大量研究,但在阐明城市小说与其他文学作品的区别方面进展较少。”[3]可喜的是,在“城市时代”命题的助推下,城市文学研究在过去十年以城市文学跨学科研究的面貌形成新一轮热潮,既产生了芬兰学派这一引领学界的城市文学研究群体,也涌现了大量学术成果,如《文学城市研究丛书》(LiteraryUrbanStudiesSeries)。在这一研究热潮中,城市文学不再囿于文学研究的单一维度,而被置于文学研究与城市研究(Urban Studies)的跨学科语境,从而赋予城市文学跨学科研究(乃至城市文学研究)鲜明的学科身份。
尽管城市文学跨学科研究总体上仍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尚未形成完备而有机的理论谱系或具有主导性的分析框架,但近十年来的学界争鸣,均是对城市文学跨学科研究进行的理论化尝试,有力地推动这一领域从碎片化走向系统化。本文基于近十年来西方学界芬兰学派城市文学跨学科研究重要文献,结合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和城市研究前沿理论,旨在阐释城市文学跨学科研究的核心范畴,以期勾勒出这一领域的研究图景。
一、 城市文学跨学科研究源起
不同于城市文学研究的传统范式,自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诸多城市文学研究者尝试从城市研究中寻求理论启示与批评工具,逐渐令城市文学研究具有跨学科意义。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城市研究“在20世纪初同时产生于英美两国”[4],旨在“研究城市区域的增长和扩张以及城市生活的性质和特性”[5]。这一学科本身具有跨学科特征,是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多种社会科学在城市语境下复合演化的产物,也可理解为城市社会学、城市人类学等学科的统称。如英国学者杰森·芬奇(Jason Finch)所说:“在20世纪,对城市的理论化是前所未有的。对城市的思考变得专业化了。这产生于理论思维和应用思维、社会学研究和建筑学实践的交汇处。”[6]城市研究具有社会实证导向,体现社会科学的思维特征。这有别于波德莱尔的城市漫游者、本雅明的巴黎拱廊等具有浓厚诗学、哲学色彩的文化理论。如果说以城市漫游与巴黎拱廊为代表的文化理论表现的是19世纪以来“过渡、短暂、偶然”[7]的城市现代性,那么城市研究的题旨则从城市现代性走向了“复合、多面”[8]的城市当代性。可以说,对城市研究维度的考量是城市文学研究不证自明的内在要求,但实际上城市文学研究跨学科意识的发展远远滞后于20世纪城市研究的形成和演化,而将城市研究与文学研究相提并论则是更为晚近的事,譬如芬奇将这一领域定性为“一个连接文学研究与城市研究的研究领域”[9]2。
值得注意的是,芬奇称这一领域为“文学城市研究”(Literary Urban Studies),而非沿用理查德·利罕(Richard Lehan)和杰里米·坦布林(Jeremy Tambling)等传统城市文学学者的说法,亦即“城市文学研究”(Urban Literary Studies)。利罕和坦布林是城市文学传统研究范式的代表人物,前者著有城市文学研究经典著作《文学中的城市》(TheCityinLiterature, 1998),后者著有《帕尔格雷夫城市文学研究百科全书》(ThePalgraveEncyclopediaofUrbanLiteraryStudies, 2018),从这一书名也可看出坦布林倾向于使用“城市文学研究”这一名称。芬奇舍弃两位前辈的旧表述,而改用“文学城市研究”这一新名称,这与芬奇所属的芬兰学派有关。
芬兰学派是城市文学领域的新兴研究群体,该学派自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引领学界,助推城市文学研究形成新一轮热潮。芬奇和埃米尔是这一学派的领军人物,他们长期主导芬兰城市文学研究界并创立“赫尔辛基文学与城市组织”(Helsinki Literature and the City Network),故笔者称以他们为代表的学术群体为“芬兰学派”。这一学派的跨学科研究视野和研究成果吸引了世界范围内研究者的目光,但在国内学界,这一学术群体则尚未受到关注。以“芬兰学派”或“文学城市研究”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中搜索,尚未见有国内文献涉及这一学派及其相关研究。
2013年,芬奇和埃米尔共同创立“赫尔辛基文学与城市组织”。2016年,该组织更名为“文学城市研究协会”(Association for Literary Urban Studies)(1)该协会主页:https:∥blogs.helsinki.fi/hlc-n/。,标志着该学术群体趋于成熟,显示出较强的国际影响力。自2018年起,该学派组织出版了《文学城市研究丛书》,目前已有8部系列专著问世,如《澳大利亚文学现代主义中的悉尼及其航道》(SydneyandItsWaterwayinAustralianLiteraryModernism, 2021)和《时间、城市与文学想象》(Time,theCity,andtheLiteraryImagination, 2021)等。无论学术组织还是研究丛书,该学派均以“文学城市研究”命名。尽管该学派并未在公开文件或文献中明确解释缘由,但不难看出,在“文学城市研究”这一名称中,“城市研究”(而非“文学研究”)被置于核心地位,突出了城市研究在这一领域中的理论价值和基础性作用。芬兰学派在丛书总序中便指出:“(该丛书的)具体研究兴趣在于探索文学城市研究中的跨学科研究方法与路径。”[10]ⅱ因而,该学派有意通过改变名称中的用词顺序,使之与传统研究范式区别开来,以扭转忽视城市研究或者将之置于次要地位的态势。
然而从其研究对象来看,“文学城市研究”仍属于城市文学研究的范畴。芬兰学派在文学城市研究协会的章程中称其研究对象为“文学中的城市”(the city in literature)[11],这一表述与利罕的城市文学研究经典著作的标题一致。此外,文学城市研究协会将坦布林列为该协会的顾问之一[12]。以上均表明这一学派所指称的“文学城市研究”与城市文学研究在研究对象上具有一致性。本质上,这一学派所指称的“文学城市研究”是城市文学研究在跨学科语境下的变体,是城市文学研究内部的新浪潮,其跨学科理念是城市文学研究在当今世界“城市时代”下的题中应有之义。因而,鉴于两者的深层从属关系,笔者认为将“文学城市研究”称为“城市文学跨学科研究”更为贴切。
二、 从文学性到城市性
芬兰学派所引领的城市文学跨学科研究的核心意义在于启发人们思考文学语境下的“城市性”(citiness)。“城市性”是芬兰学派的研究纲领。在《文学城市研究丛书》的总序中,编者开宗明义道:“与俄国形式主义对文学性(literariness)的研究兴趣相呼应,文学城市研究强调其研究对象的‘城市性’,即独属于城市和城市状况的元素,并强调关注‘城市性’对文本的影响,关注‘城市性’在研究路径方面的启示”[10]ⅱ。无独有偶,芬奇、埃米尔与该学派另一成员马库·萨尔梅拉(Markku Salmela)主编的《文学次要城市》(LiterarySecondCities, 2017),强调该学派的目标在于“推进持续进行的、关于某些(文学)文本中‘城市性’的探讨”[13]ⅵ。
芬兰学派从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的研究纲领“文学性”推演出“城市性”一词,并将“城市性”同样提升至研究纲领的高度。这并非偶然,而是芬兰学派的跨学科特征与城市研究的社会科学属性所致。众所周知,俄国形式主义文论正是试图通过对索绪尔语言学的跨学科借鉴,探究文学的科学属性,以脱离社会历史批评和传记式批评的窠臼。俄国形式主义核心人物、语言学家雅各布森(Roman Jacobson)在《现代俄国诗歌》(ModernRussianPoetry, 1921)中首次提出文学性这一概念,并指出:“文学研究的对象并非文学,而是文学性,亦即,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14]。受此影响,俄国形式主义另一代表人物艾亨鲍姆(Boris Eikhenbaum)在《“形式方法”的理论》一文中探索文学的科学基础,他明确指出:“我们和象征派之间发生了冲突,目的是要从他们手中夺回诗学,使诗学摆脱他们的美学和哲学主观主义理论,使诗学重新回到科学地研究事实的道路上来。……由此产生标志形式主义者特点的科学实证主义”[15]。总之,雅各布森等人“把文学研究的对象(文学性)作为一种科学考察的对象”[16]39,提倡借鉴语言学方法对文学作品进行客观、科学的分析。
此外,在俄国形式主义文论体系中,文学性不仅是具有科学意义的研究对象,而且被视为文学研究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种差”(differentia specifica)[17],文学由此有了自己的学科身份,而不必沦为历史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其他学科的附庸和佐证材料。同样地,在芬兰学派观点中,“城市性”是城市文学的本体属性,探究“城市性”是城市文学跨学科研究的本质要求。可以说,芬兰学派的“城市性”是对城市文学本体论和学科身份的一次追问。如果说文学性试图回答文学是什么这一问题,“城市性”则启发人们重新思考城市文学是什么,或者,在跨学科语境下城市文学应当是什么。
那么到底何为“城市性”?如何界定“城市性”?这一问题与界定文学性一样棘手。从文学性看,人们固然可以在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或济慈的《希腊古瓮颂》等具体作品中体会到文学性,但难以准确界定这一抽象概念。俄国形式主义者假定文学语言偏离于标准语言,其对文学性的界定基于文学语言与标准语言的相对性,但这一相对性本身并不稳定。伊格尔顿论及文学性时指出:“标准和偏离随社会和历史环境的转移而改变……一篇语言过去是‘偏离的’并不保证它永远而且到处如此:它的偏离性仅仅相对于某种标准的语言背景而言。”[18]5更何况,“并非一切从标准语言的偏离都是诗,例如俚语就不是”[18]5。周小仪进一步指出:“一旦涉及历史上或现实中丰富多样的文本,‘文学’的边界就十分难以划定。文学性的困难就在于文学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永远处于剧烈的变动之中。”[19]同样地,“城市性”也是一个浮动的能指。这与城市本身的复杂性不无关联。城市这一概念既具体又抽象。人们固然可以轻易列举出诸多城市,如巴黎、伦敦、上海,但却难以道明城市的本质内涵。米歇尔·德·塞托(Michel de Certeau)试图从街道平视转变为高楼俯瞰,以重新审视城市,但也承认城市如同“无尽的迷宫”[20]。坦布林认为:“城市是无定形之物(something amorphous)……我们不明白在思考城市时我们谈论的是什么,也不明白症结何在。”[21]法国当代先锋小说家乔治·佩雷克(Georges Perec)更是直言:“不要急于给城市下定义,因为城市含义甚广,我们十有八九会搞错。”[22]他们所说的城市并非单纯指城市的外在具体形态,而很大程度上指的是城市的抽象特性。因而,界定城市之难根本上在于界定“城市性”之难。尽管“城市性”是芬兰学派的研究纲领,但该学派并未在实际分析中充分界定城市性的内涵或建立明确的分析机制。
关于“城市性”的思考,应在芬兰学派的理论基础(亦即城市研究)中寻找学理依据。如果说文学性属于文学研究的范畴,那么“城市性”则更大程度上属于城市研究的范畴。城市研究中不乏对城市特性的探讨,但所使用的术语多为“urbanism”或“cityness”,而非芬兰学派所说的“citiness”。早在1938年,城市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路易·沃斯(Louis Wirth)就提出,人口规模大、人口密度高和人口异质性显著是城市有别于农村的三个本质特征[23]。美国城市社会学家萨斯基亚·萨森(Saskia Sassen)的定义则更为宽泛,她称“城市性”(cityness)为“城市的DNA”[24],城市因而成为“一个以多元性为繁荣发展之动因、化冲突为增强凝聚力之机缘的复合空间”[24]。沃斯的“urbanism”和萨森的“cityness”均体现出城市的异质性、复合性和多元性等特质。然而,对城市文学批评而言,这仍然较为笼统。美国城市地理学家艾伦·斯科特(Allen J. Scott)与迈克尔·斯托普(Michael Storper)对此也批判道,关于城市状况复合性和复杂性的观点“表面上是正确的,但在根本上是不充分的,因为这忽略了城市生活的系统性规律的存在,这些规律是可以在理论层面进行高度概括的”[25]。可见,沃斯和萨森的经典城市理论对“城市性”概念的阐释作用有限,未能体现城市文学跨学科研究中“城市性”探讨的意义。
三、 城市性问题与社会性问题
如果说沃斯和萨森的城市研究经典理论直接探讨“城市性”概念,正向地探索“什么是城市性”,那么城市研究前沿理论则往往间接触及这一话题,通过反向地思考“什么不是城市性”,将“城市性”及其意义凸显出来。具体而言,诸多城市研究前沿理论将城市性问题与社会性问题、区域性问题进行对比,以此对“城市性”作出宏观层面的界定。下文借鉴城市研究中城市性问题与社会性问题、区域性问题的对比,为城市文学跨学科研究中的“城市性”探讨寻求启示,并将对“城市性”的思考延展至对城市文学跨学科研究之研究范围与研究导向的思考。
城市性问题与社会性问题的分野将城市特质与城市内部的非城市特质区分开来。在关于“城市本身的特性”的探讨中,美国城市研究学者尼尔·布伦纳(Neil Brenner)指出,自20世纪初以来,“城市概念的界定一直是在众多社会科学领域中受到激烈争辩的问题”[26]。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一直以来人们将“在城市化空间内的”和“关于城市化空间的”(in and of urbanizing spaces)[26]问题不加区分地归入城市研究的范畴。如果说“关于城市化空间的”元素属于城市特质,那么“在城市化空间内的”元素则除了城市特质外,还涉及一般性的社会性元素。
斯科特等作了进一步探讨,提出应区分“城市中的问题”(issues in cities)和“城市的问题”(issues of cities)[25],这一区分与布伦纳的区分一脉相承。在城市空间中出现的问题未必在性质上是城市问题,而可能是更为宽泛的社会问题[25]。尽管在高度城市化的今天,城市构成了现代社会的主导形态,城市被嵌于更复杂的社会网络中,但并非所有存在于社会中的、城市空间中的元素都能笼统地归入城市特性的范畴,否则便导致“城市性”在理论表征中的泛化,甚至动摇城市研究的学理性。譬如,城市中往往存在大量贫困人口,但城市贫困未必反映了城市自身的特性,也未必是城市化所致。“贫困首先产生于宏观的社会过程,包括经济发展水平、总体就业结构和教育培训条件。”[25]尽管某些城市状况会加剧贫困,但“如果将贫困简单视为城市问题而采取相应政策措施,或许可以改善总体贫困率,但无法根除贫困”[25]。斯科特等继而将思考从城市性问题延伸到城市研究的范围与边界问题,倡导城市研究应当首先“将本质上的城市现象与其他社会现实区分开来……避免夸大城市理论的范围”[25]。
城市研究如此,城市文学研究亦然。赵炎秋关于城市文学研究范围的观点与之不谋而合,他指出,“都市生活不能等同于发生在都市里的生活。任何类型的生活都有其质的规定性,如乡村生活、小城生活等。都市生活也应有自己的质的规定性。只有内含了这种质的规定性的都市生活,才是严格意义上的都市生活……描写这种都市生活的文学才是都市文学”[27]。依据这一观点,突出反映了城市特质和城市面貌(而非单纯以城市为背景)的文学才是严格意义上的城市文学,反过来说,脱离了城市特质便会极大减损美学价值。尽管具体表述不同,斯科特等称“城市的本质”,赵炎秋则称“都市生活质的规定性”,但两者都是以一般性的社会元素与空间背景为对立面对城市研究(或城市文学研究)的性质和范围进行界定。可以说,斯科特等从城市研究出发,而赵炎秋从文学研究出发,在对“城市性”的理解上达成了共识。
四、 城市性问题与区域性问题
除了城市性问题和社会性问题的区分以外,城市性问题和区域性问题的区分也是一种对“城市性”的反向思考,并且两对区分相辅相成:如果说城市性问题和社会性问题的区分将城市特质与城市空间内部的非城市特质区别开来,提倡关注城市自身的特性,防止探讨范围的无限扩大,那么城市性问题和区域性问题的区分则将个别城市的特质与全球城市的普遍特质区别开来,提倡“城市性”探讨虽基于特定城市但不应停留于特定城市,而应超越地方意识的局限,指向作为人类生活组织形式的城市本身,将视野从个别区域的“城市性”延展至具有普遍意义的、全球性的“城市性”,从而防止探讨范围的过度局限。这可与俄国形式主义的文学性探讨相类比:依据雅各布森的观点,文学性固然寓于某些具体的文学作品中,但“文学研究者应该从具体的文学作品中,把它们抽象出来”[16]36。
尽管城市研究学者并未直接提及城市性问题与区域性问题这一区分,但这一区分潜在地存在于诸多城市研究论著中。长久以来,城市研究持西方中心主义立场,将经济发展滞后、基础设施不完善的非洲城市排除在正统城市研究范围之外[28]23-24,认为非洲城市经验“无助于丰富城市性的内涵”[29]。这无疑是将城市性问题与区域性问题混为一谈,以区域性问题来掩盖城市性问题。近年来,城市研究学界则倡导将二者区别开来。譬如,美国学者罗莎琳德·弗雷德里克斯(Rosalind Fredericks)“从达喀尔的日常城市生活中获得启示,以重新审视全球范围内城市中的基础设施、劳动力与公民权”[28]5,并指出“非洲城市,如达喀尔,是全球范围内普通城市研究与城市基础设施研究的重要理论来源”[28]149。可见,弗雷德里克斯既挑战了西方对非洲城市研究的地域偏见,也将研究从个别城市中挖掘出全球城市普遍共有的特性。这两者均体现她对城市性问题的探讨未受到区域性思维的辖制。
城市性问题与区域性问题这一区分可为审视城市文学带来启示,昭示了城市文学领域新的研究导向。在这一领域中,已有大量学者针对特定城市的文学进行研究,其中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的《文学地图丛书》(Bloom’sLiteraryPlacesSeries)最具影响力,该丛书包括《伦敦文学地图》(Bloom’sLiteraryPlaces:London, 2005)等六部专著。该丛书作了富有成效的探索,丰富了城市文学的研究实践。然而严格来说,该丛书更接近于以特定城市为背景的区域文学文化史,其主体内容在于梳理某一城市中的文学发展脉络,而非追问“城市性”及其文学表征,因而区域性意义大于城市性意义。此外,芬兰学派学者芬奇指出,以往许多针对单个或若干城市的文学研究“往往通过某种阅读视角来形成对该城市的特定看法”[9]2-3,因而“有其偏颇之处”[9]3,且往往未能超越对具体城市特征的探讨,未能在其中挖掘出适用于其他类似城市的普遍特性。
芬兰学派则致力于建立超越个别城市与区域局限的“普遍原则”[9]3,并通过《文学与边缘城市》(LiteratureandthePeripheralCity, 2015)、《文学次要城市》等论文集作了有益的尝试。以《文学次要城市》为例,该书注意到以往的城市研究与城市文学研究过于关注城市的首要性、中心性和独特性,研究者言必称伦敦、巴黎、纽约、上海等国家首都或国际大都市,仿佛唯有这些“首要城市”才具备研究价值,这无形中掩盖了在世界城市总量中占更大比例的“次要城市”。此外,首都或国际大都市往往具有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倾向,次要城市则保留了更大程度的民族性和地域性。例如,法国人将法国境内巴黎以外的所有地方都称为外省(province),传递出溢于言表的首都中心主义,而“次要城市”则天然带有地方主义(provincialism)的意味,因而对“次要城市”的探讨容易落入地域性或区域性问题的窠臼。
鉴于此,《文学次要城市》“从城市研究(包括城市历史、城市地理、城市社会学和城市规划)与文学研究两个方面”[13]5对“次要城市”进行全面审视。其中,芬奇分析了戴维·洛奇(David Lodge)的小说《换位》(ChangingPlaces, 1975)和乔纳森·科(Jonathan Coe)的小说《无赖俱乐部》(TheRotters’Club, 2001)中的英国城市伯明翰,并总结道:“在洛奇和科笔下,伯明翰这座城市代表了一种平平无奇之感,是一个调侃的对象……它具有一种‘普通’的特质……一种默默无闻的特质”[30]63。伯明翰在与伦敦等“首要城市”的对比下相形见绌,“尽管科涉及的部分话题不免消极,但这部小说是他写给伯明翰的赞美诗”[30]63。这实际上消解了关于城市特性的宏大叙事,令人重新思考以往城市概念惯常预设的首要性和独特性,激起大多数人更为熟悉的普通、庸常、平凡的城市经验。
无论在现实中还是文学中,人类的城市经验总被少数“首要城市”所代表,例如本雅明称巴黎为“19世纪的首都”[31],爱德华·索亚(Edward W. Soja)则称洛杉矶为“最典型的后现代都市”[32]。然而这类城市的居民毕竟有限,“大多数城市居民都觉得自己的城市在某种程度上次于其他更大或更著名的城市”[13]5。因而辩证地说,普通性反而是大多数当代城市共有的“特性”之一,是大多数当代城市居民共有的城市经验。2007年联合国《世界城市状况报告》显示目前全球已有半数人口居住在城市[33],而这其中,大多数人所居住的城市是不具有话语主导权的、作为他者的城市,因而对“次要城市”的探讨更具现实意义和普遍意义,也更具人文关怀的意味。芬奇明确指出了洛奇和科笔下的伯明翰具有超出地方界域的普遍意义,他评论道:“正由于它(伯明翰)具有一种‘普通’的特质,它似乎也能在某些时刻作为国家整体形象的转喻”[30]63。在《文学次要城市》中,伯明翰的“普通性”还进一步在其他评论文章涉及的诸多“次要城市”中得到呼应,如爱沙尼亚城市塔尔图、美国城市拉斯维加斯、瑞典城市奥莫尔和意大利城市威尼斯,这表明伯明翰的“普通性”是一种跨越巨大空间尺度的“城市性”,参与建构了跨区域的城市共同体想象。
以上两对区分(亦即城市性问题与社会性问题、城市性问题与区域性问题)构成了两个有机的研究取向,两者既相互补充(防止探讨范围的无限扩大与过度局限),又层层递进(从个别城市的“城市性”到全球范围内的“城市性”)。在城市研究的学理支撑下,这两个研究取向以社会性问题和区域性问题为参照,不仅重新丈量了城市文学的研究范围,而且昭示了城市文学新的研究导向,从而有助于在宏观层面把握城市文学跨学科研究中“城市性”这一研究纲领。
然而目前为止,“城市性”仍是一个宏观的纲领性概念,还有待进一步细化和系统化。单就“普通性”而言,这一概念并不能涵盖文学次要城市的全部内涵,更不是对“城市性”的最终答案,而仅是“城市性”的一种可能。关于文学次要城市的探讨还存在诸多进一步思考与对话的空间。例如,现实中与文学中的城市等级是否必然匹配?是否有城市在现实中处于次要地位,在文学中却占据首要地位?抑或反之?如果有,其背后有哪些可能的原因?再者,次要城市的“普通性”是否与其另一幅面孔即民族性产生深层关联与动态交织?次要城市居民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份,如何看待与首要城市的关系?在这些问题上次要城市的特性又如何构成具有全球尺度的城市经验?……在“城市性”探索乃至城市文学跨学科研究中,还将有无数个这样的追问等待回答。
五、 结 语
在社会科学领域“城市时代”命题的助推下,城市文学这一传统文类重焕生机。西方学界的城市文学研究在过去十年以城市文学跨学科研究的面貌形成新一轮热潮,城市文学不再囿于文学研究的单一维度,而被置于文学研究与城市研究的跨学科语境。芬兰学派对此作了初步探索,并从俄国形式主义的文学性推演出“城市性”这一研究纲领。以芬兰学派重要文献和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审视城市文学跨学科研究,可厘清城市文学跨学科研究的形成逻辑、文学性与“城市性”的深层关联。而以城市研究前沿理论进一步审视“城市性”,则可将“城市性”探讨延展至对城市文学跨学科研究之研究范围与研究导向的宏观思考。美国城市社会学芝加哥学派领军人物帕克(Robert E. Park)曾高度肯定城市文学的价值:“我们(城市研究学者)深深受惠于小说创作者,因为他们使我们得以更深入地了解当代城市生活。”[34]而在当今的城市文学领域中,城市文学研究学者则同样深深受惠于城市研究学者,因为城市研究在过去一个世纪的理论积淀为当今城市文学的理论化提供了有力的学理支撑。与城市研究一样,城市文学研究是随着城市化发展和城市生活演变而具有持续生命力的领域,新近的“城市性”探讨乃至城市文学跨学科研究更是具有巨大的探索空间。以芬兰学派为代表的城市文学研究者与其说提供了一个现成的答案,不如说作了一个华丽的开场,以开放的姿态邀请人们参与到城市文学的跨学科研究与对话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