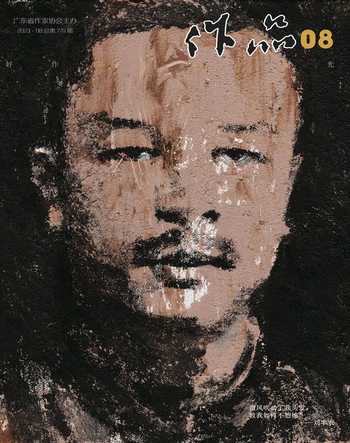三窝村故事
苏三皮
月光
三窝村的人发觉月光不见了。
最新发觉月光不见的人是渔夫。渔夫每天早出晚归,天还没有亮,他就乘着月光摇着小船出海,天一落黑,他就会蹚着月光回家。回家之前,他会把月光牢牢地缠在小船上。
这天早上,渔夫像往常一样,天还没有亮就出门了。渔夫发现到码头的路黑乎乎的,一点儿光亮也没有。渔夫倒不是很在意。这条路他走过上万遍,就算没有月光,他也一样可以稳稳当当地走到码头。这条路的任何起伏,哪怕一个拇指大小的坑洼,就像大海里的每一条鱼,渔夫都心中有数。
天落黑时,渔夫回到了码头。渔夫抬头仰望星空,没有看见月光,月亮连影子也没有。渔夫这才慌了。
渔夫惊慌失措地跑到了族长家,一路上连跌了好几跤,但渔夫完全顾不上疼痛。渔夫把族长的木门擂得像战鼓,族长极不情愿地开了门,嘟囔着把渔夫让进了屋里。族长有早睡的习惯。族长一旦睡下,就不喜欢他人打扰。但也有例外,比如月光不见了这般大事,族长也就不会去责怪渔夫。
族长让渔夫好好回忆一下,月光是何时不见的。渔夫挤破脑袋想了又想,实在想不出来。渔夫只是记得,他前天晚上回到码头时,他着实把月光牢牢地和小船缠在了一起。早上他到码头时,小船还在,绳索也还在,只是月光不见了。渔夫补充说,应该是早上出门时,月光就不见了。
族长捋着山羊胡子思考了一会儿,说这样的事情也不是没有过,他就听他爷爷说过,在很久以前,月光也走丢过一次。但月光是怎么找回来的,他爷爷并没有告訴他。族长还说,有一种可能是月光烦腻了这种日子,自己躲了起来,还有一种可能是月亮被天狗吞掉了。如果是第一种可能,那倒不用着急,月光也就和大伙儿躲个猫猫,大伙儿也不用找它,等它自觉得无趣了,自然就会出来。但是如果是第二种可能,那麻烦就大了。
听族长这么一说,渔夫就更慌了。要是月光真被天狗吞掉了,他还怎么出海捕鱼?捕不到鱼,他的妻子孩儿又该怎么办?渔夫央求族长想想办法,无论如何得把月光找回来。
族长打着长长的哈欠说,等睡醒再说吧。
渔夫愁得一整夜都没有合眼。一整夜,月光明晃晃地挂在渔夫的脑海里。渔夫不断地祈求月光只不过是厌烦了这种日子,偷偷地躲起来几天,几天后就会回来。
一大早,族长就敲锣把大伙儿聚拢在晒谷场。族长神情凝重地告诉大伙儿月光不见了。族长说,也许是月光自己躲了起来,也许是被天狗吞掉了,不管是哪种情况,作为三窝村的一分子,任何人都有责任,都得尽力而为去把月光找回来。族长话音刚落,人群就慌乱起来。一些女人拉扯着男人的衣袖,不停地问,这可如何是好?这可如何是好?……男人被问得一脸烦躁,没好气地噎了女人一句,如何是好?如何是好?你问俺的膝盖去。
最按捺不住的是渔夫的女人。渔夫从族长家出来,并没有回家,而是去了码头,在小船的船舷上坐了整整一夜。渔夫的女人早早睡了。丈夫回不回家,不影响她睡觉。她丈夫原先也有过乘着月光彻夜捕鱼的情况。但是,一听说月光不见了,她便慌了。没有了月光,她的丈夫就没法出海捕鱼,或者出海捕鱼就没法摸清回家的路,这才是要命的事情。
渔夫的女人悄悄地问渔夫,是不是他把月光给藏起来了?渔夫厌恶地瞥了女人一眼,他可没有什么心情和女人开玩笑。偷藏月光,那可是要砍头的。
族长毕竟是族长,他一点儿都不慌乱。族长把大伙儿分成两批人,一批人出去寻找月光,另一批人去采集阳光。族长有族长的盘算,要是月光找不回来,他就用大伙儿采集的阳光重新打造一个新月亮。
寻找月光的那批人,他们从北山到南山,从南山到西山,从西山到东山都寻了个遍,连月光的影儿都找不着。他们垂头丧气地回到了三窝村,悲戚地告诉族长,或许月亮真被天狗吞掉了。族长仿佛已经心中有数,他捋着山羊胡子安抚他们说,吞掉就吞掉了,天塌不下来。
采集阳光的那批人,包括渔夫和他的女人在内,马不停蹄地采集阳光。他们把阳光装在透明的玻璃瓶里,盖好盖子,细心的人还贴上封条,怕一不留神就让阳光给跑掉了。那批寻找月光未果的人们也都加入了采集阳光的队伍,他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在屋顶,在沙滩,在山腰,甚至还有人爬到树上,在一切可能采集得到阳光的地方孜孜不倦地把阳光装进他们的玻璃瓶。
时光就这么过了一年又一年,在族长认为他们采集的阳光已经足够打造一个新月亮时,族长敲着锣把大伙儿再次聚拢在晒谷场。族长动情地肯定了大伙儿的功绩,豪情万丈地告诉大伙儿,他将按照他爷爷留下的配方,用大伙儿采集的阳光打造一个新月亮,届时大伙儿就可以再次姿意地拥抱月光了,而渔夫再也不用担心出不了海捕鱼或出海捕鱼摸不清回家的路的问题。
三窝村的人们面面相觑,互相小声地探问,月光是什么东西?可是没有人答得上来。而渔夫,趁着族长讲话的空隙,悄悄地溜到码头,爬上小船,在船舷上睡着了。
渔夫做了一个梦,他梦见自己提着一个玻璃瓶走在黑夜里,半路上遇着他的爷爷,他爷爷问他手里提的什么东西这般亮眼。渔夫告诉他爷爷说,是月光。
炊烟
渔夫这天回家有些早。太阳像五月的稻子,刚涂上一层金黄,吊儿郎当地挂在西山山顶,仿佛一不留神就会掉到山后去。渔夫系好小船的缆绳,沐浴在落日的余晖中,慢吞吞地走向了三窝村。
这天好像很寻常,但又好像很不寻常。
渔夫数着自己的脚步,一步,两步,三步……数着数着,渔夫大惊失色——渔夫发觉三窝村的炊烟不见了。
以往这个时候,三窝村的炊烟仿佛商量好似的,一股劲地冒出来。族长家的炊烟是个小矮人,身子短,鼻子长,滑稽得很;李老六家的炊烟是个瘦个儿,像一根竹竿倒插在烟囱上;甜婶娘家的炊烟圆滚滚的,像裹着棉絮的熊猫;渔夫家的炊烟则像一棵笔直的树,树冠开得很宽,如果不加阻拦,就会遮盖了整个三窝村……
三窝村怎么可能没有了炊烟?没有了炊烟的三窝村,怎么会是三窝村?
渔夫顺路踅进李老六家的院子,把李老六的木门擂得山响。李老六睡眼惺忪地开了门,不明所以地望着渔夫。渔夫急切地说,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睡得这般安稳?李老六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问渔夫,怎么了?渔夫没好气地说,你就不应该睡懒觉,你家的炊烟呢?你见着你家的炊烟了吗?李老六暼了渔夫一眼没好气地说,还以为多大的事儿,走,走,走,别打扰俺睡懒觉。
漁夫自讨无趣。李老六是个光棍儿,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他想啥时睡就啥时睡,连族长也干预不着。李老六家的炊烟跟李老六一个德性,时隐时现,即便偶尔会不经意地从烟囱蹿出来,也会瘦得像一根竹竿。
从李老六家院里出来,渔夫直奔族长家。族长正坐在菩提树下和人嘻嘻哈哈地聊着天。见渔夫急匆匆地闯进来,族长止住了笑,一脸严肃地对渔夫说,说过多少回了,遇事莫慌,怎么就是没个长进?渔夫顿了一下,肚子里的那口气才刚刚跟了上来。渔夫说,村里的炊烟全不见了,咋能不慌?渔夫话音刚落,他看见一丝慌乱掠过族长的脸。但是,族长毕竟是族长,他很快就镇定下来。族长跟着渔夫到后院一看,果真是。族长家的炊烟也已不知所终,而灶膛里的火苗还蹿得老高。族长说不出个所以然,无奈地把渔夫先打发走了。
渔夫闷闷不乐地回到家里,出现在女人跟前。女人张罗着解下渔夫肩上的鱼篓,抖了两下,一条鱼也没有滑下来。女人叹了口气,轻柔地说,没鱼就少吃一顿,你也用不着垂头丧气。渔夫没有应女人的话。渔夫早上撒网时,没有留意渔网破了个大洞,鱼儿顺着大洞溜走了。这是极少有过的事情。每次撒网前,渔夫总会细致地把渔网检查一遍,但是今天,渔夫居然神使鬼差地没有检查渔网,这才导致两手空空。
渔夫发觉不对劲。怎么不对劲,渔夫说不上来,就好像有什么事情在脑门打了个结一般。要是渔夫没有疏忽,像往常一样检查过渔网,也就不至于发现不了渔网破了个大洞;倘若渔网没有破个大洞,也就不至于两手空空,更不至于在太阳下山前就回到三窝村。这里面,仿佛有一股巨大的力量牵引着这些一连串事件的发生。但是,源头在哪里,渔夫捋不出来。
渔夫并没有和女人说起炊烟不见了的事。渔夫一句话也没有说。渔夫的女人十分贤惠,她默默地伺候渔夫吃过晚饭,又给渔夫端来热水洗脚。渔夫的女人对渔夫说,你忙碌了一天,劳累了,就早些儿歇息。说完,渔夫的女人就织渔网去了。
族长和渔夫不一样。族长有早睡的习惯,渔夫没有。每次捕鱼回来,渔夫得处理渔获。渔夫把渔获分类,分大鱼小鱼,分名贵鱼和寻常鱼。渔夫还得给渔获冰封。这么一来,等渔夫忙完,已几近子夜时分。渔夫的女人第二天会将渔获挑到市场叫卖,换些银两补贴家用,间或也会拣些杂货或小物件,譬如雪花膏。渔夫的脚长年泡在海水里,每到三九寒冬就会龟裂得像七月的稻田。
渔夫屋前屋后转悠了几圈,不时仰望一下他家的烟囱。渔夫家的烟囱高大而笔直,渔夫多年前想不明白他的爷爷为什么会砌这么高大的烟囱,按理说,他们小户人家一个小烟囱就足够用了。每次渔夫问起他爷爷,爷爷总是笑而不答。有时渔夫问得急了,渔夫的爷爷就会说,你慢慢就会知道了。但是,直至爷爷驾着白鹤飞向西边,渔夫还是想不明白他们家的烟囱为什么会这般高大。
渔夫盯着他家的烟囱看了好一会儿,看不出任何一点儿炊烟出走的迹象。渔夫想,炊烟也许厌烦了这种日子,也许厌烦了三窝村,甚至厌烦了三窝村所有的人和事,它们才集体离家出走。这么想,渔夫就不禁隐隐担忧起来,炊烟们要是走得远了,认不得回来的路,那该如何是好?
这么想,渔夫就坐不住了。渔夫急匆匆地来到族长家,把族长家的木门擂得山响。所幸的是,族长还没有睡觉。要是族长睡下了,渔夫少不了挨一顿骂。渔夫对族长说,要是炊烟走得远了,回不来,那如何是好?族长笑而不语。族长伸出手,变戏法似的轻轻地吹了一口气,然后指着天西边对渔夫说,你快看。
渔夫抬起头,看见一连串炊烟正在天空中遛弯儿,像暮归的羊群。在前头带队的是族长家的炊烟,紧跟着的是李老六家的炊烟,还有甜婶娘家的炊烟……三窝村的炊烟全都在那儿。渔夫家的炊烟在队伍的最后,它像一棵从天空里长出来的树,高大笔直,宽大的树冠枝叶繁茂。而渔夫的爷爷,正躺在树杈与树杈之间的吊床上,悠然地抚摸着星星。
这么一瞬间,渔夫的眼睛湿润了。
责编:胡破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