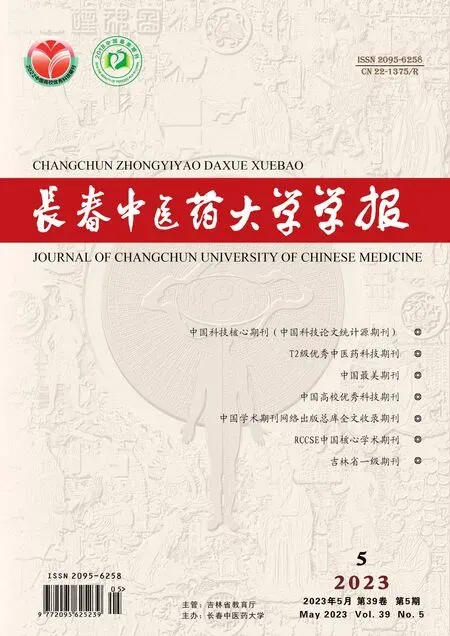人参防治疫病应用浅析
孙 健,魏 岩,张文风
(长春中医药大学,长春 130117)
1 疫病源流
1.1 “疫”的概念
疫,《说文解字》曰:“民皆疾也”,《字林》曰:“病流行也”,又名“时疫”“时气”“疠”“疫疠”“天行”“瘟”等。中医对于疫病的认识,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周礼·天官·冢宰》记载:“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吕氏春秋·季春纪》也有记载:“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礼记·月令》载“仲夏行秋令,则草木零落,果实早成,民殃于疫”,从这些文献记载来看,当时的医学水平已经认识到了疫病的存在以及其临床表现为具有传染性、流行性。随着时代的发展,到明清时期疫情的内涵最终被界定清晰,“疫”是指具有强烈传染性、大规模流行性的一类疾病。如:明·杨璿《伤寒温疫条辨》云:“盖疫者役也,如徭役之役,以其延门合户,众人均等之谓也”[1],刘松峰《松峰说疫》云:“若夫疫气,则不论贵贱贫富、老幼男女、强弱虚实、沿门阖境、传染相同,人无得免者”[2]。
1.2 “疫”的病因病机
1.2.1 “疫”的病因 历代医家对疫病的病因认识是不同的,传统中医理论多认为是由于不属于风、寒、暑、湿等“六淫”的一种特殊之气——“乖戾之气”“疠气”。如: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温病诸侯》云:“此病皆因岁时不和,温凉失节,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则病气转相染易,乃至灭门,延及外人。”[3]明·吴有性《温疫论·原病》云:“疫者,感天地之疠气……此气之来,无论老少强弱,触之者即病。”[4]
现代中医学家则认为疫病发生的病因是由于“疫毒”之邪中人。疫毒是独立于六淫之邪的特殊致病因素,具有强烈的传染性,可引起广泛流行,导致疫病发生。“疫毒”属于毒邪之一,是存在于自然界中的特殊病邪,人体外受可导致疫病发生。疫毒性质以温热居多,但也有寒湿者,可能与地理环境、人体体质等相关。疫毒是导致疫病发生的关键,人体感受疫毒后的发病程度与感邪轻重、体质强弱、病情浅深密切相关[5]。如现代中医内科学家、国医大师任继学言:“疫邪犯人必有毒,毒有强弱,有善有恶,有毒则害人”,“疫的发生主要是因自然界大气被污染,清浊之气相混,毒气自生而成”[6]。首届全国名中医、国医大师南征教授言:“寒湿肺疫病范畴,是杂气为病,疫厉之气由口鼻而入,内舍于半表半里,邪伏膜原,进而成毒邪,毒损五脏六腑。”[7]
1.2.2 “疫”的病机 人体在感受疫毒之后,根据疫毒的毒性强弱,发病有快有慢,大多发病较急,发展较快,因疫毒其来无时,其着无方,或侵犯六经、或侵犯三焦或直中脏腑、或损伤神明,无关人之强弱,血气之盛衰,触之即病,其侵犯人体的途径大略言之有三途:一是从皮毛而入,玄府开阖失司,疫毒乘虚而入,病在肌表;二是从鼻而入,疫毒从呼吸系统直接侵袭肺卫;三是从口而入,疫毒由食道进入中焦,脾胃受病,疫毒侵犯人体主要是因为正虚于内,卫虚于外,营虚于血,使三维防御系统空虚所致[6]。
在疫病的发展过程中,其病机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疫病的发生发展总趋势是病位由表入里,由浅入深,证候由实至虚;二是病理变化主要表现为正邪剧争,易致脏腑气血津液的严重失调、损害,甚而正气外脱。在此过程中,正邪剧争对疫病的病理变化及发展具有重要作用[8]。
2 人参在疫病防治中的作用
《神农本草经》载:“凡欲治病,先察其源,候其病机。”根据疫病的病因病机,中医治疗疫病往往采取清解疫毒、截断传变、扶助正气等方法,具体治法涵盖汗、吐、下、和、温、清、消、补八法。人参,《神农本草经》载:“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除邪气”[9],列为上品。考古文献疫病中人参之用,在于除邪气、助药力、滋津液、养胃气。
2.1 除邪气
按上文所述,疫病的发生是由于感受疫毒,因此祛除外邪是治疗疫病的第一要务。人参在传统意义上认为属于补虚药,但在古代文献中,古代医家认为人参亦有祛邪之功。如《神农本草经》载:“除邪气”,元·王好古《汤液本草》云:“泻脾肺胃中火邪”[10],清·陈士铎曰:“人参乃攻邪之圣药也”[11]。清·喻嘉言曰:“虚弱之体,必用人参三五七分……以为驱邪为主,使邪气得药,一涌而去,全非补养虚弱之意。”[12]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卷二》[13]载:“人参养胃汤,治外感风寒,内伤生冷,憎寒壮热,头目昏疼,肢体拘急,不问风寒二证及内外之殊,均可治疗……兼能辟山岚瘴气,四时瘟疫,常服尤佳。”其方剂组成为半夏、厚朴、苍术、藿香叶、草果、茯苓、人参、炙甘草、橘红,其组方之义便是以人参驱邪,使邪气得药,一涌而出,并非取其补养之意。
在《局方》中与之类似的尚有解利四时伤寒头痛壮热、山岚瘴气、时行疫疠的人参轻骨散,治感冒发热头痛的参苏饮,治伤寒体热头痛的僧伽应梦人参散,治四时伤寒头疼壮热的八解散等,这些方剂中人参之功效均以攻除邪气为主。
2.2 助药力
人感受外感之邪,当发汗以解表,但惟有元气旺盛之人方能鼓舞药力,始外邪借助药势而排出体外,即清·喻嘉言所言:“盖人受外感之邪,必先发汗以驱之。其发汗时,惟元气大旺者,外邪始乘药势而出。”[12]元,有本原之意,元气又名“原气”,是人体最根本、最重要的气,是生命活动的原动力。若人元气不足,则虽用祛邪之药,往往因气从中馁,使邪气欲出不出,留恋体内,甚至邪气随元气入里,发热无休,从而危及生命。因此,当人感受疫毒之时,扶助元气以助解表之药力就显得尤为重要。人参具有大补元气之功效,明·卢之颐《本草乘雅半偈》云:“无形周备,是补五脏而奠安神舍,则邪僻自除,窍穴明彻,济弱扶倾,运用枢纽者也。”[14]
《局方》载人参败毒散,治“伤寒时气,头痛项强,壮热恶寒,身体烦疼,及寒壅咳嗽,鼻塞声重,风痰头痛,呕哕寒热,并皆治之。”方剂组成是:柴胡、甘草、桔梗、人参、川芎、茯苓、枳壳、前胡、羌活、独活。明·龚廷贤《万病回春·卷之二·瘟疫》中认为本方是“治四时瘟疫通用方”,清代喻嘉言更是赞其为三气门中第一方。此方中人参便是取其助药力之功效,如清·张璐认为:“其立方之妙,全在人参一味,力致开阖,始则鼓舞羌、独、柴、前各走其经,而与热毒分解之门,继而调御津精血气各守其乡,以断邪气复入之路。”[15]
吴又可《温疫论》中治疗“疫邪留于心胸,令人痞满,下之痞应去,今反痞者”的参附养荣汤,因患者素体不足,又下后益虚,造成了健运失常,邪气留止。方中用生地黄、白芍、当归以增液,附子、干姜以温阳,另加人参一钱以助药力,使元气不致漓薄,元气足则化生阴阳,健运恢复,邪气得出,不用行气破气之剂而痞胀自消。
2.3 滋津液
疫病的诸多临床表现中常常伴有发热的症状,因此在疫病的病理演变过程中常常伴随着津液的消耗,人参对于因疫病而造成的津液消耗具有很好的修复作用。陈修园论人参曰:“余细味经文,无一字言及温补回阳,故仲景于汗、吐、下阴伤之症,用之以救津液,而于一切回阳方中,绝不加此阴柔之品……皆因寒、吐、下后,亡其津液,取其救阴。”[16]张山雷《本草正义》云:“富有津液而为补阴之最。脱血、脱汗、失精家宜之,固也。而肺燥干咳、胃枯燥渴或干呕呕逆者,皆赖以滋液生津,而无寒降戕伐、黏腻浊滞之弊。”[17]
善用人参以滋津液者,莫过于张仲景。如治疗“服桂枝汤,大汗出后,大烦渴不解,脉洪大者”“伤寒若吐若下后,七八日不解,热结在里,表里俱热,时时恶风,舌上干燥而烦,欲饮水数升”,以白虎加人参汤主之,治疗“恶寒、脉微而复利,利止亡血”,以四逆加人参汤主之,治疗“伤寒解后,虚羸少气,气逆欲吐”的竹叶石膏汤等。张仲景于阴伤之后用人参,即取其养津液之功效,故张洁古谓人参云:“止咳,生津液。”
后世医家亦常用人参以治疗疫病之津液损伤,如唐·王焘《外台秘要·天行虚羸方二首》载崔氏疗“烦躁而渴不止,恶寒仍热盛者”之竹叶汤,方中即用人参合麦冬等以滋津液。书中引《病源》云:“真气尚少,五脏犹虚,谷神未复,无津液以荣养。”[18]故人参适用于疫病过程中津液的损伤。
2.4 养胃气
胃气在中医理论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素问·玉机真脏论》云:“五脏者皆禀气于胃,胃者五脏之本也”。李东垣《脾胃论·脾胃虚实传变论》指出:“元气之充足,皆由脾胃之气无所伤,而后能滋养元气。若胃气之本弱,饮食自倍,则脾胃之气即伤,而元气亦不能充。”疫病乃是感戾气而发,若胃气充实,邪不易入。吴又可《温疫论》云:“夫疫者,胃家事也。盖疫邪传胃,十常八九”,故胃气的充实与否,直接关系着疫病的发生发展以及转归。清·冯兆张论人参曰:“气壮而胃自开,气和而食自化,退虚火之圣药也,功专补中。”[19]陈士铎云:“救胃气之损伤,非人参又何以奏功乎。”清·吴鞠通云:“人参最宣胃气”[20]。故人参在养胃气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
《外台秘要方·天行病方七首》载生芦根八味饮子治疗“天行病,加呕逆食不下”,《外台秘要方·天行呕逆方七首》载《集验》疗“天行后,气膈呕逆不下食”之生芦根汤,以及《外台秘要方·天行呕啘方七首》载文仲《近效》疗“呕逆”之麦门冬饮子方等,均以人参养胃气。书中引《病源》云:“胃家有热,谷气入胃,与热相并,气逆则呕。或吐下后饮水多,胃虚冷,亦为呕也。”以及“伏热在胃,令人胸闷,胸闷则气逆,气逆则哕。若大下后,胃气虚冷,亦令致哕也。”陶弘景《名医别录》云:“疗肠胃中冷,心腹鼓痛,胸胁逆满,霍乱吐逆,调中。”故人参可用于疫病中胃气虚弱的调养。
3 病案举例
辛酉仲夏,予迁郡城之次年,其时疫气盛行,因看以贫人斗室之内,病方汗出,旋即大便,就床诊视,染其臭汗之气,比时遂觉身麻,而犹应酬如常,至第三日病发,头眩欲仆,身痛呕哕外,无大热,即腹痛下利,脉沉细而紧。盖本质孱弱,初病邪气即入少阴,脉证如斯,不得不用姜附人参以温里。如此六七日,里温利止,而疫气遂彰,谵言狂妄,胸发赤斑数点,舌苔淡黄而生绿点,耳聋神昏,脉转弦数,此由阴出阳,必须汗解之证也。病剧会真州,诸医束手不治。适山紫家叔来探问,数当不死。余忽清爽,细道病源,谓非正伤寒,乃染时疫,缘本质虚寒,邪气直入少阴,服参附里气得温,逼邪外发,但正气甚弱,不能作汗。今脉弦耳聋,邪在少阳,乞用小柴胡汤本方,加人参三钱,必然取效。山紫家叔遂照古方,一味不加增减,而入人参三钱,一剂得寐,再剂又熟寐。夜又进一剂,中夜遂大汗至五更,次日即霍然矣。继服人参半斤始健[21]。
按语:此案为清代名医郑重光治疗自感时疫之候。郑氏曾注释《温疫论》,撰成《温疫论补注》二卷,对于疫病有着深厚的理论功底与临床经验。疫邪侵袭人体,人体阳虚体质,故病邪直中少阴,故起初用温热药以托邪外出,使邪气从三阴而出三阳,冀其汗解。然而患者素体正气虚弱,邪气留恋三阳而不能作汗而解,故表现出三阳见证而缠绵不愈。医者苟无定见,见三阳见证而误用寒凉而伤阳,或滥用表药而误汗,则祸不旋踵。郑氏于此等病证,常常能透过症候的繁芜表现,把握疾病本质,故用人参、生姜等鼓舞正气,缠绵之邪一汗而散,遂收全功。从本案可以看出,郑氏认为疫邪因人的体质不同而导致病发阴阳的不同。禀赋厚者感受疫气而发热证,禀赋薄弱者疫气侵袭则消耗人体阳气而致虚寒见证,疫证常常多见阴证,虚寒疫证常被误治,宜急用参、附、姜等以回阳救逆,若稍有差池则致阳脱。此案之中,因正虚不能作汗,故用人参扶助药力,遂“大汗至五更”,善后更是服用“人参半斤”,以滋津液、养胃气,而终收全功。
4 结语
综上所述,人参在古代疫情的防控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根据中医学对疫病病因、病机的认识,认为疫病的发生是由于机体感受了“疠气”“疫毒”,从而导致正邪交争,正气耗伤,脏腑气血津液严重失调。人参除邪气、助药力、滋津液、养胃气的功效,可以有效的针对其病因病机发挥作用。通过梳理古代医家在疫病防治中运用人参的经验,从而对现代疫情防治中如何更有效的运用人参起到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