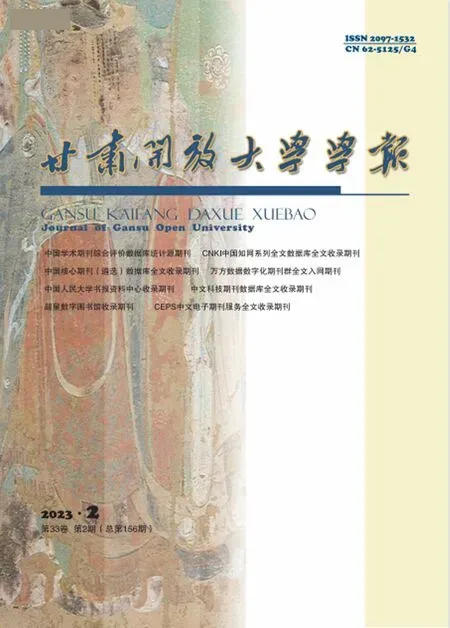对话与隔阂:甘肃故事媒介话语建构的三重视野
杨菁菁
(兰州财经大学 党委宣传部,甘肃 兰州 730000)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1]。中国故事的话语体系由一个个文化异质性强、共通情感空间窄的地方故事所形塑。甘肃故事是中国故事的地方维度,通过区域性故事实践,构建特色鲜明的中国故事区域文化书写情境。与此同时,深藏于书写情境背后的话语模式则为中国故事的再生产和再传播提供新的源泉。甘肃故事表达、维持和重构既包含甘肃地区的风土人情,也涵盖了中华文明交流互鉴的文化实践日常。因此,基于报道主题框架研究甘肃故事的媒介话语建构既是探究故事生产者对甘肃文化和历史的认知与情感含量的有效方式,又能有效促进“他者”对甘肃和中国的深度认识和理解,极大地拓展跨文化、跨地域、跨价值取向的中国区域故事传播新视野。
一、“内里”突本质,驱动话语建构
(一)包装性:媒介话语
媒介是生产符号和建构意义的工具,传播的过程是建构意义的过程,也是传播媒介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的过程。荷兰话语分析学家梵·迪克认为,“话语和新闻都是社会的产物,因为它必然表达和确认其制作者的社会和政治态度”。媒体的报道虽然源于社会现实,但并不一定“诚实反映或照出事实”,媒体将其传播意图隐藏于新闻报道背后,在这一过程中,作为诱发力的话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20 世纪50 年代末期,话语开始被理解成一种行动,也就是对世界的一种干预。我们对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的理解,以及对文化和大众媒体的研究,无不受到这种观念转换的深刻影响[2]。话语再塑着社会权力关系和文化生产模式,媒介通过话语建构将其意识形态展露无疑,与此同时,这种“后台”建构并非一种显性表达,受众对真实情况的片面认知也由此产生。托多罗夫将“话语”与“故事”并举,将它们分别视为叙述文本的“表达形式”和“表达对象”。[3]话语不是一个仅仅由能指符号构成的体系,在社会意义上具有建构性,“有助于社会结构的所有方面——这些方面直接或间接地构成或限制话语的建构……不仅表现世界的实践,而且在意义方面说明世界、组成世界、建构世界”。[4]
诸多学者从媒介话语涵盖范围、不同理论角度与内容定位、媒介话语的叙事角度、社会实践等方面力求理清其学术脉络,探讨媒介话语在整个媒介生产动态建构过程中的影响力与倾向策略。利用媒介提供的话语方式来认知信息源头与客观世界,只会更无意识地接受媒介话语形态背后的信息意义,进而在脑海中形成一个媒介所期望形成的社会图景[5]。同时,“意义的产制、协商以及权力的争夺无不是以‘话语’作为利器”[6]。作为一种区域性媒介话语,甘肃故事在反映甘肃精神文化和社会结构的同时,也在形塑个体的认知结构和情感体验,甘肃故事话语的生产受到来自社会结构内民俗文化、社会经济、内部群体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成为一个话语博弈场域的集中表征,媒介话语的内容选择则是后台选取、更改、创作的结果。
通过对甘肃故事的报道语篇中基本单位话语的框架分析,本文试图研究这些媒介话语是如何建构甘肃故事的?这些话语“凝聚”了什么?又对什么进行了“分散”?
(二)结构性:框架布局
框架理论研究发端于20 世纪60 年代。1955年,人类学家贝特森提出了“元传播”(meta-communication)的概念,所谓“元传播”,即人们为了传播而进行的传播行为,包括对所传递符号的定义及其诠释规则的约定,在这里,框架指的是就如何理解彼此符号,传受双方相互约定的诠释规则。1974 年,戈夫曼明确对框架做出了定义,他认为,框架指的是人们用来认识和阐释外在客观世界的认知结构,人们对于现实生活经验的归纳、结构与阐释都依赖一定的框架,框架使人们能够定位、感知、理解、归纳众多具体信息[7]。至此,“框架”才作为一种理论被创立起来并逐渐引起广泛注意,“在大众传播、政治传播、科学传播、视觉传播、新闻学、社会运动、风险、宗教等各个社会科学领域迅速扩散”[8]。1980 年,托德·吉特林在戈夫曼的基础上将框架理论概括为“选择、强调和排除”[9]。近年来,新闻媒介就媒介框架与受众认知的互动关系和媒介基于什么样的“后台理论”构建了“前台现实”引起重视。为研究上述问题,选择具有典型性的文本,试图揭示甘肃故事话语的产制逻辑、社会效果和实践问题。挖掘媒介文本何以在一系列话语实践中深度构建中国区域形象,由此探讨在传播层面提升甘肃故事传播效果、降低“文化折扣”的策略。
二、“表象”促聚焦,打通话语自塑
本文主要采用甘姆森提出的“诠释包裹”(interpretive package)框架中的“框架装置”,包括隐喻、描述、短语、论据以及视觉影响进行分析[10],由于本研究样本量中描述性内容繁杂,根据研究需要,主要从结构框架、流行语、范例和隐喻四个方面进行研究,其中,“结构框架”指整体叙事主要从哪几个角度进行建构;“流行语”是指总结报道主题的特色性话语;“范例”是主题内容的真实叙事本体;“隐喻”是整个主题背后所表达的深层意涵。
本文选取2016 年12 月至2022 年4 月1 日之间的报道,基于媒体属性和影响力、媒介地域性和代表性等因素综合考虑,选择新华网、人民网、光明网、中国甘肃网和每日甘肃网五个平台,以“甘肃故事”为关键词,筛掉指涉“甘肃”和“故事”这个单一内涵的相关报道,由于样本量巨大,因此抽样出1000篇新闻报道作为分析对象,通过人工清洗样本,剔除广告、消息、报道人物及内容重复、弱相关性的报道样本,最终确定了614 篇新闻报道为研究对象。研究得知,甘肃故事的媒介话语实践框架主要有三类:一是情感型框架,聚焦事件中人、事、物的情感符号表达,旨在思想、价值取向、情绪共振等层面争取“他者”对甘肃精神的认同与赞许;二是实践型框架,以具体事件为牵引,着眼于结果、成就和主体等概念,检视既有成绩所面临的挑战和困难,以期增强对甘肃取得成绩的肯定;三是区域性框架,以“大叙事”为背景,宣传甘肃省的风情地貌、民俗文化、特色饮食等内容,厚植发展优势、拓宽发展空间。
(一)入理入情“讲”,强化区域认同
情感型框架包括“红色精神”的传承者和社会建设的“奠基者”两类。“红色精神”的传承者框架以红色“人物+故事+文物”为主线,通过《100个陇原红色故事》《文物里的红色故事》系列,对红色文化的内容和形式、特征和精神进行描述,凸显了长征精神、南梁精神、红西路军精神、莫高精神、八步沙精神、“铁人”精神等红色文化话语体系核心。话语主体呈现官方化特征,政府机构是框架选取和内容编辑的传播主体,他们从“小史料”出发,旁征博引、深入凝练,挖掘红色故事背后的精神内涵,以红色精神升华故事主题,以背景铺垫深化故事内容,以时代站位凸显故事价值,通过“故事性”的外化表达,塑造价值取向明晰的内在动力,表意出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不畏艰难等共义符号所连接的甘肃形象。
“奠基者”结构框架主要从人物故事、甘肃风土人情和地域文化为角度,以耋耄老人用微缩模型留住“甘肃记忆”——《兰州握桥》、《敦煌莫高窟》、《黄河铁桥》、《羊皮筏子》……画家张盈在高楼大厦中找寻被包围的破败院落等故事和《陇人相》系列的书写为真实叙事“范例”。话语主体呈现多元化趋势,政府、媒体和普通大众分别从不同侧面,以各自熟悉的话语结构对甘肃故事进行建构,整体呈现出一种凝结着集体身份、信仰和精神的象征模型,“显微镜”似的描述手法构建出一个对内凝聚共识、对外讲好故事的互动话语语境。
(二)入人入事“讲”,突出斐然成绩
脱贫攻坚的“奋进者”框架通过文本话语符号、话语场景展现、文本话语基调等方式,构建出一个三位一体的甘肃形象。话语场域呈现公共化特征,人物主体多元、话语场景丰富、话语环境轻松,《我的扶贫故事》中甘肃“西和巧女”何芳、西和县大桥镇李坪村第一书记兼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马国栋、退伍军人杨红兵、太平洋产险甘肃分公司赵建……无不为甘肃精准脱贫贡献了力量。其次,古岔村花椒产业、永登县元山村徐达忠夫妇、元古堆村脱贫和全省75 个贫困县全部摘帽,552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这些元素构成了甘肃优秀的战贫答卷,构建出精准脱贫的实践者形象。最后,古浪南部山区进行的易地搬迁、在干旱的陇中黄土旱塬形成苹果最佳种植区、在临夏回族自治州、甘南藏族自治州等“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形成了牛羊养殖产业带……凸显了就近选取帮扶对象、科学制定脱贫方案、强化脱贫长效机制、链接乡村振兴工作等强治理能力隐喻。
此外,抗击疫情的“战斗者”结构框架从抗疫人物事件、抗疫成果和抗疫细节的描述,隐喻出战争型英雄主义叙事和团结协作的共同体形象。“坚决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战士”、全民战“疫”等战争型流行语的使用,强调了此次疫情对健康的威胁,具有极强的警示作用,能进行充分而广泛的社会情感动员,强化社会各个群体的抗疫一致性,推动舆论合意的形成。话语逻辑呈现“战争性”和感人特征,战争隐喻的背后,甘肃参与抗疫的医务工作者和其他人员则成为了战争一线的“英雄”,这种英雄主义架构有利于最大限度地调动多主体参与疫情防控,激发抗疫正能量、弘扬真善美,推进疫情防控工作顺利开展。抗疫框架的叙事将个体放入集体的语境中,帮助淡化个体恐惧感和无力感,激起对灾难的共情,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集体主义,弱化了矛盾、冲突、对抗,强化了团结、合作、紧密,凝聚了甘肃生命至上、命运与共的抗疫精神,从实践的角度宣传了甘肃的抗疫成绩。
(三)入文入域“讲”,精准着眼特色
饮食文化的“宣传者”框架通过《甘味故事》系列旨在宣传内容与形式极具特色的地方小吃和特色食品来影响消费者的认知、吸引消费者注意、刺激消费者购买。话语内容呈现口语化与娱乐化特征,“流行语”拿下“C位”、不一样的烟火、极品、点赞、成名、乘风破浪、美貌、实力派、打call、slay 全场、沙井文化、pick 我......郎朗上口,通过陇西黄芪、临夏羊肉、肃北雪山羊、靖远旱砂西瓜、八步沙溜达鸡......等“范例”,隐喻着甘肃的饮食文化、地域特征、民族特色等议题,夹杂着复杂的经济、文化和资本互动,形塑了受众对异地文化体验的感官需求。文化传播的发生逻辑意味着公共文化传播过程的支配方式,是传播技术、媒介、时空关系、参与者以及管理体制的综合[11]。
区域文化框架中的表现和隐喻指涉到多元的地区精神,文化作为区域认知主体,通常创造性地以“新奇喻指”和“奇异故事”为构建,发挥敏锐的洞察力探索文化共性,减少“文化折扣”。甘肃故事中有关甘肃文化的塑造主要以敦煌文化、丝路文化为主,辅之以省内其他地区文化,文化故事中描述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文化溯源从内容生产的角度,构筑了特色的文化审美议题。甘肃公共文化传播场域基于精神内涵的逻辑演变模式,展现出敦煌精神、大禹精神、丝路精神、黄河母亲精神……等情感倾向,有利于文化建设和文化消费目标的达成,甘肃文化传播在自我建设的过程中不断塑造甘肃文化传播的公共价值和国际文化传播的交流对话。
最后,地理地貌的“拍摄者”框架对巧夺天工的自然、人文景观的描述,话语突出显示了甘肃对自身地理的认知和解读,在甘肃故事文本表达方式上,文本内容呈现以绝美图片和文字表述构成了故事叙事的基本表达形态,时空的变换不仅没有影响景观的表现,反而以不同的组合和主题呈现方式凸显着甘肃的坚忍、强劲、豁达和洒脱,给受众带去独特的感知和心理体验。
三、“横纵”抓核心,突出焦点矛盾
甘肃故事的话语建构通过强调地域文化符号,激活区域民族文化价值审美,搭建起历史文化、集体记忆、家国情怀等仪式传递空间,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区域性表达,但与此同时,仍有一些问题显现出来。一是不同框架之间价值内核不连贯。甘肃故事的“情感型”框架和“实践型”框架都从时间和空间维度、微观和宏观视角形塑了民族团结、坚忍独立、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奋勇进取的中国精神。但“区域性”框架中的饮食文化框架和自然地貌框架更多从甘肃“有形”事物出发,展现的是甘肃客观的自然情况,其文本叙事模式多以娱乐性为主,夹杂当下“流行语”,隐喻着丰富多彩的地貌类型,话语建构存在相同议题框架重复度高、不同议题框架间隐喻重合性强的情况,其话语结构、内容和场域并未明显体现甘肃精神和中国精神,同时将这两个框架和其他框架结构作为甘肃故事的统一文本进行叙事,难以让观众了解甘肃统一的核心价值体系,容易造成传播障碍和隔阂。二是地域文化符号选取面窄。所谓地域文化,就是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经过一定的时间积累所形成的具有地方代表性的社会习俗、文化形态、历史遗存等[12]。文化是符号建构,符号是文化的构成物[13]。莱斯利·怀特曾指出:“全部文化或文明都依赖于符号。正是使用符号的能力使文化得以产生,也正是对符号的运用使文化延续成为可能。”[14]甘肃故事中对甘肃地域文化符号的选取和建构是以甘肃地域文化资源为对象,通过符号化转换而形成的一种文化传播载体,是地域文化系统运转的底层逻辑。然而,甘肃故事以“红色”、“脱贫”、“抗疫”、“敦煌”等主要议题进行建构,对河西走廊文化、长城文化、黄河文化、佛教文化、始祖文化、五凉文化、民俗文化、特色节日等符号选取较少,难以建构真实、全面、立体的甘肃文化。三是话语展示模式创新性不强。整个三类框架结构中,其文本话语展示以文字、图片和短视频的形式为主,其中文字和图片占比较大,视频拍摄趣味性较弱,通常以简单的访谈为主,缺乏吸引力。文本语言地域性较强,针对不同受众的社会背景和文化素养并未建立良好的共通意义空间,“文化抵达”能力较弱等问题,这些都影响着甘肃故事的传播和甘肃形象的塑造。
四、“分层”找切入,探寻关键路径
甘肃故事的叙事实践表明,找准叙事问题并“对症下药”才是探寻甘肃故事传播的关键路径。一是聚焦甘肃精神,统一故事价值内核。“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的甘肃精神是甘肃特色鲜明的精神标识,甘肃故事的所有框架建构,都应以此为内核,在故事叙事性和思想性上达到有机统一,以不同的创作手法讲好在甘肃发生的故事、讲好甘肃人民的故事、讲好甘肃人在省外发生的故事,不断提高精神文化认同,为甘肃社会经济发展注入甘肃力量。具体来说,以讲述甘肃饮食和地理地貌为核心的故事框架,应打破文字为主或单一视频展示的方式,把介绍事物本身与人物、文化、历史和精神内涵相结合,与其他热点话题、类似事物、文化交流进行有益碰撞,增加故事的“话题度”,找准与其他受众的“共情点”。其次,“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甘肃地形狭长,每个市区县域都有属于自己独特的饮食特征和自然风光,因此,应以市区县域为单位,由小到大,分批次、分结构进行专题介绍,专题应统一策划、统一执行,确保每个故事的核心价值体系的连贯性,依托地理地貌和饮食故事,打造甘肃特色品牌,发展文旅产业,促进甘肃经济发展。但值得注意的是,甘肃固然有甘南绿洲、沙水共生月牙泉、景色秀美崆峒山等风景名胜,但其干燥缺水风沙大等方面也不应被完全忽视,这也无形中展现了甘肃人民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品格,只有兼顾地理地貌的两面性,才能完全意义上展现立体的甘肃形象。二是提炼文化符号,多元建构故事视角。以文化人,能洁净心灵;以文通人,能沟通世界。甘肃故事文化符号的选取是讲好甘肃故事的基础,文化符号选取的第一步是建立跨学科、跨地域、多元化的文化研究平台,对甘肃文化进行整体研究、系统梳理,汇总出能表达展现甘肃悠久文化历史的关键符号,为甘肃故事的内容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其次,从传播学角度来看,减少和消除“文化折扣”的机制与操作逻辑,必须着眼于信息触达、信息解码、信息认同这三个关键性传播节点,探讨其形成的内在机理,提升传播效果与质量,这对增进社会共识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参考价值[15]。要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价值体系“风向标”,选取那些能展现甘肃精神和中国理念的文化符号,深入挖掘甘肃文化蕴含的新时代价值,不断推出契合时代精神的文化产品,以更为深邃的视野、更为博大的胸怀、更自信的态度择取最能代表甘肃变革和中发展的故事,展示多元、鲜活的民族文化形象。三是丰富讲述模式,打通故事叙事思路。差异化讲述就是根据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阶层的受众,根据他们的特点和诉求,进行针对性的话语语境策划。如面对国际受众,可以从符合全人类真、善、美的角度讲述甘肃故事;面对社会背景、经济水平、教育经历和兴趣偏好完全不同的受众,同一信息需要差异化阐释,不能将传播知识作为首要目标,以学理性和娱乐性兼具的方式,在编码过程中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真正迎合知识水平较低的普通受众的偏好;针对在甘肃的外地人和外国人,甘肃故事的讲述模式更要选择符合他们文化环境的话语模式,主要使其增强对甘肃的认同感,甚至让他们成为主动讲述甘肃故事的主体。其次,充分探索文本传播“新思路”。不同的故事类型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展示:人物故事文本可以动画形式展示,使用夸张、拟人等艺术表达方式,让文本中所蕴含的主题以喜闻乐见的方式展现出来;甘肃文化文本可以歌舞形式触达受众,在宏大秀丽极具甘肃特色的舞台上,通过表演者对甘肃文化的形象化、具像化演示,激起受众对甘肃文化的兴趣和关注;甘肃地貌与特色产品则更适合以直播的形式进行展演,直播与平台、算法、数据等技术共同构筑了“真实”、“接近”的传播场景,受众跳脱出图文展示的平面空间,而故事建构“后台”也可根据数据和受众动态进行后续文旅与文化符号消费的行动。最后,找寻多元化故事讲述主体。当地政府和官方媒体成为主导信源,可以在讲述红色故事、文物故事等内容上塑造良好的传播主体形象;网络大V 和意见领袖可以从专业视角对甘肃故事的话语建构、文本表达形式进行指导,也可以成为专业型甘肃故事讲述人;普通民众则可以充分利用B站、小红书、抖音、快手、知乎等平台,从实践者、亲历者、目击者等不同视角出发,增加故事的真实性和可看性,全面实现甘肃文化和甘肃精神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传播。
本文通过框架分析法,基于媒介文本对甘肃故事的话语实践,探讨了甘肃故事话语建构的“三大框架”和“七小框架”。作为传播实践形式的一种——“讲故事”往往在传者与受者之间嵌入了不同时空情境下的符号和情感链接,在拓宽共通意义空间和增强话语建构能力的基础上,受众对甘肃故事的感知层层转化为“内部力量”,此时“甘肃”和“故事”组合构成了“甘肃故事”的话语表达,这种表达不仅涉及甘肃的自我认知、自我建构、自我评析,更包含了他者对甘肃形象和甘肃精神的理解。甘肃故事的媒介话语建构透露出强烈的区域性和民族性的叙事倾向,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既是不同文化族群理解力差异的表现,也是甘肃故事实现跨文化、跨区域传播困境的现实原因。甘肃故事的传播亟需规避或淡化过度区域化的话语符号建构以突出普世价值观,又要在议题和传播方式上强调个性和多元化,只有这样才能与异文化者产生共情,达到构建真实、多元、美好甘肃形象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