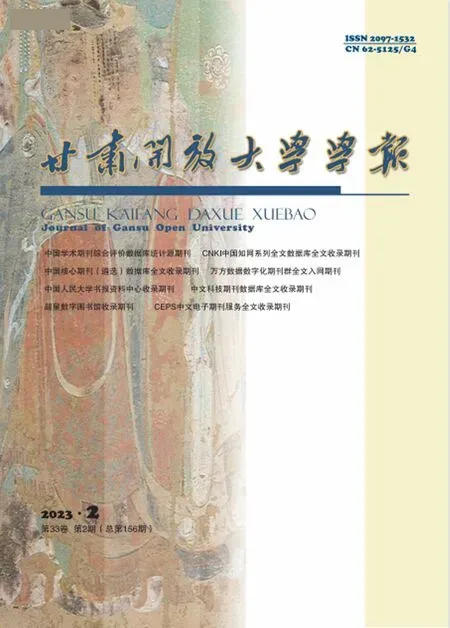论王初桐词论对浙西词派的发展
——以《小嫏嬛词话》为中心
赵远震
(江苏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王初桐(1730—1821),字耿仲,号竹所,又号巏嵍山人,江苏嘉定(今上海)人。工诗词,好著书,有词集《巏嵍山人词集》《选声集》,词论《小嫏嬛词话》。清人多将王初桐归入浙西一派,吴省兰《巏嵍山人词集序》云:“溯词坛之正派,惟竹垞为擅场。既已躏玉笥之庭,入玉田之室矣。岂知后有来者,更觉前无古人乎?我友王七自小工词,冠时独出。”[1]638吴氏认为王初桐可与浙派宗祖朱彝尊相抗衡,甚至“后来居上”。此论虽不免有溢美之嫌,但可看出这种比较是以默认王初桐为浙派词人为前提条件的。王昶亦编选《练川五家词》来标宗立派、宣扬浙派词风,王初桐被王昶选中成为“五家”之一,更加坐实了其浙派词人身份。
王初桐词论《小嫏嬛词话》集中体现了王氏对浙派词学观的继承,如推尊姜夔、张炎以及浙派领袖朱彝尊;主张“雅正”“清空”,反对秽亵、鄙俗;推崇南宋;重视声律;注重浙派咏物传统等。然而,王氏于《小嫏嬛词话》中又表现出了对浙派的突破,在继承浙派思想理论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
一、词以“自然”为宗
浙西词派自立派以来,便以咏物词著称。朱彝尊借《乐府补题》开咏物之端,一时和者不计其数。他本人亦有《茶烟阁体物集》,内多咏物之作,时人均奉为圭臬,并群起效之,大开咏物滥觞。然而浙派咏物之作颇多弊病,正如严迪昌先生所说:“一是如‘咏猫’词的堆积典故,成为‘方物略’……另一种则专事镂空凿虚,捕风捉影,纯从形式美或文字技巧上着力,刻画深细,联想多端。”[2]251这种弊病自朱彝尊始,厉鹗加以沿袭,“厉鹗词的又一缺点是咏物堆砌典故,凿虚镂空。”[2]318到了浙派后期此种情况愈演愈烈,弊病愈显。
王初桐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认为堆砌雕琢只会导致词作直涩粗晦:“或失之直,或失之涩。直则粗,涩则晦。”[3]1094这背离了浙派“风雅”的宗旨,进而他提出词应与诗一样以“自然”为宗:“作诗以自然为宗,作词亦以自然为宗。”[3]1079那种炼意饰辞、雕琢刻画之作虽极工整,却非上乘,在推尊词体的同时亦表明了词之宗尚。而后他引彭骏孙之言指明具体作法:“词以自然为宗,但自然不从追琢中来,便率意无味,如所云绚烂之极,乃造平淡耳。若使语意淡远者,稍加刻画,镂金错绣者,渐近自然,则为绝唱矣。”[3]1079这种示以学人并非泛泛而谈的作法使其立论更另人信服。同时,王初桐还对那些“自然”之词高度肯定,如他指出温庭筠《河渎神》《酒泉子》《遐方怨》《蕃女怨》等词均符合“自然”准则,并认为温庭筠正是凭借这种“自然”之词才得以独胜晚唐五代。
王初桐对浙派咏物词弊端有着清醒认识,反对堆砌典故、字雕句琢,提倡词以“自然”为宗,并提出具体作法,赞赏“自然”之词,是对浙西词派的发展与突破。
二、求“雅”亦重“情”
所谓求“雅”重“情”,即在重视词作“雅正”“醇雅”的同时又主张词应抒发感情。浙西词派发展到中后期,一些追随者片面强调词之“雅”,为了达到这一目地,不惜卖弄形式技巧,完全无视词的情感因素。正如孙克强先生言:“(浙派)对于‘雅’的理解和追求,又不免产生了极端和偏颇……强调文雅精致而忽略了词作为文学作品最根本的情感因素。”[4]247究其原因,在于他们缺乏大家的天赋才华、阅历经验,导致他们仅能学其表而遗其里,正如陈水云先生所说:“步趋朱、厉者以姜、张为尚,取其形而遗其神。”[5]
针对浙派“不足于情”的缺失,王初桐提出词应“本性情”“宣郁达情”。其《选声集·自序》云:“昔何大复论诗,谓:‘诗本性情,其切而易见者,莫如夫妇之间,是以三百篇首《关雎》,六艺始风,汉魏作者必托诸夫妇,以宣郁达情。至唐杜子美博涉世故,而出于夫妇者常少,致兼雅颂,而风人之义或缺。’词固沈著,调失流转,实歌诗之变体。”[1]640他引用何景明论诗之言来表明自己的观点,即词固然需要着实不轻浮,但像杜诗那样仅吟咏时事、关注现实,缺乏比兴情感亦不可取。词作为诗之变体,诗词一样,均应“本性情”,重视情感的抒发,在求“雅”的同时亦不能忽视“情”。
王初桐对于艳情词的欣赏便是其重视“情”的明证。如王初桐认为张先词作多情感寄托,达到了柳永词的境界:“张子野词,才不足而情有余,与柳耆卿齐名。”[3]1003其对张先词的肯定亦反映出对柳词的认可。而对于浙派来讲,柳词甜俗卑下,多淫语,这与他们所标举的“雅正”“清雅”大相径庭,故浙派对于柳词往往嗤之以鼻并大加贬低。然而王初桐却认为,只要作者于词中有情感寄托,并且是出于真情流露,那么这种艳丽之作未必不可视为雅词。当然,这里所说的艳情词并非指言语的淫哇、秽亵,而是有内在情感寄托的佳作。王初桐还十分重视词之雅正的,并非重“情”而轻“雅”,他指出:“言情之作,贵乎雅正,最忌秽亵。”[3]1009那些言语秽亵、浅露浮薄,而无真情实感的言情之作为词家大忌,并警醒学人注意分辨,切勿模仿。
在王初桐看来,除了艳情词,咏物词亦应注重情感的抒发,以能达到情景交融之境界为妙。如他认为丁澎《琐窗寒》《柳初新》等咏物词“情味无尽”[3]1097,这在本质上是肯定了于咏物之中融入情感的做法。那么咏物词如何才能融情入景?王初桐指明了具体门径:“结句须要放开,含有余不尽之意,以景结情最好……或以情结尾亦好,往往轻而露……”[3]1029即在结句以景结情或以情结尾。
同时,王初桐对这类情景交融的咏物词大加赞赏,给予充分的肯定,如他认为王士祯《醉花阴》《浣溪沙》等小令情深意切,超逸不俗,不输李璟、李煜二主,他说:“阮亭小令,极哀艳之深情,穷倩盼之逸趣。其《醉花阴》《浣溪沙》诸阕,不减南唐二主也”。[3]1096不妨试看王士祯《浣溪沙·红桥》:
北郭清溪一带流,红桥风物眼中秋,绿杨城郭是扬州。
西望雷塘何处是?香魂零落使人愁,淡烟芳草旧迷楼。
红桥位于江苏扬州,明末建成,为扬州一景。词上阙描绘了“清溪”“红桥”“绿杨”等眼前美景,清丽澄淡,令人神怡。下阙便由此联想到古时此处风景胜地——雷塘,如今何在?而当怀古伤今之愁刚欲抒发之时,却以景作结,到如今徒留荒草旧楼。整首词情景交融,清空雅正,亦运用王初桐所谓以景结情之手法,无怪乎受到王氏赞赏。可以说,无论是艳情词亦或是咏物词,王初桐均在求“雅”的同时亦看重“情”,不忽视词作情感因素,这是对浙派纯以玩弄技巧形式弊病的纠偏。
三、尊南亦重北
有明以来,词坛大多推崇以“花草”婉约为主的北宋词风,而对南宋颇为轻视。然而自朱彝尊立起宗南宋大旗之后,风气为之一变。正如陈廷焯云:“国初多宗北宋,竹垞独取南宋,分虎、符曾佐之,而风气一变。”[6]3825在朱彝尊等人的带领下,词坛风气逐渐由北宋转移到南宋。但是有些浙派后继者却陷入独尊南宋的牢笼,完全忽视北宋。在这种情况下,王初桐于词论中表现出尊南宋亦推重北宋的倾向,可以说是对浙派的补充与发展。
首先,王初桐非常欣赏北宋词作。他认为晏几道词秀气胜韵,浑然天成,他人均难以模仿学习,《小嫏嬛词话》云:“叔原词如金陵王谢子弟,秀气胜韵,得之天然,殆不可学”[3]991。同时他认为晏殊词格调高远,在宋人中不可多得:“宋人词句之最藉藉者,莫如‘红杏枝头春意闹’……余谓皆语奇而格不高,不如晏同叔‘双燕欲归时节,银屏昨夜微寒’……格调之高,直逼唐季,宋人中所不可多得。而不知者,皆以为平淡无奇也。”[3]992除了对二晏词作评价极高,王初桐对贺铸词也给予肯定,并认为贺铸词工妙精巧,思路清晰,胜于晏殊、张先诸人。《小嫏嬛词话》云:“贺方回《青玉案》词,工妙之至,无迹可寻。语句思路,亦在目前。而千人万人,不能凑泊。”“方回长调便有美成意,殊胜晏、张。”[3]1007由上可以看出他对北宋各家词风了如指掌,这种“熟悉”亦从侧面反映出他对北宋词的赏识。
其次,王初桐十分推崇周邦彦等北宋词人。对于周邦彦,浙派词家多持否定态度,虽然厉鹗曾对周邦彦给与肯定,认为“两宋词派,推吾乡周清真。婉约隐秀,律吕协谐,为倚声家所宗”[1]432,推周邦彦为倚声之宗,但这显然有标榜同乡之嫌。后来王昶、郭麐等人更是对周邦彦大加鞭笞,认为其词浮艳奢靡:“‘施朱傅粉,学步习容’的清真词是淫艳浮靡词风的代表,应在排斥之列。”[7]对此,王初桐持否定态度,他反驳道:“盖自姜、张盛行,海内词人莫不厌言北宋,即知音如周邦彦,无复窥寻,亦入主出奴之一弊也。自古文质异尚,三王之道若循环,安知数传而后,不又有厌言姜、张而竞称周、秦者乎?”[1]640此论充满辩证之思,他认为自姜夔、张炎词风盛行,浙派词人便摒弃北宋,即使是熟知音律的周邦彦,亦被他们所轻视。然而又怎能知道后世人不会轻视姜夔、张炎而重视周邦彦、秦观呢?同时,王初桐还将周邦彦的地位提升至与姜夔同等高度,认为二人并肩齐驱,分别为南北宋之冠,他说:“北宋之英华,至周清真而极;南宋之光气,自姜石帚而开。清真,北宋之殿;石帚,南宋之冠”[3]1032。除此之外,王初桐对清真词也大为欣赏,认为其词浑然天成,富艳精工:“周邦彦词多用唐人诗句,隐括入律,混然天成。长调尤善铺叙,富艳精工。”[3]1025
再次,王初桐能客观看待南北宋之争,对北宋词多理性之思。南北宋之争自古便是文学中的热门话题,最早可以追溯至宋代。李清照曾于《词论》中表现出强烈的辨体意识,历数北宋各家之失,意欲为南宋学人提供学习范式,虽有标榜自我之嫌,却有意无意地体现出南优于北的思想。而后黄昇分别编选《唐宋诸贤绝妙词选》《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将南北宋词分卷编纂的做法亦有划分时代、争论南北的意味。而明代“花草”词风的盛行,实际上就是宗尚五代北宋婉约柔美词风的反映,这导致以朱彝尊为代表的浙西词家的不满,因此他们标举南宋姜、张与之抗衡,试图拨正明代以来宗北宋的风尚,具有明显的南北宋之争意味。到了浙派中期,厉鹗更是继承朱彝尊宗南宋的做法并加以发展,“厉鹗在朱彝尊的基础上丰富了争论的内涵并提出南北宗之争的概念,借此将豪放词剔除出宗尚序列”[8]。这一行为更是加重了南北宋之争,导致浙派后继者独尊南宋,囿于南宋。
在这种情况下,王初桐理性看待南北宋之争,并对北宋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其《小嫏嬛词话》卷三云:“王小山云:‘词至南宋,始称极盛。’诚属创见。然笃而论之,细丽密切,无如南宋;而格高韵远,以少胜多,北宋诸公往往高拔南宋之上。”[3]1088王初桐认为南宋词细丽密切,是北宋词所不及;然而若论格高韵远,北宋词又在南宋词之上,此论客观公正。又云:“朱竹垞云:‘词至南宋始工。斯言出,未有不大怪者。惟实庵舍人意与余合。’余谓此论为慢词言之耳,若小令,则至南宋而始衰。”[3]1088王氏认为朱彝尊“词至南宋始工”说有失偏颇,此处所论之词仅是指慢词,若论小令,则北宋优于南宋。
总之,王初桐对南北宋之争有着清醒地认识,他认为探讨南北宋之优劣不可一概而论,应分而观之,北宋词亦有优于南宋之处,这是对浙派词人盲目推崇南宋词的一次纠偏。
四、标立“第三派”的同时兼重婉约与豪放
朱彝尊推尊南宋姜、张,目地在于构建一个可以与婉约、豪放相抗衡的“第三派”,即“姜派”或言“清空”一派,而非简单地树立个别典范人物。其促进清词振兴的出发点是好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浙派后人却独尊“第三派”,漠视甚至完全摒弃婉约与豪放传统词派,取径狭窄,作茧自缚,遂至浙派渐趋没落。对此,王初桐深表惋惜,并指出自“姜派”出,而之前婉约与豪放之风尽失:“清真以前,大抵皆言情之作,白石变而大之,尽扫旖旎,专事浩落,开出情空一派,所谓野云孤飞,去留无迹。而前此蕴蓄深厚,格韵闲远之趣,荡然无存矣。”[1]640对此,他提倡在标立“第三派”的同时亦不能忽视婉约与豪放,“大旨仍主姜、张,而出入周、秦,旁及辛、刘,庶几不拘一格云。”[1]641表现出开放、宏通的词学态度,拓宽并丰富了后期浙派词论家的视野及词派观。
(一)推重《花间集》
王初桐对于婉约的重视除了表现在对上文所提及的北宋婉约词人词作的推崇,亦表现在对《花间集》的推重上。
受明代《草堂》《花间》影响,清初词人依然难以摆脱《花间集》束缚,蒋兆兰《词说》云:“清初诸公,尤不兔守《花间》《草堂》之陋。”[6]4637王士祯早年就受《花间集》影响较深,其《花草蒙拾》自序云:“往读《花间》《草堂》,偶有所触,辄以丹铅书之,积数十条。程邨强刻此集卷首,仆不能禁,题曰《花草蒙拾》。”[6]673他交待《花草蒙拾》正是读《花间》《草堂》有感而作,而后其与邹诋谟合编的《倚声初集》更是有意接续《花间》《草堂》。
然而,浙西词派对于这种淫哇鄙陋、媚俗软弱的“花草”词风大加鞭笞,将矛头直指《草堂》《花间》,尤其是《草堂诗余》,朱彝尊极力抨击,《词综·发凡》云:“古词选本,若《家宴集》……及草窗周氏选,皆佚不传,独《草堂诗余》所收最下最传,三百年来,学者守为《兔园册》,无惑乎词之不振也。”[9]直接将词学衰颓的原因归咎于《草堂诗余》。而对于《花间集》,朱彝尊态度则相对含蓄,“即使他不再加以明确的肯定,其态度依然相当含蓄,从未有过如对《草堂诗余》那样的激烈言论”[10]。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其早年学习小令,以《花间》为宗,“朱彝尊初涉倚声,路子较杂,小令大抵学《花间》”[2]238。早年对《花间》的学习可视为其对《花间》的认可。另一方面,浙派成立之后,《花间》词风与浙派“雅正”宗旨相冲突,使得朱氏不得不避而远之。这便导致了他对《花间》的矛盾心理,因此态度也就相对含蓄。
相较于朱彝尊的温和,王昶对《花间》的态度则显得犀利尖锐,他指出明人以《花间》为宗,粗厉猥亵,与南宋词之“雅正”背道而驰,“有明三百余年,率以《花间》《草堂》为宗,粗厉猥亵之气乘之,不能如南宋之旧”[1]581。又云:“毛先舒《词谱》,沈雄《词话》,邹诋谟、聂晋诸选,仍不出《花间》《草堂》柔曼淫哇之习,是以为世儒所轻。”[11]批评诸家所选不出《花间》《草堂》牢笼,阻碍了词的发展。
与上述几家不同,王初桐对《花间集》颇为推崇,这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对《花间集》版本进行详细考证,而且对《花间集》体制颇为认可。《小嫏嬛词话》卷一:“孙光宪《竹枝》二首,《花间集》合作一首,误。余观《花间》之误,不一而足,甚至有不能句读者。只因此书七百年来,几经传写,几经翻刻,遂失当时编次之意,惟汤临川刻本稍善。”[3]979王初桐认为《花间集》经过几百年的传写、翻刻而出现讹误在所难免,情有可原。并考出《花间集》版本当以汤显祖临川刻本为善。卷三云:“《花间》体制,调即是题。宋人词集,大抵无题。《花庵》《草堂》增入《闺情》《闺思》《春景》《秋景》等题,深为可憎。”[3]1118他认为《花间》调即是题的体制最佳,宋人的词集也大多无题,而《花庵》《草堂》增加词题的做法深为可憎,打破了《花间》调即是题的体制。一褒一贬可见其对《花间》的推崇。
另一方面以《花间集》作为衡词标准,并认为后世词作均不及《花间集》。如王初桐认为晏几道、欧阳修词作皆不及《花间》高深古厚,不仅此二人,北宋学《花间》者均如此:“盖《花间》之高深古厚,两公不逮尚远。不特两公,凡北宋之学《花间》者皆然。”[3]978可见其对《花间集》推崇之高。又云:“《花间集》字法最著意设色,异纹细艳,非后人纂组所及,所谓古蕃锦也。至范文光《续花间集》,风斯下矣。黄陂张迂公《和花间词》,取《花间》之韵而全和之,犹今诗家之和陶。”[3]978他指出《花间集》艺术手法高妙,后人皆难以企及。而后世所作续、和《花间集》,犹如今之诗人所作和陶诗,与《花间》有着天壤之别。同时,他还认为《家宴集》《尊前集》等词集“皆不及《花间》”[3]978。总之,与朱彝尊含蓄内敛,王昶极力批判的态度不同,王初桐对《花间集》推崇备至,可视为其对婉约词风的重视。
(二)旁及辛、刘等豪放派
以辛弃疾、刘过等为代表的豪放词人向来不受浙派词人重视,“豪旷不冒苏、辛”“豪放者失之粗厉”。相较于前辈学者,王初桐则表现的较为宏通,其“旁及辛、刘”的言论与做法无疑为浙西词派注入新鲜血液。后来浙派后劲吴锡麒开始有意学习苏、辛,并且宣扬这种词学取径,表现出与王初桐相近的词学主张,不能不说是受王初桐影响。因为二人曾在乾嘉之际于扬州地区谈论词学,互相呈示词作[12],且王初桐比吴锡麒年长十六岁,论资排辈可算作吴氏前辈,故吴氏思想可能受王氏浸染。
王初桐对辛弃疾极为推崇,对稼轩豪迈豁达的精神状态高度赞扬,“意气轩举,千载如见”[3]1022。他认为稼轩神采焕发,气概不凡的模样即使经历千年,依旧如在目前。除了对辛弃疾人格的崇拜,王初桐对稼轩词亦高度肯定:“变调词,辛苏并称,当以稼轩为第一。刘龙洲、刘后村,学稼轩者也,皆近乎粗。”[3]1022所谓“变调词”,即豪放词,这是相较于婉约词而言。我们知道,词在苏轼之前大多为言情之作,内容不外乎男欢女爱,歌舞升平。而苏轼“以诗为词”开拓词的题材内容,以词怀古、纪行、咏史,改变了词作以往面貌,故将豪放词称为“变调词”。王初桐认为豪放词虽苏辛并称,但稼轩更胜一筹,当推为第一,而其后的刘过、刘克庄等学稼轩者所作之词均近乎粗放,与稼轩词相距甚远。其后又引张炎语:“辛稼轩《祝英台近》,皆景中带情,而存骚雅。”[3]1023表明稼轩《祝英台近》数首词皆景中带情,且存骚雅,既符合“雅正”之旨又有“情感”寄托,是对稼轩词的高度认可。
王初桐在标举第“第三派”的同时不废婉约与豪放二体,他的这种做法被其叔王鸣盛总结为“细”,“细者,非必扫尽艳与豪两派也……即间作艳体、豪体,亦自无妨。总之,以细为归耳。”[1]638-639可以说,王初桐这种“细”的词学主张,“在词论史上的‘重’、‘拙’、‘大‘、‘尖’、‘沉郁’等审美范畴外扩充了词的美学概念”[13]。同时,又丰富了浙派词派观。
五、对浙派圭臬《词综》《词律》的修订校勘
浙西词派的建立,除了与《乐府补题》的复出有着密切的联系,朱彝尊《词综》的编纂亦是一个促进因素。向风慕义者一时蜂起,遂成浙西一派。朱彝尊等人“以姜夔为‘祖’,构建起了南宋词人的‘醇雅’统序”[14],以《词综》为载体构建起浙派“统序”,因此《词综》在浙派词人看来无异于成宪,具有权威性、合法性,不容置疑。
然而,与其他浙派词人顶礼膜拜的态度不同,王初桐则敢于指摘《词综》之误,并加以修正。他在《小嫏嬛词话》中总共订正《词综》之误20处,包括文字之讹8处,文字之脱3处,名号之误1处,失注之误4 处,失题之误1 处,其他错误3 处。具体来说,王初桐对《词综》文字之讹的校正如:“周邦彦《应天长慢》‘前社客’,《词综》误作‘前客客’,查《清真集》,作‘社’。”[3]1091对《词综》文字之脱误的校正如:“张先《惜琼花》云:‘汴河流,如带窄。任身轻似叶’,《词综》脱‘汴’字,‘身’字,据《安陆集》校正。”[3]1090对前人名号之误的纠正如:“杨炎正号济翁,《词综》误作杨炎号止济翁,与《西樵语业》异。再考《武林旧事》有杨炎正诗,《全芳备祖》有杨济翁诗。又杨诚斋《诗话》云:‘予族弟炎正,字济翁。’益知止济之误。”[3]1091对失注之误加以指正:“田不伐有《洋呕集》,见白朴《天籁集》,《词综》失注。吕本中,申国公公著曾孙,《词综》失注‘申国公’三字。”[3]1091
除了《词综》,王初桐对万树《词律》亦多加勘误。众所周知,浙西词派十分重视音律,浙派填词者更是将万树《词律》视为圭臬,王初桐说:“《词律》一书,填词家奉为成宪,观其细心体会,校之毛稚黄《图谱》,功罪悬殊。但苦见闻狭隘,考证空疏,往往多以讹传讹,以臆猜测处。”[3]1104-1105批判他们对于《词律》全盘接受的行为,同时亦指出《词律》所存在的问题,即考证空疏,从而导致后人以讹传讹,以臆猜测。于是王初桐在馆阁仇校之余,凭藉点勘,在《词话》中总共修正《词律》讹误37处,除文字之讹、脱、衍外,还包括不分段、不合谱、不合韵、失注等错误。
王初桐对万树《词律》中押韵的错误多有修订,如:“《锁窗寒》,小注‘忽双眉暗斗’,自是汲古阁刊讹,查《词纬》作‘搔首双眉暗斗’,‘首’字韵‘斗’字叶。”[3]1107王初桐认为万树于《词律》中所注《锁窗寒》失韵,他指出“斗”字叶“首”字韵,而非“忽”字,应根据《词纬》校正。又如:“《逃禅集》有《玉抱肚》一词……此调不见于前,恐是清夷长者自制曲,原本三段,《词律》误作二段……并于‘左’字注叶韵,皆误。”[3]1015王初桐认为《玉抱肚》一调为杨天咎自制曲,万树《词律》将三段改为二段,同时注“左”字叶韵,均错误。总之,王初桐以批判的眼光看待《词律》,并将错误逐一指正,是对浙西词派重视格律、音律的发展。
六、余论
王初桐于词论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理论,对于纠正浙派后期之弊病大有裨益,在多方面对浙派有所发展。同时也体现出浙西、常州二派合流的思想倾向,这对同时期或稍后词论家多有影响。例如王昶于《西崦山人词话》中表现出对柳永及其艳词的认可[15],与王初桐重视北宋,重视有情感寄托的艳情词的看法颇为相似。吴衡照《莲子居词话》所持立论虽多沿袭、推崇浙西一派,但亦
可以看出常州词派开始兴起的迹象[16],体现出融合浙、常二派的倾向。这可能是受到王初桐词论的影响,因为从先后顺序来看,《小嫏嬛词话》比《莲子居词话》成书要早。至于后来兴盛于道光年间的吴中词派,其对“浙西呈现出既亲和又游离的态势”[17],与王初桐词论中所表现出的对浙派既继承又发展的态度不谋而合。况且王初桐与吴中词派同乡前辈“前吴中七子”大致同辈且关系密切、多有交游,那么王氏对吴中词派形成一些潜在影响也就不难理解了。尤其是杜文澜于《憩园词话》中所体现出的调和浙、常,融汇三派的思想,可以看作是对王氏词学观的继承。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小嫏嬛词话》具有远超词话本身的、更为深远的价值与意义。
——兼论梅里词派及浙西词派的形成过程》手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