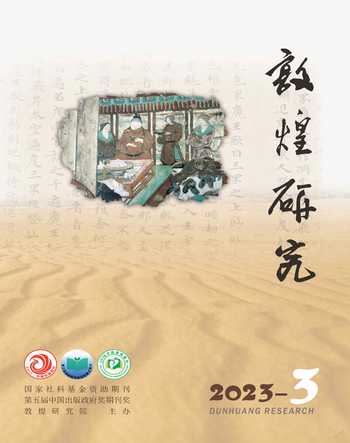莫高窟北区元代瘗窟B121窟死者身份考
吴雪梅 沙武田



内容摘要:据考古报告莫高窟北区B121窟为元代的一处瘗窟,死者为一青年女性。结合窟内随葬遗物判定该洞窟的使用年代约在14世纪中后期。死者为豳王家族一位信仰佛教的青年女性,所着服饰为“满池娇”红色莲鱼龙纹绫袍。窟内出土多件佛教文献,由此看出元代豳王家族佛教信仰背景。该窟同时也为莫高窟“元代公主”的传说提供了新的線索,推测B121窟为元代公主的瘗埋之所。
关键词:莫高窟B121窟;元代;瘗窟;速来蛮家族;“元代公主”传说
中图分类号:K87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23)03-0076-12
A Study on the Identity of the Deceased Woman in Yuan
Dynasty Cave B121 at the Mogao Grottoes
WU Xuemei SHA Wutian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19, Shaanxi)
Abstract:According to archaeological reports, cave B121 at the Mogao Grottoes was a cave used for burying the dead in the Yuan dynasty, and a young woman was once buried there. However, the various burial items found inside cave indicate that the cave was in use as early as the mid-late 14th century. Study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including manuscripts from Cave B121, can confirm that the deceased young lady can be identified as being a member of the family of Lord Bin (豳王 Bin Wang). The clothing she wore was a kind of red satin robe known as a manchi-jiao满池娇 and was intricately embroidered with motifs of lotuses, fish and dragons. Several Buddhist documents unearthed from the cave indicate that the family of Lord Bin believed in Buddhism. The cave also provides new clues regarding the legend of the “Princess of the Yuan Dynasty” at the Mogao Grottoes. It can be inferred that Cave B121 was the place where the princess of the Yuan dynasty mentioned in the story was buried.
Keywords:Mogao cave B121; Yuan dynasty; burial cave; legend of the“Princess of the Yuan Dynasty”
B121窟位于敦煌莫高窟北区崖面第三层(图1),有前室、甬道和后室,前室部分坍塌,后室大部分塌毁,现已看不出原来形制。《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考古报告推断,“石窟内有人骨,且遗物较多,故其性质应该为瘗窟”[1]。通过人骨鉴定和遗物判别,该窟为一座元代瘗窟,死者是一位青年女性。根据出土遗物数量较多分析,瘗埋的青年女性身份较高。北区考古之后,除了对个别民族语言文字残件有零星的研究外{1},就洞窟本身一直未引起学界的关注。
赵丰等对该窟出土丝绸的最新研究,给我们极大的启发[2]。加上近年来“敦煌西夏石窟研究”课题组在对莫高窟北区第464、462窟进行专题研究的同时,发现B121窟极有可能是驻守沙州的蒙古豳王家族的一位青年女性瘗窟。这对进一步研究豳王家族佛教信仰、豳王家族在莫高窟的活动、元代北区石窟属性、豳王家族丧葬习俗、元代河西墓葬考古等有所助益,草成此文,敬希方家教正。
一 随葬回鹘文、蒙文残片与瘗窟埋葬年代之判定
根据《元史》记载,元朝在河西的统治实行宗王出镇制度。元朝建立之初,令出伯、合班出镇肃州、沙州、瓜州以及哈密诸地{2}。由于敦煌特殊的经济文化地位和军事地理位置,元朝在沙州和瓜州地区同时设立沙州路总管府,由出伯家族及其后裔出镇包括沙州、瓜州在内的河西西部地区。关于出伯家族的世系及其在瓜沙地区的活动,日本学者杉山正明、松田孝一以及中国学者胡小鹏、杨富学等前贤都有详细的梳理和研究{3}。下面主要从莫高窟北区B121窟随葬出土的两件回鹘文、蒙文残片透露出的时代信息出发,对该瘗窟的埋葬年代进行判定,并就B121窟女性窟主身份给出一些新的线索。
从B121窟出土文献来看,主要有回鹘文、蒙文、西夏文佛经及文书残件。张铁山先生对B121:37(图2)回鹘文残卷进行过判断,认为该回鹘文残卷上的回鹘文字母n上有加一点,q上有加两点,此为晚期回鹘文特征,该佛经属于元代[3],考虑到洞窟作为瘗窟其使用年限必定在文本年限之后,所以B121窟的使用在元代是明确的。另外,洞窟中还出土蒙文残件B121:40,上下双栏,左右单栏,靠右侧第四栏内有汉文“扎里牙(阿)哇答儿 八十六”(图3),是该佛经的汉文简称和页次。根据内蒙古师范大学嘎日迪先生释读该经为《入菩萨行论》(或称《入菩提行论》),主要颂扬菩萨行,是7世纪印度寂天论师衔地爹瓦撰写的一部佛教经典,10世纪译成汉文,14世纪译成蒙文[4]。据此可以将该窟的使用时间进一步推研。1305年元代高僧搠思吉斡节儿(蒙语Nom-un gerel)将《入菩萨行论》译成蒙文后开始在蒙元信众间流传{1},B121:40《入菩萨行论》现在只有蒙文4行,汉译为:“犹如莲池里的凫雁,坠入无尽的地狱,如若众生完全解脱……”[4]14仅凭残存文字无法确定文本具体年代和版本,只能寻找最为接近的文本。敖特根先生曾对此文本做过记述,认为:
敦煌残叶中的三行字除了tonilbasu一字之外,完全与新德里手抄本(L6)第40叶正面第3l—33行相对应,说明德里手抄本的底本应该是与敦煌残叶同属一个版本,也就是说敦煌印本残叶年代应早于新德里手抄本(L6)年代。新德里手抄本共56叶111页,每行字数少于丹珠尔本(52叶103页)。这样一来,敦煌本也应该是56叶左右。[4]13
新德里手抄本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完整蒙文《入菩萨行论》,现存新德里印度文化国际研究院,编号L6,为罗克什·钱德拉(Lokesh Chandra)教授从乌兰巴托甘丹寺的一位喇嘛手中所得。他认为,此手抄本年代应早于1748年乌拉特固师毕力衮达赖校勘后的蒙古文木刻本《丹珠尔》中的《入菩萨行论》印本{1},接近于15世纪敖伦素木残文书{2}。敖伦素木残文书中的《入菩萨行论》为日本学者江上波夫考察敖伦素木古城时所得,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鲍培(N.Poppe)认为其年代不早于14世纪中叶[5]。
另外,根据《明史》记载,洪武十三年 (1380),五月濮英军队“进至赤斤站,获豳王亦怜真及其部曲千四百余人,金印一”[6]。洪武二十四年(1391)“斩豳王别儿怯帖木儿、国公省阿桑尔只等一千四百人,获王子别列怯部属千七百三十人,金银印各一,马六百三十匹”[6]8567。可知自1380年以后出镇掌管河西地方的蒙古豳王家族在敦煌的统治基本结束,通过莫高窟、榆林窟保留的游人题记来看,莫高窟北区大概也随着元代在敦煌统治的结束而逐渐失于管理,因此可推测B121窟瘗埋的时间最迟也在1380年明朝军队攻入以前。
结合以上随葬出土佛经的使用时代,初步可以确定莫高窟北区B121:40《入菩萨行论》残片的年代约在14世纪中叶至15世纪之间。该残片作为B121窟随葬遗物,应该为窟主生前供养诵持的文本。大体可以确认,B121窟的瘗埋时间最早也在1305年以后,更进一步推断可能在15世纪前14世纪中叶左右,此时正处于蒙古豳王家族统治敦煌时期。再结合窟主女性测定年龄在20—22岁之间,大致可以确定该女性生活的时代约在1330—1380年间。该时间段对应速来蛮受封西宁王位(1330)、养阿沙太子继承西宁王位(1348)、元朝至正三十年游人题记(1370)这几个有明确史料记载的时间段内。加之这一时期出镇瓜沙的速来蛮家族确实在敦煌莫高窟有佛事活动,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测莫高窟北区B121窟埋葬的这位女性应该就是豳王速来蛮家族统治敦煌时期的一位信仰佛教的青年女性,死后瘗埋于B121窟。
二 出土红色莲鱼龙纹绫袍与死者身份判断
B121窟也出土了各类织物约十余件。这些织物从材料上看,有丝、棉、金线,品种上有红色莲鱼龙纹绫、锁甲纹缎、红地花间翔凤织金锦(图4)、红地动物纹金纱(图5)、深蓝地柿蒂窠花卉纹刺绣等(图6);从款式上看,则有红色莲鱼龙纹绫袍和柿蒂窠花卉纹刺绣拼布等[2]8-9,仅从上述残存织物品类来看窟中埋葬的这位豳王家族青年女性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生前死后穿着华丽的丝绸服饰。
2013年中国丝绸博物馆重点对莫高窟北区出土的B121:5、B121:6、B121:8丝织品残件进行修复与复原。复原后的绫袍为红色莲鱼龙纹绫袍(图7),袍上的图案纹样为莲花、金鱼和四爪奔龙,其中每组单元内的红莲由一朵绽放的莲花和一片侧面翻卷的莲叶以及四条摇曳的水草组成,莲花周围有三条游动的鱼和两条方向相反奔走的龙(图8)。
这种由莲花池塘小景组成的纹样称为“满池娇”,是一种具有时代特色的装饰纹样,大致流行于宋元时期。扬之水、尚刚等先生均对此纹样有过探讨。扬之水先生认为满池娇的纹样可以追溯到辽代四时捺钵制度中的“春山”“秋水”题材{1}。尚刚先生认为元青花中的满池娇纹样源于皇家的御用纹样[7]。陈轩结合唐宋元花卉装饰的风格与演变研究其发展脉络[8]。总的来看,满池娇纹样起源于宋代绘画中的池塘题材,在游牧民族发展的过程中结合辽代的“春水”纹样综合表现为元代所特有的装饰纹样,其中莲花莲叶组合水禽鱼虫是此类题材的必要元素。带有龙凤纹样的满池娇在元代的民间织物和服饰上并不多见,这可能与《元典章》的明确规定有关,平民百姓禁用此纹饰{1}。尤其“天历间(1328—1330),御衣多为池塘小景,名曰:‘满池娇”{2},说明“满池嬌”纹样是元代贵族阶层的专用纹饰。这一点在元代画家柯九思的《宫词十五首》有描述:
观莲太液泛兰桡,翡翠鸳鸯戏碧苕。
说与小娃牢记取,御衫绣作满池娇。[9]
这里的“御衫”应是皇家贵族的服饰,“说与小娃牢记取”表明满池娇作为服饰纹样非御衫不可僭越。以上也从服饰制度的角度向我们暗示莫高窟北区B121窟这位能够使用龙纹“满池娇”特殊纹样的青年女性身份的高贵,可能和皇家贵族有关,另外同在B121窟出土的红地花间翔凤织金锦中所用的凤纹,进一步佐证该女性的蒙古贵族身份属性。
从莫高窟出土的这件红色莲鱼龙纹绫袍纹样来看,主要是池塘莲花和鱼、龙的组合,而且呈组合形式重复出现,大面积铺满整个织面,显然是有范本所参照进行织染绘制的。相对于早期标准的“莲花池塘小景”式的满池娇来说,B121窟绫袍上的奔龙已经有别于传统绘制的水禽动物,水禽演变为龙纹,保留的仅仅是池塘莲花和鱼纹,鱼戏莲花是长久以来吉祥图案的典型,再组合两条奔龙,除了表明B121窟窟主的皇家贵族身份外,还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借用满池娇的纹样题材来表达祥禽瑞兽、吉祥纹饰的内涵。
另外从莫高窟北区B121窟出土的其他织物残件来看,大部分残片与红色莲鱼龙纹绫袍能够缝合,经过织物纤维鉴别,其余部分的棉织物残片属于同一袍子的衬里,复原后的绫袍形制为上下两截、腰部打褶,窄袖长袍[10]。这种窄袖、腰间打褶的袍服同样在元代贵族女性中使用,属于元代贵族女性礼袍。如元末熊梦祥《析津志辑佚》中记载:
袍多是用大红织金缠身云龙,袍间有珠翠云龙者,有浑然纳失失者,有金翠描绣者。有想其于春夏秋冬绣轻重,单夹不等,其制极宽阔,袖口窄以紫织金爪,袖口才五寸许, 窄即大,其袖两腋折下,有紫罗带拴合于背,腰上有紫纵系,但行时有女提袍,此袍谓之礼袍。[11]
需要注意的是,复原后的这件绫袍是瘗窟窟主死后所着,与洞窟内的供养人服饰有所区别,这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礼仪性。中国丝绸博物馆复原后的绫袍和文献所述的元代“礼袍”可以说是完全相符的,说明这里的绫袍应该是礼袍,不能因为其与元代壁画所常见的罟罟冠、大袖袍不相符而否认它在元代贵族女性服饰中的使用。针对复原报告中对于绫袍究竟是窄袖还是宽袖的疑惑可以做出解释,红色莲鱼龙纹绫袍窄袖是合理的,绫袍是元代贵族女性所着礼袍,这也是当时元代贵族女性礼袍的实物遗存,具有重要的身份佐证信息,结合绫袍特殊的纹样属性进一步可认为B121窟死者为元代蒙古豳王家族的贵族女性。
三 B121窟与元代沙州随葬佛经现象
从莫高窟北区B121窟窟主身份考辨结果可知埋葬的这位女性为速来蛮豳王家族的一位信仰佛教的青年女性。关于豳王家族的奉佛事迹,学界已有很多研究,能够反映速来蛮家族统治时期佛教信仰情况的,大概有以下事件:第一,至正八年(1348),西宁王速来蛮携王妃、太子、卜鲁合真、陈妙因、僧守朗等沙州路河渠司90余人建《莫高窟六字真言碣》[12];第二,至正十年(1350)六月初四日,西宁王府阿速歹王子命回鹘法师萨里都统,在沙州缮写印度密教大师纳若巴(Naropa,1016—1100)所传佛经《吉祥胜乐轮》[13];第三,至正十一年(1351),速来蛮、养阿沙太子等重修莫高窟皇庆寺,立《重修皇庆寺记》碑,涉及僧俗各界[12]112-116;第四,至正十三年(1353),瓜州榆林窟因豳王家族某太子到访而重修榆林窟千佛寺{1}。
在以上几次佛事活动中,速来蛮家族对于敦煌佛教的尊崇程度明显超过前述历任豳王,其中仅速来蛮在莫高窟直接参与的佛事活动就有两次,从《莫高窟六字真言碣》《重修皇庆寺记》碑刻记载中可以得到反映。当然他在沙州的佛事活动不乏夸大之辞,如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D154V 回鹘文《西宁王速来蛮王赞》称:“此王般如此特殊神圣之人绝未有过。”[14]《重修皇庆寺记》碑中也称颂他“王之好善,优于前古,口碑载道。”[12]113回鹘文《西宁王速来蛮王赞》《重修皇庆寺记》经常被作为豳王家族在敦煌元代佛事兴盛的例证之一,究竟是真实记载还是溢美之词,有待進一步辨析。
B121窟内出土了部分西夏文、蒙文、回鹘文、汉文佛经以及佛画,这是窟主佛教信仰的重要遗存见证。经过清理,窟内主要保存有西夏文刻本《金刚经》佛经残片、回鹘文文书、活字版《诸密咒要语》、龙王画像、未能辨识名称的某西夏文密教修法、梵夹装的回鹘文佛经及蒙文《入菩萨行论》,同时随葬出土的还有藏传佛教使用的人头骨法器以及墓葬作长明灯所用的陶灯。这些随葬遗物大多伴随死者生前、死后,既有汉传佛教文本又有藏传佛教佛经、法器,说明有元一代敦煌地区蒙古豳王家族佛教信仰是杂糅的。下面结合B121窟出土的图像及佛经文本对元代沙州瘗窟随葬佛经现象进行讨论。
第一,西夏文《金刚经》残页3件(B121:35)(图9)。莫高窟北区B121窟出土的汉传佛教文本主要有西夏文佛经《金刚经》残页,内容为“净口业真言”和“奉请八金刚文”部分,属于“诵经前仪”。对于佛经卷首的启请文、真言等,BD.6358《金刚经》有题记:“诵此咒一遍,胜读本经功德一万九千遍。”{2}这说明在密教影响下该经卷首真言具有强大的诵持功能,信徒认为念诵此类真言密咒将会获得比念诵经文更大的功德。这些“净口业真言”和“奉请八金刚文”往往用于法会的启请仪式,诸陀罗尼、真言于《金刚经》文本前念诵,具有祈愿、降服、驱魔、除害的功能。西夏时期,该经所具有的往生极乐观念也使其在境内非常盛行,如任德敬生病临终时曾镂板印施此经,发愿“天年未尽,速愈沉疴,运数难逃,早生净土”[15],说明在密教流传以及传统诵经仪轨的影响下《金刚经》已被视为祛病消灾的经典,这与莫高窟北区瘗窟所表达的死者命终往生净土的丧葬观念是一致的。
第二,活字版西夏文《诸密咒要语》残片(B121:18-1至B121:18-16)(图10),系蝴蝶装,有的页面基本完整,有的上下残缺,根据史金波先生翻译可知该文本为包含了多种经咒要语的佛经密咒,其中B121:18-3经题《近诵为顺总数要语》,B121:18-15含佛经序言或发愿文的开端,残留文字“夫诸密咒……”[1]370-371,经文内容多密教修行仪轨之类。西夏藏传佛教的传播大约到中期以后,此时噶举派、萨迦派正处于上升时期,都和西夏建立了广泛的联系,这些宗派僧人曾相继应邀进入西夏,对西夏藏传佛教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藏传佛教在西夏境内的传播,各种密教修行仪轨也在境内流传,如西夏时期的经咒要语主要包括“大包楼阁随心咒、阿弥陀佛心咒、智炬如来心破地狱咒、文殊菩萨五字心咒、毗卢遮那佛大灌顶光咒、七俱胝佛母心大准提咒、六字大明咒、金刚萨埵百字咒、十二因缘咒”等[16],有一字咒、三字咒、五字咒、六字咒等多种梵字咒法,B121:18-5西夏文残片提及“五十遍为三字咒五十……”说明死者生前所诵持仪轨包括三字“唵、阿、哞”咒组陀罗尼,三字咒在阿底峡传入的白色乘青龙詹巴拉造像中也有铸写{1},这类造像多作随身携带的护身符使用,以“三字咒”代表佛陀“身、语、意”强调佛像的加持和保护作用。另外黑水城出土的编号TK321(41-37)密教仪轨中记载:“于净器内盛三白三甜食,置在面前念‘三字咒三遍,摄授成所好甘露。”[17]该咒在元代瘗窟中使用,同样应具有息灾、增寿、祈愿、往生的功能,这应与西夏人在统治敦煌时期极力倡导有关。
第三,编号B121:30-2与B121:30-3分属两页西夏文残片(图11),正反共计四面,均为墨写的西夏文佛经,有的中间文字加注小字,有的句下朱笔圈画。对此文本史金波先生做了部分翻译[1]371-372,似为七言文,具体经文名称不可判定,推测应该是某部佛经的偈颂部分,中间小注有的是书写错误涂抹后所替正字,有的为偈颂所作的注释,如B121:30-2残片中间一行右起第六、七列中间小字为“筟聁蝝笭谍篔”,汉译“具识入终之礼”。“具识”是藏传佛教中讲究的顿悟和渐修,推测与西夏人辑篡的某部修法有关。文中的西夏文有明显的译自藏文的痕迹,如“箁谴”汉译为“数趣”,指不间断受生死轮回者。另外文中朱笔圈画,小注“入终之礼”可能与死者临终入葬之礼相关,种种迹象表明这件西夏文本与生死轮回、净土往生存在密切联系。B121窟出土的这批佛经实则表明注重实践的西夏人对藏传佛教经典的选择态度,摒弃深奥义理,选取各经中便于念诵且具有实效的经咒要语,重新集成新的密咒文本,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西夏藏传佛教信仰在元代丧葬习俗方面的延续。
第四,龙王画像(B121:30-1),正面描绘龙王画像,上半部人首人身,下半部蛇身,盘坐于覆莲座上,双手拱于胸前,头戴八蛇冠,身着蛇形绿色飘带,璎珞钏环皆为黄色,红色背屏,墨绿色背景(图12)。画像背面有墨绘图形,为龙王画像装裱所用的衬纸。画像中的龙王是典型的人与动物结合形龙王,盘坐于覆莲座上,与莫高窟常见的人首蛇身缠于须弥山的造型不同,接近藏经洞所出的密教龙王形象。佛教经典中龙王往往作为“天龙八部”护法神。藏经洞出土的发愿文、祈请文中也多以龙王祈雨祈福,如P.3149《诸杂斋文》、P.2850《四门散花燃灯文》、S.5957《结坛祈祷发愿文》等都包含龙王祈雨的内容{1}。B121窟出土的龙王画像人首蛇身,图像色彩对比浓烈,具有密教龙王和印度蛇王特征(图13)。根据敦煌文献中的密教龙王研究可知此类龙王是用于“祛病祛毒者”“灭鬼驱邪者”,在墓葬中的功能应该是类似药王、千手观音之类的药神[18],具有消灾祛病、祈福延寿的功能。
总体来看,B121窟出土的文献资料既包括西夏文佛经,又包括回鹘文晚期文书、佛经,以及蒙文佛经《入菩萨行论》,多民族文字的文献在该窟集中出现说明这一时期河西地区的佛教信仰是多元和杂糅的。元代的河西统治者既接受中原汉地的龙王信仰,也接受来自西藏和印度的密教思想。密教以西夏藏传密教为主,并把各宗各派融合在一起,这是多民族多元文化在敦煌地区交流共生的体现。佛教因素出现在墓葬中,在辽金西夏元时期是非常普遍的。如宣化辽墓出土的陀罗尼经棺,上面就用汉文和梵文书写各种陀罗尼经咒,棺盖上有“陀罗尼棺,以其影覆之功,既济魂归之质,不闻地狱,永受天身,谅尘墨之良,因与乾坤而等。固谨记”字样[19]。武威西夏墓中也有写满陀罗尼经咒的木缘塔和棺前书写六字大明咒的木棺出土。这些墓葬中出土的陀罗尼、密咒要语、佛经文本都体现出的共同作用就是破地狱、度亡的功能,对于信徒而言,除祛病消灾、延年增寿、净除一切恶业等现世利益外,如何避免死后堕入地狱是他们关注的重点,而这些三字咒、六字咒所传达的忏悔灭罪、破地狱思想,恰好满足当时人们所希望的消除罪业、免堕地狱、往生净土的心愿。元代豳王家族女性瘗窟出土此类佛经,表明元代中后期河西佛教信仰者对真言密咒的重视,以及诵持佛经的无量功德和往生净土的生死观念。
四 B121窟死者身份與“元代公主”关系再议
元代莫高窟洞窟瘗埋问题,长期有“元代公主”的传说。杨富学先生讨论第464窟时代问题时认为第464窟是元代埋葬蒙古豳王家族“曾出家为尼的某公主”的瘗窟,认为第464窟的时代为元代[20]。对此问题,我们通过窟内历史、考古、图像分析后认为该窟营建前后经历了西夏的两次重修,元代中晚期成为藏经和瘗埋之所,从而使得第464窟兼具礼佛窟、藏经窟、瘗窟的洞窟属性[21]。对于“元代公主”的瘗窟,学界在第464窟营建史的相关成果中已有所讨论,否认了一直认为该公主出自第464窟的传说[21]47。现通过对莫高窟北区B121窟瘗窟的使用背景、年代、死者身份、随葬遗物的考古观察来看,“元代公主”的认识并非空穴来风,但埋葬的地点并不在第464窟,有可能在B121窟。
首先,B121窟内不仅发现元代女性的尸骨,而且骨龄测定为20—22岁,还有大量汉文、西夏文、回鹘文文书及佛经残件,年代判定约在14世纪中后期,处于速来蛮豳王家族统治瓜沙时期。另外从中国丝绸博物馆复原后的一件红色莲鱼龙纹绫袍来看,此女性属于元代蒙古豳王高级别家族成员,所着“满池娇”纹饰的绫袍实为元代皇室贵族所规定使用的“礼袍”,故其身份推测其可能为豳王家族与西宁王速来蛮关系密切的某位女性家庭成员。从莫高窟《六字真言碣》所记看,速来蛮家族成员有王子、王妃、公主、驸马等,称号几乎等同于中原地区皇室称号,与速来蛮关系密切的女性成员或为王妃或为公主,考虑到该窟与速来蛮家族关系的密切性和佛教信仰的背景以及年龄诸因素,推测此女性为西宁王速来蛮之女的可能性比较大。
其次,北大藏和东京藏的回鹘文文献中有两首赞美西宁王速来蛮和“玉女公主”的回鹘文诗歌,诗歌中的玉女公主信奉善逝三宝,信仰龙王{1},而莫高窟B121窟也出土随葬人首蛇身,头戴八蛇冠的龙王画像,似为窟主生前信仰之物,死后一同入葬。同样,对于当时所处的外部环境在玉女公主的诗歌也有描述:
当世尊的佛法遭到修改的时候,当arya-sangha圣僧的民族走向没落的时候,连遇灾才穿的破鞋和破衣也会成为所愿,一切众生将会立即变得忧伤。[14]293
“佛法遭到修改”“民族走向没落”可能是元代中后期藏传佛教遭到破坏、内地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的真实反映,包括敦煌等河西地区也随着明朝濮英军队日益向赤斤等地的逼近而逐渐走向衰落。文中的“玉女公主”推测可能与B121窟埋葬的这位供奉龙王画像的青年女性为同一人,即为速来蛮豳王家族成员之一,亡故后瘗埋于莫高窟B121窟。而且该窟内并没有男性成员一同埋葬,也没有类似莫高窟第332窟、文殊山前山千佛洞同绘夫妇供养人像,可能与其出家为尼、热衷佛教的经历有关。
以上仅是推测,关于“元代公主”“玉女公主”的问题还有待更多考古资料的进一步推进和证实。
莫高窟B121窟的考古再解读,可以说为有可能葬于莫高窟北区洞窟中的“元代公主”传说提供了新的线索,B121窟作为瘗埋豳王家族的女性墓窟,尸骨基本保存完好,服饰也具备皇家贵族属性,随葬遗物充分显示了浓厚的佛教信仰背景,其时代也大约生活在速来蛮家族统治敦煌时期,种种迹象表明B121窟有可能为元代公主的瘗窟。
除B121窟作为埋葬元代豳王家族贵族女性的瘗窟,之前我们对第462窟的探讨表明该窟也极有可能是豳王家族的瘗窟,死者同样为高级别女性(图14){1}。另第464窟在元代也曾一度作为一处埋人的瘗窟有过改造和使用[21]46-48,还有B142窟内有双塔,具备塔葬属性。我们看到,到了元代北区出现至少三处埋人的瘗窟,而且有两处还可以明确死者身份为豳王家族的贵族女性,这一点似乎暗示我们豳王家族在选择丧葬的方式方法时,之前被僧人们作为生活和禅修中心的北区石窟群[22],到了元代被元人特别是豳王家族用于葬所,这大概也是北区石窟在元代的一个重要功能。据考古报告,莫高窟北区用于瘗埋僧人骨灰、遗体和遗骨的瘗窟有25个,其中15个是专门为瘗埋死者而开凿的瘗窟,另有7个窟是改造原来的禅窟而成[1]343-346。莫高窟的瘗埋活动一直持续到元代,这位速来蛮豳王家族的青年女性在死后选择B121窟作为瘗埋活动的场所,并把大量的佛经、法器等作为陪葬品一同封入窟内也同样体现了佛教信仰下“神人共处”的丧葬理念,也是死者敬畏神佛,试图常伴其旁、永甘依附的忠实表达{2}。这种瘗埋僧人或佛教徒的方式,与第462、464窟的瘗埋活动有一定历史渊源,是元代蒙古豳王家族在敦煌瘗埋活动的继续。
五 结 语
至此,莫高窟北区B121窟是除有纪年题记的第462窟之外的另一个可以利用“三重证据”予以明确的豳王家族女性瘗窟。结合窟内随葬遗物判定该洞窟的使用年代约在14世纪中后期,即豳王速来蛮家族统治敦煌时期,死者身份为豳王家族的一位信仰佛教的青年女性。通过窟内随葬出土的西夏文、汉文、回鹘文、蒙文佛经经咒以及人头骨法器,可以看出元代豳王家族统治敦煌时期的佛教信仰背景,其在丧葬习俗上采用以窟为墓的埋葬方式,可以认为是继北区第462、464窟之后元代蒙古豳王家族在此瘗埋活动的继续。该窟同时也为莫高窟“元代公主”的看法提供了新的线索,推测B121窟有元代公主的瘗窟属性。
如果说第462窟体现的是豳王家族早期在莫高窟北区的瘗埋活动,那么B121窟则是豳王家族中后期速来蛮、牙罕沙(养阿沙太子)时期在莫高窟北区的瘗埋活动,这其中不仅仅体现的是豳王家族女性与佛教的个人行为,也为我们建构起蒙古豳王家族从早期到后期在敦煌利用佛教石窟为自己服务的史实。自莫高窟北区B121窟使用完毕后,随着明朝军队的日益逼近,元代豳王家族在敦煌地区的统治也基本接近尾声,因此B121窟也为我们研究元代蒙古豳王家族中后期在敦煌的佛事活动和丧葬习俗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资料,期待学界对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的进一步研究。
插图若无特殊说明,版权均归敦煌研究院所有,在此衷心致谢。
{1} 关于莫高窟北区出土文献的相关研究,可参见史金波《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西夏文文献初探》(《敦煌研究》2000年第3期第1—16页)、敖特根《莫高窟北区出土回鹘蒙古文〈入菩萨行论〉印本残叶》(《兰州学刊》2009年第12期第9—15页)。另见敖特根《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蒙古文文献研究》,民族出版社,2010年,第220页。
{2} 宋濂等《元史·诸王表》(中华书局,1976年,第2735页)记载:“元兴,宗室驸马,通称诸王……然初制简朴,位号无称,惟视印章,以为轻重。厥后遂有国邑之名,而赐印之等犹前日也。”
{3} 关于元代豳王家族在瓜沙地区的活动情况,相关研究成果可参见杉山正明《モンゴル帝國と大元ウルヌ》(京都大学学术出版社,2004年,第323页),松田孝一《元朝的分封制度——关于邠王(豳王)出伯与邠州的关系》(载聂鸿音、孙伯君《中国多文字时代的历史文献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303—308页),胡小鹏《元代西北历史与民族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年,第32—50页),杨富学、张海娟《从蒙古豳王到裕固族大头目》(甘肃文化出版社,2017年,第89—94页),张海娟、杨富学《蒙古豳王家族与河西西域佛教》(《敦煌学辑刊》2011年第4期,第89—97页)等。
{1} F.W.柯立夫《搠思吉斡节儿著1312年入菩萨行论疏》,载《哈佛大学亚细亚研究学报》,第17卷,1954年,第1—129页。1311年元代高僧搠思吉斡節儿奉仁宗之命用蒙文撰写《入菩萨行论疏》,并于1312年在元大都白塔寺刻印1000本,现存《入菩萨行论疏》藏德国柏林科学院。根据新德里手抄本L6《入菩萨行论》跋文考证,搠思吉斡节儿于1305年将《入菩萨行论》翻译为蒙文。根据拉希曼·茨默研究可知德国柏林科学院藏吐鲁番出土回鹘文《入菩萨行论》,见拉希曼·茨默《入菩提行论疏突厥语译本》,载《古代东方研究》,1985年第2期第309—318页。
{1} 1305年《入菩萨行论》经高僧思吉斡节儿翻译为蒙文后,1748年乌拉特固师毕力衮达赖校勘后编入蒙古文木刻本《丹珠尔》第114卷,罗意果《蒙古文〈丹珠尔〉中的入菩萨行论》,载《亚细亚研究丛书》第129卷,威斯巴登,1996年。
{2} (印度)罗克什·钱德拉《入菩萨行论》,《百藏丛书》,第230卷,新德里,1976年。关于《入菩萨行论》的印本情况参见“前言”部分。
{1} 扬之水《“满池娇”源流——从鸽子洞元代窖藏的两件刺绣说起》(载孙慧君主编《隆化鸽子洞元代窖藏》,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74页)、文章另见于扬之水《古诗文名物新证合编》(天津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124—139页)认为“满池娇”纹饰应源于辽代“春水”纹的发展。
{1} 陈高华点校《元典章》卷29《礼部二·服色》(天津古籍出版社、中华书局,2011年,第1028页)记载:“延祐元年,钦奉圣旨……命中书省立定服色等第于后。一蒙古人不在禁限。及见当怯薛诸色人等,亦不在禁限,惟不许服龙凤文。”
{2} 元人柯九思《宫词十五首》原注按语:“天历间,御衣多为池塘小景,名曰‘满池娇。”
{1} 张伯元《安西榆林窟》,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207页。参见榆林窟第15窟前室东壁门上北侧墨书题记《大元重修三危山榆林窟千佛寺记》,第15窟有墨书题记:“大元守镇造……太子业□□里至三危,睹思胜境,现□□观见光相□室中,闻香气于岩窟,由是重建精蓝,复兴佛刹,广□缁流于四姓,多兴禅定于岩间也。”
{2} 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90年,第484页;另见方广锠《敦煌文献中的〈金刚经〉及其注疏》,《世界宗教研究》1995年第1期第8页,后收入氏著《敦煌学佛教学论丛》(上),中国佛教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第371页。
{1} 即藏传佛教中的白财神,一面,怒相,一面三眼,右手持矛,左手持棒,乘青绿色的龙。见李翎《鬼子母研究》,上海书店,2018年,第459页。
{1} 有关龙王信仰的相关研究可参见张小刚《古代敦煌龙王信仰及其图像研究》(《敦煌研究》2021年第3期第57—68页)、党燕妮《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的海龙王信仰》(载《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三编》,甘肃文化出版社,2005年,第271—291页)等。
{1} 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Abdurishid Yakup)《古代维吾尔语赞美诗和描写性韵文的语文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92页。该文献现藏于日本东京大学附属图书馆,回鹘文草书写成,汉译文:“曾是诸多无数珠宝之储藏,曾经留在‘无热恼池河流,由有名的龙王九头龙所生,你是我满足一切愿望的公主。比起以善逝佛宝为首的三宝,因你有应有的坚定、洁净的信念,因你有种种珠宝和装饰才有的美姿。”
{1} 沙武田、李国、柴勃隆《敦煌石窟元代蒙古豳王家族塔葬瘗窟——莫高窟北区第462窟洞窟属性的考古学观察》(待刊)。
{2} 同①。
參考文献:
[1]彭金章,王建军. 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2卷[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136.
[2]赵丰,王淑娟,王乐. 莫高窟北区B121窟出土元代丝绸研究[J]. 敦煌研究,2021(4):5.
[3]张铁山. 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回鹘文文献译释研究(一)[M]//彭金章,王建军. 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2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361.
[4]敖特根. 莫高窟北区出土回鹘蒙古文《入菩萨行论》印本残叶[J]. 兰州学刊,2009(12):4,13.
[5]N·鲍培. 敖伦素木出土一件《入菩萨行论》残片[J]. 哈佛大学亚细亚研究学报,1954(第17卷):418.
[6]张廷玉. 明史:卷330:赤斤蒙古卫[M]. 北京:中华书局,1984:8556.
[7]尚刚. 鸳鸯鸂鶒满池娇:由元青花莲池图案引出的话题[J]. 装饰,1995(2):40.
[8]陈轩. 唐宋元花卉装饰的风格与演变研究[J]. 湖北美术学院学报,2019(2):53-54.
[9]章荑荪. 辽金元诗选[M]. 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186.
[10]王淑娟. 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元代红色莲鱼龙纹绫袍的修复与研究[M]//赵丰,罗华庆. 千缕百衲:敦煌莫高窟出土纺织品的保护与研究. 杭州:中国丝绸博物馆,2013:58.
[11]熊梦祥. 析津志辑佚[M]. 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206.
[12]李永宁. 敦煌莫高窟碑文录及有关问题(二)[J]. 敦煌研究. 1983(2):110.
[13]杨富学. 回鹘之佛教[M].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123-124.
[14]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 古代维吾尔赞美诗和描写性韵文的语文学研究[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263.
[15]聂鸿音. 西夏佛经序跋译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168.
[16]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所,中国社科院民族所,上海古籍出版社. 俄藏黑水城文献:第4册[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359-363.
[17]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所,中国社科院民族所,上海古籍出版社. 俄藏黑水城文献:第5册[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32.
[18]王航. 敦煌文献中密教龙王信仰研究[J]. 敦煌研究,2019(2):116-117.
[19]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宣化辽墓:1974—1993考古发掘报告[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246.
[20]杨富学. 敦煌莫高窟第464窟的断代及其与回鹘之关系[J]. 敦煌研究,2012(6):12-16.
[21]沙武田. 礼佛窟·藏经窟·瘗窟:敦煌莫高窟第464窟营建史考论(下)[J]. 故宫博物院院刊,2021(8):44-45.
[22]沙武田. 莫高窟北区石窟与僧人禅修[C]//郑炳林,樊锦诗,杨富学. 敦煌佛教与禅宗学术讨论会文集. 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438-448.
收稿日期:2022-02-2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敦煌西夏石窟研究”(16ZDA116);陕西师范大学“念海史学”研究生探索项目“西夏佛经版画图像研究”(NH-A-02)
作者简介:吴雪梅(1993- ),女,甘肃省民勤县人,陕西师范大学在读博士,主要从事佛教石窟考古、敦煌学研究。
沙武田(1973- ),男,甘肃省会宁县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佛教石窟考古、敦煌学、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