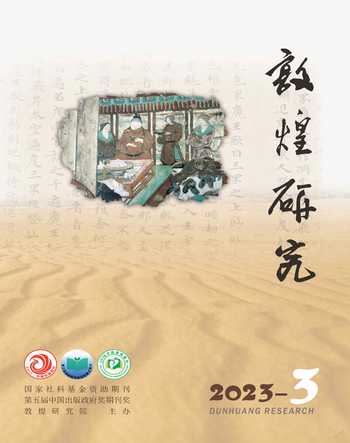论敦煌文化中人生哲学思想的融通
内容摘要:敦煌文化中的人生哲学思想是敦煌哲学的核心组成部分,是中古时期广义的敦煌人对宇宙人生问题的关照。中国传统的儒家哲学思想与外来佛教哲学思想的相互融汇变通构成了敦煌人生哲学的主要思想内涵,同时交织着道教的哲学思想,三者融汇互通在敦煌文献与石窟艺术的浩瀚海洋中。
关键词:敦煌文化;人生哲学;儒释道;融通
中图分类号:K87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23)03-0118-07
On the Integration of Life Philosophy in Dunhuang Culture
LI Runqiang
(Gansu Provincial Radio and Television Bureau, Lanzhou 730000, Gansu)
Abstract:The philosophy of life in Dunhuang culture is a core component of Dunhuang philosophy, and is most important for condensing and expressing the attention that local philosophers and regular citizens paid to human life in the cosmos during medieval times. The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onfucianism and foreign Buddhist philosophy gave birth to the central ideological tenets of Dunhuang life philosophy, which melded well with local Daoism. These three types of philosophy were incorporated into the vast body of documents and cave temple art at Dunhuang, much of which can still be seen today.
Keywords:Dunhuang culture; life philosophy of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Daoism; integration
(Translated by WANG Pingxian)
中古时期,特别是魏晋隋唐时期,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主要以儒家思想为主)受到外来佛教哲学思想的影响,从而经历了不同思想文化之间的碰撞、冲突、融合、变通的历史过程。在这一划时代的历史进程中,敦煌首当其冲。敦煌人通过手手相传的文书范本,通过直观可见的石窟艺术,借助神圣庄严的宗教仪轨,表达他们对于宇宙人生等问题的思考[1]。
一 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是一种“宇宙伦理模式”,它是将“人道”作为宇宙的有机构成而达到“天道”合一[2]。在中国哲学史上,战国时期的孟子最先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思想,他主张从人性中寻找道德的本原,即个体“内在道德”。《孟子·尽心上》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3]孟子认为,为人者,尽心知性,只要认识了自己的本性,就能把握万物的本质。天具有完善的本性,因而人同样有之,只要人实现了人性之善,就能完整地体现天的本性,也只有人才具备觉悟和主动扩充这种本性的能力。
在现存敦煌文献和石窟壁画中,天道与人道的关系首先体现在神人关系中的佛佑人安、以佛挺人。敦煌石窟中的彩塑、壁画在佛人关系上表现出鲜明的地域性,如莫高窟第156窟内塑造的佛、菩萨、天王等是营建洞窟的窟主和民众价值观的体现,而窟内单幅供养人画像绘制的比例却大于真人及窟中的佛菩萨像等,既佛佑人安,又在天人关系上以佛挺人。其次,体现在自然与人类关系中的祛病禳灾、风调雨顺。如敦煌文献S.343《愿文范本》中祈愿“风调雨顺,岁稔时丰;疫疠消除,吉祥云集”[4];P.3765《转经文》祈愿“风调雨顺,岁熟时康;道奏清平,歌谣满路”[4]482-483;北图8672《愿斋文》“惟愿百神助卫,无善福而不臻;千圣加威,有灭殃而并遣”[4]275;S.2144《结坛散食回向发愿文》祈愿“敦煌一境及我太传一族”“永离水灾之难、永离火灾之难、永离毒蛇之难、永离蛊毒之难……所有一切不祥之难”[4]563。等等。这些愿文充分表达了当地民众祈愿自然护佑、天人和谐的美好愿望。再次,体现在理想与现实关系中的天人相通、人间净土。如敦煌文献S.5957《启请文》“归依启请十方诸佛,三世如来;湛若虚空,真如法体;莲花藏界,百亿如来;大贤劫中,一千化佛;誓居三界,功德山王;同侣白衣,维摩罗诘;菩提树下,降魔如来;兜率宫中,化天大觉;无量劫前,大通智胜,十六王子;恒沙劫后,释迦牟尼,五百徒众;东方世界,阿閦毗佛;南方世界,日月灯佛;西方世界,无量寿佛;北方世界,最胜音佛”等来降道场[4]416;北图7677《结坛散食回向发愿文》“奉请清净法身毗卢遮那佛、奉请圆满报身卢舍那佛、奉请千亿百亿化身同名释迦牟尼佛、奉请东方世界十二上愿乐师琉璃光佛、奉请南方世界日月灯王佛、奉请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奉请北方世界最胜音王佛,奉请十方三界一切恒沙诸佛等来降道场……拥护我一方净土、人民及我施主阖宅姻罗、宗族,并受无疆之福;九横不侵于宝体,十善常增于闺阁”[4]567。等等。同时,莫高窟壁画中也绘制数量众多的阿弥陀经变以示西方净土,绘制药师经变以示东方药师净土,绘制弥勒经变以示弥勒净土,这些对佛国世界、净土世界的描绘是敦煌民众追求佛国净土的心理诉求,同时反映了他们向往和追求的不仅仅是佛国净土世界,更期盼的是现世人間的安定祥和与丰衣足食。最后,体现在君臣、父子关系上的精忠报国、尽孝报恩。如敦煌文献S.5546《咒愿一本》和P.2976《咒愿新女婿》中对新婚夫妇要求“孝养父母,宜姑宜嫜”“忠孝两全,文武双美”[4]397,398。甲卷S.5957和乙卷P.3765《亡考文》中提到“亡考乃堂堂美德,六郡英酋”“卫敕命则不顾其躯,事家眷乃存忠尽孝”[4]731。北图8363《亡考文》中“亡考乃蕴策怀谋,忠诚尽孝;信义周于乡党,礼乐贯于闾阎”[4]743。等等。同时,莫高窟第156窟的《张议潮出行图》及莫高窟数十幅“报恩经变”和“报父母恩重”的绢画等,都集中体现了移孝作忠、感念父母恩的伦理思想。
敦煌人生哲学所体现的天人合一,既继承了中国传统哲学对于天道与人道关系的基本理论,又融合了佛教关于人与佛、人与众生、人与自我的伦理本质,并将二者契理契机地融汇在敦煌文化中,集中展现了敦煌民众的人生观。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敦煌人生哲学思想的基石是天人关系、神人关系,在这种关系的揭示中既体现了中原文化的思想倾向,又融汇了佛教文化的基本精神,而二者的统一即敦煌人生哲学的特色。与此同时,在敦煌人生哲学中,人的本质已不完全是佛教人生哲学中的“一切皆空”,即对人的生存、追求和价值的整个现实世界当作虚幻的东西彻底否定。一方面,世俗人自我意识的潜滋暗长,是人的地位的提升,敦煌佛教不再一味地否定人的价值,更多的是倾向于中国传统思想中对人的定位;另一方面,在非自觉意识的排挤下,敦煌佛教的神权势力逐步退缩,相应的人的位置得到提升。同时,由于佛教对敦煌社会的影响,中国传统人生哲学中“天地万物人为贵”的思想也披上了佛教宇宙观、人生观的外衣。在敦煌人生哲学中,“众生平等”已然是人与人最本质的关系,“因果报应”“轮回转世”依然是人可以为人的必要条件;今生与来世并重,主观上仍然自信是佛祖虔诚的信徒,但客观上已经开始试图一步步摆脱旧有观念的束缚,越来越多地肯定人的存在和价值[5]。
二 生死相辅
佛教的生死观念与中国传统的儒道生死观念不同:儒家主张人的生命虽然有限,但是却可以通过道德学问的修养使精神达到永存和不朽;道家的生死观讲究的是“生死气化,顺应自然”。儒道将生死都视为一种自然现象[6],或是重生轻死,或是轻生轻死。而佛教主张,“生与死”不止在于生前,也不止在死后,而是在于生命个体的永恒归宿;它不是一味地重生轻死或是简单的轻生轻死,而是教导世人如何超越生死[7]。在佛教看来,人的生死有两种,即“分段生死”和“变异生死”。“分段生死”指身处生死大海中的凡夫在六道中的辗转轮回,生死交替;“变异生死”指超越生死的圣者[8]。也就是说,佛教的死亡观是通过对死亡的解析,实现对死亡的超越。
《弘明集》中曰:
凡有五道:一曰天,二曰人,三曰畜生,四日饿鬼,五曰地狱。全五戒则人相备,具十善则生天堂,全一戒者则亦得为人。人有高卑,或寿夭不同,皆由戒有多少。反十善者谓之十恶,十恶毕犯则入地狱,抵揬强梁不受忠谏,及毒心内盛徇私欺殆,则或堕畜生,或生蛇虺。悭贪专利常苦不足,则堕饿鬼。其罪若转少而多阴,私情不公亮,皆堕鬼神,虽受微福不免苦痛。[9]
佛教的宇宙论将世界分为佛国世界和世俗世界,世俗世界又分为欲界、色界、无色界三界。欲界是指深受各种贪欲支配和煎熬的生物所居住的地方,分为天、阿修罗、人、畜生、饿鬼、地狱等六道;色界是粗俗的欲望已经断绝,只是居住者仍有身体和形状;无色界是既无欲望又无形体的生存者居住之所。佛教对死亡的超越可分为人天乘、净土、涅槃三个层次。这三层次就信仰主体在民众中所占比重呈金字塔分布。人天乘属于轮回之死,最早在民众中盛行;净土是究竟解脱生死的涅槃和轮回之间的中转站。随着佛教中国化的完成,净土信仰后来居上。佛教一整套“破除我执”“了悟生死”的“闻”“思”“修”体系,通过“涅槃往生”“六道轮回”等观念来阐释对生死的理解,说明人死之后的安顿问题,而且用“念佛救度”“中阴得度”等极具实践性的方法来指导人们如何面对死亡,甚至超越死亡[10]。最终目标就是实现对死亡的终极超越,即涅槃。通过念死观修、临终帮助、中阴救度达到涅槃,从而实现对死亡的超越。总之,佛教死亡的超越体系既是理论的,又是实践的;既是经验的,又是超验的。它以对死亡的解析、通过种种法门实现对死亡的超越[11]。
中古时期的敦煌地区流行着相当数量的七七斋会文书,如P.3825《亡父母文》、S.6417《亡考文》、S.0343《愿文范本·亡文》、 S.0343《武言亡男女文》、S.5957+P.3765《亡考文》、S.6417《亡考文》、P.2237《亡考文》、P.2854《亡文》、P.2341《亡男文》、S.5957《亡妣文》、P.2226《亡考文》、北图8363《亡考文》等,是子女为父母或是父母为子女亡故后某七所做的斋文。再如S.2832(五)亡夫、(六)亡妻,S.5639+S.6540(五)亡夫、P.2449《萼啰鹿舍施追荐亡妻文》、P.2385(三)[妻]等是夫为亡妻或妻为亡夫所做的斋文。又如S.2832(一一)亡兄弟,S.5639+S.6540(六)贤弟、(七)贤弟、(八)贤兄,S.0343《亡兄弟文》等,是兄弟之间做“七七斋”所用的文书。这种七七斋会的丧俗活动所体现的佛教生死观,一方面是让逝者透悟生死,理解佛法,从而摆脱恐惧和怨恨,身心两安;另一方面也推动了佛教救度大众的死亡观念在民间的广泛流传。现存敦煌文献和石窟造像遗迹都表明,尤其是8至10世纪,敦煌地区的各种法会(如七七、放焰口、做道场等)、建寺、开窟、造像等功德仪式和活动都蕴涵着佛教的生死观念,并且具有非常实际的操作意义。从精神慰藉的角度来讲,这些宗教活动的广泛开展,不仅减轻了逝者的临终痛苦,而且抚慰了亲属的哀伤情怀。在起到临终关怀和哀伤抚慰作用的同时,还彰显出敦煌佛教精细和丰富的“终极关怀”[12]。
敦煌地区民众通过佛教信仰的方式来表达自身的生死观,在佛教艺术的创造中体会生命的不朽,在信仰中认可壁画中净土世界的真实不虚,在神佛的空间里达到生命的永恒与不朽,借助文字和图像表达自身对宇宙人生和自身存在的理解和感悟,这些都是对幸福与至善的追求与渴望。敦煌民众在世俗与信仰的双重关注中获得心灵的安慰,这在一定程度上突出了人的本质进而实现了生命的价值与尊严。
三 儒释合璧
儒释之间的融变与合璧集中体现在对传统孝道文化的继承和融通上。敦煌文书S.3728《故圆鉴大师二十四孝押座文》即为儒释融通的典型案例,主要讲述三层意思:一是宣传“孝”是成佛积善的根本,列举出目连救母、释迦牟尼孝父、舜主“孝感动天”、王祥“卧冰求鲤”、郭巨“为母埋儿”、老莱“戏采娱亲”、孟宗“哭竹生笋”、杨香“扇枕温衾”等的孝道行为{1};二是从个人言行、家庭关系、为人处世,对父母的关爱等方面列举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应遵循的各种孝行;三是强调“孝心”与“孝行”并行,指出“孝”乃儒释两家共同的伦理准则,须行孝道,便能成佛。文中各孝子孝亲的对象大多为母亲,孝行的方式也多为自我牺牲,孝子的范围既有佛祖,又有俗弟子,上至远古皇帝,下至平民百姓,既有成人,也有儿童,反映出盡孝心、行孝行、报母恩的孝亲行为是不分时间、空间,不分人物、阶层、年龄。众生皆可尽孝心、行孝行。值得注意的是,在《故圆鉴大师二十四孝押座文》将佛经与《孝经》(孔氏谭论十八章)相提并论,体现出儒家孝道与佛教俗讲的结合。而且“二十四孝”故事中多次展现出的自我牺牲精神,更符合佛教所提倡的慈悲精神。这表明,在唐宋之际,包括云辩在内从事俗讲活动的僧人,他们接受了儒家“百行孝为先”的思想,同时也迎合统治者的统治需要和广大群众的心理需求,将佛教经典中可以用来宣扬孝道的内容同本土的历史故事结合起来,将中国人喜闻乐见的孝子故事融入俗讲中,大力宣扬孝道伦理观念。对于听众而言,则在这些孝行故事和俗讲文学中渐次接受着佛教思想的熏陶[1]56。
敦煌文书中现存的S.728、S.1386、S.3993、S.5545、S.5821、S.6177、P.2545、P.2674、P.2715、P.2721、P.3378、P.3382、P.3428、P.3698、P.4775、P.4897等数十件都是抄有《孝经》的写卷。同时还有为《孝经》注疏的作品,如P.3274《御注孝经注疏》,S.3824《御注孝经集义并注》,P.3369、P.3830《孝经白文》等。其中,玄宗《御注孝经》参照诸家注解,择善从之,全文虽仅有1700余字,但内容却包括《开宗明义章》《天子章》《诸侯章》《卿大夫章》《士章》《庶人章》《三才章》《孝治章》《圣治章》《纪孝行章》《五刑章》《广要道章》《广至德章》《广扬名章》《谏诤章》《应感章》《事君章》《丧亲章》等,共计十八章[13]。玄宗开元年间御注《孝经》意在将之作为立法制度建设的重要环节,并着重强调“孝”的教化作用,突出孝中所蕴含的“忠”之义;天宝年间再注《孝经》,更多的是着眼于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强调君主的个人品行,力图强化对孝的道德约束和后天教育,这也是儒释道并举措施中大力提倡儒家的重要体现。此外,孝子故事中的孝子形象在墓葬“孝子图像”中亦被广泛采用,如东汉晚期的山东嘉祥武梁祠石室画像、四川乐山柿子湾1号东汉崖墓、河南洛阳翟泉村北邙山出土的北魏孝昌三年宁懋石室、美国纳尔逊艺术博物馆所藏北魏孝子石棺等[14]。甘肃境内发现的数十座宋金时期的墓葬中也有砖雕或彩绘的“二十四孝”人物故事,主要集中在陇西县宋墓,兰州中山林金墓,榆中金墓,临夏金墓以及永登连城,会宁,清水县白沙电峡、贾川董湾等宋金墓葬中。其中见于陇西宋墓、清水白沙电峡金墓中的睒子鹿乳奉亲的故事,在山西省壶关南村北宋元祐二年(1087)墓和洛阳北宋崇宁五年(1106)石棺刻线中也出现过。睒子本生故事本为佛教艺术题材的作品,在新疆克孜尔千佛洞、莫高窟第428窟、麦积山第127窟等北朝或以前的石窟壁画中有较多的体现,都是对传统孝道文化的宣扬。
据统计,敦煌本《孝子传》中有十六位孝子被编入后世流传的“二十四孝”,其辑写的二十六则孝行故事与元代成书的《日记故事》系“二十四孝”的内容也多有契合[15]。敦煌本《董永变》《舜子变》《父母恩重经讲经文(二)》《目连缘起》和杨满川《咏孝经十八章》、蒙书《古贤集》等中的孝子也都不出《孝子传》的范围[16]。他们同甘肃宋金墓葬中所见的孝道人物相符,大部分依据各代史书或孝子传记载,或详或略,可与史籍互证,甚至有些故事是依据当时口头传说而成,与宋金墓葬所表现的情节一致。这说明,这些孝道人物故事在当时的内地和敦煌地区都十分流行,以至于敦煌地区的佛教徒也借此来宣扬儒家的孝悌观。这些都充分体现出当时儒释融合的历史现象[1]57。
四 释道融于儒
敦煌文献中所存道教文献有道教经典、道教斋醮文书、道家符箓文书、论道文书、有关道教活动的社会经济文书、道教文学作品等。初盛唐时期,敦煌道教因官方扶持而致兴旺;吐蕃时期,经受吐蕃政权的打击而并未消亡,道教走向民间,而道教术士创造并运用隐秘方术投身于汉族军民反对吐蕃的入侵;归义军时期,道教从吐蕃统治下解脱出来但未得到官方的大力扶持,在佛教更为繁盛的局面下,道教处于弱势,道教在自由发展中走向与民间信仰相融合的道路[17]。從敦煌遗书中有关敦煌道教典籍、宫观、道士活动的记载和介绍来看,道教在敦煌可说是颇具规模的[18]。
如敦煌文书P.3562V是敦煌地区的道士为了便于从事法事活动而逐渐抄录积累的、实用性的斋愿文汇集,也是一份道家从事各设愿、祈福禳灾的范文辑。王重民先生在《敦煌遗书总索引》中定名《道家杂文》[19],陈祚龙先生在《敦煌学识小》称为《李唐敦煌流行的祈福文范之小集》[20]。其所涉及的内容和形式基本与唐代道教文献《道教义枢》所记相同。其斋文按内容排序依次包括:1. 斋愿文,2. 邑愿文(一),3. 亡考妣文(一),4. 亡考妣文(二),5. 亡师文,6. 女师亡文,7. 僧尼亡文,8. 邑愿文(二),9. 当家平安愿文,10. 病差文,11. 征回平安愿文,12. 兄弟亡文,13. 夫妻亡文,14. 亡男女文,15. 亡考文(一),16. 回礼席文,17. 东行亡文,18. 岁初愿文,19. 亡考文(二),20. 亡孩子文,21. 入宅文,22. 造宅文,23. 斋法,24. 报愿文,共计24篇。按照文书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为亡人追福祈福,如斋愿文、亡考妣文、亡师文、女师亡文、僧尼亡文、兄弟亡文、夫妻亡文、亡男女文、亡孩子文等;第二类是为斋主及其亲属等在世之人驱病免灾,祈求幸福,如亡考文、亡考妣文、僧尼亡文、病差文;第三类是祈愿天下太平、国家安宁、众生安康,如岁初愿文、斋愿文、报愿文、造宅文等。该文书是道教的七七之斋与佛教人死后中阴身之说及建七七斋的影响有关[21]。还有因事而设的斋愿活动,说明道教对日常生活和礼俗的介入很深,影响很大。这些反映出敦煌道教所进行的法事活动均按照《灵宝经》关于法事活动的相关斋期予以安排和开展,同时还反映出这些法事活动过程中的很多仪轨以及开展这些法事活动的目的。另外,敦煌文书中的《天尊说随愿往生罪褔报对次说预修科文妙经》残卷中不仅要求必须为亡人建立七七斋、百日斋及道场的供养之外,还要求见在之人必须做种种功德,为亡人荐福,以减少亡者的罪过。只要按照道经所规定的科仪进行法事活动,他们的目的就能如愿以偿。敦煌斋愿文中的所作所为与祈求也正与此相对应[21]19。
可见,为各类亡人设斋福是道家历来行事之一。亡文与愿文都体现和包括了对整个社会和人们的所作所为及所遭遇的各种事情的良好祈愿。中国道教一贯以此来争取社会和民众。大乘佛教的入世哲学走的也正是这样一条服务于社会而又依赖社会的路。从这方面讲,佛、道两家也是为达到各自的目的所采取了相同的方法和手段[22]。唐代敦煌地区的道教不仅有写经、道士、道观这些道教的载体,同时也在按照《灵宝经》所规定的斋期和科仪而从事着相应的法事活动。文书中反映的佛道关系是:佛道两教不仅能够平等共处,而且在信仰上互相兼容,行为上互相合作,处于一种深层次交融的良好状态[21]23。
五 余 论
唐代释彦琮在《唐护法沙门法琳别传》中指出:
儒教济时,人知希仰;释老利物,愚者致疑。所以托彼上庠,陈其未谕,寄之硕学,畅此玄功。故云殉主事亲,则忠孝为首;全身远害,则道德居尊;救苦利生,则慈悲作本。怀忠奉孝,可以全家国;行道立德,可以播身名;兴慈运悲,可以济群品。济群品则恩均六趣,播身名即荣被一门,全家国乃功包六合。故忠孝为训俗之教,道德为持身之术,慈悲盖育物之行。亦犹天有三光,各称其德;鼎有三足,并著其功。三教同遵,嘉祥可致也。[23]
在这段文字中,僧人彦琮并未将儒、释、道对立,而是从佛教徒的角度,比较全面地分析了儒家、佛教、道家的功用及其关系。他认为“儒教济时”“释老利物”,都要通过学校教育招揽信众,培养名师高徒发扬光大,这是儒、佛、道三家传播教义共同遵循的“体”。但其“用”有殊,一分为三:儒家的忠孝为首,道家的道德居尊,佛教的慈悲作本。心怀忠孝,可以为国家建功立业、为家族增添荣耀;道德高尚,可以树立个人威信以致声名远扬;慈悲为怀,可以自觉觉他,通济万物。故忠孝的重点是针对世俗百姓群体的教化,道德的重点是加强个体为人处世的修养,慈悲的重点是将高僧大德的慈悲之心推及世间的万事万物。这三者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协调统一于世人的慈悲本心、道德修养和忠孝功业之中。随着佛教入世的更加深入,佛教界因而对现世多持积极肯定的态度,他们一方面博览儒家经典并阐明其意涵与价值,另一方面则高度关怀时事,为儒家治世之责任和立论而言说,以建立“以儒治世,以佛修心,以道养生”的三教合一的统一秩序为目标[24]。探讨敦煌文化中的人生哲学思想,既可以探究移孝于君到移孝于佛的轨迹,也反映了传统的儒、道与佛教关系及其发展历程。佛教在各地的传播,无不取决于当地群众的需要,从主导方面讲,总是社会生活支配着宗教,而不是宗教支配着社会生活[25]。这都说明,古代敦煌民众生活和精神的需求是佛教得以传播的前提,也是敦煌文化得以交流互鉴的基础动力。
{1} 文中虽没有明确提及孟宗、杨香,但文中有“泣竹笋生名最重”“正酷热天须扇枕,遇严凝月要温床”,与孟宗“哭竹生笋”、杨香“扇枕温衾”的故事相符,即便所指非同一人,但此孝行犹存,权且作认定处理(参见潘文芳《“二十四孝”研究》,福建师范大学,2010年)。
参考文献:
[1]买小英. 由敦煌本《二十四孝》看儒释伦理的融通[J]. 丝绸之路,2019(1):54.
[2]张岱年,朱贻庭.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绪论[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1.
[3]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M]. 北京:中华书局,2011:312.
[4]黄征,吴伟. 敦煌愿文集[M]. 长沙:岳麓书社,1995:33.
[5]宋启劼. 敦煌石窟中的人生哲学[D]. 兰州:西北师范大学,2016:27.
[6]李统亚. 走出痛苦的轮回:论佛教生死观[J]. 黑龙江史志,2009(14):93.
[7]孙灵芝. 身体内求之道[D]. 哈尔滨:黑龙江大学,2012:49.
[8]罗颢. 此生可度:佛教生死观[M].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84.
[9]僧佑. 弘明集[M]//大正藏:第52册. 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86.
[10]彭兰闵. 从“念佛救度”和“中阴得度”看佛教死亡教育[J]. 法音,2009(8):7.
[11]宇恒伟,李利安. 佛教死亡理论的建构:《佛说死亡:死亡学视野中的中国佛教死亡观研究》评介[J]. 五台山研究,2009(1):63.
[12]买小英. 从“七七斋”看中古敦煌家庭的亲情关系和生死观念[G]//段小强,李丽. 敦煌学:丝绸之路考古研究:杜斗城教授荣退纪念文集. 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6:392.
[13]吴崇恕,李守义. 《二十四孝》与《孝经》的关系及其扬弃[J]. 孝感学院学报,2004(4):10.
[14]赵超. “二十四孝”在何时形成(上)[J]. 中國典籍与文化,1998(1):51.
[15]潘文芳. “二十四孝”研究[D]. 福州:福建师范大学,2010:30.
[16]徐俊纂. 敦煌诗集残卷辑考[M]. 北京:中华书局,2000:253-263.
[17]刘永明. 略论敦煌区域道教研究的意义[J]. 世界宗教文化,2019(1):120-121.
[18]周维平. 敦煌道教钩玄[J]. 青岛海洋大学学报,1999(4):89.
[19]王重民. 敦煌遗书总目索引[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290.
[20]陈祚龙. 敦煌学识小[G]//陈祚龙. 敦煌学津杂志:文史哲大系36. 台北:文津出版社,1991:99-120.
[21]刘永明.P.3562V《道教斋醮度亡祈愿文集》与唐代的敦煌道教(二)[J].敦煌学辑刊,2014(1):15.
[22]马德. 敦煌文书《道家杂斋文范集》及有关问题述略[J]. 道家文化研究,1998(第13辑):247.
[23]彦琮. 唐护法沙门法琳别传:卷中[M]//大正藏:第50册. 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205-206.
[24]郑炳林,屈直敏. 归义军时期敦煌佛教教团的道德观念初探[J]. 敦煌学辑刊,2006(2):96.
[25]史苇湘. 敦煌历史与莫高窟艺术研究[M]. 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498.
收稿日期:2022-07-25
作者简介:李润强(1968— ),男,甘肃省庄浪县人,甘肃省广播电视局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传统文化、广电传媒研究。
——《青瓷》作者的人生哲学
—— 《青瓷》作者的人生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