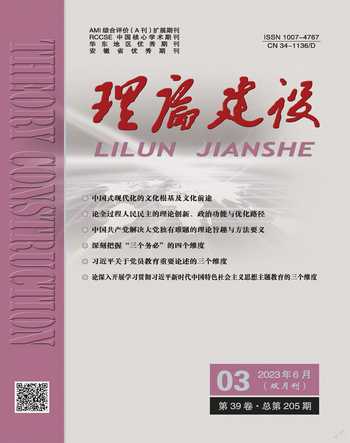论中国式现代化对四重张力的超越克服
贾磊
摘 要: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带领中国人民探索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性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在世界历史背景下持续推进的,面临着比西方现代化更为复杂的新环境、新挑战、新问题。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实现了对四重张力的超越克服:克服个体自我与社会整体之间的张力,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克服人与自然之间的张力,构建人与自然共同体;克服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张力,推动实现国家与社会协同治理;克服民族与世界之间的张力,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张力;超越克服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4767(2023)03-0009-09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1]22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推进民族伟大复兴,并不是自然而然的理论演绎,更不是一帆风顺的实践过程,而是在不断克服各种张力中推向前进。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苏联模式的现代化相比,面临更多挑战和困难。进入新的历史起点,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探析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不同张力,揭示其内在逻辑和超越克服的对策路径,对于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走好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和世界意义。
一、中国式现代化克服了个体自我与社会整体之间的张力,推动人的全面发展
在现代化进程中,个体的生活状态和行为方式会受到社会发展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影响,从而催生了“我是谁”“我要做什么”的茫然。在传统社会,中国人通过人身依附的方式来和社会建立关系并获得归属感,个体在生活世界中对于时间和空间的感知是直观的、确定的,此时个体的自我意识并不强烈,个体理解自我的存在并从个人需要出发来选择生活的情形还没有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因而自我认同问题在前现代社会并没有凸显出来。近代以来,现代化进程逐步瓦解了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为个体创造了巨大的社会流动和空间流动机会。“现代性是个体主体性确立的过程,自我意识的自由成为个体主体性确立的标志。”[2]而自我意识的觉醒和主体性的确立让个体在现代化进程中获得了自由,职业、婚姻、信仰等的选择不再受制于传统的家族共同体,传统社会对于个人的各种灌输和承诺已不复存在,因而个体的选择和决定也就无法再从社会获得确定可靠的保证。由此,自由的个体在现代化进程中陷入一种流动不安的状态,对于自我的评价是不连续、不稳定的。“我们不再从过去获取自己的认同:我们不得不在同他人的互动中积极主动地制造它们”[3],但个体与他者的关系更多体现为随着经济关系而变化的关系,人不能够按照个人的自由意志来创造社会关系,这就导致真实的自我和社会需要的自我之间存在冲突。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但这种社会关系在现代化进程中不再是稳定的、可靠的,社会关系的流动性变化让个体不断失去原有的心理定式、行为惯性和价值理念,陷入了迷茫的自我状态。现实生活中流浪、漂泊的感觉让不少个体转向虚拟网络空间来寻求身份确证和价值实现,而网络空间的符号化生存进一步加剧了个体身份确认的窘境,虚拟世界的自我和真实世界的自我发生了分离,个体无法形成统一的自我观。不少中国人发现尽管在现代化过程中解决了物质需求的问题,但快速的社会节奏和压力已经让自己无法自由选择所期望的生活追求,个体的价值体系更多是由本能、欲望、情感等非理性因素来主导,常常产生一种无以名状的焦虑,不能确定生活的目标和个人的价值是什么,甚至信奉“佛系”“躺平”哲学,由此,现代化将个人置于人生价值意义失落的危机中。
“个体自我认同的危机的发生,从根本上看,是因为个体在生活上得不到确定不变的保障和精神上找不到归宿。”[4]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让中国社会出现了剧烈的变动和转型。中国的现代化不是从传统内部自然生成的,而是伴随着近代帝国主义的侵略而从外部渗透与传播而来,是一种被动式、后发式的现代化。新中国在成立之初就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极其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取得了全球瞩目的现代化建设成就,改变了现代化的世界版图。中国快速而迅猛的现代化进程打破了传统社会植根于自然经济和血缘关系的秩序。“在这种社会转型中,人的严重认同危机的出现成了一种必然。”[5]另一方面,西方现代化是在西方理性精神和知识论传统下所发生的人类历史进程,而中华传统文化是在中国乡土社会家族结构基础上发展出的,是现代化以前社会的产物,其中包含着不少与现代文明相悖的成分,这就意味着传统文化为了捍卫自身的合法性必然会对现代化进程形成一定的阻滞。比如,中国传统社会重农抑商,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就产生了一定阻碍;重德轻法则导致了过去社会发展中对于法治建设的忽视,法对社会的规范调节作用无法充分发挥,等等。另外,现代化进程中某些大众文化组织为了获取更多经济利润而消极迎合大众、娱乐大众,从而降低了大众的科学思维能力和道德判断能力,其世俗性和娱乐性不断消解社会崇高的价值体系。一些人被物欲化平面化的大众文化商品所淹没,不再进行深刻的思索,也丧失了追求崇高的冲动,从而造成了信仰在少数人生活中的离场。
实现个体自我与社会整体的和解,不仅要让个体能够对生命之意义进行自我反思,同时也需要社会赋予个体以合理的生存环境,从而能够在个体和社会的良性互動中重塑自我认同。首先,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了个体的自我反思。吉登斯认为自我是个体的反思性投射,“我们不是我们现在的样子,而是对自身加以塑造的结果”[6]。现代化能够为个人创造更大自由,同时也会不断压缩个人自由。面对现代化这一矛盾统一体,需要强化自我的反思意识。每个人要按照自己的尺度来准确认识自己,对既有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世界图景等进行深入反思批判,不断克服自我的狭隘性,从有限的自我世界走向更为广阔的公共世界。要把握个人生活的主动权,对于生活世界中自身不同层次的需求、社会期望等作出合理回应,让个体自我意识和社会自我意识在“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中实现统一,通过丰富的实践活动来建构自我的心灵秩序和精神世界。其次,中国式现代化不断优化个体生存环境。社会情境蕴含着个体在社会中的属性规定,主体的身份确认就是在社会定位中完成的,这就需要社会能够为个体提供有序、完整、稳定的生活图景。新时代,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要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不断畅通社会各个阶层的流动渠道,让每个个体能够在社会生活中获得公平竞争的机会。政府依法依规引导资本发展,让资本要素更好地服务于个体自由全面发展。同时我们坚持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从中汲取宝贵智慧来应对个体的自我认同危机,在流变的时代为自我提供安身立命之所。
二、中国式现代化克服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张力,不断强化人与自然共同体的构建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现实问题之一。在原始社会,由于人的实践能力的局限,人和自然处在一种“自然吞并人”的消极和谐状态中。自然作为人类生存所直接依赖的存在,对人类充满了吸引力。人类不仅仅从所直接接触的自然中获取各类食物、药材、矿产等,人还对于自然有着直接的经验,并从这种经验中发展出各种神话艺术和对世界本源的想象。随着人的实践能力的发展,特别是技术的飞跃,过去人对于自然的神秘的或者诗意的理解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实用的功利主义视角。人类错误地将自己凌驾于自然之上,单方面关注从自然直接获取的效益,而忽视了自然界的资源是有限的。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警告人类:“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7]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也面临着人与自然关系二元对立的问题,有的人在发展中将自然视为与人无关的独立存在物,自然界存在的唯一价值就是满足人的占有欲望。当人把自然视为异己的客体加以征服改造,人和自然就会处在一种分裂对立的状态中。“人与自然的关系被狭隘化为单一的、功利性的占有关系,结果人的精神生活被活生生地囚禁于一个‘利字、压缩为一个‘欲字。”[8]到了今天,我们看到大山,不再感叹自然的鬼斧神工,我们更关注山脉之下的矿产;我们看到广袤的森林,立刻想到了其中蕴藏的珍贵的木材、药品等;我们看到猪牛羊,想到的是餐桌上烹饪的食品……自然不再是人的家园,而是生产的原材料,人和自然的对话,已经变成了人获得产品的过程。今天的自然在很大程度上是被严重污染的自然、被过度商品化的自然。
西方现代化是一个全球性过程,其发展根植于资本逻辑之中,对于现代化进程中人类与自然关系的考察绕不开资本逻辑。资本逻辑的本质要求和一般性特征就是对价值增值的无限追求。人与自然本应是密不可分的命运共同体,但当其置于资本逻辑支配下,就会导致这一共同体的消解。在现代化进程中,资本逻辑认为自然是实现资本增值的重要资源和手段。在资本面前,人对于自然进行了无情的剥夺。资本和技术的结合大大提高了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实践能力,自然成了被控制的对象。“资本所关心的是在大量生产有利润的产品的方向上让生产力得以发展,对于环境的考虑必然是第二位的。如产业公害所表明的那样,资本的逻辑是为了获得利润而不惜破坏环境。”[9]人与自然的对话变成了主体对于客体不断的改造和索取,自然被当作人的利益而存在的客体,是资本进行生产和再生产的原材料。这样人就错误地把自己视作自然的统治者,仅仅关注从自然获得经济利益,而忽视了人与自然作为共同体的一体性。正是由于人和自然的对立越发尖锐,才造成了今天面临的资源耗费、环境污染、物种锐减、生态失衡、灾害频发等问题。
实现现代化进程中人类与自然的和解,并不是要完全消灭资本,也不是放弃人类对于自然界的改造利用,而是在生产力的发展中来不断强化“人与自然共同体”意识,“不是资本来支配人,支配‘人—自然共同体,而是以人为本,由‘人—自然共同体来支配资本”[10]。新时代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走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绿色现代化道路。首先,树立了绿色发展理念。这一理念强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11],“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基本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12]等。为此,中国努力建立更为普及的生态教育体系,充分利用新媒介来加强绿色发展理念的宣传,重新塑造人们对于生态文明的价值取向,让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逐步转化为全社会生态保护、低碳生活等绿色生活生产模式,以全民意志来为绿色发展实践构筑最为坚实的思想基础。其次,完善了绿色发展制度体系。绿色发展并不等同于简单的环保主义或者生态主义,而是将生态文明建设与人类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有机融合起来,从顶层设计上来加强制度保障。中国结合发展实际来制定系统完善的生态法律制度、环境监督制度、污染惩治制度、生态补偿制度等,逐步形成多元主体参与、激励惩罚并重、治标治本统一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通过相应的制度安排来为绿色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推动力。最后,加强了绿色科技创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机器本身是人对自然力的胜利”[13],但这并不意味着机器就应当扮演破坏自然生态的角色。相反,科学技术在不断创新中已经和绿色发展构建了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人与自然现代化关系的构建离不开高新技术的支撑。新时代中国加大节约、替代、循环等生态技术的开发和推广应用,引导企业、院校、研究机构等加强生态领域关键前沿技术攻关,在现代化进程中构建全方位绿色创新支撑体系,利用绿色科技创新来转变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不断推动人类物质生产系统的生态化,让人的实践活动成为更加符合自然规律的活动。
三、中国式现代化克服了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张力,推动实现国家与社会协同治理
社会与国家关系问题是各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处理好这一问题对于走好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中没有解决得很好。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遇到全面治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原理很多是预测性的;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就过世了,没来得及深入探索这个问题;苏联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实践经验,但也犯下了严重错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14]中国式现代化并不是单纯发展市场经济,而是有着上层建筑的密切配合。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在国家治理中采用了政府总体控制的模式,通过集中力量办大事实现了推动现代化进程的阶段性目标。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与社会是高度一体化的,很多责任由政府来承担,国家治理采用的是“全能主义政府”治理模式,即“国家通过意识形态、组织结构以及有效的干部队伍实现了对社会生活所有方面的渗透和组织”[15],社会自治空间拓展和能力发挥受到一定影响。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這些事只要有一定的规章,放在下面,放在企业、事业、社会单位,让他们真正按民主集中制自行处理,本来可以很好办,但是统统拿到党政领导机关、拿到中央部门来,就很难办。”[16]中国作为一个超大规模并且正处在转型变化中的社会,在改革开放之初还没有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建立一整套完善成熟的现代制度机制,如果完全依靠政府来统筹各个领域治理、协调分配公共产品等,不仅会造成政府的超负荷运转,同时也会导致社会空间被行政权力不断挤压,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也就难以实现。
政府与社会面临的协调困境,一方面是受到了历史上权力观念和治理思维的影响束缚,另一方面则是现代化道路上国家社会一体化进程的后果。从历史来看,中国社会的自治传统延续了几千年。古代社会建立了自治制度,比如秦汉的乡亭里制、魏晋的三长制、隋唐的邻保制、宋代的保甲制、元代的社制、明清的里甲制等,人们从社会中遴选长老乡绅作为治理权威,借助于儒礼教化、乡规民约等来实现地方社会治理。但这种传统社会自治更多是隶属于封建皇权的自治,是家国同构下的国家统治方式,而不具备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自治涵义。传统的自治思维原则会制约现代进程中社会自治理念的发育成长。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主导着中国的社会变迁,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人民公社”“单位制”到后来的“村委会”“居委会”,都是在国家社会一体化逻辑下所建立的社会治理組织结构和管理方式,“国家与社会的现代权利关系并没有完全建构起来,社会的主体性并没有建构起来”[17]。同时,从各类社会组织发展来看,这些组织带有较强的行政化特点,实际上仍然是代行部分政府职能,抑制和束缚了社会组织在国家与公民之间支持保护作用的发挥。正是由于在国家治理中还没有建立“政府—社会—个人”的模式,公民在几乎所有事情上都是直接面对政府、依赖政府,容易引发社会分歧和冲突,加大了政府的治理压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纳入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之中,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则进一步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为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与社会协调发展道路提供了重要指导。
推进治理现代化就是要超越西方世界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治理逻辑,在新时代建立国家与社会协同治理的新格局,从而实现“强政府—强社会”的良性互动。首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新时代我们不断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针对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重点、难点和痛点来强化治理顶层设计,破除现有治理体制机制弊端,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五大领域中不断改善优化治理体系。在党的领导下汇聚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强大合力,发挥好党在其中的领导协调作用,努力凝聚不同主体的治理共识,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形成强大的总体效应。不断加强新时代干部队伍建设,建立系统完善的人才制度和政策体系,将治理能力作为干部队伍选拔考核的重要依据,切实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人才智慧支撑。其次,坚持建设服务型法治型政府。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构建较为完善的法治框架和法治程序,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利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实现社会主义的善治。着眼找准政府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角色定位,加快推动行政体制改革,通过权力清单等方式来进一步简政放权,推动行政理念从过去干预为主转向服务为主。积极创新政府治理模式手段,加大人工智能、大数据、5G等现代化技术手段在政府治理中的应用,以整体性治理和精准化治理来提高治理效能。最后,坚持构建多元化社会治理格局。充分发挥社会自治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性作用,不断提高社会进行自我管理和服务的能力。畅通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继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鼓励引导人民群众通过不同方式来反映治理诉求和意见建议,加强人民群众对政府治理的监督。充分发挥市场在治理中的作用,通过市场机制来协调社会不同主体的利益关系,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加快培育各类社会组织,积极构建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的合作机制,引领社会组织自觉弘扬公共情怀,发挥好社会组织在民主协商、政社互动、公共服务等方面的作用。
四、中国式现代化克服了民族与世界之间的张力,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马克思指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18]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都不是闭关锁国的现代化,而是要在对外开放中和其他国家进行深度交往。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拓展了世界现代化理论,克服了西方现代化的弊端,不断提高中国对全球的影响力塑造力。未来世界在迈向更高发展阶段进程中,围绕中国模式和西方模式的话语权斗争会更加激烈,特别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和对立,加剧了双方在交往中的矛盾。这些矛盾作用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政治、经济、思想等各个方面。在国际政治上,西方国家频繁在人权、民主、新冠疫情、“一带一路”等议题上挑衅抹黑中国,利用庞大的媒介体系来对中国进行污名化报道,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中国阴谋论”;在思想文化上,西方发达国家妄图借助于自身发展优势将其文化价值理念输入中国,试图通过其虚伪的自由民主等所谓“普世价值”来冲淡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同时抑制中华传统文化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世界的交流传播;在经济发展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搞贸易摩擦,利用贸易壁垒来限制中国产品拓展国际市场,对中国的高新技术企业进行赤裸裸的抵制打压,通过美元霸权企图破坏中国金融市场稳定,等等。由此可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乐意、也不允许中国式现代化取得成功,中国所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必然会遭受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强烈抵制和破坏。如果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关上对外开放的大门,就不能够汲取其他文明的经验与智慧,不能从全球来获得现代化的生产要素,就容易再次沦落到落后挨打的地步。同理,如果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放弃了独立自主,将自身的现代化建设依附于其他国家,那么就会陷入被动或者畸形的发展模式中,必然会付出高昂的代价。
当前民族与世界之间的张力实际上就是“西方中心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矛盾。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工业革命而获得了相较于其他国家的发展优势,并逐渐演化出排斥其他文明的“西方中心论”,试图通过殖民活动、霸权行为等来征服其他文明,将西式现代化道路视为国家发展的唯一样本,“世界历史发展道路的多样性、现代人类文明形态的多样性就彻底被否定了”[19]。资本主义在全球扩张的过程也是西方中心主义的渗透过程,不断在全球塑造着资本主义的“伟大神话”,强调人类历史是围绕西方文明来展开的,鼓吹西方价值观念、发展模式具有普遍性。然而“西方中心论”已经制约了不同文明的对话交流和世界历史发展,人类迫切需要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作为生存发展的价值引领和路径指向。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带领中国人民探索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从而彻底否定了资本主义文明的线性历史观和历史决定论,明确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多样性。需要明确的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并不是要否定任何文明,也不是要与其他文明发生冲突,而是为各国争取应有的发展空间和发展自主权,让世界各国能够按照自己意愿来选择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不仅让中华民族在21世纪走向伟大复兴,凸显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现实性,更有力推动了人类文明向更高形态的转型升华。“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20]亨廷顿等学者所提出的文明冲突论更多是服务于资本主义文明,冲突背后的逻辑是资本和利益的争夺。从中国古代的丝绸之路、郑和下西洋,到今天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证明了不同文明的交往并不必然会产生冲突,而是能够“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1]63。人类文明新形态以多元包容、合作共赢的姿态向世界展示了文明之间的相互交融、共生共荣。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空间维度上具有胸怀天下的特质,是对“工业革命以来西方中心主义主导下单一中心交往方式的扬弃和超越”[21]。新时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能够让全世界携手消除发展面临的弊端,实现各国利益的最大公约数,推动构建和谐共存的美好世界。首先,推动达成利益共识。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所奋斗的一切都与利益相关。利益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题中应有之义。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越来越多体现出其世界意义,为其他国家的发展提供了实践和理论上的参考借鉴。中国坚决摒弃过去国际社会中的丛林法则和零和游戏,秉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继续推动“一带一路”等国际合作,推动沿线国家政策、资金、贸易、设施等的融通,和其他国家共同构建多边贸易机制,提高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找到不同区域、国家利益的汇合点,从而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其次,推动达成价值共识。不同国家、民族的冲突摩擦本质上是一种价值冲突。推动合作、扩大共识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找到全人类的价值共识。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22]中国积极推动这一共同价值理念在全球范围内的宣传,积极揭露批判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的实质,倡导国际社会充分尊重各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包容、理解和尊重不同国家的独特价值理念,在国际社会开展平等的文化交往,以价值共识来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凝聚力。最后,推动达成行动共识。中国积极利用领导人峰会、国际论坛等交流平台,率先设置引领性战略性议题,整合不同国家的共识来构建公平合理的国际行为准则,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到国际行动中。积极构建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东盟、中非等命运共同体,有效应对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前进与倒退、合作与对抗、开放与封闭等矛盾挑战。针对区域或者世界面臨的恐怖主义、自然灾害、气候变化等难题,发出中国声音、提供中国方案,吸引带动更多国家主动参与到命运共同体构建中,为共建美好世界提供可行路径支撑。
五、结束语
实现现代化是世界历史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潮流和趋势,不同国家和地区因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地缘政治的差异而选择了不同的现代化道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性成就,彻底打破了西方现代化神话。但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着眼于中国探索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考察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面对的不同张力,有助于更好解决未来现代化进程中的诸多难题。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所表现出的张力及由此引发的问题,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过程性问题,随着现代因素的积累和各个领域制度规范的重构,特别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全面领导下,这些张力将逐步被克服,并产生巨大的活力和创造力,从而更好地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的全面开启,中国式现代化已经从被动输入型转化为自主辐射型,中国未来将会走一条高质量、可持续、包容性的发展之路,将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现代化密切联系起来,与其他国家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世界历史和人类文明稳步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2] 黄全利.个体自我认同危机及其在数字时代的凸显[J].学术探索,2015,182(1):98-103.
[3] 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M].第5版.李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95.
[4] 尹岩.论个体自我认同危机[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5):24-28,32.
[5] 王成兵.当代认同危机的人学解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35.
[6]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自我认同[M].赵旭东,方文,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86.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九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59-560.
[8] 高连福.马克思自然是“人的精神食粮”的思想意蕴[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109-119.
[9] 岩佐茂.环境的思想:环境保护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处[M].韩立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128.
[10] 鲁品越.资本扩张与“人—自然共同体”的形成——人与自然矛盾的当代形态[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1,13(2):3-9,46.
[11] 党的二十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456.
[12]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123.
[1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08.
[14] 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N].人民日报,2014-01-01(02).
[15] 郭坚刚,席晓勤.全能主义政治在中国的兴起、高潮及其未来[J].浙江学刊,2003(5):157-159.
[16]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28.
[17] 周庆智.基层社会自治与社会治理现代转型[J].政治学研究,2016(4):70-80,127.
[1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04.
[19] 侯冬梅.哲学思维方式变革下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从“西方中心论”到人类命运共同体[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49(2):31-37.
[20] 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N].人民日报,2023-02-08(01).
[21] 穆艳杰,胡建东.从主体际视角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基于马克思交往实践理论的解读[J].理论探讨,2021(2):73-79.
[2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522.
On the Transcendence and Overcoming of the
Four Tensions in Chinese Modernization
JIA Lei
(National Security Academy,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Beijing 100091,China)
Abstract: The CPC has led the Chinese people to explore a path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in the course of a century of struggle, and has made great historic achievements. Chinese modernization has continued to advance in the context of world history, and is facing new environments, new challenges, and new problems that are more complex than western modernization.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e CPC has transcended and overcome the four tensions: overcome the tension between individual self and society as a whole, promoted the free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overcome the tension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built a community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overcome the tension between society and the state, promoted the realization of coordinated governance between the state and society; overcome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nation and the world, created a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Key words: Chinese modernization;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tension; transcendence and overcoming
[責任编辑:盛 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