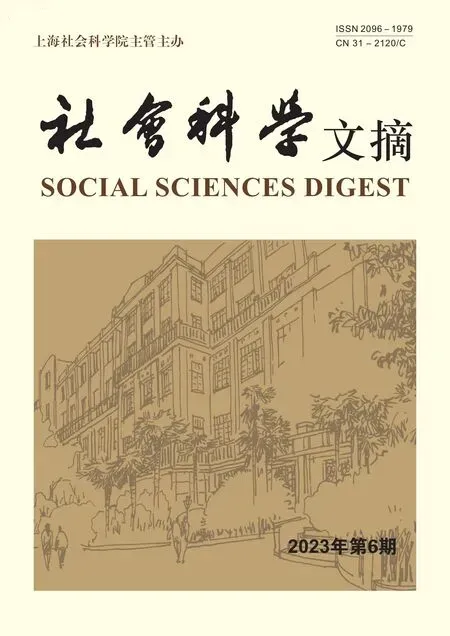“传播”术语重勘与“意义论”视阈下的传播学
文/胡易容
引论:传播研究的“意义论”与“符号学派”
约翰·费斯克曾将传播学研究划分为“过程学派”与“符号学派”。“符号学派”注重意义的交换,此学派对“传播”一词的使用具有某种普遍的理论形式结构特征,某种意义上越出了目前主要被定位为“社会科学”的传播学边界。可以沿着意义论思路,从“传播”这一术语的重勘来思考传播学理论的拓展可能。雷蒙德·威廉斯指出,要理解关于“传播系统”与“传播理论”方面的论证,有必要回溯communication当初尚未定论的词意涵。当初意涵的回溯不仅需要考察传播的向度,还至少需要考察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舶来的传播学传统发展史的偏狭保持某种反思自觉,同时重视我国引入“传播”一词的使用语境和历史语境。二是,将眼光放长远,不仅考察特定历史时期内传播的“具体形态”,更要从“传播”的本质和逻辑上的可能外延去思考传播学的“逻辑可能”。这意味着,不仅要考虑过去和当下主流的大众传播等传播形式,也应当考虑人内传播、跨物种传播、人机交互传播乃至跨生命传播这些极端形式,以穷尽传播的范畴和理论边界。三是,通过适当越出现有传播学的“社会科学”范畴,从“意义论”考察“传播”的意涵和“传播学”的可能。
从“传播”到“传播学”的术语语义理据考察
(一)“传播”的中西术语理据
“传播”(communication)一词在中西语言中各自发展,其产生关联是近代以来的事。
据雷蒙德·威廉斯的考证,communication一词可追溯的最早词源为拉丁文communis,意为“普遍”,且其现代意涵在15世纪以后就已基本具备。陈力丹指出communication源于古希腊的两个词根是com与munus,合起来意为“共有”“共享”。到17世纪时,产生了“传播媒介,通讯工具”的引申意涵。进入20世纪,随着其他传递讯息与维系社会联系的工具不断发展, communications也被来指涉这些工具手段。
中国古代汉语中,“传”与“播”连用并不多见,偶尔出现的释义为广泛流传。及至近代,传播一词随着西学东渐而逐渐被普遍使用。较早的,如1915年《清华学报》提到“学报者, ……传播学术”,1917年严继光的论文《法国大哲学家柏格森学说概略》中提到的“学说之传播广且速……”,都属于知识传播;同时期的《私立无锡小麦试验场推广良种报告》中有“育成良种,传播农村”之说,这是创新扩散的“科技传播”;陈寅恪在《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提到“印度神话之传播已若是之广”,则可以归入文化传播类。
五四一代不同学科的学人对“传播”一词的使用,已经与西方现代学术用语较为接近。但在信息科学与传播学引进之前,“传播”一词尚未作为现代汉语规范用词被普遍接受。20世纪80年代修订完成的大型辞书《辞海》尚未收录该词。
(二)我国“传播学”译名的争议与约定俗成
“传播学”的引进过程中,学科名的翻译定名充满争议。早期对传播译法较有影响力的包括“交通”(郑北渭)、“通讯”(张隆栋)、“传意”“传”或“传通”(余也鲁)等。1978年,郑北渭、陈韵昭等改为“传播学”。1982年,在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的召集下,我国大陆学界初步统一的“传播学”中文译名,逐渐成为惯例和定名,但留下的问题依然值得探讨。
从词义学角度看,“传播”的“单向度指向”与“communication”的原意并不完全对应。后者的意思既包括单向的“扩散”,也包括“交流”“交往”,其指向的传播向度可以是单向的也可以是交互的;在面向和路径上,communication可以是点对点、点对面的交流,也可以是撒播。
对此,刘海龙提出“在使用中逐渐对其进行改造,重新赋予这个传统的词汇以新双向互动意义”。这一提议对当今新媒体语境现实具有意义,但在具体操作上,存在一定困难。从构词法来看,传播是由“传”与“播”构成的同义复合词。作动词时的“传”是从一方给予另一方的行为,并不包含交互的意涵;“传”的另一个主要意涵本身即包含了“推广,散布”的意思。此行为的附加性质可以在“传”的构词中补充修饰,如传递、传导;而“播”的两个意涵要么是承接“传”的具体动作,要么指向针对广泛对象的“散布”,缺乏双向性的义素。因此,当“传”与“播”组合时,不仅单向性意味明确,还有“一对多”的意思。
实际上,学界用“传播”一词表述“双向性”意涵时,往往是通过添加前缀或置于某种上下文语境来实现的,如:人际传播、人内传播、自我传播、交互传播、网络传播等。另外,在学术译介或撰写的学术文著中,若遇到更为明确的“双向”“人际”意涵,又不便通过添加前缀的情形,就干脆舍弃“传播”的译法,而改用“交流”“交际”“交往”“沟通”等。比如,陈力丹撰写《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需要通过意涵有所区别的“交往”与“传播”来形成主副标题义项互补,如果直接用“马克思恩格斯的精神传播论”就无法展现这种词义不同侧重的微妙差异。
(三)“传播”定义的窄化对“传播学”范畴的限制及反思
相较于“传播”一词在术语方面的限制,传播学的自我窄化才是更麻烦的问题。至少在三个层面上,传播学的自我窄化可能限制了它向一门更具普适性思想的学问发展。
首先,历史惯性使然将“传播”窄化为“大众传播”。“传播学”的蓬勃发展基本上是伴随着现代媒介兴起的“大众传播”运动,于是,“传播学”似乎无须明言地就是“大众传播学”。比如,国内2000年引进的传播经典教材Communication theories: Origins, methods and uses in the mass media的中文名为《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其中省略了原著标题中“在大众媒介中”这个限定性前缀。传播学要在外延和内涵方面实现有效扩展,一种可能的途径是将社会学维度、媒介论维度、符号学或意义学维度整合于自身的体系化视角之中。
其次,由于受到现代媒介技术的变革的冲击,传播学无意识地将“传播”工具化为“技术媒介传播”。费斯克曾感慨广义媒介概念的用法正在被淡化。在他看来,将媒介定义为技术性媒介或大众媒介,是一种缺憾。他直言不讳地指出,构成传播学基础的“信息论”是一种机械性的理论。信息论视野中的信息是“信号的物理形式”而非“意义”。帕洛阿尔托学派提出的“人类不能不传播”的命题,洞见了传播作为人类普遍性的命题,所反映的人类作为“传播生物”基本生存方式是一个本质性的永恒主题。其展现出来的学科前景将远远越出“现代媒介”的范畴。
再次,将“传播场域”预设为“人类社会”。施拉姆那本经典的《传播学概论》两个英文版本的原标题分别为:Men Message and Media: A look at Human Communication; Men, Women, Messages, and Media: Understanding Human Communication。他明确了这本书的范畴——“人类”,但被翻译为中文的时候则因为不言自明而被省略了。之所以需要将“人类”标注为传播理论的前缀,恰恰说明该范畴并非不言自明。然而,当“人类”这一前缀说明在使用中被“自然地”略去而无须声明时,传播学就出现了自我窄化的倾向。
我国在引介传播学时,更注重人类传播领域,尤其集中在发生于特定范畴的“社会大众传播”。社会学框架使得传播学在某种意义上成为社会学的延伸旁支或等而下之的学科门类。对于传播的整个概念范畴边界来说,它是不完整的。由此,仅仅讨论人类社会中大众传播或人际传播这些具体的传播门类,就会对更普遍的传播范式缺乏足够的关照和哲学思考,而应当将处于边界的一些问题纳入思考范畴,穷尽传播的可能边界,并深化至“一般规律”。
彼得斯在《对空言说》(Speak into the Air)中不仅拓宽了传播的主体,也拓宽了传播的内涵,将“传播”置入更广义的思想维度当中考量。当对传播作一种更一般的预设时,社会学提供的框架就不必然构成传播发生的“母体”,而退居为视角之一。以“人—机交互”为例,这种并不符合“人与人”关系的传播或交流形式已经成为可能影响人类生存方式的核心话题之一。一种基于“传播意义”的媒介观可能更有助于我们将“人—技术”从其他语境中抽离出来,并考察日益聪明的机器是否具有“准主体性”或“亚主体性”。
“传播”的符号学外延与“传播”意义达成的层次
(一)传播的符号学外延拓展
现代“传播学”基础定义的思考已经较为全面。例如,弗兰克·丹斯和卡尔·拉尔森梳理了126种传播学定义,并主要围绕观察层面、意图性、合乎规范展开传播与非传播的区分。李特约翰基于此,围绕“传播是否必须具有意图”和“传播是否一定要被接受”这两个问题辨析了九类与传播相关行为(表1)。

表1 与传播有关的行为
这九类行为围绕“人”展开,以便区分各种行为与传播的相关性。可以结合费斯克的思路——“过程效果”与“符号意义”——来展开分析。
一是,两种路径对传播的判断依据不同。传播学者所讨论的“是否构成传播”在符号学者的探讨中成为“是否构成符号”,而对于符号意义论来说,“过程”是围绕意义实现来探讨的。例如,赵毅衡将符号过程的必要条件总结为“时间距离”“空间距离”“表意距离”。这三个距离涵盖了全部上述九种传播行为,并让传播的过程转化为一种形式逻辑,而非丹斯分类中行为是偶然或经常发生。这种形式逻辑提供了符合此形式逻辑的普遍可能。
二是,两者对形成传播的必要条件宽容度不同。信息论的传统常将“传而不通”“不传而通”的情形排除在传播行为之外。从意义形式的角度看,它们包含着同样丰富的内在意涵。“传而不通”的情形是传播的常态,但并不意味着意义未发生交换——未被解读的艺术可能是传播的失败,却可具有丰富意义生成;“不传而通”与“过程论”的逻辑是相违背的,却是意义论中常常被重点关注的现象。
此外,传播意图的主体范畴限定有所不同。无意图的传播实际上涉及如何看待人造符号之外的自然界与人的交互关系。丹斯的九种“行为”并未包括人类之外的非意图发出者在人类认知中发生的“符号过程”。符号学通过形式逻辑的方式将上述九类行为全部纳入“符号表意”,范畴远远大于丹斯的界定,它的范畴有多大呢?正如皮尔斯所说,“释义之所及,符号之所在”。
(二)“传播意义”实现的基础及其逻辑层次
沿着“符号学派”的“表意三距离说”,可以将“传播”一词的层次做如下描述:
首先,传播的物理层面及其指向的“媒介性”。在表意三距离中,时间距离与空间距离都体现为一定物理量的跨越。可以将传播必然包含的这种物理时空过程界定为传播的第一性——“媒介性”。不过,媒介性还不能完全涵盖传播学的全部内容,这也是费斯克强调的“广义的媒介观”不应被压缩为“媒介技术观”。
其次,传播活动的秩序建构——“信息属性”。要实现表意距离的跨越,可能首先需要实现从物理层面到感知层面的转换。发生时空的转化在未被设定特定的参考坐标时可能并不构成传播。客观世界本身并不必然具备与主观世界的连接性,支持进入意义领域的是客观世界的秩序——信息。信息不是某种实存的对象物,而是包括物理媒介在内世界的存在方式:(1)世界是具有其特定属性(包括物理属性在内的无穷方面)的客观存在;(2)世界运行有规律、有秩序,且这些秩序不因人的主观意志而转移,但可被人认知。
由此,我们可以将“信息”作为传播赖以实现的“第二性”。但传播学不能停留在“信息”阶段,不被感知或认知的信息依然是没有实现其意义价值的。“信息”与“意义”之间的重大区别在于,前者是客观工作假设,是意义的待在,而后者是一个进入感知或认知的释义结果。
再次,实现传播意义通达的“符号层”。若将“媒介性”视为传播客观物理存在的物理基础,则“信息属性”是这一基础的秩序性和连接性延伸。但自然界所展现出来的这种秩序并不是决定传播的全部要素,而是构成传播的“客观条件”。因此,基于主体感知的第三性就是对信息的形式化接受和处理——符号。符号是一种包含主观感知的“意义”,“被认为携带意义的感知”,而“信息”则是客观世界的秩序——既可以是自在的,也可以是人为制造的。
以上并非包罗万象的全能视角,而是从费斯克所说的“注重意义生成”的符号学角度出发,对传播学发生过程的一种解读,解读的意义不在于排他,而在于展现传播学的多元性和丰富性。
结语:传播意义论的双重敞开逻辑
大到天体运行、宇宙洪荒,小到生物基因乃至微观量子,客观物世界都具有构成媒介的潜力,但它们未被纳入认知实践范畴时,只能是自在自为的。因此,这种媒介的潜力需要通过两个层次的跃迁来实现。首先是“信息”层。“信息”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但信息与自在的物世界的不同在于,此概念是以“被接受”为工作预设的“待在”,具有可被认知性。其次,需要进一步跃迁至符号层以实现意义的共享或交换。从意义学或符号学的角度来看,传播尽管常常显现为“物理时空距离的跨越”(媒介)以及“对象秩序的显现”(信息),但其最终指向“表意距离的跨越”,也即是特定的“意义之敞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