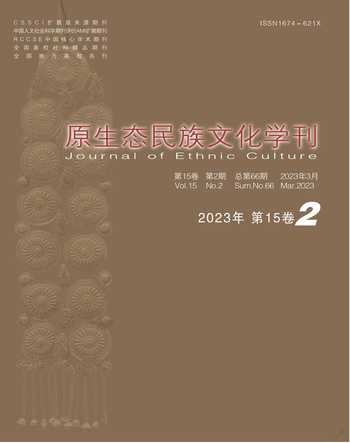乡村建设的滇池东岸之路
李伟华 朱晓阳
摘 要:以滇池东岸宏仁村的社区建设为分析对象,讨论乡村振兴和城市更新中的社区动力和研究者“介入”的撬动点,以此呼唤乡土建设中的“社区力量”。从宏仁村进行的“保新村”“修复村庙”“拆迁直播”活动中,发现具有地势意义的场所是研究者介入活动的中心;自然村组作为研究者介入的单位体现了这个单位的“社区”价值。
关键词:乡村振兴;社区力量;研究者介入;本体政治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 - 621X(2023)02 - 0022 - 11
一、引言
近几年来,做了有关社区营造和乡村建设的一些讨论。在那些场合针对的首要问题是:乡建中“社区力量”何在?
彼时我们认为这是包括艺术家、建筑师和规划师等在内的乡建力量面对的核心问题和难题。在本文中,我们想沿用这个话题,从本體政治(The politics of ontology)1的视角,讨论乡村振兴和城市更新中的社区动力和研究者“介入”(engagement)的撬动点。我们将用滇池东岸宏仁村(学术名“小村”)的案例呈现我们所理解的城市化的微观过程,并讨论相关的介入活动。对于将进入这个领域的人来说,我们的理解和经验会有意义。
回顾过去十几年在宏仁村的工作,我们主要进行了3次与“物”有关的介入活动。第1次是2010年帮助一座农民建成的宏仁新村免于拆除。这座新村从当时主流的眼光看是“城中村”;第2次是2012年和2017年协助当地人修缮了宏仁老村的一座旧庙;第3次则是2020年以社交媒体“直播”拆迁的方式,阻止了拆迁方对一所百年老宅的拆除,使之获得区级不可移动文物的名号。应当强调,我们一直将“物”置于认识当地和介入活动的中心。与此相关,我们总是从地势政治的角度来测度(mapping)某物的意义,发现地势1政治视角与当地人(包括村民、政府和开发商)之间有共识,虽然相关各方不会由于有共同的地势视角而减少他们之间的分歧和冲突。这3次事件的时间延续十年有余。我们利用其中几年(2010 - 2013年)这里被地方政府因拆迁项目“烂尾”或成为“废墟”而放弃治理的机会,协助当地人组织起来自己管理,并在2013年使自管力量成为正式村民自治组织的一部分。废墟上的村民自治和管理与上述3次“物”的演成之间关系紧密,可以说互相支持。
此外,2020年3月以后,虽然宏仁村的村小组长职务已经被别人取代,但上述空间和“物”的成果并没有逆回。因此,我们仍可以用“胜利”的眼光回顾这段历程,并从中吸取教训和经验。
二、测度滇池东岸城中村
宏仁新村是我们与2010年昆明搞的“城改大业”相遭遇时的一个介入场所。当时螺蛳湾国际商贸城项目将包括宏仁新村和老村在内的周边6个村庄及其5 700亩土地划入征收和拆迁的范围。而新建成不到半年的宏仁新村也被以城中村改造之名列为拆除对象。
今天如果一个外人初次来到滇池东岸的宏仁新村,会注意到这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所谓“熟悉”,是一眼看上去它有些像规划建成的居住小区。整个新村有502栋房子,从北到南分成28排,一条中心道路从每一排中间穿过,同一排的房子互相紧挨着,一眼看上去以为同一排的房子是连排别墅。其实它们都是紧紧挨着的独栋。与其说像城市小区,不如说更像一座“新农村”。它有貌似21世纪初的城市低层板楼小区的外貌,都是六七八层的楼房,有规划留出的小区道路,有小区道闸和随处皆有的监控摄像头。但比较一般城市小区,这里的建筑密度更高,房距更小,绿化面积少。宏仁新村的楼房底层都是按商铺格局设计的,全村502户,约2 000余人,可租客则有约20 000人。2016年,村内有300来家包括“七小行业”,涵盖餐饮、客栈、日用百货、美发美容、洗衣店、诊所药店、仓储、快递点等等店铺。整个新村就是一个住居和市场合一的场所。每一栋楼的面积都是96平方米,底层均按照批发市场的样式设计,隔成三间,可以说就是传统“三间房子”的变异体,看上去既土气又新潮。新村东边挨靠着昔日的农田灌溉和排涝大沟,现在沟顶被盖住,从南到北建成一条夜市街,街上有70余家商铺,被命名为“宏仁夜市风情街”。宏仁新村在外的名声则是“小香港”。这个表示此地繁荣的名字令一些村民骄傲,却会让一个昆明城市里的人感到有些难堪。2005年最初规划宏仁新村时,社区书记(过去的村支书)手里的蓝图是一座全由二层楼组成的新农村。但一开工后,各家根本不理会规划图,几年以后建成的都是五六层或更高的房子。在2016年,社区书记打算改变新村由各家各户自己管理底层商铺的“混乱”局面,试图引来一家公司承包整个新村的市场和小区管理。这一建议被村民代表会否决了。过了不久,昆明市政府将这里列为城中村微改造的试点,对其排污、电网和道路进行了升级整治。今天宏仁新村已经成了滇池东岸的一处地标。
十余年前,作者朱晓阳称这里为“乡村贝聿铭的震撼作品”1,曾以《宏仁新村(2001 - 2015)——一个城市“场所”的诞生》为题介绍:宏仁新村是一处体量巨大,但是紧凑和有机的场所。2它的每幢房子之间的街道宽度为10米,整个建筑群有502幢房子,建筑总面积30万平方米,占地261亩。新村建于2005 - 2010年,当时每幢房子主体投入约30 - 40万元,资金来源为征地补偿款,或集体预留安置用地转卖收入。新村的基础设施为统一设计。宏仁新村是农民与地方政府互惠交换的结果:2005政府和开发商征得600余亩地,建新亚洲体育城,宏仁则获得集体建新村的承诺。“只要老百姓不上访,你们要盖就盖”(当时村支书转述乡领导的话)。3在面临完全拆除的2010年5月,村内民意代表莫正才写了一份有绝大多数(400户)村民签字的请愿书《给我们宏仁新村农民一个生存的空间》。 这位莫正才老人是宏仁村民抵抗拆迁的主要领导人,也是下文中的百年老宅的主人。请愿书中有句说:“……历经五年的时间,到现在才基本建成,钢混框架结构,整体浇灌、防火、防震、道路宽,下水接入市政排污系统,绿化成荫,水电通畅一座美丽新农村……新村是我们失地农民历经五年,建设成的理想家园。”
新村这座身处城市化下的农民“理想家园”如何得以幸存?它是如何成为此后十余年,滇池东岸这片地方社区营造的一个撬动点?以及我们和村民与地方政府之间关于新村的共识后来如何获得?
我们在最初对宏仁新村的认识有些矛盾,对这个农民现代主义的巨无霸并无好评。从2007 - 2009年,我们在那里拍摄纪录片《故乡》,镜头中对于它的描述并无褒扬。相反,电影经常拿它与老村作为对比。但在那期间,我们感到村民对于新村有一份超乎寻常的热爱。在很多城乡结合部,农民给房子加层是为了抢在拆迁之前增加房子面积。这些加层的质量很差,有些根本不敢住。这类加层在老村也不少。但宏仁新村的每一幢房子都是用上好的材料,是在房主人的严密监督下施工建成的。在2009年我们结束电影拍摄时,已经对这个新村的看法有了大转变。
在2010年拆迁开始之前,我们与村民对于宏仁新村的地势意义有共識:首先,新村是在城市化趋势下,农民用自己的现代化想象和现代建筑技术及材料,在自己的地盘上建成的一个场所,在新的非农生境中成为他们生计的核心和日常生活的凝聚处。例如它是居住和市场的合一,是生计的主要来源。其次,新村的建造是社区力量的空间表达。相比周边的村庄,由各家各户按规划自建一座 “理想家园”的案例并不多。再次,当拆迁开始,宏仁村成为首要的拆除目标时,全村绝大多数人开始“保新村”。我们那时候意识到这是介入和营造社区的一个切入点,宏仁新村成为决定局势的一个关键。从2010年“保新村”开始,到2017年新村被确定为“城中村微改造”试点,再到2020年宏仁新村土地确权为止,经过十年,新村的名分终于得到承认。新村作为一种农民城市化与国家城市化相调适的案例,值得城市规划、城乡社会学和城市人类学去进一步研究。
三、废墟中的“共同体”:修复村庙
回顾滇池东岸宏仁村十余年历程,另一重要事件是宏仁老村大寺的修复。这座古庙的存留是在拆迁废墟中的村民自治情景下发生。
从2010年5月新村拆迁开始后的一年多时间,村委会当时以村集体无钱办事为理由,提出要将老村中的公共面积先签给拆迁办。2010年下半年,新村拆迁已经停止,城中村改造拆迁办开始将拆除重点指向老村的公共土地。村委会(社区)和村小组搬到拆迁办所在的新客堂,与其合署办公。村干部当时由拆迁办发每月补贴。村委会和村小组的做法是效仿街道办。同一时期街道办搬到承担宏仁城中村改造项目一级土地开发的螺蛳湾集团的公司所在地办公。街道办的办公室则被征收和拆除。老村内的公共设施,包括村委会、村小组办公场所、卫生室和村小学等都已经被遗弃。宏仁村的村庙——大寺成为下一个目标。当时村中小寺仍有僧人和信众在内活动,但他们也被当时的村小组领导率人上门去威胁,警告僧人尽快搬离,称寺庙作为村集体财产将要被拆除。他们的建议似乎不无道理。既然整个老村迟早要拆,那么先卖公地是较容易的一步。于是村委会提出大寺是一片无用公地,应当先卖了。事实上,宏仁大寺和小寺在拆迁开始前刚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被确定为区级不可移动文物。
虽然在新村被保全之后,大多数村民对于保留老村已经没有兴趣,但是拆大寺的建议仍然没有得到村民代表的同意。当时有一名村民代表说:“村子的庙就像一碗米线头上的罩帽,没(mou)得罩帽不叫米线,没得寺庙就不叫村子”。村民并无护卫村庙的强烈意愿,村庙的屋顶已经损坏,从里面能看到一片天。估计撑不过几次雨季就会自己倒塌。但拆迁办确实不再称要拆村庙了。拆迁办也在2011年从村里撤离。从2012年开始,在宏观调控房地产开始后,大拆大建已经停滞。宏仁新村没有被拆,老村也成了“烂尾”。直到2019年拆迁重启以前的数年时间,宏仁老村像一片“废墟”。从拆迁开始,村子的管理实际上由拆迁中涌现出来的5个民意代表操持。他们是些年纪从50 - 70岁以上的老人。后来“五个人”内部出现意见不合,剩下3个继续管理。这3个人的家庭在土改时有两人是上中农,另一人是破落的中等家庭。我们因此将他们称为“中农”之治。作者朱晓阳在几年前的一篇讲稿中概述过宏仁村发生的“废墟”上的自治。
小村因为出现相互角力而陷入一种时空的‘停滞——国家背景的城市化因抵抗和房地产市场不景气而不得不暂停,村落变成被正式系统抛弃的‘废墟。在因抵抗和其他因素,城市改造陷入停滞,形成政治真空的机遇下,乡绅 - 中农背景的精英能够利用拆迁‘废墟——一个具有时间延续的场所涌现。
在延续两年的大拆迁时期,宏仁村的正式组织(社区和小组)从村中撤出。 ‘废墟提供社区力量存在的空间,使乡绅 - 中农治理出现。2010 - 2012年,在‘无人区小村,有村民所称之‘五个人成为抵抗组织者。2013年换届选举,这3人成为村自然村组领导。2013年以来成为小组3个人中2人的背景属于上中农。应当指出形成社区力量的关键是一个空间上的社区——自然村组仍然存在。
有这样的社区存在,其内就有了乡绅 - 中农说话和定规的机会。小村前些年靠了这些人出头领导反拆迁,后来又在2013年基层换届选举时,将他们选进村小组和村民代表会(占将近三分之二代表)。1
2012年9月,3个民意代表向村民筹得3万余元修缮大寺的经费。他们带领一些村民将大寺的一间附属建筑修好,然后又修了一座新门头。当年底在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中,“五个人”之一的李绍荣被选为代表。与他竞争的对手是前村委会主任,时任村主任的父亲。数月之后,李绍荣又被选为村民小组长。过去几年以“在野”身份管理村子的“五代表”,从此成为宏仁村的“执政党”。李绍荣等民意代表是些政治“素人”,过去从未参与过村庄政治。我们在他当选后一方面想继续为他们出主意,以便其执政顺利;另一方面我们也对村民自治抱有希望。在此前两年多,李绍荣等民意代表已经习惯于定期召开“桥头上”群众大会和骨干“小组会”。2这个传统在其第一任期内继续延续。2015年9月他在一份述职报告中称:“从2013年换届以来,我们以为村民做事为主,凡事多听取村民意见、建议,大的事开村民大会通过,小的事开村民代表大会同意方可执行。已召开村民大会、户长会十三次,召开村民代表会议二十多次。”3
在最初,我们建议李绍荣和他的村小组班子(共五六人)每周开1次行政碰头会。这是模仿某些高校的院系每周行政班子联席会议。但是他们仅坚持了1小段时间就停了。李绍荣给出的理由是:几个人天天在一起,用不着每周再开一次会。2014年我们在村里的时候,曾参加过一次他们的行政联席会。我们当时发现会上有些人能讲话,但与李绍荣有分歧。李可能觉得会上很难互相沟通。李后来基本上不再召开这种行政联席会,更多地利用私下布置工作的方式沟通。当遇到重要事情时,则召开村民代表会。由于村委会和街道办将宏仁村的村民大会一向视为拆迁的对立面,因此总是不赞成召开。他们总是告诫李绍荣:如果要召开村民大会,必须先打报告,得到上级批准后才能召开。由于有阻挠,李绍荣后来召开村民大会越来越少。
李绍荣等人是以抗拆派身份入主村小组办公室。在其2013 - 2016年任期内,他与拆迁派领导的村委会基本上处于对立状态。在那个时期,村内的公共事业成就不多。但自2016年换届选举后情况有了转变。那一年李绍荣再次当选小组长,村委会主任则由3年前离任的党支部书记杨文明担任。杨属于本社区另一个自然村,在宏仁村没有人脉。由于李绍荣等民意代表的支持,杨以几十票之差赢过前村委会主任。李绍荣在此后几年与杨文明的村委会配合较顺利,村内的建设较多,例如在宏仁新村建成一条“夜市风情街”,并在2017年新村成为昆明市政府的微改造试点。宏仁老村的大寺修缮就是在2017年完成的。
宏仁村的两所寺庙虽然是挂牌不可移动文物,但在很长一段时期也是地方政府和拆迁方欲拆除的对象。在2014年左右,邻近地区的两所挂牌文物寺庙被以合并的方式拆除。2016年,当时接收老村改造的开发商也找到李绍荣协商,试图用邻村的模式,将大寺和小寺拆除。开发商建议在新村附近择地盖一所寺庙代之。开发商计划投资二千万元建新庙,新庙的地下将是改造项目的地下室部分。李绍荣拒绝了这个方案,区文管所也拒绝同意。李绍荣向区文管所打了一份要求修缮寺庙的报告。区文管所找来一家公司做了测量,并报了一个超过百万元的预算。区文管所领导本意是要拆迁方出这笔钱,但拆迁方根本无意解盘。眼看大寺的屋顶状况越来越糟,而拆迁方的计谋可能就是拖着让寺庙自己倒塌。在等了3个月(从6月 - 9月)不见文管所对报告批复后,是年十一假期期间,李绍荣带领一些村民开始修复村庙。我们当时也来到村里和他们一起施工。李绍荣本人是一个木匠,对于建房之类的木活很在行。修复工程到当年年底完成,总共花了约6万余元。我们请来区文管所负责人检查工程。他没有提出任何意见,并称可以为李绍荣等报工程款项。但不久以后,他说市文管局不批钱。原因是工程开始前没有报批。
我们多年以前就注意到大寺在宏仁村的地势价值。如以上村民代表所言:“村子的大寺就像一碗米线头上的罩帽”。从清以来滇池沿岸的一道风景是:村村有寺庙,家家有佛龛。宏仁的邻村金牌村在被拆平多年后,村庙虽空着,但仍然立在废墟上。拆迁人一般不会拆寺庙,除非如五腊和照西那样,许诺“搬迁另建”。
宏仁大寺的修复使一个重新集中“社区力量”(内在和外在)的场所出现了。在2010年,宏仁新村扮演了聚集社区力量的角色。2012年和2017年的大寺修缮也起到类似作用。观察大寺修復过程,我们发现李绍荣等参与者非常享受这项工作。虽然他承诺给参加者工钱,后来区文管所没有批准,但参加者都表示不给就算了。在修寺的那几个月,李绍荣和六七个60岁以上的老人天天来工地干活,中午按过去给集体或东家干活习惯,由一两个妇女做饭给大家吃。整个就像生产队时期的犁田组活动一样。我们在那期间拍摄的影像记录(后编入纪录片《老村》)也显示出修寺如一次其乐融融的活动。从乡村振兴的意义说,修寺还提供了本地化和低成本的乡村古建筑修复路径。依靠本村匠人、老人和妇女参加,利用废旧材料:从屋顶拆下的旧瓦到各处市场淘来的废旧木料,基本上是物尽其用。简言之,修寺是一个低成本、可行和可持续的传统乡土建筑修缮案例。
几年以后,当我们回顾宏仁大寺修缮这一事件时,深感它给今天的乡村振兴提供了一些可以借鉴的经验。今天困扰乡村振兴的一个问题是乡土建筑(包括民居)如何能够使其功能提升到城市生活水准的同时,其修缮成本又比较低廉。例如我们参与的中国城市规划院的安徽潜山项目设定每间屋子不超过5万元作为标准。要达到这一水准,除了其他因素,对于挂牌文物和申请政府资金的项目来说,很重要的是如何绕过僵硬政府采购招标程序。潜山的做法是市委和政府出面承担责任,允许省保文物杨家老屋修缮采取变通做法,以村理事会作为项目监管人。宏仁大寺工程的做法则是由村小组长(也是工程负责人和大木匠)负责,采取一面上报,一面施工方式进行。在最后批不到资金的情况下,工程也已经完成,成为一次“自愿行动”。
宏仁村大寺修缮是在非常时期和特殊条件下完成。它是在拆迁“废墟”和乡绅 - 中农治理下出现。特殊条件使乡绅 - 中农成为社区力量的支柱和领导,并使外来学者能与社区自治组织者形成共识,一起探索社区营造的撬动点。
四、直播:阳光下的“拆”
2010年“保新村”的主要组织者莫正才老人,却在十年之后不得不只身保卫自家老宅。十年前他得到全村绝大多数人的支持和拥戴。这种说法不夸张,当时包括新村已经签字的78户中的绝大多数,也包括他的儿子及其家庭,都站在莫正才身后。但在十年之后,莫正才呼吁不要拆了祖宗留下的遗产时,显得十分孤单。除了仍坚守老村的几十户外,村民对莫正才的诉求基本上不过问,他的儿子及其家人则与莫正才成为对头。这一次莫家宅院是以“传统一颗印”和“百年老宅”之称得到与他无干系的文物保护活动者的支持。这栋被称为宏仁230号的“一颗印”在2020年10月10日,因为B站直播了未遂的拆除而广为人知。莫正才对于这所宅院的自觉护卫则要回溯到21世纪初。2007年上半年,在拍摄纪录片《故乡》时,我们偶然进入莫家四合院,在那里对当时不认识的莫正才进行了访谈。莫正才用爱惜的口吻讲了这幢宅院的历史和现状,然后提到他给有关部门写了要求保护的申请。但是他没有收到过回音。三年以后(2010年),由于莫正才站出来保新村,并成为村里的5个民意代表之一,从此以后我们才熟悉起来。在以后几年,莫家院子成为村民抵抗的“小组”聚会讨论的地方。每当外面来人调查或访问,总会来到莫家宅院的“油春”(堂屋前的空地)上与莫正才攀谈。
我们已经在别处报道过莫正才及其家宅的故事1,本文将着重讨论莫家宅院如何成为一个有普遍意义和影响力的符号。
莫正才其人其宅是我们多年来在其他地方很少遇到过的“理想”案例。莫正才是宏仁村上个世纪初的乡绅的曾孙,一颗印宅院是其曾祖父于1915年建盖。莫正才从出生就居住于此。到昆明的某国有农场工作20余年,但家仍然在此。他在20世纪90年代初退休后,又回到这所房子常住。这所宅院的其他几户莫家继承人或迟或早将房产卖给留下的人家,或是搬到新批的宅基地建房另住。这些人包括莫正才的儿子。他也于1994年搬出宅院。从此以后,这里只有莫正才一个人居住。除莫家外的房主,在2010年都与拆迁办签了拆迁协议。莫正才的儿子也背着父亲将莫家的部分签给了拆迁办。这一“子代父签”的协议,被莫正才发现后要求拆迁办撤回。拆迁办表面称撤了,实际上没有。2019年拆迁办依据这份协议要拆掉莫家宅院时,莫正才向区法院提出行政诉讼,要求撤销协议。22007年以前莫正才已经向政府有关部门申请将老宅作为文物保护。这所宅院的“一颗印”形制完整,且在一百年间几乎没有任何添加或改造。莫正才对此宅爱护有加,使老宅不仅十分完好,而且生机盎然,犹如“活”物。一般外面来人,即使不熟悉主人或传统建筑,见到这幢老宅也会立刻感到有“价值”。正是有直接可感的“物性”,在2020年莫家老宅及其主人经历着几乎被拆的时刻,B站“直播”下的老宅使在场或不在场的观众亲眼看到一件标准的文物将如何遭到毁灭。这幢老宅给人的整体鲜活印象深刻,以致后来到莫家考察的省文物专家,认为不仅房子要原址保护,连院子里的一棵桂花树也属于保护范围。我们的评价与这些专家差不多。我们多年与这幢老宅的接触,感到其价值就像从土里长出来的,土坯墙让人能触摸到其生命。我们甚至觉得这座老宅的土墙有更重要的保留价值。因此当拆迁办一度以“搬迁”保护为由,准备拆下其木构搬走,扔弃老宅的墙体时,我们对此不认同,并与主张这种“搬迁保护”方案的官渡区文管所负责人在电话里冲突。后来主张原址保护的文物专家们要求对村内另一幢仅剩墙体的老宅也要求原址恢复。他们可能直接感应到了土墙的“呼唤”。
至于莫正才本人,他的思路清晰,有理性,对于法律和政策的熟知,以及他不亢不卑的态度等,总会给任何不试图以势压人的官员或观众留下印象。例如莫正才的诉求是只要保留下这所祖宗传下的老宅就可,无论谁来保护都行。他绝无一般印象的钉子户形象:以房屋为由索要更高补偿。
莫正才个人的形象及其现身说法、百年老宅的物性、近十年来许多外来访者的印象、媒体对莫家老宅的报道,再加上社交媒体对拆除事件的直播,使这幢不可避免地要被拆掉的房子,突然变成广受关注,不断发酵的系列“宏仁事件”的核心。这幢老宅在2020年10月10日拆迁行动被阻后,才过了一个多月就被区文管所确定为“区级不可移动文物”公示。公示称:“经专家评审一致认为,官渡区矣六街道宏仁村230号民居为相对完整的昆明地区典型的‘一颗印建筑,其建筑形制独特,现存木构件雕刻精美,具有一定的历史和建筑藝术价值。”1到年底,老宅已经被正式确认为文物,并被安排了抢险保护措施,例如修建排涝水沟和遮雨钢棚等。在2021年经由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调解,莫家老宅被以产权置换方式完全归国家所有,莫正才及其子以共有业主获得房屋补偿,莫正才本人还得到老宅修复后的“居住权”。这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相关条款新提出的一项居住者权利。22022年区文管部门的落架并抬升地基高度的计划没有得到专家的同意,最后的区文物局红头文件规定:“遵循最小干预的原则……对宏仁村230号民居进行原址原标高修缮。”3目前这项修复工程已经开始。
莫家老宅的今日似乎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但是这栋老宅不像此前的新村和村庙修缮,是可以随处复制的村建例子。由于老宅被列为不可移动文物,其修缮成了须通过政府招标,并以巨资投入才能完成的项目。虽然区文管部门一直想要的抬升地基(等于重建)方案没有被采纳,但其投资(包括此前搭临时保护装置费用)预计应在百万元以上。相比之下大寺的修复仅区区六七万元。如果仅就此而言,这所房子因抗拆而起纠纷、冲突不断升级,最后演成公共事件,然后不得不以更高代价摆平作为结果。这完全非我们所愿,也非莫正才所愿。一定程度上倒是证明其子所言:“列为国家文物?我们如何修得起。”莫家老宅,按莫正才和村里修缮大寺的李绍荣的看法,基本上是一幢完好的建筑。如果用当地工匠,其修缮的花费不会比大寺更多。但是它现在却向乡村公众表明乡村传统建筑想走上当地业主可负担的文物保护之道是不可能的。
通过莫家老宅的案例,可以看到宏仁大寺修复和安徽潜山传统建筑修复所探索的社区自主,或社区与政府合作的可持续发展经验,对于乡村振兴扎实落地弥足珍贵。类似这样的案例我们在昆明市内文明街历史街区也遇见过。在那里政府最终同意私人业主可以按照保护规划自己修缮房屋。我们访问过一个自己修缮的业主,她和另外两家邻居一起做,结果每家花了25万元就将一楼一底的商铺房修好。这些房子相比其他同一街上以类似莫家老宅方式修复的传统建筑,更好出租。原因很简单:投入成本较少,相应房租便宜。
五、讨论
对以上社区营造和介入活动发生与“社区”的勾连做了以下梳理。
首先是一些相关事件及其时间点。2013年,在“保新村”行动的撬动下,村小组换届选举后,村小组作为“实体”的地位得到增强。村小组组长在第二任期(2016年开始)与村委会领导合作较顺畅,双方协作做了一些改善新村环境的项目。例如将昔日排洪沟边的夜市升级改造成一条“风情街”;2017年宏仁村还成了昆明市的“城中村微改造”试点村。从2010年至2019年,北大社会学系师生和云大师生也参与了宏仁村的社区治理。我们经常为村小组提供咨询建议,参与了老村大寺的修缮和莫家“一颗印”老宅的保护。从2013年至2019年,云大教师组织的社工“云南连心”在村中开展活动,并在大寺建立了一个帮助打工子弟的活动中心。
其次是社区营造和介入活动的区域。宏仁村的社区营造和介入活动是在“社区”,具体言之,即自然村组层面实施。自然村组是社区力量依靠的政治和社会框架。介入力量在前期是与“民意五代表”对接,后期基本上是与村小组对接。但宏仁村个案与同时期全国的趋势有所不同。在国家范围,村民自治20年的历史是自然村组日益变得“有实无名”的历程。称其“有实”是指自然村组的“身子骨”仍然在。自然村组仍然是人伦 - 地缘一体的单位;仍然是土地所有权的边界;仍然是仪式性活动(婚庆、丧葬等)的中心。因为这几点,自然村组是乡村社区的基本单位。称其“无名”是指自然村组被国家治理者视为虚体。换句话说,21世纪以来自然村组的历史是在政治上“被虚体化”的历史。在一般的政治组织研究中,自然村组往往被称为“虚化”组织。大多数乡村研究者经常将行政村的干部和村小组的干部混在一起谈论。而在实践中地方政府为了便于管理和控制基层,则努力使村小组虚体化,将其容易管理和控制的村两委做实。在自然村组虚体化的治理趋势下,宏仁村依托村小组/自然村的前两次介入活动基本上是发生在拆迁停滞时期。当时村落因社区(村委会)等正式组织被拔根而去,并因景观上已经部分被拆,而可称之为双重 “废墟”。但在同一时期村庄共同体因外部压力而显得内部凝聚力很强。
一旦非常时期过去,村庄重新成为矛盾的聚合处,“社区性凝聚”也随之消散。随着村庄回到常态,正式组织重新回归和控制增强后,村小组的自治权利被逐渐侵蚀。这些问题也包括在换届选举时增加由乡/街道办对村委会和村小组候选人进行“审核”的环节等。例如在审核时,提出“男55/女50岁以上不应成为村委会/村小组长候选人”作为条件。1再例如以户口限制退休还村的公职人员参加换届选举。2从今天的角度看,这些地方土政策是与提倡乡贤和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振兴的政策相龃龉的。因为以上地方政策欲排除的村庄管理者人選正是当地的乡贤,在宏仁村是指李绍荣和莫正才这两位。其中最严重的一个问题是村小组/自然村重新由实体再次“被虚化”。这方面如随着治理下沉,村两委领导越来越变成“准公务员”。最近一些年村两委主要领导已经由地方财政发工资,做村领导时间超过20年有退休金。这些措施已经使村领导公务员化。最近更是将国家的哺农资源或项目分配都给到行政村/社区这一级。例如宏仁新村的微改造,虽然从产权和属地来看,村小组都是基本单位,但项目却是由社区(行政村)对接。
近年来治理下沉的另一核心内容是鼓励村领导人“党政一肩挑”。与乡村治理下沉并进的另一面是“村政上浮”,即“虚体化”自然村/村小组。例如收回村小组公章,由村委会/社区代章。乡村治理下沉犹如双刃剑,一面是有效,另一面则是问题。有效方面很明显:行政上浮到行政村(社区)能集中行政资源,提高行政效率;做实村两委能解决村小组/自然村缺人、缺钱和松散问题;能有效推进政府政策或项目落实。问题的一面则是:村民自治基本单位“行政村”或“社区” 实际上缺乏“社区性”,与村民“自治”的要求不符合。而如上述,以年龄限制和户口限制有道德威望的年长者进入村庄管理,村小组虚化使对侵犯村民利益的政府政策或项目失去最后一道抵御防线。更要紧的是,在本体政治时代,自然村组还有抵御非人类或环境风险的“地势”意义。这方面是行政村/社区无法替代的。1
六、结语
回顾滇池东岸宏仁村最近12年的社区营造历程,以“物”为目标的本体政治是我们和当地人遵循的进路。以上3次介入活动的重心都是放在当时研判能撬动社区力量形成的关键场所,或者说政治地势中的穴点。如何形成对地方政治局势及其关键场所的认识,则是科学与艺术结合作业的结果。现将这些作业依据的一些重要原则列举如下:
其一,进行深入和长时段田野工作,在田野中测度(mapping)并认识到关键场所及其“地势”或势位。 例如本文所涉的3处场所:新村、大寺和莫家老宅都是我们在多年参与当地活动后,获得的见识。我们将这种“参与活动”当作测度方法的核心。通过这种测度获得的对地方世界的见识要比一般的单一社会调查(survey)所获要更深入。我们认为在这种测度中,要有准备长时段持续的介入的决心,这样才能使社区力量不断聚集、兴替和可持续。
其二,从当地人视角的最重要和最被关注的场所营造开始(不以抽象的或意识形态目标为起点)——从此可寻得“社区力量”,并撬动其他后续营造活动。如本文开篇所言,我们关心乡村振兴中的“社区力量”如何能够聚集起来。本文是以“物”的介入为内容,因此建议要去发现在当地人眼光中具有势位重要性的场所。乡村建设介入的撬动点往往应该设定在此。应当强调,一般的建筑学者和规划学者出于专业训练的习惯,每到一个项目点也都会将探寻和确定项目撬动节点为目标。但是这些专业人员眼中的节点并不一定是当地人眼中的势位关键处,这些节点很可能是“奇异景观”但不负载地方的故事和历史。
其三,“外来人”要与当地人一起紧密工作和研究问题,找出解决之道。这个原则的关键是外来人和当地人要形成相互交流的习惯。我们在过去十余年之所以能较正确地认识一些关键的干预撬动点,是与常年的双向交流保持有关。此外,对于人类学者来说,将“向当地人民学习”常挂嘴边已经是常态,但在介入工作场景下,重要的另一方面是也要坚持自己的立场。应当相信在我们和当地人知识之外,还会有普遍的知识。我们或者当地人都可能会与这种普遍真理失之交臂。
[责任编辑:曾祥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