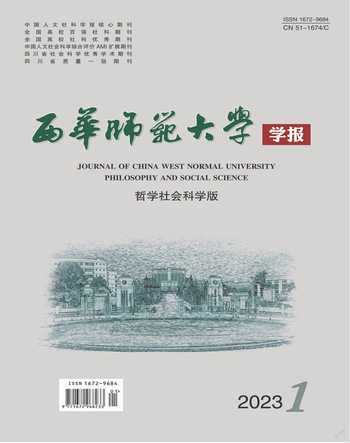情感结构与时代症候:重审1920年代丁玲北京时期的情爱书写
魏巍 李静
摘 要:对于像丁玲这样受新文化思潮感召来到北京的知识青年来说,其情感结构已然不同于“五四”初期激烈张扬的政治青年,飘零无依的孤独、理想抱负的落空、生存糊口的艰难、前途未可知的迷茫,集合成了丁玲这一代人的共同体验。丁玲早期在北京的创作既可以说是对时代情感结构的一种继承,也可以说是一种反拨,通过情爱书写,丁玲对其时流行的“感伤主义”与现代女性成长之间的关系作出了自己的判断:徒有感伤情绪在现代社会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而作为女性恋爱的客体,男性群体也并不能满足新女性恋爱的要求,“男性气概”的失落,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正要求女性变得更强大;在以经济地位决定男性气概的社会,对于经济上尚未完全独立的女性来说,无论是“浪漫爱”还是“灵肉一致”的爱情,其实都不过是水中花、镜中月。
关键词:丁玲;北京时期;情感结构;时代症候;情爱书写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2-9684(2023)01-0074-08
“情感结构”一词最早出现于雷蒙德·威廉斯和迈克尔·奥洛姆1954年合著的《电影序言》,用以表达在一定时期里大众对文学、艺术的感受和体验。在《漫长的革命》中,威廉斯进一步对其内涵做出解释:“正如‘结构这个词所暗示的,它稳固而明确,但它是在我们活动中最细微也最难触摸到的部分发挥作用的。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感觉结构就是一个时代的文化。”[1]57也就是说,“情感结构”是同一时代的人们共同的情感体验,每个人都置身其中,却难以感觉到它的存在,但每个人都在不由自主地照此行事。此外,威廉斯更强调一代人有一代人之情感结构,“新的一代人会以自己的方式对他们所继承的世界作出反应,他们吸纳许许多多可以追根溯源的传承,再生产可以被单独描述的组织的诸多内容,然而却以不同的方式感受他们的整体生活,将其创造性反应塑形为一种新的情感结构”[1]57。
“五四”落潮后,作家们的“情感结构”确实发生了微妙变化。对于像丁玲这样受新文化思潮感召来到北京的知识青年来说,其情感结构已然不同于“五四”初期激烈张扬的政治青年,飘零无依的孤独、理想抱负的落空、生存糊口的艰难、前途未可知的迷茫,集合成了这一代人的共同体验。文学创作中则普遍弥漫着一种“质疑五四”的情感主调,“怀疑”成了人物的主要情绪。“到了这个时候,历史才终于提供了必要的距离,使小说家们得以看清楚表现为历史过程的‘五四,大革命”[2]77。社会动荡、新旧观念交锋与磨合、大革命失败等诸多时代浪潮与个人遭际相结合,也点燃了丁玲的创作欲望,她捕捉到了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社会内部的喧哗与骚动,将之融入了小说人物的内心世界。
一、“感伤”情感的质疑与否定
20世纪20年代初,郁达夫就已有意识地将sentimental引入、化用到新文学乃至“五四”后期的文化场域,郁达夫自叙传、零余者式的感伤书写也吸引了众多模仿者。作家们开始普遍倾向于在小说中展示自己敏锐的神经,用感伤的笔触,率真坦诚地表露自我的伤感情绪,以引发一些乐于体验感伤、欣赏哀婉情调的同时代人的共鸣。
作为一种审美取向,这种感伤主义、忧郁多思最初往往被视为是一种特殊的情感美德,是道德敏感、心思细腻、情感丰富的表现。但一种写作风潮发展到极致往往会偏离开始的走向而往反方向发展,这样一种最初的“真”到后来反而成了被用来吸引眼球的“假”。诸多畅销故事开始竞相连篇累牍地罗列善感多思的主人公们催人泪下的不幸遭遇,情的话语、痛的言辞随处可见,歇斯底里、哭泣、晕厥也成了诸多作家争相“表演”的“节目”。显然,虽然浪漫感伤是觉醒一代最为深刻的情感,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情感结构”,有着普遍的历史合理性,但感伤主义的泛滥最终却导致了新文学同质化作品的大量增加,艺术上的粗疏与重复,无疑暴露了社会的浮泛之气。早在1923年,闻一多就曾于《泰果尔批评》一文中指出:“他若是勉强弹上了情绪之弦,他的音乐不失之于渺茫,便失之于纖弱。渺茫到了玄虚的时候,便等于没有音乐!纤弱底流弊能流于感伤主义。”[3]128尽管闻一多的批评指向的是泰戈尔,但是考虑到泰戈尔当时在中国文化界的影响,以及中国本土作家一时的创作倾向,闻一多对泰戈尔的批评无疑也可以看作是对当时文坛的一种倾向性批评。30年代,茅盾又以“创作三部曲”(《有志者》《尚未成功》《无题》)对这种带有投机性质的“颓风”予以了更具戏谑性的嘲讽[4]。回到《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不少研究者将它们与《少年维特之烦恼》并联,认为它们共同代表的是一种渴慕真正爱情而不可得的苦闷呻吟。而实际上,梦珂、莎菲的情感态度虽或多或少地显露了某些典型的感伤浪漫姿态,但特意为她们设置的爱情挫折、人生困境却更为真实地表达了丁玲对感伤思潮的反思和再定位。
以《梦珂》为例,最开始梦珂就是纤细柔弱、多愁善感的,在表哥晓淞面前有着娇滴滴的姿态,像小孩子一般柔弱,苍白而憔悴,惹人怜惜,状态上的虚空、懵懂也使她显得更加纯洁,最集中的表现是她和表哥晓淞一起去电影院看电影的情节。和表哥一起观看《茶花女》时,梦珂一边聚精会神紧盯荧幕,一边体会从前所看的这部小说,把自己化身女伶认作茶花女去分担那悲痛,沉浸在一种“命运共同体”的伤感中,从而和周围朝着小镜搽粉戴着宝光四射戒指的太太、卖香烟糖果的小贩、眼光追随女人影子的男人拉开了距离,她沉醉在自己的伤感情绪里无法自拔。但正是这种莫名的感伤、刻意酝酿的悲痛使梦珂根本无法看清周围的世界,其实,这个电影院里的众人都各自心怀鬼胎,表哥更是对梦珂虎视眈眈,而沉浸在茶花女“修眉,大眼,瘦腰,那含愁的笑容,舞态……”“可悲的身世”[5]19里的梦珂却浑然不知。在得知被表哥晓淞“背叛”之后,梦珂的一系列反应也带有明显的感伤主义惯做的姿态,她“躺在床上像小孩般的哭了起来”,把之前收到的甜情蜜意的信扯得粉碎,“满床尽是纸屑,看见纸屑,心越气了,又把纸屑撒满一地”“哭了又笑,笑了又哭”“躺在软枕上犹自流泪”[5]31。自然也有晕倒的情节,然而可笑的是,没人发现她晕倒,也没人在意,最后直到自己清醒打开房门,“门外面只有那头走廊射过来的灯光,映在墙上,现着如死的灰白的颜色”[5]31。感伤主义导致的一系列矫枉过正的感情,显然使梦珂难以体察他人、理解社会,更无法看清她自己。《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莎菲和真实的自己更有着很大的距离,她的日常生活其实庸常得近乎可怜,她总是千方百计地想要让别人“懂”自己,但事实上她也并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一方面莎菲极度渴望寻求别人的理解,另一方面又不断地施展各种小心思来破坏任何理解的可能,她甚至都不能预料自己行为的瞬息万变,前后的矛盾态度只能更加凸显其情绪的起伏不定。
如此看来,感伤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纯情想象无疑使莎菲、梦珂们失去了知人和自知的判断力。她们不仅识人不清,误读了表哥晓淞和凌吉士,凭借自己的想象轻易地给身边的每个人定位,并在很大程度上误读了自己。表哥晓淞并不是与梦珂初次见面时所表现的那般谦卑诚恳,凌吉士也并非如莎菲开始所想的那样,是一个说话就会红脸受窘、一腔热忱的重情者,甚至可能她们本人也并不如小说所传达出来的那样孤傲狷介、超凡脱俗。在最开始,梦珂和莎菲对诸多男性的感情都不能说不真挚,爱情也确实令她们对生活有了新的期待。但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她们都把纯真的感情、浪漫的幻想放在了并没有真情的男性身上,且一厢情愿地认为自己在对方心中有着至高无上的特殊位置。实际上,她们对这些男性而言并没有什么特别,这些男性对她们的感情也并没有她们想象的那样深沉,更缺乏对她们应有的尊重。梦珂被表哥晓淞和澹明当成是相互竞争的“猎物”,梦珂走后他们并没有太多的惋惜留恋,因为“澹明有杨小姐可追随,而晓淞是除章太太外还有两个很有希望的女朋友”[5]33。凌吉士很多时候是把莎菲当成“志同道合”的倾听者,满足的是自己的虚荣心,他喜欢的是女性柔顺地接受他浅薄的情意,听他说自己津津有味的享乐,以及“赚钱和花钱”的人生意义。
是幻想终究会幻灭,没有现实基础的想象如同谎言。表哥和凌吉士真面目的暴露最终宣告了梦珂、莎菲浪漫感伤想象的失败,小说在这方面的叙事似乎有一种隔空对话之感,梦珂、莎菲执着于寻求爱情、寻求理解和真诚,但丁玲却一直强调“没有爱情”“没有真诚”,这种幕后音时刻在暗示着她们的悲剧结局。揭破表哥、凌吉士等人的虚伪、浮滑之后,后面的叙事重心也并没有放在对他们的尖锐批判上,而是通过梦珂、莎菲们的无可选择进一步强调了现实中虚无缥缈的感伤,以及一系列浪漫想象的虚妄本质。
这种严酷的叙述方式、女主人公类同化的命运结局并非丁玲刻意为之,而是因为她看到了感伤思潮对个体思想行为影响的顽固性,这种气质一旦形成,就很难轻易去除,而一旦认清现实,个人将会面临更大的自我怀疑、自我否定的深渊。梦珂最终对未来不再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她不仅能清晰地看到自己的处境,对社会也有了一个辩证清晰的认识。从姑妈家离开后,梦珂不得不试图融入社会,同时开始了自我重建与主体回归的旅程。可以想象,这一环节无比艰巨,梦珂的从影以及之后可能面对的生活必将让她经受心理上仪式般的洗礼和磨砺。“莎菲女士的日记”也终于结束,因为“莎菲已无需乎此——用眼泪来泄愤和安慰,这原因是对于一切都觉得无意识,流泪更是这无意识的极深的表白”[5]75,这样一个不再反复无常、“决计搭车南下”的莎菲,隐隐约约透露了一种要告别感伤的决心。
如丁玲所感慨的,“像那些才女们,因为得了一点点不得受用,便能‘我是多愁善感呀,‘悲哀呀我的心……‘……做出许多新旧的诗”[5]68。这种对感伤的拒绝,与社会革命浪潮中的群体转向有关。扩展开去,也可以看到一种不断变化着的情感结构,感伤已不再被需要,或者说,作为曾经的一种普遍性情感结构,在不断变化着的文化场域中,感伤的诱惑力已然失效,转而成为一项被否定的“传统”。
二、传统与现代的对立:悄然失落的“男性气概”
丁玲早期诸多小说中的男性可以被概括为是一群失去了“男性气概”的群体,不管是《梦珂》中的表哥晓淞、澹明,还是《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凌吉士、苇弟,皆有如此特性。但这里的“男性气概”却值得被细细考量,它不仅应被细致地区分为“传统的”和“现代的”,从对它内涵的不同认定方式也反映出同处于一个时代的人不同的价值立场。一直以来,丁玲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已得到足够的重视并被反复诠释,而这些类型化男性形象却未被注意,即使提到也大多只是被以庸俗、卑劣等形容词来简单概括,又或者被当做是刻意地将男性贬低丑化以抬高女性,彰显女权。事实上,作为一种惯性写作模式,其中的男性形象很值得关注,对那些简单地予丁玲作品中的男性以批判和诟病的结论也应更加谨慎。
在20世纪20年代,对“男性气概”丧失的书写其实并不少见,甚至呈现出一种集体化模式,冰心、庐隐、冯沅君、凌叔华、陈衡哲、石评梅、苏雪林等“五四”第一批女性作家的小说文本中,男性形象整体就呈现出一种弱化或丑化趋势。这样来看,说到底,“男性气概”尽管与人格个性密切相关,却不是单个人的特征,更是一种群体共性,是一个社会在一定时间段内所达成的共识。这同样可以理解为一个时代的“情感结构”。可以说,丁玲对“男性气概”丧失的书写并不仅仅只是出于对男性的打压贬低或是对女性的重新建构,而是道出了一种社会现实,一种实实在在存在的群体现象。就此而言,一系列仅仅把“男性气概”看作是与“女性气质”相对的概念,并把它看作是父权制、男权主义同谋的研究,似乎忽略了“男性气概”的文化历史本源,其对两性关系研究的角度也明显过于狭隘。如果将丁玲笔下的男性群体和沈从文对都市男性的描述相对照,就更容易理解类似的这种父权制、男权主义同谋表述的不相适宜。
作为同是从湖南进入北京、上海的作家,沈从文曾在小说中把男性划分成两种,一种是都市知识分子,这部分群体多为“雄身而雌声”的“阉宦”[6]36,在沈从文笔下,这部分人既没有爱的能力也没有性的能力(《蜜柑》《八骏图》);另一种以湘西男性为模本,这一类人可能并没有读过多少书,但他们敢爱敢恨,敢打敢杀(《夫妇》《虎雏》),这与沈从文在都市社会看到的男性有着根本区别,也正是这一点,划分了沈从文对“男性气概”的个人化认定。显然,沈从文笔下的“男性气概”可以作为丁玲小说中男性人物的一个反面参照。两人相似之处在于,他们所共同看重的都是一种不言自明的非物质性的、传统的、精神上的崇高和自由感,不被任何外界俗事俗物所牵绊,荣誉而有尊严,用哈维·C·曼斯菲尔德的话概括来说,“男性气概不仅仅是进攻性;它是为了发展某个主张的进攻性,男性气概会赞同这个原因。这个原因源于具有男性气概的人所要面对的危险,因为如果你冒着生命危险去挽救自己的生命,那么你的‘生命必然是某种非物质的原因,是某种形式的抽象正义。你依然想活下去,但是要有荣誉有尊严地活下去。你的生命不是通过自然的命令强加给你的,而是你自己选择的”[7]70。但很明显,丁玲笔下的男性既没有这种“为了发展某个主张的进攻性”,也没有“某种形式的抽象正义”的成分,他們被时代的另一种与之相左的价值取向所左右。总的来说,沈从文和丁玲都并没有将这种“男性气概”放到女权主义或权力关系的对立面,他们不是与“女性”截然对立的存在,而是作为一种“社会性”的普遍存在被纳入到了“群”的概念之下,不约而同地指向了对男性庸俗、市侩的社会性批判。
值得注意的是,一直被称为是“庸俗、市侩、卑劣”(这些词汇也通常被学界用来描述沈从文笔下的都市知识分子)的凌吉士为何可以直接甚至洋洋自得地和莎菲说起自己想要的生活与所拥有的地位和钱财,谈自己的志趣,说自己“热心于演讲辩论会,网球比赛,留学哈佛,做外交官,公使大臣,或继承父亲的职业,做橡树生意,成资本家……”[5]63,这已经不能再简单地理解为一种炫耀心理,或是一种男性对女性的性别优越感,而是因为在他的认知里,在唯金钱、身份、物质为标准的世俗观念中,当时的女性应该倾慕这样的男性。对于凌吉士,情感上的依恋也不再是因为喜爱,更多的则是超出喜爱之外的物质和欲望。在莎菲看来,凌吉士并不懂得真的爱情,他既没有真诚地爱过任何一个人,也不曾得到过任何一个人真诚的爱,“他还未曾有过那恋爱的火焰燃炽”[5]63,他不会为了所谓的爱情改变一直以来的随心所欲,更不会像莎菲那样因为左右犹疑而小心翼翼,只会因为父亲未曾给他过多的钱而耿耿于怀。在凌吉士看来,莎菲也是“奇怪的女子”,他所以为奇怪的,是莎菲“破烂了的手套,搜不出香水的抽屉,无缘无故扯碎了的新棉袍,保存着一些旧的小玩具”[5]71,他不能想象莎菲单一甚至枯燥乏味的生活世界,也不会理解她那些一直保存的小物件背后可能包含着的珍贵回忆。他无能去体会,莎菲也不希求他能够懂得,所以从未向他说过一句“我自己的话”,而这个“我自己的话”就是凌吉士还尚不能懂的另一种价值观。
对于凌吉士这样的男性,仅仅进行简单的主观道德批判是不够的,种种迹象表明,在根本上,凌吉士的道德价值观与其认同和实践的这种以物质、金钱、利益为规范的社会流俗取向有着密切关联。他对待女性的方式、感情的态度、处世的准则自然与其自身素养有关,但导致其道德行为失范背后的社会伦理导向更值得关注。
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延续的文化概念,一代代的传承和建构,“男性气概”已然早已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大众取向,内涵着男性天然的人格尊嚴和身份属性。作为“情感结构”的一个重要方面,不同时期对“男性气概”的评价标准也有所不同,随着时代的革新,“男性气概”的判断标准发生了由内在到外在导向的转变。与较为看重品格和道德传统的“男性气概”相比,市场上的成功、个人的成就、财富等因素在现代社会逐渐凸显并被看作是男性身份与价值的首要标志,带有明显的功利性和外在指向性,和传统“男性气概”的内在要求大相径庭。从对权力、金钱、地位的强调可以发现,当时社会普遍认可和推崇的还是一种外在性“男性气质”,理想中的男性也应当是竞争力强和有经济实力的。表哥晓淞、澹明、云霖、凌吉士清一色的相貌出众、学业有成、头脑敏锐,与很多同龄人相比,他们有着较为优越的条件和看似光明的前途,在外界看来更是英年才俊、年少有为。正是在这种社会眼光支配下,凌吉士才可以自信而毫无掩饰地坦白着自己在莎菲看来庸俗至极的“理想”和“抱负”,他并不会意识到,这种在世俗看来的“成功”,在莎菲这里是无效的,他所极力展示的并不能给他带来真正的尊重和景仰,相反,在莎菲眼里,他不仅卑鄙、市侩,是可笑更是可怜。从根本上说,莎菲与这些男性人物之间的矛盾就在于传统与现代的冲突。莎菲认同的是传统观念上的内在性“男性气概”,类似于“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而社会流俗愈加普遍认同的是金钱、权力、地位、外表等外在性“男性气质”,两者针锋相对、格格不入。
大多数置身于流俗氛围中的人都很难具有清醒的反思和批判意识,所以也就无法对既有的流俗观念进行背离或超越,更无法恪守内心的本真。凌吉士极力表现的优势并不会改变他在莎菲心目中已经标记上的丑陋形象,乃至后来他倾尽全力表演的深情也并不会让莎菲有丝毫动摇,因为他所遵从的利益信条早已泯灭了他心中本该有的人与人之间基本的真诚交往准则,也相应地丧失了对社会的责任感,这样的人让莎菲深感失望。虽然苇弟在外表、经济、社会地位等方面都不如凌吉士,但他最为可贵的一点在于“真诚”,而这一点点的“真诚”,正是让莎菲尚有一丝愧疚感的重要原因。然而,尽管心怀愧疚,莎菲仍然不会喜欢苇弟,原因仍然在于,苇弟太缺乏“男性气概”。在莎菲面前,苇弟唯一的本能就是哭,这恰恰是莎菲所讨厌的,“请珍重点你的眼泪吧,不要以为姊姊像别的女人一样脆弱得受不起一颗眼泪……”,甚至公然告诉苇弟,“还要哭,请你转家去哭,我看见眼泪就讨厌……”[5]45,男性的女性化特征在苇弟身上表露无遗。对于莎菲,可悲之处就在于,她所认同的“男性气概”在崇尚经济、利益、实利性的社会无法得到真正的建构与实践,而她所期待的“理想”男性也就并不存在。对爱情的失望最终使她决计搭车南下,“在无人认识的地方,浪费我生命的剩余”,“悄悄的活下来,悄悄的死去”[5]78。
三、“欲望”问题:时代的症候
对情爱欲望的大胆表露无疑构成了《莎菲女士的日记》的重要内容,这是理解该小说及莎菲本人的关键,也是这部小说引起轰动的最根本原因。自茅盾评莎菲是“‘五四以后解放的青年女子在性爱上的矛盾心理的代表者”[8]215之后,很多研究者都对其中的性爱欲望有所关注,如中岛碧在《丁玲论》中说道:“敢于如此大胆地从女主人公的立场寻求爱与性的意义,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丁玲是第一人”[9]170,史书美也以《莎菲女士的日记》为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以女性的角度陈述女性为性的主体,而不是性的客体。”[10]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诸多类似评论中的具体分析内容却大多执其一端而难见其全貌,要么集中于情欲表现的大胆而忽略了莎菲内在心理的犹疑苦闷,要么关注其犹疑苦闷而故意淡化其情欲描写的重要价值,很难对莎菲心理的“矛盾”做出全面理解。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结果,就在于对“五四”时期小说中欲望内涵的探究尚未深入。
首先应该明确的是,莎菲是被凌吉士的外表深深吸引而产生了强烈欲望,“我看见那两个鲜红的,嫩腻的,深深凹进的嘴角了。我能告诉人吗?我是用一种小儿要糖果的心情在望着那惹人的两个小东西”[5]47,以及后来的妄想“假使他能把我紧紧的拥抱着,让我吻遍他全身,然后他把我丢下海去,丢下火去,我都会快乐的闭着眼等待那可以永久保藏我那爱情的死的到来”[5]71。这两段在今天读来都不免让人心生惊叹的语句,可想在当时又会荡起怎样巨大的波澜,而一个女性竟然能毫无顾忌地表达自己内心近乎于情色的欲望,也很可以看出其不顾一切的自由大胆。
“五四”时期,崇尚自由、性爱解放的言论确实随处可见,以1918年5月周作人翻译的日本女批评家与谢野晶子的《贞操论》和12月发表的《人的文学》为开端,在《人的文学》中,周作人把性爱视为“天下最私的事,一切由自己负责”,反对道学家们把一些事关个人恋爱的事件上升为有失风化,“据我想来,除了个人的食息以外,两性的关系是天下最私的事,一切都当由自己负责,与第三者了无关涉,即使如何变态,如不构成犯罪,社会上别无顾问之必要”[11]461。此后,各大报刊开始了对性爱问题的广泛讨论。如1921—1925《妇女杂志》对爱伦凯“恋爱结婚论”的讨论;1922年在《妇女杂志》上两次关于离婚问题的讨论;1923年《晨报副刊》对“爱情定则”的讨论;1925年围绕长沙赵五贞女士、广西李超女士为封建包办婚姻逼迫至死,《新潮》《晨钟》《妇女杂志》等报刊关于“新性道德”的讨论等。一系列对于性爱问题的讨论伴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打开了现代性话语的大门,现代性爱被作为文学现代性的重要内涵接受下来,给沉寂的新文化运动找到了突破口,借用刺激性的话题——性欲望,开启了新文学作家们对现代性探索的热情。
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中,情爱主题的小说成为了当时文坛创作的潮流。随着1921年郁达夫《沉沦》的出版,“自叙传”式表达“性苦闷”的话题风行一时。据沈雁冰统计,1921年4、5、6月间“描写男女恋爱的小说占了百分之九十八”[12]43。作为一种流行甚广的文学潮流,情爱小说在作家、出版、读者接受等方面都形成了强大风潮。无论是关于性爱问题的争议,还是郁达夫式“性苦闷”的抒发,抑或是此后对爱欲经验的广泛书写,对于“欲望”问题的思考始终流行于1920年代新文学的小说创作中。
然而,情爱欲望话题尽管在“五四”时期得到了充分发挥,但实际上,对于这种反映个性解放的思想诉求,质疑之声一直不绝于耳,过于张扬裸露的欲望表现,往往并不能被广泛接受。现代性爱观念对“旧道德”解构的同时,也并没有忽略对“新性道德”的建构。郭沫若、张资平、叶灵凤、茅盾等都共同对此做出了努力,“对于社会上各种名分的规律加以攻击,要重新估定价值,建立更为合理的生活,在他的本意原是道德的”[13]305。原本,周作人在《人的文學》中的现代性爱观念即是以“人性”为出发点,也正是以此为中心,他又进一步指出“灵肉本是一物的两面,并非对抗的二元。兽性与神性,合起来便只是人性”[14]2,在他看来,不仅纵欲是人性的一面,禁欲也是人性的一面,而合于人性的“道德”就是要使这两个方面都得到满足。这样,“灵”与“肉”就被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他追求的是一种“灵与肉”相结合的、从而达成理想的现代性爱关系。
至此,“五四”启蒙精英们对“灵肉一致”的强调,已经对欲望的进一步解放有了很大的约束。此外,情爱中所包含的非欲望倾向,也被“五四”时期的一些作家特别是女作家放大,这又构成了对欲望约束的另一维。
通常情况下,现代性爱话语被广泛传播的同时,必定会有旧伦理秩序维护者出面反对,面对他们的嘲讽和攻击,女性作家们在处理男女两性之间的爱欲问题时自然更为谨慎。冯沅君、庐隐等女性作家在涉及男女之间爱欲心理时的回避态度早已为人所注意,“在论及五四早期女作家情爱主题时,多数评论者都会不无遗憾地注意到女作家有意规避性爱题材的深度描写,我们习惯将这种情况归结为爱情中‘灵与肉的分离”[15],女性作家们纷纷选择抛弃情欲书写来维护爱情的神圣纯洁,这也就派生出对情爱叙事的另一支影响较为深广的主题模式——“浪漫爱”的书写与想象。于是,在以冯沅君、庐隐等为代表的“浪漫爱”式的情爱小说中,爱情更多被表现为一种“柏拉图式”的,欲望则维持在缺席状态。在纯洁甜蜜、美轮美奂的精神之爱里,男女主人公们从现实的庸碌中抽身,穿越到一个纯洁、闲散、清新的世界,在一种理想主义的、浪漫绮丽的想象中顽强地维护着男女两性之间的纯洁性。
由此,对“灵肉一致”的强调与一些女性作家作品对“浪漫爱”的纯粹表现就形成了“五四”情爱小说的两个重要方向,欲望的解放与压制就这样同时产生又相互纠缠。由这一路径溯源,再回到莎菲,大致就能够理解她心理上的迟疑、矛盾。其实,《莎菲女士的日记》总体展开的正是莎菲已经被解放了的情感欲望却遭到了种种压制的过程——一种“灵肉一致”的道德和“浪漫爱”高尚想象的双重压制。
和庐隐、冯沅君笔下的女主人公们一样,莎菲也有着“浪漫爱”的幻想并时刻以此提醒自己。凌吉士在她最初的想象中就有着高贵的灵魂和骑士般的风采,在黯淡庸常的日子里,爱情也被她视为是生命中最纯洁的神圣之物,甚至是苦闷人生的唯一出路和救赎。她期待看重的是一种“真的爱情”,一种两性间人生观、价值观上的高度一致。在这一点,丁玲和“五四”后第一批女作家们并无二致。
丁玲的特殊性就在于,她在“浪漫爱”式的写作中又引入了“欲望”之维,“欲望”的强大以及两性关系之间复杂暧昧的张力在小说中得到了完整深入的体现。《莎菲女士的日记》开篇,莎菲已经处于幻灭的困境,关在房间里无所事事,每天呆呆的坐着,等着,挨着,不快活、不满足,不想读书,不求上进,似乎只有爱情才是人生的唯一慰藉。整本日记表现更多的就是莎菲神经质式的、自顾自的、自我夸张式的表演,她向自己提出了无数死循环式的问题:为什么大家不能再多懂得我一些?如若没人懂我我要那些爱做什么呢?既然没人懂我他们又爱我什么呢?凌吉士的出现使她的关注点有所转移,坠入情网的她又在反复追问自己,凌吉士是在捉弄我吗?他知道我如此思慕他吗?我爱他吗?他爱我吗?如果我私自承认爱恋了他,那我还值得被人尊敬吗?如果明知他是什么样的人我还压制不住自己狂热的欲念,那表示我究竟是怎样不堪的人?我会失掉所有的自尊和骄傲吗?……莎菲将所有目光集中于凌吉士,她的朋友在她眼里也不过如木偶一般,没有生命、没有性格,给人的感觉似乎都很空洞、很模糊。唯一被莎菲精雕细琢的,只有凌吉士。他的颀长的身材、白嫩的面庞、鲜红嫩腻的小嘴唇、柔软的头发、耀人的眼睛,以及另外一种说不出、捉不到的丰仪,在整部日记中被不厌其烦地加以勾勒。在此,凌吉士似乎已不再是一个“真的”人,更像是莎菲幻想和自我陶醉所想象出来的形象,莎菲阴湿的住所、低矮的房间、房间里油腻的书桌、三条腿的椅子,似乎也很难容得下这样一个高贵的美人儿。深感模糊的迷恋,使莎菲步步沦陷,直到最后,用力推开凌吉士的那一刻,莎菲恍然清醒,为了一个明知是虚假的爱情,要放弃她的自尊、她的骄傲,甚至是活下去的勇气究竟值不值得。莎菲说这本日记是为了纪念死去的蕴姊,其实蕴姊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被看做是莎菲本人的延伸,她似乎在告诫自己如果继续陶醉痴迷于所谓的“爱情”,就会像蕴妹一样,如果不是“被神捉弄般的去爱上那苍白脸色的男人”,就不会死得这样快。临近结束,之前多面的“自我”以及“自我”产生的所有幻想统统幻灭,小说叙述节奏突然加快,很像是欧洲电影的惯用技法,前半部分慢慢道来,最后的,带有冲击性的情节不可遏制的、不能随时间缓缓而来似的冲决而出,莎菲的绝望、对自己的嘲笑、疯狂般的自我放弃、决定默默离去的决心拥挤排出,给人留下的只有难以平复的心理震荡。
比之于“浪漫爱”中的理想主义,丁玲却在“欲望”背后挖掘出了爱情真实的一面,突出了“欲望”的强大以及“灵”与“肉”的极端不和谐。一方面她写出了凌吉士对于莎菲的强烈诱惑性,另一方面则集中于莎菲沉重纠结、反反复复的心理顾虑。诱惑引发欲望,欲望带来悔恨,挣扎沦陷中又走向了更加繁复的道德顾虑,莎菲是无法置道德舆论于不顾的。更为真实的是,欲望与现实纠缠扭结,挣扎、矛盾散去后留下的绝望之感以及无法排遣的痛苦让人难以释怀。在这个意义上,丁玲写出了标榜自由解放、灵肉一致、纯洁高尚的爱情理想背后的琐屑、现实与退缩。一系列真实的表现剥离了附着在“爱情”之上的自由、解放、纯洁想象,透露的却是情爱本身某种不可说不能解的质地与属性,而这些又恰恰构成了对情感内涵最为真挚的认识。
20世纪20年代初期新知识分子的性爱理想大多是“灵肉一致”,是两性之間的和谐共生。但是,一方面,“灵肉一致”的性爱观联结着高度理性的个体,这往往与整个社会的进步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在人类哲学历史传统中,一直都存在着“灵”与“肉”,即理性与欲望的二元对立,这种对立的结果几乎都要使肉体受到理性的超自然约束,而在很多情况下,理性并不能时刻控制感性,现实生活中“灵”与“肉”的结合并非那么完美。“灵肉一致”的道德约束对于20年代的大多数人来说都是可望不可即的。这一问题在后来的“五四”反思中逐渐受到关注,新知识分子们对之前的主张也有了些许改变。1927年,由叶灵凤、潘汉年主编的《幻洲》就相继推出了专门讨论爱欲问题的“灵肉号”“灵肉续号”,并引起了较大反响。与“五四”时期“灵肉一致”的表述不同,他们在征稿启事中就直接指出,“中国大家还是马马虎虎,掮着‘自由恋爱、‘灵肉一致、‘精神的、‘肉体的几句幌子,骗人骗己”[16]。潘汉年则将“五四”时期的爱欲观念称为一种“灵与肉的误解”:“近来常听见一般朋友谈到‘灵肉冲突,‘灵肉一致的问题,我常常惊奇:什么是灵?什么叫肉?从来想不出一个真确的解释,我不知道灵与肉从何分别?请问人无肉从何而生灵?”[17]周全平也认为“灵肉一致的恋爱论”还是“传统观念在里面作梗”[18],“灵”“肉”的简单缝合此时已被作为最主要的批判对象。显然,置身于这个时代的丁玲也共享了这些时代思潮,对莎菲心理的冗长铺叙,以一种直面的姿态道出了人性解放后必然要面对的现实。它清晰地呈现了一个真实的人内心欲望的强大,正是从这一点出发,丁玲对“灵肉一致”“浪漫爱”的爱情观、人性观进行着质疑。
四、余论
作家的创作离不开时代环境的影响。丁玲早期在北京的创作既可以说是对时代情感结构的一种继承,也可以说是一种反拨。通过情爱书写,丁玲从一个女性特有的敏感性出发,对其时流行的“感伤主义”与现代女性成长之间的关系作出了自己的判断:徒有感伤情绪在现代社会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而作为女性恋爱的客体,男性群体也并不能满足新女性恋爱的要求,“男性气概”的失落,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正要求女性变得更加强大,正如梦珂从影之后的隐忍,“那奇怪的情景,见惯了,慢慢的可以不怕,可以从容,使她的隐忍力更加强烈,更加伟大,能使她忍受非常无礼的侮辱了”[5]40。在以经济地位决定男性气概的社会,对于经济上尚未完全独立的女性来说,无论是“浪漫爱”还是“灵肉一致”的爱情,其实都不过是水中花、镜中月,正如《国际歌》歌词所说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女性的幸福,全靠她们自己。
[责任编辑:蒋玉斌]
参考文献:
[1] 雷蒙德·威廉斯.漫长的革命[M].倪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2] 赵园.艰难的选择[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
[3] 闻一多.闻一多全集:第2卷[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4] 张霞.论茅盾1930年代短篇小说的互文书写[J].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5):89-96.
[5] 丁玲.丁玲全集:第3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6]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2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
[7] 哈维·C·曼斯菲尔德.男性气概[M].刘玮,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
[8] 袁良骏.丁玲研究资料[G].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
[9] 孙瑞珍,王中忱.丁玲研究在国外[G].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
[10]史书美.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女性自白小说[J].当代,1994(3):122-123.
[11]周作人.谈虎集[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7.
[12]茅盾.茅盾选集:第5卷[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
[13]陈子善,王自立.郁达夫研究资料:下[G].广州:花城出版社,1985.
[14]周作人.周作人卷[M]//苦雨斋文丛.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
[15]陈宁,乔以钢.论五四女性情爱主题写作中的边缘文本和隐形文本[J].学术交流,2002(1):152-156.
[16]灵与肉征文启事[J].幻洲,1927(3).
[17]潘汉年.性爱漫谈[J].幻洲,1927(4):156-157.
[18]骆驼(周全平).我的灵肉观[J].幻洲,1927(6):267-272.
Emotional Structure and Epoch Symptoms:a Review of Ding LingsLove Writing in Beijing Period
WEI Wei,LI Jing
(Institute of Chinese New Poetry,Southwest University,Chongqing 400700,China)
Abstract:For young intellectuals like Ding Ling who came to Beijing under the influence of new cultural trends,their emotional structure is already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fiery political youth in the early stage of the May 4th movement.The common experience of Ding Lings generation is composed of the loneliness of drifting around,the failure of ideals and aspirations,the difficulty of survival and life and the confusion of unknown future .Ding Lings early creation in Beijing can be said to be both an inheritance of the emotional structure of the times and a kind of reverse.Through love writing,Ding Ling made her own judgmen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opular“sentimentalism”at that time and the growth of modern women:sentimental feelings can not solve any problems in modern society;as the object of female love,male group can not meet the new female ‘s requirements for love affair;the loss of“masculinity”actually requires women to become stronger to some extent;in the society that economic status determines masculinity,for women who are not yet completely independent economically,both“romantic love”and“consistant love in soul and flesh”are nothing more than the moon in the water ,flowers reflected inthe mirror.
Key words:Ding Ling;Beijing period;emotional structure;epoch symptoms;love writ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