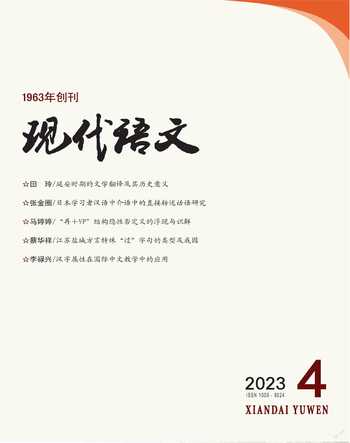日本学习者汉语中介语中的直接转述话语研究
摘 要:在HSK动态作文语料库日本学习者的语料中,直接转述话语使用频率较高。学习者大都能够掌握直接转述话语的基本结构,部分学习者甚至具有非常娴熟的直接转述话语运用技能,这主要表现为不同管领词的选取、管领词修饰语以及不同类型引导句和转述句的恰当使用等。与汉语目的语文本相比,日本学习者汉语中介语系统中的直接转述话语也存在需要改进之处,主要包括:引导句和转述句的语序单一,基本都采用“引导句+转述句”的模式;管领词类型相对单一,超过80%的用例都使用“说”;冒号和引号使用不规范现象比较普遍。
关键词:日本汉语学习者;中介语;直接转述话语
转述是人类日常交际非常重要的一种语言行为,转述行为所产生的话语就是转述话语(reported speech)。在汉语文献中,则经常使用“引语”一词来表示转述话语。转述话语很早便引起了东西方学者的关注,人们从语言学、修辞学、叙事学、心理学、社会学等角度,对它开展了广泛深入的研究。仅就语言学角度而言,转述话语的类型、结构特征、保真度、起始和结束边界、交际功能、引导词的类型等问题,都曾是学界讨论的热点话题。这些研究基本都是针对母语者所产出的转述话语而开展的。除了二语写作中的引用话语和引用能力得到较多讨论外[1]-[3],二语学习者其他类型交际活动中转述话语的使用情况,还很少引起学界的关注。至于汉语中介语系统中的转述话语研究,也基本处于空白状态[4]。这与转述话语在语言交际中的重要地位是极不相称的。
本文拟以日本学习者作为个案,对汉语中介语系统中的转述话语进行全面描写,以期对二语学习者习得汉语转述话语的情况有一个基本了解。之所以选择日本汉语学习者作为考察对象,主要是基于语料方面的考虑。通过对北京语言大学HSK动态作文语料库的初步调查,我们发现,日本学习者的作文总数多达3211篇,仅次于韩国学生;同时,这些作文语料中的转述话语使用频率很高,类型较为丰富,能在较大程度上反映出汉语二语学习者习得转述话语的某些共性,并可以作为进一步开展国别对比研究的基础。
需要说明的是,以往对中介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偏误现象,这对精准聚焦习得薄弱环节、快速提升教学效果具有重要意义。不过,中介语作为一个既有独立性、又有动态性的语言系统,对深入认识人们习得第二语言的过程具有重要价值。因此,对中介语的研究,不应仅关注其中的偏误现象,学习者对目标语言的正确用法同样需要纳入考察范围。唯有如此,才能全面把握二语学习者的语言能力及其发展过程。本文对汉语中介语中转述话语的描写和分析,正是建立在这一认识基础之上的。
虽然不同学者对转述话语的分类不尽相同,但一般都包括直接转述话语和间接转述话语这两个基本类型。其他类型的转述话语使用频率较低,通常只出现在一些追求语言丰富性、生动性的文学语篇中,在第二语言教学中较少涉及,中介语系统中也极少出现。在我们所收集到的HSK动态作文语料库日本学生语料中,能够明确识别的直接转述话语共有1018例,间接转述话语只有143例,二者的比例约为7:1。由此可见,日本汉语学习者在使用转述话语时,具有明显的选择倾向性,即更侧重于使用直接转述话语。因此,为使研究更为集中,本文只讨论直接转述话语的使用情况。需要说明的是,日本学习者汉语中介语的用例均出自HSK动态作文语料库,不再一一注明出处;汉语目的语的用例则在句末标明出处。
一、直接转述话语的结构特征
在汉语中,一个标准的直接转述话语由引导句和转述句两部分构成,其中,引导句在前,转述句在后。在书面上,引导句后一般加冒号,而转述句则放在双引号中。日本学习者的汉语中介语中,很多直接转述话语都符合这一标准结构,这是学习者成功习得的表现。例如:
(1)由于这个原因,他一直跟我说:“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要说没有钱,钱是我给你的。我不想看你就因为担心花很多钱而死心。”
(2)等电车来时,他忽然问我:“你想不想喝什么饮料?”
(3)先开始的时候十分困难,那样的时候{CJ-zhuy我}①自言自语地说道:“我一定{CJ-zy能}成功的,不要怕失败。”
唐善生指出:“引号是确定直接引语的重要标记,一个引语无论有没有其他标记,只要有引号就是直接引语。”[5](P124)因此,在有些情况下,冒号可以替换成逗号或直接省略,并不影响直接转述话语的识别和其功能的正常发挥。例如:
(4)一[BD、]两个月以后,和中国朋友{CC中国人的朋友}聊天时,她突然说,“你的发音比以前好多了!”
(5)我的母亲跟我说“你失败了一次也别灰心[BQ、]失望[BQ,]应该有跟你合适的选择。”
虽然在書面文本中引号是确定直接转述话语的重要显性标记,但并非唯一的手段,因为决定直接转述话语性质的是转述者的视点(point of view)[6](P367)。当转述者将视点锚定在原说话人的时空、尽量完整地呈现原说话人的话语时,所产出的就是直接转述话语。由于存在视点的转换,因此,直接转述话语中的人称代词、指示代词、时间词等索引性成分与当前的直述话语存在区别[7](29-45)。
在日本学习者的汉语中介语中,有些转述话语并未使用引号,但我们仍然可以根据其中的索引性成分判断出其直接转述话语的身份。例如:
(6)我的上司比我大几岁,他虽然经验不多,但是他的工作成绩不错。他经常跟我说:你又失败了。你的对手又比你早报道。你怎么办。如果继续这样,你没有好前途呀!
(7)就是看我们生活太辛苦{CJ+zxy的样子}[BQ,]有人对父母说,我可以帮助你们。这个意思是他(我爸爸的上司)说,你们的孩子中那个中间的老三卖{CQ给}我吧。我好好照顾他。我们有两个女儿,但是没有儿子,可以吧。他这样说。
(8)放假结束后同学们都问{CC告诉}我你去了哪里{CQ?}好像{CJX}你{CQ跟}放假前完全不一样{CD的}了![BD,]我就告诉了同学,我把爷爷送到天堂去了![BD。]
例(6)中,虽然转述句并没有放在引号内,但是由于作者在言说动词“说”后边使用了具有展示功能的冒号,再加上人们根据语义表达对转述句中人称代词移指情况的识别,所以读者仍能较为快速地判断出言说动词后话语的直接转述话语身份。这种情况在日本学习者的汉语中介语语料中比较常见。例(7)仅在言说动词后加了逗号,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其后转述话语的身份识别,读者只有结合语境识别出其中的“我”和“你们”分别指称原交际互动中的说话人和听话人,才能判断出该转述句为直接转述话语。例(8)更进一步,在引导句“同学们都问我”和转述句“你去了哪里……”之间没有任何形式上的边界标记,其身份识别需要读者付出更多的认知努力。
从语言本身来说,上述几例中的划线部分并不违反直接转述话语的结构规则和功能表达,只是由于缺少必要的标点符号,導致其身份识别和语义解读存在一定的困难而已。对直接转述话语来说,书面中的冒号和引号类似于语言层面的话语标记,虽然它们的使用与否并不影响句子结构的合法度和逻辑语义的表达,但是可以发挥一定的语用功能,以促进受话人更好的理解,保障交际互动的高效进行。在风格较为自由活泼或规范性要求相对较低的汉语文本中,如文学作品、自媒体文章等,类似例(6)那样只用冒号标记直接转述话语的现象也比较常见,但是例(7)、例(8)这样的书写方式则明显属于不够规范的用法,是二语学习者对直接转述话语的书面表现形式了解不深或书写态度不够严谨而造成的。
在标准汉语文本中,直接转述话语的引导句和转述句的语序存在三种情况:一是“引导句+转述句”,二是“转述句+引导句”,三是“转述句1+引导句+转述句2”。在日本学习者的汉语中介语语料中,绝大多数直接转述话语的引导句都位于转述句之前,引导句位于转述句之后的只有9例,占比不足1%。例如:
(9)“我们没有水喝了,到底怎么办呢?”一个和尚对其他两个说了。
(10)“中屿,你的电话!”有一位同学叫我。我听{CQ了}就接电话{CJX}去{CQ了}。
在我们所收集的语料中,没有发现引导句插入转述句之间的用例。
在语篇表达中,适时调整引导句和转述句的语序,可以避免形式的呆板单调,同时,也有助于信息的凸显、篇章的连贯和叙述节奏的变化,是语言使用者语篇能力的体现。在日本学习者的汉语中介语系统中,超过99%的直接转述话语都使用“引导句+转述句”这一种语序类型,说明学习者对直接转述话语的语序多样性仍缺乏明确的认识,需要在教学中予以专门强调。
二、直接转述话语的引导句
在真实的书面文本中,除了少数自由直接转述话语外,绝大多数的直接转述话语都包含一个引导句,用于引领、导出其后的转述句。引导句对于描述被转述话语的言说情态、标示被转述话语的起始边界等都具有重要作用。
(一)直接转述话语引导句的管领词
徐赳赳指出:“如果我们把某个引号内的直接引语看作是一个管界的话,那么引出这个引语的动词,就是管领词。”[8](P60)根据他对355篇汉语报刊叙述文语料的统计,在引出引语的管领词中,用得最多的4个词语是:说(34%)>问(15%)>道(4%)>喊(3%),其他的管领词占比很少,如“骂、讲、告诉、叨念、解释、惊呼、称、答、想、写、认为”等。可以发现,引导句中的管领词绝大多数都是言说行为动词。除此之外,还有少数认知思维动词(如“想”“认为”)和书写动词(如“写”),由后两类动词引导的转述句可以分别称作“思维转述”和“文字转述”。从结构上来看,它们与言说动词引导的“话语转述”并无本质区别,因此可以一并讨论。
在日本汉语学习者的汉语中介语语料中,直接转述话语引导句中的管领词体现出明显的使用倾向性,据粗略统计,超过80%的管领词都由“说”充当。管领词“说”的主语通常都是有生主体,如“医生”“他”“我父母”“韩非子”“古人”“有人”等;有些情况下,也可以是非有生主体,这时一般是信息名词[9](P534),如“医学杂志”“信里”“电视上”“电子邮件”“新闻”“报道”“规定”“歌词”“俗话”等。其中,“俗话说”已经成为一个具有固化性质的管领词组。在现代汉语中,作为言说动词的管领词“说”已经发展出引语标记的用法,放在其他言说动词后边,删除后不影响语句的可接受性[10](P110)。这在日本学习者的汉语中介语中也有少量用例:
(11)我问老师问题的时候,有的老师回答说:“这是习惯,没什么理由,别多问,该记住!”
(12)我父亲在我上高中的时候常常劝我说,“现在的日本经济太不景[B经]气,……”
与“说”类似,言说动词“道”在现代汉语中也已经发展成一个内容宾语标句词[11](P110)。例如:
(13)朋友看出我的心事,马上说道:“你应该高兴啊!这就是你的家,在中国的家!”
(14)在大学里认识的一个朋友问道:“你的生日几月几号?”
需要说明的是,这类引导句中使用“言说动词+说/道”的用例非常少见,在全部语料中只有不到20例。唐正大、单俪娉指出,在汉语书面文本中,“道”还经常用在一些表达言说伴随行为的动词短语后,如“一拍大腿道”“连连摆手道”[12](P489)。在我们所考察的语料中,并没有发现此类用法。
语料中其他较为常见的管领词还包括“问”“回答”“想”“告诉”“写”“讲”“叫”“喊”“骂”“劝”“商量”“宣布”“认为”“觉得”“强调”“主张”“提到”等。在引导句中使用不同的管领词,可以更为准确地表现原说话人言说/思维/书写行为的次范畴特征,如“宣布”虽然也是一种“说”,但并非一般的“说”,同时,也使行文表达富于变化,能够增加篇章的文采。语料中不同管领词的择取,体现了汉语学习者的这种努力和尝试,并且大部分都能正确使用。值得注意的是,在管领词的选取上,“说”占据了绝对优势,远远高于母语者产出的标准汉语文本,这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仅有少数学习者掌握了一定数量的除“说”以外的其他管领词;二是虽然部分学习者已经习得一定数量的管领词,但是对其用法掌握得并不熟练,难以有效输出。
直接引语是一种展示(demonstrating)行为,就像人们可以展示别人打球时如何发球、朋友如何瘸着腿走路或钟摆如何晃动一样,说话人也可以展示别人是如何说话的,这种展示的别人的话语就是直接转述话语[13](P764-805)。在口语交际中,这种展示行为可以通过模仿原说话人的语气、语调、语速、重音甚至身势动作、面部表情等方式来实现,但是由于在书面表达中缺少这些手段,因此,说话人只能用描述(describing)的方式进行说明。在标准的汉语文本中,这些说明性的文字,通常都是作为引述动词的方式状语、伴随状语或状态补语出现的。在日本学习者的汉语中介语语料中,这种情况也比较常见。例如:
(15)那时我母亲总是在脸上带着一丝复杂的表情说,“是吗?”
(16)他摸着我的腦袋说:[BC;]“这个女孩子挺聪明,她有她的好处,长大以后,一定会发挥她的本领。”
其他类似的表达还有“微笑着说”“嘲笑地说”“红着脸大声地说”“很高兴地说”“很生气地说”“高高兴兴地大声地说”“兴高采烈地说”“开玩笑地说”“安静地说”等。
(二)直接转述话语引导句的类型
如前所述,一个典型的直接转述话语结构由引导句和转述句两部分构成。所谓“引导句”,顾名思义,就是说它对后边的转述句具有引领、导出作用。含有言说动词充当的管领词的引导句,可以有效地发挥这种引领、导出功能,是典型的引导句。在有些情况下,一个小句虽然对后续的直接转述句具有一定的提示作用,但其引领、导出功能并不像言说动词那样明显,这样的小句可以视为非典型的引导句。例如:
(17)做父亲的摇着头:“像朱四判官这种老奸巨滑的土匪头儿,什么歹主意行不出?!关八爷硬想冲着老虎讨皮毛,未免太傻了!”(司马中原《狂风沙》)
(18)说到这里,她又哭了起来:“……人家……人家的客人,……只晓得慰护自己的姑娘……而你呢……你呢……倒反要作弄我……”(郁达夫
《祈愿》)
由于缺少言说动词,有人可能会将以上两例中的转述句视为自由直接转述话语。考虑到例句中的划线部分在文本语境中都表示言说活动的伴随动作和行为,与其后的转述句具有较强的关联性和提示性,并且该类用法在叙事文本中普遍存在,因此,我们也将其视为引导句。
在日本学习者的汉语中介语语料中,根据引导句和转述句之间的关系,可以将引导句大致分为三种类型:及物型、同指型和伴随型。
1.及物型引导句
及物型引导句指的是由言说动词(包括思维动词和书写动词)充当管领词的引导句。从句法结构上看,学者们普遍认为直接转述句具有较强的独立性,不能看作言说动词的句法宾语[14](P12-13)。不过,从语义来看,直接转述句都可以视为引导句中言说动词所表言说行为的内容,言说行为对转述话语具有较强的控制力,如果没有言说行为的话,也就谈不上他所说出的话语。因此,我们将由言说动词充当管领词的引导句称为“及物型引导句”。以上所举学习者中介语中直接转述话语的用例,其引导句基本都属于这一类型,兹不赘举。
2.同指型引导句
有的引导句含有言语类信息名词,如“话”“谚语”“诗”等,该信息名词与其后的转述句具有同指关系,即信息名词的内容就是转述句所表示的话语。根据信息名词与转述句的结构关系,同指型引导句又可以分为两种:同位同指型引导句和判断同指型引导句。其中,同位同指型引导句中的信息名词与转述句具有松散的同位关系,判断同指型引导句的信息名词与转述句存在判断关系。
先看同位同指型引导句。在我们所考察的语料中,同位同指型引导句共有43例。例如:
(19)我喜欢圣经的一句话:[BC。]“要爱别人像爱自己一样。”
(20)所以最近我们听到这样的声音:[BC.]“让我们消灭{CC消除}烟吧。”
(21)听说最近某市政府出台了一项规定:在公共场所边走边抽烟的人将被罚款。
再看判断同指型引导句。在我们所考察的语料中,判断同指型引导句共有23例。例如:
(22)我现在也忘[C]不了那时母亲冲着我说的话。那就是“对什么事情问题不在于自己会不会,而在于自己去做不做!!”
(23)“[BC「]先生,您不应该在这里吸烟的。您有没有看到那个图像{CD吗}?”[BC」]这{CD个}是有一天我对一位男人说的话。
(24)在日语当中有一个很有名的谚语说“孩子是看着父母的背长大的”。
需要说明的是例(24),虽然引导句中有言说动词“说”,但由于其主语并非具有自主性的有生主体,而是无生的信息名词“谚语”,因此,其言说行为义已经弱化,仅起到联系信息名词与其后转述句的作用,与表判断的系词“是”功能类似,所以我们也将它归为此类。
3.伴随型引导句
伴随型引导句即上文所说的非典型引导句,用来描述原说话人言说活动的伴随动作、行为或状态。例如:
(25)于是我们走过了几处等生意的滑杆,我们连连地摆手——我不累,不累。
(26)第二个、第三个和尚高兴地点头。[BC,]“做饭,清洁都要你们做。”
(27)不久,他们三个又争吵起来。“你这个自私鬼!”“好你个臭和尚!”“你是我孙子!”
(28)我感到有些不耐烦了。“爸爸累了。以后再说,好不好。”之后孩子就哭了。“爸爸不理我”。
这种类型的引导句使用频率很低,在我们所考察的语料中,只发现8例。伴随型引导句后都隐含了一个言说动词“说”或思维动词“想”,由于读者可以通过转述句所带的引号或其中的人称代词、特殊语气等识别出其直接转述话语的身份,因此,它可以通过展示的方式直接呈现出来,不再需要言说/思维动词充当的管领词的引导。伴随型引导句一般出现在具有生动性和故事性的文学叙事文本中,是写作者较高语言表达能力的表现。
三、直接转述话语的转述句
转述句是直接转述话语的主要组成部分,它是对另一时空中已经存在或将来可能存在的某个话语形式的直接展示。根据日本学习者汉语中介语语料中的相关用例,我们拟从转述句的类型、转述句的边界以及自由直接转述句等几个角度分别进行描写分析。
(一)直接转述话语转述句的类型
直接转述话语转述句的最基本特征是对某个话语形式的完整呈现,这一话语形式可以是具体言说的,也可以是以内部思维或文字形式体现的。根据不同的观察角度,直接转述话语的转述句可以分成不同的类型。
1.单层转述句和多层转述句
这是从转述句的层级结构来划分的。所谓“单层转述句”,指的是整个转述句表示的都是引导句中行为主体本身的所言、所思、所想。它可以是一个最简单的小句,也可以是一个复杂的语篇。所谓“多层转述句”,指的是在转述句中又包含了另外一层或多层转述。从理论上来说,转述句的这种递归性可以是无限的,不过,由于人类认知和现实语言交际的局限性,一般的多层转述句其实都是双层转述,三层或三层以上的转述句在实际语言运用中非常少见。根据汉语标点符号使用规范,第一层转述句一般放在双引号中,第二层转述句则置于单引号中,第三层再放到双引号中,如此反复。
以上所举各例中的直接转述句,都是单层转述。以下是多层转述句的例子:
(29)母亲告诉我[BQ,]“别人说女儿长得像爸爸,他高兴得不得了”[BC,]。[BC”]
(30)有一天,李和尚想出了个办法:[BC。]“我们作一个{CC座}大仙,让大家看一看。那时跟山下的农民说,如果每周把一杯水浇上大仙的头,就会幸福”[BQ。]
在我们所考察的语料中,多层转述句只有3例,并且都为双层转述。以上两例中的第二层转述句“女儿长得像爸爸”和“如果每周把一杯水浇上大仙的头,就会幸福”,由于缺少必要的标记手段,其直接转述句的身份并不明确。
2.现实转述句和虚拟转述句
如果转述句所表示的话语是原说话人已经产出的、在客观世界现实存在的实体,我们称之为“现实转述句”;如果转述句所表示的话语实际并未有人说出,只是当前说话人假设在未来或可能世界中某个言说主体会说出的话语,则称之为“虚拟转述句”。虚拟转述句的引导句中经常会出现表达虚拟情态的成分,如“如果”“也许”“可能”“肯定”“会”等。需要说明的是,在虚构的故事讲述中,虽然转述的故事人物话语并未存在于真实世界,但是其结构形式和表达功能都与现实转述句完全一致,而区别于虚拟转述句,因此,我们将其归入前者。上文所举用例中的转述句基本都属于现实转述句,下面是虚拟转述句的例子:
(31)也许有的人说“自杀是不道德的行为”。可我觉得“自杀”和“安乐死”是意思不一样。
(32)那我们三个{CD各}人不能{CQ都}买{CQ到}饮料。那时候大家可能说,“你先买吧!我不要。”
在我们所考察的语料中,虚拟直接转述句共有22例。
(二)直接转述句的边界
如前所述,直接转述话语是对另一时空中某一话语形式的直接展示,它立足的是原说话人的视点,与当前说话人的直述话语处在不同的层面,其中的人称、指示成分的所指对象与前后的直述话语迥异甚至恰好相反,因此,说话人或写作者必须用明确的手段标示直接转述话语的起始和结束边界,否则,就可能会引起误解。唐善生详细描写了汉语书面文本中转述话语边界除引号之外的若干标记手段[5](P214-224)。
在日本学习者的汉语中介语中,绝大部分直接转述话语的转述句放在引号内,这可以使读者准确地识别转述句的起始和结束边界。在10多条没有加引号的转述句中,由于引导句中言说/思维/书写动词的存在,转述句的起始边界比较容易确定,其结束边界有时可以凭借一些手段准确识别出来。例如:
(33)另外一个和尚说:[BQ“]不行,我们必须用水。所以还是我们应该下山抬水。不过抬水的时候抬得少一点,怎么样?[BQ”]最后{CC终后}一个和尚说:……
(34)古本这么回答,[BQ“]我们不高兴{CQ看到}其他人的不幸福。我们乐意{CC高兴}为有困难的人提供我们的产品。[BQ”]我听到古本先生的讲话{CC说话}以后,感觉作买卖就是这样。
在以上两例中,划线部分表示另外一个转述行为,或者是对一个转述行为的评价性话语等,读者可以据此确定其前位置为转述句的结束边界,这也可以从语料库标注者的标注得到验证。有些时候,转述句的结束边界到底在何处,并没有比较显性的手段进行标识,读者只能通过反复理解文意后进行确认,有时甚至会出现识别错误。例如:
(35)我非常感谢你们。我这次还想跟你们说,我很感谢[BD,]你们给我来中国留学的机会。虽然我在中国很寂寞,但是我体会{CJ-sy到}{CQ的}、[BC,]学会的东西非常多。我有了与在日本上学的朋友不同的经验。这是很难得的事情。而且我也{CC又会}知道了爸爸妈妈多么爱我。
(36)我听说,现在抽烟的人之中{CC之[C]间[F間]}至少一半人说,“其实我愿意改掉{CC停}抽[C]烟的习惯。[BQ”]我至今好几次试过[C]{CJX}了戒烟{CC禁烟}的方法,可是{CC还是}这就是很难,更{CC供}痛苦,所以我不想继续{CC进行}吸烟,但是不得不吸烟,说实话我愿意成为{CC成[C]}{CD了}一个不抽烟的人。”
在例(35)中,标下划线的句子无疑是直接转述句,但后边的哪个或哪些句子还属于转述句,则难以做出明确的判断。例(36)的划线部分是一个较长的完整直接转述句,原作者在起始和结束边界处都使用了引号,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语料库标注者却在转述句的第一个小句后标注了“[BQ”]”,即认为在此处缺少了后引号,也就是将其后的话语解读为当前说話人“我”的直述话语,而非对“抽烟的人”话语的转述。由此可见,直接转述句的边界识别确实是一个可能会引起语篇误读的问题。
(三)自由直接转述话语
所谓“自由直接转述话语”,指的是没有引导词,以展示方式直接呈现的原说话人的话语。在语篇中适当使用直接转述话语,特别是在多个人物的直接转述话语连用时,能够加快故事讲述节奏,展现故事人物矛盾冲突,增强互动的紧迫性。
在日本学习者的汉语中介语语料中,共有19条自由直接转述话语的用例。例如:
(37)他接我的电话{CQ时}很高兴,就问我身体怎么样,过得好不好[BD,]等等,[BC。]我一个一个地回答了,然后——“爸,我有话跟你说”“什么事?”“我……退学了。我打算去中国。手续也办好了。”“什么!?你,你……”。“我今天找你。等会儿再说。”“……好吧。”
(38)我赶快去她{CD的}那边[BQ。]“我好想你!!我爱你!!但是我身上只有二百元,我不得不回中国。[BC—]再见![BC—]”我跟她聊{CQ了}一个小时后回去{CJX}中国{CQ了}[BD…]。
(39)然后{CC以后}我用日语问他,“你为什么会说汉语呢?”“我最近刚开始学习汉语,[BC。]我觉得很有意思。”
(40)她跟我国妇女拥有同样的问[B门]题。她为做{CC搞好}比前素质高的工作[BQ,]辞职到合资{CQ企业}去了。“人家说我就说吧!我也爱孩子[BQ,]也爱自己的时间。就是一次的人生嘛[B吗]!”
例(37)中,划线部分都是不同人物的自由直接转述话语连用,由于每个单独的转述句都放在引号内,因此,彼此之间界限清晰,不会引起误解。这种转述话语的设置方式,生动地呈现了人物会话的互动场景,再加上问号、感叹号、省略号、破折号等标点符号的使用,大大增强了叙事的戏剧效果,体现了学习者较高的转述话语使用水平。例(38)中,在自由直接转述话语之前,由于有对原说话人言说行为发生前其他动作行为的描述,因此,可以较为自然地引出转述话语,这种情况接近于前文所说的由伴随型引导句引导的直接转述话语,在标准的汉语文本中也较为常见。例(39)中,划线部分的自由直接转述话语紧接其前带引导句的直接转述话语,并且一问一答,衔接自然流畅,也符合一般的汉语表达习惯。不过,在例(40)中,自由直接转述话语的使用缺少必要的引入和过渡,显得较为突兀,不太符合正常的汉语表达习惯。
由此可见,所谓的“自由直接转述话语”其实并不是绝对自由的,即使其前后没有显性的引导句,也必须通过其他手段进行必要的引介,如问答互动、时间上有直接先后联系的说话人动作行为的描述等。
四、直接转述话语的偏误
在日本学习者的汉语中介语语料中,和直接转述话语相关的偏误现象主要出现在引导句中和标点符号的使用上。需要说明的是,转述句部分虽然存在诸多别字、错字、错词、误加、遗漏等偏误现象,但我们认为转述句作为对另一语境中某个话语形式的直接呈现,是一种元语言成分,与当前话语并不处于同一层面上,其内部构成及其存在的问题与当前叙述话语无关[15](P92),因此,我们暂时不考虑转述句内部的各种偏误现象。不过,如果转述句作为一个整体,与前后直述话语的组合出现偏误,则需要纳入考察范围。
(一)直接转述话语引导句中的偏误现象
上文对直接转述话语引导句中管领词的使用情况进行了详细描写,我们发现,日本学习者的汉语中介语中虽然并不存在成系统的管领词偏误现象,但也出现了个别管领词的使用不当。例如:
(41)我小时候,我父母常常吩咐我,“认真学{WWJ}
(42)通过采访可知,从来{CC曾经}没有{CQ被}打过的一位小孩儿自豪地回答{CC表明},“我将来绝对不会像我同学的父母那样打自己的孩子[BQ,]因为我也没被爸爸妈妈打过”。
(43)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医生在媒体上发言说{CC发表},“我还以为家人同意给病人{CJ-sy实施}安乐死,[BC。]所以给病人{CJ-sy实施了}安乐死。”
(44)我再也忍不住了,跟他们说除了有什么急事以外,都不让他们的朋友这么晚打来。一个同屋她道,“对不起,我没想到影响你。以后我一定小心”。
(45)俗话说{CD道}得好:一寸光阴一寸金,[BC、]寸金难买寸光阴。
例(41)中,“吩咐”虽然也可以用作引导句管领词,但是用在此处表义不够准确,根据其后残缺转述句的部分内容,此处的言说动词应该使用“嘱咐”。例(42)中,“表明”不能作为言说动词引出直接转述句,语料标注者将其标为“错词(CC)”并更正为“回答”。例(43)中,“发表”同样不能引出直接转述句。例(44)中,“道”是一个具有文言色彩的言说动词,在现代汉语中已经虚化[11](P111),不适合直接用作引导句的管领动词。例(45)中,“俗话说得好”作为一个用来引导谚语、俗语的较为固定的组合,其中的管领动词“说”不能随意替换为其他成分。
如果说单纯的管领动词在使用上较少出现偏误的话,那么,当写作者为了更为准确地描述被转述者言说行为的细节状态,从而需要为管领动词加上修饰语,或者想凸显言说行为的某些时间要素时,则会出现相对较多的偏误。这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情况:
1.状语标记“地”的误用,例如:
(46)妈妈回答{CD地}说:“不能想什么,不能考虑什么,我只是拼命地过那些天{CC那一天}。”
(47)我一看它感到对不起它{CJgd},反而对妹妹指责地说:“这是因为你不照顾它。”
(48)如果家长严厉{CC批评}地跟她说[BQ:]
“你再也不能跟他玩儿了。”那么女儿肯定对父母表示不满,而且更想跟那个男同学一起玩儿了。
(49)我父亲小时候跟一个同学打架,哭着回家了,我爷爷一看他就生气{CQ地}说[BQ:]“只有打敗对手,才允许回家。”
(50)她笑笑地告诉我:“我非常喜欢{CC热爱}汉语。……”
例(46)~例(48)中,“回答”“指责”“批评”本身就是言语行为动词,它们只能与其后的言说动词“说”构成连动结构,从次范畴角度叙述一种言说行为,而不能加“地”降级充当状语修饰、说明“说”的方式。例(49)中,作为一个表达情绪状态的动词,“生气”经常用来修饰、说明言说动词“说”的伴随状态,此时需要在“生气”后加状语标记“地”。孤立地看,上述引导句修改为“我爷爷一看他就生气,说”也可以成立,但此时“生气”就成了一种惯常行为,与上文文意显然不符,因此,这里的偏误应确认为状语标记“地”的遗漏。例(50)中,“笑笑”作为单音节动词重叠形式,只能充当谓语核心,无法充当修饰成分。
2.持续体标记“着”的误用,例如:
(51)吸烟者叹气着说:“抽烟的地方越来越少了”。
(52)悟和尚有一点不好意思地{CC着}说“我看今天天气就知道明天一定会下雨的,所以您们不用这么急。”
(53)我不知不觉哭着{CC得}对家人说:“对不起,我什么都不能做了。”
例(51)中,“叹气”是一个离合词,加持续体标记“着”后,应该说成“叹着气”。从客观事实的角度来看,“叹气”和“说”这两个口部动作行为有两种可能的存在状态:一是只叹一次气,然后开始言说行为,此时一般表述为“叹了一口气(,)说”;另一种情况是在“说”的过程中穿插多次叹气行为,也就是将叹气识解为一种持续状态,此时就需要加入持续体标记“着”,或者是将“叹气”在句法上实现为状语,即“叹气着说”。在标准的汉语文本中,确实存在这种用法,但是由于“叹气”是一个瞬时动词,本身的状态性不强,因此,“叹气着说”的可接受度较低;如果使用对举形式“唉声叹气”以增加其状态性和描写性,则可接受度会大大提升。例(52)中的“有一点不好意思”,无论是分析成动宾结构还是状中结构,都不能在后边直接加持续体标记“着”,但是可以整体作状语后加“地”修饰“说”,如标注所示。例(53)中,“哭”作为“说”的伴随行為,应该用连动结构表达为“哭着对家人说”;如果将“哭”实现为状语,则需要增加其描写性,如说成“嚎啕大哭地对家人说”。原文中在“哭”后用“得”,有可能是双重偏误,即作者将本欲表达的“哭地对家人说”中的“地”错写成“得”,而“哭地对家人说”本身也是不合法的结构。
3.完成体标记“了”的偏误。这种情况相对较为常见,例如:
(54)他{CD就}让我上车,[BC、]一直握着我的两[B二]只手说{CD了}[BQ:]“对不起,太冷了吧!”
(55)那个时候我们的班三十多个人讨论谁做[B作]班长最合适,但是谁也没说{CD了}“我要做[B作]班长”[BQ,]
(56)去朋友家时我看到了枪,[BC。]我问{CD了}朋友“你为什么带枪,[BC?]”朋友说[BD“]是为了防护自己。[BC。][BD”]
(57)可是父亲有时候[BD,]告诉我{CD了},“[BC『]要[C]是{CJ-sy想}去旅行{CJ+zxy的时间}[BQ,]你应该学习,不要玩,现在只要努力,一定会成功”[BC』]。
(58)父亲说“我养着你们,我的工资都是你们的生活费。”这时[B此]母亲骂{CQ了}他一顿“我养孩子,那么从今天起你照顾孩子吧!我去做工作。”
张金圈、樊留洋指出,现代汉语中的“说了+引语”共有两种类型,其中,“说了1+引语”结构中的引语都是间接引语,经常出现在说理性、论证性的语篇中,主要功能是为了增强信据力,如:“老板说了,他不同意这件事。”其中的“了”是表示动作行为完成的“了1”。“说了2+引语”中的引语都是直接引语,“说”表示的转述行为与之前小句所表示的动作行为之间存在明显的时间相继性,该结构的主要功能是凸显前景信息,标示情节的转移,如:“有一天玩着玩着,周成王就跟他说了,‘将来我要是当了王,当了皇帝,我一定要封你为最大的官。”其中的“了”是表达事态出现变化的“了2”[16]。例(54)中的“说了”并不符合上述两种情况,而只是客观地叙述过去的言说行为,因此,这里不应加“了”。需要说明的是,如果在“说了”后面加上数量宾语“一句”组成“说了一句”,则该例同样可以成立,并且此时必须出现“了”。其中原因,尚需进一步探讨。例(55)中,引导句是一个否定结构,此时要严格排斥动词后“了”的使用。
例(56)中,引导句使用了“主语+动词+了+简单宾语”结构。当这种格式表示经常发生且比较具体的动作时,一般不能不足,需要有后续句,如:“我吃了饭,就去上班。”[17](P436)如上文所言,直接转述句是一种带有展示性质的元语言成分,类似于言说过程中手势、表情等的展示,它与前后的引导句和其他叙述话语不在同一个层面上,二者之间不存在常规的结构关系,因此,无法帮助“主语+动词+了+简单宾语”结构的引导句实现自足。同时,句中的“了”是一个完成体标记,表示动作行为的完成和实现。而根据文意,这些用例中的引导句都是表达事件进程中的言说行为,并不强调言说行为的完成和实现,因此,无需在言说动词后加“了”。例(57)中,“告诉我了”本身在句法上可以成立,当用于标示情节转移、作为前景信息时,也可以充当直接转述话语的引导句,如:“正在大家不知所措的时候,父亲告诉我了:‘……”但是在该例中,“告诉”之前有时间副词“有时候”,整个小句表达一种惯常行为,与上述条件不符,所以无法成立,而“父亲有时候告诉我”则是一个合法的引导句。
例(58)中,引导句中的“骂他一顿”的无标记解读是表达未然时间,检索CCL语料库可以发现,“骂他一顿”之前通常会出现表达意愿的心理动词或情态动词,如“想”“要”“得”“恨不得”等,而该例却用于现实情态(用时间词“这时”限制),所以无法成立。当添加完成体标记“了”后,“这时母亲骂了他一顿”叙述过去一个完整的言语行为事件,则可以构成一个合法的引导句。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该引导句如果改为“骂他”,同样可以接受;但“骂了他”则因为违反上文所说的句法语义限制而无法成立。
由此可见,直接转述话语引导句中“了”的使用情况非常复杂,因它的隐现所造成的引导句的合法与否,涉及众多因素,还需进行专门的描写分析。
4.经历体标记“过”的偏误,例如:
(59)从我小时候{CQ起},我父母经常跟我说{CD过}“做{CC当做}有理的人比学校的成绩重要的”。
(60)有一天,我对妈妈说{CD过}:“为什么我的爸爸常常不在家?我的朋友都跟他的的爸爸一起玩儿,特别是星期天,他们都全家出去玩儿。我爸爸不爱我们吗?”
引导句中的“言说动词+过”表示该言说行为是曾经发生过的事件,同时,在这一基本意义基础上,与“言说动词+了1”类似,“言说动词+过”也衍生出一定的语篇功能,即曾经存在的某个言说行为及其话语内容,可以作为当前论述的证据或原因,具有增强信据力的功能,如:“毛主席说过:‘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我们都要时刻注意锻炼身体。”不过,例(59)、例(60)却并不符合“过”的基本用法和“言说动词+过”的语篇功能等要求。例(59)中,句首状语“从我小时候{CQ起}”和引导句中的副词“经常”,表明它们所修饰限制的言说事件是一个惯常行为,这与“过”所表达的曾然事件存在明显冲突,因此,这里不能用“过”。例(60)中,句首状语“有一天”用于引入一个单纯的对过去时空中某一事件的叙述,而不是将一个曾然言说行为作为另一事件的原因或论述的证据,因此,也不能加“过”。
(二)直接转述话语中与转述句有关的偏误
这类偏误/错误虽然数量不多,但其成因却能引发人们对直接转述话语的次类划分以及使用规则和条件的很多思考。例如:
(61)那时候发生一件事。就是看我们生活太辛苦的样子,有人对父母说,[BQ“]我可以帮助你们。[BQ”]这个意思是他(我爸爸的上司)说,[BQ“]你们的孩子中那个中间的老三卖我吧。我好好照顾他。我们有两个女儿,但是没有儿子,可以吧。[BQ”]他这样说。可是那时候我妈妈完全不赞成。因为,[BQ“]孩子们都是从上帝借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应该好好照顾他们。如果我把这个老三给你的话,我怎么对得起{CC對不起}上帝呀。虽然生活辛苦,但是我们一定抚养这个孩子。[BQ”]
(62)我认为“安乐死”是好的。法律上也不许犯罪是最好,并且经济上的问题也可以解决。我说[BD“]为什么安乐死好。[BD”]因为一位人得了一种不治之症,十分痛苦,我们也觉得使人痛苦。
(63)他全身疼痛,流着眼泪要求你“杀我吧!”。这时候能够使他解脱痛苦的唯一的方法是什么?我认为这就是“安乐死”。
(64)即使妻子十分痛苦,要求我帮助她自杀,也{CJX}{CD犯罪}便是犯罪。一个人的生命比地球更重要{CJX},俗话说。所以法律制裁是正确的。
例(61)中的划线部分是作者直接转述妈妈的话语,由于它的功能和目的是在于完整展示另一个言说行为,无法与连词“因为”所要求的后续句的逻辑说明关系实现契合,所以不合法。当然,并非所有的直接转述句都不能充当原因分句。例如:
(65)当时强调“教育要革命,学制要缩短”,所以初中、高中都压缩成了两年,统共四年的中学生活里,因为“不但要学文,还要学工、学农、学军,批判资产阶级”,所以正经在课堂里上课的时间,归里包堆也就半年。(刘心武《钟鼓楼》)
上例中的划线部分放在引号内,说明作者也是将其视为一种直接转述话语的,但却合法充当了“因为”所引导的分句。对比例(61)和例(65),可以发现,前者展示的是特定语境中特定主体的特定言说行为,而后者展示的则仅仅是某一特定的话语形式;与前者相比,后者更容易实现从转述层面的元语言重新识解为直述层面的对象语言的过渡,因此,例(65)一类的说法完全可以接受。
例(62)中,作者首先指出“我认为‘安乐死是好的”,然后通过设问方式引述这一观点并解释原因。但作者在使用引号标记所引的上文言语片段时,却出现了话语的杂糅,即被引述部分只是“安乐死好”,疑问词“为什么”应当是对“说‘安乐死好”这一行为原因的提问,而非对“安乐死好”这一判断的提问。因此,正确的表达应该是“我为什么说‘安乐死好”。语料标注者只标注为引号的多余,并未认识到真正的错误所在。
例(63)中,划线部分是一种不太规范的表达。如果将“流着眼泪要求你”和“‘杀我吧!”分别作为两个独立小句,在前一小句后加以停顿,同时在口头上增加“‘杀我吧!”的情感色彩和祈使口气,整个语段的可接受性较强。但是,如果将“流着眼泪要求你”和“‘杀我吧!”视为一个完整的兼语小句,则可接受度较差,因为兼语结构“要求你VP”中的VP应当是“你”实施的某一行为,而“‘杀我吧!”则是展示的另一主体的言说行为,所以造成了表达上的冲突。这可以视为是直接转述和间接转述的杂糅,“他说:‘杀我吧!”是直接转述,“他要求你杀他”是间接转述。根据从直接转述话语到间接转述话语的转换规则,如果直接转述句是祈使句,则相应的间接转述句不但要有人称、时间等指示成分的转换,而且直接转述引导句中的言说动词,也要根据祈使句的语力类别转换为不同的施为动词,如“要求”“请求”“建议”“命令”等。因此,该例中的表达可以有两种修改方式:“他全身疼痛,流着眼泪要求你杀他。”或者“他全身疼痛,流着眼泪对你说:‘杀我吧!”
按照人们的一般认识,在书面文本中,直接转述话语的引导句与转述句的语序比较灵活自由,引导句既可以放在转述句之前或之后,也可以插入转述句之间。例(64)却表明引导句“俗话说”后置于转述句是不合规范的。这也启发我们:引导句的语序可能会受制于其次类划分,不同类型的引导句可能会有不同的语序要求。这需要研究者根据实际语料做进一步的细致考察。
(三)直接转述话语中标点符号的偏误
吕叔湘、朱德熙将本文所说的直接转述话语称为“直接引”,作者指出,直接引的句子一般放在引号中,如果不用引号,前边最好用冒号,不要用逗号,以免使人误会是间接转述话语[18](P330)。其实,在汉语小说文本中,作者为了避免形式上的单一化,往往对直接转述话语的标点方式进行灵活调整。就文学作品来说,偶尔进行这样的安排尚无可厚非,但是在以追求规范为首要目标的二语写作练习中,诸如此类的现象则很难看成写作者为追求变化而有意为之的结果,而只能视为学习者对直接转述话语标点符号使用规则掌握不全或写作态度不够严谨所致。
从HSK动态作文语料库的标注来看,标注者对未正确使用冒号和引号的直接转述话语进行了偏误标注,认为它们存在着标点的误用或缺失。例如:
(66)第三个和尚一边听孙和尚的意见,又一边听空和尚的道理,他突然开口说[BQ:]“我叫悟,其实我当和尚以前学过自然学,如果您们不介意的话听我的意见好吗?”
(67)第三个和尚终于开了口:[BC,]“你们两个去山下抬水吧”。
(68)另外一个和尚说:[BQ“]不行,我们必须用水。所以还是我们应该下山抬水。不过抬水的时候抬得少一点,怎么样?[BQ”]
(69)那时候,突然弟弟的手机响了。是大弟。他说:[BC;][BQ“]我有要给你见面的人。在这里等着”[BC。]
(70)他说[BQ:]“[BC‘]你做得{CJ-zy很}好,谢谢!有机会再来吧[BQ。]”[BC]
(71)我爸爸说“高毅,我不是生你扔掉东西的气,而我生你骗我的气。如果你这样下去,大家老不相信你,将来也许在很重要的局面下,“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我担心你的将来。”
(72)第二个和尚突然开口说:[BC,]“[BC「]那这样{CQ的}方法{CC方式}怎么样?我们招聘一个青年人,让他去山下抬水。”[BC」]
(73)可是父亲有时候[BD,]告诉我{CD了},“[BC『]要是{CJ-sy想}去旅行{CJ+zxy的时间}[BQ,]你应该学习,不要玩,现在只要努力,一定会成功”[BC』]。
例(66)中,引导句后缺失冒号,标注者进行了添加;例(67)中,则在引导句后使用逗号,标注者将它修改为冒号。这两种情况在我们考察的语料中比较普遍,这可能与日语书面文本中较少使用冒号(:)这一标点符号有关。例(68)中,直接转述句未加引号,标注者标注为引号缺失。例(69)中,直接转述句同样未用引号,并且在引导句后错用了分号。例(70)中,将直接转述句放在单引号内,标注者标注为单引号的误用和冒号的缺失。例(71)中,在直接转述句中嵌套了另一层直接转述句,按照汉语标点符号的使用规范,第二层转述句应该用单引号(‘)标识,这里错用了双引号。可能是出于疏漏,标注者并未对此进行标注。例(72)、例(73)中,写作者误用了日语书面文本中的引号形式(「」和『』)。
在日本学习者的汉语中介语语料中,上述标点符号的不规范用法都有若干用例,有些还比较常见,说明这是一种具有规律性的偏误现象,需要引起对日汉语教师的高度关注,并在写作教学中给予足够的重视。
由于HSK动态作文语料库中收录的都是高级汉语学习者的语料,因此,直接转述话语的总体使用情况比较乐观。学习者大都能够掌握直接转述话语的基本结构,部分学习者甚至具有非常娴熟的直接转述话语运用技能,这主要表现为不同管领词的选取、管领词修饰语以及不同类型引导句和转述句的恰当使用等。与此同时,与汉语目的语文本相比,日本学习者汉语中介语系统中的直接转述话语也存在需要改进之处,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引导句和转述句的语序单一,基本都采用“引导句+转述句”的模式,缺乏必要的变化;二是管领词类型相对单一,超过八成的用例都使用“说”,使用频率远超正常的汉语文本,其他管领词仅偶现于个别语篇;三是冒号和引号使用不够规范的现象较为普遍。总之,直接转述话语是叙事语篇中比较常见的语言现象,但现有的汉语二语写作教材对此关注不够,国际中文教师应针对学习者习得、产出直接转述话语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进行更有针对性的教学。
附录:
HSK动态作文语料库语料标注及代码说明
[C]:错字标记,用于标示考生写的不成字的字。用[C]代表错字,在[C]前填写正确的字。
[BC]:错误标点标记,用于标示使用错误的标点符号。
[BQ]:空缺标点标记,用于标示应使用标点符号而未用的情况。把[BQ]插入空缺标点之处,并在[BQ]中BQ的后面填写所缺的标点符号。
[BD]:多余标点标记,用于标示不应使用标点符号而用了的情况。把多余的标点移至[BD]中BD的后面。
{CC}:錯词标记,用于标示错误的词和成语。
{CQ}:缺词标记,用于标示作文中应有而没有的词。在缺词之处加此标记,并在{CQ}中CQ的后面填写所缺的词。
{CD}:多词标记,用于标示作文中不应有而有的词。把多余的词移至{CD}中CD的后面。
{CJ}:病句标记,用于标示错误的句子。
{CJ-/+sy}:述语残缺或多余。
{CJ-/+zy}:状语残缺或多余。
{CJ-/+zxy}:中心语残缺或多余。
{CJX}:语序错误标记,用于标示由于语序错误而造成的病句。标在语序错误的词语的后边。如果是相邻的两个成分语序错误,按照自然顺序,把{CJX}标在前一个成分的后边。
{CJgd}:固定格式错误标记,用于标示固定格式搭配上的错误。
{WWJ}:未完句标记,用于标示没写完的半截子的句子。标在未完成句的末尾处。
参考文献:
[1]Gebril,A. & Plakans,L.Investigating Source Use, Discourse Features, And Process in Integrated Writing Tests[J].Spaan Working Papers in Second or Foreign Language Assessment,2009,(7).
[2]Pecorari,D. & Shaw,P.Types of Student Intertextuality and Faculty Attitudes[J].Journal of Second Language Writing,2012,(2).
[3]马蓉.二语学术写作的文献引用能力及其个体影响因素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
[4]何丹.来华留学生间接引语偏误分析及教学策略[D].广州: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
[5]唐善生.汉语话语指研究[M].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6]董秀芳.实际语篇中直接引语与间接引语的混用现象[J].语言科学,2008,(4).
[7]Li,Charles N.Direct and Indirect Speech:A Functional Study[A].In Coulmas,F.(ed.).Direct and Indirect Speech[C].Berlin:Mouton de Gruyter,1986.
[8]徐赳赳.叙述文中的直接引语分析[J].语言教学与研究, 1996,(1).
[9]相原茂.谈信息名词[A].第三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会务工作委员会.第三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选[C].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1.
[10]方梅.北京话里“说”的语法化——从言说动词到从句标记[A].全国汉语方言学会《中国方言学报》编委会. 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第十二届年会暨学术研讨会第三届官话方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6.
[11]刘丹青.汉语里的一个内容宾语标句词——从“说道”的“道”说起[A].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中国语文》编辑部.庆祝《中国语文》创刊50周年学术论文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12]唐正大,单俪娉.言语—体势联动与直接引语结构“VP道”[J].世界汉语教学,2020,(4).
[13]Clark,H.H. & Gerrig,R.J.Quotations as Demonstrations[J].Language,1990,(4).
[14]邢福义.汉语复句与单句的对立和纠结[J].世界汉语教学,1993,(1).
[15]张金圈.从跨语言视角看拟声词、名称词与引语的关联性[J].语言教学与研究,2022,(5).
[16]张金圈,樊留洋.“说了+引语”的结构特征与话语功能[J].汉语学习,2023(待刊).
[17]孔令达.影响汉语句子自足的语言形式[J].中国语文, 1994,(6).
[18]吕叔湘,朱德熙.语法修辞讲话[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A Study of Direct Reported Speech in Chinese Interlanguage of Japanese Learners
Zhang Jinjuan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Qufu Normal University, Qufu 273165, China)
Abstract:This study examines the use of direct reported speech in Chinese interlanguage produced by Japanese learners. Data was collected from the HSK Dynamic Composition Corpus, which contains written compositions from Japanese learners of Chinese. The study found that most learners are able to use the basic structure of direct reported speech, and some use it skillfully by selecting appropriate speaking words, using speaking word modifiers, and varying the types of introductory and quoted clauses. However, compared to standard Chinese, the learners' use of direct reported speech has several areas for improvement, including a limited variety of speaking words, a single word order for introductory and quoted clauses, and nonstandard use of colons and quotation marks.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instruction on direct reported speech could be beneficial for Japanese learners of Chinese in improving their language proficiency.
Key words:Chinese language learners of Japanese;interlanguage;direct reported speech
基金項目:2022年国际中文教育研究课题重点项目“汉语二语学习者的转述话语及转述能力发展研究”(22YH45B)
作者简介:张金圈,男,曲阜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教授,文学博士。
①中介语语料中标注符号的说明,详见文末附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