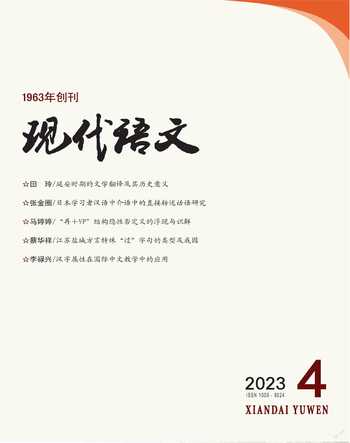《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与《汉语国际教育用音节汉字词汇等级划分》的词汇对比研究

摘 要:《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于2021年7月1日正式实施,其词汇表的研发参考了2010年发布的《汉语国际教育用音节汉字词汇等级划分》。两个词表的收词情况既有联系又有不同。对两者的收词情况、词汇等级调整情况、词汇增减变化等情况进行分析,探讨《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的实施对词汇教学的指导作用,并提出国际中文教育中词汇教学的具体策略。
关键词:《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汉语国际教育用音节汉字词汇等级划分》;词汇;教学;国际中文教育
《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以下简称《等级标准》)[1]于2021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这是国际中文教育70多年历史上由教育部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面向外国中文学习者发布的首个全面描绘、评价其中文水平和语言技能的规范标准[2](P31)。《等级标准》的发布实施,将成为国际中文相关标准化、规范化语言考试的命题依据以及各种中文教学与学习创新型评价的基础性依据。《等级标准》的出台并非一蹴而就,从2010年的《汉语国际教育用音节汉字词汇等级划分》(以下简称《等级划分》)[3]再到2021年的《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收词情况、词语等级等都发生了一些变化。
一、从三级到“三等九级”
《等级标准》词汇的研发参考了《等级划分》,两者既有联系又有传承。《等级标准》提出的三等九级新范式,是基于2010年第一个国家标准《等级划分》大规模样本统计数据分析和多元化比照整合构建的[4](P149)。
《等级标准》提出了三等九级的新框架,所谓“三等九级”,指的是初等一至三级,中等四至六级,高等七至九级[5](P6)。《等级划分》里采用的标准是一级、二级(中级)和三级(高级)。一级为初级,又称“普及化等级”,在一级词汇表中,又分为两个档次,第一档次为最常用词,第二档次为常用词。其中,第一档次的最常用词包含最低入门等级最常用词以及最常用词。《等级划分》对二级(中级)词汇没有再进行水平细分。在三级(高级)词汇中,分为了高级和高级“附录”,相当于《等级标准》里的高等七—九级。两者的收词情况,具体如表1所示:
三等九级的框架是《等级标准》的基础架构,是《等级标准》最主要的标志,是中文国际教育面向全球化、国际化、规范化长远稳定发展历史的选择,是认知新时代《等级标准》的新维度、新定位[4](P149)。《等级标准》采用三等九级的划分方法更为清楚明了,无论是对学习者还是对教师而言,使用起来都更加直观,同时也能更好地对接国际标准。
二、《等级标准》的收词变化
《等级标准》词汇表共收词11092个,与《等级划分》普及化等级、中级、高级及高级“附录”三个等级的词汇数量一致。通过对二者收词情况的比较,可以看出,《等级标准》发生了以下变化:
(一)词语跨等调整
首先,《等级标准》对《等级划分》中的收词进行了跨等调整。这类情形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等次调低,一种是等次调高。
1.等次调低
所谓“等次调低”,是指某个词语在《等级划分》中的级别比《等级标准》中的高,在《等级标准》中调低了。据统计,这样的词语有175个[6](P35)。在等次调低的词语中,以名词居多,尤其是和生活、工作相关的常用词语。例如:
生活类:衬衫、衬衣、大门、单元、电动车、店、定价、饭馆、房价、高跟鞋、高价、工作日、红包、裤子、快递、票价、晴天、裙子、上衣、鼠标、卫生间、药店、羽绒服、信封、姓名等;
饮食类:饼、饼干、果汁、烤鸭、美食、奶茶、薯片、薯条、晚餐等;
娱乐类:户外、动物园、歌词、旅行车、喜剧等;
工作學习类:表格、词语、分组、简历、班级等;
水果类:苹果、梨、香蕉等;
动物类:狗、猪等;
亲属称谓:姑姑等。
《等级标准》之所以把这些词语的等次调低,主要是为了解决学生生活学习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体现了急用先学的原则。这些词语义项较少,词义透明度高,相对来说更容易掌握,教会学生这些词语,能够满足基本交际的需求。这也符合《等级标准》里所提到的“3+5”新路径,通过语言的量化指标,设置合适的话题,布置适当的任务,从而使学生尽快掌握语言交际能力。
在等次调低的过程中,《等级标准》遵循了两个基本原则:一是遵循共同语素原则,二是遵循语义场原则。就遵循共同语素原则而言,通过《等级标准》的调整,包含共同语素的一组词进入到同一等,但级别略有不同。比如,由“窗”这个共同语素组成的词语,“窗帘”由原来的高级调整为中等五级、“窗台”由高级调整为中等四级、“窗子”则由普及化等级调整为中等四级,再加上等级没有改变的“窗户”“窗口”,这一组以“窗”为共同语素的词语都处于“中等”等次。
就遵循语义场原则而言,这主要体现在对同一语义场词语的处理方面。比如,同样是表示时间的“前年”“今年”“明年”“后年”,在《等级划分》中分属于不同的等级,“前年”“后年”属于中级词,而“今年”“明年”则属于普及化等级;经过调整后,这一组和时间相关的词语均调整为初等等次。类似的处理还有“后头”一词,从原来的高级调整为四级,这样就和“前头”同属于中等等次。
2.等次调高
所谓“等次调高”,是指某个词语在《等级划分》中的级别比《等级标准》中的低,在《等级标准》中调高了。等次调高的情况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从普及型等级调整到中等等次,这样的词语约占67%,比如:白酒、并(动)、不管(连)、产量、称(称为、动)、承认、冲(动)、出口(离合词)、窗子、大姐、大妈、大众等。由中级调到高等等次,这样的词语约占33%,比如:报(动)、彩电、产物、电报、都会、粉丝、腐败、甘心、割、革命、工会、公益、共识、骨头、观测、官员、国防、敬礼、境外、境内、兼、魔术、奇迹、卡(动)、卡子、签(名)、事务、释放、水稻、丝、丝毫、条约、同志、统治、物资、袭击、响应、像、学历、学士、演习、一度、议会、拥护等。极个别的词语则由初级调整到高等等次,比如:“像(名)”“非法(形)”“同志”。
第二,语义场相关的词语一并调整。比如,“出口”和“进口”二词,原先均在普及化等级,在《等级标准》中都跨等调整为四级。“境内”和“境外”也属于这种情况,它们同时由中级调整为高等。
第三,从初级调整为中等的词语中有很多兼类词。这样的词语有:“高度(名、形)”“根据(动、介、名)”“会谈(动、名)”“将(副、介)”“进口(动、名)”“民主(名、形)”“万一(名、连)”“选举(动、名)”“依据(动、名)”“一路(名、副)”“与(介、连)”“组织(动、名)”“作为(介、动)”等。
第四,同音同形词的等次调整。原先在《等级划分》中属于同一级别的同音词,在《等级标准》中进行了重新调整。比如,“称一称”的“称”和“称为”的“称”,在《等级划分》中都属于初级,“称一称”的“称”为最常用词,而“称为”的“称”为常用词;经过调整,“称一称”的等级不变,仍为初级,而“称为”的“称”则调到了中等五级。类似处理的词语还有“报”“刻”“签”等。作为动词的“报”具有多个义项:a.告诉:报告;b.回答:报以掌声;c.报答:报效;d.报销:报差旅费;e.报复:报仇;f.报应:现世报[7](P48)。由于该词的动词义项丰富,学习难度较大,因此,被调到高等。而“报(名)”的义项单一,学习难度相对较低,故仍在初等。
第五,逐渐被新生事物所取代,在生活中的重要性降低,或者使用频率不高的词语。比如,“彩电”“电报”等词由中级调整到高等。随着黑白电视机的消失,不存在和“彩电”的对比,“彩电”一词的使用频率明显降低;“电报”也逐渐被现代通信手段所取代,因此,两词在《等级标准》中的词汇等级变高。“白酒”“皮鞋”等词语也是如此。
(二)《等级标准》新增词语
词表的制定是某个时间段基于语料库进行词频统计的结果,而词汇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因此,随着时代的变化,词表的收词也会发生变化。与《等级划分》相比,《等级标准》新增了53个词语,这些词语分布在初、中、高三等。其中,分布在初等的有12个,它们是:不客气、称(动)、读音、短裤、多云、可乐(名)、木头、生词、听写、外卖、音节、预习;分布在中等的有16个,它们是:…分之…、打(量)、多样、二维码、附件、火腿、料(动词)、毛笔、期中、期末、首(名)、所(助词)、微博、微信、消费者、原告;分布在高等的有25个,它们是:伯父、伯母、厂家、大数据、俄语、工科、红薯、理科、聋人、农民工、配送、人工智能、时尚、填空、条例、团伙、微型、物流、摇晃、疫苗、余额、侦察、正能量、志气、纵然。
在新增加的词语中,有些是和学生的学习情况密切相关的,如“读音”“预习”“听写”“生词”“工科”“理科”等;有些是随着社会发展、科技进步而出现的,如“大数据”“配送”“物流”“人工智能”“二维码”“微信”等。
(三)《等级标准》删减词语
与《等级划分》相比,《等级标准》还删减了一些词语。在删减的词语中,有些是现代社会生活中不再常见和常用的词语,如“包干”“大锅饭”“公用电话”“托儿所”“挂历”等;有些则是在交际中易于引发负面联想而造成误会的词语,比如,删除了“聋子”一词,而新增了“聋人”一词。此外,还有一些在严格意义上不属于词语而属于词组的,如“海上”“街上”“脸上”“墙上”“山上”等方位词组,“抽出”“放在”“回乡”“上街”“上山”等动宾词组、动补词组,上述情况在《等级标准》中都删除了。
(四)其他变化情况
有些词语在《等级划分》里有两种写法,在《等级标准》中都统一为一种写法。这样的词语有:成分(成份)、訂单(定单)、订婚(定婚)、混浊(浑浊)、看作(看做)、摩擦(磨擦)、起程(启程)。其中,括号之前的词语为《等级标准》所采用的写法。同时,有些词语的书写形式亦发生了改变。在《等级标准》中,“同仁”改为“同人”、“拉拉队”改为“啦啦队”、“执著”改为“执着”、“下工夫”改为“下功夫”、“作证”改为“做证”等。
在《等级划分》中词性分开的词语,在《等级标准》中都进行了合并,因此,原来的两个词在《等级标准》中就变成了一个词。比如“代”,原来是动、名各为一个词,在《等级标准》中则合并为一个词,注明动、名词性。类似的情况还有:“方”“光”“根本”“将”“角”“进口”“另外”“轮”“每”“偏”“气”
“如”“上”“下”“虚”“则”“直”“张”“在”“镇”等。
在《等级标准》中,有些词语的解释更为明确、更为规范。比如“高尔夫球”,原先称“高尔夫”,《等级标准》中则增加了一个说明性的语素“球”,明确了这个词语的内涵。再如“面”,在《等级划分》中只列出为名词词性,在《等级标准》中则加以区分,作为“见面”的“面”是面1,作为“面条”的“面”是面2;而作为量词的“面”,亦归属到面1。《等级标准》还对个别词语的词性进行了区分,如“则”区分为则1和则2,其中,则1是连词,则2是量词。
此外,《等级标准》还对一些词语的读音进行了订正。如“指甲”,在《等级划分》中的读音为zhījia,在《等级标准》中更正为zhǐjia;“晕车”由yūnche更正为yùn//che;“指头”由zhítou更正为zhǐtou。
总的来看,《等级标准》中词语等次的调整、词语数量的增删,都反映出该标准是遵循了科学性的原则的,既符合学习者的认知规律,也符合循序渐进的教学规律。同时,它所收录的词语还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日常交际能力,能够让学生真正地学以致用。《等级标准》对某些兼类词通过合并在一起并采用词性标注的方法来加以区分,使得读者使用起来更为方便,操作性更强。而《等级标准》对有些词语书写形式的更正及读音的修订,也反映出它作为一个国际性标准的规范性。
三、《等级标准》的词汇联通
《等级标准》将音节、汉字、词汇、语法四种语言基本要素作为衡量中文水平的“四维基准”。因此,《等级标准》在制定这四个要素量化指标时,充分考虑了各个要素之间的联系。
在一级500个词语中,有很多词语作为语法点再次出现。如方位名词“上”“下”“里”“外”“前”“后”
“左”“右”等;疑问代词“多”“多少”“哪里”“哪些”;人称代词“我(们)”“你(们)”“他(们)”;指示代词:“这”“那”“这里”“那里”“这些”“那些”等。此外,还有数词、量词、副词、介词等。据统计,这部分词语共有108个,占一级词汇总量的21.6%。其中,虚词(副词、介词、连词、助词、语气词)有38个,占一级全部语法词的35.2%。
据我们统计,在二级的772个词语中,作为语法点出现的有88个,占11.4%。在三级的973个词语中,作为语法点出现的有85个,占8.7%。在四级的1000个词语中,作为语法点出现的有53个,占5.3%。在五级的1071个词语中,作为语法点出现的有49个,占4.6%。在六级的1140个词语中,作为语法点出现的有51个,占4.5%。在高等七—九级的5636个词语中,作为语法点出现的有102个,占1.8%。在这102个词语中,数量最多的是副词,有49个,占该等级全部语法词的48%。
从三级开始,语法点出现了一些固定短语。这些固定短语同样出现在词汇表中,如:看起来、有的是、看来、来得及/来不及、说不定、一般来说、得了、不得了、不敢当、用不着、不怎么样、不怎么、好(不)容易、就是说/这就是说、算了、别提了、除此之外、归根到底、没说的、无论如何、也就是说、由此可见、与此同时、这样一来、综上所述、总的来说、总而言之等。在国际中文教学时,则不能将这些短语仅仅作为词语来对待,而是要把抽象的语法现象落实到一个个具体的短语上面。也就是说,词汇教学要与语法教学相结合,不仅要理解它们的语义,更要把握它们的用法,并通过词语的具体用法来掌握相关语法。
总之,如果从一个个的具体词语来看,上述词语显然均属于词汇教学;而如果从词语的类别来看,它们又都属于语法教学。换言之,词汇教学和语法教学不是截然分开的,而应该是相辅相成的[8](P150)。事实上,词类教学在语法教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据王鸿滨统计,在《语法等级大纲》各类语法点的数量与占比中,比例最高的是词类,占35.84%,固定短语则占5.07%[9](P29),两者合计占到40%以上。因此,在国际中文教学时,教师要格外重视语言各个要素的联通,也就是《等级标准》里所提到的“四维基准”。
四、《等级标准》下的词汇教学策略
词汇在二语学习中占据重要的地位,贯穿了汉语教学的始终,词汇教学的效果直接影响着留学生汉语的整体水平[10](P41)。词汇学习的目的是顺利完成交际任务,实现交际目标。第二语言学习首先必須掌握一定量的词汇,如果没有一定量的词汇作为基础,学习者对语言的处理就会十分缓慢,从而影响到学习的效果。
(一)以《等级标准》为规范,指导词汇教学
作为面向新时代的新规范,《等级标准》用于指导国际中文教育的教学、测试、学习与评估。在国际中文词汇教学时,我们应以《等级标准》为参考,对教材生词表进行词语等级核对,明确词语等级,确定哪些词语需要重点讲解与操练,哪些词语需要替换、补充或删减,在这一基础上,制定科学的教学目标。同时,《等级标准》中已经修订了的读音或写法,在教学时必须认真贯彻执行。
(二)急用先教急用先学,打好词语学习基础
在《等级标准》中,很多词语的等次下调,其中,有些是学习者学习生活中会经常遇到的。根据急用先教的原则,来解决学生学习、生活的“急难愁盼”问题,因此,应在初、中级阶段补充一些常用的专有名词,充分利用好5%的弹性。那么,如何利用好这5%的弹性呢?《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国家标准·应用解读本)》提到:为适应各地中文教学多样化、本土化的需求,每一级的音节、汉字、词汇、语法各项量化指标在教学实践中可以灵活掌握,既可以从中替换5%左右的内容,也可以减少5%左右的内容[11](PⅡ)。这就为词汇教学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和自由度,也符合二语习得的i+1
理论。对一些专有名词,我们可以适当替换,如各国各地的风俗习惯、风景名胜、特有食物等。也可以按照同一语义场原则进行补充,如《等级标准》中收有“冠军”“亚军”(都是五级词),但没有收录“季军”,在教学时就可以补充,使这一组词语形成一个语义场。
在进行国际中文词汇教学时,教师还可以根据学生需求与词语难度进行灵活调整。《等级标准》中,一些具有密切联系的词语并不处于同一级别,甚至是跨越了词汇等次,考虑到教学的实际需要,可以把它们放在一起进行教学。比如,“大使馆”“留学”“办理”都是三级词汇,而“签证”则属于五级词汇,在实际教学中,可以把这一组词群同时教给学生,并创设语境,让学生尽快掌握它们的用法。
(三)搭建词语网络,掌握成句表达
《等级标准》中新增了一些词语,对于这些新出现的词语,不仅要了解语义,还要让学生能够实际运用,可以通过补充这些词语的引申或隐喻的意义,使学生掌握其语用功能。语言教学的根本任务是培养学习者在不同情境下运用语言进行交际的能力,语言教学和语言学习都要突出交际性。国际中文教师应通过新词语的教学为学生搭建一个词语网络,而不仅仅是学习几个孤立的词语。比如“微信”一词,与此相关的用法有:微信扫码(扫微信)、微信扫一扫、微信朋友圈、微信好友、微信支付、微信聊天、微信二维码等。我们在讲解“微信”一词时,首先要确定“扫”的引申意义,其次要分析和“微信”有关的重点搭配,通过这种方式,使学生掌握“微信”一词的主要用法。同样,跟“外卖”一词有关的用法有:点外卖、送外卖、外卖软件、外卖小哥、外卖骑手等。
国际中文词汇教学应注重有效输出,在词汇层面上,还有很多短语语块以及惯用语语块,它们在《等级标准》中均以固定格式体现。因此,国际中文教师还应重视学生的语块和成句表达训练,帮助学生通过模仿记忆,建立模式,养成语感,在学生遇到真实交际场景时,能够说出有意义的句子、语段乃至篇章。我们要鼓励学习者使用语块策略,把语言形式和语言功能结合起来,使学习者真正掌握相关用法,实现自由交流。
词汇的学习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因此,教师在进行词汇教学时应循序渐进,难点分散,不要期望在一节课中让学生掌握一个词的不同词性的所有用法。比如,“光”是一个同形同音词,它可以作副词、名词、形容词,在《等级标准》中划分为三级。在具体的教学中,可以对“光”不同词性的不同用法分次、分级讲解,通过对词汇类型的区分,来实现学习任务的有效分解。同时,就多义词而言,对其义项也不宜过度扩展,应选取和学生学习生活、日常交际相关的常用义项,让学生真正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
综上所述,本文对《等级标准》和《等级划分》的收词情况、等级调整情况、增减变化情况进行了对比,探讨了《等级标准》的实施对词汇教学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词汇教学策略。我们也注意到,还有个别词语在《等级标准》中没有明确说明。比如“粉丝”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中有两种解释[7](P386):一是“用绿豆等的淀粉制成的线状食品”,标为粉丝1;二是“指迷恋、崇拜某个名人的人,[英fans]”,标为粉丝2。我们认为,这两个语义应加以区分,并进行等级划分。再如三级词汇中的“通常”,其词性只标注了“形”,但它还有副词的用法,特别是在三级语法点中出现了作为频率副词的“通常”。因此,我们认为,应该为“通常”的词性增补副词用法。总之,二语学习者的词汇量和词汇掌握程度,是衡量其二语水平的重要指标。作为新时代的国家标准,《等级标准》为汉语词汇教学提供了科学依据和重要参考,它在规范词汇教学的同时,也有助于提高词汇教学和学习的效率。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M].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21.
[2]刘英林,李佩泽,李亚男.《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的中国特色和解读应用[J].国际汉语教学研究, 2022,(2).
[3]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汉语国际教育用音节汉字词汇等级划分[M].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0.
[4]刘英林,李佩泽,李亚男.汉语国际教育汉语水平等级标准全球化之路[J].世界汉语教学,2020,(2).
[5]刘英林.《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的研制与应用[J].国际汉语教学研究,2021,(1).
[6]李华.《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词表改进的分析——基于与《汉语国际教育用音节汉字词汇等级划分》词表的对比分析[J].语言教学与研究,2023,(2).
[7]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Z].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8]杨玉玲.汉语要素教学法(语法词汇教学篇)[M].北京: 北京語言大学出版社,2020.
[9]王鸿滨.《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中语法等级大纲的研制路径及语法分级资源库的开发[J].国际汉语教学研究,2021,(3).
[10]李如龙,吴茗.略论对外汉语词汇教学的两个原则[J].语言教学与研究,2005,(2).
[11]刘英林,马箭飞,赵国成.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国家标准·应用解读本)第二分册:词汇[M].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21.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Vocabulary of Chinese Proficiency Grading Standards for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and The Graded Chinese Syllables, Characters and Word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Teaching Chinese to the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
Li Shaoho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Law, 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Handan 056038, China)
Abstract:Chinese Proficiency Grading Standards for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was officially implemented in 2021. The standards was based on The Graded Chinese Syllables, Characters and Word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Teaching Chinese to the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 that was released in 2010. Both of them are related and differen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llection of words, the adjustment of vocabulary levels and vocabulary increases and decreases.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guidance of the standards on vocabulary teaching, and puts forward the strategies of vocabulary teaching for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Key words:Chinese Proficiency Grading Standards for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The Graded Chinese Syllables, Characters and Word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Teaching Chinese to the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vocabulary;teaching;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作者简介:李少虹,女,河北工程大学文法学院讲师,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