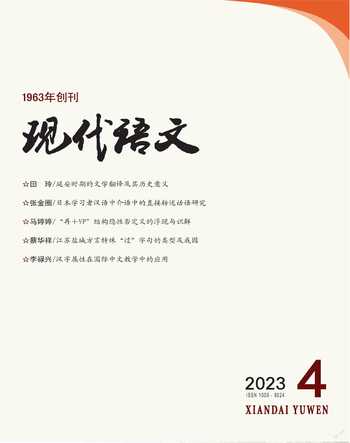论面向国际中文教育的中医语体语法教学



摘 要:中医语体蕴含着鲜明的中医思维、体现了中医学专业特色的句法特点和话语方式。它既具有正式体、典雅体的特点,又具备中医语域特定的话语模式。对中医汉语语法教学的概念予以界定,在以教材语料和专家语料为主的封闭语料库中,考察中医汉语各层级语法单位的分布和特点,主要包括:名词、动词、虚词、古句型、四字格等。中医汉语的特殊话语方式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主要表现为:有标复句—无标/单标复句/意合/流水句的共存,引用古语,特定的篇章构造模式等。在此基础上,构建出“词法—构式”的中医汉语语法教学体系,并以“气”类构式为例,对中医汉语语法教学展开探讨。
关键词:中医语体;正式体;典雅体;中医汉语构式;话语方式;中医汉语语法教学
一、中医语体语法与中医汉语教学
冯胜利指出:“语体是实现人们在直接交际中最原始最基本属性的、用语言来表达或确定彼此之间关系和距离的一种语言机制。”[1](P1)作者还将语体划分为两组基本范畴:正式与非正式,典雅与通俗。中医学是一门极富中国文化色彩的学科,与其他专业领域用语相比,中医汉语专业词汇及话语的特殊性极为明显。
(一)中医语体语法
总的来看,中医语体是蕴含着中医思维、体现中医学专业特色句法特点和话语方式的一类语体。它既具有正式体/典雅体的特点,又具备中医学语域特定的话语模式。因此,中医语体语法也体现出语体语法的鲜明个性,应视为正式体/典雅体下位分支的一部分,不仅具有此类语体的共性,亦具有本领域的特性。通过对自建中医语料库的分析,可以发现,中医语体语法体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中医语体的文本,单双音节并存,具有古代汉语的韵味。比如:“血属阴而主静,气属阳而主动。”[2](P5)此例中的“血属阴”“气属阳”为单音节+单音节+单音节,如果替换为双音节的“属于”,就失去了中医汉语的独特韵味。
第二,多用四字格表达,内部单双音节交替,韵律感较强。比如:“发汗解表”“扶正祛邪”“固脱生津”“活血化瘀”“调和气血”“和解表里”“虚则补之” “实则泻之”“夏伤于暑”等。
第三,保留了古代汉语的语法结构、用词特点,这些结构或词汇大多是从医学典籍中萃取而出,历经数代医书及医师,约定俗成。比如:“常山畏陈皮。”[2](P6)“肝属木,在液为泪。”[2](P38)
第四,专名术语。这些术语有的仅在中医学用语中出现,如“津液”;有的也在其他领域使用,但是词义不同,如“气”。
第五,中医汉语的话语方式具有特定的语域特点,它主要表现在无标复句和古汉语虚词系统、句式的套用。这是由医学经典的时代特性所决定的。无标复句在古代典籍中的运用较为普遍,这种话语方式也被中医文本沿袭下来,比如:“学医不知经络,开口动手便错”[2](P133),这是表假设关系的;“头痛医脚”,这是表紧缩关系的。同时,它还表现在对古代汉语中虚词系统的延续使用以及对古汉语句型的套用,如“夏伤于暑”中的“于”;“肝属木,在液为泪”中的“在……为……”等。
上述表现,究其原因,是中医学专业学科内涵使然。现代中医学注重古代典籍的引用和传播,有的是源自中医经典论著,有的是来自历代医家医案。中医语体更像是一个融合了多个时期语言样本的“大熔炉”,引用、沿用或者化用了各个时期汉语的表达方式,在现代中医文本中仍然行使着表情达意、传达信息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说,它是在引用、沿用或者化用历代医学用语的同时,与现代中医用语的有机结合,换言之,是时代积淀和学科发展使然。因此,可以说,这种“换形拉距”[3](P407)的基本特征是:古语引用、沿用与化用。
(二)中医汉语教学
专门用途英语(English for Special Purpose,简称“ESP”),是20世纪60年代形成的外语教学理论,它是相对于通用英语(English for General Purpose,简称“EGP”)教学而言的。作为专门用途汉语教学(Teaching Chinese for Specific Purposes)的分支之一,中医汉语教学主要是通过对中医药文本的听读与表达训练,使学习者积累一定量的中医药专业词汇,熟悉中医药文本的特殊表达句式,了解有关的中医文化背景和知识,从而更为深入地理解中医药学。随着“中文+职业教育”教育理念的提出,国际中文教育与职业教育的融合也得到了更多的关注。2019年,医学汉语水平考试正式开考;2020年,《医学汉语水平考试(MCT)大纲》正式颁布,“中文+医学”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新阶段。在这一背景下,作为基础性研究的中医汉语的语言要素,如字、词、短语、句型、句式、篇章语境等,亟待开展,以助力“中文+中医”专用汉语教学的规范化、标准化、科学化建设。
具体来说,我们要研究中医汉语语法,必须立足于中医这一特定语域,立足于中医语体语法这一基础。上文所述中医语体语法中的独特现象:单音词、四字格、古语、专用词、独特的话语方式等,为中医汉语语法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抓手。有鑒于此,本文拟从中医语体语法角度入手,挖掘在中医汉语语法教学领域的定性和量化因素。
二、中医汉语构式
总的来说,构式的定义经历了一个发展和修正的过程。在本文中,我们主要采用Goldberg修改后的构式概念[4],将构式理论融入到中医汉语语法体系中。在构式理论的观照下,结合中医语体语法、专用汉语教学的实际状况,深入挖掘中医汉语语法特性,并将中医汉语领域的固定结构、句式句型等命名为中医汉语构式。所谓“中医汉语构式”,是指中医语域中能够体现中医汉语特点的、与普通汉语不同的独有的语言型式。它们在形式或功能的某个方面,不能从其组成成分或其他构式中完全预测出来。
本文主要讨论的是中医汉语教学,因此,首先需要对有关研究材料进行筛选。作为处于中医专业学习前预备教学阶段的专门用途汉语教学,中医汉语语言点的选择需要兼顾专业性和频率性。前者是一种定性的指标,需要专家的介入、指导;后者则是一种定量的指标,需要基于一定规模的语料的统计和分析。因此,考察中医汉语教材中的词语构式情况,可以为中医汉语教学提供更直接的参考;而中医学专家对术语结构的遴选,可以为我们提供学术层面的参考。对这两类语料的深入挖掘,能够使中医汉语教学语法研究更具针对性和专业性。
(一)中医汉语语料库的构建
根据专业+定量的标准,我们自建了中医汉语语料库,该语料库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教学语料库,二是专家语料库。就教材语料库而言,穷尽性地收集目前普遍使用的中医汉语教材作为该语料库的语料,包括徐静主编的《中医汉语综合教程》[2]和罗根海、赵熔主编的《实用中医汉语·精读(提高篇)》[5]。就专家语料库而言,主要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的《中医基础理论术语GB/T 20348—2006》[6]。需要说明的是,本文语料基本是来自自建中医语料库,以下不再标注出处与页码。
(二)统计方法
如前所述,Goldberg对构式外延的界定相当广泛,包括从语素开始的各级语法单位。考虑到中医汉语教学的实际状况,本文将中医汉语型式限定在短语层级以上的。同时,在对中医构式的梳理过程中,我们还面临着如何处理特殊的中医专用词语的问题。中医词语作为中医构式构件的组成部分,在某些特殊的构式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采取了“词语—构式”的方法进行统计和归纳。首先,统计教材中所出现的专名术语。对《中医汉语综合教程》(205个)和《实用中医汉语·精读(提高篇)》(217个)进行了统计,并将三音节以上的固定结构进行了词语层面的析出,厘清专名术语的分类和层级关系。比如,对“金生水”这一词条,从中析出名词:金、水;动词:生。其中,有53例重合,有45例四字格。其次,以《中医基础理论术语》中的1291个术语为对照,对已经归纳的类型进行判断和补充。再次,在两者的基础上,得出中医汉语各层级构式表。
(三)数据及讨论
根据“词语—构式”体系,我们主要统计了《中医汉语综合教程》和《实用中医汉语·精读(提高篇)》专业术语中的词语系统占比情况。周延松对《实用中医汉语》精读教材中的专名术语进行了统计,研究发现,双音节专业词汇占比最大,由此认为,中医汉语专业词汇的分布格局,与现代汉语双音节词占绝对优势的情形是非常吻合的[7](P84)。不过,作者并未深入挖掘具有特殊地位、起着关键作用的词语系统。我们在自建语料库中发现,虽然中医汉语专业词汇仍然以双音词为多,但是单、双音词在内容分布上是不一样的。
1.名词系统→构式
我们首先对两种教材中的中医汉语名词系统进行了归纳、统计,共有235例。具体分布如表1所示:
从表1中的相关数据及教材语境中的实际用例,我们可以获取以下信息:
首先,中医汉语名词系统的分布比较分散,在病症、经络、物质类中,有些是用单音节词语来表示的,尤其是物质类。不难发现,这些概念往往是中医汉语中的准核心词,具有悠久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黄帝内经》时期的上古汉语。
其次,中医汉语名词具有多义性,有的名词不止一个语义。比如,“三焦”“经方”的语义比较丰富,它们都是经过历代医学思想发展而逐渐形成的,要得到其确切语义,需要结合具体语境来识解。
再次,中医汉语名词的概念意义具有模糊性和相对性。比如,“阴”和“阳”这对概念。它们指的是宇宙中对立统一的两个事物,或者一个事物中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可见,“阴”“阳”属性是在对立统一的两个事物(或两个方面)中来讨论的。因此,即使是同一事物,在不同情况下,可能就会出现有时属阴、有时属阳的现象;更有“阴中有阳”“阳中有阴”的现象。此外,在一定条件下,阴和阳还会相互转化。
2.动词、形容词系统→构式
我们接着对两种教材中的中医汉语动词、形容词系统进行了归纳、统计,共有107例。具体分布如表2所示:
出现的凝固结构中的单音形容词进行了单独统计。从表2可以看出,在中医汉语动词系统中,单、双音节分布呈现出明显的不同:及物动词主要由单音节担任,这种情况共有19例,它们是:主、属、生、乘、侮、化、运、伤、喜、悲、合、犯、逆、恶、克、扰、袭、藏、志;而双音节及物动词仅出现2例,它们是“调和(气血)”“调整(阴阳)”。与之相反,不及物动词则多由双音节词语担任,如“疾病痊愈”“津液停滞”。
从表2还可看出,形容词在四字格凝固结构中出现时,大多为单音节,如“补虚润燥”“运盛气衰”,也有双音节,如“寒性凝滞”。形容词在相对独立使用时,则大多为双音节,如“精亏虚,气血就亏虚”,也有单音节,主要出现在古句型中,如“精气夺则虚”。
之所以会形成以上现象,主要是由于以下原因:一是受到四字格的格式压制,表面上似乎是与其他句法成分形成2+2的模式,实际上是四字格内部的“嵌偶单音词”[8](P98)的体现。二是受到现代书面语正式体的制约,现代书面语正式体一般采用合偶双音词的形式。第三,如果是处于古句型或者出现古虚词时,则不受上述制约,体现出古代汉语尤其是上古汉语单音词的倾向。总之,形容词单双音节的特点,反映出中医汉语所受到以下層面的影响:四字格、古句型和现代正式体书面语。
我们将动词、形容词系统与构式系统综合起来审视,可以发现这样的图式型构式:
X+V单+Y 如:经属阴 肝为阳;
X+V双 如:阴阳调整 肺气上逆;
X+A双 如:心阳虚;
X单1+A单1+X单2+A单2 如:补虚润燥;
X双+A双 如:湿性黏滞 气血失调。
同时,在中医汉语中,单双音节的名词、动词、形容词是有其专用性的,如“气”“邪”“生”“属”“主”“调整”等。所谓“专用性”,是指在中医汉语中不能用同义的其他词汇来替代。比如,“金生水”不能说“金产生水”;又如,“精气夺则虚”不能说“精气被抢夺则亏虚”。冯胜利指出,典雅体通过古语“嵌偶”、“古语必双”来达到古语今化的效果[9](P24),正式体具有“双+双”的“合偶双音词”的特点[8](P96-97)。不过,在中医汉语中却并非完全如此。这显示出中医汉语虽然具有典雅体的特性,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又不仅限于典雅体,而是一种特定语域的语体,我们应该以同中存异的眼光来看待这一语域的语体语法现象。
3.虚词系统、框式结构系统与四字格结构系统
我们又对两种教材中的中医汉语虚词系统进行了归纳、统计,共有10例;还对源于古句型的框式结构系统、四字格①结构系统进行了归纳、统计。具体分布分别如表3、表4、表5所示:
综上所述,在封闭语料中,中医汉语的词法、句法具有鲜明特点,主要表现为以名词、动词、形容词为主的词法系统,以虚词、图式型构式、四字格、框式结构、特殊句式的句法系统为主线的“词语—构式”体系。体系内部相互影响,彼此制约,这也成为构建中医汉语教学语法体系的基础支撑。同时,该体系内部的制约层级可以暂拟为:文言句型、文言虚词>四字格>图式型构式>词法系统。
三、中医语篇话语方式
中医学语篇同样呈现出正式与典雅共存的特点,这与冯胜利[3](P406)所提出的正式体与典雅体相吻
合。下面,我们就以中医学专业教材《中医基础理
论》[10]、《针灸学》[11]为例,对中医语篇的话语方式展开分析。
(一)正式体
首先,中医汉语具有正式体特征,表现在语篇话语方式中,就是倾向于使用有标(双标)复句。所谓“双标复句”,是指复句前后件均出现标志。这在中医汉语篇章的论述部分较为常见,是正式体的主要体现。例如:
(1)由于自然环境的变化时刻影响着人的生命活动和病理变化,因而在疾病的防治过程中,必须重视外在自然环境与人体的关系。(《中医基础理论》)[10](P16)
(二)典雅体
其次,中医汉语具有典雅体特征,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无标或单标复句的使用;二是篇章构造模式比较特殊;三是大量引用古籍、古语。
1.无标或单标复句
在中医汉语篇章中,有时会采用无标的“意合”复句、流水句或者后件单标的复句,使文脉清晰、文气畅达、语句贯通。这种类似于流水句的语段加合方式,与中医学的深层意蕴相契合,是中医汉语典雅体在话语篇章中的重要体现。例如:
(2)中午之前,人身阳气随自然界阳气的渐生而渐旺,故病较轻;午后至夜晚,人身阳气又随自然界阳气的渐退而渐衰,故病较重。(《中医基础理论》)[10](P15)
(3)肝主疏泄,调畅气机,促进血行;肝藏血,调整血量,防止出血,有助于脾。(《中医基础理论》)[10](P88)
2.特定的篇章构造模式
在中医汉语篇章中,往往采取固定的行文模式,以行使不同的语用功能。如“中药名+药性+功能+主治”的模式:
(4)麻黄味辛性温,归肺、膀胱经,功能是发汗解表,宣肺平喘,利水消肿,主治肺和膀胱经的寒性病症。(《中医基础理论》)[10](P299)
3.引用古籍、古语
在中医汉语篇章中,还大量引用医学典籍和古代术语,为相关观点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例如:
(5)法于“四气调神”,“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与自然环境保持协调统一。(《中医基础理论》)[10](P16)
(三)中医古语和现代书面语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医汉语语体实为现代书面语和中医古语的混合体,同时还包含一定的白话成分,这主要表现为正式体和典雅体的融合。这里的“现代书面语”是指阐释、描述中医学内容的书面正式语;“中医古语”是指阐释、描述中医学内容的文言词汇、句型、句式。冯胜利在分析书面正式语体的典雅度时指出:“文和白二者必须取‘三两结伴、交替而行的原则”[8](P104),这在中医汉语中也有类似表现。与冯先生的观点有所不同的是,中医汉语主要体现为现代书面语与中医书面语(中医古语)的离散分布与内部聚集。其中,中医书面语(中医古语)为必选项,换言之,中医构式在中医汉语语体中是必须使用的,不能将它替换为其他表述,如现代汉语书面语、口语等。例如:
(6)防治原则,是关于疾病的预防和治疗的思想
现代书面语
和原则。主要介绍治未病的预防思想及其与养生的关
现代书面语 中医古语
系,闡述治病求本的治疗思想和正治反治、标本缓急、
现代书面语 中医古语 中医古语
扶正祛邪、调整阴阳、调理精气血津液、三因制宜等
现代书面语 中医古语
治疗原则。(《中医基础理论》)[10](P24)
(7)经络内属脏腑,外络肢节,沟通内外,贯串
中医古语 中医古语
上下,将人体各部的组织器官联系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现代书面语
(《针灸学》)[11](P75)
四、中医汉语语法教学
上文主要是从中医汉语构式和话语方式出发,归纳出中医汉语语体的整体特征,这就为中医汉语语法的外向型教学提供了依据和参考。在此基础上,我们构建出“词法—构式”的中医汉语语法教学体系,并以“气”类构式为例,对中医汉语语法教学展开探讨。
(一)中医汉语语法教学现状分析
就中医汉语教学的研究现状来看,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医汉语词汇方面[7],分析中医专用词汇与通用词汇的差异,探究词汇的选用与通用大纲的关系,而很少从词汇层面进入到词法/句法/篇章的范畴,对中医汉语语法的体系构建更是鲜有系统论述。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医汉语教学阶段,还出现了换用、转用中医句法型式的现象。为了降低学习难度,在预科教材或者预科教学中,将中医专用表达方式转换为较为通俗的普通汉语表达方式,比如,将“肺主呼吸”转换为“肺管呼吸”,将“肝司疏泄”转换为“肝管疏泄”,将“肝开窍于目”转换为“肝开窍在眼睛”。这里的“主”“司”为词类活用,“开窍于”则属于特殊句式。这种表达转换暂时回避了中医汉语语法教学,虽然便于学生理解掌握,但是进入到中医学学习阶段之后,由于中医语体的特殊性,学生将无法在相关文本中找到与之同样的表达,这就使留学生实际上面临着专业知识和专业语言知识技能的双重任务。这种局面的形成,反映出预备学习阶段与专业学习阶段的脱节,也不符合专用汉语教学的目标和定位。
(二)中医汉语语法教学体系的构建
长期以来,中医汉语语法教学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事实上,中医汉语存在着一系列非常明显并独具特点的语法表征。我们在具体教学实践的基础上,构建出中医汉语语法教学体系架构,该体系以专用词语为底层基础,以构式为框架,并与中医汉语的特殊话语方式紧密结合。具体如图1所示:
(三)中医汉语语法教学实践
在中医汉语教学中,面对的基础类主题主要有阴阳五行、脏象、气血津液、经络、病因病机、养生预防等。中医汉语语法教学应该以这些主题为纲,以相应构式为用,深入挖掘中医汉语语法的内涵所在。因此,这里以“气血津液”中的“气”类构式为例,对如何将中医汉语语法教学体系落实到具体实践中进行探讨。我们对中医汉语中“气”类的主要构式进行了归纳、统计,具体如表6所示:
从表6可以看出,在中医汉语语法体系中,关键词汇“主”“之”“能”与中医构式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们也是中医构式语法教学体系的主要支撑。
1.培养中医汉语语体意识
首先,应明确中医汉语语体的特殊性,它是一种融典雅体和正式体于一身的书面语,而不同于普通汉语中的口语,“气”类构式同样如此。中医汉语构式的学习,并非简单地进行词汇和句型识记,还应在“教”与“学”的过程中,大力培养学习者的语体意识,并将其作为语法教学的基本原则贯彻始终。
2.核心词语的分层架构教学
在中医汉语语法教学中,可以采取核心词语语义内涵——构式——功能语境的分层架构方法。具体到“气”类构式教学来说,在第一个环节,集中分析动词“出”“主”“为”、虚词“之”“能”的语义、语用功能,并将其作为新词语言点进行语义内涵挖掘;在第二个环节,对主要构式进行归纳、讲解;在第三个环节,对构式和构件进行功能—语境的解析,其中,[±嵌偶]、[±合偶]、[±四字格]、[±古句型框式结构]等特征,需要在解析中明确指出、重点剖析。具体如表7所示:
3.现代/中医书面语的转换训练
首先是现代书面语与中医书面语(古语)的区分训练。教师可以设计二者交杂的语例,让学生标注出哪些是中医古语,哪些是现代书面语。如例(6)、例(7)所示,再如:“天气下降,地气上升,天地阴阳二气氤氲交感,相错相荡,产生宇宙万物,并推动着它们的发展变化。”[10](P28)
其次是现代书面语与中医书面语(古语)的转述训练。即训练学生将中医古语转述为现代书面语/口语,将现代书面语/口语转述为中医古语,通过双向/多向转述,增强学生对两种语体的理解和运用。比如,将“血为气母”转述为“血是气的母亲(或本源)”;又如,将“卫气在脉之外运行”转述为“卫行脉外”。
再次是中医汉语构式的扩展训练。教师提供相应的语料,带领学生进行替换和发散练习。比如:在“A能+V+N”中,除了“气能生血”之外,还可以表述为:“气能行血”“气能摄血”“气能生津”“气能行津”“气能摄精”等。
综上所述,本文以语体、语法理论为观照,对中医汉语语法教学的概念予以界定,在以教材语料和专家语料为主的封闭语料库中,考察中医汉语各层级语法单位的分布状况和主要特征。将“词法—构式”作为中医汉语语法的研究路径,是中医汉语语法教学的一个有益尝试。中医汉语特殊语法是在名词、动词、形容词为主的词法系统和图式型构式、四字格、框式结构、特殊句式为主的句法系统互动下而形成的。在中医汉语语法教学研究中,需要对以下方面着重关注:基础性的单音节中医动词及其构式;带有古汉语特点的十个基础虚词及其构式;五类典型的古语框式结构;凝固结构,尤其是四字格的内部架构方式;中医汉语篇章中的话语方式:有标复句与正式体,无标复句/意合/流水句与庄典体。我们认为,中医汉语语法教学应该是分层次的,并贯穿于中医学留学生的预科阶段及专业学习阶段。总之,中医汉语语法的研究空间十分广阔,仍有一些空白之处需要深入探索。在后续研究中,还可以在这一基础上,进一步推动留学生中医汉语语体能力发展的研究以及“中医汉语古语度”的自动测量研究等。
参考文献:
[1]冯胜利.语体语法及其文学功能[J].当代修辞学, 2011,(4).
[2]徐静.中医汉语综合教程[M].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3.
[3]冯胜利.论语体的机制及其语法属性[J].中国语文, 2010,(4).
[4]Goldberg,A.E.Argument realization:The role of constructions, lexical semantics and discourse factors[A].In ?stman,J-O. & Fried,M.(eds.).Construction Grammars:Cognitive Grounding and Theoretical Extensions[C].Amsterdam:John Benjamins,2005.
[5]罗根海,赵熔.实用中医汉语·精读(提高篇)[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
[6]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GB/T 20348-2006 中医基础理论术语[EB/OL].(2006-05-25)[2023-01-25].https://std.samr.gov.cn.
[7]周延松.专门用途汉语教学中的专业词汇问题——基于中医汉语地视角[J].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 2014,(10).
[8]冯胜利.论汉语书面正式语体的特征与教学[J].世界汉语教学,2006,(4).
[9]冯胜利.汉语语体语法概论[M].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8.
[10]孙广仁.中医基础理论[M].北京:中國中医药出版社, 2002.
[11]梁繁荣,王华.针灸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6.
①为了深入考察中医四字格的使用情况,这里主要以《中医基础理论》1291个术语中的559个四字格和教材中的49个四字格为参考,以确保统计的全面性。
The Stud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tylistic Grammar for Chines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On the Perspectiv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onstruction and Discourse Mode
Guo Limi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Liaoni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henyang 110847;
College of Arts,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8, China)
Abstract: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tyle is a kind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CM) style, which contains the thinking of TCM, embodies the syntactic characteristics of TCM specialty and the mode of discourse. It has bo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ormal style/elegant style and the specific discourse mode of TCM register. This paper defines the concept for the study of teaching grammar of TCM Chinese, and examines the distribu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grammatical units at different levels in TCM Chinese, including nouns, verbs, function words, ancient sentences pattern, four-characters,etc. in a closed corpus based on textbook corpus and expert corpus. It is believed that “morphology—construction” will provide an operable framework for the study of grammar of TCM Chinese. The special discourse mode of TCM Chinese also has the value that can not be ignored, which is reflected in the coexistence of marked compound sentence, unmarked compound sentence, single marked compound sentence, parataxis and run-water sentence, the quotation of ancient sayings, and the specific discourse structure mode.
Key words: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tyle;formal style;elegant style;TCM Chinese construction;discourse mode;teaching grammar of TCM Chinese
基金项目:2022年国际中文教育研究课题青年项目“基于‘话题—功能—构式的中医汉语教材语料库建设与应用研究”(22YH38D)
作者简介:郭力铭,女,辽宁中医药大学国际教育学院讲师,首都师范大學文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