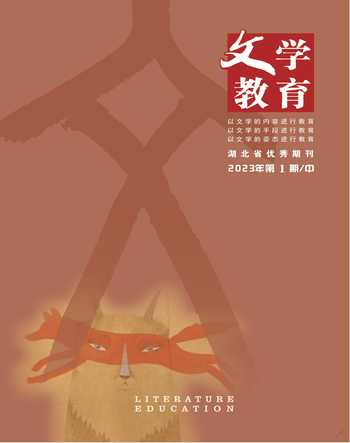徐则臣笔下的余松坡形象与北漂的困惑
邢译文
内容摘要:王城中的他们,有海归、有精英、有大学生,也有保姆、快递员,还有孩子。他们带着各自的过往,奔涌到北京,奔波在北京的大街上,奔向自己的未来,追寻自己的价值感。徐则臣的《王城如海》只有十余万字,容量和复杂性却并不比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逊色,它内容包罗万象,使用了错综的结构和具有戏剧性、象征性的意象及情节。其中,主人公余松坡的形象尤其复杂,与作者自身的经验和思考息息相关。
关键词:徐则臣 《王城如海》 余松坡 北漂
徐则臣《王城如海》的情节围绕海归先锋实验戏剧导演余松坡展开。余松坡新剧《城市启示录》的内容被认为冒犯了“蚁族”年轻人,他因而被推上舆论焦点,困扰非常,不得不考虑回应舆论和改动剧本的问题;另一方面,他与堂哥余佳山偶遇,回忆起隐秘的往事,梦游症在焦虑中频繁发作。雾霾笼罩下,北京这个城市本身的困惑和矛盾被慢慢揭露,而这些困惑和矛盾却并没随故事落幕得到解决。
一.《城市启示录》:剧中角色“教授”就是余松坡的化身
小说一个引人注目之处,在于采用了“戏中戏”的杂糅文本结构,每一章节都由两部分构成:主文本——小说剧情的记述,围绕主人公余松坡展开情节;副文本——余松坡作品《城市启示录》的剧本段落,采用戏剧文体,置于该章主文本前。《城市启示录》这一作品在主文本剧情中占重要位置,其内容争议和改剧本事宜推动着情节的推进;作为副文本,又以蒙太奇式的手法影射着主文本,形成互文关系。
虽然助理撒玉宁坚称让“蚁族”感到被冒犯的观点是“戏里人物的观点”,但事实上,剧中角色“教授”就是余松坡的化身。剧中的教授与导演余松坡都是经历多年海外生活后回国的知识分子,對北京的审视天然带有一种国际性的批判视角。教授做过全世界很多城市的比较研究,现在回到北京、研究北京,等于要把北京也纳入到他的比较中来,用评价伦敦、巴黎、纽约等世界上的城市的标准和体系衡量北京。而面对记者,余松坡给出了他对这个比较的看法:和“稳定、饱和、自足的城市形态”的伦敦、巴黎、纽约不同,北京无法“从一个乡土中国的版图中抠出来独立考察”,它“被更广大的乡村和野地包围着”,在浮华之下,还有“一个乡土的基座”。这个基座是北京的复杂性的重要组成,依赖着千年的历史、传统和由人情构建的社会关系,与这座城市里的“蚁族”、与小说中出现的各色人物都紧密关联。这些“京漂”远离家乡,处于北京这个拥挤驳杂的大城市的边缘,精神上难以融入,是这座城市的“他者”,实际又已成为北京与乡土相连的“根系”,以“居住在北京的人”和“来自乡土的人”的双重身份纠结地存在着。
余松坡回国后很难从现实中脱身而出,他必须面对现实问题、成为一个现实主义者,去关注北京、关注当下中国的生活,去寻求现实与实验戏剧的融合。然而,他认为正因为中国“不适宜搞实验戏剧”,才“值得去尽心尽力地搞一搞”,已经站在一种视察般的俯视视角,这与他作品中试图将世界诸多城市同北京比较的教授不谋而合。教授看到小月河的“蚁族”,“悲哀、心痛和怒其不争瞬间占领了他的光脑门”,他斥责他们为何待在这里过这样的生活,他意味深长地说:“你们啊——”被省略的半句话由观众自由填补,余松坡自己也未必知道应当是什么,正如他认为这段议论引发的批评不是常规的艺术批评,却想不通这些批评的性质,也做不出通过改动剧本解决问题的可行方案。事实上,戏剧本貌传达的信息已经最贴近余松坡想表达的意图,他只是意识不到也无法直面自己潜意识中的真实立场,即舆论所指的、与剧中的海归教授一致的,对“蚁族”年轻人的“轻蔑和不信任”。两人的疑惑、焦虑、愤怒、对“京漂”现状和对北京这个立体而复杂的王城的不安相互关联和呼应,形成复调,内蕴的是作者对这些问题的思考。
小说第九章的副文本展示了教授与他初恋情人的对话。在《城市启示录》中,初恋情人正是北京城的象征。她在昏暗与模糊中仿佛依然年轻妩媚,永不迟暮,不枉教授多年痴心不改;等看清楚了,却发现她已憔悴衰老,正如古老的事物裹着文化的包浆,“一个崭新的现代的超级大都市包裹着一个古老的帝都,光鲜亮丽,既藏污纳垢,又吐故纳新”。教授已经娶了外国的妻子——外国妻子象征着他在外国见过的城市:伦敦、爱丁堡、开普敦等等——却始终对初恋情人念念不忘,正如他在国外数十年,精神上却从未离开北京。他说自己爱这片土地,来研究北京是想看得更清楚;他说自己爱这片土地上的人,爱她。而初恋情人只觉得他可笑,告诉他:“别用你的伦敦经验来审判北京。”即使被放在世界坐标上,北京也拒绝被用这样自诩世界的虚伪视角审视。余松坡也一样。他曾生发北京情结,在北京学习生活,后来又逃离北京,如今不可避免地从世界回到这里;而年轻的“京漂”们却拒绝被余大导演居高临下地批判。
教授和他所象征的余松坡都没有批判北京的资格,那么谁来进行批判呢?余松坡,或者说余松坡背后的作者徐则臣,选择了一只名叫汤姆的猴子。这是一个具有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动物意象,余松坡称它为“先知”。“汤姆”这个名字则可以追溯到“贝德兰的汤姆”这一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典型疯丐形象,当时疯人和傻子常常在戏剧中占据重要位置,成为理智的化身和真理的卫士,莎剧《李尔王》中被放逐的爱德伽就曾自称“可怜的汤姆”。①而《城市启示录》中的猴子汤姆有超人的灵性和非人的动物性,属于人类社会的异质,与疯丐这一文化符号不谋而合。它绝不虚伪,通过特异的敏锐嗅觉,感知和展示着北京最真实的现状——“拥挤、颓废、浓郁的荷尔蒙,旺盛的力比多,繁茂的烟火气,野心勃勃、勾心斗角、倾轧、浑浊、脏乱差的味儿”,感知和展示着这个城市以及生活于此的漂泊者们的复杂性。
二.面具和《二泉映月》:余松坡一直在试图逃避自己的罪感
《王城如海》采用双线叙事结构,两条主要线索一明一暗:明线即《城市启示录》引发争议,由此展开回应舆论、修改剧本等情节;暗线即余松坡时隔多年偶遇余佳山,这唤醒了他多年的噩梦,只有听到《二泉映月》才能平静,由此引出余松坡隐秘的过往和内心世界。双线交织并行,余松坡在舆论问题上的茫然和焦虑,其根源就藏在他的过往之中,是他矛盾、犹疑和逃避的表征。
小说中,十九岁的余松坡为争取当兵名额,在村长半暗示半胁迫下举报了他的竞争者——堂哥余佳山,导致后者蒙受了十五年牢狱之灾。余松坡因此产生了沉重的负罪感,常年被梦魇纠缠。愧疚中他最终放弃了这个名额,逃离家乡,逃到北京,既而又逃到国外,逃到纽约,逃到《二泉映月》的乐声中。身为一个“纠结、犹疑、怯懦和沉默的人”,余松坡一直试图逃避自己的罪感。
《二泉映月》这个意象具有民族特色,同时因为余松坡的父亲常拉,又成了父亲的象征。小说开端,读者就能从保姆罗冬雨眼中看到《二泉映月》的神奇——余松坡的妻子祁好对它重视非常,花大功夫教会保姆如何迅速让它响起,这支能让余松坡平静下来的二胡曲子显得无比神奇,制造了颇有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悬念。在联系村长张罗当兵事宜、不得不举报余佳山时,余松坡与父亲是共犯、是阴暗秘密的共同承担者,是一样饱受良心折磨的人,这首曲子也就成了余松坡逃避沉重原罪的精神避难港。祁好抚慰他的身心,为他播放这支曲子,尊重和守护他的秘密,但也无法接近他的内心。原罪意识“暗含着人类对自己进行道德评价的基本尺度,显示着人类对自己的道德状况的强烈焦虑和深刻认识”②,这正是余松坡的焦虑之源。只有在《二泉映月》的乐声里,他才得以从焦虑中喘息,感到自己和父亲“被清洗了一遍,还可以重新做回一个心无挂碍的善良人”。
余佳山曾从北京归来,又因北京之行入狱,他点燃了余松坡的北京情怀,因此余松坡离家后去了北京,试图看清一些什么。在外来者眼中,“无论从物质还是精神上,北京代表了无穷的想象,也意味着无尽的幻象”③。但余松坡越“看”、越了解,就越焦虑不安。北京并非众人幻想中的“乌托邦”,这个有着巨大的速成的奢华假象的城市,其实紧紧地连着它的乡土“基座”,而余松坡的怯懦让他拒绝承认自己乡土性的身份——他的原罪因人情起又伤害了人情,与乡土密切相关。他只能继续出走,逃到纽约。在这个“大都会”里,他终于获得一种世界化的视角,以安全的距离观察北京、观察中国。这一点在剧中教授的身上也有所隐喻。远在世界,余松坡通过自我放逐,终于能稍微消解心中的原罪。
但逃到远处并不能让余松坡真正实现自我救赎。面具是逃避的象征,他一方面收藏了许多面具,一方面成为剧作家和导演,躲起来不敢登台,让剧中角色作为他的一张张面具替他说话。余松坡对被揭下面具充满恐惧。然而他纠结的原罪意识也导致了他内心世界的分裂,既想躲起来,又忍不住去探寻;既害怕被戳穿,又忍不住要表达和自辩。因此生活中他是一个沉默的人,在先锋戏剧领域却一直走了下去。也正因此,回国后他才试图用自诩世界的视角来批判北京,而这必然引起年轻人的非议——他原本没有这个批判的资格,面具下的他就是一个来自乡土的漂泊者。
对余松坡而言,患上和父亲一样的肺癌是无法逃脱的诅咒,是因“罪”而来的“罚”。对死亡的恐惧催促着他要找到余佳山,这样他才可能得到原谅、得到真正的救赎,他的噩梦恶化为梦游,梦游中他试图把那些面具都破坏,以暴露真实的自己。然而梦醒后,他的怯懦又使他活在“面具”后,只敢在遗书中向“灵魂保险箱”忏悔原罪。现身北京的余佳山成了余松坡的过往、原罪和乡土性身份的象征,这提醒了余松坡他和“蚁族”们本质相类,从乡土中来,居住在北京,渴望着世界。见到余佳山,他再也不能置身事外,以艺术框架下的世界视野审视北京。
正如前文所述,余松坡意识不到也无法直面自己对“蚁族”们的否认立场。他深知这些低收入劣居群体是北京运转不可或缺的“齿轮”,因此出于现实主义的考虑,他否决了助理撒玉宁弱化甚至删除剧本中“蚁族”内容的建议。但是,究竟如何看待以“蚁族”为代表的“京漂”、如何让他们认同这部剧,余松坡终究是茫然的。他不断绕道天桥想见到余佳山,却不敢与他相认,隐喻他已经逃避审视自己身份和内心许久,而对“京漂”的审视即是对他自己的审视。他矛盾而纠结,不敢直面自己的批判意图,也没有否定自己的勇气,于是只能在批评中愈发焦虑。
崇拜者罗龙河无意间发现了余松坡尘封的过往,小说的明线和暗线在此交汇,把故事推向结局。罗龙河没能成功制造出余松坡和余佳山的对峙,余松坡秘密的守护者祁好戏剧性地提前归来,代替余松坡承受了与余佳山见面的结果,但余松坡家中收藏的诸多面具已被余佳山打碎。徐则臣直言:“面具于余松坡来说是潜意识里对隐藏秘密的需要,对余佳山来说是妖魔鬼怪的幻象。”④在这个层面上,精神失常的余佳山起着与剧中的猴子汤姆相似的作用,他也是人类社会的异质、拒绝虚伪而寻求真实的存在,余松坡逃避的象征已经被他破坏。而等祁好醒来,余松坡必须面对现实,他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尚不可知。
三.徐则臣与“余松坡”:做一个“无条件的现实主义者”
需要注意的是,小说中的副文本《城市启示录》剧本片段并不能和主文本中余松坡创作的《城市启示录》完全等同。这些副文本是徐则臣假托余松坡创作,而非单纯的以余松坡的语言进行的书写,戏剧文本的《城市启示录》附丽于相应的主文本,无法被剥离开进行独立解读。因此,在小说最终章的副文本中,本应躲在面具后的余松坡竟走上舞台参与了这出戏剧,也就不难理解了——这是一个戏剧角色、一个艺术框架下的余松坡,是另一张面具,他“不是余松坡”“只是饰演余松坡”。剧中的教授是余松坡的化身,而“余松坡”的“面具”下正是作者徐則臣本人。
作为在京生活多年的“京漂”作家,徐则臣的写作不可避免地将北京作为思考的起点。他此前就写过“京漂”系列小说,以“京漂”小人物的视角描绘北京城。《王城如海》的主角虽依然是“京漂”,但余松坡海归博士的身份已经决定了小说完全不同的视野,徐则臣对京城的认知也已经与写“京漂”系列小说时不同。正如他所言:“现在你让我描述北京,我会语焉不详……我肯定比过去看得更清楚,但我觉得越来越看不清楚。”⑤余松坡身上寄寓了徐则臣更深层次的思考。
作者原本“想把城市本身作为主人公,把城市作为研究对象,看看复杂全球化时代下北京到底是什么样的”⑥,但写作过程中仍然偏向了人的描写,故事中形形色色的人展现着北京的各种边缘和侧面,其中最复杂最核心的人物无疑是余松坡。“王城堪隐,万人如海,在这个城市,你的孤独无人响应;但你以为你只是你时,所有人出现在你的生活里:所有人都是你,你也是所有人。”⑦在这个意义上,余松坡堪称是作者笔下北京城的缩影,是漂泊者眼中复杂而矛盾的分裂、焦躁、时空纵横,想和世界接轨,又被乡土的惯性束缚。因此,笼罩着整篇小说的雾霾就成了余松坡内心焦虑和不安的具现,成了原罪的象征,唯有余佳山兜售的新鲜空气和治霾神器可以缓解和驱除。另一方面,“蚁族”冯壬宣称他们的漂泊有意义,宣称他们没有失败、只是尚未成功,余松坡不敢否定这些年轻人的自我激励,因为否定了他们等于否定了他自己。这些年轻人将北京视作有无穷机会和成功之路的幻想之地,盲目地来到北京,想要“到世界去”,然而“从世界归来”的现实却已经在余松坡身上,消解了“到世界去”的意义。北京有和余松坡同样的矛盾和焦躁:它高速发展,它由乡土奔向世界,它将何去何从?这正是徐则臣向读者提出的困惑。
北京的复杂性使这个困惑很难得到解答。不过,追寻这个答案的方法还是有的。这就是作者借剧中“余松坡”之口给余松坡的建议:做一个“无条件的现实主义者”,“关注这个城市,关注这个国家的每一点风吹草动”——只有正视现实,方能看清现实,尤其当我们深陷其中。
注 释
①曾绛,罗益民.爱德伽伪装疯丐的人文意义[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5).
②李建军.忏悔伦理与精神复活——论忏悔叙事的几种模式[J].小说评论,2006(6).
③曾攀.时代的精神状况——徐则臣论[J].小说评论,2021(1).
④⑥徐则臣,赵依.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与徐则臣谈新作及其他[J].朔方,2017(4).
⑤徐则臣.智性的作家靠思辨来推进小说[J].南方都市报,2017(1).
⑦徐则臣.《〈王城如海〉后记》[J].东吴学术,2016(5).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论徐则臣文学的发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