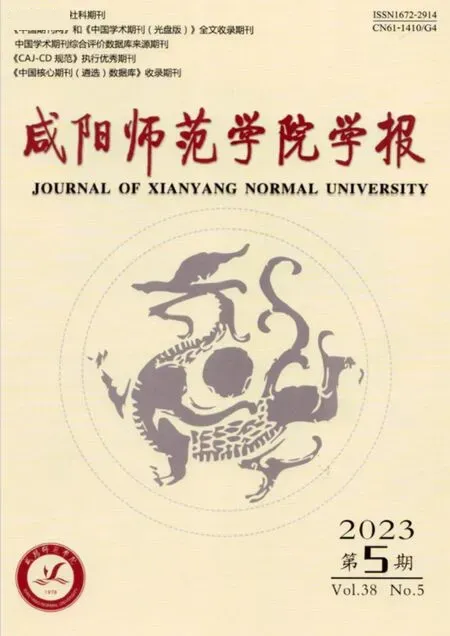《淮南子》对先秦道家“无为而治”的理论偏转
王效峰,陈 冲
(咸阳师范学院a.文学与传播学院,b.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陕西 咸阳 712000)
在治国之道的问题上,“旨近《老子》”“大较归之于道”的《淮南子》,虽对先秦道家“无为而治”的“神化”境界颇为倾心,但在汉初“大一统”的政治体制及“清净无为”的施政表象之下,却在不觉间运用了汉儒以及法家思想的相关理论,对道家“无为而治”的政治理念进行了改写。
一 “我无为而民自化”:先秦道家的政治理想
道家之“道”最基本的品格,是“无为而无不为”。“道”既“无为而无不为”,当然可以施之于治国理民。先秦道家的治国理想可以概括为“无为而治”。老子曾向“侯王”推销过他的“无为”之道的治国理民之效,《老子》有云:“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1]209;“不道早已”[1]276;“治大国,若烹小鲜。以道莅天下……众德归焉”[1]298。
值得注意的是,在先秦时代,以“无为”为稳妥易施的治国大道,不仅是道家对“人主”的期许,同样也是儒家、法家树立的治国标格。不过,由于儒、法两家对“无为”各有自己不同的理解,故而他们所期待的“无为而治”,也与道家迥然有别。例如,“三代”是儒家心目中的大治之世,尧舜是儒家最敬重的有道圣君。《论语·卫灵公》有云:“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欤?”[2]162由此可见,儒家心目中的“圣”君,也是“圣”在能达到“无为而治”之境界。但儒家心目中的“无为而治”,是唯“德”(仁义道德)是尚,“至诚无息”,别无它为。例如,行“仁政”是儒家所推尚的最佳理民方式,《荀子·解蔽》中说:“故仁者之行道也,无为也。”[3]404仁心“无为”,才能确保“仁政”畅通。《孟子·离娄上》有云:“(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4]172-173所谓仁心“无为”,用孟子的话说,就是“居仁由义”,“诚之”不已,除此之外,别无所为。故而,《礼记·中庸》说:“(故知)君子诚之为贵。诚者……成己……成物……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故至诚无息……如此者,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5]706由此可见,儒家向往的“无为而治”,就是要求人主“居仁由义”,以“至诚”之心“合外内之道”,在“成己”中“成物”。至于先秦法家,其治国理政强调对法、术、势三者的综合运用,重操作,讲实效。其定义的“无为”,就是唯“法”是从,法术势“一”而不二;所追求的“无为而治”理想,就是大小臣工,在遵法守职之外,别无所为。韩非之所以要不厌其烦地去辩“八奸”、析“十过”、明“亡征”、揭“安术”,所追求者,无非是为了“臣守职而君垂拱”。
道家在论及“无为而治”时,所谓的“无为”,是专就人主而言的。“无为”,就是要求人主在理民治国的时候,循“道”而行,任民自治。具体来说,就是“我无为而民自化”,即要求握有权力的人主,“守道真”“因自然”,给“民”留足“自化”的最大空间。
可以这样来界定道家“无为而治”与儒、法两家“无为而治”的分野:道家的“无为而治”,是以“无为”之心,行“有为”之事;儒、法两家的“无为而治”,实际上是以“有为”之心,求“无为”之效。有学者曾用“道”“德”“术”来概括儒、道、法在“无为而治”上的区别:“概括而言,先秦儒家所说的‘无为’偏重于‘治之德’,关注的是君主道德楷模的树立和影响;先秦道家所重的是‘治之道’,关注的是‘循道而行’的内在合理性;先秦法家所重的则是‘治之术’,关注的是切实的为治效率。”[6]156此说大体可从。在此基础上,本文想进一步说明的是,《老子》第三十八章有云“(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1]212,据此,可以条理出一种关系:有“道”者必有“德”,而有“德”者不必有“道”;有“德”者必有“术”,而有“术”者不必有“德”。例如,儒家以“仁义”为“为政”之“德”,道家却斥责儒家之“仁义”背“道”而驰,治国无“道”。法家治国,持“法”任“术”,儒家却斥责法家“仁义不施”,治国无“德”。把这层关系落实到“为政”之道上,可以说,当道家期许“人主”以“无为”之“道”治国时,实已涵盖了要求“人主”要有“为‘无为’”之“德”,要有“为‘无为’”之“术”。道家思想在汉初之所以能脱颖而出,成为汉初的思想时尚,就因为道家所主之“清静无为”的“为政”之道中,既有“为政”之“德”,又有“为政”之“术”,有儒、法为“治”之所有,施之于政,立见“与民休息”、理“乱”成“治”之效。曹参以“无为”之道治齐,“齐大治”,给汉廷树立了样板。文、景以“节俭”为“德”,以“静”施政,终成就大治之名。
先秦道家期许的“无为而治”,集中见于老氏之书。《老子》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1]209“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唯施是畏。”[1]268“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1]273“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1]284“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1]250“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入无间,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1]237“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1]64上引《老子》所云,一方面证实道家的“治之道”,源自“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另一方面也说明当道家期许“人主”以“无为”之“道”治国时,实已涵盖了要求“人主”必须有“为‘无为’”之“德”,例如“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我无为,而民自化……”云云,也涵盖了要求“人主”必须有“为‘无为’”之术,例如“以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云云。于是,老氏之“道”,在追问“世界归本何处”“天地如何生成”之外,还有两条进路:一是把老氏的“无为”之道“修之于身”,“无为”可转化成人全“德”葆“真”之“则”;二是把老氏的“无为”之道“修”之于邦国,“无为”可衍生出治国理民之“术”。“间世”主义者庄子,沿第一条进路,取老氏“无为”之道为“大宗师”,以之为全“德”葆“真”、“齐物”“逍遥”、“达生”“至乐”之则,开出道家新生面。身历嬴秦“暴政”之苦而心仪黄老之学的汉初时人,沿第二条进路,把老氏“无为”施之于政,以“清静无为”为治国理民之术,开创了为后世史家所称许的“文景之治”。
身历文、景之世,以“备帝王之术”自炫,“近老归道”的刘安及其宾客,在撰述《淮南子》的时候,免不了要在“无为而治”上有所阐发。
二 “道本自然”:《淮南子》对“为‘无为’”的必要性论证
按古人对夏、商、周三代文化的断代,“夏尚质,殷尚鬼,周尚文”。按今人对周代文化的评价,“周尚文”中蕴含着“实践理性”精神的觉醒。尊“道”崇“德”的道家,用“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的“道”,替代“尚鬼”之殷人心目里在冥冥之中掌控世界、有善恶、有予取的“天”,应该是“实践理性”觉醒绽放出的思想之花。和殷人意识中“有为”之“天”相反,道家之“道”最突出的品格是“无为”,即无善恶、无予取、无意志、无目的。或许是为了让人更方便地认识“道”的“无为之所益”,老氏特地从“以仁义挠天下”的儒家那里,借来一个“仁”字,用“不仁”来摹状“道”的“无为”性:“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1]78老氏虽然把“圣人不仁”和“天地不仁”放在一起言说,但两个“不仁”并不属于同一个层次。“天地不仁”是“实然”,即实际就是如此。天地就是在自然而然地运行。“不仁”,就是“麻木不仁”,即无目的、无意志。天,麻木不仁地“雕刻众形”,并不关心自然万物的生灭存亡;地,麻木不仁地“覆载万物”,并不关心人间社会的喜怒哀乐。“圣人不仁”则不同。“圣人不仁”是“应然”,即依理应当如此。“圣人不仁”之“不仁”,仅仅是个摹状词,老子在此只是希望理民治国的“圣人”,能够循道而行,“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因自然,守道真,不妄作,并不是教唆“圣人”去做冷血动物。美国学者史华兹(Schwartz)“隔岸观火”,把老氏言说“圣人不仁”的意向性看得一清二楚:“就意向性而言,它并不是善的,它只是想使得‘道’所蕴含的自发‘无为’的力量能够在人类事务中达到它们自己的目的。”[7]211老氏“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1]87言说的意向性,也应该作如是观,其无非是想说循“道”治国理民,“我无为而民自化”。道家之老庄,在论“无为而治”的治道上取向有别:老子侧重宣扬“无为之所益”,教人主为“无为”;庄子则侧重揭露“有为”之有害,教人主弃“有为”。同时又殊途同归:识得“无为之所益”,也就明白了“有为”之有害;洞察到“有为”之有害,即会顿悟“无为之所益”。
论及治道,《淮南子》承老氏之余绪,倾力宣扬“无为之所益”:
天设日月,列星辰,调阴阳,张四时,日以暴之,夜以息之,风以干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见其所养而物长;其杀物也,莫见其所丧而物亡。此之谓神明。[8]2035
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月照其夜,日照其昼,阴阳化,列星朗,非其道而物自然。故阴阳四时,非生万物也;雨露时降,非养草木也。神明接,阴阳和,而万物生矣。故高山深林,非为虎豹也;大木茂枝,非为飞鸟也;流源千里,渊深百仞,非为蛟龙也;致其高崇,成其广大,山居木栖,巢枝穴藏,水潜陆行,各得其所宁焉。[8]2044
这两段文字,意象密集,辞采飞扬,意旨却很是单纯。用如许铺张的巧丽文字,仅仅说的是“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的素朴真理。不过,“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确实是道家倡导的“无为而治”的根基。
在老子那里,“无为之所益”不在别处,就在“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中。“无为而治”是圣人治国理所当然的方式。“理所当然”的事物是无须论证的。故而,老子论“无为而治”,功力全花在端正人主“为‘无为’”之德,条理人主“为‘无为’”之术上。《淮南子》不同,它要给“无须论证”的“理所当然”做出论证。论证时动用的资源,却是和道家思想完全不同质的、比附性的“天人同构”——人的精神和形体结构都和天道密切关联:
夫精神者,所受于天也;而形体者,所禀于地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背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故曰一月而膏,二月而肤,三月而胎,四月而肌,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八月而动,九月而躁,十月而生。[8]722
天有九重,人亦有九窍;天有四时以制十二月,人亦有四肢以使十二节;天有十二月以制三百六十日,人亦有十二肢以使三百六十节。故举事而不顺天者,逆其生者也。[8]387
故头之圆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天有四时、五行、九解、三百六十六日,人亦有四支、五藏、九窍、三百六十六节。天有风雨、寒、暑,人亦有取与喜、怒。故胆为云,肺为气,肝为风,肾为雨,脾为雷,以与天地相参也,而心为之主。是故耳目者,日月也;血气者,风雨也。[8]722
在“天人同构”的视野里,人形是“天象”的直接落实,人性是“天道”的直接落实。通俗地说,人是“天”的仿生物或“克隆”品。既然如此,人也就应该像天一样,秉持自然无为的原则,“遵天之道”“循天之理”“以天为期”,以“无为”治天下。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淮南子》对“无为而治”强作解事的论证,虽然说得天花乱坠,却和先秦道家的“无为而治”仅不搭界,而且相背反。“天人同构”是汉儒信守的观念,其主旨是讲天人感应的。落实到治国上,如《礼记·月令》所示,纯是“有所为”地“仿自然”,而不是“无为”地“循自然”。《淮南子》强作解事,用“天人同构”给“无为之所益”做论证,实在是“画蛇添足”。
与此同时,《淮南子》还从神话传说和历史经验出发,以古代道家式的圣王为学习榜样,进一步论证人君应当如何如何。这样的论证方式,在《老子》书中不多见,在《庄子》书中倒是经常使用,《庄子》自言“寓言什九”,是《庄子》最基本的陈述策略之一。《淮南子·原道训》云:
泰古二皇,得道之柄,立于中央,神与化游,以抚四方。是故能天运地滞,轮转而无废,水流而不止,与万物终始。风兴云蒸,事无不应;雷声雨降,并应无穷;鬼出电入,龙兴鸾集;钧旋毂转,周而复币;已彫已琢,还反于朴。无为为之而合于道,无为言之而通乎德;恬愉无矜而得于和,有万不同而便于性;神托于秋豪之末,而大宇宙之总。其德优天地而和阴阳,节四时而调五行。呴谕覆育,万物群生;润于草木,浸于金石;禽兽硕大,豪毛润泽,羽翼奋也,角觡生也,兽胎不贕,鸟卵不毈;父无丧子之忧,兄无哭弟之哀;童子不孤,妇人不孀;虹蜺不出,贼星不行;含德之所致也。[8]1-2
昔舜耕于历山……当此之时,口不设言,手不指麾,执玄德于心,而化驰若神。使舜无其志,虽口辩而户说之,不能化一人。是故不道之道,莽乎大哉!夫能理三苗,朝羽民,徒裸国,纳肃慎,未发号施令而移风易俗者,其唯心行者乎?法度刑罚,何足以致之也?[8]60
传说中的“泰古二皇”,因为“得道之柄”,所以能“神与化游”,天下大治;历史人物大舜,因为“执玄德于心”,所以能“化驰若神”。据此,《淮南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是故圣人内修其本而不外饰其末,保其精神,偃其智故,漠然无为而无不为也,澹然无治而无不治也。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所谓无不为者,因物之所为也。所谓无治者,不易自然也;所谓无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8]60《淮南子》对治道“无为之所益”的这一层论证,没有上一层论证时“自作聪明”,尚知“调适上遂”——超越经验,臻于原理。得历史经验的支撑,《淮南子》就顺畅地将“无为而无不为”之常道,向下落实为根本的为政原则,而不仅仅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了。
三 从“无为”到“有为”的内在偏转
史华兹在对老子所向往和设想的道家式圣王“无为”而治的行为进行分析时,发现其中有一个他所谓的“道德偏转力的问题”:“确实,圣贤—君王的行为中似乎包含有尚未解决的矛盾。他似乎深思熟虑地创造了一种使得世界退回道的质朴状态的乌托邦。要回复到原始状态,肯定得籍助于自觉的筹划。”[7]221既然是“自觉的筹划”,那么自然而然地,这种筹划不可能不含有偏向,不含有深思熟虑的选择。这样,道家式的圣王们“用来否定文明的‘政策’本身似乎就是‘有为’的例证”[7]222。史氏所谓的“道德偏转力”指“无为而治”,实乃道家或崇信道家思想的政治家基于“深思熟虑”上的“自觉筹划”。行“无为而治”,其间有一系列致曲工夫——“为无为”之“德”、“为无为”之“术”——要去做,决不是用“纯任自然”四个字就可以简单了结。
史氏所提出的“道德偏转力”问题,是个颇有启发性的问题。确如史华兹所言,道家倡导的“无为而治”,的确是道家在体道的基础之上,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对人主的行为的自觉筹划。验之以汉初有名的“萧规曹随”,其“无为而治”的表象之下,“自觉筹划”的意味甚浓,并且也取得了明显的治理效果。但是这种“道德偏转力”,是否意味着“无为”只是道家炫人的“口实”,高唱“无为而治”的道家,实质上是“挟术以逞其私”,企图借“无为”做遮掩达到“有为”的目的?或者说,鼓吹“无为而治”的道家,实质上是在鼓励人君“深思熟虑”地“为”其所“欲为”?自从韩非《解老》《喻老》以来,对老氏“无为而治”的理解,一直存有这样的看法。那么,如此理解老氏的“无为而治”,更明确地说,“无为而治”可能“包含”的“道德偏转力”,是从道家“无为”思想逻辑中发现的,还是用其他思想,例如儒、墨、法思想去诠释乃至改写“无为”时催生出来的?从《老子》书中能明确看到,这种“道德偏转力”,不是“无为”思想逻辑中固有的。从《淮南子》中能够依稀感到,发生这种“道德偏转”,泰半是以“儒”释“道”时催生出来的。此处,本文只在道家“无为”思想逻辑之中,讨论此种“道德偏转力”如何诱使《淮南子》虽心仪老氏却常违老氏之旨而不自知。
这种把“无为而治”理解为“无为”之下的“有为”诉求,其实已经为实现从“无为”向“有为”的“偏转”设下了伏笔。这一点,《淮南子》里有所表现。尽管《淮南子》对于“无为而治”的“神化”境界颇为倾心,但其还是不知不觉地突出了在行“无为而治”时,要做到从“无为”到“有为”的贯通。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一意向,并不是从“无为而治”自身逻辑中引发出来的。在老子倡导的“无为而治”中,“无为”和“无不为”分明有不同的行为主体,其间不存在所谓“道德偏转”的逻辑。之所以能发生“从‘无为’到‘有为’的贯通”之类的“道德偏转”,是《淮南子·修务训》的作者在对某些“为‘无为’”实践中暴露出的倾向性问题的反省中激发出来的。
《淮南子·要略》在对《修务训》言说意向的披露中,点出了“无为”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
《修务》者,所以为人之于道未淹,味论未深,见其文辞,反之以清静为常,恬淡为本,则懈堕分学,纵欲适情,欲以偷自扶,而塞于大道也。今夫狂者无忧,圣人亦无忧。圣人无忧,和以德也;狂者无忧,不知祸福也。故通而无为也,与塞而无为也同;其无为则同,其所以无为则异。[8]2128-2129
按《修务训》的说法,“修务”之“修”,就是修“本业”;“修务”之“务”,就是“务方术”。言下之意是:假如想做好某一方面的工作,必须对这一方面的内部规律——《要略》所谓的“道”,有一个透彻的理解:修“本业”;必须有一套结合具体实践制定出的、有助于推动这一方面工作展开的有效办法——《要略》所谓的“论”:务“方术”。否则,无论是多么完善的施政纲领,付诸实践,都会走向自己的反面。按《修务训》的说法,“修务”问题,是从对实施“无为而治”的具体实践中暴露出的“某种倾向”的反思中萌生的,“或曰:‘无为者,寂然无声,漠然不动,引之不来,推之不往。如此者乃得道之象。’吾以为不然”。结合《要略》所言,此一倾向,滋生于“于道未淹,味论未深”。也就是说,舍“为‘无为’”的精神实质不去理解、去贯彻,而热衷于搞花架子,做表面文章,遂以“寂然无声,漠然不动”为“得道之象”,以之炫己,以之蒙人,“纵欲适情”,“以偷自挟”。《修务训》揭露出的这种怪现象,在“贵尚黄老”的文景之世是个别现象,还是突出矛盾?诚如《要略》所言,在当时的政治实践中,有两种“无为”:“通而无为”——遵循“无为”之道的精神实质而“为‘无为’”的真“无为”;“塞而无为”——违背“无为”之道的精神实质而“为‘无为’”的伪“无为”。因此,《淮南子》以为,为了对治“塞而无为”,有必要对“无为”之道的精神实质做出更深更细的诠释:
(1)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所谓无不为者,因物之所为。所谓无治者,不易自然也;所谓无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根;百事有所出,而独知守其门。故穷无穷,极无极,照物而不眩,响应而不乏,此之谓天解。[8]60
(2)君道者,非所以为也,所以无为也。何谓无为?智者不以位为事,勇者不以位为暴,仁者不以位为患,可谓无为矣。夫无为,则得于一也。一也者,万物之本也,无敌之道也。[8]1494
(3)或曰:“无为者,寂然无声,漠然不动,引之不来,推之不往;如此者,乃得道之像。”吾以为不然。尝试问之矣:若夫神农、尧、舜、禹、汤,可谓圣人乎?有论者必不能废。以五圣观之,则莫得无为,明矣。……圣人忧民,如此其明也,而称以“无为”,岂不悖哉![8]1939
(4)若吾所谓“无为”者。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在正术,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功],权[推]自然之势,百曲故不得容者,事成而身弗伐,功立而名弗有,非谓其感而不应,攻而不动者。[8]1950
前两条是《淮南子》对“为‘无为’”精神实质的理解。
引文(1)摘自《原道训》。在这里,《淮南子》对于“为‘无为’”为政之道中的“无为”和“无不为”进行了自己的诠释。“为‘无为’”为政之道中的“无为”,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先物先”,即在物的自然情状尚未表现出来、条件没有成熟之前,不能去施加人为的影响;“无不为”则是在物的自然情状表现出来、条件成熟之后,依照物的自身情状,顺势而行,任物自为。这样,围绕物的情状发生前后,“无为”和“无不为”就实现了互相衔接,前后贯通。而“衔接贯通”的关键在于“守其根”,即“淹浃”于“道”——深入领会“为‘无为’”的精神实质;“守其门”,即“深味”于“论”——真切把握“为‘无为’”的方法要领,不为字面上的“无为”“无不为”所眩。假如果能舍去此说中有忽视乃至混淆“无为”和“无不为”“有不同的行为主体”之嫌疑的话,那么,在《淮南子》对“无为而治”的所有诠释中,相对而言,这一段确实较洽当,既有现实针对性,又不甚违老氏之本旨。
引文(2)摘自《诠言训》。在这里,《淮南子》把“无为”定位于“君道”,大体不差。在《老子》书中,在治道范围内言说“为‘无为’”的地方,泰半是对人君说的:要求人君守道真、因自然、不妄作,让“民自化”、让“物自成”。假如“智者不以位为事,勇者不以位为暴,仁者不以位为意”,是为政的主体——人君以及居“位”之臣的自我规范:我有“智”而不妄生事,我有“勇”而不胡逞强,我有“仁”而不乱炫耀,如《老子》第五十七章说的,“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那么,这一段阐释,颇得老氏“无为而治”的真谛。假如“智者不以位为事,勇者不以位为暴,仁者不以位为意”是人君对居“位”臣工的防范,口中不说,心中常念不能让臣工中的“智者”用他手中的权力妄为奸事,不能让臣工中的“勇者”用他手中的权力动辄犯上,不能让臣工中的“仁者”用他手中的权力邀买人心,那么,这一段阐释已经严重地跑调儿了,“无为”已经被解释成“欲取故予”、静观其变、“该出手时才出手”的驭下之术。而如此理解“无为”,是韩非的理解意向,不是老氏的“期待视野”。
后两条是《淮南子》对当时“为‘无为’”政治实践中暴露出来的倾向性问题的澄清,以及有针对性地矫正。
引文(3)摘自《修务训》。在这里,《淮南子》对于“无为”就是“无所作为”的认识进行了批判。老氏倡导的“无为而治”里的“无为”只是“不妄为”,即治国理民最好的方式是不妄加干扰,让民自治,“顺理成章”,求一个“水到渠成”。把老氏“无为”理解成整日拱手居默、什么事都不做,是对老氏“无为”的最大误解。《淮南子》把以“寂然无声,漠然不动”视为“得道之象”从而束手不作,当作“无为而治”实践中的头等问题集中回应,自有其正确的一面,但对这一态度的回应,也显现出其思维存在不清不密之处。
之所以有这样的判断,是因为:其一,在当时“为‘无为’”的政治实践中暴露出的带有倾向性的问题,究竟是以“寂然无声,漠然不动”为“得道之象”,从而整日拱默、束手不作,还是去秦未远,暴政余习未脱,急于作为,烦政忧民呢?如果是二者并存,或者竟是后者,那么,《淮南子》回应的“正确”程度,仅仅是“学理不差”而已。其二,《淮南子》说“无为”不是拱默。以“寂然无声,漠然不动”为“得道之象”乃是时人对“无为”的根本性误解,完全正确。但是,《淮南子》用“五圣广有做为”,去回应时人对“无为”的误解,却是犯了方向性错误而不自知。诚如《要略》所言,以“寂然无声,漠然不动”为“得道之象”从而束手不作,根子在“于道未淹,味论未深”。故而,纠正误解的最有效的办法是重申“为‘无为’”的精神实质——“守道真,因自然,不妄为”。例如,突出剔抉神农“相土地(之宜)”“教民种谷”、尧“殛鲧于羽山”、舜“作室,筑墙茨屋”、禹“决江疏河”“平治水土”、汤“轻赋薄敛”等等所作所为中,一以贯之的“守道真,因自然,不妄为”的基本精神,就足以解惑见真。而不是如《修务训》那样,泛泛强调广有所为,如此只会鼓励人恣意兴作,从而走向“无为”的另一反面。而“鼓励恣意兴作”引发的后果,比起“束手不为”,更不知要严重多少倍。“束手不为”,尚能在客观上给老氏“无为而治”中“我无为而民自化”留存有活动的空间,而“恣意兴作”,无论是出于“忧民瘼”的“髙尚”动机,还是出自“逞私志”的卑鄙念头,都是老氏“无为而治”要根除的对象。《淮南子》在“修务”的语境中,泛泛而谈“五圣广有所为”,用“五圣”之“广有所为”而不是用“五圣”之“有所不为”去诠释“无为”之旨,所能引起的客观效果,无疑是把“无为而治”从政治实践的土壤上连根拔除。设若“无为而治”被连根拔除了,谈论“无为”“有为”,不就是空洞无意义了吗?
引文(4)摘自《修务训》。引文(4)沿引文(3)的思路,进一步对“无为”的意义进行“有为”式的“充实”。以为“无为”的精神实质,在“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功],权[推]自然之势”[8]1955。假如孤立地就事论事,以本文对老氏“无为”的理解——“守道真,因自然,不妄作”课之,《淮南子》之《修务训》对“无为”的诠释,除了“循理”远不如“守道”准确(在《老子》里,“道”和“理”不是同一层次的概念,见《韩非子·解老》[9]),“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功]”有鼓励兴作的嫌疑,“权(推)自然之势”有把“因自然”当作权宜之计的嫌疑而外,尚无大错。当《修务训》进一步把“无为”具体落实为“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在正术”“事成而身弗伐,功立而名弗有”[8]1955时,问题就出来了:“无为而治”势必要发生“道德偏转”。
按老氏的本旨,“无为而治”实际上是“道常无为无不为”在政治领域里的延伸。按《老子》第五十七章里的说法:“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行“无为而治”,涉及两个层面的人——施政之“君”和受治之“民”。因而,在实施“无为而治”的时候,“无为”和“无不为”,施用的对象有清晰而严格的分野:“无为”,是“无为而治”对施政之“君”为政之“德”的要求;“无不为”,则是“无为之治”赋予受治之“民”的权力,或者说,是行“无为而治”给受治之“民”带来的福祉。“无为”和“无不为”之间,也存在不容颠倒的因果关联:因为施政之“君”为“无为”——少干涉,乃至不干涉,所以受治之“民”才有了“无不为”的空间——在自治中“自化”“自正”“自富”“自朴”,全面地完善自身。而《淮南子·修务训》却认为只要“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在正术”“权[推]自然之势”,人主就可以放手让他的臣工们去“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功]”,即为所欲为了。用这种方式包装过的“无为”,实质上,已经混淆了“无为而治”中“无为”和“无不为”不容混淆的分野,颠倒了“无为而治”中“无为”和“无不为”之间不容颠倒的因果关系,把“无为无不为”修正成“君无为,臣无不为”。而“君无为,臣无不为”,即“君逸臣劳”式的“无为而治”,未脱韩非窠臼,不仅不是老子的思致,还和老子“无为而治”的基本精神相背反。当然,应该看到,《淮南子》鼓励的“臣无不为”的时候,有一个限定的前提——“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入正术”。但这一限定前提,仍然挽救不了它的根本性失误。因为,按道家的认识,“私志”“嗜欲”,正是“有为”滋生的根源。只要“有为”,就免不了“私志”“嗜欲”的介入,更何况是“无不为”?“公道”和“私志”、“正术”和“嗜欲”,只是些文字符号。用这些文字符号包装的内容,决不像文字面标示得那样,“公私”不并存、“正邪”不两立,“公道—私志”“正术—嗜欲”之间,并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更为重要的是,在老子思想里,所谓“公道”“正术”,就是“我无为而民自化”,根本就不存在什么人主只要出于“公道”、秉以“正术”,就可以“无不为”的逻辑。《淮南子》的诠释,实质上是要收回“无为而治”许诺给受治之民的权力——“无不为”,把它重新交还给施政之君,让受治之民除了成为“耕战”的工具之外一无所为。这种样式的“无为”,绝对不是老子希望看到的,而是“有为”之君主才乐于受用的。
四 结语
准确评价《淮南子》有关“无为”的言说,不是一件简单易了的事。有论者认为,《淮南子》对于“无为”的理解,其积极意义甚明。假如“积极意义”指其对“无为”就是“拱手居默,甚事莫为”的校正,“甚明”之说尚可接受。假如指其打通了所谓“‘无为’和‘无不为’之间的界限”,非常重视对于客观条件恰如其分地利用,因物性而为之,循理举事,因资立功,从而在看似被动的不为物先、执后而行的状态中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等等,就需要谨慎再三,力避认“伛”为“恭”。《淮南子》心仪老氏“无为”是事实;《淮南子》言说老氏“无为”时常自违老氏之旨而不自知,同样是事实。尤其是在“打通‘无为’和‘无不为’之间的界限”时,思路不对,思维不清,严重违背了老氏之旨,几乎要葬送掉“无为而治”。
导致《淮南子》“心仪老氏又常自违老氏之旨而不知”的原因是复杂的。其一是《淮南子》作者自身的原因。刘安为“流名誉”而著书,有急于求成之心,著书又假众宾客之手,宾客们道家之学的修为浅深不一,精粗有别。故而,以“急于求成”之心,言说老氏“无为”之道,必然要“常自违老氏之旨而不知”,乃至于强作解事,“笔走偏锋”,标新立异以求高,也是可以预见的。其二是外部大环境也存在“言说‘无为’自违老氏之旨而不知”的诱因。“贵尚黄老”,始于孝惠,盛于文景。在汉初,主“清静无为”的黄老之学以堪为“与民休息”之“术”才成为思想时尚的。在这一背景下,韩非的《解老》《喻老》,肯定很有市场。例如,汉景帝就甚好“刑名家言”。汉武帝在即位之初,整顿学校,清理学术,首先罢黜的便是“明苏、张、申、韩之术者”。而经韩非“解”“喻”过的《老子》,至少在“无为”上和《老子》完全异趣。本文之所以在对《淮南子》“无为”言说的分析中,屡屡剔抉其中包藏的“韩非因子”,正是基于对这一层背景的省察。更为重要的是,老氏“无为而治”的经验基础,是基本上如“自治”的农村村落一样的“小国寡民”,因此行“无为而治”,易如反掌。但是经过数百年的转相征伐,已经实现了天下一统,昔日的“以一人奉天下”转换成“以天下奉一人”,统治者已经以“天”之“子”自居,习惯于称“孤”道“寡”。让习惯于称“孤”道“寡”的统治者“无为”,彻底下放手中的权力,任民自治,已无任何可能性。在“文景”那样的“大一统”政治体制内,严格要求在老氏之学的界域之内言说“无为”,只有学术意义,而无现实意义。因此在政治领域里言说“无为”,就不能不结合现实的政治体制另辟蹊径,进行有针对性地言说,哪怕是有违于老氏,这或许是《淮南子》如此言说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