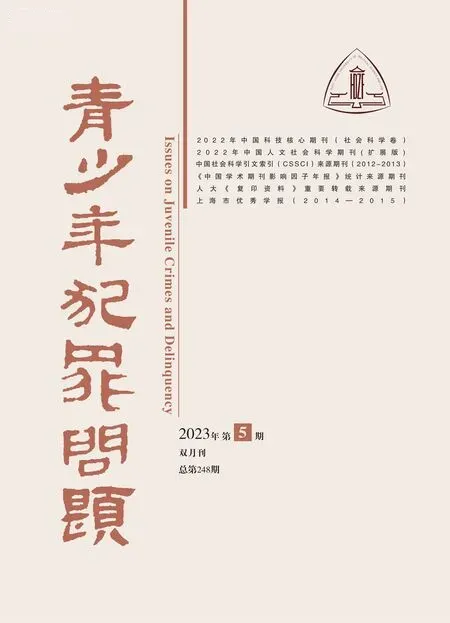论犯意转化
马荣春 田玉琼
张明楷教授指出,犯意转化、另起犯意与行为对象转换首先是关联故意的认定,进而是罪数论需要讨论的问题。其中,犯意转化会导致行为方式、性质产生变化而影响故意内容的认定。(1)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266页。前述论断符合发生学规律和认知心理学规律:人的内心活动支配人的行为并决定行为的方式与性质,而人的行为方式与性质又回过头来印证人的内心活动,可谓主观支配客观,而客观反映主观。由于直接影响故意认定和罪数认定,从而关涉刑法责任主义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和刑罚个别化原则,且可勾连运动刑法观,故犯意转化便成了刑法学理论中一个“小中见大”的实际问题。
一、犯意转化的基本类型
由于较少受到关注,犯意转化的基本类型尚未见有条理的归纳或概括。
(一)过失向故意的犯意转化
以往的刑法理论只是较多地关注故意向故意的犯意转化,正如犯意转化是指行为人在犯罪行为的过程中改变犯罪故意而导致此罪与彼罪的转化。(2)贾宇主编:《刑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年版,第172页。由于故意和过失是基本的罪过形式,故当犯意转化发生在基本的罪过形式之间或其内部,便形成了犯意转化的基本类型,且犯意转化的基本类型首先包括过失向故意的犯意转化。
张开骏博士指出,犯意变化不仅表现为此故意向彼故意的变化,也可表现为此种罪过向彼种罪过的变化,即过失向故意变化(故意向过失变化在理论和实践中很难存在),是指行为人过失地导致某种法益产生危险状态或者发生基本结果,有能力采取措施却拒不采取乃至实施积极行为,导致了危险状态现实化或发生更严重结果的情形。此种犯意变化,需要先后存在过失和故意罪过,且在其支配下先后实施过失行为与故意行为(包括作为和不作为)。(3)张开骏:《犯意和对象变化的犯罪认定》,载《当代法学》2015年第3期。对过失向故意的犯意转化,可作出如下定义:过失向故意的犯意转化,是指伴随着前行为向后行为的推进,行为人的犯罪过失向犯罪故意发生演化。张明楷教授认为,过失向故意的转化即行为人的过失行为导致某种法益产生危险,但故意不消除危险,而是希望或放任结果发生。例如,行为人不慎将烟头扔在仓库里,具有发生火灾的危险,行为人能够及时消除危险,但其转念又想通过造成火灾陷害仓库保管员而故意不消除危险,从而导致火灾发生。这便是由一般过失转化为犯罪故意,对其行为应认定放火罪而非失火罪。又如甲系乙聘请的家庭保姆,负责处理家务和照顾乙两岁多的儿子丙。某日下午五点半左右,甲给丙喂桂圆时,不料桂圆核卡住丙喉咙而无法吐出,甲随即将丙送往附近药店救治。但甲怕承担责任,向药店工作人员隐瞒了丙被桂圆核卡住喉咙的事实。返回乙家后,甲又向赶来的120急救医护人员隐瞒真相,致使医护人员无法采取针对性急救措施而延误抢救时机。丙被送往某市儿童医院,经抢救无效于同日晚十点半因异物吸入、窒息、脑疝、多器官功能衰竭而死亡。甲将有核的桂圆喂给丙吃,导致桂圆核卡住丙的喉咙而无法吐出时,就对丙的生命产生了危险。如果甲对医护人员说出真相仍未能避免死亡结果发生,甲成立过失致人死亡罪。但本案的甲因为怕担责任而没有说出真相,虽然其并不希望死亡结果发生,但对结果持放任态度,应认定为间接故意的不作为犯罪即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4)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297-298页。基于同样理由,过失行为虽然已经造成了基本结果即成立基本的过失犯,但在能够有效防止加重结果发生的情况下,行为人具有防止加重结果发生的义务却故意不防止的,对加重结果成立故意犯罪。例如,司机甲于黑夜在车辆较少的道路上违反交通法规过失将三人撞成重伤后,便下车查看情况,本可以将三人送往医院抢救,但想到被害人死亡也无所谓,便立即逃走,三名被害人后来全部死亡。如果三名被害人是濒死的重伤,则行为人的行为本身就能成立交通肇事罪。而如果行为人将三名被害人送往医院就可以救助其生命而被告人故意不救助的,则“可能”另成立不作为的故意犯罪。(5)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297-298页。
当张明楷教授所举的前述具体个案能够例证过失向故意的犯意转化时,则可总结或概括出过失向故意的犯意转化的基本特征:一是在事物的时空上,犯意转化是发生在犯罪行为的继续发展过程中,即转化后的犯意或新的犯意并非形成于另一个或又一个行为过程;二是在事物的价值上,前后犯意即转化前的过失和转化后的故意有着同质或包容的法益指向,亦即作为整个犯罪过程发展阶段的转化前的行为和转化后的行为有着同质或包容的法益侵害性。于是,前述两个基本特征便隐含着过失向故意的犯意转化的判断标准,而此判断标准就是犯意转化和另起犯意的甄别标准。这里,我们可将第一个特征即时空特征所隐含的标准视为过失向故意的犯意转化的外在标准或形式标准,而将第二个特征即价值特征所隐含的标准视为过失向故意的犯意转化的内在或实质标准。于是,符合前述标准的便是过失向故意的犯意转化,否则便可能是另起犯意。如在前述丢烟头的事例中,如果行为人出于陷害的目的又在危险区内扔了一个烟头而造成了更大的火灾,则行为人的行为便不属于犯意转化而属于另起犯意,从而应按照失火罪和放火罪予以数罪并罚,因为“又扔了一个烟头”开启了另一个或又一个行为过程,而出于陷害目的的故意则支配了该独立的行为过程。又如在前述交通肇事的事例中,如果行为人对被害人死亡的“无所谓”不是表现为消极的逃逸而是积极地将被害人弃置于路基之下而使得被害人难以得到及时救助的行为,则行为人的行为同样不属于犯意转化而属于另起犯意,从而应按照交通肇事罪和故意杀人罪予以数罪并罚,因为“积极地将被害人弃置于路基之下”又开启了另一个或又一个独立的行为过程,而对被害人死亡的“无所谓”所对应的间接故意则支配了该独立的行为过程。在前述经过假想的两个事例中,虽然失火罪与放火罪具有同质的法益侵害性,或交通肇事罪所对应的公共安全法益侵害性与故意杀人罪所对应的公民生命法益侵害性具有包容性,但在时空上,后一个犯意即故意及其所支配的法益侵害性与前一个犯意即过失及其所支配的法益侵害性并非处于同一个行为发展过程,即其不具备过失向故意的犯意转化的第一个或首要特征,即“同一时空”标准。而在过失向故意的犯意转化的场合,由于是转化后的犯意即故意主导或支配了犯罪行为的发展走向并决定了行为过程的最终结局,故应按转化后的犯意即故意的具体内容来作出犯意转化的责任认定。如在前述出于陷害目的而故意不消除火灾危险的例子中,对行为人的行为最终应认定为放火罪;而在前述撞伤人后却见死不救的例子中,对行为人的行为最终应认定为交通肇事罪的结果加重犯。这里要指出的是,在过失向故意的犯意转化的场合,前后犯意所指向的法益关系有两种情形即同质关系(如前述丢烟头案和保姆喂食桂圆案)和包容关系(如前述交通肇事弃被害人于不顾案),且以同质关系为常见。前后犯意所指向的法益关系具有同质关系的情形,还可形成于渎职犯罪中。正如我们所知,刑法理论对滥用职权罪和玩忽职守罪的区别围绕着罪过形式问题一直存在着较多分歧,而通行的观点,是故意实施的违背职责的行为是滥用职权罪,而过失实施的违背职责的行为是玩忽职守罪,亦即玩忽职守罪是过失犯罪,而滥用职权罪是与之对应的故意犯罪,但故意与过失是位阶关系而非对立关系。(6)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250页。但针对玩忽职守罪的主观方面只能是过失的通行观点,较早有不同的声音,或曰玩忽职守罪的主观方面既可以出于故意,也可以出于过失,故在司法实践中,就必须注意要把明知故犯的行为,也纳入玩忽职守罪的范围;(7)张保尔:《对玩忽职守罪主观要件的再认识》,载《政治与法律》1988年第2期。或曰间接故意也可构成玩忽职守罪,并且间接故意的玩忽职守罪,罪犯的主观恶性程度较过失的玩忽职守罪更大。(8)丁凌波:《间接故意也可构成玩忽职守罪》,载《中南政法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随后,仍间或有人提出,玩忽职守罪可以是出于间接故意。具言之,在现实生活中,某些担负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明知自己不履行职责的行为会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重大损失,仍然严重不负责任,放弃或背离职守而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此时其主观上则表现为间接故意。(9)张光辉:《玩忽职守存在间接故意罪过形态》,载《检察日报》2014年8月20日,第3版。在本文看来,出于间接故意的玩忽职守罪应该得到肯定,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某甲在夜间值班时发现有人正在盗窃本单位财物,但其贪生怕死而任由犯罪分子将本单位财物窃走,致使国家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由玩忽职守罪的主观方面可以是间接故意,本文要进一步指出的是,玩忽职守的行为在主观方面不仅可由过失向间接故意转化,甚至可由过失向直接故意转化。于是,诸如前述某甲放任国家财产遭窃仍应认定为玩忽职守罪而最终难以形成真正的犯意转化,而由过失转化而来的直接故意将使得玩忽职守行为演变为滥用职权行为,从而形成真正意义的犯意转化。如某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办理某单位或个人石油勘察许可证申请过程中先是粗心大意,但就在制作许可证时一下子想起申请单位正是自己亲友的任职单位或申请个人就是自己的亲友,于是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将许可证制作齐全且交于不符合条件的申请单位或个人。在前例中,行为人的主观罪过由过失转化为间接故意。显然,前例仍然只能认定该国家工作人员的行为构成玩忽职守罪。而如果该国家工作人员出于讨好或巴结的目的而授意申请单位或个人伪造申报条件且随后将非法办理的许可证交于申请单位或个人,则其行为便在直接故意之中构成滥用职权罪。显然,滥用职权罪与玩忽职守罪指向的法益具有同质性,而过失向直接故意的转化能够使得玩忽职守罪向滥用职权罪发生转化。由此也可见,认为滥用职权罪的罪过不包括直接故意,(10)储槐植、杨书文:《复合罪过形式探析——刑法理论对现行刑法内含的新法律现象之解读》,载《法学研究》1999年第1期。是存在局限的;而将滥用职权罪的罪过形式只限于过失,更是让人难以接受的。(11)蒋铃:《滥用职权罪罪过形式的深度探讨》,载《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13年第2期。
进一步地,过失向故意的犯意转化又可大致划分为疏忽大意的过失向间接故意和向直接故意的犯意转化、过于自信的过失向直接故意的犯意转化。但这里要强调的是,前述只是对过失向故意的犯意转化的大致划分,而在现实生活中,过失向故意的犯意转化或许会形成丰富多彩的“曲折”形态。如无论是疏忽大意的过失向间接故意的犯意转化,还是疏忽大意的过失向直接故意的犯意转化,中间都要经由过于自信的过失,即以过于自信的过失为犯意转化的“转化中介”,因为疏忽大意的过失毕竟是“无认识过失”,(12)马克昌:《比较刑法原理外国刑法学总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65页。而从“无认识过失”不可能一下子“转化”或过渡到间接故意或直接故意。过失向故意的犯意转化甚至会形成由疏忽大意的过失到过于自信的过失到间接故意再到直接故意的更“曲折”的形态。如当行为人出于疏忽大意在禁烟区扔了一个烟头,便有从其身边经过者提醒其将烟头踩灭,但行为人置若罔闻,自觉不会引起火灾。几乎正当此时,行为人顿生陷害他人之恶意:着火就着火吧!谁曾想行为人陷害他人之恶意瞬间陡增:着火更好!于是,行为人最初疏忽大意过失中的危险演变为其最终的直接故意的火灾实害。当然,前述情形仍属于由轻而重的犯意转化,对行为人的责任认定及其主观恶性和再犯危险性评价仍应以最终的罪过内容为考察材料。
(二)故意向故意的犯意转化
张明楷教授指出,犯意转化的第一种情况是,行为人以此犯意实施犯罪的预备行为,却以彼犯意实施犯罪的实行行为。如行为人在预备阶段具有抢劫故意,表现为准备抢劫工具,但在进入现场后发现无人在场,于是实施了盗窃行为。在这种情况下,通常认为应以实行行为吸收预备行为,但事实上可以根据重行为吸收轻行为的原则认定犯罪。犯意转化的第二种情况是,在实行犯罪的过程中犯意发生改变,从而导致此罪与彼罪的转化。这种犯意转化应限于两个行为所侵犯法益具有包容关系的情形。如行为人在伤害他人过程中改变犯意而意图杀死他人,或在实施杀害行为过程中,由于某种原因改变犯意而认为造成伤害即可,故其停止侵害行为。又如,行为人见他人携带装有现金的提包便起抢夺之念,但在抢夺过程中转化为使用暴力而将被害人打倒在地,抢走提包。(13)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266-267页。显然,故意向故意的转化应视为犯意转化的主要类型或通常表现。
过失向故意的犯意转化和故意向故意的犯意转化所形成的基本分类,可视为采用了犯意内容这一标准。进一步地,作为犯意转化一个基本类型的故意向故意的犯意转化又可作出更加具体的类型划分。由张明楷教授所列的犯意转化的两种情况,即第一种情况是行为人在犯罪预备阶段是此犯意但在实行阶段是彼犯意,而第二种情况是行为人在实行犯罪的过程中将此罪犯意改变为彼罪犯意,我们还可想到的一种情形是:在犯罪预备阶段,行为人将此罪犯意改变为彼罪犯意,如在犯罪预备阶段,行为人原先是为伤害被害人做准备,后改变为为杀害被害人做准备,或与之相反。由此,故意向故意的犯意转化便在发生时空上形成三个基本类型,即犯罪预备阶段的犯意转化、犯罪实行阶段的犯意转化和犯罪预备阶段与犯罪实行阶段之间的犯意转化。这里对故意向故意的犯意转化所作的前述分类采用的是时空标准。由此可见,当下教材对犯意转化作出两个类型的描述即犯罪预备阶段与犯罪实行阶段之间的犯意转化和犯罪实行阶段的犯意转化,(14)贾宇主编:《刑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年版,第172-173页;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266-267页。是存在不足或局限的。张开骏博士认为,犯意或对象的变化,当然限于变化前后行为人已实施了相应行为,不管是预备行为还是实行行为。(15)张开骏:《犯意和对象变化的犯罪认定》,载《当代法学》2015年第3期。这就说明:在犯罪预备阶段是可能发生犯意转化的。
由于行为对象通常是法益的直接载体,故行为人对行为对象的故意往往对应着对法益的故意即对法益的犯意。由此,行为对象便可构成犯意转化的切入点。又由于行为对象虽有现象层面的差异但可有价值层面的共性,因此故意向故意的犯意转化又可按照行为对象是否同一为标准即行为对象标准而作出两个分类,即同一行为对象上的故意向故意的犯意转化和不同行为对象之间的故意向故意的犯意转化。严格来说或实际上,故意向故意的犯意转化的对象标准也有时空标准的意味,因为同一行为对象或不同行为对象原本就是时空性存在,正如刑法的空间效力包含属人管辖原则。(16)陈兴良:《本体刑法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24页。
需要强调的是,正如过失向故意的犯意转化,故意向故意的犯意转化也会出现“曲折”的形态,如在“性动机”的支配下行为人先是出于强奸的目的实施强奸行为,接着又出于对被害人不好嫁人或难以面对家人的怜悯而放弃了强奸行为,转而出于猥亵的目的而实施强制猥亵行为,但在实施强制猥亵行为时,出于“机会难得”等得失心理,行为人又恢复其强奸目的而最终实施强奸行为。在前述情形中,对行为人的责任认定及其主观恶性和再犯危险性评价仍应以最终的罪过内容为考察材料。
最后,与在过失向故意转化场合前后犯意所指向的法益具有同质或包容关系不同,故意向故意转化场合前后犯意所指向的法益只具有包容关系。而无论是过失向故意的犯意转化,还是故意向故意的犯意转化,犯意转化又都可以分为两类,即由轻而重的犯意转化亦即“犯意升高者”和由重而轻的犯意转化亦即“犯意降低者”,而“升高”或“降低”正是作为犯意转化“奠基”的“法益包容性”的一种“弦外之音”。
二、犯意转化与另起犯意和行为对象转换的甄别
当学者在讨论犯意转化时,常将其与另起犯意和行为对象转换问题放在一起,这就意味着此三个概念确需予以甄别。
(一)犯意转化与另起犯意的甄别
张明楷教授指出,犯意转化与另起犯意具有区别,前者是此罪转化为彼罪,故不会实行数罪并罚;后者是在前一犯罪已经既遂、未遂或中止后,又另起犯意实施另一犯罪行为,故当实行数罪并罚。具言之,犯意转化与另起犯意有三个重要区别:(1)行为在继续过程中,才有犯意转化问题;如果行为已经终了,则只能是另起犯意。例如,甲以强奸故意对乙实施暴力之后,因为乙正值月经期而放弃奸淫,便另起犯意实施抢劫行为。由于抢劫故意与抢劫行为是在强奸中止之后产生的,故甲的行为成立强奸中止和抢劫二罪。(2)同一被害对象才有犯意转化问题;如果针对另一不同对象,则只能是另起犯意。例如,A以伤害故意举刀砍B,适逢仇人C出现在现场,A转而杀死C。A的行为针对不同对象,应成立故意伤害与故意杀人二罪。(3)在两个法益具有包容关系时,才可能存在犯意转化,如果没有包容关系,则应认定为另起犯意。例如,A先对B实施伤害行为,导致B昏迷。此时,A发现B戴有首饰便见财起意而将B的首饰转移为自己占有。A的行为属于另起犯意,成立故意伤害罪与盗窃罪,实行数罪并罚。(17)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267页。前述是张明楷教授对犯意转化与另起犯意的区别所作的例证。
首先,犯意转化的“转化”当然意味着是在行为的继续发展过程中,而“另起犯意”的“另起”当然意味着另一个或又一个独立的行为过程,故张明楷教授所指出的犯意转化与另起犯意的第一点区别可视为二者的时空之别,且这一区别当无疑问。再者,当前后行为所侵犯的法益不具有包容关系时,当然不可能形成犯意转化,从而张明楷教授所指出的犯意转化与另起犯意的第三点区别可视为二者的法益之别。至于其所说的第二点区别,即将犯意转化的对象条件限定在“同一对象”即原先的被害对象,仍是当下刑法理论对犯意转化的一种通行认识,正如犯意转化是针对同一被害对象存在的,而另起犯意既可以针对同一犯罪对象也可以针对另一不同对象。(18)贾宇主编:《刑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年版,第173页。然而,我们或许会遇到这样的个例:A与B、C兄弟俩都有仇,但对C仇恨更深。某日,当A正以伤害的故意砍B,恰逢C也随后出现在现场,故A便转而以杀人的故意砍C且致C死亡。前述可能发生的个例与A正以伤害的故意砍B,但A越砍越气而索性将B砍死这一也有可能发生的个例,有何实质区别呢?这里,虽然B、C兄弟俩是两个不同的被害个体,但在规范评价上都属于“他人”,而“他人”的法益之间是完全可以形成包容关系的。因此,似乎不应将是否针对所谓“同一对象”作为犯意转化与另起犯意的区别,而这将引起下文要讨论的犯意转化与行为对象转换关系的讨论。由此,犯意转化与另起犯意的区别似应只归纳为两点:一是是否发生于前行为的继续发展过程中,即如果发生于前行为的继续发展过程中,便为犯意转化,而若开启了另一个独立的行为过程,则为另起犯意;二是前后行为所侵犯的法益是否具有包容关系,即如果前后行为所侵犯的法益具有包容关系,便为犯意转化,而若不具有包容关系,则为另起犯意。在前述两点区别中,第一点区别可视为对应着一种时空标准,且此时空标准实即外在标准或形式标准;而第二点区别可视为对应着一种价值标准,且此价值标准实为内在标准或实质标准。由于前述两点区别必须同时存在才能区别开犯意转化和另起犯意,故前述两种标准的相互结合才是犯意转化与另起犯意的完整的甄别标准。易言之,发生在前行为的继续发展过程中且前后法益具有包容关系的,便为犯意转化;相反,则为另起犯意。
实际上,犯意转化与另起犯意的区别也可作出如下重新概括并予以引申:一是犯罪过程是否具有同一性,即分别体现犯意转化和另起犯意的行为是否属于前后相继的同一犯罪过程;二是被侵犯的法益是否具有相通性或可过渡性。前述两点区别派生出犯意转化和另起犯意的第三点区别,是否一罪的区别:犯意转化对应着罪数认定的一罪,而另起犯意则对应着罪数认定的数罪。如果前述三点区别是用“是”来回答,则属于犯意转化;而如果其中有一项是用“否”来回答,则属于另起犯意。可见,犯意转化的特点或成立条件隐含在一个“转”字里,而另起犯意的特点或成立条件则隐含在一个“另”字里。例如:行为人潜入某女大学生宿舍欲行窃。当其发现该宿舍没有值得其盗取的财物而刚要离开时,住在该宿舍的一名女生恰好开门进宿舍。于是,在短暂的僵持后,行为人强令该女生脱光衣服让其“一饱眼福”。在该女生羞怯地背对着行为人时,行为人偶然发现该女生还手戴一块价值不菲的手表。于是,行为人又喝令该女生摘下手表。随后,行为人拿着手表逃离现场。显然,在前例中,行为人的行为发生两次另起犯意,而应按照盗窃罪(未遂)、强制猥亵罪和抢劫罪予以数罪并罚。可见,犯意转化的“转”字意味着“承继的一个”,而另起犯意的“另”字意味着“独立的另一个”。
进一步而言,犯意转化可视为一种“犯意绎演”,故其刑事责任应注重当下;而另起犯意,则可视为一种“犯意新演”,故其刑事责任应“旧账新账一起算”。易言之,与另起犯意引起两个行为实体和责任实体而应予数罪并罚不同,犯意转化最终只剩下一个行为实体和责任实体而只能按一罪论。可见,恰当甄别犯意转化与另起犯意,直接有助于我们对犯意转化问题的进一步理解。
(二)犯意转化与行为对象转换的甄别
由于“转化”与“转换”几乎同义,故犯意转化与行为对象转换也需予以一番甄别。张明楷教授指出,行为对象转换,是指行为人在实行犯罪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将原先设定的行为对象转换到另一行为对象上。例如,甲原本打算抢劫他人名画而侵入住宅,但入室后抢劫了手提电脑。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行为对象的转换依然处于同一犯罪构成之内,且法益主体没有变更,故成立入户抢劫的既遂,而非入户抢劫的未遂与普通抢劫既遂。再如,乙原本打算盗窃A的财物便侵入了A、B合住的房间,但侵入房间后仅盗窃了B的财物。虽然法益主体不同,但由于财产法益并非个人专属法益,故仅认定为一个盗窃既遂即可。但是,如果行为对象的转换导致个人专属法益的主体变化,则属于另起犯意。例如,甲为了强奸A女,在A女的饮食中投放了麻醉药。事后,甲发现A女与B女均昏迷,且B女更美丽,于是仅奸淫了B女。甲的行为成立对A女的强奸中止和对B女的强奸既遂。又如,乙为了抢劫普通财物而对X实施了暴力,在强取财物时,当发现X的提包内不仅有财物而且有枪支,乙便使用强力仅夺取了枪支。乙的行为成立抢劫中止与抢劫枪支既遂(数罪并罚)。(19)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267-268页。稍加分析,我们便可发现,在所谓行为对象转换的背后,张明楷教授是立足于法益侵犯的转换来分析和处置问题的。具言之,在行为对象转换的场合,如果存在诸如性自主权这样的专属法益侵犯的转换,则为另起犯意,从而应数罪并罚;如果存在财产法益这样的非专属法益侵犯的转换,则非为另起犯意,但也非属犯意转化。以法益的专属性而将行为对象转换排斥于犯意转化之外,是以往刑法理论回答行为对象转换问题的一种通行立场或主张。
专属法益与非专属法益的对应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但通过专属法益与非专属法益的对应而对行为对象转换作出两类处置,并不具有妥当性,因为即便专属法益在某种意义上较非专属法益更加重要,但其似乎只能说明法益侵害性的轻重有别,而与犯意转化或另起犯意这类犯罪主观活动的变化本身没有关联性。易言之,即便承认所谓专属法益,但专属法益并不因行为对象转换而形成另起犯意,从而引起数罪并罚。例如,甲出于索债目的而在某日上午将张三骗来予以非法拘禁。临近中午,甲让张三的妻子李四来顶替张三接受非法拘禁。临近傍晚,甲又让张三的儿子王五来顶替张妻李四继续接受非法拘禁。在前例中,人身活动自由是公民的专属法益,且张三、李四、王五是不同的行为对象,但只能认定甲构成一个罪即非法拘禁罪而不可能,也不必要通过另起犯意,且以数罪并罚来解答问题。于是,在张明楷教授所举的具体事例中,为何甲放弃奸淫A女而选择奸淫B,甲可成立强奸中止与强奸既遂,而甲侵入住宅后放弃抢劫名画而选择抢劫手提电脑,却不可以成立抢劫中止与抢劫既遂?这里,当名画的价值大于或远远大于手提电脑,则行为人放弃抢劫手提电脑而选择抢劫名画,那么张明楷教授是否会改变看法?实际上,在其所举的行为对象转化的四个具体事例中,前三个事例都属于不同行为对象之间同等法益侵犯的转换,即前两个事例都属于不同行为对象之间财产法益侵犯的转换,而第三个事例则属于不同行为对象之间性自主法益侵犯的转换。但第四个事例则属于不同行为对象之间不同等却依然具有包容性的法益侵犯的转换,因为枪支在对应着财产法益的同时还对应着公共安全法益。当然,提出前述疑问并不意味着本文主张应将行为对象转换统统作为另起犯意处置。在本文看来,在行为对象转换的场合,应一分为二地看待或处置问题:如果行为对象转换只引起同等法益侵犯的转换(前述第一、二、三事例),则其首先不存在另起犯意的问题,同时也不引起犯意转化的问题,因为此时的行为对象转换丝毫不影响定罪问题包括犯罪的阶段形态和罪数形态,正如行为目标转换即“故意转换”,是指行为人在实施一个构成要件行为时,有意识地把自己对一个对象进行攻击的目标设定转移到另一个目标上去的情况。例如,当行为人为了盗窃一个价值连城的铃铛而闯入他人的住所,但后来仅拿走了其他东西,则认定一个未遂的入室盗窃和一个既遂的普通盗窃还是仅仅认定单一的既遂的入室盗窃,便成了问题。于是,司法判决总是宣称,故意指向的改变是不值得注意的,因为这种案件能够被看成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差误”,而这种有意识的行为对象转换,完全是为原来的计划服务的。(20)[德]克劳斯·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王世洲译,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342-343页。所谓“不值得注意”和“为原来的计划服务”意味着同一个构成要件行为的对象转换不影响故意的认定和该构成要件行为所对应的罪名的成立,从而不发生数罪并罚的问题,即前述行为目标转换或“故意转换”所指向的个例应认定为单一的入室盗窃既遂,因为同一个构成要件行为的对象转换对构成要件本身丝毫没有形成影响,正如故意完全相同、对象变化时,由于行为性质相同且在同一构成要件之内,罪名不变,故将对象变化前后的行为作概括的整体评价而仅认定为一罪,未尝不可(尤其是对象所属的主体也完全相同时)。(21)张开骏:《犯意和对象变化的犯罪认定》,载《当代法学》2015年第3期。但如果行为对象转换所对应的是虽不同等但具包容性的法益侵犯的转换,则其所引起的实质上并非另起犯意而仍然是犯意转化的问题,因为行为对象的转换即新的行为对象的选择是发生在行为的继续发展过程中,且新行为对象所对应的法益包容了原行为对象所对应的法益。可见,认为专属法益主体转换不可能形成犯意转化的学者,其基本逻辑是:当侵犯不同主体的专属法益,则只能数罪并罚,正如聚众斗殴致一人重伤的,应以故意伤害罪论处,而同时致数人重伤的,应以数个故意伤害罪实行数罪并罚。(22)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063页。由张明楷教授的立场推论,聚众斗殴致一人死亡的,应以故意杀人罪论处,而同时致数人死亡的,应以数个故意杀人罪实行数罪并罚。而既然只能数罪并罚,便不可能形成犯意转化。但忽略的是:在同一犯罪过程中,当不同主体的专属法益之间具有包容性,行为人转换行为对象即法益主体所形成的乃是法益侵害性包容的局面,则为何不能形成犯意转化呢?除了前述A将对B的伤害故意转化为对B的兄弟C的杀害故意这一事例,还有可能发生A将对双方有仇的B的猥亵故意转化为对随后出现在现场的B的姐妹C的强奸故意,诸如此类的事例以犯意转化论处又有何不可呢?可以认为,借由专属法益而将行为对象转换排斥于犯意转化之外而论以数罪并罚,是“过度法益论”的一种体现。而“过度的法益论”所体现的是陈璇教授所指出的片面的“对象理性思维”,即法益理论的思维特点就是单纯以保护对象为关注点。(23)陈璇:《法益概念与刑事立法正当性检验》,载《比较法研究》2020年第3期。因此,在本文看来,“过度的法益论”所体现的是片面的“保护理性思维”,而片面的“保护理性思维”使得法益论忽略了手段的正当性与和比例性。这里值得指出的是,在形成犯意转化的场合,严格地讲,已经不存在“同一个构成要件”,如在出于抢劫普通财物的故意而开始实施暴力,但在发现被害人的提包内另有枪支时仅夺取了枪支的例子中,行为人开始的暴力行为是抢劫罪的构成要件行为,而随后的暴力夺取行为则是抢劫枪支罪的构成要件,但前后构成要件行为也存在包容关系,且此种包容关系可借助“法规竞合”或“法条竞合”予以描述。可见,客观中肯地辨析行为对象转换问题,是对犯意转化的更进一步深化。
在对犯意转化与另起犯意和行为对象转换予以甄别之余,为进一步澄清犯意转化这一概念,我们还有必要将犯意转化置于主客观相对应或主客观相结合之中予以一番考察。张开骏博士认为,如果心存的犯意或行为对象仅是行为人的计划或意欲,在尚未实施时就发生变化,并在新的犯意或对象情况下才实施相关行为,或者反过来,即在变化之前实施了相关行为,变化之后没有实施任何行为,都无讨论犯意或对象变化的意义,因为它们不会影响犯罪认定。理由在于,仅有意欲的犯意或对象而缺乏行为,则不存在客观违法,也就免谈主观责任。比如,A 本欲伤害他人,但在未付诸实施时即改为杀人故意并实施暴力行为。不管被害人最终是生或死,仅成立故意杀人罪一罪。尽管A曾有伤害故意,但没有在此罪过心理支配下实施行为(哪怕是预备行为),则不存在故意伤害罪的客观不法,也就没有余地讨论所谓犯意变化对犯罪认定的影响。再如,B欲杀害他人,但在未付诸实施时即改为伤害故意并实施暴力行为。不管被害人最终是生或死,仅成立故意伤害罪一罪,同样没有必要讨论所谓犯意变化对犯罪认定的影响。(24)张开骏:《犯意和对象变化的犯罪认定》,载《当代法学》2015年第3期。可见,无论是过失向故意的犯意转化,还是故意向故意的犯意转化,都是行为人的犯罪心理活动变化与外在举止活动并行或“齐头并进”的过程。易言之,犯意转化是主客观相对应或主客观相结合的犯罪变化过程,亦即犯意转化是一个动态的主客观相结合构造。
三、犯意转化的责任方案
犯意转化的责任处置是犯意转化问题的最终落脚。犯意转化的责任处置已经提出了多种解决方案。
(一)“想象竞合犯方案”的否定
对于所谓犯意转化的第一种情况,张明楷教授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应以实行行为吸收预备行为,但事实上对此还难以一概而论:一方面,抢劫预备行为严重而盗窃行为并不严重时,以后者吸收前者明显不当;另一方面,因为抢劫预备行为严重而仅以抢劫预备论处,则没有评价盗窃既遂部分,导致评价不充分。因此,对这种行为应当认定为想象竞合犯,从一重罪处罚。(25)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266页。在本文看来,运用想象竞合犯理论来处置学者所谓犯意转化的第一种情况,并不合适,因为正如张明楷教授指出,想象竞合犯也称想象的数罪、观念的竞合、一行为数法,是指一个行为触犯了数个罪名的情况。(26)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482页。显然,在其所谓犯意转化的第一种情况中,由于先后存在着抢劫和盗窃这两种不同的犯意,且此两个不同的犯意分别对应或支配不同的行为即抢劫行为(抢劫预备行为也是抢劫行为)和盗窃行为,故张明楷教授对所谓犯意转化的第一种情况按照想象竞合犯论处的最终主张,明显与想象竞合犯的行为数量特征即“一个行为”不相符合。不仅如此,按照想象竞合犯从一重罪处罚却走向了张明楷教授所反对的“评价不充分”。而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当张明楷教授在所举例子中强调,抢劫预备行为严重而盗窃行为并不严重时以后者吸收前者明显不当,其有坚持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之意味,但问题是:在犯意转化的场合,行为人的罪责轻重及其再犯危险大小应在一种动态性之中向前考量且应以行为人后来的主观内容和实际危害为考察材料,即应将犯意转化后的行为人作为究责对象,唯有如此,处罚才因具有事实针对性而具有正当性和有效性。可见,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和刑罚个别化原则并不支持犯意转化的“想象竞合犯方案”。而按照张明楷教授的主张,在犯意转化的场合,如果还以转化前的故意与行为来定性犯意转化的个案,则犯意转化的提法便失去了实际意义。
(二)“并行评价方案”的否定
“并行评价方案”是在逐一评判其他方案的基础上所提出的。(27)张开骏:《犯意和对象变化的犯罪认定》,载《当代法学》2015年第3期。这里,被刘宪权教授用来引出讨论的是如下三种具体事例:①甲在故意伤害他人的过程中,改变犯意杀死他人;②乙在抢夺他人装满现金的提包的过程中遭遇抵抗,进而对他人使用暴力强取财物;③丙在杀害他人的过程中改为伤害故意,继而施加伤害,没有致人死亡即停止。我国台湾地区学者郑健才认为,犯意升高者,从新意(变更后的意思);犯意降低者,从旧意(变更前的意思)。刘宪权教授认为,例1和例2对行为人只需以“高位犯罪”的既遂论处,例3以 “高位犯罪”的中止认定,但将 “低位犯罪”作为犯罪中止的 “造成损害”因素加以考虑。(28)刘宪权:《故意犯罪停止形态相关理论辨正》,载《中国法学》2010 年第 1 期。前述主张的共同点是对行为人一律认定为犯意高的罪名一罪。于是,甲、乙应分别定为故意杀人罪和抢劫罪,丙仍认定为故意杀人罪,但其不妥之处在于:以犯意的高低论罪,缺乏法理依据;在犯意降低的场合,先前的高犯意之罪有可能成立中止,而后来的低犯意之罪通常是既遂,此时仍以高犯意的中止犯定罪,存在罪刑失衡之虞。(29)张开骏:《犯意和对象变化的犯罪认定》,载《当代法学》2015年第3期。对于犯意转化,另有学者主张一律以变化后的新犯意认定为一罪,(30)范德繁:《转化犯的新视野——事实转化的展开》,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3 年第 1 期。但这一主张也有不妥:忽视了变化前的犯意和犯行,特别是例3犯意降低情形也完全可能是前罪成立中止、后罪成立未遂,此时仍以低犯意的轻罪认定也会造成罪刑失衡。于是,学者提出了带有折中色彩的方案。具言之,就上述三个例子而言,在行为人针对同一对象的犯罪过程中,存在前后两种犯意,犯意变化前后均实施了相应行为,而不同犯意支配下的两个行为的性质不同,即均具有客观不法和主观责任,故理应进行单独的刑法评价,即成立两罪且应实行并罚。这样评价和处断既是对罪行危害性的充分评价,体现刑法的法益保护机能和罪刑均衡原则,对于行为人也不存在过分苛责和侵犯人权的问题。至于变化之前的犯罪性质,应根据所处的行为阶段和犯意变化原因而定。由此,甲成立故意伤害罪(中止)和故意杀人罪(既遂),乙成立抢夺罪(未遂)与抢劫罪(既遂),丙成立故意杀人罪(中止)和故意伤害罪(既遂),都实行并罚。(31)张开骏:《犯意和对象变化的犯罪认定》,载《当代法学》2015年第3期。此即张开骏博士的“并行评价方案”。
张开骏博士认为,“并行评价方案”具有很大的合理性。其一,它是在尊重犯罪事实基础上的刑法充分评价,即对变化前后之行为的更大的否定性评价和对行为人更大的非难谴责,故其刑法的法益保护机能、社会秩序维持机能以及刑法规范效力的确证与刑法对社会公众的行为规范指引,都更加积极和有效。其二,在犯意和对象变化情形中,对变化前后的犯意和犯行进行独立的刑法评价,即分别认定犯罪且实行并罚,这样的 “并行评价”的思考方式和操作办法具有直观性和便利性,且避免了 “犯意转化”“另起犯意”“对象转换”等概念术语纠缠带来的理论困扰。其三,“并行评价”积极的一面是,在刑事和解不断被推广应用,被害人权益越来越受到重视的时代背景下,其为司法机关增加了督促被告人寻求谅解、积极赔偿以实现刑事和解的筹码,从而为保护被害人权益争取了主动权。其四,英美法系国家或地区的刑事案件动辄数项、十几乃至数十项罪名的指控,虽与大陆法系可能存在思维方式差异,但其理论思维和司法操作显然不是空穴来风、随心所欲,其犯罪评价和认定的合理性应被我们认真对待和借鉴。总之,“并行评价”具有刑事理性,能够指导和统一司法实践。(32)张开骏:《犯意和对象变化的犯罪认定》,载《当代法学》2015年第3期。对“并行评价方案”的合理性,该学者还作了进一步的补充或强调。其一,以数罪进行评价和处断,乃是针对前后两种犯意及其支配下的性质不同的两种行为,分别进行独立评价,而不是对此犯意和行为评价后,再纳入到彼犯意和行为中评价一次,故不存在重复评价的问题。其二,前后两个行为侵害的法益即便存在包容关系,也并非完全相同,以一罪论处恰是没有充分评价,这是一罪论的弊端。其三,在犯意升高的场合,以较重的后罪吸收前罪,即以新犯意的后罪定罪处罚还算“自然”,但当犯意降低时,无论是比较前后罪之轻重,还是最后以重的罪认定,都会显得不“自然”。而唯有单独评价,分别定罪且实行并罚,才既符合法理,也更加妥当、自然。其四,刑事司法不应依赖缺乏法理和有失公正的简便,应接纳依据法理和有利公正的“繁琐”。(33)张开骏:《犯意和对象变化的犯罪认定》,载《当代法学》2015年第3期。如何看待张开骏博士所提出的“并行评价方案”呢?
在其论断中,所谓更大的否定性评价和更大的非难谴责,都是其“刑法充分评价”的一种转述。“刑法充分评价”当然能够带来诸如更加积极有效的法益保护机能和刑法规范效力确证等效果,但“并行评价方案”是否在犯意转化的场合造成了“评价过度”而在实践效果上适得其反或至少打了折扣?在本文看来,答案是肯定的。张开骏博士所谓“并行评价方案”能够避免“犯意转化”“另起犯意”“对象转换”等概念术语纠缠带来的理论困扰而具有司法操作的直观性和便利性,其难免有回避问题甚或混淆问题之嫌,因为犯意转化截然有别于另起犯意,而行为对象转换虽不必然但可能是犯意转化。其主张“并行评价”能为司法机关增加督促被告人寻求谅解、积极赔偿以实现刑事和解的筹码,从而为保护被害人权益争取了主动权,如果刑法评价本身是不客观和不公道的,则通过督促刑事和解以增强被害人的权益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又何在呢?而在其进一步补充或强调的所谓合理性中,所谓“并行评价方案”不存在重复评价的问题,实有“欲盖弥彰”之嫌,因为既然是转化了,则被转化者消弭于转化者之中,故作为我们评价材料的应是转化后的犯意及其所支配的行为。由此,对被转化者还不依不饶地“并行评价”难道不是“重复评价”吗?张开骏博士同样认为,所谓一罪论没有充分评价,但“并行评价”难道不是“重复评价”或“叠加评价”,从而是“过度评价”吗?至于所谓刑事司法不应依赖缺乏法理和有失公正的简便而应接纳依据法理和有利公正的“繁琐”,其言本身无错,但“并行评价”这一“繁琐”符合法理和有利公正吗?最终,“并行评价方案”貌似最为合理可取,但其存在的问题甚至多于其他方案。
(三)“从新意方案”的再主张
对犯意转化,最终如何究责呢?“从新意方案”能够得到从刑法基本法理到刑法基本原则以及运动刑法观的系统性说明或支撑。
首先,“从新意方案”符合刑法基本法理。犯意转化责任的“并行评价方案”提出者,着意强调其方案符合法理,甚至当符合法理的情况下,其方案即使“繁琐”也不要紧或有必要。这里,张开骏博士所指涉的所谓法理到底是什么呢?从其所谓唯有单独评价,分别定罪且实行并罚,才既符合法理,也更加妥当、自然,我们可知张开骏博士的所谓法理不过是数罪并罚的刑法理论而已。在本文看来,刑法法理本应符合实际问题的事实真相,即刑法法理本应是实际问题的事实真相的观念反映,故犯意转化的责任方案只有在对接实际问题的事实真相中才有符合刑法法理可言。作为刑法生活事实中的一个实际问题,犯意转化的真相就藏于“转化”二字之中。“转化”意味着事物发展前后之间内在的承继与演进,而非某种“既定”或“既成”,亦非不同事项在时空上的“并起”,故“想象竞合犯方案”不符合犯意转化的事实真相,因为“同时符合”意味着该方案没有辨识或辨识不了犯意转化的事实真相,同时“并行评价方案”也不或更不符合犯意转化的事实真相,因为其所主张的“独立评价,而数罪并罚”更是通过“先后符合”将犯意转化混同于另起犯意,从而将一罪一罚混同于数罪并罚。由“转化”所造成的最终的一个犯意支配最终的一个行为事实,意味着犯意转化只对应着一个刑法事实,从而只对应一个犯罪构成,最终对应一罪一罚。这就是犯意转化责任方案应遵循的基本刑法法理。但在以往的责任方案中,只有“从新意方案”遵循了前述由刑法事实决定犯罪构成,进而由犯罪构成来说明罪名和罪数的法理,但该方案却没有得到深入论证;而该方案之所以没有得到深入论证,或许与“从新意”的当然性认知有关。之所以“重复评价”或“叠加评价”即“过度评价”应予避免,是因为在犯意升高的场合,我们应该关注的只是后来的主观恶性更深和再犯危险性更大的行为人,而非将先前的主观恶性较浅和再犯危险性较小的行为人与后来的主观恶性更深和再犯危险性更大的行为人予以“重复关注”。此处,“重复关注”夸大了“恶人之恶”;而在犯意降低的场合,我们应该关注的只是后来的主观恶性变小和再犯危险性变小的行为人,而非将先前的主观恶性较深和再犯危险性较大的行为人与后来的主观恶性变小和再犯危险性变小的行为人予以“重复关注”。此处,“重复关注”忽略了“恶性变轻”的事实。由此可见,法理、事理和情理是相辅相成和相互渗透的,而“从新意方案”至少又是较好地体现了法理、事理和情理的相辅相成和相互渗透。
其次,“从新意方案”符合刑法基本原则。这里所说的刑法基本原则又首先是指刑法责任主义原则。具言之,在“犯意降低”这样的犯意转化的场合,“重犯意”通常是对应着预备行为阶段,而“轻犯意”通常是对应着实行行为阶段。虽然对犯罪的刑法评价是就整个行为过程所作出的评价,但国外“处罚预备犯是例外”的立法例已经表明刑法评价的重点是犯罪的实行行为,因为相比之下,能够较深体现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与再犯危险性的是实行行为而非预备行为。因此,对于“犯意降低者”仍应“从新意”,是刑法责任主义原则的题中之义。刑法责任主义暗含着一种无声的强调,即“行为之时”的主观罪过以及行为人的再犯危险性是刑事非难的对象,但“行为之时”是由“预备行为之时”和“实行行为之时”所构成,而在犯意转化的场合,又只能在“预备行为之时”和“实行行为之时”的主观罪过以及行为人的再犯危险性这两者之间选取其一作为犯意转化场合定罪量刑的主观事实基础。由于是“新意”而非“旧意”支配了在时空上接近刑事非难的不法行为,即“实行行为之时”相较于“预备行为之时”更具有体现行为人主观恶性及其再犯危险性的“现时性”,故从刑事责难的“报应性”和“预防性”出发,应选取行为人“实行行为之时”的主观罪过及其再犯危险性作为评价材料,即对于“犯意降低者”,仍应“从新意”,而“从新意”则是刑法责任主义原则的充分体现。至于在“犯意升高者”的场合,“从新意”更是刑法责任主义原则的直接体现。
再次,“从新意方案”另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和刑罚个别化原则。正如所举的具体事例所印证,犯意转化的第一种情况也体现着转化前后两个行为所侵犯的法益具有包容关系,正如抢劫转化为盗窃。接下来的重要问题是,在犯意转化的场合,如何最终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对于“犯意升高者,从新意”这一方案或主张,应无疑问,因为“犯意升高者”对应着行为人最终的主观恶性和再犯危险性,故这一方案,无论是刑事处罚的正当性,还是刑事处罚的目的性和有效性,其都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但对于“犯意降低者,从旧意”这一方案,本文予以否定,即“犯意降低者,仍应从新意”,理由仍然在于:在犯意转化的场合,行为人的罪责轻重及其再犯危险性大小应在一种动态性之中向前考量且应以行为人后来的主观内容和实际危害为考察材料,即应将犯意转化后的行为人作为究责对象,唯此,处罚才因具有事实针对性而具有正当性和有效性。实际上,在犯意转化的场合,无论是“犯意升高者”,还是“犯意降低者”,正如行为人的罪责轻重及其再犯危险性大小应在一种动态性之中向前考量且应以行为人后来的主观内容和实际危害为考察材料,即应将犯意转化后的行为人作为究责对象,只有“从新意”,才能真正地体现或落实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和刑罚个别化原则。正如在学者所举的丙本欲杀死他人的例子中,当行为人虽然没有致死被害人但其却以特别残忍手段造成被害人严重残疾的,依法《刑法》第234条可判死刑,而若按照故意杀人罪的中止犯处理,对行为人的量刑只能在“十年之下”,因为按照《刑法》第24条的规定,对于中止犯,造成损害的,“应当”减轻处罚。这里,“犯意降低者,从旧意,明显背离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也同时背离了刑罚个别化原则。
恩格斯曾指出:“蔑视社会秩序最明显、最极端的表现就是犯罪。”(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16页。在犯意转化的场合,行为人对社会秩序的蔑视程度只是在转化后而非转化前才具有最终的形成性和真实性,故“从新意方案”从刑法责任主义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和刑罚个别化原则那里获得的支撑又可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论断那里寻求一种加固。而雅各布斯又曾指出,正是责任与目的的联系给刑罚和刑罚份量提供了本质意义,即其决定着刑罚的归属和归属的份量。(35)[德]格吕恩特·雅各布斯:《行为 责任 刑法——机能性描述》,冯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页。当转化后的新犯意才对应着既成和真实的责任,从而与刑罚的目的特别是特殊预防的目的才能形成真实的联系,则“从新意方案”对刑法责任主义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和刑罚个别化原则的契合性便可从“刑罚的归属和归属的份量”中得到一种映现。
最后,“从新意方案”符合运动刑法观。运动刑法观是日本著名刑法学家团藤重光将万物流动原理引入刑法学所形成的一种刑法观,即“犯罪和刑罚的关系也决不是静止的、固定不变的现象”。(36)马克昌主编:《近代西方刑法学说史略》,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版,第353页。由于“新意”及其所支配的行为是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客观危害及其再犯危险性的当下说明,且“当下”又是“过往”的演变和沉淀,故“从新意”在符合动态刑法观之中体现或实现着刑事究责因具有针对性而具有的正当性和有效性。相比之下,对犯意转化的“犯意降低者”却“从旧意”即“从旧意方案”,总免不了“算旧账”的气量狭小而有违刑法的谦抑精神。而对犯意转化的“并行评价方案”也因抓住“旧意”不放而同样有违刑法的谦抑精神。易言之,在犯意转化的场合,我们应“既往不咎”或“不咎旧意”而“只咎新意”。实际上,无论是犯意转化责任处置的“从旧意方案”,还是其“并行评价方案”,都体现着一种“沉湎过去”的刑法思维,而这种“沉湎过去”的刑法思维其实是一种僵滞思维,从而背反着运动刑法观。而在犯意转化的场合,无论是立于主观层面的“行为人之恶”,还是立于客观层面的“行为之恶”,无论是“从旧意方案”抑或变相的“从旧意方案”,还是实为数罪并罚的“并行评价方案”,都体现一种“走不出过去”的保守刑法思维,而此刑法思维正是运动刑法观所要扬弃的。可以这么认为,无论是“从旧意方案”抑或变相的“从旧意方案”,还是实为数罪并罚的“并行评价方案”,其都忽略了犯意转化意味着行为人在时空延长线的人格塑变,(37)马荣春:《罪刑关系论》,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年版,第80-81页。而对犯意转化的责任处置应采用一种发展变化的眼光来看待犯罪人。
此外,还需要强调的是,“从新意方案”对于犯意转化的“犯意降低者”有着“犯意自觉降低”的无声要求,即当适用“从新意方案”时,犯意降低是出于犯罪中止所对应的一种“自觉”而非“无奈”,因为出于“无奈”的犯意改变只有犯意转化之表或犯意转化之名而无犯意转化之里或犯意转化之实,故其不属于犯意转化。如当行为人在实施强奸过程中觉得自己已醉酒而陷入“性无能”,便由强奸故意转变为强制猥亵故意,且在后一故意的支配下对被害人实施强吻、抠摸阴部或搓捏乳房等行为。相反,如当行为人在实施强奸过程中觉得强奸得逞会造成被害人日后难以嫁人或无法面对家人,便由强奸故意转变为强制猥亵故意,且在后一故意的支配下对被害人实施强吻、抠摸阴部或搓捏乳房等行为,则应视为犯意转化而适用“从新意方案”。“从新意方案”对“犯意降低者”的“自觉性要求”,进一步体现了该责任方案对刑法责任主义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和刑罚个别化原则的体现或信守。
结 语
犯意转化是故意认定和罪数认定中的一个实际问题。继犯意转化的基本类型和犯意转化与另起犯意及其与行为对象转换的甄别,我们最终可得:犯意转化,是指在同一犯罪过程中,行为人将对同一行为对象的此犯意转化为在法益指向上具有同质性或包容性的彼犯意,或将对某一行为对象的此犯意在另一行为对象上转化为法益指向具有包容性的彼犯意的犯罪主观活动变化。进一步地,犯意转化可从犯意的基本内容和发生的具体空间而作出基本类型和更加细致的划分。当采用时空同一性和法益同质(包容)性相结合的判断标准,则犯意转化与另起犯意可谓泾渭分明,而行为对象转换虽未必是但可能是犯意转化,而是否专属法益并不说明行为对象转换是否属于另起犯意。最终,在犯意转化的场合,无论是“犯意升高者”,还是“犯意降低者”,采用犯意转化责任的“从新意方案”,不仅符合刑法基本法理、能够得到从刑法责任主义原则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和刑罚个别化原则的高度支撑,而且能够得到运动刑法观的观念提升。特别是在过失向故意的犯意转化的场合,“从新意方案”更显示其合理性与可行性,而这一点是所有其他解决方案所忽略的。但是,出于“无奈”的犯意改变不属于犯意转化,故不适用“从新意方案”。
由于转化型抢劫罪的立法规定(《刑法》第269条)、刑讯逼供致人伤残、死亡按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从重处罚的规定(《刑法》第247条)和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死亡以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处罚的规定(《刑法》第292条),都事实地对应着犯意转化,且形成着法益侵害性包容,故犯意转化是一个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都相当重要的理论课题而应予更加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