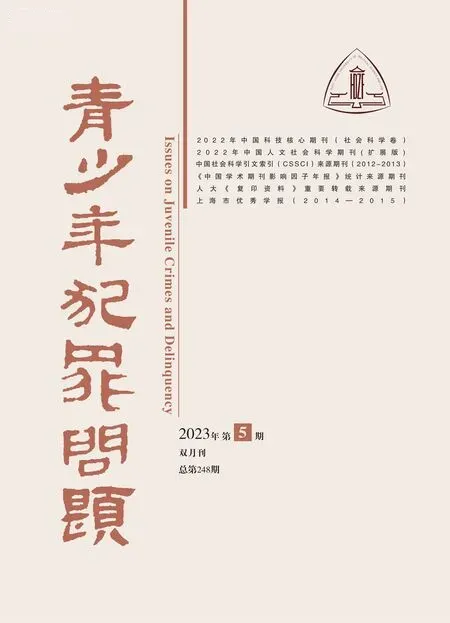论刑事责任年龄的法理依据
熊谋林
引 言
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研究和思考从未间断,学术界已积累了不少成果。就是否应当降低至12或13岁所实施的严重犯罪问题,至少是讨论了30年的理论和社会热点。(1)参见赵秉志:《我国刑法中的最低责任年龄不应降低》,载《政治与法律》1988年第3期;赵秉志:《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责任问题研究》,载《山东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01年第2期;张建军:《我国刑事责任年龄之检视》,载《政法学刊》2007年第4期;陈波:《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的根据与适用》,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20年第3期;唐琳:《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不是应对“坏孩子”的明智之举》,载《犯罪与改造研究》2020年第8期;李晓莹:《关于降低刑事责任年龄问题的思考》,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虽然《刑法》第17条有所规定,《刑法修正案(十一)》也将刑事责任年龄降低至12周岁,但如何评价有关刑事责任年龄的起点和分段问题难以取得共识。学界除了对民国及各国刑事责任年龄的参考借鉴外,至今未给出中国刑事责任年龄的理论依据。这场辩论的核心,主要围绕刑事责任年龄的功能,刑事入罪和定罪的判断标准,刑事责任的立法和司法等展开。要回答这些问题,不仅需要充分理解刑法典和刑事司法对刑事责任年龄的制约和作用,而且还需要从国际国内法律层面理解少年司法的基本原则和法理依据。
然而,由于对刑事责任年龄的法理依据缺乏深入系统论证,刑法学界对此很难有力回应,中国是否应当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在此背景下,《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顺应舆论呼声和热点关注而将刑事责任年龄从14周岁降低到12周岁,又用“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的实体和程序要件予以严格限制。应当承认,在《刑法修正案(十一)》所规定的条件下,12-14周岁的未成年人极其罕见地会被追究刑事责任。但这不应当视为刑法本身的实体限制,而是“最高人民检察院不予核准”的诉讼程序控制。(2)参见蒋安杰:《追诉低龄未成年人为何要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胡云腾大法官如是详解》,载搜狐网2021年1月3日,https://www.sohu.com/a/442199854_162758。对于地方司法来说,社会舆论长期处于强势地位,也不排除12-14周岁的未成年人在将来会因成为众矢之的而被核准追诉。问题是,中国刑法和刑事司法实践如何避免“个案”成为常态,否则刑法学家关于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所引发的受刑能力和刑罚效果担忧便成为了现实。(3)参见赵秉志:《我国刑法中的最低责任年龄不应降低》,载《政治与法律》1988年第3期。
刑事责任年龄的法理依据依然缺乏系统研究,当前关于少年司法的国内法和国际法理上几无涉及便是最好例证。也正因如此,除了某些热点案例引发的事实性关注以外,无论是刑法学界还是青少年法研究专家均不能有效回答:中国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刑事责任年龄体系?就全球而言,国内学术界注意到刑事责任年龄的早期现状,尤其注意到少数国家有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倡议和实践,故部分人大代表以此为契机呼吁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详见后文)。然而,鲜有研究从比较法层面论证年龄背后的法理依据和对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后的反馈意见。事实上,倡议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代表,对国际刑事责任年龄的标准和规则存在明显误读,更对国内法的配套体系缺乏深入思考。正因如此,《刑法修正案(十一)》基本上是,惩罚和威吓的感性认知多于关爱和矫治的理性认识。倡议者不仅未能认识到国际法层面升高刑事责任年龄的大趋势,也未能认识到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配套法律基础和矫正措施的不足。例如,丹麦在2010年将刑事责任年龄从15周岁降低到14周岁,但2012年又重新提高到15周岁。(4)Committee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Fifty-sixth Session. Consideration of reports submitted by States parties under article 44 of the Convention, April 4 2011, CRC/C/DNK/CO/4, at https://www2.ohchr.org/english/bodies/crc/docs/CRC.C.DNK.CO.4_en--.pdf; Child Rights International Network. Minimum Ages of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in Europe, at https://archive.crin.org/en/home/ages/europe.html.日本刑法的刑事责任年龄虽是14周岁,但其家事法院裁定移送刑事起诉前不能当然认为犯罪,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2010年明确建议日本提高刑事责任年龄到16周岁。(5)Committee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Fifty-fourth Session. Consideration of reports submitted by States parties under article 44 of the Convention Concluding Observations: Japan, 20 June 2010, at https://www2.ohchr.org/english/bodies/crc/docs/co/CRC.--C.JPN.CO.3.pdf.巴拿马在1999年《青少年刑事责任年龄特别法案》中(6)DE LA LEY 40 DE 26 DE AGOSTO DE 1999, DEL RÉGIMEN ESPECIAL DE RESPONSABILIDAD PENAL PARA LA ADOLESCENCIA, at https://www.sijusa.com/wp-content/uploads/2020/05/tu_l_40_1999.pdf.将刑事责任年龄从14周岁降低到12周岁。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评价为“不正当的紧迫关切,导致儿童司法条款的削弱,违背了《儿童权利公约》”,故建议巴拿马提高刑事责任年龄。(7)Committee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Fifty-eighth Session. Consideration of reports submitted by States parties under article 44 of the Convention,Concluding observations:Panama,21 December 2011, at https://www.refworld.org/pdfid/4efc96f12.pdf.
有鉴于此,本文在总结最新研究的基础上,系统梳理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国际国内法理依据,以期更加科学地建立起未成年人刑事责任体系。本文的重点不是比较刑事责任年龄的具体规定,而是从国际法和国内法两个层面来看刑事责任年龄相关的基本原则和法律措施。这些有关未成年人是否构成犯罪、采取何种矫治和处罚措施、如何展开诉讼程序的诸多内容,事实上可以直接解读为观察未成年人入罪入刑的国际国内法的法理依据。笔者相信,只有从国际和国内法两个层面,充分认识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法理依据,才有可能为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入罪入刑年龄提供清晰的理论参考。
一、未成年人犯罪及刑事责任年龄研究的文献综述
(一)文献总评
截止到本文展开文献综述之日(2023年4月17日),笔者以“刑事责任年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为搜索关键词,分别在中国知网检索出学术期刊1353、756篇论文。虽然从数量上看,刑事责任年龄的范畴远大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但从内容看,大量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论文主要围绕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展开(如图1所示)。

图1 中国知网文献数量及检索主题词共现矩阵(截止到2023年4月17日)
就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研究而言,既有研究主要呈现出七个维度的特征。第一,针对未成年人本身展开研究,研究主体集中于未成年人、罪错未成年人、青少年犯罪、犯罪主体、未成年犯罪。第二,研究刑事责任年龄本身,如恶意补足年龄、最低年龄、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低龄化等。第三,围绕刑事责任展开研究,如责任能力、刑事责任。第四,关注于刑法,主题有刑事立法、刑法典、我国刑法、刑法修正案等。第五,从刑法理论角度研究未成年人犯罪,如刑法理论、社会危害性、严重不良行为、犯罪行为、构成要件等。第六,从刑事政策和刑事司法角度研究未成年人犯罪,如刑事政策、少年司法、工读学校等。第七,是针对个罪的研究,如故意杀人罪和抢劫罪。
从近年的趋势来看,刑事责任年龄一直是未成年人犯罪研究的学术重心,尤其是《修正案(十一)》前后呈猛涨期。有关未成年人犯罪的研究在2021年达到顶峰,最近四年集中在刑事责任年龄、情节恶劣、刑法修正案三个主题中。未成年人犯罪研究紧跟立法,这反映了学者们高度的问题和理论意识,但2022年与2021年相比也反映出理论热度降低。从这个角度讲,未成年人犯罪作为法学关注的显学,其背后的学术理论依据是否能超越法律规定本身还尚待疑问。抑或说,未成年人犯罪作为刑法保护和犯罪控制的焦点话题,如果没有《修正案(十一)》,是否依然能成为学术关注的问题?
总体而言,有关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研究集中在刑事立法和社会热点案例等表层内容,刑事责任年龄后的法理、哲学、历史依据等更深层次讨论极为欠缺。从目前中国知网的搜索情况来看,鲜有研究探索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法理依据。笔者以“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和“法理”为组合关键词,在中国知网没有搜索到关于法理的研究文献。以“刑事责任年龄”和“法理”为组合关键词,只搜索出李进平、刘红关于完善刑事责任年龄上限的论文。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虽提出基于本国国情、借鉴国外立法,但内容却是建议设定老年人犯罪的最大年龄。(8)李进平、刘红:《刑事责任年龄上限的法理分析》,载《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因此,从刑事立法和法学理论来说,只有重视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年龄的最基本、基础的法理问题,才能在理论和学术研究上以不变应万变。遗憾的是,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和努力还显然不够。
(2)相关法理问题探讨
鉴于未成年人犯罪及刑事责任年龄的法理探讨极为稀缺,笔者用“未成年人”和“法理”为共同关键词,在中国知网搜索出22篇学术期刊文章、3篇学位论文。就学术期刊来讲,未成年人犯罪有关的理论探讨约占2/3,集中在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针对规范问题展开讨论。徐建针对《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法律责任,从法律责任的特殊性、法律责任的多种规定、不同主体法律责任的专门规定、未成年人本人法律责任四个角度介绍了未成年人法律责任的问题。(9)参见徐建:《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法律责任——〈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法理简介(三)》,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00年第1期。万红从法理角度,论述了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国家干预、儿童独立人权、儿童最大利益的三重转变,并提出成立专门机构、统一案件职责、明析处置措施、完善配套措施等四个方面的建议。(10)参见万红:《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法理分析与优化探究》,载《江西警察学院学报》2022年第3期。姚建龙针对浙江省慈溪市出台的《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人员信息公开实施办法》论证了公开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人信息的合理性。(11)参见姚建龙、刘昊:《“梅根法案”的中国实践:争议与法理——以慈溪市〈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员信息公开实施办法〉为分析视角》,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17年第2期。
第二,从宏观刑事司法制度和法律规制方面探讨。邓喜莲基于《修正案(十一)》从刑事责任治理和制度完善角度,提出“预防为主,惩罚为辅”的理念,并建立阶梯式的预防矫治措施。(12)参见邓喜莲:《未成年人刑事责任治理与制度完善的法理思考》,载《社会科学家》2021年第4期。
第三,针对未成年犯罪具体制度的法理分析。黄京平等讨论了暂缓起诉的法理基础,(13)参见黄京平、刘中发、张枚:《暂缓起诉的法理基础与制度构建——兼论对犯罪的未成年人适用暂缓起诉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郝占辉、陈慈俭分析了犯罪档案记录封存制度的合理性,(14)参见郝占辉:《未成年人犯罪档案记录封存制度的法理解读》,载《兰台世界》2012年第35期;陈慈俭:《关于未成年人刑事污点消灭制度的法理分析》,载《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自正法、万红针对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实施现状论证了相关完善措施。(15)参见自正法:《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法理基础与规范逻辑》,载《内蒙古社会科学》2021年第2期;万红:《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法理分析与优化探究》,载《江西警察学院学报》2022年第3期。肖建国围绕上海创立的“缓处考察、诉前考察、社会服务令”等犯罪未成年人考察制度,呼吁建立全国性的制度。(16)参见肖建国:《违法犯罪未成年人考察制度的法理审视》,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06年第5期。
第四,围绕刑法规定,对具体要件要素展开法理分析。但整体上来看,目前围绕刑法规定的法理解读极其稀少,这凸显了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问题法理研究的重要性。中国知网的搜索结果显示,只有李永升、安军宇从刑法学角度论证“情节恶劣”属于客观处罚条件,包含积极要件和消极要件两个部分。(17)参见李永升、安军宇:《低龄未成年人犯罪“情节恶劣”的法理探寻》,载《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22年第4期。
总体来看,有关未成年人犯罪的法理探讨,集中于具体的刑法制度和理论的法规范解读。法律背后的理论研究虽然比较充足,但依然呈现出围绕现行刑法和刑事理念的探讨,鲜有研究在刑法、刑事司法、刑事政策之外来论证未成年人犯罪和预防的法理。这也从侧面论证了,为什么理论界无法为未成年人犯罪防控体系提供良好的制度设计和学术贡献。
(三)关于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学术论争
关于降低刑事责任年龄问题,虽然有少部分论文对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持肯定态度,但持反对或批评态度的学者并非个案。例如,《青少年犯罪问题》编辑部曾明确以“刑事责任年龄下限不宜降低”发表卷首语。(18)参见《青少年犯罪问题》编辑部:《刑事责任年龄下限不宜降低》,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17年第2期。肯定派的理由基本与人大代表的建议相同。王登辉认为,“反对降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观点显得偏执”,理由是:任何人应当对自己的错误行为承担一定的不利后果,被害人比加害人更值得保护,当前12-14周岁的人的辨认和控制能力不低于1979年已满14周岁的人。(19)参见王登辉:《降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基本问题研究》,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20年第4期。王恩海基于收容教养制度名存实亡的现实情况,旗帜鲜明地提出“应当毫不犹豫降低刑事责任年龄”。(20)参见王恩海:《应毫不犹豫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20年第4期。反对派对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正当性根据和刑罚效果提出疑问。林清红认为,“刑罚对14周岁以下的青少年不具有多大效用,对其成长极为不利,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起点不利于保障刑法的稳定性和统一性”。(21)林清红:《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起点不宜降低》,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16年第1期。李伯毅认为,“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至12岁以下缺乏理性基础、正当性根据存在疑问,只是单纯回应报复需求的工具,对遏制犯罪并无显著作用”。(22)李伯毅:《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限度及理由》,载《南海法学》2020年第6期。余敏、何缓认为,“儿童无罪责,欠缺入罪正当性”是“刑罚儿童无效果,违背刑法谦抑性”“有违个体社会化规律”“不符合历史发展趋势和国际立法形式”。(23)余敏、何缓:《对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起点的商榷》,载《中国检察官》2018年第8期。刘俊杰认为,“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与世界各国的立法现状及趋势相悖,我国未建立完善的少年司法制度,反而应当适当提高刑事责任年龄起点”。(24)刘俊杰:《论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起点的不可行性》,载《法学杂志》2020年第7期。邓君韬认为,“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与责任体系和犯罪圈相违背,应当激活收容教育与工读教育机制”。(25)邓君韬:《年龄与认知:“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引发的思考》,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20年第4期。
2021年11月,《民主与法制》整理了刑事责任年龄是否应当下调的讨论专稿。在这份稿件中,罗翔秉承其2019年的观点,不仅主张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甚至主张取消刑事责任年龄的限制,但曲新久和刘艳红持坚定的反对和批判态度。罗翔认为,“刑法无法改造人性,只能遏制邪恶”,所以“对于故意杀人这种重罪,任何年龄阶段的人都应当负刑事责任”,民法修改“满足了社会的实际需要,刑法也不能固守法律的逻辑命题”。(26)宋韬:《胡云腾、曲新久、刘艳红、罗翔:关于降低刑事责任年龄问题的讨论》,载《民主与法制》2021年第43期;厚大法考:《是孩童还是罪犯?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道路选择——厚大罗翔老师》,载百家号2019年5月13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33414076379167245&wfr=spider&for=pc。曲新久认为《刑法修正案(十一)》主要是立法者“为了回应舆论关切而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这“破坏了刑法的刚性”。(27)宋韬:《胡云腾、曲新久、刘艳红、罗翔:关于降低刑事责任年龄问题的讨论》,载《民主与法制》2021年第43期。刘艳红则认为,“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不利于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理由是:“以民法思维代换刑法逻辑,是对刑事责任年龄制度背后法理的根本性误解”,“民法下调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未成年人的年龄和刑法不应下调最低刑事责任年龄标准最终殊途同归,即皆从各自的角度实现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人本思想”。(28)宋韬:《胡云腾、曲新久、刘艳红、罗翔:关于降低刑事责任年龄问题的讨论》,载《民主与法制》2021年第43期;刘艳红:《人性民法与物性刑法的融合发展》,载《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2022年4月,上海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所长姚建龙研究员也旗帜鲜明反对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参与交流的专家《中国法学》白岫云编审与中国社科院大学林维教授也基本对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持反对态度,批评《刑法修正案(十一)》过于简单地迎合舆情民意,欠缺法律人的理性、慎重,没有专业全面的实证调研就仓促立法。(29)裘欣璐:“刑司名家大讲坛‘为什么必须反对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以及为什么反对无效——对中国少年法学研究的初步检讨’讲座顺利举行”,载上海政法学院刑事司法学院纪检监察学院2022年4月17日,https://www.shupl.edu.cn/xssfxy/—2022/0417/c110a108671/page.htm。
二、刑事责任年龄的国际依据
(一)《北京规则》
《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是专门针对少年刑事司法的第一个国际规则,也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以中国首都命名的联合国规则。这对于刚刚结束“文革”的新中国而言,这份规则的国际影响和国际法意义深深影响了国际刑事司法。之所以以《北京规则》简称,原因在于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下属的常设组织——犯罪预防与控制委员会组织起草的初稿,于1984年5月14-18日在北京召开的区际筹备会议上正式定稿。(30)See Department of Public Information, New York. The Beijing Rules: United Nations Standard Minimum Rules for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venile Justice. 12 Police Stud. 82 (1989).尽管《北京规则》本身并没有给出刑事责任年龄标准,但北京规则作为全球少年最低司法限度标准,至少有三点与青少年刑事责任年龄相关的法理值得重视。
第一,以“心理、精神、智力成熟度”所代表的责任意义为核心,会员国自主规定的刑事责任年龄“不应太低”。《北京规则》第4条专门规定,“在承认少年负刑事责任的年龄这一概念的法律制度中,该年龄的起点不应规定得太低,应考虑到情绪和心智成熟的实际情况”。(31)《北京规则》的中文版本为“应考虑到情绪和心智成熟的实际情况”,但这个翻译在专业术语表达上有问题。英文表达“Bearing in mind the facts of emotional, mental and intellectual maturity”,最准确的表达应当是“应考虑情感、精神和智力的成熟度的实际情况”。按照本规则说明中所解释的法理,关于刑事责任年龄要考虑的两个因素,孩子本人是否能辨别和理解行为的反社会责任后果,越轨和犯罪行为的法律责任与其他社会权利和责任密切有关,如婚姻状况和法定成年等。同时,根据说明,“如果将刑事责任的年龄规定得太低或根本没有年龄限度的下限,那么责任概念就会失去意义”,《北京规则》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真正倡议在于,明确或提高某些设置较低或根本没有年龄下限的国家刑事法律中的刑事责任年龄,其进步意义恰恰在于“可高但不可低”的国际倡议。也正因如此,《北京规则》在其通过后的几十年,各国内部和联合国才逐步接受。
第二,以少年福祉为目标,剥夺人身自由只能基于严重暴力犯罪和没有其他合适对策,且需保持在最低限度。按照《北京规则》17.1审判和处理的指导原则,“(b)只有经过认真考虑之后,才能对少年的人身自由加以限制并应尽可能把限制保持在最低限度;(c)除非判决少年犯有涉及对他人行使暴力的严重行为,或屡犯其他严重罪行,并且不能对其采取其他合适的对策,否则不得剥夺其人身自由;(d)在考虑少年的案件时,应把其福祉看作主导因素”。同时,说明中明确指出,规则17.1(b)鼓励尽可能采用缓刑等监外教养办法,这意味着少年司法必须以维护少年的福祉和未来前途为首要目标,不能像成年人犯罪那样有“罪有应得和惩罚性处分”理念,更不能采用严厉的惩罚性办法。规则17.1(c)旨在避免对少年实行监禁,除非没有其他适当的办法可以保护公共安全。 本条规则的核心在于,少年司法不能有报应主义目标,不能动辄采用监禁,监禁不能作为首选而只能是最后的手段。只有当采取其他办法没有效果的情况下才能考虑监禁,如果没有采取其他办法或压根就没有采取其他办法的可能,刑法直接赋予监禁刑惩罚肯定存在法理逻辑错误。
第三,以多种灵活的非监禁措施为处理办法,对少年违法行为应最大限度避免监禁、迫不得已才使用监禁。《北京规则》中有多条规则强调了非监禁的优先措施及替代性处理办法,规则18列举了(a)照管、监护和监督的裁决;(b)缓刑;(c)社区服务的裁决;(d)罚款、补偿和赔偿;(e)中间待遇和其他待遇的裁决;(f)参加集体辅导和类似活动的裁决;(g)有关寄养、生活区或其他教育设施的裁决。规则19的说明从两个方面解释了对监禁加以限制:从数量上(“万不得已的办法”)和从时间上(“最短的必要时间”),并解读了不这样做的原因是监禁的消极影响和非监禁的相同效果。尤其值得强调的是,这是第六届联合国大会第4号决议的基本指导原则之一:“除非在别无任何其他适当办法时,才把少年罪犯投入监狱。”
(二)《儿童权利公约》
《儿童权利公约》于联合国大会1989年11月20日通过,中国于1989年8月29日签字并于1992年3月2日批准,但提出了关于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和国家计划生育的相关保留。 就公约本身而言,有以下五个层面值得注意。
第一,将最大利益作为儿童权利保护的首要原则。公约3.1规定,“关于儿童的一切行动,不论是由公私社会福利机构、法院、行政当局或立法机构执行,均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一种首要考虑”。然而,公约本身并没有将其阐明为基本原则,最早在2003年第5号一般性意见中才将其作为原则提出来。按照最大利益原则,“该原则要求政府、议会和司法机构都要采取积极措施。每个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都必须采用最大利益原则,系统地审查其所作出的决定和采取的行动在目前或以后将会对儿童权利和利益产生何种影响,例如,拟议或现行法律或政策或行政行动或法院判决”。 儿童权利委员会在2013年第14号意见专门就儿童最大利益做了关于“儿童的最大利益: 一项权利、一项原则和一项行事规则”的全方位阐述,但遗憾的是这份原则并未明确涉及刑事责任年龄。2020年第20号一般性意见进一步将“最大利益”进一步解读为:“这是儿童的一项实质性权利、一项解释性法律原则、一项行事规则,既适用于儿童个体,也适用于儿童群体。所有执行 《公约》的措施,包括法律、政策、经济和社会规划、决策和预算决定,都应该遵循确保将儿童包括青少年的最大利益作为涉及儿童的一切行动的首要考虑因素的程序。”
第二,关于儿童刑事处罚的禁止性前提和最后手段的限制条件。根据《公约》第37条,儿童不受酷刑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尤其不得判处死刑和无释放可能的无期徒刑,这与《北京规则》所规定的内容相同。儿童的自由限制应满足最短时间和最后手段两个基本要求。对儿童的逮捕、拘留或监禁应符合法律规定,但不能在未采取其他手段的前提下将刑事处罚作为首要选择。
第三,关于倡议成员国制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内容。《北京规则》只是提示各国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不应规定太低的原则性倡议,《儿童权利公约》则把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作为必要事项写入条款。因此,公约40.3规定,缔约国应致力于促进规定或建立专门适用于触犯刑法的儿童的法律、程序、当局和机构,尤其是(A)款明确规定,“规定最低年龄,在此年龄以下的儿童应视为无触犯刑法之行为能力”。
第四,继续倡议多种非刑罚处理办法。与《北京规则》强调对违法行为刑事裁决为非监禁处理办法相比,《儿童权利公约》更看重不作为犯罪(非刑事裁决)的多种处理方案。公约40.4规定:“应采用多种处理办法,诸如照管、指导和监督令、辅导、察看、寄养、教育和职业培训方案及不交由机构照管的其他办法,以确保处理儿童的方式符合其福祉并与其情况和违法行为相称”。
第五,关于鼓励缔约国制定更有利于儿童的法律。公约第41条规定,“本《公约》的任何规定不应影响更有利于实现儿童权利且可能载于下述文件中的任何规定:(A)缔约国的法律。”就刑事责任年龄而言,本条内容高度肯定各国在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基础之上,规定更高的无触犯刑法之行为能力的年龄。尽管公约本身没有强制要求各国制定统一的刑事责任年龄,但毋庸讳言,本条鼓励并肯定各国基于儿童福祉考虑,将刑事责任最低年龄设置得更高。
总体来看,《儿童权利公约》和《北京规则》具有高度一致性,关于最后手段和最短时间,以及限制和剥夺自由的管控,都与儿童福祉的优先考虑密切相关。在此基础上,《儿童权利公约》在刑事责任年龄的强制性倡议基础上,充分明确了刑事制裁只能是其他社会化和人性化处理办法无效以后才能采取的手段。
(三)《利雅得准则》
《利雅得准则》,全名为《联合国预防少年犯罪准则》,因于1988年在利雅得阿拉伯安全研究与进修中心召开的专家会议上讨论定稿而得名,1990年12月在古巴第八届预防犯罪与罪犯处遇大会获得通过。《利雅得准则》是继《儿童权利公约》之后专门关于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的国际准则。本规则虽然没有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但《利雅得准则》明确重申,只有严重损害和危害他人的行为,才能对未成年人给予定罪和处罚;有关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治理的官方措施只能是最后手段,且应当在最短的时间范围内。《利雅得准则》从法律政策、措施、理念方面,给予各国制定预防青少年犯罪的政策和措施提供指导,对犯罪和刑事责任年龄的设定方面具有如下四方面的重要意义。
第一,就法律政策而言,《利雅得准则》第5条要求各国提供青少年受教育的机会,尤其是明显处于危险或面临风险的青少年更应被给予教育的机会;采取专门化的防止不端行为的理论和方法,以减少发生违法的动机、需要和机会或诱发的条件。
第二,在理念方面,《利雅得准则》要求各国应着重于青少年的整体利益并以公正、公平的思想作为指导,从而采取官方干预措施。明确告知各国,维护所有青少年的福利、发展、权利和利益是基本立场和出发点。同时,该规则第5条(e)明确阐明,“青少年不符合总的社会规范和价值的表现或行为,往往是成熟和成长过程的一部分,在他们大部分人中,这种现象将随着其步入成年而消失”。尤其是(f)警告成员国,“把青少年列为‘离经叛道’‘违规闹事’或‘行为不端’,往往会助成青少年发展出不良的一贯行为模式”。
第三,就措施方面,《利雅得准则》明确申明收容教养、监禁等官方干预措施只能是为了青少年利益而采取的最后手段。该规则第6条明确说明,正规的社会管制机构只应作为最后的手段来利用。第46条规定:“将青少年安置教养的做法,应作为最后的手段,而且时间应尽可能短,应把他们的最大利益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尤其是e项明确说明,针对青少年自身而言的监禁条件只能是:“孩子的行为表现对其有严重的身心危险,如采取非安置教养办法,其父母、监护人或孩子本身,或任何社区服务,均无法应付此种危险”。
第四,关于青少年犯罪的防止和处理方案,《利雅得准则》鼓励各成员国根据本国国情制定可靠、科学合理的方案和法律。该规则第48条规定,“防止违法不端行为的方案应以可靠的、科学的研究结果为依据”。第56条规定了不当刑事处罚的行为,“为防止青少年进一步受到污点烙印、伤害和刑事罪行处分,应制定法规,确保凡成年人所做不视为违法或不受刑罚的行为,如为青少年所做,也不视为违法且不受刑事处罚”。然而,关于哪些行为是不当刑事处罚行为,《利雅得准则》及之前的联合国文件均没有清晰指明。直到联合国《第10号一般性意见》第8条才明确指出,这些不当处罚行为就是指“流浪、逃学、出走”等身份违法行为。
(四)《哈瓦那规则》
《哈瓦那规则》,全名为《联合国保护被剥夺自由少年规则》,于1990年12月14日在联大第68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国目前没有签署加入和提交批准文书。其制定依据包含《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公约》《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儿童权利公约》《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该规则的制定背景是:对世界各地被剥夺自由少年所处的条件和情况感到震惊;被剥夺自由少年最易受到虐待、伤害,他们的权利遭到侵犯。因此,本规则在阐述制定缘由时,明确申明坚持以未成年人的身心福祉为核心,秉持监禁只能是最后手段,要求各国在刑事责任年龄的框架下严格控制剥夺少年的自由。具体来看,本规则仍有三点值得重视。
第一,重申剥夺自由的最后手段和时间尽可能短。该规则第2条明确规定,剥夺自由不仅只能基于维护少年的身心福祉的目标,而且限于特殊情况,“作为最后的一种处置手段,时间应尽可能短”。关于剥夺自由的概念,该规则11(B)定义为,“对一个人采取任何形式的拘留或监禁,或将其安置于另一公私拘禁处所,由于任何司法、行政或其他公共当局的命令而不准自行离去”。
第二,将少年定义为18周岁,并鼓励各国制定法律规定禁止对一定年龄的少年剥夺自由。该规则第11条(A)将少年定义为18周岁,明确各国法律可以规定禁止对某一年龄界限(未满18周岁)少年剥夺自由。
第三,制定了各种少年的基本权利和剥夺自由的条件和管理措施。该规则第17条规定,“被逮捕和审前拘留只能限于特殊情况,并采取替代办法,否则应尽量可能短”。第38条规定,“义务教育阶段的少年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并尽可能在拘留所外的社区学校进行”。第63-65条规定,除非少年有自我伤害、伤害他人或严重毁坏财物的行为,禁止对少年基于任何目的使用束缚工具和武力,禁止拘留所人员携带和使用武器。
(五)儿童权利委员会《第10号一般性意见》
《北京规则》关注到各国刑事责任年龄不应太低,《儿童权利公约》也呼吁缔约国规定无触犯刑法之行为能力的最低年龄。然而,在随后长达二十年时间里,联合国并没有拿出切实可行的关于最低年龄是否太低的评估办法和推荐建议。直到2007年日内瓦会议,儿童权利委员会才在《第 10 号一般性意见(2007 年) :少年司法中的儿童权利》明确拿出刑事责任年龄的最低标准和值得赞赏的高标准。有鉴于这份意见对评价《儿童权利公约》各缔约国的刑事责任年龄至关重要,同时刑事责任年龄又与少年司法的基本法理有关,故从如下四个方面予以详述。
第一,重申少年司法的一般性原则。在不歧视原则中,号召各缔约国废除专为儿童设立的身份犯罪等刑法专款,给予儿童平等的法律保护。在儿童最高利益原则中,重申“保护儿童的最高利益意味着,在处置少年罪犯时,诸如镇压、惩罚等传统的刑事司法目标都必须让步于实现社会重新融合与自新的司法目的”。在生命、生存和发展权原则中,将对少年犯罪的处置作为预防少年犯罪和保护儿童权利的重要方式,提请各成员国注意;重申禁止死刑和无期徒刑;采用剥夺自由的做法对儿童身心发展不利、妨碍重新融入社会;剥夺自由只能作为最后手段和采取最短时间。
第二,警示各缔约国预防少年犯罪的整套措施体系的重要性,“若不制定出一整套旨在预防少年犯罪的措施,会有严重的缺陷”。在关于成长环境的问题上,意见指出,如果少年的成长环境本来可能滋生犯罪,那就不符合最高利益原则,各国应采取措施确保少年所享有的适足生活水平权、健康照顾权、受教育权、免遭暴力伤害的受保护权、免遭经济或色情剥削等权利。关于预防方案,意见指出应重点关注和支持弱势家庭、给予风险少年特殊的照顾和关注,尤其是辍学儿童或由于其他原因未能完成其学业的儿童。
第三,关于不诉诸法律和司法审理的措施,重申逮捕、拘留、监禁等措施是且只能是最后的手段。针对大量诸如偷盗等财产犯罪或其他轻微违法行为,需严格贯彻不诉诸司法的具体违法行为。对于需要司法干预处理的违法行为,也应该善于运用缓刑、社区监督等非监禁等转化后替代性处置方案。严格做好犯罪记录封存,规定可查阅的档案需限定在一年以内。此外,还提醒各缔约国注意,不可采取任何阻碍儿童重返社会的诸多行动,包含足以造成名声败坏、社会孤立、贬斥的公共舆论。
第四,关于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儿童权利委员会明确为缔约国提供了关于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的法理依据。首先,委员会明确阐明“低于12周岁的刑事责任年龄不是国际上可接受的水平”,同时肯定14或16周岁“可促进少年司法制度 ”的“值得赞赏水平”。关于规定12周岁的最低国际标准的法理,主要是针对那些没有最低刑事责任年龄或低于12周岁刑事责任年龄的国家。针对这个问题,意见C.32明确提出,“委员会鼓励各缔约国将其较低的最低刑事责任年龄提高到12岁为绝对最低责任年龄”,同时鼓励“继续提高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幅度”。关于14至16周岁的刑事责任年龄,委员会一方面敦促各缔约国不要将最低刑事责任年龄降低至12周岁,另一方面又以“较高的最低刑事责任年龄,诸如 14 或 16 岁,可促进少年司法制度”为由,肯定14-16周岁的合理性。其次,委员会强烈建议,年龄作为追究儿童刑事责任的唯一标准,各缔约国不能以严重罪行或被视为足够成熟等理由,突破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再次,委员会建议将18周岁作为各国少年司法规则的最低上限标准,要求那些少年司法上限为16或17周岁的国家修改法律,并高度赞赏和鼓励缔约国将少年司法年龄的上限设置更高,如21岁。
(六)其他国际规则
联合国关于儿童专题的国际公约和准则只有13个,但这些公约只是少年司法规则的很少一部分。大量与儿童犯罪和少年司法相关的公约文件在“刑事司法”专题中,大概有30多份国际公约和文件。除了本文所明示的诸多公约和规则外,如下国际法文件也显示出刑事责任的法理依据。由于诸多内容属于少年司法原则的重申,故略作介绍。
首先,《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规定了诸多关于青少年司法的基本内容。本规则起初于1955年8月30日由联合国防止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历经多次修正,于2015年12月17日在联合国大会通过最新版本。序言4.2明确重申,“一般而言,青少年不应判处监禁”。该规则11.(d)明确规定“青少年囚犯应同成年囚犯隔离”。该规则23.2规定青少年囚犯有获得体育和文娱训练的权利。规则98.2规定了关于为青少年囚犯提供有用行业方面的职业训练的内容。规则104规定,“青少年囚犯应接受强迫教育,监狱管理部门应予特别注意”。该规则112.2规定,“未经审讯的青少年囚犯应同成年囚犯隔离,原则上应拘留于不同的监所”。
其次,《刑事司法系统中儿童问题行动指南》(以下简称《指南》)基于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6年7月23日第1996/13号决议通过,后于1997年7月21日正式通过,其对象是秘书长及联合国各有关机构和《儿童权利公约》的缔约国。在B.13具体目标中,《指南》规定,“虽然国家立法规定了刑事责任年龄、法定成年人年龄和承诺年龄,但各国仍应确保儿童享有受到国际法保障的所有权利,特别是公约第3条、第37条和第40条规定的那些权利”。规则14指出,各国未成年人司法特别应注意以下方面:“(a)应有以儿童为核心的全面的少年司法程序;(b)应由独立专家组审查现有的和拟议的少年司法法律及其对儿童的影响;(c)凡尚未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的儿童均不得受到刑事指控;(d)国家应设立主要对犯有刑事行为的少年行使司法权的少年法庭,并应制订旨在顾及儿童特定需要的特别程序。或者,普通法院应酌情纳入这种程序。”
总体来看,联合国公约反映出,刑事责任年龄是与儿童最高利益原则、摒弃惩罚思想、严格限制入罪,以及对儿童的非监禁处理、监禁最后手段、最短时间等基本法理相配套的法律规定。就各国而言,刑事责任年龄本身并无实际意义,因为年龄与身份违法、矫正措施、刑法外与刑法内规定有重要差别。(32)熊谋林:《比较视角:未成年人违法与矫正措施略考》,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12年第2期。然而,公约之所以要关注刑事责任年龄,其核心内容是用“无触犯刑法之行为能力”去肯定儿童的无犯罪能力。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联合国想要用统一的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管理和监督那些将身份违法作为儿童犯罪特例,以及刑事责任年龄低于12周岁的国家。正因如此,有关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才从1984年《北京规则》(4.1)规定“该年龄的起点不应规定得太低”,到1989年《儿童权利公约》40.3.A发展为“规定最低年龄,在此年龄以下的儿童应视为无触犯刑法之行为能力”,再到2007年第10号文件明确把12周岁作为最低年龄。与此同时,《儿童权利公约》的若干一般意见,告诫和要求缔约国不能将14至16周岁的刑事责任年龄降低,反而鼓励成员国继续提高刑事责任年龄。尤其是在针对社会舆论造势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时,联合国官方解释的刑事责任年龄设定依据,应当是“医学和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发现,而不是传统或公众需求”; 同时,针对呼吁惩罚或严打青少年犯罪的降低呼声,联合国文件也明确指出“打击青少年犯罪(Fighting Juvenile Crimes)是错误的做法”,(33)See 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 Innocenti Digest: Juvenile Justice, at https://www.unicef-irc.org/publications/pdf/digest3e.—pdf .正确的做法是提高青少年司法标准和处理规则。
三、刑事责任年龄的国内依据
(一)《未成年人保护法》
《未成年人保护法》作为未成年人保护的专门立法,从1991年9月公布以来,分别于2006、2012、2020年三次修订。在刑事责任年龄规定方面,四个版本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均没有规定刑事责任年龄,只规定了“本法所称的未成年人是未满十八周岁的公民”。1991年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只肯定了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不公开审理,以及不予刑事处罚的收容教养机制。纵观《未成年人保护法》近三十年的发展,如下三个内容可观察未成年人保护的重要法理特征和内容。
首先,从结构上来看,未成年人保护的责任主体逐渐强化政府主体的保护措施,但各部门的联动保护和早期干预机制不明。《未成年人保护法》前三个版本一直按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司法保护四章安排条文,2021年修正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新增网络保护和政府保护两章。前三版《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对人民政府及其民政部门的职责限定于救助和收养儿童,新增的政府保护章中第92条将以前的救助和收养理念改变为“临时保护”理念。尤其是第五、六项,首次将“监护人教唆、利用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行为,未成年人需要被带离安置;未成年人遭受监护人严重伤害或者面临人身安全威胁,需要被紧急安置”纳入到临时保护体系以内。然而,纵观四个版本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未成年人保护过于依赖学校保护,其他保护的联动干预机制不明。虽有针对严重不良行为可以送至专门学校的部分规定,但将严重不良行为的矫治与犯罪行为预防转移至《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没有任何法律将预防和矫正未成年人行为作为提前干预的强制性措施。
其次,从保护未成年人的原则来看,将尊重和强调未成年人保护的多种“应当遵循”原则统一为“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在早期的三个版本中,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只有应当遵循的理念要求,没有具体的指导原则和内容。1991年《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保障合法权益、尊重人格尊严、适应身心发展、教育与保护相结合,2006年和2012年变成尊重人格尊严、适应身心发展、教育与保护相结合。2020年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4条,将之前应当遵循的原则统一为一个原则,即“保护未成年人,应当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与此同时,本条将2012年版本的三个“应当遵循”的原则改为六个“处理涉及未成年人事项,应当符合下列要求,即特殊、优先保护、尊重人格尊严、保护隐私、适应身心发展、听取未成年人意见、教育与保护相结合。换句话说,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直到2020年版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才植入国内法律中,之前的诸多“应当遵循”仅是基本要求而已。
最后,从未成年人司法保护角度,保护一般未成年人权益和受害者权益方面值得肯定,但涉罪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较为欠缺。就涉罪未成年人,四个版本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虽强调“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但如何贯彻的具体措施不明。除了专门机构或专人办理、与成年人分开羁押、禁止歧视方面等已有规定的内容外,司法措施和决定如何体现对涉罪未成年人的保护上均没有涉及。即使是2020年版,有关未成年人保护的羁押例外原则、程序保护、不诉机制、非刑罚处置、量刑指导原则等具体措施均没有涉及。这些内容不仅是处理涉罪未成年人的核心,也是整个刑事责任的基本法理依据,这些缺失恰恰反映出涉罪未成年人的专门保护法理依据不足。
(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于1999年6月28日公布,分别于2012年、2020年两次修正。三个版本《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结构基本相同,但2020年新修订的版本改动比较大。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从结构上删除“未成年人犯罪的自我防范”一章,另一方面新增和加强预防犯罪的具体措施。总体来看,由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偏重于犯罪预防,故对涉罪未成年人的处置和矫治方面的指导性规则规定不足。由于中国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专门法律就只有《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但这两部法律里面都事实上没有涉罪未成年人的具体保护措施和司法原则。尽管如此,《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的部分内容仍然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的配置和处置相关,具体解读如下。
第一,从条文规范的内容上来看,《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相关条文宣示意义较为浓厚,诸多条款直到2022年才有较为清晰的实质权责。从1999年第一次公布以来,该法一直将各级人民政府作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主体,内容主要围绕制定规划、组织工作、提供政策和经费保障、执行检查、宣传教育等六大方面展开。正是由于这些内容本身的不明确性,故《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长期围绕政府职能而展开,但就如何落实预防青少年犯罪的具体措施方面稍显不足。2020年新修订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加大了干预和矫治措施的内容。就干预方面,2020年新修订版第31条新增学校管理教育措施五项,即予以训导、要求遵守行为规范、要求参加专题教育、要求参加校内服务活动、要求接受心理辅导和行为干预、其他措施。就矫治方面,2020年新修订版第41条新增对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的九种矫治教育措施行为。即予以训诫,责令赔礼道歉、赔偿损失,责令具结悔过,责令定期报告活动,责令遵守行为规范,责令接受心理辅导、行为矫治,责令参加社会服务活动,责令接受社会观护,其他措施。
第二, 2020年《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将刑事责任年龄嵌入严重不良行为的定义中,同时强化其矫治措施,但对涉罪和未涉罪的未成年人如何处理都稍显不足。2020年新修订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38条虽将“严重不良行为”定义为“指未成年人实施的有刑法规定、因不满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不予刑事处罚的行为,以及严重危害社会的下列行为”,第41条也新增严重不良行为未成年人的九种矫治措施。然而,该法不仅没有刑事责任年龄的具体规定,对涉罪未成年人的早期越轨行为的矫治明显不足,也没有矫正和处置方面的特别规定。第43条和第44条针对一般严重不良行为或“严重危害行为、情节恶劣或造成严重后果;多次实施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拒不接受或者配合矫治教育措施;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教育行政部门有权单独或会同公安机关将未成年人送入专门学校接受专门教育。但这些措施都是针对“因不满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不予刑事处罚”,而不是已经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涉罪未成年人。
第三,关于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办理,三个版本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均没有关于未成年人司法的特别程序规定,也没有将最大利益、监禁作为最后手段、最短期限等基本原则规定在法律中。以2020年版为例,诸多关于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理主要设置在“对重新犯罪的预防中”,内容包含社会调查、合适成年人、社区矫正、未成年人分开羁押、法治教育、安置帮教等基本内容。换句话说,《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事实上并没有将非羁押、非监禁等社会化处理措施等前置措施纳入到未成年人犯罪的矫治内容中,也没有将监禁的前提条件和最短期限等基本内容纳入相关条款。因此,就已经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犯罪人来说,《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事实上缺乏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处理条款,这就说明未成年犯罪人只要构成犯罪就将直接面临刑法和刑事司法程序。如果真是如此,则明显与司法和监禁作为最后手段、替代性转置措施等国际法原则相距甚远。
(三)《刑法》
清末修律时,1905年沈家本主修的《刑律草案稿本》将12周岁作为论罪起点,但1907年冈田朝太郎起草的《大清刑律草案》又将16周岁作为论罪起点。(34)黄源盛:《晚清民间刑法史料辑注1905-2010(上)》,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25、48 页。自1935年《中华民国刑法》以来,虽然各时期草案对刑事责任年龄围绕12、13周岁有所微调,但正式的刑法典一直是14周岁。(35)刘倩:《论刑法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制约》,西南财经大学2021年硕士学位论文。就现行刑法而言,1997年《刑法典》与1979年《刑法典》一脉相承,按照已满14未满16周岁对部分严重犯罪行为、16周岁以上对所有犯罪承担刑事责任。2021年《刑法修正案(十一)》又将12周岁作为责任年龄起点,用故意杀人和重伤、情节恶劣、最高检核准作为限制条件。从当前情况来看,要正确理解刑事责任年龄的刑法依据,不仅需要从刑法本身来看,还要结合《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两个专门法来看。如此一来,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法理依据,有三个方面值得探讨。
第一,关于未成年人罪与非罪的矫治衔接问题。1997年《刑法典》以来,我国一直采用负刑事责任就有罪入刑,不负刑事责任就收容教养或专门教育的二分法处理方式。然而,从笔者之前的调查了解情况来看,不负刑事责任的收容教养实际上并未真正落实,从而出现《刑法修正案(十一)》修订过程中广大代表所指出的“一放了”之局面。这也就出现了,未成年人不负刑事责任就不收容教养或专门教育,但只要触犯刑法应当负刑事责任,则直接按有罪判刑方式来处理。由于禁止对未成年人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那么有期徒刑也基本是未成年人刑罚的最佳选择。然而,在欠缺前期收容或专门教育的情况下,这显然不符合监禁作为未成年人处罚“最后手段、最短时间”的基本国际法理。先前的研究发现,在2011年刑法关于缓刑的内容修正以前,超过60%的未成年人犯罪直接被判处实刑。(36)熊谋林:《未成年人犯罪与矫正实证研究——以成都市温江区为例》,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14年第2期。虽然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增加了关于未成年人“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应当宣告缓刑”的内容,但笔者调查的2012-2013年未成年人犯罪的缓刑率仍然只有30%左右。(37)熊谋林、胡瑶、 江南燕、 周静: 《再谈未成年人犯罪与矫正——以德阳市六个基层法院为样本》,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14年第4期。那么,对于绝大多数判处实刑的未成年人来说,犯罪就直接判处监禁实刑,显然不符合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因此,就中国的少年司法来说,最大的问题不是刑事责任年龄如何规定,而是如何落实收容教养或专门教育的问题,如何有效落实非监禁刑的问题。
第二,关于涉罪未成年人的刑事处罚与具体犯罪的衔接问题。尽管中国从1979年以来,坚持对未成年人“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但是否能对12至16周岁的未成年人适用缓刑,还需根据其承担刑事责任的具体罪名和法定刑配置来分析。从现行《刑法典》来看,无论是已满12未满14周岁,还是已满14未满16周岁,涉及命案的刑罚配置基本很难适用非监禁处罚。以故意伤害致人重伤为例,按照《刑法修正案(十一)》和《刑法》第234条的逻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此时,即使对已满12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减轻处罚,也只能在3年以上10年以下判处刑罚,这显然不符合“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缓刑条件。尽管根据《刑法》第99条,以上或以下均可包含3年有期徒刑“本数”,但这在量刑指导意见之下的具体量化指标之下,很难到达3年底线。同理,对于故意杀人罪来说,即使是已满12未满14周岁的人构成犯罪,也仍然很难适用缓刑。就已满14未满16周岁来说,无论是1979年刑法还是1997年刑法所规定的含有加重情节的抢劫和强奸犯罪行为,也基本上是应当处刑10年以上的犯罪行为。换句话来说,只要已满12周岁未满16周岁未成年人构成犯罪,绝大多数情况下可能判处实刑。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就在于刑法典本身的法定刑配置,这从反面也说明当前刑法对于未成年人的刑事处罚规则还有很大的调整空间。
第三,关于涉罪未成年人的非监禁刑的优先考虑问题。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以后,除了关于未成年人“应当宣告缓刑”的相关规定以外,没有任何其他关于未成年人非监禁刑的相关规定。尽管《刑法修正案(八)》也将社区矫正嵌入到缓刑执行过程中,然而社区矫正的前提是宣告缓刑,同时如何实施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正也没有明确规定。虽然《社区矫正法》采用了作者曾倡议的类似于“预防、帮教青少年越轨委员会”(38)熊谋林、胡瑶、张琪、马丽源、代亮亮、刘美彤:《青少年越轨、犯罪与“社会一体化”预防理念 ——基于四川省三市调查的启示》,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15年第1期。的“社区矫正委员会”,也在第七章有关于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特别规定,但7个条文除了人员配置的原则性内容外,本身并没有回答如何矫正的问题。《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第3条也有关于地方人民政府根据需要设立社区矫正委员会的相关规定,但也只在第55条有关于未成年人的特别规定。虽然目前难以全面评估社区矫正法实施以后的情况到底如何,但有限资料显示人员缺乏、专业化程度低、形式多于内容、社会一体化程度低等基本问题并没有改变。(39)熊谋林、胡瑶、张琪、马丽源、代亮亮、刘美彤:《青少年越轨、犯罪与“社会一体化”预防理念——基于四川省三市调查的启示》,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15年第1期;张凯、张延琦: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的实施效果、实践难题及解决思路 》,载《社区矫正理论与实践》 2022年第4期;翟中东、孙霞:《〈社区矫正法〉实施两年来若干问题的思考》,载《犯罪与改造研究》2022年第9期。从总体来看,在刑法欠缺关于未成年人非监禁刑的优先处置原则的情况下,不仅《社区矫正法》及其办法本身没有将非监禁处遇落到实处,广大涉罪未成年人的其他矫正措施也未落实。因此,在综合评估刑法相关规定以后,单纯的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入罪标准,而忽略涉罪未成年人的非监禁优先处理规则,并不能贯彻以少年“最大利益”原则为考虑的刑法和刑事司法措施。
(四)《刑事诉讼法》
自1979年公布《刑事诉讼法》以来,虽经历了1996、2012、2018年三次修正,但关于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的相关规定在1996年以后变化不大。为有效阐述《刑事诉讼法》所反映的未成年人程序法理,如下从不同版本的《刑事诉讼法》简要阐述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的相关法理规定。
第一,1979年《刑事诉讼法》没有特别规定未成年人特别诉讼程序,未成年人相关规定比较欠缺。从法律条文上来看,涉及未成年人的只有法定代理人到场(第10条)、指定辩护(第27条)、不公开审理(第111条)等三个最基本规定,也有关于法定代理人享有的申请回避权(第23条)、上诉权(第129条)。显然,1979年《刑事诉讼法》在未成年人诉讼程序上的特别保护上比较欠缺,尤其欠缺对未成年人分开关押、置于特殊羁押场所的相关规定。也正因为如此,实践中除了收押少年犯和不满16周岁不予处罚的少年,还收容一些有违法行为,但尚未构成犯罪的少年,甚至出现少年直接置于成年犯监狱、劳改队、看守所等混合羁押的情况。直到1982年3月,公安部才首次公布《公安部关于少年犯管教所收押、收容范围的通知》,明确要求少管所只能收纳已满14周岁未满18周岁被判有期、无期和死缓的少年犯;不构成犯罪确有必要收容教养的犯罪少年,已满14周岁以上需要地区公署或省辖市公安局审批,未满14周岁报请省市级公安厅、局审批。然而,对于非罪行为收容教养问题的处理,刑诉法在本阶段没有相关内容。在法律层面,直到1994年《监狱法》第十章才有“教育改造为主”(第75条)和关于未满18周岁的少年犯在未成年犯管教所分开执行刑罚(第74、76条)的相关规定。
第二,1996年《刑事诉讼法》结构安排与1979年刑事诉讼法基本一致,唯一的变动是在修正案第102项中新增“对未成年犯应当在未成年犯管教所执行刑罚”。然而,这次刑诉法仍然没有关于未成年人分开羁押的特别规定,也没有未成年人羁押作为最后手段的内容。
第三,2012年《刑事诉讼法》是未成年人刑诉程序修改最大的一部法律,新增“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特别章。本次修法不仅将《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教育、感化、挽救方针,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方针原则写入刑诉法,还创造性地规定了多个少年司法的专门诉讼程序规则,包括:专人办理规则(第266条)、未成年人调查(第268条)、限制逮捕和分开关押、管理、教育(第269条)、附条件不起诉(第271-273条)、犯罪记录封存(第275条)。总体来看,2012年新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大量内容契合了《北京规则》《儿童权利公约》《利雅得准则》的羁押例外、专业队伍、分开关押、不诉等少年刑诉特别程序规则。尽管2012年刑事诉讼法以后的未成年人非羁押率有所上升,然而,附条件不诉本身限于“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这造成严重刑事犯罪的未成年人很难适用附条件不诉规则。
第四,2018年《刑事诉讼法》基本沿用了2012年修正版的内容,只有关于不需要认罪认罚具结书(第174条)和不适用速裁程序(第223条)的两处规定。总体来看,当前《刑事诉讼法》对于少年司法程序与1979年刑事诉讼法相比有较大变化,2012年以后的《刑事诉讼法》的限制逮捕和《刑法典》应当判处缓刑的措施也相互呼应。从这一方面来看,当前《刑事诉讼法》对于涉罪未成年人来说,一定程度上部分贯彻了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然而,应当看到,目前的刑诉法规则重点仍然在犯罪以后的处理,对涉罪未成年人非罪处理规则指导不足,尤其是附条件不诉的范围过于狭窄。
总体来看,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体系的修正和规定比较突兀,呈现出与国内法规定脱节的明显现象。一方面,国内法关于未成年人少年司法规则的规定呈现出时间短、内容新、非罪和有罪处遇规则不完善等特点。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降低,不是在评估已有法律实施状况的前提下修改刑法,而是在配套法律措施未立法或实施状况较差的情况下单纯修订刑法。在时间短和内容新的问题上,大量关于未成年人非监禁处理和限制羁押实际上在2012年前后才有所规定,《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直到2020年才有各政府主体关于未成年人犯罪和严重不良行为的矫正干预等内容,刑法上直到2020年的《刑法修正案(十一)》才用“专门教育”替代“收容教养”。从规则不完善的情况来看,主要体现在非罪处理的具体规则不明,有罪非羁押和非监禁刑罚基本原则的具体落实不协调。由于各种未成年人司法措施的法律规定过于严苛,现有法律有关限制逮捕措施、附条件不诉、缓刑规则事实上很能运用于已满12周岁未满16周岁的严重犯罪行为。
另一方面,我国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降低至12周岁以后,事实上又将刑事诉讼中的逮捕和监禁直接运用于已满12周岁未满14周岁或者已满14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身上。虽然1997年《刑法》规定了收容教养,但未成年人的收容教养因其性质不明而长期面临无法有效落实的尴尬局面。(40)雷杰:《我国收容教养制度的困境与完善路径》,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19年第3期;刘世恩:《试论我国少年收容教养制度建设》,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03年第4期。尤其是2003年前后,孙志刚案引发的对“收容”合法性的思考,(41)童之伟:《孙志刚案提出的几个学理性问题》,载《法学》2003年第7期。有关未成年人的收容教养在之后就基本处于停滞状态。2020年《刑法修正案(十一)》在规定专门教育的同时,降低了刑事责任年龄,但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显然未考虑到专门教育本身的优先程序。由于专门教育的前提是“不满十六岁不予刑事处罚”,这就使有罪的刑事处罚已经不适用“专门教育”,使得刑事处罚直接冲到未成年人矫正的第一线。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国少年司法的实体规定与程序措施显然又与“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及其衍生规则有一定距离。
四、结论:重申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法理依据
本文将写作重心放在了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国际国内法律规定梳理,故始终以责任年龄为主线来审视其背后的实体法、专门法、程序法法理依据。综合来看,本文认为刑事责任年龄应当遵循的国际法和国内法依据,主要有两个方面组成。
从国际法层面来看,今天的中国少年立法和司法在形式上还是可圈可点,但也应当注意从实质层面如何理解和衔接国际法规则等问题。不仅分开羁押、专门法庭、专人办理、缓刑、附条件不起诉等条款在形式上看符合国际法准则,而且最低刑事责任年龄、死刑、专门教育、限制逮捕、法律援助规则在实体上也符合国际法规则。近年的立法的确反映出中国与国际法规则逐步接轨,然而,如果中国要在国际法上走在前列,引领全球少年立法和司法,还需充分注意到如下三个国际法理问题。
首先,应当充分重视《北京规则》对中国自身的意义,以及中国是《儿童权利公约》的签约国。《北京规则》作为唯一一个以中国首都命名的国际法规则,明确指出“刑事责任年龄不应规定得太低”,万不得已、最低限度、最短时间的剥夺自由只能以针对严重暴力犯罪和监禁替代措施没有效果为前提。《儿童权利公约》本身所提出的触犯刑法能力的最低年龄必须以“儿童最大利益”、非刑事处罚的优先性、刑事处罚的最后手段等作为前提,这是直接需要缔约国履行的义务。其次,中国应当充分切实的在《儿童权利公约》框架下,正确理解《利雅得准则》《哈瓦那规则》《曼德拉规则》《刑事司法系统中儿童问题行动指南》所展现的更加具体的非刑事处罚和非监禁处理的优先性规则、剥夺自由的底线规则。最后,应当充分注意到《第10号一般性意见》的动因和最新的国际动态。12周岁作为最低年龄是因为低于12周岁是“国际上不可接受的水平”,从而强制要求没有最低限度年龄缔约国认真履行国际法义务。与此同时,应当意识到,这并不意味着那些已经规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国家可以将刑事责任年龄降至12周岁。与此相反,联合国鼓励“继续提高最低年龄”,以及联合国针对巴拿马将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从14周岁降低至12周岁的做法而作出的强烈批评。(42)Committee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Fifty-eighth Session. Consideration of reports submitted by States parties under article 44 of the Convention, Concluding Observations:Panama. 21 December 2011, at https://www.refworld.org/pdfid/4efc96f12.pdf.
从国内法层面来看,尽管国内法目前有诸多关于保护未成年人和少年司法的特别规则,但多数规则是最近十年才入法。这些规则内容本身非常新、时间短,不仅诸多新规则和内容与已有的法律规定的契合程度未作深入分析,而且这些规则的实效检验还相当不够。
首先,2020年10月7日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在将“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写入的同时,两个月后《刑法修正案(十一)》就将刑事责任年龄从14周岁降低到12周岁,这是否符合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自然不言而喻。其次,《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和《刑法修正案(十一)》在2020年12月26日同一天修改关于专门教育的规定,关于严重不良行为直接送专门教育的内容与刑事责任年龄的降低同时完成。最后,修订刑事责任年龄以后,应当考虑的是用什么方式来矫正严重犯罪的12至16周岁的未成年人。无论是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写入未成年人缓刑条款,还是2012年刑诉法修正后的附条件不起诉和限制逮捕措施,可能都很难运用到12周岁至16周岁的未成年人身上。
因此,在专门教育、非刑事诉讼、非羁押、缓刑尚未落实到实处的情况下,监禁刑等刑事处罚成为直接上升为针对已满12未满14周岁未成年人罪犯的初次矫治方法。这种立法结构和司法处理规则显然与国际法理有一定距离。尽管《刑法修正案(十一)》已成既定事实,但这并不当然意味着其合理性。笔者认为,未来的中国刑事责任年龄及其相应规定,可以朝三个方向发展。第一,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起点问题,中国未来很大可能会像丹麦一样重新回到14周岁。第二,需要彻底地落实专门教育问题,优先考虑非刑事司法手段,将司法措施作为最后手段。第三,继续修正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激活附条件不起诉、非羁押和监禁替代措施,以最大利益原则为基本前提,加大未成年人立法,从而使监禁刑作为最后手段。
中国法学家和犯罪学家应当重视未成年人法制的国际法理,在充分理解和运用国际法规则基础之上,以科学和时代的视角完善国内立法和司法。笔者相信,中国的未成年人立法和司法实践经验,必将在未来某个时间段引领国际法规则。但实现这个宏伟目标的前提,自然是在国际法规则基础上贡献中国的法治智慧,而不是无视国际法规则或与国际法规则背道而驰。因此,认识当前中国未成年人法治是解决理论、立法、司法问题的关键,否则非刑法专业人士所营造和引领的刑法修正必然在历经弯路以后重回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