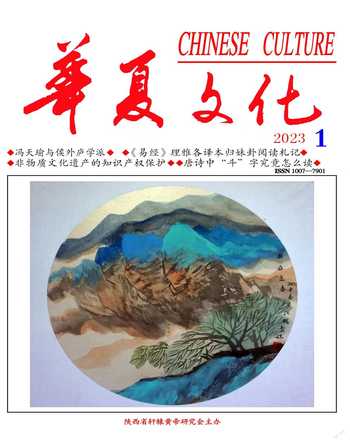从彳部看黄侃“治《说文》之方法”之“求相次”
李敬文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是我国语言学史上第一部按照部首编排的分析字形、说解字义、辨识声读的字典,以小篆作为目标字形,建构了严密的汉字构形系统,首创文字形音义贯通综合研究的方法,成为中国传统语言学的根基。
《文字声韵训诂笔记》纂集黄侃先生论学语录二百余条,蕴含深刻广博的语言文字学研究思想,提出一系列关于《说文》研究的方法论和结论,对学习研究《说文》具有指导意义。通过对《笔记》“治《说文》之方法”之七“求相次”进行闡释,并用这种方法对《说文·彳部》进行探究,可以发现《说文》本身的系统性。
一、黄侃先生“治《说文》之方法”之“求相次”
黄侃重视《说文》条例,《笔记》中关于《说文》研究和论述的记录繁多,对《说文》研究具有极大价值。其中“看《说文》三法”、“治《说文》之方法”、“《说文》之研究法有七”归纳了《说文》研读逐步深化的三层方法。“方法”平列八条,探求《说文》六书、经典使用、孳乳机制、引经、正篆和重文关系、声韵关系、编排顺序、谐声系统等,归纳了探究《说文》体例规律的途径。
其中“求相次”即探求《说文》的编排顺序,包括部首之间和内部辖字的次序。黄侃在段玉裁、王筠等前人基础上进一步补充:“《说文》字叙,大抵先名后事,排列皆有意义。其不以意义为次者,即以声音为次。”可知《说文》部内主要按照义的标准排列:首先列名词(名词又按照与部首字关系先近后远),其次列动词,再次列形容词(附属义类);除了义的标准,偶尔会按照声韵标准将音近字相次,或义、训的标准将近义词相次(先美后恶)。
二、求《说文·彳部》辖字相次
(一)部首“彳”:《说文》与新解
《说文》训“彳”为微小的步伐,像人的下肢三部分相连接的形象,徐锴、段玉裁等维护许慎的说解,并进一步讲解象形内涵,将“三属”解释为大腿、小腿和脚。
王筠《释例》根据实际应用情况对“彳”、“亍”作了新的说解,提出二者都是行字的省写,本应放在“行”字之后。这一新解为后学者所认同,清人罗振玉《增订殷墟书契考释》从甲骨文字形出发,提出“彳”、“亍”二字都是“行”(行道)的省写。今人就甲骨文、金文字形来探究基本认为“彳”与道路、行动有关,为“行”字的省写,如邹晓丽依据甲骨文、金文材料作新解:“用半个‘行表示行走之意,只作偏旁,单独使用只有‘彳亍,又写作‘踟蹰”(参见邹晓丽:《基础汉字形意释源》,中华书局2007年,第80页)。
可知许慎无法看到更早期、象形性较强的字形,依据篆文说解,因而进行了理据重构,但并不能因此就说《说文》的说解是完全错误的,对此我们既要看到古文字的系统,也要看到《说文》的系统,即王宁老师所说的“把《说文》整体系统成熟和古文字构形意图明确这两个方面的优越性结合起来”(《基础汉字形意释源》,序二)。
(二)彳部辖字
辖字首列“德”、“徑”,《说文》训“德”为登升,为动词,却放在辖字首位,其原因可能在于典籍实际应用中多用为名词。“徑”训为“步道”即步行的小路。
动词为彳部的主体,又可以大致分为几类:一是行走专名,如“復”(往來也)、“”(復也)等,“”训为“復”而列在其后,也体现了黄侃所说“以义同异为次”“训相联则最相近”等排列规律。二是行走状态,这一部分基本遵循美恶相次的原则,即先列表行走顺利的字,如“循”(行順也)、“彶”(急行也),又如“”(均训为“使也”),连绵词而相次,体现了“两字为名之物,必使相从”的规律;再列表行走艰难的字,如“後”(遲也)、“徲”(久也);后列与行走相关的行为,这一部分与行走之意关系更远,如“得”(行有所得也)、“律”(均布也)。末尾列反文“亍”(步止也),遵循“反文居末”的规律。
(三)小结
彳部下辖三十六字,基本遵循以类相从的条例,大致可以分为名词、动词、反文,动词又基本按照先实后虚原则分为行走专名、行走状态、行走相关行为,其中同一义类的字“训相联则最相近”,训释相同或为递训关系的字相次。但这种区分并不十分清晰,中有杂错。可知《说文》的编排次序并不是绝对的。
三、求《说文·彳部》与前后部首相次
(一)彳部与前后部首据形相次
彳部前后部首基本都从彳,也都有行走的意思。段注对彳前后部首的形体关系作了沟通:“彳蒙辵从彳而次之,廴又蒙彳而次之,?蒙廴而次之,兼蒙止。行蒙彳部彳、亍二文而次之。”([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766页)值得注意的是,部首有时不仅与一个部首存在承接关系,如“?蒙廴而次之,兼蒙止”,“?”与“廴”、“止”两个部首均具有形体关系。根据段注为这一组部首作系联图如下:
可知这一系列部首的形体顺序不是线性的,而是多维网状的,这一组部首典型反映了《说文》编排的顺序原则:首先根据形体,据形系联,到“牙”又凸显意义,“齿”因为有“止”所以系联到一起,“牙”、“齿”无形体关联,依据意义来系联。部首中也有形、义均无关的特殊编排情况,如走部前一部首为“哭”,形体不相近,段注为“有形不相蒙者此是也”。
(二)彳部与前后部首构形相通
“彳”与前后部首不仅在字形上相近,据形索义也都有行走的意思,如:“辵”为“彳”前部首,从彳从止,《说文》训为“乍行乍止也”;“廴”为“彳”后部首,从彳引之,《说文》训为“长行也”;“?”从廴从止,《说文》训为“安步??也”;“行”从彳从亍,《说文》训为“人之步趋也”。
这些部首辖字也多有重文或体,黄侃《说文同文》彳部整理了部分异体字,说明“彳”与其他部首的关系:“彳同蹢、?、蹐,又同蹏。徑同徎。往同迋,去。忂同躣。同馺。同命,借为俾。徬同傍。徯同、匸。待同竢、偫。同丨。同遲。很同?、艮、詪。?同踵。御同駕,古文。亍即足字,同逗、、躅”(黄侃、黄焯:《说文笺识四种·说文同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9页)。邹晓丽论述了这一部分部首的通用关系,提出“辶”由“止”“彳”“走”“辵”演变而来,在古代作偏旁时常通用,如“跃”、“?”、“趯”是异体字;“廴”是“辵”“走”的异体字,由“彳”的末一笔拉长而成,所以读音同“引”(《基础汉字形意释源》,第82页)。徐复、宋文民也提出“甲骨文彳字与行、辵、廴等通用不分,后乃加以区分,各有专属”(徐复、宋文民:《说文五百四十部首正解》,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28页)。
可知走、止、癶、辵、彳、廴、?、行、足等在最初造字时,构形功能上具有互通的特点。不同的形符可能有相同的表意功能,如 “止” 与 “足” 都可以用来表示脚的某个部位,“辵”、“彳”都主要表示走路。许慎对这些异体字划分归类,其构形系统与古文字系统不同,存在人为的构意分化。
结语
黄侃先生在前人总结的基础上发展了《说文》部内辖字的排列条例,包括以意义为次而先名后事,不以意义为次者即以声音为次,以及以义同异为次而训相联相近。
《说文》彳部辖字基本遵循以上条例,彳部与前后部首的形体系联呈现网络状,体现出《说文》部首“据形系联”与“据义系联”同时进行。行走义部首重文体现出许慎对其进行了人为的构意分化。对此我们既要看到古文字的系统,也要看到《说文》的系统;不应仅作个体性研究,更需要整体性看待。
(作者:北京市海淀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邮编1008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