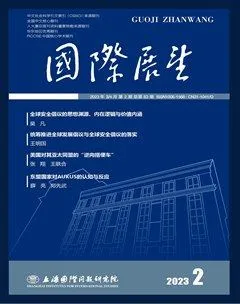阿富汗和伊朗跨界河流治理的双重困境
孙德刚 章捷莹
【內容摘要】 当前,国际水资源争端升级,跨界河流治理成为全球治理的重点和难点。跨界河流治理有霸权护持、议题补偿、制度嵌入和身份建构四种模式。同为伊斯兰国家、社会同质化、经济联系密切的阿富汗和伊朗之间的水资源争端白热化,其背后是两组结构性矛盾。一方面,上游弱国阿富汗拥有地理区位优势,掌握开发主动权;下游强国伊朗拥有政治经济优势,掌握外交主动权。权力平衡是两国跨界河流治理困境的内部根源。另一方面,美国占领阿富汗后为遏制伊朗而支持阿富汗,印度出于对抗巴基斯坦的目的而支持阿富汗,第三方的选边站队导致水资源争端国际化。域内外大国的权力斗争是两国跨界河流治理困境的外部原因。要破解上下游、域内外双重困境,两国应在跨界河流治理中对内抑制资源民族主义,对外获得必要的国际发展和安全援助,从利益共生到安全共生,从单边治理到全流域共治,建立跨界河流命运共同体。
【关键词】 跨界河流治理 命运共同体 全球治理
【作者简介】 孙德刚,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主任、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上海 邮编:200433);章捷莹,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 邮编:200433)
【中图分类号】 D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568-(2023)02-0079-23
【DOI编号】 10.13851/j.cnki.gjzw.202302005
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人口快速增长、全球变暖加速和水污染日趋严重,加上跨流域治理赤字、水资源分配谈判效率低下等问题,世界人均可用淡水量继续呈下降趋势。水资源总量不足与分布不均是国际水冲突的客观因素。在工业化不断加速、城市化不断推进、工农业用水量不断增长的背景下,世界面临日益严重的水资源短缺问题。从双边层面来看,跨界河流还被赋予特殊的文化含义,如成为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象征,由此资源民族主义成为地区水冲突的主观因素。在跨界河流水资源博弈中,捍卫水权成为各国国内政治的动员工具,也是执政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能力与意志的象征。 于是,低政治领域的跨界河流治理问题上升为高政治领域的主权和国家安全问题,使谈判陷入僵局,甚至引发外交危机乃至水战争。 从地区层面来看,水资源的匮乏与长期存在的族群矛盾、宗教冲突和领土纠纷等因素相互叠加,加之域外大国介入,导致区域内跨界河流治理日益复杂化,成为全球安全治理与发展治理的难点。
阿富汗与伊朗同为西亚伊斯兰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历史传统、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方面具有同质性。 阿富汗与伊朗在经贸领域也存在密切的共生关系。 美军占领阿富汗后,超过450万阿富汗难民涌入伊朗,进一步密切了两国的人员往来关系。然而,这两个同质化和依存度很高的国家在跨界河流治理领域的合作却裹足不前,双方在这方面的谈判陷入僵局,争端久拖不决。2001年美国推翻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后,伊朗多次寻求同阿富汗新政府就赫尔曼德河与哈里河的水资源开发及利用开展谈判,但阿富汗反应冷淡,甚至在上游单方面启动大规模水电站项目,不愿同伊朗实现跨界河流的共同治理;伊朗也采取反制行动,驱逐阿富汗难民,威胁暂停阿富汗中转贸易和电力供应。
针对阿伊在跨界河流治理中面临的难题,既有研究主要从“谈判能力说”“非对称权力说”和“国际环境塑造说”三个维度进行分析。首先,“谈判能力说”认为,国家谈判能力不足影响跨界河流治理效能。一般而言,跨界河流治理有助于上下游国家共同维护生态环境、开发河港、发展国际航运、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 但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各国对相对收益的预期依赖于对等的外交谈判。 弱国阿富汗缺乏与强国伊朗开展水权谈判的议价能力,担心过多让渡水权会遭到国内民众批评,导致两国迟迟未能启动水资源谈判。 与伊朗相比,阿富汗缺乏训练有素的水文气象专家和国际法知识渊博的外交官,而且连年内战导致阿富汗水文信息严重缺失,这是阿富汗政府不敢同邻国开展水权谈判的主要原因。 其次,“非对称权力说”认为,上下游国家的权力分布影响跨界河流治理。跨界河流的自然与社会条件分别塑造了两类“水霸权”,前者是自然环境赋予上游国的天然区位优势,后者源于流域内国家经济和军事实力。就前者而言,地理位置赋予的优势地位,使上游国家即使处于结构性权力的劣势地位,也可以拒绝下游强国的强制性合作。 就后者而言,流域强国可以通过强制性霸权、功利性霸权、规范性霸权和意识形态霸权等手段,胁迫弱国参与由霸权国主导的合作机制。 再次,“国际环境塑造说”认为,国际环境塑造格局,格局影响跨界河流治理。文森特(Thomas Vincent)和华纳(Jeroen Warner)提出,阿富汗得益于多极化的国际环境,抓住了伊朗因核问题而遭国际社会孤立的机会窗口,引入第三方力量,利用美国和北约的军事与财政支持,平衡伊朗的影响力,维持其在哈里河上修建水电站的单边开发权。
以上国内外学者对阿富汗和伊朗跨界河流治理研究取得了初步成果,但未能解释为什么两国跨界河流谈判迟迟未能重启,而其他地区的跨界河流治理却实现了机制化。同样因跨界河流而形成上下游关系,为何欧洲的莱茵河、北美的科罗拉多河、南美的亚马孙河等形成了流域内共同开发机制,而阿富汗和伊朗至今难以推进国家间水资源谈判与河流治理?中亚、南亚、西亚和非洲地区的跨界河流流域不仅缺少稳定的合作机制,而且常因水源分配与水电站建设等问题而引发外交危机。
本文擬对阿富汗和伊朗的跨界河流争端进行过程追踪,探讨两国难以开展实质性合作的根源,分析两国水争端安全化和国际化背后的双重困境。
一、上下游博弈:阿伊跨界河流争端的内部根源
阿富汗是多条跨界流域的上游国家,拥有优先开发河流的水权力(hydropower)。阿富汗境内有三条主要的跨界河流,分别是流向巴基斯坦的喀布尔河(Kabul River)、流向伊朗的赫尔曼德河(Helmand River)以及流向伊朗和土库曼斯坦的哈里河(Harirud River)。 2001年美军入侵阿富汗后,卡尔扎伊(Hamid Karzai)和加尼(Ashraf Ghani)领导下的阿富汗政府均未能同邻国就跨界流域水源分配问题展开实质性谈判,反而单方面推进跨界河流的水电站项目,伊朗则不断向阿富汗提出抗议和警告。赫尔曼德河与哈里河是阿伊之间最重要的跨界河流。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生态环境的恶化与人口快速增长,两国为满足国内粮食消费均大力发展灌溉农业,积极推进水电站项目,造成水资源缺口日益增大。两国未能就跨界河流水资源分配与合作开发达成协议,成为地区安全隐患。
(一)阿伊关于赫尔曼德河流域的水资源争端
鉴于赫尔曼德河 对沿岸居民生活与生产用水的重要价值,阿富汗政府早在1947年就开始对赫尔曼德水系进行水文研究,1949年11月成立赫尔曼德河流域管理局(HVA),综合开发该流域的经济价值。 阿伊围绕赫尔曼德河的水资源争端由来已久。伊朗巴列维(Mohammad RezāShāh Pahlavi)政府与以穆罕默德·查希尔(Mohammed Zahir Shah)为国王的阿富汗政府曾商讨该河水量分配问题,但未达成共识。1948年,在美国的斡旋下,两国同意设立赫尔曼德河三方委员会,研究赫尔曼德河水文信息并提出争端解决方案。1951年,该委员会发布报告,建议伊朗在赫尔曼德河水域的份额为每秒22立方米。伊朗方面认为该水量不能满足其需求,分配方案偏袒上游国家阿富汗,故拒绝了美方的调解。
此后,两国进行了多轮磋商,最终达成了水资源分配方案:伊朗向阿富汗提供港口使用权,为阿富汗转口贸易提供便利,阿富汗同意增加伊朗的水份额。1973年,双方签订了《阿富汗—伊朗赫尔曼德河水条约》(Afghan-Iranian Helmand River Water Treaty)。条约规定:下游国家伊朗可从赫尔曼德河获得平均每秒26立方米(相当于每年8.11亿立方米)的水量,其余水量归阿富汗支配。作为回报,伊朗则须向阿富汗开放境内的阿巴斯港(Abbas)和恰巴哈尔港(Chahbahar)的使用权,为内陆国阿富汗提供国际贸易走廊。 为提高双边制度化合作水平,两国同意成立赫尔曼德河委员会,共同处理水量监测与分配问题。
然而,阿伊未能形成长效合作机制。首先,两国国内局势相继陷入动荡,包括1973年阿富汗政变、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及苏联入侵阿富汗、1994年塔利班的崛起、2001年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等,双边水合作失去稳定的政治保障。其次,条约的执行难度大。《阿富汗—伊朗赫尔曼德河水条约》第四条为“灵活性条款”,即河流水量低于正常年份时,阿富汗有权减少分配给伊朗的份额。水量检测等技术性问题一旦被政治化,上游国家阿富汗便拥有与邻国伊朗讨价还价的能力,如以缺乏水文数据为借口拖延谈判,甚至拒不履行条约的规定。这为两国愈演愈烈的水争端埋下隐患。
1998年,阿富汗塔利班对哈扎拉人、塔吉克人和乌兹别克人实施了报复性打击,造成至少2 000人死亡,其中11名伊朗外交官和记者遇害。 伊朗与塔利班政权的关系迅速恶化,赫尔曼德河水源分配问题再度凸显。受两国关系恶化的影响,赫尔曼德河流入伊朗境内的水量大幅减少,塔利班一度收紧赫尔曼德河上的卡贾基大坝(Kajaki Dam)向下游的供水,切断流往伊朗的水流,进一步引起伊朗的不满和抗议。2000年前后,伊朗遭遇史上最严重干旱。在上游限水与下游干旱的双重冲击下,哈蒙湿地的生态系统遭遇历史性危机,湖水干涸导致渔业资源大幅下降,居民失去生计,下游流域的沙尘暴波及124个村庄,造成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 为此,伊朗在联合国控诉阿富汗塔利班阻断赫尔曼德河,要求联合国采取强制措施,敦促塔利班保障伊朗公民依法享有的水权。 2001年塔利班政权垮台后,伊朗立即开展外交攻势,同阿富汗临时总统哈米德·卡尔扎伊举行谈判,呼吁阿富汗认真履行《阿富汗—伊朗赫尔曼德河水条约》,保证向伊朗提供充足水量。2002年12月卡尔扎伊政府恢复河流供水,但伊朗认为阿富汗并未提供足额水量。阿富汗则援引条约的“灵活性条款”,称季节性干旱和气候变化导致流入伊朗境内的水量不足。 两国围绕跨界河流的水资源争端仍未尘埃落定。
鲁哈尼(Hassan Rouhani)担任伊朗总统后,伊朗频频利用阿富汗难民问题向阿政府施压,敦促其重新修订《阿富汗—伊朗赫尔曼德河水条约》,商讨哈里河水分配问题。阿富汗政府则以水资源谈判为诱饵,呼吁伊朗维护阿富汗难民的权利。 2019年加尼在阿富汗总统大选中获胜后,伊方不支持阿方新总统,称支持加尼的条件是两国签署战略合作文件,重新分配赫尔曼德河水资源。
2021年,莱希(Seyed Ebrahim Raisi)担任伊朗总统,阿富汗塔利班重新掌权,双方就跨界河流治理问题再度进行接触。伊朗试图利用阿富汗局势动荡和塔利班新政权未获得国际承认的“软肋”,迫使阿富汗让步以获得更有利、更稳固的水资源分配权。然而,尽管塔利班已承诺将同伊朗就赫尔曼德河和哈里河水资源重新谈判,展现出善意姿态,但迄今谈判未能启动,合作成效甚微。2022年1月,因赫尔曼德河水源不足,伊朗爆发反阿富汗示威游行,阻断了与阿富汗的边境贸易通道。 同月,伊朗扎博尔市民众不满阿富汗限水政策,袭击了阿富汗商贸车队,要求塔利班政府给予下游更多水源。 2022年7月,伊朗总统莱希要求有关部门尽快与塔利班政府沟通,商讨两国合理共享流域水资源问题。塔利班政府一方面积极回应,另一方面又重启卡贾基大坝二期工程, 加重了伊朗对水安全的疑虑。
综上所述,阿伊在赫尔曼德河流域的水争端持续了数十年。伊朗指责阿富汗将赫尔曼德河“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和“阿富汗的私人产品”,但阿富汗否认损害伊朗水权。 因水博弈造成的不信任,加上阿富汗与伊朗政府的不断改组,水资源谈判遥遥无期。塔利班政府认为时间在自己一边,故对水资源谈判采取拖延战术。但是其落后的水资源管理方式、低效的水资源利用率和相对不足的谈判能力,使之倾向于单方面开发水资源,满足国内灌溉用水,同时利用水力发电弥补国内电力缺口。
(二)阿伊围绕哈里河流域的水争端
哈里河发源于阿富汗中部山区,向西流入伊朗境内,随后向北形成伊朗与土库曼斯坦的界河,最终流入土库曼斯坦境内的卡拉库姆沙漠。 该河全长1 124公里,42%的流域位于阿富汗境内,年均流量约55立方米/秒。 作为阿富汗境内主要水系之一,哈里河流域承载着农业灌溉和水力发电的双重任务。2016年,印度援建阿富汗的兼具发电、灌溉功能的萨尔玛大坝(Salma Dam)开工建设。该大坝被称为“印度—阿富汗友谊大坝”,灌溉面积30.09万公顷,占阿富汗灌溉耕地总面积的9%,惠及人口200万人,成为哈里河上游第一大坝。 阿富汗新修的这一大坝引起下游国家伊朗和土库曼斯坦对水资源不足的担忧。哈里河是伊朗和土库曼斯坦在萨拉赫斯(Sarakhs)边境地区共同修建的友谊大坝的唯一水源,也是伊朗边境城市萨拉赫斯和马什哈德(Mashhad)的主要饮用水来源。伊朗在地表水供应上对阿富汗依存度很高。萨尔玛大坝投入使用使哈里的水流量减少了约62%,导致伊朗和土库曼斯坦在下游的友谊大坝的可用水量从每秒507立方米减少到每秒215立方米。 水坝的修建破坏了上下游国家的政治关系,导致信任赤字。哈里河流域上下游国家竞相修建水坝、争夺水源,尤其是阿伊未能就水资源利用与分配签署全流域协议,两国围绕哈里河水资源分配问题始终僵持不下。
2016年阿富汗萨尔玛大坝竣工后,阿富汗又于2019年启动帕施丹大坝(Pashdan Dam)建设。 大坝启动修建以来,伊朗将阿富汗难民问题、过境贸易问题、电力供应问题与哈里河水分配利用问题进行捆绑,以此在谈判中向阿政府施压,甚至纵容当时的反政府组织塔利班破坏大坝建设,导致水争端问题上升为国家安全问题,解决难度进一步增大。
纵观阿富汗与伊朗跨界河流水源争端的百年历史可以发现,水资源的稀缺性和两国依靠水源灌溉农作物、推动水力发电的同质性是引发争端的客观原因;两国外交龃龉和政治互信缺失是争端的主观原因。一方面,流域小国往往利用多边主义对流域大国形成制度约束力,如南美国家通过多边制度约束巴西。但是阿富汗和伊朗的跨界河流争端主要涉及这两个国家,不像亚马孙河流域涉及多个主要国家,故无法形成亚马孙河流域治理那样的制度嵌入模式。另一方面,尽管阿伊两国都是伊斯兰国家,但是伊朗以什叶派穆斯林为主,阿富汗掌权者(塔利班、卡尔扎伊和加尼政府)都以逊尼派普什图人为基础,与伊朗关系密切的哈扎拉人和塔吉克人处于阿富汗权力的边缘位置,导致阿伊两国领导层貌合神离,相互猜疑,未能像欧洲国家治理莱茵河那样建立身份建构模式。
二、第三方介入:阿伊跨界河流争端的外部原因
近百年来,域外大国的军事占领导致阿富汗局势持续动荡,安全问题不断外溢到邻国,伊朗首当其冲。对伊朗而言,阿富汗政治稳定有助于两国通过合作解决常年困扰伊朗边境的难民、毒品走私与水资源争端等问题。同时,敌对国家在阿富汗的军事存在会威胁伊朗的国家安全,故伊朗必须确保阿富汗避免受到域外大国的军事控制。 阿富汗则开展第三方外交,引入主要大国及一些国际组织的力量,形成多元平衡,防止受制于伊朗。巴基斯坦是印度的首要竞争对手,印度通过与阿富汗建立特殊关系对巴基斯坦形成“两面夹击”,在水资源争端中客观上站在了阿富汗一边。同时,伊朗是美国在中东的头号敌人,被美方认定为中东地区有能力挑战美国主导权的“反体系”国家,进而采取诸多敌对行动。 阿富汗是美伊角力的“中间地带”,伊朗反对美国占领阿富汗,美国对伊朗干涉阿富汗内政保持警惕,反对伊朗在跨界河流争端问题上胁迫阿富汗。在跨界河流争端问题上,为达成同阿富汗的合作,伊朗采用“议题补偿”和“强制合作”双重手段。但是,第三方行为体美国和印度的介入,削弱了伊朗在水问题上的影响力和谈判优势。其结果是阿伊两国的跨界河流爭端升级为三边博弈,跨界河流争端国际化和多边化,增加了阿伊就跨界河流治理问题进行谈判的难度。
(一)域外大国的介入与伊朗“议题补偿”策略的失效
“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美国以阿富汗塔利班包庇“基地”组织为由出兵阿富汗,推翻了塔利班政权。在美军占领下,阿富汗实现民族和解的关键是伊朗支持的北方联盟与美国支持的普什图族临时政府达成妥协。 阿富汗塔利班是美国和伊朗的共同敌人。由于担心塔利班卷土重来,伊美暂时缓和对立,在联合国举行的阿富汗问题波恩会议上密切合作,共同支持普什图族出身的卡尔扎伊担任总统。 然而,随着塔利班的式微,美国和伊朗的矛盾上升。尽管伊朗政府宣布全力支持美国反恐,但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表示,美国不接受伊朗温和派总统哈塔米(Seyyed Mohammad Khatami)在阿富汗问题上的“示好”姿态,仍将伊朗视为“邪恶轴心国”。
2002年8月,阿伊两国在赫尔曼德河水资源问题上达成共识。阿富汗宣布加大对下游供水,但仅十天后,在美国的压力下,阿富汗又切断了赫尔曼德河的水流。 卡尔扎伊政府既亲美,又不愿公开得罪伊朗,故向伊朗推脱是季节性降雨不足导致的断流。然而直到2002年年底,流入伊朗境内的水量依然没有达到其预期。 阿伊水分歧的背后是美伊结构性矛盾,两国在阿富汗展开激烈的安全竞争。
2004年9月,阿伊双方召开了修订《阿富汗—伊朗赫尔曼德河水条约》的会议。伊朗凭借自身的实力优势,收容来自阿富汗的400多万难民,以及作为阿富汗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和最重要的贸易中转国地位,以向阿富汗提供发展援助和能源供应为条件,换取阿富汗保障伊朗的水资源供应。然而由于美国的破坏,会谈未取得实质性进展,但这并未能阻止伊朗对阿富汗进行“议题补偿”的努力。伊朗政府在国际会议中支持阿富汗战后重建,增加对阿经济援助,秘密资助时任总统卡尔扎伊及其他高官,希望换取阿富汗实权派精英对伊朗水权的尊重。 2013年,伊朗向阿富汗援助了总价值达1 000万美元的两台购自德国的发电机组,并承诺将扩大对赫拉特省和尼姆鲁兹省的电力出口。作为“议题补偿”,伊朗希望阿富汗政府认真履行《阿富汗—伊朗赫尔曼德河水条约》,避免因水资源争端而爆发边界摩擦。 然而,尽管伊朗提出了多议题联动的合作倡议,但在美国和印度的干扰下,阿富汗依然选择拖延战术,拒绝伊朗提出的增加跨界河流水源的诉求。
美国和印度对阿富汗的安全和经济援助,增加了阿富汗与伊朗讨价还价的筹码。第一,美国与伊朗的秩序观不同,在巴以、伊拉克、阿富汗和海湾安全秩序等问题上,美伊存在权力竞争。针对伊朗通过议题联系与阿富汗进行利益交换的倡议,美国发出警告,称伊朗图谋在阿富汗推行“门罗主义”,将美军和北约军队赶出阿富汗。美国参与阿富汗水利设施建设,防止阿富汗在经济上依附于伊朗。美国还帮助阿富汗政府在赫尔曼德河与哈里河流域规划大型水电站,修建了赫尔曼德河流域储水量与装机容量最大的卡贾基大坝。 2004年,美国国际开发署投资5亿美元用于卡贾基水电站的扩建工程,成为美国在该国单次投入最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该投资既有助于美军维护阿富汗局势稳定,又避免阿富汗在跨界河流问题上屈服于伊朗,起到了分而治之、一箭双雕的作用。阿富汗战争结束后,美国对阿富汗的发展援助也逐年增加。2011年美国对阿富汗的经济援助达13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其中用于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经费达6.5亿美元,起到了进一步离间阿伊的作用。 2016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又援助阿富汗三台涡轮机并投入使用,使卡贾基水坝的储水量达17.15亿立方米,装机容量高达52.5兆瓦。美国的援助使阿富汗稳固了上游的优势,“稀释”了伊朗对阿富汗进行“议题补偿”的各类倡议的效果。
第二,根据2014年《世界水法案》,美国将阿富汗列为水安全领域高优先地位国家,给予阿富汗更多的经济援助和政策倾斜,同时鼓励芬兰、日本、法国等域外国家加大对阿富汗水资源开发力度,削弱伊朗的地缘和传统影响力。 在国际组织层面,美国于2022年发布《白宫全球水安全行动计划》(White House Action Plan on Global Water Security),称美国将与欧盟、七国集团、二十国集团和联合国等多边组织合作,以多边合作的方式改善包括阿富汗在内的伙伴国的基础设施,维护阿富汗这个“非北约盟友”的水安全。 在美国的鼓励下,欧盟、英国、德国等成为阿富汗的主要援助方。
第三,印度作为地区大国对阿富汗提供的援助也弱化了伊朗“胡萝卜”政策的吸引力。进入21世纪以来,巴基斯坦和印度、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相继爆发多起边境冲突事件,印度加强同阿富汗合作以孤立巴基斯坦,间接阻碍了阿富汗与伊朗的水合作。2002年,印度宣布斥资7.5亿美元参与阿富汗基础设施重建。 印度出资在哈里河上游建设萨尔玛大坝,因为该大坝的建成将截留大量本该流入伊朗的水源,使伊朗与土库曼斯坦的友谊大坝面临无水可储的窘境,此举引发了伊朗的强烈反对。2021年2月,出于遏制巴基斯坦的目的,印度和阿富汗签署谅解备忘录,印度将帮助阿富汗再建设一座大坝,即拉兰德大坝(Shahtoot Dam),以解决喀布尔用水紧张问题。该大坝计划投入资金2.36亿美元,预定三年完工,届时将为200万阿富汗人提供饮用水源,增加灌溉用水并提供电力。 印度与伊朗关系友好,但印度与阿富汗在水资源领域的合作客观上影响到下游国伊朗的利益。
通常,资金充足的上游国家更有能力采取单方面河流开发行动,而阿富汗虽有意愿却缺乏建设水电项目的技术与资金。在此情况下,经济实力雄厚的下游国可通过技术转让和经济援助的方式获得上游国的水权承诺,实现上下游共同开发。然而,美、印等国的发展援助,使阿富汗获得了必要的资本和技术,削弱了伊朗通过“议题补偿”同阿富汗共同开发跨界河流的吸引力。
(二)域外大国介入与伊朗“施压胁迫”策略的失效
在域外大国帮助下,阿富汗在喀布尔河、哈里河与赫尔曼德河流域兴建了众多水利基础设施。 其在上游的单边行动不可避免地招致下游伊朗的不满,伊朗官方表态中充满对阿富汗水电项目的担忧和警告,认为阿富汗水电站建设威胁其国家安全。伊朗在“议题补偿”策略失败的情况下,采取了一定范围的“强制合作”措施。伊朗具有实施“强制合作”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兩国经济体量上的不对等性;二是经济相互依赖的非对称性,表现在伊朗是阿富汗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和最重要的国际贸易中转国,而阿富汗对伊朗的贸易占比较小;三是伊朗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伊朗的这些优势赋予了其对阿富汗经济制裁和政治胁迫的潜在能力。
第一,针对阿富汗在上游的单边开发行为,伊朗从中央到地方一致表达了强烈谴责,以外交抗议和政治胁迫的方式对阿富汗政府施压。 2015年10月,伊朗时任外长扎里夫(Mohammad Javad Zarif)指责阿富汗单方面开发上游水资源,认为卡玛尔汗大坝将严重限制赫尔曼德河流入伊朗锡斯坦—俾路支省的水量。 该省既是伊朗国内最贫困的地区之一,也是逊尼派穆斯林聚居区,缺水会带来严重的社会危机。一旦因水源不足而出现渔业减产或耕地荒漠化,当地极端组织就会借机制造混乱,发动恐怖袭击。 2017年,时任伊朗总统鲁哈尼在一次国际会议上谴责阿富汗政府在未开展环境评估并知会伊朗的情况下,单方面开发上游水资源,认为此举影响了伊朗水安全。随后,阿富汗有关官员强硬回击了鲁哈尼,强调阿富汗经济严重依赖农业,水资源开发利用有助于促进本国经济发展,阿富汗是在国家利益和国际公约的基础上合理开发水资源。
第二,伊朗一度通过支持塔利班来反制阿富汗政府,但收效甚微。伊朗对阿富汗政府对美、印的“一边倒”政策表示不满,反对驻阿美军支持伊朗俾路支斯坦省的叛乱武装,因此在美军占领阿富汗后放弃了早期与阿富汗塔利班的对抗策略,转而暗中支持塔利班某些派别,制衡阿富汗政府和驻阿美军。 在此过程中,阿富汗政府建设的水利项目成为塔利班武装袭击的重点目标。 2020年10月,塔利班袭击了卡玛尔汗大坝,造成6名警备人员死亡、3人受伤,激起了当地居民强烈的反伊朗情绪,甚至爆发民众抗议活动。尽管伊朗政府否认是幕后推手,但阿政府宣称,“赫尔曼德河是我们的,国家将不惜一切代价捍卫大坝、抵御入侵。” 阿富汗政府动员了数以百计的当地青年,扩充地方安全部队,鼓励民兵武装拿起武器保卫大坝等国家重点基础设施。塔利班武装袭击水坝工程的行为,使阿伊间的信任度进一步降低,伊朗的“强制合作”策略失效。
为了防止跨界河流治理中伊朗对阿富汗实施经济制裁和政治胁迫,美国及其盟友加大了对阿富汗的经济援助力度。美军占领阿富汗以来,美国加大经济援助力度,助力阿富汗基础设施重建。 美国也加大对阿经济和社会“输血”,但阿富汗发展问题积重难返,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国民经济体系。2011年,美国提出“新丝绸之路”计划,推动阿富汗、巴基斯坦同中亚和南亚地区的互联互通,为阿富汗经济转型提供契机,减少阿富汗对伊朗的经济依赖。 此外,国际开发协会、亚洲开发银行、欧盟、德国、英国、日本、瑞典、加拿大等组织和国家均向阿富汗提供了大量的援助,削弱了下游强国伊朗对阿富汗的强制能力。
为阻止伊朗向阿富汗军事渗透,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国还加强对阿军事援助。印度也向阿富汗提供了大量军事和经济援助,是仅次于美国、日本、英国、德国的第五大对阿援助国,印度还一度向反塔利班的北方联盟提供武器装备,派出军事顾问。 尽管伊朗和阿富汗实力悬殊,但阿富汗两任民选政府凭借美国等西方国家和印度的支持,使伊朗难以实施政治胁迫或诉诸军事手段解决跨界河流争端。 通过军事和经济援助,大国在阿富汗形成了多元平衡,以北约、上海合作组织为代表的地区组织,以美国、俄罗斯、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大国,以沙特、土耳其、哈萨克斯坦为代表的地区强国等在阿富汗频繁互动,使伊朗难以在阿富汗形成垄断性权力,无法通过“强制合作”迫使阿富汗在跨界河流问题上妥协。
显然,伊朗、阿富汗和域外第三方的博弈形成了复杂的关系,尤其是美国与其他域外国家的经济和军事介入制约了伊朗通过“议题补偿”与“强制合作”迫使阿富汗在水资源方面让步的效果,成为阿伊跨界河流治理赤字、水争端国际化的外部原因。伊朗要求阿富汗重启赫尔曼德河与哈里河水资源问题谈判,阿富汗在外部大国的默许下采取拖延战术,对伊朗的供水口惠而实不至。
因此,在第三方介入的背景下,伊朗的“议题补偿”和“强制合作”方式均难以产生实际效果。一方面,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和印度提供的经济援助,伊朗难以将双边贸易额、国际中转贸易和能源供应转化为跨界河流的激励手段。另一方面,阿富汗虽是弱国,但占据上游的优势地理位置;伊朗虽是地区强国,但却处于下游的劣势地理位置,在外部大国的军事援助下,伊朗难以建立“水霸权”,无法像美国围绕科罗拉多河治理那样,依靠绝对权力优势建立“霸权护持模式”。
三、阿伊跨界河流治理的双重困境分析
西亚、北非地区淡水资源不足全球的1%,水资源的稀缺与用水量逐年增加导致上下游国家的水争端长期得不到解决。 受资源民族主义和水资源安全化的影响,各国都将水资源视为执政合法性和国家安全的重要标志,国家间对水资源的争夺常常导致冲突的国际化和多边化。 尼罗河、约旦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赫尔曼德河与哈里河等跨界河流成为中东河流治理的难题。伊朗同阿富汗的水争端主要集中在赫尔曼德河与哈里河流域。按照学界对水资源稀缺性与合作可能性的“倒U型”曲线理论,与人均可再生水资源仅1 571立方米的下游国家伊朗相比,人均水资源占有量1 758立方米的上游国家阿富汗更有推进跨国水资源谈判的动机。 在跨界河流争端中,下游伊朗处于被动地位。与巴基斯坦同阿富汗存在“杜兰线”争议不同,伊朗与阿富汗不存在悬而未决的领土争端。同时,鉴于两国在经济体量、贸易依存度和军事实力等方面的巨大差距以及伊朗对阿富汗的经济、文化影响力和在难民问题上的话语权,伊朗和阿富汗的跨界河流合作本应取得进展,或以广泛的议题联系为基础开展水权合作,或依托伊朗的实力迫使阿富汗在水资源谈判上妥协。
(一)阿伊跨界河流治理的上下游困境
对伊朗而言,主动发起与阿富汗的跨界流域合作是其对阿外交的重中之重。由于地下水的过度开采和地表水的跨国分布,伊朗国内缺水问题日益严峻。 水资源匮乏、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和人口的迅速增长导致伊朗严重的环境危机,影响了伊朗的粮食安全和政治社会稳定。20世纪90年代末期,由于阿伊两国关系恶化,塔利班政府曾切断赫尔曼德河向下游的供水,导致伊朗锡斯坦—俾路支斯坦省的哈蒙湿地出现严重的湖水干涸危机与次生灾害。 因此,伊朗迫切希望改善同阿富汗的双边关系,保护伊朗东部逊尼派穆斯林聚居区生态环境,防止水资源匮乏引发当地民众的分离主义情绪。
伊朗与阿富汗的非对称权力关系和非对称上下游关系是双方安全困境的内部根源。按照有限领土主权原则的《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阿富汗作为经济发展落后的上游国,开发跨界河流应以不对下游国“造成重大损害”为前提,但尚处于较低发展水平的阿富汗无法为其水利开发行动对下游国造成的损害提供合理公平的补偿。 《阿富汗—伊朗赫尔曼德河水条约》的关键条款模糊,在缺乏多边机制约束的情况下,阿富汗担心同伊朗开展域内水合作,可能会使本国处于不利的谈判地位。 因此,阿富汗缺乏同伊朗开展水合作、重启条约谈判的意愿。在两国的跨界流域合作中,阿富汗是既得利益者,掌握主动权;伊朗是利益受损者,在外交上更加积极主动。
美国推翻塔利班政权后,伊朗积极参与阿富汗国家重建,不仅在军事和财政上援助北方联盟,而且帮助阿富汗建立過渡政府,以期与阿富汗在跨界河流问题上形成利益共同体。伊朗多次向阿富汗政府提供援助,如在2002年关于阿富汗重建的东京会议上认捐5.6亿美元,在2006年的伦敦会议上认捐1亿美元,主要用于阿富汗赫拉特省的基础设施重建。 作为在阿富汗投资的一部分,伊朗还帮助阿富汗建设清真寺、学校和新闻机构,并接收来自阿富汗的留学生,对阿富汗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 伊朗对阿富汗的军事、经济优势以及经济与文化影响力,都是其迫使阿富汗在水权方面妥协的筹码。
阿富汗境内水资源相对丰富,但由于长期战争造成水利设施破坏,而且其境内河流又主要依赖季风与高山融雪补给,淡水资源利用率低,缺乏储存与节水技术,使阿富汗同样面临严重的水资源短缺问题。 数十年的内战使阿富汗的灌溉和水力发电等生产性基础设施几乎处于崩溃状态,2018年阿境内的790万公顷耕地中只有360万公顷得以灌溉,同时有80%的电力依靠从邻国进口。 阿富汗国内水利设施的灌溉能力不足迫使当地居民改种耐旱的罂粟,导致阿富汗成为区域毒品泛滥的源头。 因此,为使更多耕地得到灌溉,并满足国内用电需求,阿富汗历届政府都重视境内河流的水利工程建设,优先满足国内的用水需求。
阿富汗与伊朗同为发展中国家,均面临粮食安全问题,阿富汗97%、伊朗80%的跨界河流水资源用于农业灌溉。 由于水资源稀缺和上下游国家外交关系的波动,阿伊围绕水资源分配的博弈从未停止过。水谈判迟迟未能取得进展,背后是三类行为体互动的结果:上游国、下游国和域外大国。在互动过程中,上下游国家之间的权力关系既是由地理位置决定的,又是由综合国力强弱决定的。从阿伊跨界河流治理困境可以看出,上游弱国、下游强国的权力分布格局不利于跨界河流合作。
从上下游国家关系互动来看,由于阿伊跨界河流主要流经这两个国家,难以形成多边合作机制。作为弱国的阿富汗,在双边谈判中处于不利地位,故无法像亚马孙河流域国家那样,通过机制化路径实现水合作。同时,伊朗是以什叶派为主体的伊斯兰神权制国家,阿富汗是以逊尼派普什图族为主体的国家,两国农业发展的同质化造成了对水资源的恶性竞争;阿伊外交龃龉造成了政治友好度降低,使两国难以像欧洲国家围绕莱茵河治理那样,在共同的文化认同基础上开展跨界河流合作。
(二)阿伊跨界河流治理的域内外困境
伊朗影响阿富汗外交主要依靠两种策略。首先是“议题补偿”策略。强国通过某些令弱国感兴趣的议题对其进行物质利益补偿,以换取后者对前者水权的保障。 在此背景下,占据区位优势的小国根据其对“议题补偿”的满意度,决定是否进行流域合作开发。作为流域内强国,伊朗具备引导阿富汗参与跨界河流协同治理的潜在能力。1988年两伊战争结束以来,伊朗亟须维护国内政局稳定与促进经济稳步增长。伊朗与阿富汗开展密切的经贸往来,2013年两国贸易额已达50亿美元,占阿富汗外贸总额的1/3。伊朗向阿富汗出口食品、药品、石油和水泥,阿富汗尤其依赖伊朗的石油、燃料和电力。由于阿富汗的工业基础薄弱,其对伊朗的贸易依存度是伊朗对其贸易依存度的200倍以上。 双方经贸关系的不对称性为伊朗提供了在水争端上制衡、制裁阿富汗的条件。此外,在难民问题与毒品问题治理上,阿富汗有求于伊朗,两国拥有广泛的议题合作空间,可以为双方就跨界河流合作提供利益交换的基础。 同时,伊朗对阿富汗第三大族群哈扎拉人有较大影响力,与阿富汗第二大族群塔吉克人也保持着良好关系,这两大族群成为阿伊开展跨界流域合作的政治纽带。 其次是“强制合作”策略。在跨界河流治理中,流域国家的实力差距使强制性合作成为可能。 正如托马斯·谢林(Thomas Shelling)所指出的,威胁的效果取决于对方是否深信不疑。威胁方必须重新组合或调整自己的威慑政策,向对方展示自己施加威胁的决心。否则,胁迫会丧失其自身价值。 据此,强国为获得弱国的水权让步而发出的强制信号必须是可信的,使弱国感受到强国有决心、有能力实施报复和打击。否则,弱国只会将强国的恐吓与威胁视作一种口头上的虚张声势而不予理睬。 在此过程中,强国将跨界河流水争端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使之达到在国内凝聚民意、在国际上展现争夺水权的决心。 流域内国家如果拥有综合国力优势,弱国将被迫采取合作态度,如放弃单方面修建水电站和拦洪坝等。然而,跨界河流治理不光是流域内国家间关系问题,域外大国的干预也成为重要变量。域外大国具有联合弱国遏制地区霸权国的动机,以防止地区霸权国垄断整个流域。尤其是域内大国与域外大国存在安全竞争的背景下,域外大国更倾向于在冲突方之间选边站队,避免流域内小国追随地区大国。由于美国和印度的介入,伊朗难以对阿富汗采取“强制合作”的措施。
在上下游国家将跨界河流问题上升为国家安全问题、域外大国介入纷争的背景下,跨界河流的非传统安全议题成为复杂的国际关系问题。从阿伊水资源争端可以看出,域外大国从权力平衡出发,依靠两种手段干预流域内国家的水合作:一是通过为上游弱国的水利项目提供发展援助,降低强国对弱国提供利益补偿的吸引力,破坏上下游国家的利益共生关系;二是与弱国建立军事联系与安全援助关系,以常态化驻军或签订双边安全协议等方式,防止弱国受强国的胁迫而妥协。
因此,在上下游、域内外国家的共同作用下,伊朗无论是诱导性的“议题合作”,还是胁迫性的政治施压都无法打动阿富汗。阿伊跨界河流治理陷入上下游、域内外双重困境,水谈判与水资源共同开发遥遥无期。
结 束 语
阿富汗与伊朗关于水权的争夺长期持续,冲突、分歧是常态,有效的危机管控机制尚未形成。两国的权力对比关系和上下游区位优势形成错位,结果相互抵消,这是跨界河流治理困境的内部根源;第三方的介入成为阻碍阿富汗与伊朗开展跨界水资源共同开发的外部原因。作为地区强国,伊朗掌握“议题补偿”和“强制合作”的“胡萝卜与大棒”优势,但美国通过与阿富汗合作制衡伊朗,印度通过与阿富汗合作制衡巴基斯坦,使阿伊两国难以形成有效的跨界河流治理模式。域外大国的介入,导致伊朗提出的跨界河流治理方案对阿富汗来说难以形成吸引力与合意性,故阿富汗合作动力不足。美国等国的军事介入,也使下游强国伊朗无法通过政治胁迫促使两国加强跨界河流治理,故阿伊未能形成合作范式。2021年以来,伊朗和阿富汗政治生态均发生重大变化。在伊朗,保守派代表人物莱希担任总统,宣布新一届政府将邻國放在对外关系的首要位置。伊朗表示愿意与塔利班政府修复关系,同时呼吁塔利班尊重阿富汗什叶派族群的宗教权利,维护两国边境安全,共同打击“伊斯兰国”及其分支,修订《阿富汗—伊朗赫尔曼德河水条约》。2021年塔利班攻占首都喀布尔后,宣布成立“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为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再度掌权的塔利班以更加务实的姿态同伊斯兰神权国家伊朗打交道。 即便如此,伊朗与塔利班政权的关系仍处于不确定状态,2022年两国还因跨界河流水资源问题爆发冲突。
当前,伊朗和阿富汗塔利班政府均面临稳定政局、发展经济、打击恐怖主义和应对西方制裁等艰巨任务,均释放出改善关系的积极信号,但是跨界河流治理既涉及内政问题,又涉及外交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难以在短期内取得国内和国际共识。美国和北约从阿富汗撤军后,拜登政府对阿富汗局势的干预能力下降;随着印度和巴基斯坦关系总体缓和,印度打“阿富汗牌”的意愿也不如以前。美国以及相关西方国家和北约从阿富汗抽身,为上下游国家直接谈判提供了积极条件。发挥域外力量的积极作用,促进阿富汗和伊朗在跨界水资源争端问题上由上下游零和博弈到全流域共治,是亚洲国家构建“跨界河流命运共同体”的有效路径。
[责任编辑:石晨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