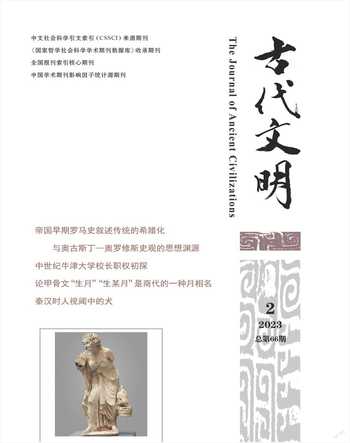帝国早期罗马史叙述传统的希腊化与奥古斯丁—奥罗修斯史观的思想渊源
关键词:罗马史;狄奥尼修斯;阿庇安;奥古斯丁;奥罗修斯
DOI: 10.16758/j.cnki.1004-9371.2023.02.002
410年,罗马城被阿拉里克(Alaric,394—410年在位)率领的西哥特人(Visigoths)攻陷。此事旋即在罗马帝国境内引起震动与思想混乱——部分基督徒对基督教事业在罗马帝国的发展前景感到悲观迷惘;一些多神教徒则借机指责基督教为盛极一时的罗马帝国带来了苦难。为了回应这一尖锐挑战和为基督教辩护,神学家、思想家、希波主教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354—430)写下在基督教政治思想史上影响深远的名著《上帝之城》(De civitate Dei),代表基督教会阐述了自己的政治观与历史观。2在完成这部巨著前10卷的初稿后,他又建议自己的学生、来自西班牙的修士奥罗修斯(Paulus Orosius,盛年在414—417)创作了一部《历史七书》(Historiae adversus paganos),对传统罗马史叙述体系进行了系统批判。传统观点认为,《历史七书》是奥古斯丁思想指引下记述自始祖亚当(Adam)至417年人类世界整体史的一部划时代的拉丁文基督教“普世史”著作。
通过《上帝之城》与《历史七书》建立起来的奥古斯丁—奥罗修斯史观不仅有力回击了同时代多神教徒的发难,并在其身后持续产生着深远影响。在长达千年的中世纪时代,奥罗修斯一直作为西欧世界公认的历史权威受到推崇,《上帝之城》这部西方政治思想史名著的历史影响更是如日中天。然而,值得后人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乃是奥古斯丁—奥罗修斯“普世史”观念的思想源头。众所周知,奥古斯丁本人的政治思想仅仅零散地分布于他的其余现存著作中,他几乎从未对之进行过系统论述。奥罗修斯则并不以深邃严密的理论思维见长。另一方面,虽然奥古斯丁之前的基督教作家们也曾站在神学的立场上,回应过多神教徒对基督教信仰的种种非难;但从“普世史”的视角出发,系统向拉丁语世界阐释基督教历史观的任务则是由奥古斯丁与奥罗修斯完成的。那么,《上帝之城》与《历史七书》中完整缜密的历史解释体系究竟是横空出世,还是另有所本呢?这是早期基督教史学思想研究中往往被人忽视,但又难以解释的一个重要问题。
按照奥古斯丁本人的说法,他对拉丁史家著作的批判采取的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做法,即从后者赞美、歌颂罗马人辉煌业绩的文本中汇集反映罗马世界罪恶、虚弱、苦難本质的证据。7而他集中批判多神教罗马观的《上帝之城》卷3也确实是以拉丁作家们的文本材料为核心依据的。他在本卷中广收博引维吉尔(Virgil,前70—前19)、西塞罗(Cicero,前106—前43)、撒路斯特(Sallust,约前85—前35)、泰伦斯(Terence,前2世纪人)、瓦罗(Varro,前116—前27)、弗洛鲁斯(Florus,2世纪前后人)的记述与观点,并在多处刻意反其意而行之,提出了与作者原意截然不同、甚至针锋相对的见解。8奥罗修斯则声称自己的主要史料来源以“普世史”作家庞培·特罗古斯(Pompeius Trogus,盛年在前1世纪)与塔西佗(Tacitus,1—2世纪间人)为基础。但从现存文本的证据来看,奥罗修斯对庞培·特罗古斯作品的参考程度似乎十分有限;而其他几位拉丁作家则根本无法为两位基督教学者提供任何意义上的“普世史”视角。
笔者认为,作为早期基督教历史观的奠基人,奥古斯丁在4—5世纪的拉丁教父中扮演着颇为独特的文化角色。他并不精通希腊文,却对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和希腊文化有着相当深入的理解,晚年又创造性地吸收了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普罗提诺(Plotinus,205—269/70)的观点。奥古斯丁自391年起在希波担任教士,于395年出任希波主教。他长期生活的地区正是拉丁文化与希腊文化彼此交融、竞争与冲突的边界地带。奥罗修斯则在其“普世史”作品中对希腊地区的历史给予过密切关注。《历史七书》中包含着对波利比乌斯(Polybius,约前200—前118)、约瑟福斯(Josephus Flavius,1—2世纪间人)等人希腊文“普世史”作品的零星引用。奥古斯丁与奥罗修斯的思想也必然吸收了来自希腊文罗马史著作中的“普世史”观念。奥古斯丁—奥罗修斯历史叙述体系中对“自然灾害”与“内战”两种元素的强调与解读方式,暗示了这种“普世史”观念与狄奥尼修斯(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约前60—7年以后)、阿庇安(Appian,约95—165)等帝国早期希腊文罗马史作者之间的共性与可能存在的渊源关系。
一、奥古斯丁—奥罗修斯罗马史解释体系中的核心符码
奥古斯丁—奥罗修斯罗马史撰述的核心思路,是揭示罗马政权在漫长历史历程中经历的苦难与犯下的罪恶,诸如“饥馑、疾病、战争、劫掠、掳掠人口、屠杀”等灾祸。多神教徒崇拜的神祇们从不回应他们的祷告与祈求。《西比尔预言书》(Sibylline Oracles)的权威在这些灾难面前毫无用处,最终被罗马人抛弃。必须承认的是,奥古斯丁与奥罗修斯为其历史解释体系添加了一项对基督教信仰而言不可或缺的要素——将耶稣基督的降生确立为世俗历史的转折点。从这层意义上讲,奥古斯丁—奥罗修斯确立的早期基督教历史观确实具备自身的创新性与独特性,并非对古典史学传统的照抄照搬,而是开辟了西方史学思想史上新的篇章。
然而,支撑《上帝之城》历史观的两项核心元素——自然灾害与内战——并不属于基督教思想的典型特色,而是承袭自古典史学传统。奥古斯丁在本书卷3中用一连串咄咄逼人的反问句质问道:
那些神明因此生幸福的稀缺与虚妄而受到尊崇;可当被他们贩卖了言而无信的谎言的罗马人遭遇这些灾难时,那些神明究竟在哪里?当执政官瓦勒里乌斯(Valerius,前5世纪人)保卫卡庇托林山(Capitoline Hill)免遭被流放者和奴隶焚毁而牺牲,从而暴露了他自己要比至高首领指挥下的众多神明更有能力保护朱庇特神庙(Temple of Capitoline Jupiter)时,他们当时又在哪里?当罗马城已被邪恶的阴谋折磨得疲惫不堪,利用短暂的和平间隙派遣使者前往雅典(Athens)寻求优良法律,却又遭受饥馑和瘟疫的折磨之时,他们又在哪里?当罗马民众因饥馑而创设赈粮官,斯普里乌斯·麦利乌斯(Spurius Maelius,前5世纪人)在饥馑加剧之际分配谷物给饥民,结果被指控为觊觎王位;以及那位官员在一场严重且危险的城内骚乱中,被独裁官卢奇乌斯·昆提乌斯(Lucius Quintius,前5世纪人)命令骑兵队长昆图斯·塞尔维利乌斯(Quintus Servilius,前5世纪人)杀害之际,他们又在哪里?
笔者认为,奥古斯丁在上述文本(以及《上帝之城》卷3中的诸多类似段落)中清晰闡释了自然灾害与内战(其中包括了被撒路斯特、阿庇安与奥古斯丁等作家称之为“内战”的罗马城内政治派系倾轧与阴谋暴力活动)之间的恶性循环关系。突如其来的天灾会加剧罗马政权的内部矛盾,导致内战接二连三地发生;内战造成的无序与杀戮又会进一步加深天灾所导致的苦难。在奥古斯丁的笔下,内战的阴影笼罩着罗马历史发展的每个阶段,因而罗马人民和遭到罗马帝国压迫的各族群所承受的苦难也是永无休止的。面对这些灾难的罗马人选择向虚幻的神灵祈求,但这样的努力最终只能是无济于事。类似的逻辑思路在《上帝之城》卷3中得到了一以贯之的延续:卡米卢斯(Camillus,约前446/5—前365)时代的罗马遭到了瘟疫、内讧与维爱人(Veii)、高卢人(Gaulians)入侵等多重灾难的轮番重创;同萨谟奈特人(Samnites)作战期间的罗马人同时受到瘟疫与内乱的困扰;苏拉(Sulla,前138—前78)与马略(Marius,约前157—前86)的内战与公敌宣告运动令罗马人民生不如死;罗马元老院对和谐之殿的祝愿必然只能化为泡影。5罗马政坛上的尔虞我诈毁掉了全意大利的幸福;共和国建立以来此起彼伏的内战则将整个有人居住的世界拖入了深渊。
相形之下,奥罗修斯很少在其作品中直接论证自然灾害与内战之间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关系。但二者也同为《历史七书》中论证罗马历史悲惨、邪恶性质的重要依据,并且往往在前后紧密衔接的历史叙述中相继出现。奥罗修斯十分重视对罗马共和时代(前509—前27)自然灾害现象的记述:埃特纳火山(Etna)的喷发与疫病的肆虐同时给地中海世界带来了苦难;突如其来的疫病冲淡了罗马人征服外敌、凯旋的喜悦;罗马建城后的第481年(前271),承载着上天怒火的瘟疫席卷罗马城,令苦苦翻检《西比尔预言书》的罗马祭司们一筹莫展;罗马建城后的第507年(前245),火灾与水患再次搅局罗马人举办的凯旋式,促使罗马元老院对一名维斯塔贞女(Vestal virgin)的渎神行为展开彻查。
在奥罗修斯的历史叙述体系中,内战同样构成了贯穿罗马人苦难始终的一条核心线索,被视为各种形式的罗马政体永远无法摆脱的痼疾。按照奥罗修斯的观点,罗马内战早在罗慕路斯(Romulus)与雷慕斯(Remus)的手足相残中业已拉开帷幕;周而复始的内战给罗马人民和诸行省带去了无尽的苦难;类似的内战从前曾导致了雅典、斯巴达(Sparta)等强邦的衰落,而罗马世界内战的破坏性还要更胜一筹;罗马建城后的第606年(前146),罗马人平定科林斯(Corinth)叛乱的战火与焚毁迦太基城(Carthage)的烈焰遥相呼应,令全地中海的居民陷入巨大的恐慌之中;罗马建城后的第662年(前90),继同盟者战争而起的又一场内战加剧了米特拉达梯战争(Mithridatic Wars,前89—前65)导致的苦难。
从《上帝之城》与《历史七书》的写作动机来看,对自然灾害、罗马内战及其相互关系的记述、渲染与评析完美服务于两位作者的创作目的。在基督教史观的语境中,这些历史信息(其中不乏夸大其词与裁剪斧凿的痕迹)论证了基督降临之前罗马历史的苦难与血腥本质,揭露了多神教崇拜体系的盲目和无用,为两位作者接下来阐述耶稣基督降临与帝国皈依基督教之后的线性进步式历史发展规律做好了铺垫。然而,来自帝国早期的两位希腊文罗马史作者——狄奥尼修斯与阿庇安——的文本证据似乎表明,这种历史叙述模式并非完全由早期基督教史观首创。
二、狄奥尼修斯、阿庇安罗马史中的相似表述
奥古斯丁—奥罗修斯历史叙述体系中的重要元素之一——自然灾害——同样也在狄奥尼修斯的《罗马古事记》(Roman Antiquities)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这些材料的最终史源很可能是与《西比尔预言书》有关的史料,或罗马共和时代的所谓《大祭司年代记》(Tabula apud pontificem)。无论如何,与李维(T. Livy,前59—17)、撒路斯特、塔西佗等拉丁作家相比,狄奥尼修斯显然给予这些历史信息更多的重视。他记载了伍尔西人(Volsci)中间的一场在“希腊与蛮族世界中”从未有过的大瘟疫;他记录了卡麦里努斯(Quintus Sulpicius Camerinus)与弗拉乌斯(Spurius Larcius Flavus)担任执政官期间(前490)肆虐于罗马城的一场牲口瘟疫。随后,狄奥尼修斯又讲述了皮纳里乌斯(Lucius Pinarius)和弗里乌斯(Publius Furius)担任执政官期间(前472)罗马城忍受的一场可怕瘟疫。自然灾害深刻影响了罗马政治的发展走向。普布利乌斯(Publius,前472/1年保民官)试图建立僭主制度的阴谋便被一场横扫全意大利的瘟疫打断。在罗马建城后的第300年(前452)里,罗马城又遭遇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大瘟疫。科苏斯(Aulus Cornelius Cossus)第二次出任执政官之年(前428),意大利中部遭遇了一次导致河水断流的严重干旱。不久之后,罗马城又经历了一次极为罕见的雪灾。他还详细转述了前监察官披索(Piso,约前180—前120)对罗马城内一次大瘟疫的记载;并记载卡米卢斯卸任执政官(前392)后罗马经历了干旱与瘟疫的自然灾害连锁反应。狄奥尼修斯还提及了世人在罗马广场上目睹的异象,并认真比较了雅典与罗马城中出现的所谓超自然征兆。
相形之下,阿庇安《罗马史》(Roman History)对自然灾害现象的着墨不多,但相关记载同“神意”与“命运”的关联却更为紧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与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卷3中的处理方式相似,阿庇安对自然灾害的大段记述几乎无一例外地出现在他的《内战史》(The Civil Wars)中。这反映了“天灾”与“内战”在阿庇安头脑中的天然联系。阿庇安《内战史》中的自然异象分别出现于苏拉与马略的内战爆发之前、恺撒(I. Caesar,前100—前44)与庞培(Cn. Pompeius,前106—前48)大动干戈之际,后三头的公敌宣告运动开始之前,以及绥克斯图·庞培(Sextus Pompeius,前67—前35)切断罗马城海上运输补给线之际。阿庇安的相关记载往往带有十分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在阿庇安眼中,这些异象反映了诸神的意志与命运的走向,是凡人所无法抗拒的,预告着世界霸权归属的转移与有人居住的世界内部的巨大动荡。
“内战”元素在阿庇安的《罗马史》中占据着几乎超过一切拉丁史著的重要地位。在其現存文本中,阿庇安以将近一半的篇幅和极其生动细致的文笔,叙述了自共和早期以来的罗马内战史。他的《内战史》序言笔力雄健,理路清晰,内容全面,跳出了撒路斯特、李维等拉丁作家单纯从道德论角度解读内战的窠臼,对导致罗马内战的经济、政治与个人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达到了古典时代罗马史著作中关于内战原因分析的最高水平。他对公敌宣告运动的罪行、及其带给罗马人民巨大苦难的详细记载,深刻且富于批判精神,可以给人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相形之下,由于处理题材为早期罗马史且后半部分大量佚失,狄奥尼修斯《罗马古事记》现存文本中罕见就内战对罗马历史直接影响进行的正面讨论。但正如后文谈及的那样,对内战危害性与何种政体能够最大限度避免内战危害的反思构成了贯穿《罗马古事记》的一条核心逻辑线索,同样在狄奥尼修斯的历史观中占据着牢不可破的核心地位。
需要指出的是,对罗马史上自然灾害与内战现象的记述当然不是希腊史学家们的专利。李维同样对共和时代特定场合下的灾异有过零星记载,这些素材似乎与狄奥尼修斯、阿庇安的相似材料拥有共同的史源——很可能是保存于共和时代官方文献中的某种年代记。对于共和晚期以降内战史事的记载更是广泛见于恺撒、奥古斯都(Augustus,前27—14年为罗马帝国元首)、撒路斯特、李维、塔西佗、卢坎(M. A. Lucan,39—65)等众多拉丁作家的作品中。然而,笔者认为,狄奥尼修斯、阿庇安等帝国早期希腊史家对自然灾害、内战等要素的描述具备有别于同题材拉丁文著作的特征——这些记述与观察,同希腊史家对世界性帝国兴衰交替的现象及不同政体的优劣与演变规律的思考紧密相连,进而服务于“普世史”这一具有典型希腊化时代特征的历史编纂模式的基本框架。而奥古斯丁—奥罗修斯历史叙述体系则恰恰脱胎于这套希腊史学特征浓厚的“普世史”写作模式。
与此截然不同的是,在撒路斯特、李维等拉丁史家的道德论语境中,自然灾害对恪守古风、上下同心、蒸蒸日上的罗马共和国的消极影响微乎其微;而内战乃是罗马古风道德体系崩塌后产生的最大恶果之一,在拉丁作家的史观中几乎意味着历史的终结。罗马在共和国晚期(前2—前1世纪)陷入内战的根本原因并非共和制度本身的缺陷,而是道德、纪律的废弛与军阀个人野心的膨胀——这种道德滑坡足以摧毁最优秀的政体制度。在这样的预设命题下,拉丁作家所关注的核心问题集中体现为,罗马人民古风道德的维系与罗马政权势力的兴衰及二者间立竿见影的动态联系。李维在《建城以来史》(Aburbe condita)中关注的主角始终是罗马与意大利,高卢、迦太基、希腊与东地中海世界只有在同罗马展开交往后才会进入其视野。他不情愿、也不擅长撰述地中海世界的“普世史”。即便是洞察人性、睿智敏锐的塔西佗与卢坎也无法真正摆脱道德论史观的束缚。要之,在拉丁作家表述的道德论史观中,自然灾害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微乎其微,而内战则意味着道德体系的崩塌和有意义历史进程的终结,甚至在不少拉丁史家的话语中直接构成了罗马史发展的终点。事实上,撒路斯特和李维最终都陷入了无法指望通过人事运转来摆脱内战危机的悲观主义。
希腊文罗马史作家则对自然灾害与内战有着不同于拉丁史家的理解。狄奥尼修斯《罗马古事记》声称,自然灾害被一些人视为神明震怒的标志,在另一些人眼中则只是出自偶然(τυχηρ??)。但狄奥尼修斯本人显然相信命运与神明对“普世史”进程具有引导作用,并将自然灾害视为天意的某种反映。在其历史观框架内,命运塑造了“亚述(Assyria)—米底(Media)—波斯(Persia)—马其顿(Macedonia)—罗马”这条霸权兴替的基本线索。阿庇安同样在《布匿战争史》(Punica)中提到了雅典、迦太基、米底、亚述与波斯等霸权的兴衰,甚至大胆地借小西庇阿(Scipio Aemilianus,前185—前129)之口预言了罗马霸权也终将灭亡的命运。
狄奥尼修斯、阿庇安对罗马内战乱象的关注则与他们在普世史视角下对政体优劣及其演化规律的思考密切相关。《罗马古事记》的核心主题之一是揭示罗马政权如何在优秀的、希腊式的政体支撑下克服外部强敌与内部矛盾所带来的一切艰难险阻。在狄奥尼修斯笔下,“政体”这一概念具有广义性,涵盖了政治组织形式、宗教信仰、礼仪风俗、语言饮食的方方面面。狄奥尼修斯借布鲁图斯(Brutus,前509年执政官)之口指出,内战是最高形式的恶,是一切优秀政体都应力求避免的结果。他在《罗马古事记》中插入了大量演说词,以便在不同历史情境下比较、论证不同政体的优劣。在他看来,罗马混合政体的温和特征为平民与贵族的合作与妥协保留了余地,从而为日后罗马的世界性霸权奠定了基础。罗马共和国的优良法律根源于希腊,并吸收了后世雅典法律的优长,达到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效果。狄奥尼修斯认为,通过政体研究提炼出各城邦、帝国治理模式的成败得失,进而总结出在“普世史”框架内具备普遍适用性的一般规律,实为史学研究的根本目的所在。在广义上的政体研究方面,《罗马古事记》要比李维的同题材史著内容丰富得多。无独有偶,阿庇安《内战史》的序言试图从农业、财政、政治体系等方面剖析罗马在共和国末年陷入内战深渊的体制性原因,与拉丁史学传统中道德论史观判然有别。他在探讨罗马内部的债务危机时援引了波斯帝国的案例进行类比。他认为苏拉独裁事实上一度在罗马恢复了废除已久的君主制。他还将罗马内战的惨烈同希腊世界的相关案例,以及元首制时代的和平局面进行了对比。这些处理方式无不与作者的“普世史”视角相得益彰。要之,大量证据表明,通过对自然灾害、内战等罗马史中固有元素的发掘,狄奥尼修斯、阿庇安及其先驱波利比乌斯、波塞冬尼乌斯(Posidonius,约前135—前51)一道,将原本属于希腊史学专利的“普世史”视角导入了罗马史的叙述体系,同时也将原本孤立、独特的罗马史素材纳入了记述世界性帝国兴衰交替、分析不同政体优劣与演化规律的“普世史”叙述框架。
文本证据表明,奥古斯丁—奥罗修斯历史叙述体系对“自然灾害”与“内战”两大核心要素的阐释主要遵循的是希腊文罗马史作家的“普世史”分析模式,而非拉丁史家们相对简单的道德论思路。例如,奥罗修斯便在其关于历史兴衰规律的探讨中提出了“雅典—拉栖第梦(Lacedaemon)—波斯”霸权兴替这种明显带有普世史特色的解释范式。与此同时,两位早期基督教史观的奠基者也对希腊作家的罗马史叙述体系进行了必要的改造,隐匿了后者对罗马军事业绩、社会风俗与英雄人物的讴歌与赞颂,剔除了其中关于政体演变规律的丰富内容(在罗马帝国统一地中海世界的政治背景及轻视凡俗政治的基督教语境中,这些话题已极少有人关心),丰富了阿庇安等希腊史家将自然灾害与政权内部矛盾联系起来的观点,补充了将基督(Christ)降临视为世俗历史转折点的神学观念。奥古斯丁与奥罗修斯当然是站在神学立场上否定、批判罗马世俗历史的独立价值与积极意义的,认为罗马政权不过是上帝实现其意志的工具,基督降临之前的罗马史也远非试图嫁祸基督教的多神教徒们所鼓吹的那樣光辉壮丽、充满美德。而以狄奥尼修斯与阿庇安为代表的帝国早期(前1世纪末—2世纪)希腊文罗马史作者的立场则显然并非如此。因此,全面解读两人的罗马观,对于理解早期基督教历史观的源流具有重要意义。
三、狄奥尼修斯与阿庇安的罗马观
狄奥尼修斯的《罗马古事记》从传说时代记述到第一次布匿战争(First Punic War,前264—前241)前夕、与波利比乌斯的《历史》相接续。作者自称,撰写《罗马古事记》目的之一便是回馈罗马这座旅居城市对自己的厚爱。他在写作过程中广泛参考了重要拉丁与希腊史家的作品。其基本立场显然是亲罗马的。他盛赞罗慕路斯不杀壮年战俘的政策优于希腊人的制度;他赞美水渠、良好道路与下水道体系是罗马文明对全人类的三大突出贡献;他称赞罗马政体的弹性最大限度地避免了内战风险,为日后罗马的霸权奠定了基础。狄奥尼修斯十分推崇罗马人的军事才能,曾礼赞过罗马人在同一天赢得两场辉煌胜利的业绩;他认为罗马人在军事技术方面远胜过一切蛮族。狄奥尼修斯在作品中赞扬过许多罗马英雄的个人美德,如最终放弃功名而保全罗马城的玛尔奇乌斯(Marcius,共和国早期将领)。他还颂扬过作为集体的罗马人民的大度与公正精神。从这些材料来看,狄奥尼修斯的《罗马古事记》堪称对罗马文明与罗马人美德的一曲颂歌。他还在自己的修辞学著作中更为直白地宣称,是罗马政权的崛起反哺了希腊文明,促成了希腊文化的中兴。
阿庇安的《罗马史》前半部分采用国别史的体例,以便服务于论证罗马凭借武功与命运建立霸权的主题;后半部分则聚焦于罗马内战,带有较强的政治与道德批判意味。他在《罗马史》中高度评价了罗马人的优秀品质,认为他们远远胜过从前来自亚洲的统治族群,凭借自身的明智与幸运而赢得了霸权。他在作品中赞美了罗马的强大军事实力,认为他们在实力上升期受到过命运的垂青。他还讴歌过小西庇阿、恺撒、奥古斯都等罗马英雄人物的文治武功。总的来说,与《罗马古事记》相似,阿庇安的《罗马史》同样具有歌颂罗马历史与罗马人丰功伟绩的性质。
然而,也不可忽视《罗马古事记》与阿庇安《罗马史》中潜藏着的另一种张力。两位希腊史家对罗马政权的正面评价并不是毫无保留的。狄奥尼修斯曾在记述罗马王政时期(前753—前509)第三王图鲁斯(Tullus,前672—前640年在位)事迹的时候,暴露了自己内心的真实看法,认为当时罗马人仍为蛮族。他尽可能地对自己身处时代的政治领袖奥古斯都保持沉默,有时也不无微词。而阿庇安则更为直接地表达出对罗马政权的批评意见,有时甚至完全不加掩饰。他在《汉尼拔战争史》(Hannibalica)中不客气地指出,命运并非始终眷顾着罗马人。《布匿战争史》中叙述迦太基覆灭的文本几乎将同情完全倾注到了遭到罗马征服的迦太基人身上,历数了罗马人的蛮不讲理、贪得无厌与冷酷无情。他借珀尔修斯(Perseus,前1世纪马其顿王)使节之口谴责了罗马在外交上的言而无信;并在《米特拉达梯战争史》(Mithridatica)中用无情笔触批判了罗马将领苏拉的心狠手辣与横征暴敛。却对坚持抵抗罗马、直至身亡的米特拉达梯(Mithridates VI,前120—前63年在位)进行了相对正面的评价。而最为明显的证据来自于他在《布匿战争史》中对征服者小西庇阿心理活动所进行的、很可能出自主观虚构的描写:
西庇阿注视着这座城市——一座自建城以来的700年间统治过众多土地、岛屿和海域,跟其他最强大的帝国一样掌握着大量军队、舰只、战象与金钱,并在于困境中保持昂扬斗志方面远胜过后者(它在失去了全部战船和武器后,仍在饥馑与激战中坚守了整整3年之久)的城市。据说,目睹这一场景的西庇阿潸然泪下,公开哀叹敌人的不幸命运。他一直默默思索着各种城市、族群、帝国与个人不可避免的灭亡命运,思索着曾经盛极一时的特洛伊的陷落,思索着亚述、米底与强大的波斯帝国,还有最近的强盛帝国马其顿的衰落。他不由自主地念出了那位诗人的词句:“那一日终将到来:我们神圣的特洛伊(Troy)、手持长枪的普里阿摩斯(Priam)与他统治的人民都将走向灭亡。”
波利比乌斯回忆道,当他私下里(因为波利比乌斯是他的老师)向西庇阿询问,这些诗句所指为何的时候。西庇阿毫不犹豫地说出了自己祖国的名字,因为他在思索人事的变幻无常时为罗马的命运感到忧心忡忡。
可见,阿庇安绝非罗马政权的阿谀奉承者。他的历史观保持着高度的自主性与独立性。事实上,阿庇安毕生以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ia)公民的身份为荣,并将罗马对自己家乡的治理在一定程度上视为一种奴役。尽管未见奥古斯丁或奥罗修斯直接钻研过狄奥尼修斯、阿庇安罗马史著作的直接证据,他们却很可能通过某种渠道,间接把握了此类帝国早期希腊文罗马史作品的叙述模式,并敏锐地抓住了其中暗藏的张力与批判性,创造性地将之改造为自身重构罗马历史记忆的有力武器。
四、叙述体系的希腊化及其对早期基督教拉丁史学的潜在影响
早在前5世纪末,希腊作家列斯波斯的赫拉尼库斯(Hellanicus of Lesbos,约前480—前395)可能已经提及过特洛伊将领埃涅阿斯(Aeneas)奠定罗马城基础的传说。到前4世纪,学者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前384—前322)与本都的赫拉克勒德斯(Heracleides Ponticus,约前390—前310)均隐约听说过罗马的存在。然而,希腊本土的绝大部分知识精英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曾真正关注过罗马文明的成长与崛起。因此,罗马共和国在前3—前1世纪以摧枯拉朽之势统一地中海世界之际,希腊人更多的感受是一种无可名状的震惊。罗马文明的根本性质,以及希腊人在罗马帝国治下的文化身份等问题,成了奥古斯都时代与第二哲学运动时期(约60—230)希腊知识精英们热烈讨论的焦点。狄奥尼修斯是较早承担起向希腊读者介绍罗马文明起源问题的史学家之一,系统阐发了(尽管并非首创)罗马人与希腊人同源的历史观。《罗马古事记》并非一部东拼西凑、随意为之的作品。作者对罗马共和时代的执政官年表等基本文献进行过相当认真的研究,表现出求真求实的史学探索精神。到2世纪,另一位希腊史家阿庇安又精心撰写了一部比李维同题材著作更为精炼、更合乎希腊读者口味的希腊文《罗马史》。他的《罗马史》同样不是对拉丁史料的简单摘录,而是展示了希腊知识精英特有的历史观与写作风格。在写作过程中,狄奥尼修斯与阿庇安均广泛参考了前辈拉丁、希腊史家们的相关论述。更为重要的是,两位作家还自觉承担起了将拉丁史家、诗人、学者关于罗马文明的历史记忆希腊化的使命。狄奥尼修斯和阿庇安对罗马史进行希腊化改造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一项举措,乃是将当时希腊史学中通行的“普世史”历史观导入了罗马史的叙述体系,从而深刻影响了后世罗马史与基督教史学的撰述方式。
狄奥尼修斯与阿庇安的希腊文罗马史撰述先驱——波利比乌斯选择用断代式的“普世史”体例,讲述罗马共和国在不到53年内,在“命运”(τ?χη)佑助和优良混合政体的支撑下征服地中海世界的历史,并在《历史》开篇处总结了“波斯—拉栖第梦—马其顿—罗马”的世界性霸权兴替线索。然而,事态的发展往往出乎撰写同时代历史的史家们的预料。波利比乌斯在有生之年便不得不调整自己最初制订的“普世史”写作方案,将记述年代的下限由前168/7年后延至前146年,以便观察罗马对被征服地区的治理成效。但这样一来,波利比乌斯的断代“普世史”就不得不在残暴的罗马军团焚毁迦太基与科林斯的火光中结束,完全无法呼应罗马在命运庇护下统一地中海世界、以善政治理被征服人民、开启“普世史”历程中一个全新时代的史著主题,等于宣告了其“普世史”历史观的破产。事实上,历史进程远未在波利比乌斯人为设定的“普世史”终点处戛然而止。波利比乌斯的巨著对拉丁、希腊世界的罗马史撰述均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利用“普世史”体系重新解释罗马历史的任务并未圆满完成。
狄奥尼修斯严厉批判了波利比乌斯将“普世史”的核心内容限定在不到53年的时间段内的做法。与此同时,他又受到波利比乌斯在“普世史”视角中关注罗马政体优长的启发。《罗马古事记》的标题“?ωμαικ? ?ρχαιολογ?α”说明,狄奥尼修斯至少是熟悉“普世史”的写作体例的。他在序言中提出“亚述—米底—波斯—马其顿—罗马”这条世界霸权的交替线索;比较了雅典、罗马与迦太基的海上势力。罗马地区起初被蛮族占据;但如今的罗马人在血缘、文化和语言上都是希腊人的后裔,并借助希腊“政体”的优势兴起,成为新的世界性霸权。通过对罗马希腊性的论证,狄奥尼修斯将整部罗马史纳入希腊世界的视野与“普世史”的研究范围。
阿庇安则选择在其《罗马史》中另辟蹊径,以国别史的体例呈现罗马征服已知世界的纷繁复杂头绪,并以《内战史》作为罗马与迦太基、本都等列强争夺地中海世界霸权的延续。由于文本散佚的缘故,现在难以讨论阿庇安对奥古斯都终结内战后罗马历史的处理方式。但他的史学视野显然带有“普世史”的典型特征。除了罗马与其他族群的交往史外,阿庇安还以插话的形式叙述了凯尔特人(Celts)、伊利里亚地区(Illyria)、罗马征服前的叙利亚(Syria)与库勒尼(Cyrene)等地区的历史,从而填补了“普世史”视野下先前史著的叙述空白。
如前所述,狄奥尼修斯和阿庇安均可被归入“亲罗马派”,或至少是对罗马政权的评价较为积极的史家行列。然而,在将“普世史”视角导入罗马史的叙述体系时,两人也不可避免地带入了这种历史观对世界性霸权交替与各种政体弊端的固有政治批判立场。
“普世史”的撰史传统诞生于希腊知识精英的视野逐步拓展、希腊世界内外的外交关系趋于复杂化的社会文化背景。在其发展历程中,“普世史”逐渐分化出了重视族群与文明兴衰交替,以及关注政体演变规律的两种模式。在第一种模式的创作实践中,希罗多德(Herodotus,约前484—前425)与泰西阿斯(Ctesias,前5世纪人)最早构建了“亚述—米底—波斯”霸权兴替的“普世史”演化模型。波利比乌斯的前辈、史学家埃弗鲁斯(Ephorus,约前400—前330)进一步将希腊世界的内部纷争(阿庇安等人笔下的“内战”)也纳入到世界性霸权交替的“普世史”叙述体系中来。希腊化时代的思想家们又为这种世界性、区域性霸权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普世史”叙事模型填充了宗教与伦理色彩。德米特里乌斯(Demetrius of Phalerum,約前350—前280)在其已佚著作《论命运》(Περ? τ?χη?)中强调了命运与神意在人间霸权兴替历程中的主导作用。学园派哲学家阿瑞斯托克塞努斯(Aristoxenus,盛年在前335年)则指出,促使世间列强走上争霸道路的根本动力在于对财富的贪欲和渴望。这种逐渐丰富起来的“普世史”观念本身就包含着对包括罗马帝国在内的一切世界性霸权的道德批判,以及对一切政治军事强权万古长存可能性的明确否定。在阿庇安采用的这种“普世史”视野下,无论是本都国王米特拉达梯对罗马人组织的疯狂屠杀,还是罗马内战中后三头发起的公敌宣告运动,其本质都是毫无道义可言,但在强权政治中无法避免的灾难与罪恶。而在政体演变的“普世史”模式中,即便是相对优良的斯巴达、罗马式“混合政体”亦有其难以克服的内在弱点,承袭希腊政体与马其顿霸权的罗马政权终有灭亡之日。波利比乌斯与阿庇安对罗马帝国末日的预言,实为这一“普世史”逻辑思路推演的必然结论。这些针对罗马世界性霸权的批判性认识被5世纪的奥古斯丁、奥罗修斯等基督教作家所沿袭,成为他们重塑罗马史的基本面貌、确立基督教化的“普世史”观念的思想源泉。
奥古斯丁、奥罗修斯等基督教学者直接从帝国早期希腊文罗马史著作、译本或节编本中汲取灵感的可能性,是无法轻易否定的。以狄奥尼修斯的《罗马古事记》为例,这部作品曾在1—2世纪期间被帝国知识精英们广泛阅读,并得到过斯特拉波(Strabo,前64/63—约24)、普鲁塔克(Plutarch,约46—119)等学者的直接征引。这部作品的标题和体例先后影响了两部与基督教文化和“普世史”传统同时存在交集的著作——约瑟福斯的《犹太古事记》(Judean Antiquities)和伪斐洛(Ps. Philo)的《圣经古事记》(Biblical Antiquities)。
此外,与“普世史”观念联系紧密的斯多葛哲学(Stoicism)也曾对早期基督教伦理学产生过深远影响,奥古斯丁等思想家也很有可能通过斯多葛主义的哲学作品了解过“普世史”罗马观的基本内容。《旧约·但以理书》(Vetus Testamentum, Daniel)所构建的世界性霸权兴替模型“巴比伦(Babylon)—米底—波斯—马其顿—希腊化诸王国”根源于希腊知识精英的“普世史”思想。尼科拉奥斯(Nicolaus of Damascus,约为前64年生人)最早将《旧约圣经》中的史料纳入了希腊“普世史”的叙述体系;庞培·特罗古斯的拉丁文“普世史”在3世纪也被希波吕托斯(Hippolytus,约170—235)介绍给了基督教文化圈。奥罗修斯本人在《历史七书》中直接引用过波利比乌斯与约瑟福斯的“普世史”。种种证据表明,在希腊化—罗马帝国时代的文化交融浪潮中,希腊文罗马史中承载的“普世史”观念早已与其他希腊文化元素一道,同早期基督教文化建立起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即便奥古斯丁与奥罗修斯并不知晓狄奥尼修斯与阿庇安的著作(这样的可能性其实微乎其微),这两部帝国早期希腊文罗马史中的“普世史”构建思路仍会通过种种媒介渗入到5世纪基督教作家们的历史记忆当中。武断地认定奥罗修斯只能从特罗古斯的拉丁文“普世史”作品中汲取灵感,甚至否认奥古斯丁—奥罗修斯历史解释体系与希腊“普世史”观念之间显而易见的相似性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有理由相信,狄奥尼修斯《罗马古事记》与阿庇安《罗马史》这两部史著对罗马共和时代自然灾害与内战的详细记录,以及在“普世史”語境中对罗马政权采取的批判性立场,通过种种渠道影响了奥古斯丁与奥罗修斯的罗马观,进而塑造了早期基督教“普世史”史学传统的基本面貌。
[作者吕厚量(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北京,102488;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100101]
[收稿日期:2022年8月2日]
(责任编辑: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