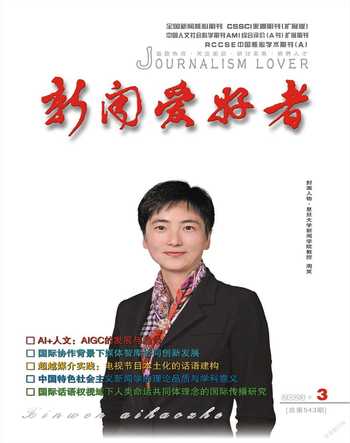新媒体时代公益传播的平台化研究
李子林

【摘要】进入新媒体时代,平台媒介的产生为第三部门开展公益传播活动提供了新的技术载体,并逐步发展成为当下公益传播的主流基础设施。重新审视平台对于公益传播实践的结构性塑造过程发现,平台为公益传播行动者网络的形成提供了四种类型的可供性,分别为问题化阶段的“可见性”、利益赋予阶段的“聚合性”、征召与动员阶段的“交互性”与“可获得性”。在多重可供性的共同作用下,平台作为“非人类行动者”,得以持续而快速地吸纳多元利益攸关方加入公益传播网络,最终产生了超越传统媒介的裂变式传播效应。
【关键词】公益传播;平台;可供性;新媒体
进入新媒体时代,平台媒介的产生催生了“平台社会”的形成,也对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进行着深刻的结构性重塑,公益慈善领域也不例外。随着互联网与社交媒体的普及与发展,大型互联网公司主导的数字平台为第三部门的公益传播活动提供了新型技术载体,激活了更广泛的传播资源,使之逐步发展成为当下公益传播的主流基础设施。从依托广播、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介的单向传播链条来获取大众注意力,到借助互联网平台实现公益信息的跨时空、裂变式传播,我国的公益传播模式正在逐渐走向“平台化”。平台逻辑开始渗透到公益传播过程之中,无形中改变着传播的运作机制、叙事语境与权力分配格局。作为一种具备连接性、开放性与公共性的“中介力量”,数字平台对于传播的意义已经超越了物理的、计算的层面,而进入到了更广阔的社会经济情景之中。[1]
尽管平台已经在公益传播领域展现出空前的影响力,但鲜有学者对平台时代公益传播的内在逻辑与运作机制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当前国内外传播学界流行的“可供性”(Affordances)概念,强调了技术物为特定用户群提供的面向目标行动的可能性[2],这也为我们探索平台对公益传播过程的影响提供了一个创新性的理论范式。本文将基于“可供性”的理论透镜,探究数字媒体时代下平台为公益传播提供的可供性类型,并对其如何强化传播效应进行深入分析。
一、文献回顾与理论框架
(一)公益传播的平台化
尽管学界对于公益传播定义的表述有所差异,但仍存在一些基本的共识:在属性上,公益传播必须是非营利性的,区别于为获取市场利益而开展的商业传播活动。在目标上,公益传播的目的是为了提升社会公众对公益议题、活动或文化的关注。在内容上,传播内容应当聚焦在具有社会价值的公益议题上。[3]在主体上,包括政府、企业、公益组织、媒体、公众等均可以成为公益传播的主体。本文将重点讨论由公益慈善机构发起或主导的公益传播行动。当前,传播学领域的相关文献主要围绕公益传播的主体与模式、媒介与工具、规范与监管等议题进行理论探索与经验研究。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社交媒体的普及,许多公益组织开始谋求数字技术与公益业务的深度融合,以期通过平台嫁接、技术赋权的方式进一步拓宽筹款渠道、调动社会资源、链接受助对象、加强标准化建设、助力信息公开等。[4]互联网平台的出现帮助公益组织开启了新的数字化运营时代。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数字平台作为公益领域的新入场者,为公益传播活动提供了触达大众的数字化“入口”。背靠其强大的技术、资本与市场优势,平臺能够聚合多方资源,帮助公益组织获取更多的公众注意力,进而形成跨地域、规模化的裂变式传播效应。[5]
(二)可供性理论与行动者网络分析框架
“可供性”作为产生于生态心理学领域的理论概念,目前已经在传播学界发展了数十年,逐渐延伸出较为系统的研究谱系。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生态学家詹姆斯·吉布森于1977年提出,被用来指代环境为动物提供的行动可能性,突出强调了动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属性。[6]被引入传播学领域之后,通常被用来考察技术在人类社交互动与传播实践中的应用及其所带来的影响。既有研究识别了新媒体传播技术为公益集体行动、线上知识分享、合作创新、公民政治参与等人类行动实践提供的多元可供性类型。可供性概念对于理解“特定人类行为如何在某种媒介形态中产生”的问题具有重要价值,因而可以为本文探索新媒体时代公益传播的平台化机制提供一种创新性的分析路径。[7]
公益传播的本质是公益信息、观念或意义在多元行动主体之间的流动和传递,其中涉及原本分散的公益机构、捐赠者、受助者、平台企业、平台等,人类或非人类行动者个体在互动中发生连接,最终聚合形成公益传播行动网络的过程。借鉴布鲁诺·拉图尔等人提出的行动者网络分析框架,本文将公益传播行动者网络的形成过程划分为“问题化”“利益赋予”“征召和动员”三个阶段[8],并致力于识别出每个阶段中平台为公益传播提供的可供性类型,进而解释不同类型的平台可供性如何促进新媒体时代公益传播平台化模式的成功实践。
二、新媒体时代公益传播的平台可供性
(一)问题化阶段:平台“可见性”
“问题化”涉及构建行动者网络的初始阶段,指的是核心行动者对有待传播的公益议题进行初始定义,并将其明确表达出来的过程。[9]其中,核心行动者指的是作为传播主体的公益慈善组织,他们首先需要发现具有传播价值的公益议题。另外,由于社会问题的种类纷繁复杂,并非所有议题都能成功进入受众的视野。因此,公益慈善机构需要借助特定的媒介渠道将其构建的传播叙事表达出来,以吸引更广泛的社会注意力。
平台媒介所供给的“可见性”,无疑为公益慈善机构发现“问题化”内容、呈现“问题化”结果提供了一种更为高效的便捷渠道。这种“可见性”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对“传播主体”的可见性。依托微博、微信、抖音等面向公众的社交媒体平台,任何有受助需求的个体或群体都可以便捷地借助平台渠道在个人社交账号上发布求助信息,或是借助互联网的连通性与社交性联系到公益慈善机构表达诉求,使得众多亟待关注的公益议题对于传播主体可见。二是对“传播客体”的可见性。在“前平台时代”,公益机构通常以新闻报道、电视广告、线下活动等形式来宣传公益议题或项目。依托传统渠道的传播方式往往受到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存在传播速度慢、传播范围窄、传播效率低的多重问题。而平台传播的优势之一是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局限,迅速拓展传播内容在公众的能见范围,也让公益机构有了面向社会的发声平台。
(二)利益赋予阶段:平台“聚合性”
“利益赋予”指的是核心行动者对其他行动者的利益进行再阐释,说服他们接受自己定义的一致利益。[10]在公益传播网络建立之初,平台“聚合性”为公益传播的参与方创造了某些激励因素,促使他们达成对共同利益的一致认知。由于异质性的行动者在资源禀赋上存在差异,要达成特定的个体目标需要依靠与外部环境的资源交换,这种基于获取资源的利益诉求使得多元主体在公益传播领域存在合作的可能性。具备“聚合性”的平台媒介可以连接与整合各个利益攸关方所拥有的经济、信息、知识等资源,增强行动者参与公益传播网络的个体动机。
对于公益机构来说,依托互联网媒体平台可以直接面向社会公众发布公益信息、展示公益项目、宣传组织立场,并借助平台的传播效应吸引更多的社会关注,实现对社会资源的广泛动员。从机构管理的角度出发,平台也为公益组织的项目运作提供了技术便利。[11]就平台企业而言,营利性是其从事经济活动的根本目标,参与公益传播行动更多的是出于组织战略层面的理性考量。作为理性行动者,平台企业寄希望于借助与公益机构的合作来增加平台流量,提升关注度与影响力,最终反哺于企业经济效益的增加。就受助者而言,平台的出现提升了个体需求的可见性以及公益服务的可获得性。公益需求的传播不再是自上而下的,部分平台开通了针对受助者的线上求助通道,为他们提供向公益机构直接反馈需求的传播渠道,也因此让更多小众的、弱势的群体需求被关注。对于社会公众来说,平台降低了他们参与公益传播、开展公益捐赠的技术门槛,并且可以不经过任何组织中介实现与受助者的直接沟通交流,从而有助于提升公益参与体验。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作为一个“非人类行动者”,平台在整体行动网络中进行资源整合与利益分配,已然成为促进各个利益攸关方产生协作动机的优势媒介。经过利益调和之后,平台与多元主体之间产生了某种“互利—共生”关系:平台的角色是负责供给传播渠道、技术与工具,其他行动者则向平台提供传播议题、内容叙事、注意力与关系网络等。“互利—共生”关系的建立为下一步公益傳播行动网络的拓展奠定了基础。
(三)征召与动员阶段:平台“交互性”与“可获得性”
“征召与动员”指的是招募行动者加入公益传播行动网络,并维持网络稳定运行的过程。[12]动员更多行动者接收和传递公益信息,以推动更广泛的公益参与,是公益传播的核心目标。平台为促进这一目标的实现提供了两种类型的可供性:
一是交互性。不同于传统媒体封闭、单向的传播模式,在一个开放、共享的媒体平台中,信息通常是依托人际互动的多向传递。平台用户不仅仅只是信息的接收者,同时也是积极主动的信息扩散者、信息生产者或信息加工者。以单个主体作为传播的中心节点,由平台赋能个人,个人将接收到的公益信息向其所在的人际网络辐射扩散,基于社交情景不断编织出传播网络。公益信息经由用户个体的熟人关系网络不断向外延伸和拓展,进而产生“一传十、十传百”的裂变式传播效应。另外,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平台为利益相关者提供了公共讨论的“虚拟场域”,有关公益议题的交流和探讨不再需要一个实体的物理空间来承载,仅仅通过平台提供的评论、群聊等功能就能得以实现。这种必要的社会讨论也成为扩大公益传播效应的有效方式。
二是可获得性。平台对于征召和动员公益传播者的另一个重要作用,在于极大降低了公益传播行动的参与门槛,使得普遍的平台用户获得了参与公益传播的便捷渠道。在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主导的公益传播模式下,读者或观众想要对公益信息进行再传播难度较大,通常需要付出极高的成本。而进入平台传播时代,作为信息接收者的用户只需要借助“转发”“评论”等功能,就能在几秒之内完成一次传播行动。由于平台为公益传播实践提供了“可获得性”,越来越多的个人或机构被征召进公益传播网络,因此平台也被认为是一种低门槛、高效率的动员工具。
三、总结与讨论
聚焦新媒体时代公益传播的平台化现象,本文综合运用可供性理论与行动者网络分析框架,探索性地回答了“平台可供性如何作用于公益传播实践”这一问题,并识别出了“可见性”“聚合性”“交互性”“可获得性”四种公益传播情景下的平台可供性类型(见图1)。在四种可供性的共同作用下,多元行动主体通过平台媒介在互联网空间中编织出了庞大的公益传播网络。
关于平台如何作用于公益传播过程,本质上探讨的是技术如何社会性地将公益传播者组织起来并实现社会建构的。数字媒体时代,传统媒介的单向传播链条被平台媒介的多向传播路径所取代。平台对于公益传播的意义已然超越了物理、技术层面,成了具有能动性力量的“非人类行动者”。然而这种塑造社会的力量并非只有积极的一面,同样隐藏着机器主义侵蚀人本主义的风险。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当下数字平台的架构设计已经使其具备了操纵平台用户、垄断数据资本、改变权力配置的能力,由此也引发了理论界与实践界对于平台扭曲传播伦理、侵蚀公益文化的隐忧。当前,必要的制度规制是避免此类伦理风险的当务之急。未来,这场平台化变革会将公益传播导向何方,还有待进一步的理论辨析与实证探讨。
参考文献:
[1] 何塞·范·迪克,孙少晶, 陶禹舟. 平台化逻辑与平台社会:对话前荷兰皇家艺术和科学院主席何塞·范·迪克[J]. 国际新闻界,2021(9): 49-59.
[2] Zheng Y, Yu A. Affordances of social media in collective action: the case of Free Lunch for Children in China[J]. Information Systems Journal,2016,26(3):289-313.
[3] 王炎龙,李京丽,刘晶. 公益传播四维框架的构建和阐释[J]. 新闻界, 2009(4): 18-20.
[4] 马贵侠,谢栋,潘琳. “互联网+”时代中国公益组织互联网传播能力评估实证研究[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19(8): 162-169.
[5] 白红义. “平台逻辑”:一个理解平台——新闻业关系的敏感性概念[J]. 南京社会科学, 2022(2): 102-110.
[6] 张志安,黄桔琳. 传播学视角下互联网平台可供性研究及启示[J]. 新闻与写作,2020(10): 87-95.
[7]匡文波,邓颖.媒介可供性:社交平台赋权粉丝社群的情感表达[J].江西社会科学,2022(7):168-176.
[8]Callon M. Some elements of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domestication of the scallops and the fishermen of St Brieuc Bay[J].Sociological Review Monograph, 1986,32(2):196–233.
[9] Mahring M, Keil M , Holmstrom J, et al. Trojan actor-networks and swift translation: Bringing actor-network theory to IT project escalation studies[J].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People,2004,17(2):210-238.
[10] Mahring M, Keil M, Holmstrom J,et al.Trojan actor-networks and swift translation:Bringing actor-network theory to IT project escalation studies[J].Information Technology & People,2004,17(2):210-238.
[11]林敏華. 对公益组织互联网传播能力的实证研究:以广州本土公益组织为例[J]. 青年研究, 2014(1): 31-39.
[12]Mahring M,Keil M,Holmstrom J,et al.Trojan actor-networks and swift translation:Bringing actor-network theory to IT project escalation studies[J].Information Technology & People,2004,17(2):210-238.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博士生)
编校:赵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