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音乐作品中的中国
平果
約翰·凯奇(John Cage)是二十世纪美国最具代表性的先锋派作曲家之一,因一首《433”》被大众知晓,声名鹊起。他是前卫的作曲家,也是大众传媒影响下的公众人物,其乐谱和著作已出版畅销多年。即便是不太了解现代音乐的人,也都能就让钢琴家“无事可做”的《433”》打趣几句。
凯奇身上一直背负着各种标签,他有许多让人无法理解的矛盾行径,他离群索居,爱好采集蘑菇……推崇他的人视他为打开全新思路的先锋艺术家,反对他的人则称其是哗众取宠的“小丑”。他不仅是作曲家,也是诗人、画家,他活跃于舞台、剧场,对东方文化十分着迷,常年研习禅宗、《易经》。
这位极具争议的作曲家最常被人讨论与误读,遗憾的是其晚期佳作鲜少被人关注、理解。而这些作品中,恰好隐藏了他多年来先锋实验的艺术成果,比如创作于他生命最后五年的系列作品数字音乐(Number Piec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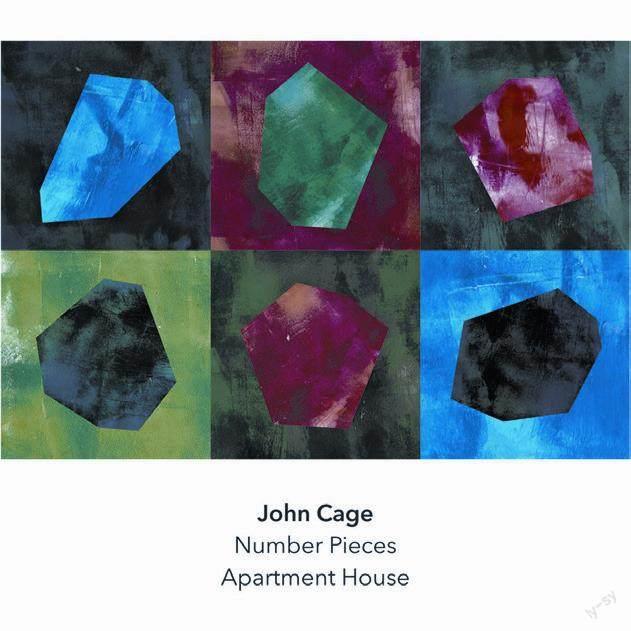
约翰·凯奇的数字音乐以表演者的人数来命名。作品《一》(One)是由一名演奏者演奏的作品,作品《一9》(One9)则是第九部由一人演奏的作品。凯奇记录在册的数字音乐共计五十二首,其中也包括少数几首仅仅被凯奇提及但未有乐谱或未完成的作品。凯奇在创作时广泛运用了自己创造的“时间括号”(time bracket)技术,即在乐谱中构建音高与数字两种维度,前者常常包括一个音符或是一组和弦,后者提示演奏者开始与结束的时间,开始的时间相对灵活,结束的时间则是固定的。
凯奇在为该系列作品设定音高时,使用了抛掷硬币的方法,令其具有随机性。他将不同的音高编号对应《易经》里的六十四卦,然后根据硬币给出的卦数去找对应的音符。而更为具体的音高排列,如音与音之间的关系,是否有升降号,音与音之间是上行还是下行,具体多少度等都由凯奇通过继续设置问题再抛硬币寻求答案的方式一一得出,音乐处处充满了未知与偶然。在该系列作品中,凯奇将自己的意愿降到了最低,由硬币透露出的“天机”代替他给予作品基本轮廓,每一个音高背后都藏着“机缘”。


《一百零八》(O n e Hundred and Eight)是数字音乐系列中乐器编制最庞大的一部作品,由一百零八人组成的管弦乐队进行演奏,即传统的西方管弦乐队配置加上部分没有规定配置的打击乐器。凯奇在选择打击乐器时,希望乐器间能避免同质化,音色要有所区别,他更为青睐中国钹、土耳其钹、日本寺院里的锣、雷鸣器和加美兰铜锣,通过这些乐器的使用令整部作品的东方气息更加浓郁。
《一百零八》由五个沉默段落穿插起声音段落,使用了灵活的时间括号。因为有些括号的时间区间是重叠的,所以音响结构上也会因为演奏者的选择不同,出现多个时间切片叠加的效果,这比以往采用时间括号写作的作品要更为复杂,不同的音色层次如密云般交错、浮动、变化。
按照凯奇的提示,长音应该是柔和的,短音应该是响亮的。在这样的设定下,作品有了明暗斑驳的光影。简单的单音,甚至传统的和弦与不协和的噪音交织在一起,又因为沉默段落的围绕,在听觉上指引我们关注异质性音色的冲击。同为晚期作品,《一百零八》让人想到凯奇几乎在同时段与冠点版画工作室(Crown Point Press)合作的诗歌与画作。凯奇晚期的诗歌作品《I-VI》中也出现了不同元素的并置,同样具有偶然因素,在似乎彼此无关的诗句里重复同样的节奏。我们能从诗句里找到和作曲家的音乐相似的韵律。
从1985年到1992年,凯奇与冠点版画工作室合作,通过烟熏纸张来制作一系列画作——在印刷机床上生火,用湿纸穿过它,待火熄灭后在纸上留下优雅的漩涡图案。随后将来自不同材料的图像叠加到这张纸上,比如茶壶底和从建筑工地捡来的金属零件等。
在这些作品中,纸张的褶皱和烟熏纸后留下的火烧印记产生了一种模糊性和连续性。凯奇对这些十分着迷,并将其映射在数字音乐中。那些消散于呼吸间的音色,如烟熏纸上的痕迹,为音乐平添了几分模糊与朦胧。无论是弦乐柔和暗哑的长音,还是短笛在瞬间释放出的刺耳尖利的短音,最终都会在时间中褪色消散。

《一百零八》是系列作品里引入沉默段落最多的一部,开场便是长达一分三十秒的静默,但静默并非无声,我们能从中隐约听到环境空间震颤的声音——淅沥的雨声、嘀嗒的水流声以及远处的风声。在沉默段落的映照下,声音段落的起落似乎有了更多氤氲的回响。在看似无声的瞬间,作曲家的留白给予演奏者和听众思考、参悟的机会。此刻,时间与空间重合,视觉和听觉融合,听众与演奏者交汇。
数字音乐系列作品也可以两两组合,《一百零八》往往与大提琴独奏作品《一8》或日本雅乐笙独奏作品《一9》一起演奏。当它们组合出现时,你也可以将其视为协奏曲。这时你可以称组合作品为《一8和一百零八》(One8 and One Hundred and Eight)或《一9和一百零八》(One9 and One Hundred and Eight)。
《一8》包括五十三个自由的时间括号,由大提琴家迈克尔·巴赫(Michael Bach)用他自己发明的弯曲的琴弓来演奏,以表现微分音技法带来的绵延性与持续性,声部的音色层次更细密。粗扁、沙哑的持续音仿佛硬物在岩石上用力摩擦产生的效果,但再浓重的纹路也会被消磨殆尽,好像被时间洗礼的岩画,轮廓已不再清晰。
当《一8》与《一百零八》同时进行时,由于时间括号的重叠,大提琴在某些沉默段落亦能发出声音。因此,有些思考的空间被压榨了,有些曾经躁动的时刻却又倏然静默。《一9和一百零八》的设计则更为巧妙,充分表达了凯奇对东方哲学的理解与审美倾向,其中笙的加入让《一百零八》更有水墨意韵。
《一9》由十个灵活的时间括号组成,其中的材料可以在没有伴奏的情况下演奏。这部作品是凯奇为日本雅乐笙(唐代从中国传入日本,并保留唐制,为十七簧笙)演奏家宫田真由美而写的。1990年,两人相识于达姆施塔特音乐学院,凯奇被雅乐笙的声音迷住了,形容该乐器在《一9》里的音色为“如东方水墨般透过画笔流淌而出”。
在笙与乐队交汇的段落,音响效果愈发饱满充沛,结构也被强化了,笙的独特音色赋予了作品古朴的韵味。高涨的音势没有持续太久,很快又随着疏散的音高减缓。笙的高音音色透亮而尖锐,同为长音,终究比不上弦乐部分那般柔和。随着乐曲进行,乐队的声音逐渐稀薄,笙的长音逐渐得以凸显,颇有些许问询的意味。当笙的部分与《一百零八》的沉默段落重合,整部作品便仅剩寥寥数音与大量的留白。不同音高之间相距极远,在缓慢的时间进程里音乐的气息被拉长了,寂寥空旷的意境在这样洗练的“笔触”下自然显现。每一个单音最终都被细密地渐弱了,在静默中留下了几抹微妙的痕迹,混沌的时间与空间为笙明亮的音色笼上了一层雾霭,世界一片鸿蒙。

《一百零八》本身沉默的空间因为组合演出而被占据了,笙的问询之声也似乎扰动了原有的沉默气氛。但回响的空间里,在声的不断变异,有声与无声之间,听者的时间感被强烈冲击,感受到了一个从未发生过改变的东西。
沉默不再是一种构成要素,而是一种“自在”;不是无声,而是声音的自行其是;是一种行动并激发着新的行动。凯奇不再拘于追求形式上的静默,他努力探索着非动亦非静的永恒。
音乐比诗歌和视觉作品的自由度更大,后两者一旦呈现,便可能幻化为时空的定格。而凯奇的音乐可以在表演中发生变化——时间括号为作品中的声音提供了适度的自由,因为每一次演奏都可以有所不同。凯奇曾解释这个时间过程像是“天气”,表演者在设定的范围内可以随心所欲地使声音变短、变长、变响、变轻,音乐如天象般变幻莫测。当多个演奏者各自拥有一定的自由时,彼此的演奏也会根据其他演奏者的选择而产生新的效果,音的长短、轻重、厚薄、明暗就产生了更多样的层次。
时间括号里持续不变的时间勾勒出了作品骨架,其中由每一个音高引导的声音事件的时间顺序也大致相同,但具体每一个音高的起落点却总是不同的。同样的天地间,不同的“天气”,音乐被重新定义。时间括号的使用让“道”显形。
从演奏的角度来说,表演者好像被迫置身于一个类似禅坐的环境里,音符并不密集,又有大段的沉默、留白,在舞台上不能时时有所为,杂念和技术薄弱处都更容易显形,反倒增加了表演难度。就像书圣王羲之信手拈来的一个“点”,其功力远远深厚于少年献之的“大”字。作为演奏者,究竟是献之还是羲之?凯奇的作品真的如戏谑调侃的言论所说,不需要技术吗?表演者在演奏他的音乐时,必须面对自己,看见自己,奉献出最纯然的自己。

而这一切的背后,又有一个无形的力,主导着舞台上的发生。无常的自然、日常的生活被作曲家浓缩在舞台上,每一个演奏者看似有选择,却仍被未知推着走。作曲家看似没有展露自己任何的意愿,实则却牢牢握紧了指挥棒。正如凯奇在1967年的《从星期一开始的一年:新的演讲和作品》(A Year from Monday: New Lectures and Writtings)中写道:“艺术的功能是模仿自然的运作方式。”这句话在他的创作中被贯彻始终。
凯奇的朋友们曾在受访时谈论起他使用硬币进行作曲的方式。凯奇并不关心硬币、数字对应的卦象内容,他感兴趣的是数字本身,数字的产生过程,与声音进行对应时的复杂关系。“我认为,声音之间的关系就如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比我所能探寻到的更为复杂。因此通过简单地放弃选择的权利,我才不会失去那种关系。我尽量保持自然的复杂性,并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来观察。”凯奇的音乐仿佛能映照出天人关系。他把对“道”的求索倾注在他的晚期作品中。
曾在凯奇的拍档——先锋舞蹈家康宁汉的学校研习现代舞的编舞家林怀民在他的《松烟》里用到了凯奇的《一百零八》。林怀民对《松烟》的构想源于中国书法,他希望舞者可以体现出安静、稍纵即逝的状态。“松”是人的身体,庄严肃穆;“烟”则是舞蹈的表情。作品呈现出了书法艺术生动的气韵和笔墨以外的留白。凯奇曾在访谈中说,他试图使数字音乐像在水面上写字一样——一个无比优雅的动作,不会留下任何痕跡。在美学上,林怀民与凯奇是一致的。当舞者在以放大数百倍的宋代瓷器的蟹爪纹和冰片纹做成的布景舞动身姿时,《一百零八》的清、透、空、静成了《松烟》所追寻的东方古典精神。

林怀民在受访时说,西方的朋友常常对中国人所说的“气韵”感到难以捉摸,而凯奇却用十分西式的乐器配置,呈现出了深具东方哲学精神的寻道之乐。
凯奇的晚期作品,之所以可以跨越东西方文化差异,是因为他自身的创作就包含不分东西的共性——自然为出发点,以硬币为笔,用机缘作乐,最终在音乐里实现了“无我”的境界,这与中国传统文化所追求的“天人合一”不谋而合。这位颠覆了西方二十世纪下半叶艺术的艺术家,用一生无畏践行着自己的极端“实验精神”,历经数个风格阶段,将高度概念化、形式化的沉默演化为与天地融合的清寂永恒。
“经过这么多年,我终于写出了美妙的音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