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与影:塔诺波斯基的多媒体歌剧《影子之上》
宋冉

1955年4月,弗拉基米尔·塔诺波斯基(Vladimir Tarnopolsky)出生在乌克兰东部的一座港口城市。他从小便对音乐有着浓厚的兴趣,长大后,他进入莫斯科音乐学院学习作曲和音乐理论,后成为莫斯科音乐学院教授,现就职于德国慕尼黑大学。他创作了许多不同体裁的作品,如为女高音和钢琴而作,取材于苏联作家、诗人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来散落一些话吧……》的《散落的话》;取材于契诃夫的著名剧作《三姐妹》《海鸥》与《万尼亚舅舅》的歌剧《三姐妹》。他的音乐作品获得过诸多奖项,包括肖斯塔科维奇奖、欣德米特奖等。
塔诺波斯基的多媒体歌剧《影子之上》(Beyond the shadow)以柏拉图的洞穴寓言为灵感,作曲家和编剧想要通过歌剧的形式表现出寓言中光明和黑暗、真相与表象之间的斗争。这部作品是由贝多芬音乐节委约创作的,首演于波恩,来自纽伦堡的艺术家巴比斯·帕纳约蒂斯(Babis Pangiotidis)将声音转化为幽灵般的互动灯光,以现代的方式诠释柏拉图的理论。
柏拉图的影子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讲到一个关于洞穴的神话故事。他設想有这样一个洞穴,它有一条长长的通向地面的通道,和洞穴等宽的光线能照到洞底。有一些人从小就住在这个洞穴里,他们的脖子和腿脚被捆住了,无法走动,也无法扭头去看,只能朝前看到洞穴的后壁。他们背后远处高的地方有些东西在燃烧着发出火光。火光跟这些被囚禁的人之间有一堵矮墙,沿着这堵墙有一条道路,矮墙的作用就好比木偶戏演员和观众之间的屏障,有人举着用木头、石块或者别的材料制成的假人或假的动物从矮墙后经过。假设其中有囚徒被释放出来,在他眼睛直视光亮时一定非常痛苦。此时如果有人告诉他,往日他所见到的东西都是虚假的,现在看到的才是真实的事物,他会做何反应?如果让他重回到洞穴之中,他是否会觉得黑暗?
书中关于洞穴囚徒的一系列问答想要讨论的是人性开明者与人性封闭落后者的本质差别。在囚徒没有转过身之前,他会认为墙壁上的影子是真的。但只有在转身面对太阳时,他才能看到真相。


从古希腊至今,影子在艺术领域是一个永恒的课题。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艺术家们对影子有了新的诠释。有的认为影子使他们想起了死亡,有的认为影子是一种早期照片,还有认为影子是一种精神骗术的,诸如此类。
柏拉图的洞穴理论不单存在于哲学和艺术中,它已渗入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一刻。现代人习惯于固定的生活模式,喜欢待在舒适圈内。如果突然让他做舒适圈外的事情,他就会感到不适应和痛苦,此时就深陷柏拉图所说的囚徒困境中无法自拔。
歌剧《影子之上》以柏拉图的洞穴理论为依据,剧中的主人公就像洞穴里的人一样。作曲家用灯光和音乐声来模拟洞穴理论中的日光和交谈声,让主人公被视觉和听觉的“光”牵着走。
“影子”结构与设计
歌剧由七场组成,其中第七场又可分为A、B、C三段,因此总共有九个段落。剧中共有五个声乐段落,其余为编舞段落和器乐段落。这部歌剧不是在讲述一个连贯的故事,而是以“影子”作为每一段的核心进行串联,每个段落都是分散、各自独立的。作曲家从柏拉图、普林尼、但丁等多位哲学家的观点中汲取灵感,融入到歌剧中。
不同于传统歌剧的大篇幅歌唱,这部歌剧声乐的比重减少,旁白和舞蹈的比重增加。演唱者们没有具体的人物角色,他们代表的是抽象的事物。因此,作曲家为了弱化角色的个人色彩,强调无法被具象化的事物,没有设置独唱段落,所有的歌唱段落都是重唱。歌词也没有使用对话体,没有独白,而是诗歌的形式。歌词传递的是哲学理论、观点或描述哲学故事中的场景。歌唱成了作曲家传递观念和想法的窗口。
由于歌剧叙述方式的特殊性,下面我将选取比较有代表性的四个场次进行讲述。
洞穴理论主要出现在第五场《山洞里的囚徒》,开场时地上投射出许多单词,表演者走过时会有光照在身上。伊始,囚徒们在无声地歌唱,仿佛声音被外界切断。后来终于开始歌唱,他们唱着“一直以来,我们都在走过一个巨大的灌木丛……走出山洞,比紫色深得多,最暗的黑暗。这里是最深、最黑暗的护城河……”囚徒们此时好像已经看过洞穴外面的世界,发现外面的世界被最暗的黑色所包围。
在这之后,囚徒们的正面影子被投射在舞台背后的半球体上,侧面影子被投射在舞台右侧的墙壁上,这两种影子都比身体要大许多。“来自星辰的光线使影子和身体的比例基本相当,而来自火光的光线使影子比身体要大得多。”因此可以推测这是被洞穴里的火把照射形成的影子。《影子简史》中认为侧面的影子代表着自我,结合开场时囚徒们所唱的歌词,可以推测囚徒们已经见过外面的世界,自我意识有所觉醒。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再次回到洞穴,又要被限制活动,是否会产生出不甘的心情?

高潮部分,半球体上投影出类似池塘中浮游生物的画面,它们也许暂时被困在池塘中,但终有一天可以逃离。被困的囚徒也是一样,自我意识觉醒之后,灵魂就能从黑暗的世界前往光明的世界。在这一场的结尾,舞台陷入黑暗之中,三名囚徒再一次被束缚在洞穴中,不知何时才能挣脱。
第三场《艺术三重唱》和第四场《女孩追踪着她爱人的影子的轮廓》分别是根据神话人物美惠三女神的故事和普林尼在《博物志》中所说的一个故事而作。
美惠三女神(The Graces)指的是希臘神话中分别代表妩媚、优雅和美丽这三种品质的三位美丽女子。她们是众神的歌舞演员,为人间带来美丽、欢乐,美惠女神的生活是希腊人所追求的生活。歌剧第三场由三名女歌唱家分别饰演三女神,她们出场时站在舞台左侧的三根巨大空心柱中。当灯光亮起,她们唱道“我们是三种艺术……我们是神性的光……我们生活在美丽之中,我们在爱中生存,光是我们的生命”。
普林尼的哲学故事大致讲述的是一名制陶工的女儿爱上了一个男孩,在男孩即将远航时,女孩根据油灯光照下男孩投射在墙上的影子画了个轮廓。她父亲将黏土敷在这个轮廓内,制作出一件浮雕作品。普林尼笔下的这个故事表明了影子与时间的关系,阳光下的影子表示时刻的变化,但夜晚的影子是无法表达自然时间的,流动的进程在它身上停止。在歌剧中这一场由两名舞者表演,男舞者寓意囚徒,女舞者寓意艺术。作曲家将普林尼的故事与柏拉图的理论相结合,再借用神话中的人物,形成了第四场。
第七场又分为A、B、C三个段落。之所以要单独分出三个段落,而不是将其变成第八、第九场,是因为它们相互关联。虽然段落标题之间关联性不大,但内容是连续的,一名黑衣舞者作为主角从始至终处在舞台上。伴随着舞台灯光的变化,他仿佛从迷茫走向光明,最后出现了一名白衣舞者,代表的可能是他想寻找的真理。在洞穴理论中,影子作为距离太阳最远的阶段,也是离真理最远的阶段。A段黑衣舞者在舞动时,身后的背景板上投射着他的影子,而在B段和C段时影子消失了,这代表着他离真理越来越近。最后囚徒和女神们呆滞地在一旁看着两名舞者共舞,仿佛黑衣舞者已经脱离洞穴到达了外面的世界。
声音与光影
作曲家利用乐器的特殊色彩性表现以及音色的对比塑造出了光与影的变化,并且通过改变发声方位,使听众有了不一样的观剧体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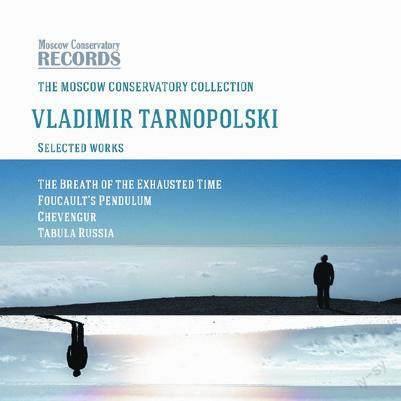
在常规乐器的使用上,塔诺波斯基在乐曲很多地方扩展了音区的使用范围。例如在第五场,小提琴在极高和极低音区间跳跃,得到一种尖锐刺耳的效果,为作品带来了怪异的听觉感受。除了对音区的扩展使用,作曲家还使用弱音器,获得了更柔和、朦胧的音色,同时增加了幽默感。此外,演奏技法的创新也创造出了新的音色,这样的音色变化让音乐变得丰富、生动起来。
在《影子之上》中,塔诺波斯基偏爱木管音色,其他音色大多情况下都是伴奏。歌剧的气氛螺旋上升,为了配合不同的情绪,所使用的乐器也不同。当需要叙事或表达平和情绪时,木管音色就会大量出现;当激烈争论或表达激动的情绪时,打击乐和铜管乐与木管、弦乐相配合,增加乐队的整体强度,提升气氛。
器乐曲被穿插在场与场之间,相互关联。它们穿插在声乐曲与舞蹈之间,如同阴影中突然出现的一束光。这些器乐曲所用的乐器音色以弦乐和木管音色为主,做到了前后统一,更加凸显出它们之间的联系。
这部歌剧特殊之处在于管弦乐队所处的位置。两个管弦乐组在左右两侧的阳台上,膨胀、消失、聚集在一起,有时在左有时在右,制造出一个会呼吸的空间。一层层和弦在声波冲击下颤动,堆积成越来越强的波浪。在演奏中,指挥家精确指导的合奏形成了横向的潮汐效应,似乎要把音乐厅溶解。作曲家这样做的原因有二:第一是声音从左右两侧传到观众席,会给听众们带来听觉上的新鲜体验;第二是弱化管弦乐队的存在感,以使观众将视线集中在舞台上。
影子折射
影子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埃及和古希腊时期,如今我们都在续写影子的历史。塔诺波斯基也是影子历史的续写人,他没有用生涩难懂的音乐语言去刻意营造哲学氛围,正如《法兰克福汇报》所说,这部歌剧“与那些认为现代艺术已成为哲学的诊断相反,这种音乐让所有的人都能感受到,音乐让所有的哲学沉入痛苦的、愉悦的声音岩浆中”。在优秀艺术家们的帮助下,多媒体与歌剧非常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光在舞台上的半球体上徘徊,使之变成一个新的舞台。美惠三女神和山洞囚徒模糊成两道声线,黑衣舞者与白衣舞者在尽情地跳舞。

两千多年前的古老命题至今仍焕发生机,是因为不断有人往里注入活力。柏拉图的影子话题在各个时期都以不同的方式被人提及,如此庞大的思想之山,想用歌剧来表达实际上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对传统的再诠释表露出作曲家的民族特性。塔诺波斯基曾说:“在俄罗斯,作品实际是征服某种混乱的过程,这是在大自然的船上冲浪,是一种充满戏剧性的尝试。”在不断的尝试中,古老的命题才得以生机勃发。
《影子之上》与塔诺波斯基以往作品不太一样的是以哲学故事为依据,在光和声音的空间里娓娓道来关于光和影的故事。塔诺波斯基虽然不被大众所熟知,但他对世界上许多作曲家都有着深刻的影响,中国音乐界对他也有所关注。塔诺波斯基坚持着自己的个性,发出自己的声音,用《影子之上》为当代音乐找到困境中的突破,寻找到那一缕光明。
“人们想获得自由,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不能。他们说他们想看到真理之光,但他们做不到,许多人甚至没有试图找到一条路……这就是柏拉图所说的‘大多数人没有希望。深刻的悲哀在于戏剧本身。但生活就是这样,我们必须接受它并努力走向光明——在艺术的帮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