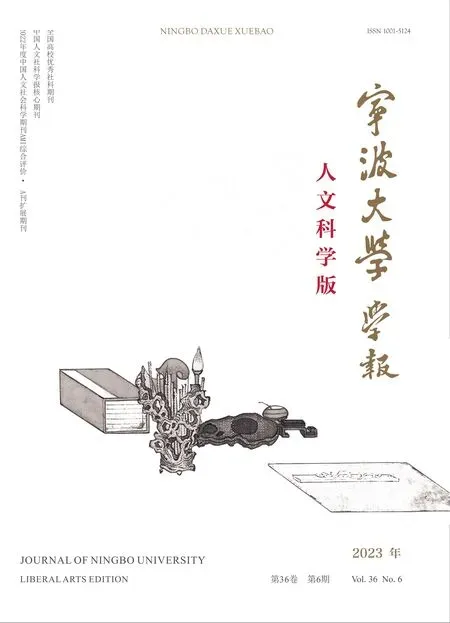论谢灵运山水诗的时空、行迹书写与景物刻画
马黎丽
(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贵州 兴义 562400)
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之二十认为柳宗元深得谢灵运诗歌情韵,故曰:“谢客风容映古今,发源谁似柳州深?朱弦一拂遗音在,却是当年寂寞心。”[1]12对于政治失意、身被贬谪、在山水间寻求心灵慰藉的谢、柳二人来说,“寂寞心”三个字,是把握住了他们山水诗作的深意和用心。谢灵运诗歌的山水书写中蕴含的情感,与柳宗元《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海畔尖山似剑铓,秋来处处割愁肠”[2]124的直抒胸臆相比,往往显得比较含蓄和隐蔽,但其诗歌中惯见的时空、行迹书写与景物的细致刻画,实际负载了许多深切感受乃至痛苦体验。
一、时空的大幅开阖与情感的起落
谢灵运诗歌有大量对时空开阖的书写,即顾绍柏所言“境界开阔”,“在有限的篇幅里包容万千气象”[3]24-25。永初三年(422)谢灵运被贬出京城,出为永嘉太守[4]1753,从他出守永嘉到第一次隐居始宁期间所作的一系列诗歌①,集中显现了命运的变化带来的情感起落,既能代表谢灵运山水诗的成就,也突出地反映了谢诗中时空开阖与情感起落紧密相关这一特征。
谢灵运离别京城之际作《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发都》[5]35:
述职期阑暑,理棹变金素。
秋岸澄夕阴,火旻团朝露。
辛苦谁为情,游子值颓暮。
爱似庄念昔,久敬曾存故。
如何怀土心,持此谢远度。
李牧愧长袖,郄克惭躧步。
良时不见遗,丑状不成恶。
曰余亦支离,依方早有慕。
生幸休明世,亲蒙英达顾。
空班赵氏璧,徒乖魏王瓠。
从来渐二纪,始得傍归路。
将穷山海迹,永绝赏心悟。
诗歌开篇写“述职期阑暑,理棹变金素”,即蕴含着一个时间的大幅变化。诗人原定于夏末启程,却一直延宕到秋初[5]36。这持续半个月的延宕过程,暗示了诗人内心的拒斥、不甘和怨愤。顾绍柏《谢灵运集校注》中明确指出这首诗歌不仅表达了对故土知己的依恋,也抒发了生不逢辰的慨叹,间接流露了对徐傅集团的不满[5]35-36。“秋岸澄夕阴,火旻团朝露”二句描写离京前夕的情形,内心极度不平的诗人在水边滞留了整整一晚,从秋阳西下,堤岸在澄净的水中投下倒影,一直呆到秋晨的草叶上凝结着一颗颗露珠之时②。细致的景物描写,正是诗人借仔细观察自然景物以排遣牢骚惆怅的行为。这种从夏到秋、从暮到朝的时间开阖,使得诗人内心的苦闷被拉长和延续,变得更为深广。
《初发都》之后诗人所作的《邻里相送方山》[5]40,开篇写“祗役出皇邑,相期憩瓯越”,隐含着一个大幅度的空间变化。作为政治中心的“皇邑”,和地处偏远的“瓯越”,代表了诗人截然不同的两种命运,否泰的变化和起落,通过两个相隔甚远的地点得以表现。诗人貌似只是平静地叙说行程的起点和终点,实际却通过巨大的空间隔阻表达了内心的失意。从“皇邑”到“瓯越”,巨大的空间距离形成无情的障碍,将诗人与亲友隔阻两地。所以诗人按捺不住内心的悲忧,直抒胸臆地表达了对亲友的依依不舍:“解缆及流潮,怀旧不能发。”[5]35
最典型的时空开阖变化,集中在谢灵运的记游诗歌里,通常用在开篇以概述行程。如谢灵运经过富阳游览富春江时所写《富春渚》[5]45:
宵济渔浦潭,旦及富春郭。
定山缅云雾,赤亭无淹薄。
溯流触惊急,临圻阻参错。
亮乏伯昏分,险过吕梁壑。
洊至宜便习,兼山贵止托。
平生协幽期,沦踬困微弱。
久露干禄请,始果远游诺。
宿心渐申写,万事俱零落。
怀抱既昭旷,外物徒龙蠖。
“宵济渔浦潭,旦及富春郭”,在时间上从暮延续到朝,空间上从渔浦潭跨越到富春郭[6]378,也是一个谢诗常见的大幅度的时空开阖,仔细体会,能感受到其中隐含着一个匆促紧张、分秒必争、马不停蹄的行人。夕发朝至的旅程,不仅意味着赏玩美景的急切,更多的是诗人需要借助这种疲惫的游览方式,来纾解和忘却内心的郁结。诗人感叹自己“平生协幽期,沦踬困微弱”,但是在行舟急流的惊险旅程中,诗人久困官场的郁结得到了宣泄,不禁庆幸自己此番虽身被贬谪,却能实现远游的夙愿,抛却尘世俗事。
谢灵运还有很多朝出暮归的记游诗,在时空的大幅开阖中,隐含着对世道、人生的失望以及对自身的宽解和劝慰。如《石壁精舍还湖中作》[5]112:
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
清晖能娱人,游子憺忘归。
出谷日尚早,入舟阳已微。
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
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
披拂趋南径,愉悦偃东扉。
虑澹物自轻,意惬理无违。
寄言摄生客,试用此道推。
开篇是典型的谢氏记游风格:“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昏旦”一句概括了山中从早到晚景色的变化,暗含了诗人朝出暮归的行程。这首诗歌描写景物尤为精工巧似,是谢灵运山水诗的代表作。诗中对景物的刻画真实生动,别具匠心,展示了诗人游览山水之至乐。然而诗歌结尾部分却突然归结到“澹泊寡欲,以山水自适的道家思想”[5]112上去,这种谢氏结尾广为古今论者诟病,被命名为“玄言尾巴”,被视为玄言诗的遗留[3]27。
但是抛却玄言诗的影响不论,这种与前面美景刻画部分看似颇为脱节的结尾,实际上隐藏着诗人对苦闷心绪的努力排解和自我宽慰。此首作于景平二年(424)夏[5]112,是谢灵运辞去永嘉太守任的次年[4]1754,诗中颇有无官一身轻的轻松惬意。“出谷日尚早,入舟阳已微”,很明显,此番出山入湖、早出晚归的行程,依旧十分紧凑,甚至颇为急促。这种快节奏、高强度的行程,依然有着通过身体的疲惫忘却烦恼的用意。结尾部分的玄理之谈,看似是诗人试图以自身经验对他人有所启发,颇有骄矜之意味,但其中的无奈和情非得已亦是比较明显的:只要思虑淡泊,外物就微不足道;只要心无挂碍,就不会违背道的原则。这些道理,对于政治上遭遇打击排挤的士族子弟谢灵运而言,无疑是时时必须的自我宽解和劝慰。在“昏旦”和“山水”构成的阔大时空中,独自匆促行走的诗人形象依然带着些许焦虑孤寂的意味。
若以陶渊明诗歌进行比较,谢诗的特点会更为明晰。以《归园田居》为例,“少无适俗韵”一首中,陶渊明描写了从草屋到远村的一个较为阔大的空间:“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7]55这个空间是随着诗人的目光由近及远有序而徐徐展开的,诗歌节奏舒缓,人物悠闲自适。再如“种豆南山下”一首,诗人书写了种豆南山、荷锄狭道的空间变化,以及从晨兴到带月的时间变化,但整首诗歌仍是舒缓闲适的,人物形象从容不迫。如果说这两首诗的舒缓从容主要得自于诗人情绪的稳定,那么“久去山泽游”则是另一番景象。“久去山泽游,浪莽林野娱。试携子侄辈,披榛步荒墟。徘徊丘陇间,依依昔人居”[7]59,诗人携带子侄探访林野,在郊野荒坟之间发现了前人居住过的痕迹,于是深切感悟“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7]59,充满感伤消极的人生无常之叹。尽管诗人内心十分痛苦,但是从林野到丘陇的阔大空间,仍然是有序而徐徐展开的,其间的诗人,虽唏嘘不已,却步履从容,表现出看透人世沧桑的冷静和睿智。
陶渊明是对官场失望后主动归隐的,所以他无论是处在怡然的心境还是疲累的处境或是感伤的心绪之中,都能保持内心的从容淡定,他诗歌中的时空总是徐徐展开,诗中的人物步履亦总是不疾不徐。谢灵运则不同,他因政治迫害而遭遇贬谪,心中的不平和愤激之情,很难彻底平复。
对于这种寄情山水却难以真正获得心灵解脱的困境,在离开建康、初发永嘉之时,谢灵运就进行了预言:“将穷山海迹,永绝赏心悟。”[5]35失去知己相赏的山水之乐,其底色永远是感伤失意的。这种感伤失意在谢诗中时有浮现,如亦作于第一次隐居始宁时期的《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5]118:
朝旦发阳崖,景落憩阴峰。
舍舟眺迥渚,停策倚茂松。
侧径既窈窕,环洲亦玲珑。
俯视乔木杪,仰聆大壑淙。
石横水分流,林密蹊绝踪。
解作竟何感,升长皆丰容。
初篁苞绿箨,新蒲含紫茸。
海鸥戏春岸,天鸡弄和风。
抚化心无厌,览物眷弥重。
不惜去人远,但恨莫与同。
孤游非情叹,赏废理谁通?
开篇“朝旦发阳崖,景落憩阴峰”,概述了日出到日落、从南山往北山途经巫湖的行程,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一个大幅度的开阖。诗中记述了于巫湖中所见美景,但是诗人的内心并没有得到抚慰,他慨叹“不惜去人远,但恨莫与同。孤游非情叹,赏废理谁通”,字里行间充满孤独失意之情。顾绍柏认为“赏废”指的是“好友在一起能赏心吐胆”的“赏心”随着挚友庐陵王刘义真被杀而废止[5]120,从这个意义上讲,诗歌中蕴藏的就不仅止于感伤失意,更有隐秘的悲愤之情。这些幽微的情感,隐藏在时空的巨大开阖中,诗人仿佛一只渺小而执著的困兽,在山水之间焦躁地游走,借以稀释和消弭内心的烦恼。再如《登上戍石鼓山》“极目睐左阔,回顾眺右狭”[5]68之句,阔大的空间,以及“日没涧增波,云生岭逾叠。白芷竞新苕,绿苹齐初叶”[5]68的美景,都未能抚慰诗人内心的苦闷,他感叹“佳期缅无像,骋望谁云惬”[5]68。阔大的空间,寂然的美景,映照出诗人的孤独愁苦。
谢诗中时空的大幅开阖通常作为对行程的概述出现在诗歌的开头,有时候这种时空的开阖也会在诗歌中间突然出现。如知永嘉时所作《晚出西射堂》[5]54:
步出西城门,遥望城西岑。
连障叠巘崿,青翠杳深沉。
晓霜枫叶丹,夕曛岚气阴。
节往戚不浅,感来念已深。
羁雌恋旧侣,迷鸟怀故林。
含情尚劳爱,如何离赏心。
抚镜华缁鬓,揽带缓促衿。
安排徒空言,幽独赖鸣琴。
开篇写向晚时分“步出西城门,遥望城西岑”,所见“连障叠巘崿,青翠杳深沉”,本是青翠幽深的景象,诗人突然笔锋一转,从秋晨开始书写:“晓霜枫叶丹,夕曛岚气阴。”晓霜和丹枫一下子打破了深色的宁静的画面,诗人内心的情感瞬间流动起来,从清晨白霜丹枫的冷艳,一直流向傍晚青峰山气的暗沉,形成时间的开阖和空间的变化,仿佛诗人心灵的木门一开一合、吱吱呀呀,放出许多年华易逝、孤独苦闷的心绪:“节往戚不浅,感来念已深。”时光的流逝未曾冲淡诗人内心的感伤和不平,只要稍稍有所感怀,被刻意压制的情绪便汹涌袭来。
可见,谢诗中时空的开阖对应着情感的起落变化,时空的巨大开阖,映衬出诗人匆促行走、东奔西突的孤独形象③,以及诗人的微渺与别无选择。时间和空间的开阖变换,是命运对诗人无情的抛掷,也是诗人内心愤激不平之情兴起的波澜。
二、变换不定的行迹与情感的起落
在阔大的时空中,为了排遣忧闷,谢灵运始终不停地在山水之间奔波游走。大好河山带给他心灵的慰藉,但并不能完全消除他内心的痛苦。挥之不去的失意和不平常令诗人心底兴起波澜,这种情感的波动不仅形成诗歌时空的大幅开阖,亦形成诗歌中诗人行迹的变换不定和由之而来的错综复杂的画面。
《过始宁墅》作于“赴任途中经过故宅家园之时”[5]41,“表达了对仕途的厌倦、故乡山水的依恋和打算回归隐居的心愿”[8]30:
束发怀耿介,逐物遂推迁。
违志似如昨,二纪及兹年。
缁磷谢清旷,疲苶惭贞坚。
拙疾相倚薄,还得静者便。
剖竹守沧海,枉帆过旧山。
山行穷登顿,水涉尽洄沿。
岩峭岭稠叠,洲萦渚连绵。
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
葺宇临回江,筑观基曾巅。
挥手告乡曲,三载期归旋。
且为树枌槚,无令孤愿言。
诗歌不宁静的心绪,集中反映在诗人变换不定的行迹之上。“山行穷登顿,水涉尽洄沿”二句的含义是说自己“已游遍故乡的山山水水”[5]44。“上山叫登,下山叫顿”,“逆流而上曰洄,顺流而下曰沿”[8]31。两句十分凝练地概述了自己遍游家乡山水的情形。孤独的诗人,在这个空间里上下疾行:“岩峭岭稠叠,洲萦渚连绵。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葺宇临回江,筑观基曾巅。”他忽而在山岭,忽而在洲渚,忽而看天上的白云,忽而看林间的细竹,忽而身临回江,忽而伫立山巅,快节奏的画面切换,给人一种应接不暇的紧张感。这忽高忽低的空间变化和错综的景象,折射出诗人的行止不安与心绪不宁。正如陆机《猛虎行》抒写自己心中的郁结不平,亦是通过忽而在山巅、忽而在谷底的行迹变换进行表现:“长啸高山岑,静言幽谷底。”[9]666《猛虎行》中的行迹变换亦包含了空间的大幅开阖,在这巨大的空间之内,诗人行迹的快速切换,传达出内心的不安和焦躁。
有时候,诗人的行迹是清晰的,诗歌画面也是有序的,但是仍然无法消弭诗歌内蕴的紧张感。如《夜发石关亭》:“随山逾千里,浮溪将十夕。鸟归息舟楫,星阑命行役。亭亭晓月映,泠泠朝露滴。”[5]50山行千里,水行十夕,每天傍晚歇息,星阑赶路,长时间、远距离、快节奏的行程,营造出匆忙急促的紧张氛围。尽管结尾两句描写了宁静美好的晓月清露,但这仅仅只是诗人踏上新的路途之前瞬间的凝神,这一瞬间仿佛涌出许多喷薄欲出的情绪,但是诗人欲言又止,并将它们凝固在一个清冷的画面里,那一颗颗坠落的露珠,在晓月的映照下,为诗歌增添了几许孤凄的况味。
谢诗行迹的变换不定,常蕴含着诗人隐秘的不安心绪。如《登永嘉绿嶂山》[5]56:
裹粮杖轻策,怀迟上幽室。
行源径转远,距陆情未毕。
澹潋结寒姿,团栾润霜质。
涧委水屡迷,林迥岩逾密。
眷西谓初月,顾东疑落日。
践夕奄昏曙,蔽翳皆周悉。
蛊上贵不事,履二美贞吉。
幽人常坦步,高尚邈难匹。
颐阿竟何端,寂寂寄抱一。
恬如既已交,缮性自此出。
这首诗歌作于永初三年深秋,顾绍柏认为诗人“带着浓厚的兴趣遍游绿嶂山……暗示自己要弃职归山,做一个高尚的隐者”[5]56,李运富认为诗人“陶醉之余,颇为自己能参透玄理、不累政事而移情山水的高尚品行宽慰”[8]39。两位学者都认为诗歌中的情感是愉悦轻松的。但是,仔细观察诗人的行迹,会发现诗歌中同样深蕴着难以消弭的不安和焦躁。诗人笔下描摹的绿嶂山之秋水、修竹十分动人:“澹潋结寒姿,团栾润霜质。”但是接下来诗人笔下的行程开始变得迷乱起来:“涧委水屡迷,林迥岩逾密。眷西谓初月,顾东疑落日。践夕奄昏曙,蔽翳皆周悉。”诗人沿着溪涧行走,前路曲折,诗人多次辨不清去向。待走到水穷处[5]57,诗人舍岸登山,深林杳然,层叠的岩石愈发高密,诗人顿觉恍惚迷离,一时间辨不清天上是初月还是落日。当天色暗下来,他把“树林和山崖最幽深最隐蔽的地方”“全都游览到了”[8]39。
诗人或许只是游兴盎然,在溪涧与密林中盘桓终日,天色已晚尚流连忘返;但是从诗人的行迹来看,从溪涧到山林,诗人多次不辨方向且恍惚迷离,天黑之后仍在密林中探寻,这时的行迹并不具有清晰的线索,而是变换不定,显示出诗人是在昏暗的密林中漫无目的地四处游走。这种终日不肯歇息,甚至在密林中逗留到傍晚的游览方式,显然是不符合常情的。纵然密林中别有风景,但夕阳西下之后深林尤为昏黑荒寂,诗人又怎能领略呢?所以“蔽翳皆周悉”,不像是游兴未尽的行为,更像是忧闷来袭之时的焦躁不安。因此接下来诗人谈玄说理,以“蛊上贵不事,履二美贞吉”表达不以做官为贵、而以坦荡为美的愿望,表达对“幽人常坦步,高尚邈难匹”的向往等,其实正是自我宽解和自我劝勉。
谢灵运书写景物,较少进行有序的书写,他常有意打乱空间顺序,增添行迹不定之感,这样的写作手法有时会带来读者理解上的差异。如《石室山》一首,诗中的石室山据顾绍柏考证位于永嘉郡郊外楠溪江畔,诗歌开篇即言“清旦索幽异,放舟越坰郊”,说明石室山是一个人迹罕至之地。其地得山水之妙:“莓莓兰渚急,藐藐苔岭高。石室冠林陬,飞泉发山椒。虚泛径千载,峥嵘非一朝。”[5]72此六句中,诗人将空间顺序打乱,开始是上句写兰渚,下句则写苔岭,接下来的两句都写山上的景物(林木、瀑布),再接下来又是上句写水的全貌,下句写山的全貌。李运富认为“虚泛”一句应“兰渚”一句[8]50,顾绍柏则认为“虚泛”句承“飞泉”句[5]73,顾绍柏将“虚泛”释为“水之广大”,笔者认为用来形容飞泉并不恰当,还是理解为呼应“兰渚”为佳。这种理解上分歧,正是由于诗歌中诗人行迹不定、画面错综复杂导致的。《石室山》以“灵域久韬隐,如与心赏交”[5]72,表达石室山久不为人所知、如今却得为己见的欣喜,将人与山比喻为知己。这是诗人在大自然中获得的心灵慰藉,但同时也正凸显了诗人在人间的孤独和落寞。
“怅恨独策还,崎岖历榛曲。山涧清且浅,适以濯我足。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欢来苦夕短,已复至天旭”[7]60-61,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开篇直抒胸臆,点明怅恨之情,但是随着诗人行走山路、濯足山涧,他的心情渐渐明朗起来,于是归家盛情款待近邻,“欢饮达旦。诗中虽有及时行乐之意,但处处充满纯朴之情”[7]61。谢诗往往是乘兴出游,兴尽却难免心生惆怅。陶诗却是怅恨独返,于山水之间得到慰藉;谢灵运始终难以消除内心的忧闷,陶渊明则往往能够得到解脱;谢诗中诗人常行迹不定,诗歌画面错综;陶诗中诗人行迹则有条不紊,不疾不徐,榛曲,山涧,村居,行程依次展开,情感欣喜而又宁静。或许陶渊明笔下多有二三素心人相伴,诗中常有田园的暖意。谢灵运笔下多是山水间的独游,诗中常有孤寂凄冷的况味。诗人行迹与情感起落的对应,在谢诗中无处不在[8]45。如《东山望海》④:
开春献初岁,白日出悠悠。
荡志将愉乐,瞰海庶忘忧。
策马步兰皋,绁控息椒丘。
采蕙遵大薄,搴若履长洲。
白花皓阳林,紫虈晔春流。
非徒不弭忘,览物情弥遒。
萱苏始无慰,寂寞终可求。[3]66
诗人本是登高远眺,却在想象中策马遍览兰皋、椒丘、大薄、长洲、阳林、春流,这快速切换的行迹和错综交替的画面,传达出的不是赏心悦目的愉悦之情,而是诗人自己所说的“览物情弥遒”“萱苏始无慰”的深切忧思。诗歌结尾“寂寞终可求”所表达的辞官归隐之意[5]68,正是诗人无奈的抉择。
大多数时候,谢灵运并不直抒胸臆,而是将这孤寂凄冷的心境,隐藏在变换不定的行迹和错综的画面里,以这种无序和多变,来传达内心的不安。
三、钻貌草木与情感起落
叶嘉莹论及山水自然诗歌,曾说谢灵运山水诗主要是刻画形貌,所以被刘勰批评为“钻貌草木之中”[10]3。叶先生又说:“大谢诗的特点就是在于他不写感情,反而把景物的刻画写得这么复杂,把哲理写得比较艰深,而且在复杂艰深中传达出一种力量。你要一层层地深进去的话,就会发现那是一种挣扎……你要透过他的复杂和艰深,去体会他那一种在政治的矛盾中挣扎的、不得已的、勉强把自己压下去的痛楚。”[10]4-5
叶先生所说可谓大谢知音之论,而叶先生讲大谢诗歌也最是贴合透彻。复杂的景物刻画和艰深的哲理揭示,都深蕴着谢灵运的无奈挣扎和深切痛楚。谢诗中的“玄言尾巴”,其本质是诗人的自我宽解,而诗人“钻貌草木”以求精工巧似地刻画景物,其本质亦是排解忧闷,寻求自我慰藉。精工巧似的景物描写,需要沉浸其中的细致观察和全心的注意力,这个过程正可以暂且忘却烦忧,在大自然的美景中获得心灵的慰藉。谢灵运擅长刻画景物,这样的诗歌比比皆是。如《登池上楼》[5]63:
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
薄霄愧云浮,栖川怍渊沉。
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
徇禄反穷海,卧疴对空林。
衾枕昧节候,褰开暂窥临。
倾耳聆波澜,举目眺岖嵚。
初景革绪风,新阳改故阴。
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
祁祁伤豳歌,萋萋感楚吟。
此首作于景平元年(423)初春,诗歌“首先道出进退两难的矛盾心理以及对谪迁海滨的不满情绪”[5]64,在“徇禄反穷海,卧疴对空林”的凄凉情境中,诗人推开窗户,眺望远山,以排解内心的愁绪。他欣喜地发现,春天已经来临,在初春的阳光与和风之中,池塘边生出了嫩绿的青草,园中的柳树上,新飞来的鸟儿发出悦耳的鸣叫。“池塘生春草”一句,相传为诗人苦吟而“有神助”所得[11]277,之所以成为佳句,正是因为体物之工细,描摹之贴切。而诗人之所以下笔如此细腻,正是因为他在满腹愁闷的驱使下,对大自然进行沉浸式的观察体会的结果。大自然的蓬勃生机令诗人的精神为之一振,获得了暂时的精神解脱,所以他以“持操岂独古,无闷征在今”进行自我勉励和宽慰[5]64-66。
谢灵运山水诗的代表作《石壁精舍还湖中作》也有非常精彩的景物刻画,诗中“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两句所描述的情景,不仅摹写了傍晚的景色,而且生动真实地展现了天慢慢黑下去的过程:夕阳西下之时,大地上树林的深处和沟壑的低洼处,往往最先暗下去,仿佛是主动收敛着暗黑的暝色。而此时天边的晚霞,还有着最后一些光亮,在山头流连徘徊,渐渐地,晚霞也似乎把从地上蔓延开来的夕霏(傍晚的雾霭,也就是暝色)收敛起来,随即,天空也黑下去了。“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两句也颇具匠心:芰荷多生于水中,蒲稗多生于水边,所以这两句隐含着诗人行船时由湖中划向岸边的过程,这个过程通过水生植物的变化表现出来。在对湖光山色的细致体察中,诗人的情绪十分愉快,他写道“披拂趋南径,愉悦掩东扉”;但是接下来却开始谈论玄理:“虑澹物自轻,意惬理无违。”李运富认为结句充满“参透玄理不为外物所羁的惬意”[8]72。顾绍柏认为最后几句“归结到澹泊寡欲,以山水自适的道家思想”[5]112。二者都认为结句表现了谢灵运所获得的心灵解脱。诚然,山水大观已成为谢灵运所寻求到的摆脱苦闷的最佳方式,但无论是赏玩池塘春草,还是忘情林壑暝色,这都深蕴着身被贬谪、落魄失意的士族子弟的痛楚和挣扎,以及他在这挣扎之后与命运的和解。
与大谢相比,小谢(谢朓)的山水描写虽“仍然沿袭谢灵运前半篇写景、后半篇抒情的程式”[12]855,但基本摆脱了大谢谈玄说理的收尾模式,继承了大谢对景物的细致体察,且这些景物描写与诗中的情感起落有着更明显的关联。如《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诗》,小谢遭谗被讥,被迫离开西王府,诗歌开篇“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以奔流不息的江水为喻,抒发心中的悲愤,令人耳目一新。这种强烈的悲愤随着京城越来越近,诗人在远眺中被眼前的景色所吸引而内心的情绪逐渐得到了平复:“秋河曙耿耿,寒渚夜沧沧。引领见京室,宫雉正相望。金波丽鳷鹊,玉绳低建章。”[9]1426“金波”两句体物尤为工细,尽管诗人仍然思念着西府同僚,但是他也已然开始庆幸自己远离了西府的小人和危险的处境。细腻的景物描写,成为情绪平复的过渡。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认为陶渊明诗歌“描写景物并不追求物象的形似”,“只是写出他胸中的一片天地”[13]79-80。陶渊明笔下的景物,常常是写意的,正所谓采菊东篱,悠然见山,表现和谐宁静、悠然自得的生活场景与心境。陶渊明也非常擅长细节刻画,比如田地里茂盛的杂草和稀疏的豆苗,比如自己劳作归来,在屋檐下盥洗并尽兴饮酒等。当陶渊明被迫陷入生活的困境,他还会将其困穷之状真实细致地刻画出来:“凄厉岁云暮,拥褐曝前轩。南圃无遗秀,枯条盈北园。倾壶绝余沥,窥灶不见烟。”[7]226“倾壶绝余沥”一句最为传神,贫居潦倒的诗人,举起空酒壶,等待里面最后一滴酒倒出来,一直到壶中滴酒全无。这种细节的真实,令人仿佛亲眼所见。诗歌结尾诗人从贫居的愠怒中解脱出来,直言“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7]226,他在古时圣贤的身上寻求到了慰藉。
对生活情境细致的摹写,让陶渊明成为自身困境的旁观者,能够以冷静的目光审视命运,从而超越一己之苦,从古往今来的同道身上获得精神上的支持。同样的道理,谢灵运与谢朓亦对山水景物进行精细刻画并沉浸其中,借此平复心绪,以冷静的目光审视自己的命运,从而暂时忘却内心的愁苦。所以,钻貌草木,不仅仅是谢灵运在诗歌艺术手法上的创新,亦是诗人在以诗歌应对情感起落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选择。
四、结语
李运富指出谢灵运“在赞美自然景物中又反反复复地表示自己要抛开世俗,隐居修养”,并说这种反反复复的表示“正是他内心矛盾犹豫的结果”[14]3。这反反复复的表示,也正是叶嘉莹所说的“挣扎”。谢灵运的山水诗情、景、意交融,其玄言结尾大多时候亦瑕不掩瑜,不妨碍诗人的真情流露,且“在复杂艰深中传达出一种力量”。
注释:
①本文采纳顾绍柏《谢灵运集校注》一书对谢灵运诗作的编年。
②这两句或许为了押韵而颠倒了顺序,但此二句不管是顺序还是倒序,其间都有一个从早到晚或从暮至朝的时间开阖。
③诗人行程之紧张匆促,全因心情所致,与赴任永嘉的期限无关,因为《过始宁墅》曾写自己“枉帆过旧山”,可见诗人乃绕道而行,并不急于赶路。
④此首顾绍柏《谢灵运集校注》依《艺文类聚》《广文选》题作《东山望海》,李运富《谢灵运集》依《永嘉县志》《诗纪》题作《郡东山望溟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