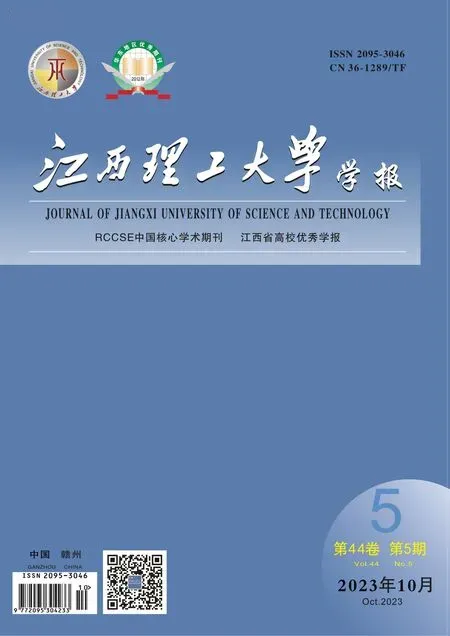接受美学视域下客家民间故事的翻译探索
黄斐
(嘉应学院外国语学院,广东 梅州 514021)
一、引 言
客家民间故事源于客家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后经口口传唱而世代流传。不确定作者为何人的客家民间故事之所以能保存并流传至今,一方面离不开历代客家人的搜集、整理和讲述;另一方面也与客家民间故事在流传的过程中经过说唱者的不断修改和加工而具有的美学价值和文化内涵相关。较之探源其出自谁人之手,倒不如思其流传之技以求未来之变。客家民间故事的传播方式极具特点,它既能整合客家劳动人民生活经验,又能适应已有语言接受能力、社会心理和美学判断的成人群体阅读需求,还能根据儿童阅读习惯特点进行有趣性及生动性的调整。作者的广泛性及文本的多样性特征为客家民间故事创造性文本的生成奠定了基础,而读者群体的适切性为深入研究客家民间故事的丰富内涵、客家民间故事对客家文化跨文化传播的作用都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视角。翻译是“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影响着文化跨界传播的广度和深度”[1]。客家文学翻译的研究刚刚起步,可进一步研究的空间很大。以客家民间故事的翻译为例,目前尚未有较成熟的研究。如果把文学翻译研究视为翻译研究多元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那么民间文学翻译无疑处于边缘位置,而客家民间文学翻译则是这边缘位置里最微弱的存在。中西文化差异特别是地方方言特殊性对客家文化的对外输出造成了一定阻力,例如思考如何让翻译成外文的中国文学、文化经典在译入语环境中被接受、被传播并产生影响,使得外译行为未能取得预期的成功的原因[2]。翻译不仅是语言之间的转换活动,还是一项跨文化交际活动,在推动我国文化输出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读者群体适切性下客家民间故事翻译如何进一步提升其文化审美,以适应不同文化背景读者的需求是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
二、中国文化走出去背景下客家民间文学的研究现状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内容占了较大篇幅。报告提出,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国文化的输出对世界重新看待中国、认识中国、理解中国,有着重要且无法取代的意义。文化全球化不是世界某种强势文化的一统天下,而是全球各民族文化的多元共融。作为全球化语境下文化交流媒介的翻译,既要重视异域文化的内引,又要注重本土文化的外输[3]。钟俊昆在谈及加强客家民间文学研究时曾提及从事客家民间文学研究的人少之又少之现状。他将这一现象归结为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受研究环境的影响,作为文学内部小分支的民间文学历来就难以进入主流研究者的视野,客家民间文学在民间文学百花园中占的地位不显赫,少有人去关注;另一方面是“客家民间文学的基础薄弱……客家民间文学长期以来所积累下来的基础并不扎实”[4]。由此看来,客家民间文学研究已然先天不足。
所幸,即便现状如此,仍有不少学者致力于客家民间文学的研究工作。随着对开创客家民间文学的学者们(如黄遵宪、罗香林、李金发、钟敬文、朱希祖、古直)所创作作品的相关整理工作推进与研究成果的发表,一大批基础性材料为后期深入开展客家民间文学翻译研究提供了极为宝贵的文献资料。20 世纪80 年代,赣闽粤客家地区的不少文史工作者积极投身于“三套集成”的采写。到了20 世纪90 年代, 亦有学者十分注重对赣南客家民间文学的记录与整理,以建构与弘扬客家文化,如赣南客家地区的严恩萱(《严谨文存》等)、杨遵贤(《对联雅俗谈》等)、杨启昌(《昌平斋闲谈》等)。客家民间文学研究在客家对联、熟语等方面的成果突出。如黄火兴(《客家情歌精选1900 首》《梅水风光——客家民间文学精选集》等)、胡希张(《客家山歌知识大全》)、罗英祥(《客家情歌精选录》)、曾海丰(参著《梅县风采集》),将粤东客家民间文学以书籍形式展现在读者面前。客家山歌大师汤明哲、余耀南等老一辈艺术家们以演唱的方式把客家民间文化从书本带上了舞台,让客家文化走进了更多人的视野。闽西客家民间文化也吸引了许多文化学者对客家文化的关注,如王耀华著《客家艺能文化》、马卡丹著《连城风物》等、陈泽平与人合著《长汀客家方言熟语歌谣》等[5]。这些学者对当地文化建设及文化传播不遗余力。客家民间文学张力十足。但从现有的客家民间文学研究资料不难发现,其仍停留在文学收集整理的层面,对文化输出的关注尚不够,与其他学科相综合的研究方法和能力也有待提升。
在中国文化走出去背景下,客家民间文学的研究应关注全球多元语境需求。多元语境下接受美学视域下的翻译思考,不仅有利于思考非主流文化在文化输出过程中如何实现继承与创新,也有利于推动在传播融合手段多样性、文化竞争力提升途径、客家文化的海外传播策略等方面的综合性研究。
三、接受美学视域下的客家民间文学翻译
接受美学理论之所以能满足客家民间文学多元化探索的需要,且有丰富综合研究途径的作用,与翻译学科属性密切相关。翻译与美学的结合是翻译研究的一种方向,翻译美学作为翻译理论中的独立学科方兴未艾。1992 年,奚永吉所著的《翻译美学比较研究》的出版标志着国内翻译美学研究意识开始萌芽[6],而1993 年由傅仲选出版的《实用翻译美学》一书则正式开启翻译美学进行的独立研究[7]。两部专著都肯定了原语和目的语的艺术价值和美学价值,从实用性角度剖析了英语文学文本和汉语文学文本的美学因素对译者选择的影响。之后的学者通过研究语言与美学的关系、翻译美学的理论框架建构、译者的审美心理能力及目标语读者审美视角与习惯等实现了翻译理念与方法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结合[8-11]。有学者指出,在中国传统的翻译理论研究中,“几乎所有的译论命题都有其哲学—美学渊源, 历史定势和文化整体形态的发展促使译学与哲学尤其是美学联姻”[12]。而在国外,对翻译美学进行系统描述和研究的著作始于Shirley Chew 和 Alistair Stead 编著的Translation Life: Studies in Translational Aeathetics。而据译史研究,西方的译论之芽也是首先依附于哲学与美学之树而枝叶渐丰的[13]。这种运用美学基本原理研究审美主体、审美客体及审美客体间的“审美再现”能动性,于翻译实践而言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翻译美学体系建构具有的延迟性与审美客体的理解不统一有一定关系,具体表现为审美客体是否应将“译文”与“原文”一起考虑。但翻译美学审美客体的开放性并未影响学者们在审美客体的构成要素上达成一致。国内外目前的研究成果表明,翻译审美客体的构成要素体现在文本形式和文本内容两方面。前者包括语义及语法层面审美信息,而后者体现在情志和意象信息上①由于受到内容系统隐含性导致的语言模糊性与开放性的特点影响,接受美学理论下的文学翻译创造性叛逆观点有了理论阐释的空间。。
与传统的翻译美学立足点不同,接受美学理论主要探讨的是读者在审美活动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强调“接受”这一概念,更重视文本与读者之间的关系,因此,又被称为“接受理论”。接受理论由康斯坦茨大学的青年学者汉斯·罗伯特·姚斯和沃尔夫冈·伊瑟尔首先提出,随后发展为德国的一个重要文学理论流派。其后十多年里,“接受理论异军突起,越过国界,传播到西欧各国,并在美国大陆上与读者反应批评合流,影响远及日本”[14]。接受理论影响巨大,对学者们如此,对之后研究更是如此。正如霍拉勃所述:“从马克思主义者到传统批评家,从古典学者、中世纪学者到现代专家,每一种方法论,每一个文学领域,无不响应了接受理论提出的挑战。”[15]孕育于20 世纪60 年代方法论危机中的接受美学理论是文学学者们努力打破传统的文学研究方法后产生的文学理论。
接受美学理论除了以现象学美学和阐释学美学为基础外,还吸收了布拉格结构主义理论中的空白论思想、解释学理论、交往理论、萨特的恢复读者地位的理论和马克思的生产—流通—消费的循环模式理论的营养[16]。接受美学理论并不是从研究作者与文本之间的关系到研究文本与读者关系的转移,而是将文学作品视为动态过程,并以此来构建作者、作品和读者之间的关系。这个动态过程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作者与作品之间的关系,另一部分则是读者对作品的期待。接受美学研究的是作品到读者这一过程中读者反应的主观性理论。接受理论认为文本的意义实现不是对文本本身某一意义的解释,而是读者通过阅读后能否实现意义传递。这一视角充分体现了读者地位的重要性。因为,读者都有“期待视野”,即在文学接受活动中读者前期所具有的各种经验、文化修养、心理素质、知识水平、审美情趣、鉴赏水平等共同构成对文学作品的审美期待。所以,任何一部文学作品,即使它以崭新面目出现,也不可能在信息真空中以绝对新的姿态展示自身[17]。
接受美学视域下的翻译活动便是通过翻译活动的完成来提供一些诸如预告、暗示等信息,激发读者开放以往记忆并带入文学作品的特定情境,来修正或实现已有的期待,从而成就文学作品阐释的多样性和独特性。通过读者的阅读过程,文本的未定性被作品的意义取代,进而填补已有意义与新认知之间的联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需要完成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使读者的期待视野与文学文本相融合,也就是“视野融合”。只有如此,读者才能产生接受和理解。在接受美学视角下的翻译活动中,译者的任务是复杂的。译者主观能动性的参与须先解决对原文理解中的接受影响,随后要预见译语读者对译文接受与阅读参与后进行接受的再生成。文学文本中的空白是作为第一读者的译者先去填充的。译者对读者的预见成功与否直接决定了读者在进行阅读活动时对文本处理是否流畅。因此,译者扮演着桥梁和媒介双重角色,努力使译文读者的期待视野与文本作品译本达到最大化融合。
接受美学视域下的客家民间文学翻译活动研究是在动态过程中构建客家民间文学创作者、作品和读者之间的关系,通过翻译活动来满足客家文化传播过程中多元文化背景下不同译者与读者的阅读需求和客家文化视野融合的综合研究构建的需要。客家民间故事是客家民间文学中的重要门类之一。客家民间故事来源于生活却高于生活,口口相传至今,是本土化民间叙事性作品的重要代表,具有显著的文化特征。研究客家民间故事述说者的意图与接受者的内化过程对客家文化传播途径的理解尤为重要。若以原作者的视角探索与文本的内在关系,困难重重。因为绝大部分流传至今的客家民间故事的原作者早已无迹可寻。现今的客家民间故事是经述说者收集整理后才流传至今的。述说者可能是民间故事的第一翻译者,也可能是前一译本的转述者。接受美学视域下的客家民间故事语内翻译,译者需要着重处理已有的文字材料或口述收集本,通过对阅读者或倾听者的接受度进行分析,结合不同地区的生活实际,进而使用恰当的翻译方法和策略,以实现客家民间故事的传播。结合文化背景下的生活实际且为满足读者和听者的多元需求,客家民间故事呈现出同一主题而版本各异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彰显文化独特魅力与其勃勃生机。这为客家民间故事实现语际翻译提供了重要的翻译实践参考。
客家民间故事在文化自信建构中起着增强文化认同感、传播文化特色的重要作用。其外译研究不足,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源于其译文(本)分散,结构化特征不显著;二是未有较为稳妥可靠的翻译方法;三是客家文化内涵存在小众化特点,不足以代表该文化的大部分意义,无法承担文化传播的主要角色。要改变客家民间故事外译现状,可从现有的语内翻译的多个版本入手,将小众化形象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本质的文化内涵建构联系,运用适当的翻译原则和方法彰显传统文化特色、实现跨文化传播。译者首先需要解构源文本中小众文化的本质内涵,其次将这些内涵特色与中国文化传统进行联系并加以意义重构,最后与外国读者的阅读习惯进行整合并形成最终译本。此外,客家民间故事的翻译还需译者具有一定的方言文化知识,能处理语言复杂性和文化融合度等问题。
对需要处理客家文本的译者而言,确定目标读者群对读者接受度及其接受视野的预判有着重要意义。客家民间故事的读者群中儿童读者的范围是不受限的。通常,译文的儿童目标读者有国外儿童读者和国内儿童读者两类。前者对客家文化无前期认知或较少认知,对所涉之人物及事件的重构行为不反复,不确定性及空白填补复杂性较少。接触此类翻译作品的原因大多是对家族历史及渊源的传承或纯粹对某一小众文化的兴趣。国内儿童读者选择英文译本,或因本属客源地为实现汉英教学及文化普及而起,或因其他属地儿童为了解文化多样性及人物特点等兴趣而生。客家民间故事译本的读者群还会涉及部分旅居异国或客居本地的成人,其读者期待视野或阅读兴趣与儿童目标读者契合。当然,成人读者的前期经验与儿童读者有所差异,但若前期经验少或近乎无,两者则有等同视野期待。不管是教导起始或是文化关怀,所期待的客家民间故事译文都应是既保留了客家文化特点,又传达了中国文化特色,且融合国际视野的一种文学存在。因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只要秉持此翻译原则,就能最大程度找到较为适合的翻译方法以满足不同类型读者的共同期待。下文以客家民间故事中广为人知的《李文古》故事名篇《三戏先生》①节选自黄火兴编撰的《梅水风光——客家民间文学精选集》。为例,从接受美学视角结合客家民间故事探讨其适用性。
四、接受美学视角下的客家民间故事主要特征及翻译策略
客家民间故事主要指客属地区以口头形式流传的、题材广泛而且想象丰富的叙事体故事。民间故事来源于生活,又超越于生活实际情况,带有某种或虚幻,或荒诞,或夸张的成分。由于客家地区使用方言的特殊性,客家民间故事除具有贴近生活、类型化、泛指化等特点外,还具有俚语多、俗语多、比喻多等特点。要实现满足读者期待视野的外译,客家民间故事翻译需关注以下四个方面的特征。
(一) 客家俗语普遍性特征
论及客家俗语特征,可以先从乡土文学谈起。乡土文学最早出现在19 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以地方特色、方言土语、社会风俗画面描绘具有浓郁乡土色彩的村镇生活与风土人情的文学作品。 在乡土文学中,不仅地方色彩涉及方言土语的运用,而且社会风俗画面的表现也需要通过方言土语来加以体现。实际上,要研究乡土文学的翻译就必须研究乡土语言的翻译,即维护乡土语言的本色,便是维护了乡土文学作品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存在的根本所在[18]。
这些乡土语言既能反映当地的风土人情、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又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当地人们语言表达的习惯,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俗语”。曲彦斌认为,俗语一词是汉语的固有词汇,具有自己的特定含义和文化底蕴,其“俗”不仅具有通俗的、大众的、约定俗成的、俚俗的等语义,尚有民俗的意思[19]。从乡土文学作品的语言使用特征上来看,确实如此。客家俗语在固定的语句或句式中,通过一定的修辞方式将生活经验和愿望以简单凝练而形象化的方式进行创作。因此,意义的表达是完整的,也是约定俗成的。但意义表达的方式是多样的,甚至是随着民俗变化而变化的。在完整性和多样性共同作用下,客家俗语具有了有趣性和独特性。
目前,方言翻译研究方法中,张谷若主张的“方言对译法”[20]和韩子满提出的“口语对译法”[21]受到较多关注。与此同时,王恩科提出了读者因素应纳入方言翻译研究中进行描写性研究,进而有效解决互译的必要性及方法性问题[22]。读者期待视野为客家民间故事翻译策略的研究拓展了思路。例如,《李文古》故事中,李文古趁机嘲弄了教书先生,文中提到,“先生一听,正打痛了自己的‘烂脚’”。此处的“烂脚”显然是极具地方特色的民俗表达方式。我们可以将“烂脚”理解为“痛处”,考虑读者因素进行互译后可以表述为“aching leg”进行“Let Li Wengu hold his aching leg”的描述翻译,也可以意译为“give him a handle/become fair game”①此处参考《英译广东口语词典》的用法。。翻译地方语言可以将方言对译法与口语对译法结合起来,再根据读者期待进行整理。在翻译客家民间故事时,可以在与现代汉语语言用法对应的地方使用方言对译法;而在翻译俗语,特别是一些约定俗成的语句时,采用口语对译法则更加适应语言表达的具体场景。此外,译者在翻译时是否充分考虑将读者接受因素进行融合显得格外重要。如上述例子,译者在理解原文各个词句的同时,对原文艺术画面进行了意象再造,通过使用译文语言构建一个综合语言信息与美感经验的格式塔意象,使读者获得完整统一的审美体验。因此,客家民间故事翻译中的俗语可以采用直译方言、口语对译的方法综合语言信息与构建美感经验的意象。
(二) 客家人物形象“俗”的特征
许多客家民间故事会通过讽刺、夸张、戏谑等方式对某种人物贪婪、懒惰、狡黠等特点进行讲述。这种描述“丑陋”人物形象的方法在文学写作中极为常见。这些人物形象虽与已有的客家人勤劳、勇敢、善良等既有形象冲突,却也能见到人无完人的真实感。翻译时保留“丑陋”的人物形象不仅是故事情节的需要,也是故事主题的需要。这些对比手法如果在翻译时被省去,不仅会影响读者接受译本时对故事重构的完整性,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客家民间故事的趣味性。因此,保留这些“丑陋”形象的存在是必要的。传达过程中,因为方言特点,虽然一些“丑陋”形象并不容易在文字中完整保留,但是许多描述“丑陋”形象的口语表达却保留了下来。融合的过程是译者在后期根据预设读者的需求,对“丑陋”保留的多少和以怎样的方式进行“丑陋”保留的过程。
以《李文古》故事中的《三戏先生》为例,“丑陋”形象主要体现在两处:一是先生形象。故事中的先生形象与常规的先生形象显然是冲突的,没有勤恳认真的教育者姿态,有的更多是懒散不自律的举动。二是李文古机智灵活的形象。与通常的主角形象不同,这一主角显然不完美。李文古虽然机灵,却也古怪,语言有时更是俗不可耐。可这正是乡土故事最真实的地方,没有过多的英雄主义修饰,有的是更人性化的描述和风俗人情的趣味。例如,在故事中有这么一个情节,先生嘲笑李文古不知天高地厚。李文古不满先生嘲弄,反唇相讥。李文古说道:“我知道,天有两个矢忽那么高!”不顾先生训斥,李文古又言:“真的,我妈给我‘摒屎’的时候,总是说我‘矢忽’拱到半天高。我一个矢忽半天高了,若两个矢忽不就顶天了么?” 翻译实践中,可以运用叙事化手法翻译故事原委,在考虑读者接受度后,对一些“丑陋”形象运用普通用词,以减少读者群体在阅读时的不适。如可以处理为:Wengu explain, "It's true! when my mother wipe my arses, she always said that I arched half a sky high. One of my arses is half a sky high.If two arses, will they go up to the sky?"为了叙事上下衔接,先生说的“你真是不知天高地厚!”若译为“You don't understand yourself”或者“You are ignorant of your own ability/situation”都不及“Not to measure yourself!”的表达效果。因为“measure”带来的是上下文对“测量”这一俗语的有意为之。因此,在翻译客家民间故事的过程中,处理具有乡村特色的民俗人物形象时,适当将文化俗语进行叙事描述,更能关注语义在微观和宏观层面的相互制约和调节作用,恰如其分地表达原文意义。
(三) 客家叙事冲突特征
语言既是人类交际的工具,又是人类交际的产物。语言可遵循美的规律与物质产品一样带给读者美的精神体验。但是,在不同的社会活动中,由于交际目的的需要和情境、手段的制约,语言会用不同的修辞方式在特定情境中以既定读者能理解的要求和表现加以呈现。英国著名翻译研究学者莫娜·贝克(Mona Baker)从叙事的角度对翻译与冲突进行了深入分析和讨论[23]。这种结合社会学、交际理论及叙事研究的跨学科研究更加注重叙事与语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下文以莫娜·贝克的叙事策略中的“选择性挪用”与“参与者挪用”来阐释客家民间故事中的叙事冲突与翻译现象。
客家民间故事的叙事冲突,除了因俗语和方言带来的与读者已有语言产生冲突外,还有一些因“丑陋”形象带来的特殊情感与道德冲击。客家民间故事对于故事的戏剧化描述常常是开放的,没有特定的讽刺,也没有特定的指向。译者可能会根据读者期待进行目的性的修正,这往往与译者的翻译思想和翻译策略有关。译者为译文的第一读者,对所处理信息必然会进行反思,不可避免运用自身推理来支持或反对某个叙事。在接受美学视域下看待叙事冲突及其所采用的叙事方式及策略,恰恰反映了叙事是无法避免的客观存在。译者在处理叙事时也不可避免受到作为第一阅读者自身价值观和叙事定位的制约。因此,译者更要考虑到大部分读者在理解乡土文学作品时语境上带来的客观困难,处理译文时应尽可能使用接近原文的直译,甚至是译文的回译,以克服读者在阅读时无法通过已有经验进行建构的困难。译者为解决自身由于叙事冲突带来的特殊处理,可以在基本“传达”的情况下,做出适度“融合”。在处理客家叙事冲突的翻译中,传达与融合需要与环境相协调。例如在《李文古》故事中提到,李文古的先生是个不太严格要求自己的人,常常邀人打鸟、 “打斗聚”等。“打斗聚”这个词是客家民俗的一种活动,意思是说,在闲暇时间三五好友在一起聚餐。这时需要译者结合客家民间环境进行叙事处理。结合该故事的叙述对象是李文古的先生,在“不太严格要求自己”对照之下,“打斗聚”的理解就不能简单认为只是约上人一起吃东西而已。翻译时,可将其理解为“贪吃贪料(玩)”的意思,译为“Be too greedy for foods and fun”。环境协调可以是在尽量接近原文基础上根据读者期待进行的叙事策略处理,也可以是译者通过对现实社会的重构调停叙事冲突。译者在考虑读者接受度的审美传达中,通过文本时空的架构拉近读者与源文本叙事的距离,再通过删除或者添加的方式对叙事冲突点进行论点融合,实现叙事改写下的文本重现。
(四) 客家文化地域性特征
翻译不仅是处理两种语言的交流,更是两种文化信息的沟通和传递。客家文化具有非常明显的乡土文化特征,影响其英译的文化因素包括历史因素、生活经验因素和客家生活环境与社会发展因素。这些因素常常造成翻译和理解的困难。客家文学著作承载着极其丰富的民俗文化,外译过程中容易造成文化缺失[24]。
研究客家民间故事的翻译,应该着重关注民俗故事中鲜明的形象和丰富的想象,以及内含的文化信息和文化特征。不同的地缘文化和地缘历史会造成诸多文化差异。在翻译实践过程中,语言层面的保留与传达使得译文能够符合故事完整度和流畅度这两个基本要求,也能符合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客家文化的基本了解,但无法将客家特征和文化背景在译文中真正恰当地体现出来。其中的难点正是缺少融合的恰当方法。如融合某类习语的翻译方法,确实能较好实现文化传达,但未能保留语言风采和文化品质。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作为翻译实践中的一大难题,其涉及面广、可变因素多。接受美学视域下的客家民间故事翻译以译语读者为中心,在翻译时必须充分考虑读者的接受性,尽可能最大限度地使译文接近原文,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文化交流的目的。有些本体确实不雅,可采取意译的方法,虽说失去了原文的文化特色,但用语上保留了原文的韵味,符合接受美学中的读者期待;有些喻体缺失,不容易建立联系的,则可通过保留读音的方式加以说明释疑。比如“禾毕”又称“禾必子”,《客家话通用词典》解释其为“似麻雀而小的鸟”。有不少人认为这种“禾毕”就是麻雀,但当地也有人认为它跟麻雀有不同。对此,音译加注释的方法可以兼容此类民间特征词。可翻译为“vo bid”(A small sparrow that likes to eat rice in Hakka area.)。音译方法应融合释义补充,以补偿受译方产生的信息不对等或是文化信息的缺失,表达出原作的意图。
对于“弱势语言与文化”来说,外来术语的译介方式恰恰相反,即可能首先倾向于主动接纳“异化”译名,以后到了一定的发展阶段才又有了重新“归化”修正的意识[25]。异化翻译在翻译文化特征的效果上是有效的。但跨语际复制的模仿与传递过程中,意义的融合是为了读者在接受视野下能通过联想建立不同文化负载词意义的有效传达,以便更好地延续和完善文化概念,建立普遍意义上的符合“保持(或遗传)”特征的文化传递。
五、总 结
在接受美学理论指导下,通过关注客家民间故事的主要特征,进而从读者维度探讨翻译中译者保留、传达与融合客家文化的可行性,为地域性文学作品的跨文化传播提供策略参考。研究中发现,客家民间文学翻译稀缺,加之相关研究不足,是中国文化走出去背景下客家民间文学翻译研究难成系统的最大原因。但同时也表明继续研究客家文学翻译的空间和可能。在客家文学翻译研究中,人们大多关注方言翻译的民俗个案研究,重视其翻译的等值问题,较少涉及客家文学翻译研究的文化意义。实际上,客家文学作品翻译过程中的文化因素翻译,值得更多关注和重视。中国文化走出去背景下,传播客家文化,讲好客家故事,不仅能让更多人了解客家文化及其内涵,还能增强中华民族文化凝聚力与向心力。此外,地域性文学跨文化传播的语言策略探讨对中国本土民间文学话语体系的构建与发展而言,亦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