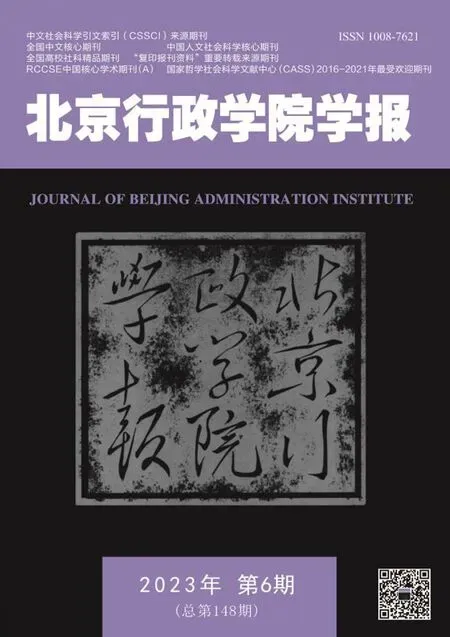中国法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先驱探索
——探寻李大钊法理学的理论体系
□徐爱国
(北京大学法学院,北京 100871)
一、研究背景
中国学人对李大钊的认识有个不断深化的过程。首先,他是一个革命家和政治家。他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同时,他还是一个理论家。他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者,是一个较早研读外国原始文献的政治家。他既研读过启蒙主义,也专门研究过共产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他读过私塾,上过北洋法政学堂,留学过日本早稻田大学。他办过报,出任过图书馆馆长,担任过大学人文社科的教授。他的时政评论、会议演讲、外文翻译、授课讲义,既有思想的闪光,又有厚重的理论总结。相对于他的政治学、史学和哲学,他的法律思想被后人忽视了。在纪念李大钊同志诞辰130 周年座谈会的讲话中,曾醒目地出现过李大钊“法学”的字样①李大钊“留下大量著作、文献和译著,内容涉及哲学、经济学、法学、历史学、伦理学、美学、新闻学、图书管理学等诸多领域”,参见王沪宁:《在纪念李大钊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9年10月28日第3版。。比较而言,通过对中国知网数据库关于李大钊研究的检索发现,中国法学界对政治先驱者的法律思想的研究,尤其是对李大钊法学思想的研究略显不足,这与他在中国现代历史上的地位是不相符的。因此,学界有必要深入系统地研究李大钊的法律思想。
李大钊的法律之缘,贯穿于他的一生。从早年求学到壮年就义,都与法律相关。1927 年的《狱中自述》讲到他攻读法政的初心。他说,迫于中国危机,“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乃赴天津投考北洋法政专门学校”[1]297。在这里,李大钊“习法政诸学及英、日语学”[1]297。该校政治专业开设的法律课程有《大清律例》《大清会典》、宪法、民法、刑法、国际公法、私法、商法。在读书期间,他仔细研读和批注过日语原版的《豫科法学通论》和《正科刑法讲义》①《豫科法学通论》是李大钊在预科第三学年所用的教材,原书为日文,书中标记了多种符号,并分别用中文、日文和英文做了90 多条批注,对统治权、立法权和行政权运作方式,以及法律效力,作了“法理图解”。参见王海:《李大钊同志批注过的两本讲义》,《文物春秋》2007 年第4 期;朱成甲:《李大钊早期思想与近代中国》,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4页;闫夏:《李大钊思想日渐成熟的转折点——求学北洋法政专门学堂》,《天津法学》2017年第4期。。毕业后,李大钊赴日本东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科开设的法学课程有宪法、民法要论和刑法要论[2]。不过,李大钊一年后退学。李大钊在洪宪之变后归国,担任过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也在北京大学、朝阳大学、女子师范大学、师范大学、中国大学讲授史学思想史和社会科学等课程。如同马克思和列宁一样,李大钊从法学院走向了政治学和政治运动。李大钊的理想在政治,法学只是通向政治的一条道路。即使如此,他所从事的政治活动不乏法律抗争的底色,在政治手段与法律手段可供选择之际,他宁愿选择政治;在政治方式不足以获取权利的时候,他寄希望于法律。乱世暴力横行,法治只能运行于文明时代,乱世不可以言法治。
相对于政治学、史学和经济学而言,中国法学界对李大钊思想的研究较为薄弱,专门研究李大钊法学思想的著作不多。研究人员多为马克思主义、党史和政治学的学者,法学专业人员偏少。研究内容以李大钊著作文本研究为主,引导性和概述性的论文偏多,政治应时性研究居多,法律味道相对不够,尚未将李大钊法律思想与其政治思想区分开来。以现代法学的划分标准,李大钊的法律思想涉及他的法理学、宪法学、国际法学、人权法学、劳动法学和女权主义法学等。
从现有学术成果看,国内学者对李大钊宪法思想研究成果最多,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研究次之②孙全胜:《论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法学观》,《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23年第1期;侯欣一:《李大钊马克思主义法学观的形成及在中国的传播》,《荆楚法学》2021年第1期;王茜、王宇:《李大钊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法学的重要贡献及启示——纪念李大钊诞辰125周年》,《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对他的国际法思想③《李大钊的国际法思想》是为数不多研究李大钊国际法思想的论文,文章把李大钊的国际法思想归纳有三:其一,提倡民族自决;其二,反对秘密外交和“以夷治夷”外交政策;其三,废除不平等条约。参见:韩德培、罗楚湘、车英:《李大钊的国际法思想》,《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人权法学[3],以及他所经历过的法律事件和活动,法学界尚未深入系统地研究。可以说,李大钊法学思想,是一个尚未被开发的“富矿”。本文的主题,聚焦于李大钊的法理学研究,横向讨论他的法律一般理论、法律文化学和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纵向兼顾他早年的启蒙主义法学和后期的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
二、法律的一般理论
1923—1924 年,李大钊撰写了大量的史学论文和演讲稿,在论及历史和历史哲学的时候,他曾经提到过“法律的一般理论”一词。他说,哲学是一般性的理论,与一般理论对立的有社会哲学,后者有时候可称之为政治哲学、法律哲学和经济哲学[4]。在区分史学学科的时候,李大钊区分了普通历史和特别史。特殊社会现象的历史包含了政治史和法律史,“政治史、法律史等乃考察一种社会现象本身的经历者”。特殊社会现象史,对应有一般的理论研究,“对于法律史,则有法理学”。进一步区分,则“法律之分为民法、刑法、商法等”[5]。他在天津上学的时候,研读过日本学者写的《法学通论》。经法律史学家考证,20 世纪早期中国法理学,都是从日本“法学通论”汉译本认识法律的④程波:《汉译〈法学通论〉教科书与近代中日法律名词交流研究》,《朝阳法律评论》2010年第1期。。李大钊对法律的初步认识,也是从日本版的《法学通论》开始,不过他在北洋法政学堂阅读的是日文原版。法学通论只是概述,要达到法理学的高度,需要时间的积累和沉浸式的冥思苦想。在日本留学时期,他撰写的《民彝与政治》一文,仅试图从中西思想史的角度建构他的法理学。直到1919年他撰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才提出了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法理学观点和方法。可以说,从“法学通论”到“法律一般理论”,最后到“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发展,构成了李大钊法理学的思想史。
(一)中国传统的法理学
“法理学”一词,严格地说来自罗马,词源为“法律的知识”。18—19 世纪,法哲学和法理学的概念开始形成,欧陆多用“法哲学”,英美多用“法理学”。在德国人康德那里,他严格区分了“法律的形而上学”和“法理学”,前者是法律的哲学,后者是法律的知识,法哲学高于法理学⑤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沈叔平译,商务印书馆,1991,第38页。。在英国人边沁和奥斯丁那里,他们确立了法理学的范围:法理学就是科学的法律一般性理论①奥斯丁:《法理学的范围》,刘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第10页。。康德和黑格尔、边沁和密尔,在李大钊的著述中经常出现,李大钊也经常运用他们的学说。但是,李大钊法理学所依据的一般理论,其渊源还是来自中国知识和学术的传承。
中国法理学一词,法律史学家追踪到1904 年梁启超的《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那篇演讲稿[6]。梁启超说,近世法学称世界上有四大法系,中国算是其中之一,“既有法系,则必有法理以为之原。故研究我国之法理学,非徒我国学者所当有事,抑亦全世界学者所当有事也”②梁启超:《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载《梁启超法学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年。文选出自《饮冰室合集》第2卷,中华书局1936年版。。梁启超以西式的概念回溯中国思想史,将中国法理学思想追溯到前秦的儒道法三家,以论证他“有法律必有其法理”的观点。道家的放任主义、儒家的人治主义和礼治主义、法家的势治主义,构成了中国的法治主义内涵,这就是梁启超的法理学。以西方术语重新解读中国法律历史的传统一直被延续下来③杨鸿烈:《中国法律思想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第3页。杨鸿烈此书原版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12 年至1928 年期间,中国出版的法理学和法学通论计有17 种。先有法学通论,后有法理学。最早的法学通论出版于1919 年,最早的法理学出版于1925 年。其中,李达翻译日本学者穗积重远的《法理学大纲》,由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 年出版[7]。李大钊没有使用“法理学”这个词,但是他认真思考了中国法理学的原理。
(二)法律的权力论
李大钊对政治的浓厚兴趣,决定了他更关心法律与权力的关系。法律的权力论,一直是法律政治学派的核心。法学界将法律的政治学派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的批判法学,然后回溯到20世纪初期美国的现实主义法学④Daria Roithmayr,Symposium;Critical Legal Politics:left vs.MPM:Politics and Denial,22 Cardozo L.Rev.1135(2001).。再往前溯源,就溯及至19 世纪30 年代的英国分析法学,最后来源于霍布斯的《利维坦》。法律政治学派的核心观点是,法律只具有工具论的价值,是达成政治目的的手段。法律来自主权者的意志,法律的实现需要国家的强制力。拿霍布斯的话说,法律是一种命令,不是建议,“是国家用语言、文字或其他充分的意志表示”“命令他用来区别是非的法规”⑤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85,第206页。。不过在这里,李大钊的文章中没有见到霍布斯的名字,他对法律与权力的理论则源自卢梭的社会契约论。
李大钊使用的翻译名为“卢骚”,参照的版本是日本学者中江兆民翻译的《民约论》。李大钊的引用是:“夫藉力制人而为合于义,则藉力抗人亦为合于义矣。力之所在即权之所在也,则天下之人将唯力是求。”[8]247这里的说法,更类似于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的话:“暴力支持他,暴力就推翻他。一切事物都是这样按照自然的顺序进行着,无论这些短促而频繁的革命的结果如何,任何人都不能抱怨别人的不公正,他只能怨恨自己的过错或不幸”⑥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李常山译,商务印书馆,1962,第128页。。卢梭关于社会契约和法律公意说的准确表达,来自他的《民约论》。按照现代中文翻译本的《社会契约论》,卢梭的说法是:人人将其权利全部奉献给一个政治的主权,通过主权的力量保护每个人的法律权利。个别意志的联合为众意,众意消除冲突形成的合意为一般意志。现代人称“一般意志”为“公意”,公意的外在表现,就是法律⑦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第39页。。主权的行使、政府的成立、法律的设施、治安的保卫,都需要强力的存在。
李大钊对法律与权力关系的研究作了进一步推进。他以刑法为例,称国家维护政府的存在,就需要有刑典。刑典施行有效,就需要物质的强力。反过来说,强力的施行,为法律所许可。李大钊区分了“权”与“力”,受法的约束而不任性,“力”可以是“权”。刑法有国家权力支撑,人民心存畏惧。作奸犯科,必定受到强力的迫制[8]243。专制社会,强力为政府的基石;现代社会,强力甚稀。李大钊的思路与卢梭是一致的,法律离不开强力,但是只有强力来自人民的意志,受到民意的约束,才有正当性,“强力”才变成为“合法的权力”。是否受到民意的约束,是区分专制和民主社会的标准。
法律与政治权力的关系,当时的通说是政治之力大于法律之力,法律之力只能服从政治之力,因此立法者不能不顾忌政治之力。李大钊不赞同这个观点,他觉得两种力量即使悬殊,也要考察政治权力是否在合法范围之内。这有些现代“政治权力应该在法律框架下运作”的意思,他说,“若其强力含有破毁法律之性质,且恒有其倾向,有其行为焉,则为非法之暴力,而非政治之所能容”[8]245。
李大钊寻找的理论根据之一,是英美的政治学家,而非严格意义上的法学家或者法律史学家。他引用英国布赖斯(旧译蒲徕思)“法律上主权与事实上主权”的区分。主权是国家最高的政治权力,不受法律约束的权力,是事实上的主权;受到法律约束的主权,是法律上主权与事实上主权的完美状态,“换言之,国家完美之组织,务求合法权力与实际强力联结于相同之人或团体。有合法之权力者,应令强力附诸其侧,以致人之服从”[8]245。李大钊文章中曾经提及过英格兰普通法的柯克大法官,可惜他没有讨论英国普通法的历史,没有提及柯克大法官与英国国王的抗争,没有触及普通法“国王应该在法律之下”“国王应该尊重法律”的原则[9]。但是,李大钊的法律思想与英国法治主义的历史是吻合的。政治强力也要服从法律,主权也要受到法律的限制,是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李大钊时代,政治权力肆虐,尚未能提出法律高于政治的命题,只能退而求其次,政治权力与法律权力的联合,或政治权力要获得法律的支持。
李大钊引用美国政治学家詹克斯(旧译甄克士)的说法,要仔细考察政治的现实情况,不能仅仅相信宪典中的规定。现代的说法,是要区分“书本上的法律”与“行动中的法律”。美国政治学家的说法是,当时的俄国、德国、英国都为“君主制”,但是与政治形式和权能相比,三者之间完全不同。英国实际为共和国,美国纽约的“寡头政治”不亚于俄国“沙皇”的专横,而土耳其的“苏丹”也受到一定的法律限制。李大钊总结说,当事实上的强力与法律上主权分离的时候,强力应该服从法律,而不是违反法律而行动。“以非法之暴力,而凌轹法律上之主权,则社会督责,公民逆命,自有制裁之道矣”[8]246。“自有制裁之道”,李大钊最后求助于卢梭的“暴力革命”的理论:暴力支持暴君,暴力也推翻暴君,这是暴力的辩证法①李大钊引用卢梭,来自日本学者所选《民约论》,疑似有误。此处的文字,更接近于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参见李大钊:《暴力与政治》,《李大钊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第250页,作者注10。。
《暴力与政治》发表于1917 年10 月。8 个月后,也就是1918 年7 月,李大钊与其友人商榷,李大钊进一步阐释他的权力与法律论。这个时候,他区分了“强力force”与“意志will”,朝着卢梭的理论更进了一步。他援引时任美国总统威尔逊的说法,政府就是有组织的强力(organized force),这个强力并必然包含有组织的武力(organized armed force)。“盖近世之良政府,不恃治之武力,而恃被治者之悦服(free consent),是即政府以宪法与法律为之范,而宪法与法律又以社会之习惯为之源也”[10]297。李大钊说,这个说法与孟子“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有异曲同工之妙。Free consent 就是全民同意而形成的卢梭的“公意”或“普遍意志(general will)”[10]300。在这篇文章中,李大钊注释里引用了胡适的哲学著作,里面出现了霍布斯的名字,并道出了霍布斯与卢梭、霍布豪斯与黑格尔的学术争议[10]302-303。
(三)法律与道德
较之法律权力属性的论述而言,李大钊对道德议题论述较少。但从广义上说,李大钊早期将法律归结为体现民意的“民彝”,思维方式上与传统的自然法法学是一致的:区分法律的现实规定和法律的理想状态,法律之上有法律价值的追求。这也是法律的价值,其实就是法律的道德论。改变专制之下的暴力之法,确立共和精神的民彝之法,这也是法律的道德论。这种法律道德的内容,是自由、民主、平等和进步。1919 年,李大钊发表《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一文。这时,他已经开始接触并传播唯物史观。文章集中讨论了道德问题,其中也涉及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首先,李大钊界定了道德的含义。一方面,他把人类的道德本性,与动物自我保存、种族繁殖看作有着同等的根源,不同于后天可以学习的科学、法律、政治、宗教和哲学。另一方面,道德与法律又有一致性,都是精神的构造,都受制于物质和经济。善恶、利他、牺牲、忠信、正直、公平、义务和良心,都是道德的范畴,“道德就是适应社会生活的要求之社会本能”[11]133。
这里,李大钊也把风俗与习惯纳入道德范畴来讨论,同样认定风俗习惯决定于物质和经济因素。老人与妇女的社会地位,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风俗,都可以用唯物史观来解释。狩猎时代的老人被弃,是因为迁徙中的老人被作为负担;畜牧和农业时代的老人受尊重,是因为老人是知识经验的宝库。游牧时代的女子受尊重,农业时代地位下降,都与她们的经济能力相关。男狩猎女耕作的时代,一妻多夫制产生,女子贞操观念弱;牧畜时代,实行一夫多妻,女子贞操观念强;工业时代,女子的贞操由绝对变成相对,女子可以离婚可以再嫁;公有制社会,男女平等。除了唯物史观,李大钊有点孟德斯鸠“法的精神”的意味了,人类的法律制度,与自然环境相关,风俗习惯决定于自然地理的环境。这里,李大钊的法律道德论,不仅仅是简单“善与恶”的道德意义,更具有伦理的社会意义。
三、法律民彝论
李大钊在法理学上的一个顶峰之作,便是他1916 年写的《民彝与政治》一文。李大钊的民彝论,学者有较多的研究。但“民彝”内核为何,学者有着众多的分歧①参见侯且岸:《李大钊研究的学术史思考》,《北京党史》2023 年第1 期;朱成甲:《李大钊早期民彝思想初探》,《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85 年第2 期;陈荣文、陈开琦:《李大钊的“民彝论”法律思想》,《社会科学研究》,1994 年第4期;《从“心力”到“民彝”:民国初年李大钊关于政治正当性的思考》,《史林》2017年第2期;赵书昭、段立全、侯佳:《文化融通视角下李大钊“民彝”思想新探》,《唐山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崔卫真:《论李大钊的民彝史观》,《唐山学院学报》2019年第1期。。这里,我们换一个角度,不去关心他的政治学,而是把焦点放在李大钊关于法律的一般理论上。如果说法律与政治、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是法律的外在范围限定的话,那么民彝论就是李大钊阐释的法律内在规定性。在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前,法律民彝论是李大钊法学的一个高点,是对求学时代的一个理论总结。民彝论融合了他对中西文化的理解,多层次、多维度地解释了法律的内在属性。
(一)“民彝”的三个侧面
在解释“彝”的含义时,李大钊不乏法律思想火花和对法律的历史解说。他开篇就指出了问题的起点:天生众民,有形下之器,有形上之道。道即是理,民以理的指引达于善德。中国“道与器”的二元对立概念逻辑,李大钊用来解释政治与法律。不过在这二元对立的基础上,他加上了第三个维度,那就是“法”。道、器和法三位一体,构成了他的民彝。民彝是一个合体,有物质、有精神,还有物质与精神合一化作而成的“法”。如此的思维方式,既有中国古代的逻辑,又有西方哲学的味道。更重要的是,他最后把民彝归结为“法”,与他受到的法学教育存在内在的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讲,李大钊的法律论虽比梁启超晚了12年,但是他超越了梁启超,不是简单地用西式的名词概念裁剪中国法律思想史,而是融合了中西哲学及法律的历史,内在实质性地提出了自己的法理学。具体言之,李大钊将民彝解剖为三种含义。
第一,“彝”之义在于“器”。宗彝者宗庙之常器。“器”为国家神明尊严所在,窥窃神器者,律以叛逆论处。李大钊将彝器的重要性,比作古罗马的十二铜表法[12]269,认为它不仅仅是金石之家鉴赏的对象,而且是民之大义的载体。古代政治神器在于宗彝,如今政治神器在于民彝。李大钊对古代法律的认识,是有更多的历史材料作旁证的,除了罗马十二表法刻在铜器上外,汉谟拉比法典刻在大理石上,摩西十诫刻在法器铜板上,子产铸刑鼎,邓析刻竹简,都是法律之器的表现形式。法律史上称之为由习惯法到法典的转变,拿梅因的话说,那是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法律发展的连接点②“在我所提到的几个国家中,到处都把法律铭刻在石碑上,向人民公布,以代替寡头统治阶级的记忆的惯例”。参见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1959,第9页。。
第二,“彝”即为“平与常”。这里,李大钊从器物转到精神的层面,把民彝归结为“民性”“习性”“信仰”或“民意”。他说,政治与法律,贵在与民性相通,“依有方之典刑,驭无方之群众”。不同政体下,法律的“习性”不同。专制政治下,法律源自君王的好恶,而不是顺应人民的天性。结果必然是“法网日密,民命日残,比户可诛,沿门可僇也”。法律要与人民的习性匹配,反之,法律将起不到治理的效果。李大钊回顾了欧洲法律史。他说,中世纪猎巫运动,官方以巫术罪的名义,杀害了成千上万的巫师,但并没有遏制巫术的存在。其中的原因是当时的人们相信巫术,法律的规定与民众的信仰发生了冲突。“彼其非常之法,果为政治之良图,而离于其民,已失其本然之价值,不能收功,反以贻害”[12]270。李大钊呼吁,民意国情乃是长治久安之道。这里,不同政体决定了不同的法律习性,多少有些孟德斯鸠的影子。共和、君主和专制之下,政体的原则不同:共和政体崇尚品德、君主政体在乎荣誉、专制政体偏向恐怖。法律是酒,政体是酒杯,酒在不同的酒杯里酒的品质是不一样的③参见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上册,商务印书馆,1961,第19页。。共和之下的法律,体现了民意,会促进民主和法治;而专制之下的法律,体现了君主的个人意志,是专制主义的工具。这个时期的李大钊,充分吸收了启蒙学者的智力成果。
第三,“彝”即为“法”。政治与宪法,是李大钊在北洋法政学堂和早稻田大学学习的重点。在法律与政治之间,他偏向于政治;在公法与私法之间,他偏好于公法:这是李大钊法律思想的一般特点。当然,这与李大钊所处的时代有关,1913—1927 年间,北洋政权更替频繁、民主与专制针锋相对、外国势力虎视眈眈,乱世需要宪法和公法发力,调整民间细故的私法显现不了社会的力量,相当部分还在适用大清帝国的民事规范①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北洋政府时期的公法与私法出现反差。宪法更替频繁、政治斗争惨烈,公法混乱不堪,但是私法却在有序推进,逐步朝着法治文明发展。中国法律史上,大理院的审判对私法的贡献颇巨,还形成了“法律规定、习惯法和条理”的法律适用顺序。关于法律史研究,宪法与私法有着完全不同的景象,而现代史和党史的研究,基本上不论及私法。《中国法制史》编写组:《中国法制史》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第256页。。李大钊经历过近代多个版本的宪法文本。一个受到法学教育且对政治有浓厚兴趣的年轻人,将宪法当作研究和政论的重心,都在情理之中。在民彝与政治问题上,李大钊最后把民彝归结为“法”,归结为“宪法”,意味着民主与宪法在李大钊内心中有至高的地位。
李大钊明确指出,民彝就是宪法的基础。比较宪法,是民国早期学术中的显学。李大钊对欧洲和北美各国宪法有着细致的阅读和翻译,还撰写过大量宪法性的政论文章。这里,李大钊从学术上对他早年的宪法思想进行了有力的总结,将宪法与民彝关联起来。他称英国宪法基于英国人的固有本能。李大钊援引戴雪的《英宪精义》,将“此其所云英人固有之本能,即英之民彝也”[12]271。戴雪把英国宪法的特征总结为:一是法治主义,二为议会主权,三是宪法惯例[13]。这里,李大钊将第三项英国宪法的惯例单列,以论证他的民彝论:国法与民彝相通,有利于政治上的疏通。
2.法律民彝论要义
宪法只是外在的形式,宪法的内核则是政治。要解释宪法的内在精神,必定会从法学深入到政治学。这是偏重政治学法学家通常的做法,李大钊在此推出了约翰·密尔的自由主义、达尔文的进化论和法治主义三面大旗。理想的民彝,就是自由、民主、进步和法治。
首先,在1916年李大钊心里,善治的参照是密尔所描写的代议制和自由论。集民众个人的才智,用于公共的政治事业,代议制造成政治上的伟绩。代议制的基础在于个人的自由,在于个人与他人之间的权利界限。这里,李大钊将民彝与自由、意志自由联系了起来,“此类意念自由,既为生民之秉彝,则其活动之范围,不至轶越乎本分,而加妨害于他人之自由以上”[12]272。他比较了民主与个人崇拜的优劣,民主可以长治久安,而个人英雄主义则不可依赖。一个社会一旦失去了自我膜拜英雄,就必定导致政治的腐败。崇古敬圣者,贯穿于历史的“典章制度,德礼政刑”,“纲常法度之入人既深也,先圣创其规仪,后儒宗其模式”[12]275。民主优于英雄的个人魅力,李大钊时代,马克斯·韦伯的“克里斯玛个人魅力的英雄主义”[14]尚未正式传到中国,但是亚里士多德的政体论、孟德斯鸠的共和主义和卢梭的民约论,已镶嵌进中国学者的知识结构之内。
李大钊在论述自由时,特别强调了言论自由的重要性。苏格拉底“被以慢神不道、惑众倾邪之罪而戮之”,托尔斯泰被逐出教会,都是因言论自由被法律惩处的例子。然后,“真理正义,且或在邪说淫辞之中也”。结论是,“立宪国民之于言论自由也,保障之以法制,固为必要,而其言论本身,首当洞明此旨”[12]283-284。天经地义和邪说淫辞,并非一成不变,“法律禁之,固所不许,社会压之,亦非得宜”,所以,立宪政治需要不同的思想,需要言论的自由[16]。
其次,李大钊以进化论的观点批评政治法律史上的复古主义和英雄主义。启蒙主义和进化论,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两大主流理论,李大钊顺应了这样的历史潮流。从思想史的角度看,中国式的启蒙是西方18 世纪理想主义与19 世纪历史主义的叠加。从学术史的角度看,启蒙主义的理想与历史主义的现实存在矛盾,启蒙主义对未来的向往与历史主义的保守发生着冲突,但是,对于清末民初内乱外患的中国来说,兼容了启蒙主义和历史主义,消除或者掩饰了其中的矛盾,最后表现为阳光般地追求民主自由的进化论。李大钊指出,理之创立于古者不必其宜于今也,法之适用于前者不必其合于后也,“是则民彝者,可以创造历史,而历史者,不可以束制民彝”[12]277,后一句,可以称为经典。民彝是一个“神”一样的存在,历史、典章、法律都是它的派生物。这里,李大钊擅长讨论大历史观下的政治与典章,但从学术史的角度看,其中的法理,既有自然法学所论法律制度与法律理想的紧张关系,也有历史法学所叙法律与民族精神的对应关系。自然法学的核心在于理想和价值,历史法学相信民族精神或者法律的进化,18—19 世纪西方自然法学与历史法学同时存在于李大钊的法学思想之中。虽然这个时候,中国法理学界只知道18 世纪的孟德斯鸠和卢梭,外加19 世纪的边沁和密尔,尚未深入研究法学中的历史学派。梅因的“从身份到契约”说、萨维尼的“法律民族精神”说、斯塔姆勒“可变内容的自然法”和科勒的“法律与文明论”尚未出现在李大钊的著述中。尽管如此,李大钊的法学理念与19 世纪欧洲法学心灵相通,天涯比邻。
最后,李大钊从中国古代经典中发掘出“法治主义”。英雄崇拜衍生出人治与法治的论题,中国历史的资源很多。李大钊从老子“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出发,先推演出“人治”:“法律,死物也,苟无人以持之,不能以自行”,后引申出“法治”:“若惩人治之弊而专任法律,与鉴法治之弊而纯持英雄,厥失维均”。不过,在唯民主义与英雄主义之间,前者为立宪之本,后者为专制之原。立宪之道,在能导民自治而脱他治。李大钊说,欧洲的代议制尚处在试验之中,是否优良,有待观察,但是不退回专制,则笃信无疑。
李大钊的法治主义理想,在于法律为“政治行为之准则”的理想,在于“秩序与进步”的兼顾。他援引海智氏(Hedges)的话说,“法令与判决即多数表布之意思,迄于为新行立法制定所更,为兹土之法律,并政治行为之准则焉”。[12]285在秩序与进步方面,李大钊提到,秩序为法之事,进步为理之事。这里李大钊提出了“理”概念,明确区分“法”与“理”,以理之力著为法之力,才有安全与秩序;以理之力摧法之力,才有进步与演化。秩序为法之所守,进步为理之所摧。新教之于天主教的革命,卢梭、孟德斯鸠和伏尔泰之于法兰西大革命,都是“理”对“法”的推动力①“近世自由政治之轨者,起于孟德斯鸠、卢骚(卢梭)、福禄特尔诸子之声也。他如狄卡儿、培根、休谟(旧译秀母)、康德之徒……而清新之哲学、艺术、法制、伦理,莫不胚孕于彼等之思潮”,李大钊《〈晨钟〉之使命》,《李大钊全集》第1卷,第331页。。李大钊将英国《大宪章》(也称《自由大宪章》)、《权利请愿书》(即权利法案),美国《独立宣言》和“吾国之南京《约法》(即《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都视为“理之力冲决法之力,而流露之民彝”[12]285-286的法律成果。“理”决定了“法”,“法”体现了“民彝”。
李大钊高度评价“理”的地位,阐释了“理、法和民彝”的关系:“盖法易腐而理常新,法易滞而理常进。国之存也存于法,人之生也生于理。国而一日离于法,则丧厥权威,人而一日离于理,则失厥价值。故立宪国民之责任,不仅在保持国之权威,并宜尊重人之价值。前者政治法律之所期,后者学说思想之所为。前者重服从、尚保守,法之所禁不敢犯也,法之所命不敢违也。后者重自由、尚进取,彝性之所趋,虽以法律禁之,非所畏也。彝性之所背,虽以法律迫之,非所从也。”[12]286这里,李大钊融合了中西方哲学的精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核心,就在于“国法、人情与天理”②“所以天理国法人情,实在是三位一体,实在都属于法的范围。没有天理的国法乃恶政下的乱法,没有人情的国法乃霸道的酷法,都不算是助长人类生活向上面有益于国家社会的法律”,参见陈顾远:《天理·国法·人情》,载《中国文化与中国法系——陈顾远法律史论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277页。;西方法律传统的基本逻辑,就是“事实、规范与价值”三位一体③“阿奎那所作的亚里士多德式的思辨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区别,与现代我们所指的‘事实’与‘规范’或者‘实然’与‘应然’的对照相比是如此相似”,参见菲尼斯:《自然法与自然权利》,董娇娇、杨奕、梁晓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第29页。。到此,李大钊完成了他的法律民彝论:法律的本质在于民彝。民彝有器、道和法三个面相。法律的内涵则是现代社会的民主主义、进步主义和法治主义。法律的内在逻辑,无非法的权威、理的价值和彝的神圣。
四、马克思主义法理学观
李大钊并没有专门文章论述马克思主义法理学,但在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他信手拈来丰富的法理学素材。李大钊阅读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典,通俗地表述了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法理学。在论证马克思主义原理处,他经常以法律或法律史为例来予以说明。从理论渊源上看,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法理学,既有对西方启蒙学者法律理念的批评继承,也有对共产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历史梳理。
(一)对西方法学家的评论
从古代的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和托马斯·阿奎纳,到近代的孟德斯鸠、卢梭和伏尔泰,乃至19世纪的边沁和密尔,李大钊都有涉及。可以说,西方思想史是李大钊理论的一个重要来源。20 世纪20 年代之前,他阅读大量欧洲古典和启蒙主义的著作;20 年代之后,他转向马克思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李大钊是一个具有思想史视野的学者,是一个广泛吸取外来思想的理论先驱。
20世纪20年代早期,李大钊在北京大学政治、经济两系开设《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和《社会立法》两课,准备了大量的材料[16]306。李大钊的重心在政治学和哲学,20 年代后期开始涉足史学,而由于他年轻时代法学的背景,加上法律思想与哲学政治学思想的交叉性,李大钊也评析过思想史上的思想家。
博丹(旧译鲍丹)是16世纪法国著名的政治学家和法律学家,他的主权论一直是思想史上的一座里程碑①“博丹的主权理论是欧洲政治思想史发展史的一件大事”,在主权理论的指导下,他继而详尽分析了国家这一现象,并使《共和国论》成为一本不朽名著,参见朱利安·富兰克林:《主权论》“导论”,博丹《主权论》,李卫海、钱俊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第6页。。李大钊专文介绍了他的理论,在法律思想方面,评析了博丹法律与历史的关系。博丹的历史观点得益于对法律的研究,法律与历史自始至终连为一体、不可分开。李大钊说,博丹更愿意成为一个法律的哲学家,而不像居雅斯(Jacques Cujas)那样专攻罗马法,只读拉丁文。罗马法毕竟过于狭隘,不足以解释罗马法之外的世界,不能成为一般性的普遍法则。要弄清法律的一般规律,发现“一切法典,皆有他们的根柢与理论”,“欲达到此法则,须谘(咨)询于法理家,同样亦须谘(咨)询于历史家”[17]。为此,博丹区分了自然法与人为法,认定这一区分乃是法律普遍形式的原点。这里,李大钊更看重历史与哲学,更看重法律规定内在的精神和一般发展规律,人为法只是表层,自然法才是法律的深层结构。
对孟德斯鸠的理论,李大钊赞赏和批评并存。一方面,李大钊称赞孟德斯鸠有亚里士多德和亚当·斯密一般的创造力。李大钊说,孟德斯鸠时代的“法兰西的法律,惨忍无人理,仁明如孟氏者,自不忍出视此等法律之推行,而不思所以摧除之也”,因此才有了后来的《论法的精神》。论法的精神讨论法律与风俗、气候、信条、政体的关系,孟德斯鸠遵循历史的研究方法,“他求着纯粹的当作那么多历史的事实去说明那些法律”[18]370。另一方面,李大钊还是认为孟德斯鸠存在致命的缺陷,那就是仍然“太把法律看作孤立的事实,看作独立的现象,看作静止的与完全的存在了”,“不知道一个法律对于别一法律的关系”,“不知道一个法律的阶段对于别一阶段的关系”,“不知道法律的每一阶段与系统,对于宗教、艺术、科学与产业的共同存在,及同时代的阶段与系统的关系”[18]371。李大钊说,“社会现象如法律者,不能如自然哲学与化学的纯粹物理的现象以为说明”,而在于法律发展和演化的普遍法则[18]371。李大钊说,孟德斯鸠的缺陷是18 世纪学者的共同难题,他们缺乏一个真实的研究方法,比较立法学的完备科学,要等到19世纪。孟德斯鸠以其“异常的推测力”能达到“近似的说明”,但由于缺乏科学的方法,导致著作“安排错混,结构紊乱”[18]372-373。他既不演绎,也不归纳,把狭隘的人类立法经验统合,与真理并列[18]376。李大钊用大量篇幅批评孟德斯鸠的理论,这显示了他强大的理论功底,这一点与梁启超泛泛介绍孟德斯鸠和严复毕恭毕敬翻译孟德斯鸠有着天壤之别,究其原因,在于这个时候的李大钊不再是一个清末民初的旧式文人,而是具有唯物史观的马克思主义者。
在评论法律思想史上学者理论的同时,李大钊提出了不少自己对于法学研究的看法。他认为,对于法律的明白、自觉的解释,古希腊、罗马和中世纪的人们并不能提供。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第4 卷提出了30 个名词,就是没有“法律”的定义,“未有一焉符于法律的现代科学上的意味者”[18]374,而孟德斯鸠称“法律是起自万物本性的必然关系”,同样没有提出一个关于法律的概念。
李大钊也肯定孟德斯鸠的理论贡献,比如赞同他将法律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法律随民族特殊性不同而内容各不相同。他论述过政体有君主、贵族与共和的三分法,政体之下有民刑法典、节用法和妇女法律的对应关系,立法、行政和司法的权力分离,政治自由与法律的关系,法律与民族精神的关系,法律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宗教信仰与法律的关系,孟德斯鸠都仔细鉴别、适当评论。同时,李大钊对此的论述也不乏法律思想的火花。在法律与民族性问题上,李大钊说,人为的制度与法律,是一种民族性的效果,而不是他的原因。民族之间的人种差异、道德质性、历史往例和物理境遇都不相同,因此移植一个民族的法律到另外一个民族难以奏效。李大钊肯定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认为这是他法理和政治学的“真正的神髓”[18]378。
李大钊对孟德斯鸠结论性的评价是,他“大规模和最有力”地指出了法律、习惯和制度“实在是什么东西”,但是“孟德斯鸠未曾有建立历史哲学的志愿”,尚未将法律与社会有机体之间的“原因与境遇”揭示出来,这一任务的完成有待于历史学派的兴起和历史科学的进步[18]382-383。
(二)马克思主义法学
李大钊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认识,源自于阅读《资本论》《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和《经济学批评》等文献。在他所引用的《经济学批判》文字中,涉及了法律的论述。“社会的物质的生产力,于其发展的一定阶段,与他从来所在那里面活动当时的生产关系,与那不过是法制上的表现的所有关系冲突。……于是乎社会革命的时代(到)来。巨大的表面构造的全部,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动,或徐,或激,都变革了”[19]13。
李大钊的演绎,是一切社会上的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哲学的精神构造,都随经济的构造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精神构造为表面构造,基础构造则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李大钊称赞马克思的社会学是一种进步,将三门各自发展的学科融为一体,也就是经济、法律和历史,并断定经济现象决定了法律现象。“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他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他们一切的基础”,“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子女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20]。
李大钊认真对待不同的声音,在法律对于经济的反作用问题上,李大钊援引了马克思与恩格斯合作的《共产党宣言》,也强调法律对经济的变更力量。李大钊提及的例子,就是劳工运动对经济行程的影响。资本主义的经济趋势是导致工人日益贫困化,但是工会运动能够反害为利,争取更多的劳银。英国的铁路总会、交通总会和矿业总会三家联合,向政府和资本家提出各种条件,声势浩大、成效显著。李大钊评论道,“这自觉的团体活动,还没有取得法律的性质,已经证明他可以改变经济现象的趋势,假使把这种活动的效力,用普通法律,或用那可以塞住经济现象全进路的财产法,保障起来,巩固起来,延长他那效力的期间,他那改变经济现象趋势的效力,不且更大么?”[19]20-21
李大钊还引用了欧洲法律史上的例子来说明法律对经济的反作用:其一,诺曼人从法国侵占了英国,征服了英国全境,为了保持其大地产权,制定了限嗣财产制和信托制,以保其独占权。其二,与英国相反,大革命后,中产阶级剥夺了贵族和僧侣阶级的财产,他们意在分割而非独占,因此制定了遗书遗产特别法,防止地产重新回到大地产制。英法两国的法律实践提供了法制影响经济进程的范例。因此,“经济现象和法律现象,都是社会的原动力,他们可以互相影响”[19]21。
即使如此,李大钊仍然坚持唯物史观,称法律对于经济的影响,并不改变经济发展的大势。或者说,当法律的影响与经济发展趋势一致的时候,法律的作用才能显现,反之,与经济大势相反的法律,也起不到改变经济的作用。比如资本家的贪婪与劳工的自卫,都是资本主义下的自然趋势,这样工会的抗争与工会立法才能发挥作用。再比如,假定英国立法遏制大地产、法国立法抑制小地产,法律也不会取得好的效果,因为英国大地产制和法国的小地产制与英法经济发展趋势一致。所以,“团体行动、法律、财产法三个联续的法则”,“不能拿他们推翻马氏唯物史观的全体”[19]22。马克思唯物史观除了经济决定法律等表层构造外,还强调阶级之间的对立与竞争,李大钊得出了“法律是阶级的法律,政治是阶级的政治,社会是阶级的社会”的结论[11]138。
(三)社会主义法律:从空想到科学
李大钊明确区分了共产主义(Communism)和社会主义(Socialism)。从政治、法律和经济三方面考察社会主义,那就是:政治上,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法律上,一方面废除私有制和遗产制的旧的经济生活与秩序,另一方面规定新的经济生活与秩序,将资本财产法、私有者改为公有者的制度;经济上,满足劳动者的欲望和收益[16]245。
李大钊追溯了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史,虽然他的重点在于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但是其中偶尔也关涉到法律制度。在介绍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时候,他指出盗贼罪源自贫困,贫困则来自私有制。圣西门“尽7年之力研究生物学与法律学”,蒲鲁东在巴黎二度被“监禁三年”,称私有制乃“万恶之渊源”,欧文向英国政府呼吁制定工厂法“借此救济一般工人之困苦生活”[16]249,256,275。在评析蒲鲁东理论时,李大钊较多篇幅论及他的法律思想。在刑法方面,他列举了蒲鲁东关于盗夺的15 种形式:街上杀人越货、杀人主谋共谋、破坏账目、窃取财货、欺诈、伪造文书、制造假币、诈欺、诈骗、滥用信用、彩票抽奖、高利贷、食租、不当得利和过分生产的利息。在民法方面,蒲鲁东反对占有制度,称“民法并不是为保护财产而设,是为人类之财产平等起见而设”,“民法根本之精神是在乎平等财产”。李大钊评论说,蒲鲁东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其观点建立在自由和正义之上。在蒲鲁东看来,法律是束缚自由之物,保护所有者的利益。因此,“法律、国家乃违反正义及自由之物,所谓法律、国家,不过有产阶级之维持其地位者”。蒲鲁东要废除违反自由和正义之物,“惟有契约则须遵守”,遵守契约则要以自由意志为归宿[16]273。
对于欧美现代国家里的宗教团体,李大钊将其归结为乌托邦运动的一部分,他专章讨论过美国境内多个来自欧洲的宗教社会团体。由于不满欧洲宗教迫害,欧洲宗教团体到美洲寻找宗教自由的新大陆。对此,历史学家讨论很多,其中,现代法律与古老宗教教义存在矛盾冲突,充斥着法律史文献。
另外,唯物主义有着自己的思想史,李大钊追溯到孔多塞、圣西门、梯叶里、米涅和基佐,在他们眼里,“时代的理想、教义、宪法等,毕竟不外当时经济情形的反映”。李大钊再提蒲鲁东的所有权理论,称赞他以经济解释历史。李大钊对唯物史观的归纳是:经济塑造社会的表面构造,法律、政治和理论都是表面的构造,不能影响经济现象。“法律他是人类的综合意思中最直接的表示,也只能受经济现象的影响,不能与丝毫的影响于经济现象。”[19]7-8
李大钊列举出具体的例证,证明经济能够影响法律,而法律不能影响经济。17、18 世纪的商法,试图抑制商业的价格、奖励输入金块,以及英国推行反托拉斯法遏制垄断,都没有成功,都说明“法律的力量不能加影响于经济趋势”。有些法律,曾经与经济对抗,但抗争的结果,是法律适用范围缩减最后归于无效。比如,欧洲中世纪遏制暴利的法律与高利率经济现象对抗,利润来自经济自然涨落,法律即使存在但实际上无用,成为废物。“法律现象远追不上他欲限制的经济现象,却只在他脚后一步一步地走,结局惟有服从而已。潜深的社会变动,惟依他自身可以产生,法律是无从与知的”,“欲以法律现象奖励或禁遏一种经济现象的,都没有一点效果”[19]9。
从对博丹和孟德斯鸠的评论,到空想社会主义和早期唯物史观理论的梳理,最后形成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理论,李大钊的理论进路异常清晰。他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提炼出法理学的一般原理,内容是准确和完整的,与20世纪40年代后李达的法理学大纲中的马克思主义法理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一致的,他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先驱。
遗憾的是,李大钊离世过早,没能继续他的学术研究,也没来得及阅读同时代苏联法学家的国家与法的一般理论。新建立的苏联需要自己的理论,与李大钊同时代的苏联法学家众多,其中最有名气的算是斯图契卡和帕舒卡尼斯。斯图契卡1921 年出版《论法律的革命作用与国家:法学通论》,他给出的法律定义“法律是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并为这个阶级有组织的武力所保卫的一个社会关系的体系”①参见凯尔森:《共产主义的法律理论》,王名扬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第79页。其中“阶级”“武力”和“社会关系”关键词,与李大钊的表述十分接近。帕舒卡尼斯于1924 年出版《法的一般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开启了“法的商品交换理论”,将阶级意志论和生产关系论深入到了商品的交换和法的一般理论②参见帕舒卡尼斯:《法的一般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姚远、丁文慧译,商务印书馆,2022,第29页。。两人的著述和争论,是新生苏维埃法学的一个黄金时期,开启了共产主义法律理论的时代。历史虽然不能假定,但是,如果李大钊1927年能够度过劫难,继续追踪苏联的法律理论,那么他必定会推动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研究与应用,更早地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法理学。
结语
李大钊早年在北洋法政学堂和早稻田大学的法政教育背景,为其打下了初步的法学基础。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是李大钊的主色调,而法律和法学则是他政治实践和政治理论的一个底色。探寻李大钊法理学,是现时代法学研究者的一个历史使命。
李大钊的法理学思想的形成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从启蒙主义角度出发,他提出了“法律民彝论”;从唯物史观出发,他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法理学。如同现代中国革命的理论家一样,李大钊的思想史轨迹是从民主主义法学转变为共产主义法学的。李大钊对于法律与权力、法律与道德的专题研讨,充分体现了他的理论功底;而对政治权力合法性与正当性的论证,充分显示了他法律政治学的理论功力。
法律民彝论是李大钊早期法理学思想的一个顶峰。他以中国古代哲学的“道与器”二分法展开他的法律民彝论,最后融合近代西式的民主、自由和进步的理念,把法律的本质归结为法治主义。兼顾中西、追求民主和法治,李大钊开创了独具特色的法理学。
李大钊法理学的归宿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他从法律和法学的角度阐释了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一般原理。李大钊批判和继承了16—19世纪从博丹、孟德斯鸠、卢梭和密尔的西方政治与法律思想史,继承和发展了共产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法律学说,从马克思的经典中提炼出唯物史观的法律一般理论。李大钊是早期共产党人中善于充分吸取外来法学理论资源的理论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