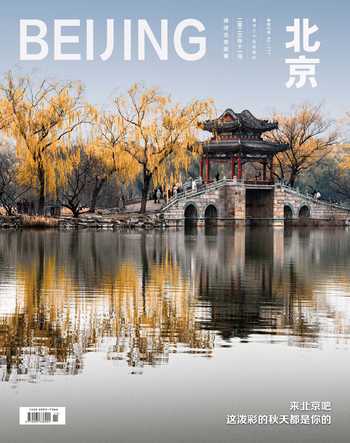老字号,心头好 秋日限定的“斋”里饽饽
北京最权威的“民间餐饮榜单”上,向来只有“号”,而不认“星”。老字号的每一道菜肴,不仅是美味的传承,更是历史与文化的延续。食肉如此,挑选点心也一样。北京人称呼点心为“饽饽”,作为老北京的社交神器,老北京人走亲访友、婚丧嫁娶都靠饽饽交际,一个饽饽匣子串联起亲戚朋友、街坊邻里。吃饽饽讲究时节应景,不仅要应和各个时令的习俗,更与食材何时上市息息相关。四月的鲜花玫瑰饼、鲜花藤萝饼;五月节的江米小枣粽子、五毒饼;盛夏的绿豆糕;八月中秋节的自来红、自来白、提浆、翻毛月饼;九月重阳,应节供应的是重阳花糕……
敬老是中国人最深厚的根脉意识,重阳节是名副其实的“中国老人节”,因而这个节日与亲人,与故乡自有深刻的情感交集。重阳节时,除了登高望远,北京人也会选择买上重阳花糕回家看望父母。北京的重阳花糕是一种用两三层枣泥馅,中间夹上青梅、山楂糕、葡萄干等果料制作而成的糕点,咬上一口,香甜软糯不腻人。著名文学家梁实秋出生并成长于北京,在离开故土后,花糕成为让他眷恋的老北京味道之一。在《满汉细点》一文中,他曾写道:“花糕是北平独有之美点,在秋季始有发售,有粗细两品,有荤素两味。主要的是两片枣泥馅的饼,用模子制成,两片之间夹列胡桃、红枣、松子、缩葡之类的干果,上面盖一个红戳子,贴几片芫荽叶。”可见,已经形成记忆的味道并不会因为一个人的成长或离去而消失,相反,它始终牵连着漂泊在外的游子。
北京重阳花糕太过有名,以至于它们“不甘心”仅仅成为小说和散文中的点缀,而且还要化身为一段往事中的主角。在《唐鲁孙谈吃》一书中,作者唐鲁孙就曾讲了一个关于重阳节花糕的故事:北洋军阀曹锟最爱吃重阳花糕,有一年关照嬖人李彦青订一批重阳花糕给他几位贴心的旧属,谁知李彦青事一忙给忘了。重阳节曹锟在怀仁堂宴请政要听京戏,忽然问王承斌吃到花糕没有。王根本未曾蒙赐,又不便说明,含糊其辞。李彦青知道早晚西洋镜拆穿,一定有麻烦,于是连夜派人到正明斋叫开大门,立刻开炉赶制两千只重阳花糕分别送出。此例一开,北平饽饽铺一年到头都有重阳花糕卖。
老北京点心花样繁多,做工精细,不仅老北京人对它们怀有独特的情愫,文人笔下更是能常见它们的身影。北京稻香村是光绪二十一年(1 8 9 5),由南京人郭宝生创办于前门外观音寺,即现在的前门大栅栏西街东口,迄今已有100多年。不论是枣花酥,还是经典的山楂锅盔,稻香村的京味儿老点心总承载着最美好的味蕾记忆。其中,稻香村的山楂锅盔形似锅盔,精选山楂馅料,工艺、口感均保持原味。馅皮酥松,内如金糕,色泽通透、酸甜可口,疏松软糯,尤为许多北京人所喜爱。
1 9 1 2年,鲁迅来到北京教育部工作,因为看不到个人的未来,情绪十分低落,常常宅在绍兴会馆里辑录金石碑帖,校对古籍。彼时,位于观音寺的稻香村糕点店,离绍兴会馆不过两三里路,鲁迅常常会去光顾。根据《鲁迅日记》统计,从1913年到1915年,短短两年里,他在日记中记录去稻香村买糕点就有15次,山楂锅盔等老北京传统糕点,可能正是他那段幽暗时光中为数不多的亮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