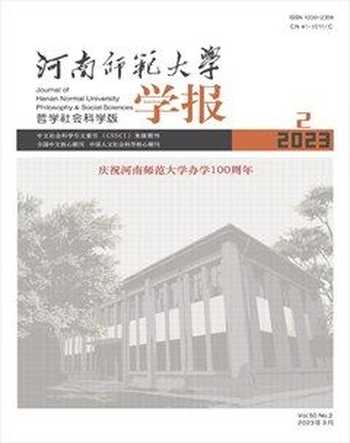商周铜器铭文纪时方式及对历史散文的沾溉
陈芳兵 李山
摘 要:商周铜器铭文纪时方式的发展呈现出清晰的脉络。殷商铜器铭文纪时受甲骨卜辞影响较大,周朝损益殷商纪时方式,确立了纪时单位“由大到小”排列的新表达模式,并在不同时期表现出鲜明的特征。西周初期和春秋战国之交,铜器铭文纪时先后出现两次较大的变动。第一次是统治者主动进行的历法革新,第二次是铭文纪时在历史环境中的被动调整。铜器铭文纪时中呈现出的整体性意识、线性意识与记事重于纪时意识,为编年体历史散文的问世和发展提供了必要准备,铭文纪时单位和表达方式也为编年体历史散文所借鉴。铜器铭文的纪时意识和纪时表达共同影响着后世历史散文的创作,塑造着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和角度,具有重要的文学和文化意义。
关键词:纪时方式;变化原因;历史散文;文化意义
作者简介:陈芳兵(1991—),女,河南汝州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先秦铜器铭文文学研究;李山(1963—),男,河北高碑店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文化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7ZDA254)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2023)02-0084-07
收稿日期:2022-10-08
纪时书写是商周铜器铭文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各种因素影响,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特征。前辈学者对此进行过有益的探索,多致力于历法考察或铭文纪时词语含义的探究[王国维、董作宾、郭沫若、陈梦家等在相关方面均取得丰硕成果。参见叶正渤:《金文月相纪时法研究》,学苑出版社,2005年,第15-27页。]。王晖、林甸甸、叶正渤等学者关注铭文纪时方式,或侧重考察铭文纪时与早期历史叙事之间的关系,或归纳西周铭文纪时特征,但均存在一定的缺憾[王晖《论西周金文记时语词及大事系“年”的史学意义》指出铜器铭文中的“纪年”现象,是编年体史书记事方式的萌芽。(王晖:《论西周金文记时语词及大事系“年”的史学意义》,《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林甸甸在此基础上提出“纪日用语”的确立与早期历史叙事间的演变关系。(林甸甸:《“纪日用语”与西周早期叙事方式的萌芽》,《文学评论》,2019年第2期。)此二人的研究成果虽涉及铭文纪时考察,但侧重阐释铭文纪时与历史叙事的关系,未进行文体贡献、文化意义等方面的探究。叶正渤《略论西周铭文的记时方式》对铭文纪时方式进行分类,但其探究局限于西周时期,成果有待进一步提炼和完善。(叶正渤:《略论西周铭文的记时方式》,《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本文拟通过梳理商周不同时期铜器铭文纪时方式,分析其变化原因,挖掘铭文纪时中蕴含的思维意识,揭示其对历史散文的影响,以期认识商周铜器铭文纪时方式的自身价值、文体贡献,以及文化意义。
一、商周铜器铭文纪时特征
商周青铜器中包含纪时书写的铭文虽占少数,但它们反映了早期人们对时间的认知和纪时方式的萌芽,并在不同时期呈现出独特风貌,是后世纪时表达的雏形,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以下从纪时语言和纪时方式两方面,对梳理所得约1100多篇商周青铜器纪时铭文分别加以分析[商周铜器铭文绝大多数不纪时,在包含纪时表达的铭文中还有少量仅纪年、仅纪月或者仅纪日的表达现象,因其未能展现对纪时单位的排列,故统计时均未计算在内。]:
首先,殷商铜器铭文纪时语言和纪时方式受甲骨卜辞影响较大。殷商铜器铭文多于文首纪日,以天干地支标示具体日期。对月份和年份的表达,或兼而有之或只纪其一。以“月”为纪月单位、“祀”为纪年单位[有学者认为以“祀”纪年,意思是以经历周年的宗庙祭典表示一年的时间。],均使用数字标示具体月份和年份,置于文末。纪时方式承袭甲骨卜辞,按照“从小到大”的顺序排列纪时单位。如《宰椃角》(《殷周金文集成》09105)的“庚申……才六月,隹王廿祀羽又五”[《殷周金文集成》以下简称《集成》,《新收殷周青铜器铭文暨器影汇编》以下简称《新收》,《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以下简称《铭图》,《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续编》以下简称《铭续》。],其行文思路与殷墟卜辞的“癸未卜,争贞:旬亡祸?三日乙酉夕,月有食。闻。八月”[李圃:《甲骨文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页。]颇为相近,另有《小臣俞尊》(《集成》05990)、《小臣邑斝》(《集成》09249)、《四祀邲其卣》(《集成》05413)等约60篇铭文,均可作如是观。该现象直至西周早期铜器铭文纪时中仍然存在。
其次,西周铜器铭文继承先周语言习惯,对殷商纪时表达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周人保留殷商纪月和纪日方式,革新纪年单位,改“祀”为“年”,加入月相这一新纪时模块。具体来说,西周铭文承袭殷商使用数字标示具体年份,该手法后演变成铭文纪年的绝对主体表达。如《庚嬴鼎》(《集成》02748)的“隹廿又二年”、《作册睘卣》(《集成》05407)的“隹十又九年”等320多篇铭文。但康昭时期出现以事纪年的新表达,即以该年发生的重大事件作为纪年标志,但数量相对较少。如《旅鼎》(《集成》02728)的“隹公大保来伐反夷年”,《鼓罒每簋》(《集成》04047)、《作册卣》(《集成》05432)、《士上盉》(《集成》09454)等约10篇铭文均使用这一新的纪年方式。月相是以月亮变化情况代表所记时间在一月中的大致区间。西周早期出现较多的是“既望”,有少量的“既生霸”“既死霸”,中晚期月相词使用逐渐多样化。
上述铭文纪时语言在整个西周时期较为稳定,仅铭文纪时模式有所变动。成康时期的铭文纪时模式表现出新旧杂糅的特点,仍保留有浓重的殷商痕迹,是纪时表达的过渡状态。具体有两种主要形式:一是在“从小到大”顺序纪时后加入月相,表现为“日+月+月相”。如《保卣》(《集成》05415)的“乙卯……才二月既望”,约有5篇铭文属于此类表达。二是在纪时后又保留殷商文末纪年的习惯,表现为“月+日+年”“月+月相+年”。如《作册析觥》(《集成》09303)的“隹五月……隹王十又九祀”,《何尊》(《集成》06014)、《大盂鼎》(《集成》02837)、《小盂鼎》(《集成》02839)、《作冊析尊》(《集成》06002)等7篇均属该纪时类型。上述两类纪时方式在西周中期已极为少见,中期仅有《五祀卫鼎》(《集成》02832)、《吴方彝盖》(《集成》09898)等极少的殷商遗民铜器铭文仍以“月+月相+日”纪月纪日并于文末纪年,是殷商遗民习俗的偶尔表现,并非普遍现象,至西周晚期则基本消失。
纪时单位“从大到小”排列模式,代表西周铜器铭文纪时的新变。它兴起于西周早期,中晚期数量迅速增加,分别为233例和115例,远多于早期的59例,是两周时期最主要的纪时方式。该模式使用“隹”作为纪时标志,统领纪时要素。各纪时单位按照“从大到小”顺序组合,多使用“月+月相+日”或“年+月+月相+日”的形式,另有一些“月+日”“月+月相”的变体。西周晚期纪时方式与中期纪时模式差别不大,仅不同阶段组合要素略有差异。但晚期铭文纪时更趋成熟和统一,其变体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在类型上都已大幅减少。
其中“月+月相+日”的纪时模式贯穿整个西周时期。如《员鼎》(《集成》02695)的“隹正月既望癸酉”,又如《公鼎》(《新收》75)的“隹八月初吉丁丑”,《公贸鼎》(《集成》02719)、《昌鼎》(《新收》1445)、《伯鲜鼎》(《集成》02664)、《晋侯对鼎》(《新收》851)、《南宫柳鼎》(《集成》02805)等220多篇均属于这一类型。其中尤以西周中期数量最多,有150多篇。
“年+月+月相+日”的纪时表达流行于中期和晚期。如《庚赢鼎》(《集成》02748)的“隹廿又二年四月既望乙酉”,《师酉鼎》(《新收》1600)的“隹王四祀九月初吉丁亥”,《伯大祝追鼎》(《新收》1455)、《史伯硕父鼎》(《集成》02777)、《吴虎鼎》(《新收》709)、《大鼎》(《集成》02807)、《兮甲盘》(《集成》10174)等约80多例铭文均是对此类纪时表达的展现。
除此之外,在“从大到小”纪时模式的变体中,“月+日”集中出现于西周早期,类似纪时铭文约有50篇,以《寓鼎》(《集成》02718)的“隹十又二月丁丑”,《中鼎》(《集成》02785)、《善鼎》(《集成》02820)、《仲中父簋》(《集成》04023)、《伯庶父簋》(《集成03983》)等為代表;“月+月相”多出现于中晚期,如《伯吉父鼎》(《集成》02656)的“隹十又二月初吉”,《倗伯鼎》(《铭图》4卷491页)、《师秦宫鼎》(《集成》02747)、《格伯簋》(《集成》03952)、《邓公簋盖》(《集成》04055)等近40篇铭文属于这一纪时模式。其他如“年+月+日”“年+月”或“年+日”的纪时铭文数量过少,不再赘述。
再次,春秋时期铜器铭文纪时多沿袭西周,仅局部表达有所调整。战国时期纪时语言和纪时方式均发生较大变动。多数春秋时期铜器铭文保留西周纪时语言和表达形式,仅部分铭文出现“吉日”等新月相词语。春秋晚期,铜器铭文出现四季纪时。如《昭王之即鼎》(《铭续》1卷281页)的“隹正孟春吉日唯庚”,《乐书缶》(《集成》10008)、《越王者旨於睗钟一》(《铭图》28卷7页)等属于这一类型表达,但仅有5例,是铭文纪时新要素的萌芽。
战国时期铭文纪时的语言表达发生较大变化。铭文纪时单位于“年”之外,还出现“岁”和“祀”。如《陈纯釜》(《集成》10371)的“陈犹立事岁”、《盦章鏄》(《集成》00085)的“隹王五十又六祀”,《陈喜壶》(《集成》09700)、《公子土斧壶》(《集成》09709)等11篇铭文均属于该纪年类型。纪年和纪月在保留数字标识基础上,分别出现以事纪年和新的纪月词汇,但数量相对较少。其中,以事纪年与西周初期表达大致相似,以《鄂君启车节》(《集成》12110)的“大司马卲阳败晋师于襄陵之岁”,《公孙潮子钟五》(《新收》1139.1)、《子禾子釜》(《集成10374》)等约8篇铭文较为典型;新的纪月词汇亦属个别现象,如“夏属之月”“冰月”等。战国时期多数铜器铭文纪时不再记载月相。
与上述变动较大的纪时语言相比,春秋时期纪时方式承袭西周,较为稳定,仅战国时期有所简化。比较而言,春秋时期主要流行完整纪时模式,该模式继承西周铜器铭文“从大到小”纪时方式,对各部分纪时要素详细记载,多数采用“月+月相+日”表达形式。例如《庚儿鼎》(《集成》02715)的“隹正月初吉丁亥”,《叔原父甗》(《集成》00947)的“隹九月初吉丁亥”,《陈侯鼎》(《集成》02650)、《伯辰鼎》(《集成02652》)、《以邓鼎》(《新收》406)等近200篇均是这一纪时类型。另外,约20例铜器铭文以“月+日”方式纪时,如《晋姜鼎》(《集成》02826)的“隹九月丁亥”,《叔液鼎》(《集成》02669)等。另有极少量以“年+月+日”“月+月相”等变体纪时,大致不出西周纪时模式。
战国时期盛行简约纪时模式,约有430篇,是当时铭文纪时的主要形式,该结构不再进行纪时模块的完整表述,铭文纪时极大简化,对年、月、日等纪时要素仅择其一或其二进行记载,如《十年陈侯午敦》(《集成》04648)的“隹十年”,《商鞅戟》(《集成》11279)的“十三年”等。
要之,殷商时期铜器铭文纪时受甲骨卜辞影响,纪时单位按照从小到大顺序排列。进入西周,经过早期多种纪时方式共存发展后,中期逐渐形成“从大到小”排列纪时单位的统一样式,从而稳定流传下来。春秋时期铜器铭文继承西周纪时传统,重视纪月,较少纪年,春秋后期月相逐渐消失,开始记载四季。战国时期铭文主要纪年,甚少辅以月、日记载,十分简洁。
二、商周铜器铭文纪时变化原因
商周铜器铭文纪时方式在西周早期及春秋战国之交先后经历过两次较大变化。第一次变革主要集中于月相模块的增加和纪时单位顺序的调整,是统治者主动进行的历法变革;第二次变动主要体现在纪时模块的简化和纪时语言的新变,是铭文写作受社会环境影响进行的被动调整。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次变化源于周初历法革新。《逸周书·周月解》明确记载西周统治者在建国初期进行过历法改革,“改正异械,以垂三统。至于敬授民时,巡狩祭享,犹自夏焉。是谓周月,以纪于政”[黄怀信:《逸周书校补注译》,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251页。]。这一革新表现在铭文纪时方式上便是月相模块的加入和纪时顺序的调整。
月相纪时不见于甲骨刻辞或殷商铜器铭文,而源自先周部族纪时传统。先周卜骨中已出现月相,周公庙“肜祭”卜辞记载“五月哉死霸壬午”,月份、月相及干支俱全。又如先周卜骨“隹十月即 亡咎”(H11:55),不少学者认为“即”便是早期月相记载。西周初期,统治者在制定历法时将月相引入并逐渐推广。深究周人月相意识,可能源自其农耕观察。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古代,人们认识时间多以太阳月亮作为直观稳定的参照物。太阳东升西落,表示一天昼夜更替。月相阴晴圆缺,代表一个月时间轮回。其实,月相变化是地球公转产生,是地球在绕太阳轨道上运行,月亮受光面与地球夹角变化导致。而地球公转对耕作影响巨大,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及二十四节气无一不是源自地球公转。因此,长期农耕文化浸润中,周人积累丰富的物候经验,将月亮变化作为四时变动标杆,通过对其标记以期更好认识时间、指导农事。故西周在纪时中加入月相词语,以便对所纪时间进行更加形象的界定。
周初统治者调整纪时顺序,将“由小到大”殷商纪时范式变为“由大到小”的西周样式。“由大到小”的纪时模式早在先周卜辞中就已出现。周公庙“肜祭”卜辞的“五月哉死霸壬午”,及周原甲骨H31:3的“八月辛卯卜”均予以印证。由于文献缺失,尚无法确知该范式出现的具体原因,大致有两种可能:其一,可能与先周甲骨的卜刻目的和记事方式有关。殷商纪时方式源自甲骨卜辞即事发问,点状纪时。卜刻完毕甲骨片被作为档案性质收集起来以备来日查找,甲骨彼此并无内容联系,甚至能够发现甲骨上独立补刻日期的痕迹[例如《载王事》一篇,甲骨文字自左至右竖排卜刻,行文阅读亦按此顺序。但在卜骨的最左侧中部,刻有“二月”二字,李圃隶定将其附于文末,作为甲骨纪时要素。但文末尚有足够的空余,这充分說明“二月”并非与前文一起刻上。大概是将甲骨整理归库时为便于日后翻找此片甲骨,临时进行的标签式补刻。],而先周卜骨中尚未发现类似的现象。合理推测,先周甲骨或许在卜刻目的和保存使用上与殷商有较大差别,进而影响到卜辞的纪时思维。其二,周原甲骨纪时表达中已出现“年”“月”“月相”等要素,且周人农耕生活对时间有较高认知需求,或许可以催生出“从大到小”排列纪时单位的纪时方式。因此,周人形成的这种“从大到小”纪时方式可能源自先周甲骨独特的卜刻目的和使用需求。
第二次变化与社会变革关系密切。春秋战国之交,社会变革剧烈,铭文纪时发生巨大变化,呈现出主要纪年的简洁风貌,这是铭文纪时第二次变化中最显著的特征。由于王权下移,诸侯各自为政,天子威信丧失,周王室不再颁朔,缺少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对全国进行纪时表达的约束。各诸侯国自由发挥,铜器铭文随之变动,纪时呈现出多元化特征,语言表达统一性降低,出现不少新纪时词汇,形成多元化纪时风格。该现象始于春秋,至战国尤甚。
春秋战国之交,铜器铭文变革明显,主要纪年,甚少纪月和纪日,表达十分简洁。产生该现象原因大致有三:首先,战国时期社会动荡,礼乐的神圣性进一步削弱,铭文对仪式时间的记载也随之简化。西周时期,礼乐活动时间的选择和执行都需遵循严格的规定。铭文中详细纪时也是重视礼乐的表现。如《礼记·月令》中记载,不同月份的不同时令,均有与之相对应的祭祀对象和祭祀要求。延至战国,礼崩乐坏已甚,礼乐仪式在社会文化中的崇高地位丧失殆尽。因此,记载相关内容的铜器铭文地位逐渐下降,纪时要素日益简化。其次,铜器铭文写作重心转移,导致其纪时书写简化。西周铭文以记事为主,旨在勒功炫耀。时间作为叙事的重要构成,需在铭文中被详细标识出来。至战国时期,铭文功能由叙事转变为标记,铸刻内容多为器主身份、器物信息等。这一时期的器物多为用器或兵器,并非用于某一日祭祀,亦无需频繁铸造,仅纪年已能够满足需求,对纪月或纪日的需求不高。例如《五年司马成公权》(《集成》10385)仅记载督造和主造部门官吏姓名,以及器物重量等内容,“五年”的纪时已能够满足记录需求。最后,简帛、木牍、石刻等类型文献的进一步发展繁荣可能分担了铭文的部分纪时功能。战国时期存在不少记录各国史料的编年类竹简文献,在相对连续的纪时序列下对史料予以集中整理和保存,较铭文能更好实现文献的纪时功能。因此,铭文写作在对竹简等底稿内容进行选择的过程中,对纪时的关注逐渐降低。当然,由于所去年代久远,西周稳定的纪时模式在战国时期已经不具有权威性和约束力。鉴于上述种种原因,战国铭文很少纪月和纪日。
与战国时期不同,春秋铜器铭文重视纪月与纪日,较少纪年。由于社会动荡,周天子无法有力号令诸侯,统一的王年不再是各诸侯愿意遵从的历法标准,“隹王某年”的纪时表达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春秋时期为数不多的纪年铭文所纪均为诸侯之年,表现出对东周天子王年的漠视,如《蔡侯申盘》(《集成》10171)的“元年正月初吉辛亥”的“元年”是蔡平侯元年,又如《者氵刃
钟一》(《集成》00121)的“隹越十又九年”,指越王勾践十九年。春秋时期铜器铭文强调纪月纪日原因可能有二:其一,西周形成的纪时习惯深入人心,短期较难更改,因此保留对纪月和纪日的方式。其二,这一时期虽礼崩乐坏,但诸侯对待礼乐仍保有一定敬畏之心,所铸器物以礼器数量居多,铜器铭文书写相对严肃,纪时也较战国时期更为规范。
春秋晚期开始,铭文纪时放弃使用月相,转而以四季来标示时间。如《乐书缶》(《集成》10008)的“正月季春,元日乙丑”、《昭王之即鼎》(《铭续》1卷281页)的“隹正孟春吉日唯庚”等。该变化可能得益于生产力的发展和历法的进步。春秋战国时期由于铁制农具的出现及发展,井田之外大量私田被开发出来,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纪时认知的进步。四季纪时远优于参考月相的阴晴变化,对于农事的指导更加明确、有力,能够满足飞速发展的农耕需求。
总之,商周铜器铭文纪时方式的变化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历史状况密不可分。西周初期的变化是由统治者主导的一场自上而下的纪时改革。春秋时期,王室渐趋衰微,为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铭文纪时酝酿着局部的变动,至战国中期呈现出显著变化。两次变化都是社会历史的产物,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
三、商周铜器铭文纪时范式对历史散文的沾溉
殷商甲骨在占卜结束后被深埋储藏于地下,直到19世纪末才逐渐开始被发掘和认识,因此对早期史传文学的影响相对较小。青铜器则活跃于商周的祭祀仪式和日常活动中,包括史官在内的人们可以频繁接触到铜器铭文,并受到其纪时思想的影响。商周铜器铭文作为纪时文本的早期形态,是后世史官纪时思维和表达方式的肇始,为历史散文提供了宝贵的纪时范式。
其一,纪时的整体性意识对历史散文的沾溉。整体性纪时意识是指铭文纪时能够以宏观视野,通过特定纪时方式,将散状时间点纳入大的时间框架中,使其有序排列构成一个整体。它起源于西周铜器铭文“从大到小”纪时方式,并对《尚书》《左传》等史传作品的框架體系和篇章结构产生重要影响。
西周铭文“从大到小”纪时模式从宏观视角观照时间,以大纪时单位勾连小纪时单位,建立起各纪时要素彼此之间的联系,使其构成统一的整体。例如《麦方彝》(《集成》09893)的“才八月乙亥”,该纪时方式不仅记载具体时间点“八月”和“乙亥”,更重要的是突出“乙亥”在“八月”这一整体时间区间中的位置。西周中期述祖思潮兴起,史官对《尚书》体例的设定明显受铭文纪时整体性意识的影响。《尚书》将虞夏至春秋(秦穆公时期)的时间跨度划分为《虞夏书》《商书》《周书》等子单元,以突出框架体系在纪时上的整体性。不仅如此,子单元乃至单篇之内,亦受纪时整体性思维的影响。多数篇章于文首纪时,与所叙事件紧密结合,共同形成纪时的整体脉络。与之相似,《左传》创立“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的编年体例,将春秋时期繁杂事件依据其发生时间有序纳入鲁国国君在位的相应年份,不同年份事件彼此作用,构成鲁国十二公250多年的历史。该构架强调不同时间单位之间的紧密联系,同样展现出铭文纪时整体性意识对史传作品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史记》进一步跳出编年纪时限制,采用本纪、世家、列传等纪传体例还原历史原貌,“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司马迁:《史记》,第四册,中华书局,2011年,第2874页。],展现出司马迁的整体思维和对史料的宏观把握,是铭文纪时整体性思维在史传作品中的运用。
其二,纪时的线性思维对历史散文的沾溉。线性纪时是指铜器铭文依照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将不同时间点所系事件依次连起来,真实再现时间流动原貌的纪时思维,是纪时整体性意识在具体表达中的产物。它萌芽于铜器铭文跨时段纪时和以事纪年的手法中,并在早期历史散文的纪时书写中发挥重要作用。
与殷商相比,西周铭文“从大到小”纪时模式已暗含线性纪时的要义,之后发展出的跨时段纪时和以事纪年手法更是对线性纪时思维的突出和强调。昭王时期,铜器铭文出现跨度较大的纪时表达,其形式多为先叙述大的时间范畴(即纪年),后以纪月或纪日为标志,引出不同子范畴内事件的叙述。例如《乖伯簋》(《集成》04331)的“隹王九年九月甲寅,王命益公征眉敖。益公至,告。二月,眉敖至,觐,献帛。乙未,王命仲致乖伯归乖伯貔裘”。通过对“王九年”中“九月甲寅”“二月”“乙未”的有序排列,使得相关时间点及所系事件建立起先后的线性关系,增强了纪时的连续性。受该思维影响,《尚书》在处理史料中繁多的时间点时,亦采用类似模式。如《尚书》依据“虞夏”“殷商”“周”等时间顺序整理史料,甚至单篇之中也以线性纪时作为行文标准。例如《召诰》中“……越若来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越三日庚戌……越五日甲寅……若翼日乙卯……越三日丁巳……越翼日戊午……越七日甲子”[顾颉刚,刘起纡:《尚书校释译论》,中华书局,2005年,第1432—1434页。],与铭文纪时一脉相承。在“越若来三月,惟丙午朏”的大范畴内,以干支纪日的同时突出子范畴彼此的时间间隔,依次叙述“(丙午日)三日后的戊申日”“(戊申日)又过了三日的庚戌日”“(庚戌日)五日后的甲寅日”“(甲寅日)第二天乙卯日”等时间点发生的事件,既展现了时间的线性次序,也体现了不同事件之间的发展关系。同样,《左传》形成“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刘知几:《史通》,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5页。]的编纂模式和编年体例,也是运用铭文线性纪时意识排列和整理史料的结果。《左传》以鲁国十二公在位顺序及时间为参照,将纷杂的事件进行线性整理,对每年的历史进一步按照四季和十二月的形式予以梳理,还原时间流动的本来面貌,是线性纪时意识相对成熟的展现。除此之外,《国语》所确立的国别体例,虽较少精确纪时,但一国史料大致按照事件发生时间的先后顺序进行线性排列。纪传体史书亦是如此,例如《史记》的“本纪”部分,便是按照《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等所属朝代的时间先后排列,甚至具体到一篇之中的叙述也遵循时间顺序线性记载。
另外,铜器铭文中“以事纪年”是其线性纪时思维的又一展现。该手法通过改变纪年方式,将发生在同一年的两件事依次巧妙联系起来。如《旅鼎》(《集成》02728)的“隹公大保来伐反夷年,才十又一月庚申……公易旅贝十朋”,记录了在“召公奭征伐反夷”这年十一月庚申,旅受到召公的赏赐。铭文以事件代替数字纪年,将“召公伐反夷”和“旅受赏”两件事联系起来,不仅呈现出二者的先后顺序,还暗示其因果关系——极可能因为旅在讨伐反夷的战争中表现出色,才受此赏赐。《尚书》借鉴类似表达,不仅关注当下或局部时间,且运用线性纪时思维,将向前回望纳入文本纪时的考虑范畴,通过这一纪时思维将西周历史连缀起来。如《金滕》的“既克商二年”[顾颉刚,刘起纡:《尚书校释译论》,中华书局,2005年,第1223页。],既梳理了“克商”与“王有疾弗愈周公请代之”等事件先后顺序,呈现出更加清晰的线性时间脉络,又增加了这些事件的内在联系,显示出西周中后期文献整理开阔的纪时视野,对后世历史散文影响深远。
其三,记事重于纪时思维对历史散文的沾溉。该思维方式强调在叙述中关注事件本身,不必详细记录每一事件的时间,甚至在不影响整体叙事前提下,仅对事件发生先后顺序予以展现。这一纪时思维源于铜器铭文,后对早期史传作品的纪时和叙事等不同方面产生较大影响。
记载器主功绩是铭文产生之初的最主要目的,纪时作为纪功的附属品,文本篇幅占比较少[多数商周铜器铭文仅关注对事件本身的展现,在纪功叙事中没有纪时书写,再一次印证铭文记事重于纪时的思维。因其不涉及纪时表达,正文部分对此类铭文不再展开论述。]。进入春秋战国时期,器型和功用的变化使得铜器铭文纪时方式日益简化,呈现出更宏阔的视野。例如《中山王鼎》数百字长篇铭文,创作者仅在文首以“隹十四年”将纪时一笔带过,文中大量篇幅用于记事记言和祝嘏祈福。《左传》受这一思维风格的影响,在王年框架下仅记载四季和月份,鲜少进行干支纪日。纪时主要目的之一是为排列和编订历史事件提供线索,而不是对具体时间的追究,甚至在一些史料记载中表现出对事件发生时间的忽略。例如赵穿杀害君主后,史官仅记下“赵盾弑君”。若史传书写重视纪时,依据史官随君记史这一传统,晋史官应立即写下“某年某月某日几时,赵盾弑君”。此外,记事重于纪时思维使得史传创作者更加关注事件本身的内在联系,进而为隐去显性纪时标志创造出国别体和纪传体体例提供了可能。例如,记载长勺之战中“曹刿论战”一事,编年体的《左传》文首有“十年春”的表达,而国别體的《国语》开篇即云“长勺之役,曹刿问所以战于庄公”,进一步淡化纪时,将注意力集中于史料的叙述和编排。又如《史记》关注事件内在联系,不再单纯按照时间连缀篇章,亦是受记事重于纪时意识影响的表现。
其四,纪时表达对史传文学的沾溉。除上述三种纪时思维外,商周铜器铭文在具体的纪时表达上也为史传作品提供了书写范式,主要表现在铭文纪时单位和表达方式两方面。
早在周原时期的先周卜骨就已经出现“年”的语例表达[周人甲骨早在周原时期就已经有某年的语例,如H11:64:六年。],西周建国之后正式改“祀”为“年”。除此之外,继承甲骨卜辞而来的对月份的记载和对“月”这一单位的使用,以及春秋晚期铜器铭文纪时中出现的“春夏秋冬”四季要素[周人早在周原甲骨H11:83中就已经有“今秋楚子来告”,表明有秋季的使用,但西周铜器铭文不见相关表达,因此本文认为铭文中较为成熟的四季纪时出现于春秋晚期。],均在漫长的发展中成为标记时间的基本视角和纪时单位,对历史散文纪时产生深远影响。例如《左传》大框架便是以“年”为单位,按照鲁国十二公在位年限进行编订,在具体年份中以“四季”和“月”为主要单位进行纪时和记事,极个别情况使用天干地支纪日。
商周铜器铭文还在具体的纪时方式上为历史散文提供范例。西周铜器铭文纪年以“王在位时间”为参照,采用“隹王某年”的表达形式。该方式在《左传》中仍发挥重要作用。《左传》编年的依据便是鲁国十二公在位时间,其表达形式和内涵与铭文一脉相承,如“隐公二年”“庄公三年”等。商周铭文中以数字纪月的手法也被历史散文所继承。春秋时期铭文纪月如《郸孝子鼎》(《集成》02574)的“王四月”和《越王者旨於睗钟三》(《集成》00144)的“正月季春,吉日丁亥”等,与《左传·隐公四年》中“四年春,王二月”已十分接近。不同的是后者表现出文本创作的润色和雕琢,将四季置于月份之前,表明创作者已经认识到四季包含月份,表现出“从大到小”纪时的整体性思维。类似的纪时方式在其他历史散文中俯拾皆是,如《国语》的“三十二年春”[左丘明:《国语》,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1页。],《汉书》的“五年冬十月”[班固:《汉书》,第一册,中华书局,2012年,第43页。]等。在记载一些较为重大的事件时,历史散文沿用铭文干支纪日的方式,例如“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16年,第一册,第235页。],“三年春,王三月壬戌,平王崩”[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16年,第一册,第27页。],等等。
要之,铭文纪时分别在思维意识和具体表达上为后世历史散文提供了范式。但也应该看到,整体性纪时、线性纪时和纪事重于纪时这三种意识是彼此联系又相互作用的。例如“由大到小”的纪时方式所确立的整体性意识,同时在具体纪时中也塑造着线性纪时的思维。“以事纪年”的表达形式和“记事重于纪时”的意识在产生根源上又以整体性意识为前提。
四、余论
商周铜器铭文所建立的纪时思维和纪时方式除文学影响外,还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西周建立的“从大到小”排列纪时单位的形式,为先秦乃至后人标记时间确立了整体性的概念,塑造着中国人认识世界的视角和改造世界的方式。例如日晷以指针影子移动来纪时的设计思路和表现手段,展现出古人对时间的线性认知。与之相似,今天钟表的指针移动方式和纪时办法亦是铭文纪时思维在文化和生活中的发展之一。又如,二十四节气的制定也受到铜器铭文纪时思维的启发。在丰富的农耕实践经验基础上,依照不同的物候特征,从整体上将一年时间依次分为二十四个线性节点,以此更好地指导农事活动。另外,后世“天人合一”思想也受铭文纪时的整体性思维启发,强调时间和空间的和谐统一,等等。因此,商周铜器铭文纪时思维是文化要素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文化影响直到今天仍然存在。
The Time Recording Method of Bronze Inscriptions in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and Its Implications to Historical Prose
Chen Fangbing1,Li Shan2
(1.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China;2.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China )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bronze inscriptions in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shows a clear context. The inscriptions on bronze vessels of the Yin and Shang Dynasties were greatly influenced by Oracle Bones . The Zhou Dynasty established a new expression mode of “from large to small”,which absorb the time recording method of the Shang Dynasties, and showed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in different periods. In the early Western Zhou Dynasty and at the turn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nd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here were two major changes in the time recording method of the bronze inscriptions. The first was the calendar reform carried out by the rulers on their own initiative; The second is the passive adjustment of time recording method of bronze inscriptions in the historical environment. The holistic consciousness, linear consciousness and the awareness that recording events is more important than recording time, which provides necessary preparations for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Historical essays. The chronological units and expression methods of bronze inscriptions are also used for reference by historical essays. The concept and expression of the time recording method of bronze inscriptions affect the creation of later historical essays and shape people's way and angle of understanding the world, which has important literary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Key words:time recording method;reason of changing;historical essay;cultural significance
[责任编校 海 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