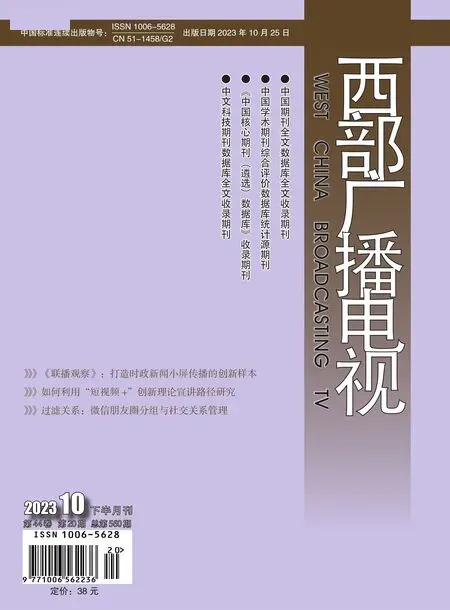三界说视域下《青春变形记》中主体的认同与分裂
陈淑洁
(作者单位: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
《青春变形记》是导演石之予在奥斯卡最佳短片动画《包宝宝》之后,创作的又一部关于家庭与个人成长的动画影片。影片通过刻画一个13岁女孩李美琳(下文称“美美”)在成长过程中与自我、父母、朋友之间的相互影响与碰撞,既展现了女孩的青春洋溢,又刻画了社会关系的复杂多样,最终为我们讲述了一个个体勇于接纳自己、敢于表达自我,以及与外界其他个体和谐共处的理想故事。
雅克·拉康作为国际上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被称为“法国的弗洛伊德”,然而拉康与弗洛伊德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他强调语言对主体产生的重要影响。我们在阅读拉康的文字时,总是能感受到一种召唤,一种来自内心深处的召唤。这股力量仿佛成为我们一生追逐的动力源,促使我们不断地去揭示关于主体的真相。拉康的“三界”是一个框架,而非内容,主要是“一系列的功能运作,它既对主体的存在有一种结构化的作用,也对我们认识主体的生存秩序有一种方法论的意义,它可以帮助我们阐释主体性的构成”[1]392-400。在“主体三界说”中,拉康将主体分为三个层次:想象界、象征界与实在界。“三界”既是主体存在的三个维度,也是构成主体的三种机制[2]84。在不同的界域内,主体自然呈现出不一样的表现形式。《青春变形记》正是在个人与家庭、社会的不同维度下,展现了主体的不同样貌。
1 想象界:主体与他者的幻想
想象界是拉康在“镜像阶段”的基础上提出的,两者虽有很多重叠的部分,但是仍有不同之处。相比镜像阶段强调的是主体的时间辩证法、一个有关现象学主体的神话叙事,想象界更侧重在主体间的互动关系中描述主体构成及其与现实世界的关系。于是,自我与他者变成了揭示想象界奥秘的一个缺口。
1.1 主体的一场自我狂欢
拉康所述的想象界关注的是主体与“自恋式”认同、主体与现实的想象性认同之间的关系。“想象界首先指的是主体与其构成性认同之间的关系,其次指的是主体与现实之间的关系”,而这种两种关系都伴随着主体的想象性完整与实际上的破碎。影片一开始便是美美的一段自述:“从我13岁开始,我就一直在做我喜欢的事情,每一天,每一刻,都是我说了算。”在美美关于自我的认识中,她是可以独立自主的,是可以掌控自己生活的完美个体,如有着优异的成绩、志趣相投的朋友、关怀备至的母亲、值得热爱的偶像等,这些都是美美形成的关于自我的“真实形象”,是她眼中的自己。在自己创造的世界中,美美对自我充满了“自恋式”的喜爱与愉悦,在选择性忽略现实的情况下,美美对自己的生活状态是认同的,并且认为那就是真实自我。
然而,这个理想的自我形象却是脆弱的,不堪一击的,是一场废墟之上的狂欢舞会,随时都有坍塌的可能性。现实中的美美还只是一名初中生,身边同学对她的评价是争强好胜、麻烦精,是被妈妈同化的一类人,且需要在父母的照顾下生存,没办法去想去的音乐会,也无法反抗来自母亲的全方位监管。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终究会激发出意想不到的矛盾。影片中,美美变成了一头红熊猫,影片的这一情节设计旨在通过外在具象化的形式将美美真实的、一直被囚困着的、不断挣扎的自我展现出来,说明她是有野心的,也像同龄孩子一样热爱一些疯狂事物,有着鲜活的性格,而不是和母亲一样,只能过着循规蹈矩的生活。
1.2 “他者”的虚幻魅影
美美想象中的自我与现实中的自我有着很大的不同,或者说有巨大的落差。这就涉及主体的误认与异化的问题。主体第一次在镜像中看到自己的形象时,会反复试探,直至确认那完整的影像就是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主体也确认了自己与他人、与外界环境之间的关系。可是,镜中的形象只是自我形象的投射,更是对他者形象的一种理想化想象,于是从那一刻起,主体在对自我与他者进行识别和认知时就产生了误认。美美想象中完美的自己是在他者视角的审视下形成的,与其说那是美美自我的理想形象,不如说是他人对于美美的期待式认同。她是母亲眼中的乖巧女儿,是老师眼中的聪明学生,是朋友眼中的活泼伙伴,是同学眼中麻烦的一员,这些来自众多外界的想象就构成了美美眼中的自己。
于是,我们看到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那道裂缝:与完整的身体形象相对应的是破碎的躯体,与“理想我”相对应的是他者的建构,与美好的外界环境相对应的是无处不在的争吵与矛盾[2]84。美美正是在这种无处不在的差异与误认中对自我进行身份建构的,这就注定了悲剧的发生,因为她可以是很多“他者”,却永远不是“自己”。美美那不断被压抑着的、内心深处的欲望,更是推动着一场闹剧的到来。
2 象征界:“我”与社会关系的互动
象征界是先于主体存在的,主体只有认同象征界所代表的秩序,进入语言的秩序内,才能获得主体性的身份,这就是象征界的认同。同时,获得主体身份时也意味着欲望的象征化,是欲望在象征界的登记注册[2]84。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欲望就是可以满足的,正是因为欲望的象征化才意味着对原始主体的抹杀,使欲望永久性成为他者的欲望。关于他者的欲望、欲望与他者之间的关系,就成为困扰主体一生的难题。
2.1 母亲与朋友:“小他者”的压抑与认可
“在拉康的逻辑中,主体的象征性认同的完成有赖于俄狄浦斯情结的解决,而这一解决的关键就在于主体对属于象征秩序和大他者场域的父亲功能、父法或者说‘父之名’的确认,并且首要的是对父法的禁令即父亲的‘不’的确认。”[1]401-411可是,也正是因为如此,主体在成为一个社会性存在的同时,也成为一个“被阉割”的主体,一个欲望永远被埋葬和压抑的主体,只能屈从于父法的逻辑之下。
美美生活在一个“虎妈猫爸”式的家庭中,在这一家庭中,母亲俨然扮演着一个“父之名”的角色[3]。在看似全方位的关怀中,母亲所代表的隐形压迫其实是一场对美美主体性的“谋杀”。表面上看,美美是在母亲无微不至的关怀中成长起来的,她接受着母亲对她的赞美,如“今天是优秀学生,明天就会是联合国秘书长”。她成为母亲要求下的一个“完美的形象”,却被迫一直压抑着内心真实的想法。在母亲那般令人窒息的“保护”下,美美受到了同学和朋友的嘲笑,加之对外形的担忧,她再一次感受到了认同感的消失,由此陷入对自我身份的怀疑和无尽的自责中。
在这时,“小他者”——来自朋友的支持与理解,给予了美美心底渴望的认同与关爱。在“小他者”身上,美美再次看到了自我理想形象在外部世界的投射。对于自己的红熊猫形象,母亲的反应让美美一度怀疑自我,然而这份悲伤在朋友这里得到了化解。在她的三个朋友眼中,红熊猫是可爱的,是酷酷的。正是在朋友的认可下,美美克服了一次又一次情绪变化的测试,再一次获得了对自己身体的掌控权。得到妈妈的许可回到学校后,美美发现身边的同学并不是像母亲那样排斥自己,不敢看自己,而是眼中亮晶晶地看着她,想要和她接触,这种截然不同的反应,冲抵了美美内心的那份不自信与担忧。
2.2 宗祠与社会:“大他者”的制约与失衡
拉康认为,“象征就是契约,它们首先是契约的能指,然后才构成所指”,“象征界实际就是一个法的世界,一个契约的世界”,“进一步地说,人的世界是因为这种契约而可能的,人能够言谈,不是因为他能使用象征,而首先是因为象征使其成为了人”[1]420-431。影片中通过父亲和母亲的描述交代了红熊猫的来历:在古代家族与红熊猫签订的一份契约,获得了红熊猫的力量才生存了下来。正是这一份契约,为这个家族带来了足以维系生命的力量,获得了在象征世界中的身份。
可是,在母亲甚至是家族的长辈看来,这份契约背后所代表的力量已经由最初的祝福变成一份诅咒,忘记了正是这份与红熊猫的约定才使得家族能够生存发展。或许可以说,正是因为他们对这一契约的误认才促成了美美现在的反叛,才造成了其对自我的不认同。这种误认造成的后果,可以从影片后期美美妈妈的情绪不受控以及庞大的红熊猫体积看出。美美的妈妈在几十年的外界的束缚下,在长期得不到自己母亲认可的情况下,压抑在心底的欲望是无比可怕的,所造成的破坏也是惊人的。
3 实在界:欲望的满足与崩坏
实在界,是拉康三界说中最难以理解和定义的,它不像是想象界有具体的语言描述,也不似象征界可以有特征去把握,实在界的难以理解之处就是在于它的悖论性。实在界在本质上就是一个“无”,其表达的意义不是不存在,而是不可知,它永远生活在彼岸[2]84。在拉康的关于三界的很多描述图中,实在界常常隐藏在阴影下,这就表明了它的不可抵达性和不可能性。作为一个“无”中之有的存在,实在界总是会在人们无意识的言语行动中现身,以不完整的样貌让我们一直去追寻。于是,个体会在实在界的不断驱使下开始对自我身份的不断验证,对内心欲望的无限追逐[4]。
“原初的东西实际就是一种性驱力、一种原欲、一种原始欲望,可它通常是受到压抑的、被禁止的,无法直接表现自身,因而只能寻求以置换和凝缩的方式在无意识的表象中间接地获得呈现,人类社会的原初大法就是为此而确立的。”[1]440-450影片中,红熊猫形象总是在情绪失去控制时出现。这份驱使变形的力量便是埋藏在美美及其家族心中的那份被压抑、被禁止的“无”。只不过影片借红熊猫的外形将这份“无”变成了现实世界的“有”,让观众可以直观地感受到这份力量的巨大与可怕。美美变成了红熊猫,她期望通过这份力量来实现自己的愿望:赚取音乐会的门票钱,得到周围同学及朋友的喜爱,挣脱母亲的束缚。这份力量不断推动着美美行动,去满足内心的欲望,但是由于欲望的无法到达,美美最终只能坠入欲望的深渊,这份力量也就转变成了摧毁现实的武器。美美把家、学校、聚会、音乐会都搞得一团糟,这便是只顾满足自我欲望所带来的后果。
另外,正是欲望的外显使我们看到了美美内心深处一直渴望的东西,那是她真实的样子:喜欢追星,喜欢摇滚音乐,喜欢和朋友一起嬉戏玩耍。她有着这个年龄段孩子的天性,我们也看到了她内心的呐喊:宗祠职务、考试成绩、小提琴、踢踏舞,我们一直表现得很好,如果他们还是不信任我们,哪还有什么意义呢?在母亲的教导下,美美一直规规矩矩地生活,坚守着家族的责任,仿佛一台机器,并且视自己内心的欲望如洪水猛兽,只能藏在床底,因为一旦被发现就会被摧毁。这是现实世界对主体的“阉割”,使得主体一直是残缺的,是胆小懦弱、害怕现实的。而主体的这种残缺是父母以爱的名义造成的。影片中,美美的妈妈以保护美美的名义将她囚困在屋子中,禁止与外界人接触,可悲却又现实。
4 结语
《青春变形记》的导演石之予从小生活在重庆,后随父母移民到多伦多。作为一名华人导演,石之予的影视作品中处处都充满着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描绘,使得更多人对中华文化产生认同。另外,石之予还站在全球化的视角对个体认同的问题加以考量,如《青春变形记》的主人公生活在多元化的文化中,她所面临的矛盾与冲突更是多方面的[5]。美美的爸爸在驱逐红熊猫的仪式前说了一段话:“重点不在于推开不好的东西,而是给它腾出空间,和它共存。”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头“野兽”,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这并不可怕。面对自己的欲望时,我们要正确看待其负面影响,但也要认识到它可以成为一股力量,是推动自己实现目标的力量,这样就可以获得内心与外界的短暂平和。
——拉康对《孟子》的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