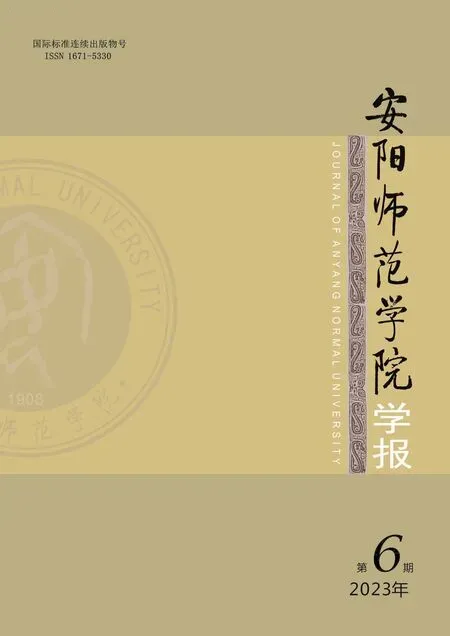论小剧场戏曲跨文化改编的文学特征
吕姵瑾
(云南艺术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
小剧场戏曲这一概念源承于小剧场话剧,小剧场戏曲在传统戏曲的基础上进行文本的改编,表演的创新,以及对于舞美的重构,使传统戏曲在传承经典的同时,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小剧场戏曲也并不是狭义上的在“小”的空间内上演的戏曲,而是强调内在蕴含的先锋性、实验性和现代性。1991年的《秦琼遇渊》是大陆最早将小剧场理念融入戏曲的剧目,改编自汉剧《秦琼表功》,由奎生先生编剧,京剧演员周龙导演、演出。小剧场戏曲发展迄今已走过三十余载,经过世纪交替时期的起步与探索,目前已经成为当代戏曲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成为业内关注的热门现象和年轻人更加喜闻乐见的戏曲形式。
“跨文化简单理解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国家之间文化艺术的相互交流、学习和借鉴。中国戏曲在与西方多个不同文化背景国家的交流中,既有中国对西方戏剧发展的影响,也有西方戏剧对中国文化的渗入。”[1]因而,将国外知名戏剧文学作品改编为小剧场戏曲形式进行演出,就是跨文化改编的小剧场戏曲。这类作品在小剧场戏曲先锋性、现代性、实验性的基础上,又兼收国外作品的故事内核、精神内旨以及戏剧流派的特点,在当代的语境中做出在地化,剧种化的解构、融合、改编,为戏曲的全球化、年轻化发展带来更多的可能性。纵观小剧场戏曲的跨文化改编历程,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使得其产生出独有的特色。
一、文本交融:思想的包容性
“不同的文化背景具有审美的差异性,精神内旨的差异性,而跨文化改编则需要在两种极具差异的作品之中寻求契合点,这无疑是跨文化改编的重要前提。”[2]剧作的剧本是整个戏剧创作过程中的起点,因此,小剧场戏曲的跨文化改编将文本的改编作为重要阵点。戏曲作为中国千年传承的戏剧门类,在接纳外来文化时展现出极强的包容性,在对外来文艺作品的接纳过程中,展现出两种不同的特点。
在对原作的改编创作中,一类是重新诠释题旨,即保留其原作的精神内核和大致情节,对故事进行中国化的改编,以及注入中国特有的价值观、当代精神或是“中式幽默”,使其焕发出新的生机。比如小剧场京剧《小吏之死》,此剧改编自契诃夫小说《一个文官的死》。原作讲述了在剧场看戏时,一个小公务员不小心在将军背后打了一个喷嚏,因为过分害怕冒犯将军,对将军进行了不分场合的七次道歉,最后彻底激怒将军,吓得一命呜呼。契诃夫的原著是一贯于契诃夫风格的,在平静、温和的生活下的暗讽,因此小公务员的悲剧命运在表面上表现的并不深刻,以至像小公务员自身的错误行为导致的悲剧发生,作品中的批判和讽刺意味并不很强烈。戏曲《小吏之死》的改编则使原著中的讽刺精神变得辛辣,强调用强烈的夸张形式,浓墨重彩的风格,进行鲜明的讽刺。《小吏之死》保留了原著的大致情节,将其改编成了一出独角戏,大致讲述了明朝落第秀才余丹心受到巡抚赏识,被提拔为九品典史,但在一次宴会上不小心把口水喷在巡抚大人脸上,希望求得大人原谅,但是弄巧成拙,最终自己吓死自己。在文本的改编上,不仅将时空、人物、故事都合情合理挪到中国古代,还将原著中的七次不同时空的道歉转化为一次道歉,更符合传统戏曲的时空规律,同时以丑角作为主角,结合其故事背景,又增添了黑色幽默的色彩。
一类是抛弃原著本身的题旨,融入中国式的人生哲思,对原著进行根本性的改写,使原著精神完成一场中国化的转化。 实验京剧《王者俄狄》便是这样的作品,本剧改编自古希腊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俄狄浦斯王》改编自古希腊的神话故事,是一部命运悲剧,也是世界剧坛常演常新的优秀作品。讲述了忒拜国王子俄狄浦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杀父娶母,导致国家灾难频发,最后在先知的揭示中得知自己的命运,刺瞎自己的双眼。这样宿命式的悲剧展现了古希腊悲剧中人与命运的冲突,在冲突中再现俄狄浦斯坚韧的精神,以及在宿命面前的抗争与无力。改编京剧《王者俄狄》在文本的改编上,抛弃了原剧顺序的写作手法,转而使用倒叙,将忒拜城瘟疫肆虐的情景作为整部戏的开端,只选取俄狄王得知真相并走向自己命定悲剧的这一段进行整部剧的铺陈。瘟疫横行、民不聊生的城邦迫使青年俄狄必须要肩负起君王的责任,但他越为此努力就越接近残酷的真相,诠释了君王在民族的兴亡和自身命运面前做出的大义选择。同时,老国王成为了生活在远古中国的一个少年天子,拥有远大的抱负和少年的家国情怀。古希腊戏剧本身的时空是多变且灵活的,改编剧《王者俄狄》也充分将这一点与中国戏曲中对于时空的处理进行了融合,充分运用了戏曲移步换景、虚拟性等美学特点,在这样的改编中,将原著本身的寓意进行了中国化的升华,改变了原本的个人与命运抗争的命运悲剧,融入了中国式的人生哲思,中国人家国天下的情怀。在《王者俄狄》中俄狄王是一个中国传统的明君形象,于江山社稷、家国百姓有责任感,所以他在得知他的死能够换取百姓平安时,坦然的走向灭亡的宿命。从原本的命运悲剧,变成胸怀家国抱负的天子陨落,在吸取古希腊戏剧哲学思辨的基础上进行改写,探寻了一条古希腊戏剧中国化改编的新路径。
二、文本转向:叙事视角的转化
小剧场戏曲的跨文化改编进程中,除了将原著思想在中国进行了在地化的诠释之外,还大胆的转换叙事的视角,把叙事视野聚焦于主人公之外的人物上,以主角之外的人物作为叙事的主要视角,注入中华文化和当代中国精神,展开故事的铺陈。《麦克白》是剧坛常演常新的作品,原剧中的主角为麦克白,是国王的表弟,麦克白平叛归来遇到三个女巫,声称他为未来的国王,麦克白与夫人受到女巫的蛊惑,弑君上位,最后因为过于残暴,众叛亲离,麦克白被削首而亡,夫人也疯癫死亡。在原作《麦克白》中,麦克白夫人一直是贪婪、恶毒、残忍的形象,在原剧中戏份不多,但却是麦克白弑君篡位行为的最早煽动者。在小剧场戏曲的跨文化改编中,分别出现了不同的剧目都对其形象进行了颠覆,昆剧《夫的人》,实验川剧《马克白夫人》以及滇剧《马克白夫人》都颠覆了原本的叙事视角,把麦克白夫人当作主角,深入剖析了麦克白夫人的心理和情感变化。
实验川剧《马克白夫人》于1999年首演,本剧对原著进行了叙事视角的颠覆,将麦克白夫人作为主角,采用表现主义的表现方法,展现麦克白夫人的心理,该剧刨除了麦克白夫人之外其他所有的人物,直接从高潮处切入,基本以背景形式出现,甚至麦克白的戏份都很少,只在关键的情节出现,本剧仅麦克白夫人有道白和唱段,演出形式近乎独角戏。对麦克白夫人形象进行了在地化的诠释,她既冷酷无情、充满野心,但也会流露出中国传统夫妻观中妻子对丈夫的温情、顺从、以及忠诚;她也有善良的本性,但却被欲望所吞噬,她是欲望的殉道者,是悲剧的作俑者。本剧将原作改编成近乎独角戏的形式,使得戏曲本身空间灵活的特性能够得到发挥;同时在保留原作麦克白夫人形象的前提下,将叙事重心设定为麦克白夫人,这样的颠覆与重置,颇具当代性与实验性。在2020年的小剧场戏曲艺术节中,滇剧版《马克白夫人》成功入围,此剧移植于实验川剧《马克白夫人》,跨越20年,依旧有经久不衰的舞台魅力。
2015年诞生的小剧场昆剧《夫的人》,同样将叙事视角聚焦于麦克白夫人,本剧以麦克白夫人临终前的梦境作为主要叙事线索,闪速回顾她的一生,但与实验川剧《马克白夫人》不同的是,它赋予了《麦克白》新的精神内核。剧名《夫的人》即为“夫君的人”。对此,余青峰编剧解释说,“我们希望以剧名,点出一个东西方共通的话题———女人是附属品吗?”。[3]一直以来,“恶”是麦克白夫人展现给大众的形象,但在《夫的人》中,麦克白夫人是以“恶”这一极端的方式来成就麦克白的梦想,她所做的一切并非出于个人对权力的渴望,而是出于爱——“但求不必四海征战,夫妻不离不弃”,在剧中她还有一段重复的话“我是夫人,二八年华,嫁入夫家。我的夫,骁勇善战,气宇轩昂,他,乃盖世英雄也! ”每次出现这段话,麦克白夫人的情绪也出现变化,崇拜,失望,怀疑,从一开始的崇拜,是认为自己的丈夫理应成为国王;而后的失望,是因为麦克白成为国王后的冷漠与残酷与她一开始的期望大相径庭;进而便是失望、怀疑,直至麦克白死去。这样的“重复”具有力量,是主人公的精神写照,也是主人公作为女性悲剧命运的体现。看似是麦克白夫人在幻想中面对夫君每一次的心理变化,实则是她根本不会爱自己,她的爱是通过爱别人实现的,因此她崇拜、失望、恼怒,她看似“恶”,却很可怜,在当时社会的伦理束缚中,女性的自我价值被压抑与消解了。这也是《夫的人》所想探讨的问题,从人性的叩问到女性价值的思索,这是具有普世意义的探讨,中西方所共同的问题,女性应当是何种地位,女性如何获得幸福,女性如何摆脱男权视角的凝视,如何正视自己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夫的人》通过叙事视角的转化,探讨女性问题,赋予剧作新的精神内核,具有强烈的当代精神和现代色彩。
三、文化显影:跨文化改编的困境
首先,不同文化、文体的交融,异质文化的介入势必会导致戏曲本身假定性的实现受到阻碍,文本在此过程中产生形变,势必也会影响剧作本身的文学性体现,影响由假定性构成的戏曲舞台表演时空。以《小吏之死》为例,不可否认的是,它在保留原作精神内旨的同时,进行在地化改编,添加了中式黑色幽默的成分,体现了小剧场戏曲在跨文化改变的过程中,展现出的思想上的包容性。但不同文体的交融,导致戏曲假定性实现起来颇为困难的问题也在此剧中有所体现,原作中的第三人称转述,在本剧中使用了独白自述,原作是小说,以第三人称的叙述视角描绘出一个辛辣讽刺的社会图景,本剧将这些第三人称描绘转变为男主伊凡的自述,进而完成整个戏的勾连。无论是中国戏曲还是西方戏剧,假定性都使得在舞台上时空转换成为可能,如果按部就班的使演出时空等同于现实时空,那故事会变得冗长乏味,《小吏之死》的困境在于,需要依托假定性来推进故事的进展,但由于使用了大量的独白,呈现出一种如同布莱希特间离效果一样的破碎感,演员在舞台上既需要直抒胸臆,一人分饰多角,又要保证故事的推进,因此需要通过独白的形式,以剧中人物的精神世界的转化取代理性的叙述。原作《小公务员之死》又是一部叙事性极强的作品,需要一定的情节构造,需要舞台时空有所转换,至此,由于想要兼顾叙事性和写意性的《小吏之死》中的逻辑世界变得混乱,剧作试图由假定性构建起的舞台时空与文本的叙事空间脱节,造成观众观看的“破碎”之感,剧情破碎、随机、反复、跳跃,这正是由于文本在改编过程中过于粗糙导致的。
其二,跨文化的创作不应当停留于显性文化层面的交织和拼贴,而应当是东西方美学内部灵魂的交流和互通。以昆剧《椅子》为例,改编自法国剧作家尤奈斯库的荒诞派戏剧《椅子》,原作讲述了荒岛上生活着两个老人,一个老汉和他的妻子,两人一个九十五岁,一个九十四岁,他们邀请了一些贵宾来岛上听他们两人漫长生活的智慧结晶,但他们不会演讲,于是请了一个演说家,观众看不到这些贵宾,只看到两个老人嘴里不停说着客套的话,在舞台上堆满椅子,直到两人行走困难,演说家来了,在黑板上写下一些没有意义的字母,看不见的观众无人回应,甚至有稀稀落落的嘲笑声,演说家灰溜溜的退场。昆剧《椅子》讲述了九旬夫妇王生和茜娘在古代无名小岛上对着一堆椅子追忆一生,随后相顾无言,相继跳海。在演出中,对人物,地点以及口语表达做了在地性处理,使之在中国本土更加“地道”,也保留了一些跨文化的痕迹,比如演出中一开始出现的台词“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对于孤岛这一环境的表述相当于对原作中信息的重叠,也给观众带来一种延展的意向,让本剧在观众心中有了不错的“第一印象”。但本剧在跨文化的改写中,在东西方美学内部灵魂的交流互通问题上并未下足功夫。约瑟夫·奇阿里曾在 《当代戏剧的界标》中将尤奈斯库的创作归纳为一种“幻想性”,并且是“可确定它着意于什么”的作品[4]——尤奈斯库的创作看似是无逻辑的、反复的、枯燥的表征,实则是具有清晰指向性的,这些杂乱与破碎的表征,如同量变到质变的积累,最后堆砌起尤奈斯库精神里庞大且破碎的世界观。尤奈斯库是荒诞派戏剧的代表人物,“荒诞派最富于革命性的是它对待语言的态度”[5],抛弃以往以对话推进剧情进展的语言体系,进而遣散戏剧情节,以达到反戏剧的目的。在昆剧《椅子》中,导演没有沿用原作中这些无意义的对话,而是将荒诞派戏剧文本中的意向符号作为戏曲念白中的点缀。因此,昆剧《椅子》只是将跨文化作为了一个噱头,而并未真正在剧作中展现出跨文化应有的文化交融。在《椅子》中,导演还使用了“竹篮打水”这一意象帮助观众理解尤奈斯库所想表达的抽象概念,但这样“竹篮打水”的意向符号落地,虽然使剧作更具戏曲的韵味,但大大缩减了荒诞派创作本身应有的意义和深度,使荒诞这一概念沦为空洞的形式。在昆剧《椅子》的演出中,也打破了尤奈斯库剧作中“量变到质变”积累的过程,原作的内旨基本被舍弃,文本内容也进行改动,原作只为昆剧《椅子》提供了一个外壳,仅仅起到丰富观感的作用,这样的跨文化改编,看似是两种文化的碰撞交融,但实则是文本的表面拼贴,东西方文化在交融的过程中是失衡的。昆剧《椅子》的本质仍然是戏曲本体,尤奈斯库的原著在这样的改编中是次要的,边缘化的。
四、总结
东方戏曲和西方戏剧存在一种共通的创作模式——在舞台表达方式中呈现假定性。其虽然有着不同的表现方式,但这种不同假定性的交融与转化是戏曲想要跨越文化差异、展现出其包容并济文化特征的重要方式。跨文化创作语境是如今戏曲改编避不开的话题,在跨文化的语境中,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原本稳定的关系被打破,两方关系必须在这个进程中发生交融与贯通的形变。如今的戏曲跨文化改编,便面临着这样的困境——有改编之意识,却无法做到将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合理、均衡的融合。这是跨文化小剧场戏曲创作中的创作困境,是目前亟待思考解决的问题。
——他者形象的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