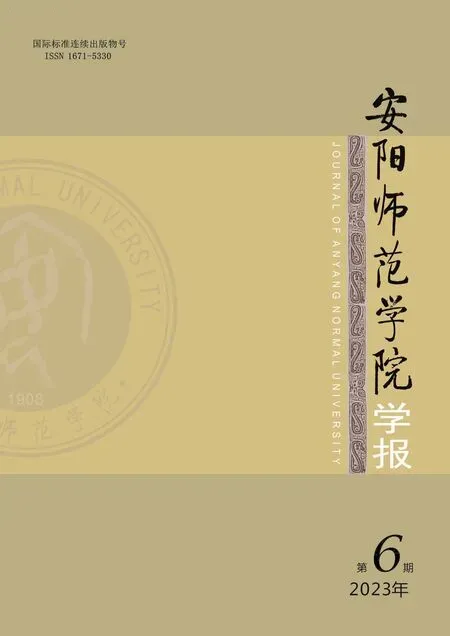“气氛”至“美”的在场探赜
代 敏,宛小平
(安徽大学 哲学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9)
“气氛”在经验中作为普遍词出现在不同场域,客观“存在”似毋庸置疑,实则其根源性解析与何以存在仍需佐证。气氛作为介于主客之间的被定调的空间在场,其在场性即存在则为关键性因素,而对于在场的研究却是易被忽视的。作为新现象学美学家波默(Gernot Böhme)对于在场(存在)是如何发展出其新美学思想的?在其气氛美学中“在场”固然重要,尤其是在气氛转向“美的气氛”中扮演何种“角色”?则仍需深入研究。
一、“气氛”与“美”
(一)“气氛”
气氛(1)“Atmosphäre”一词德文释义有:大气层,大气圈;(人际)气氛,氛围;环境;大气压力(压力单位),贾红雨与杨震等研究者皆将其译为“气氛”。中文中亦有“气氛”一词,《说文·气部》:“氛,祥气也。”段玉裁注:“谓吉凶先见之气统言则祥、氛二字皆兼吉凶,析言则祥吉氛凶耳。许意是统言。”直至汉,刘向《说苑·辨物》:“登灵台以望气氛。”气氛皆为:显示吉凶的云气。(Atmosphäre)是否客观存在?波默指出:“‘气氛’概念之所以模糊不定,其根本原因在于传统的存在论(基于存在物的规定性),而从此视角来看气氛不存在,但事实并非如此。”在《通往一种生态美学》[1]一书中,波默最早提出“气氛”这一概念,但此时气氛更多作为一种气候与生态环境意义上的存在,并不具有美学意义。波默认为:“这个‘与’即新美学涉及的环境质量与人的处境感受‘之间’的关系,介于两者之间通过它而被相互关联起来的东西就是气氛。”[2](P11)作为一种无意识下的客观联系物将客观与主观身体在场性感受共同显现。介于“之间”的气氛:“气氛是一种‘中间’(in-between),由于主体和客体(物质的,但也是社会的和象征的)共同存在而成为可能。”[3](P121)具有“共同存在”的气氛因“间性”而超主观(extra-subjective)存在。
中国关于“气氛”的研究,表现于对于艺术作品“意境”或“气韵”的研究。法国汉学家、哲学家朱利安 (F·Jullien)认为:“中国山水画中的云雾不是对自然的模仿再现,也不是具象(figurative)的写实,而是为了营造一种‘半晴半阴’‘若有若无’的‘之间’(entre)的氛围。”[4]显而易见,在研究意境与气氛存在问题研究时,学者都关注了“间性”问题。在面临艺术美与特殊的情感体验时都注意到了在场性的问题,所研究的问题也始终离不开存在问题。
(二) “美”
美,在美学学科的创建者鲍姆嘉通看来是感性研究。休谟指出,美并非事物本身的属性,它只存在于观赏者的心里。黑格尔认为美是理性的感性显现同时将美放入艺术领域。此后美与艺术紧密挂钩,中国的宗白华则清楚的阐明美与艺术的关系即:美学是研究“美”的学问,艺术是创造“美”的技能。
朱光潜指出:“美是客观方面某些事物、性质和形状适合主观方面意识形态,可以交融在一起而成为一个完整形象的那种特质”[5],可见美作为具有“交融”特质,具有主客之间联系的“中介”作用。
作为“中介”(间性)的美是无法定义或根据传统的物的规定性来佐证存在的。在波默看来,“传统存在论实质上是一种物存在论,也就是说,这种存在论是在物—属性、实体—偶性这种模式之下来看待事物的。”[6]而气氛存在以间性存在,自我主体与非我主体;主体与客体物;此客体物与彼客体之间的二分,必将导致之间距离,而距离下的间性则为其存在佐证,此间性即:“在场”。 将“在场”引入艺术本体论研究并非是波默的独创。海德格尔指出:“存在者的存在被把握为‘在场’,这就是说存在者是就一定的时间样式即‘现在’而得到领会的。”[7](P30)海德格尔将存在者置身于时间样式中把握从而确定此在的优先地位。在其对于艺术作品的本源研究中将真理放置于存在理论中,解弊真理之真相,从而将“在场”(存在)置于本真之中,创造一个世界。
“间性”(中介)即气氛何以转化为“美”则离不开“情感”(生命力在场)。波默的气氛美学是在德国新现象学家史密茨(Hermann Schmitz)身体哲学的基础上建构的。史密茨的气氛是作为空间物以无边界为存在特质,是拥有感染力与情调的载体。但却将气氛流于神秘而飘忽不定。波默并不同于史密茨的神秘气氛表达。他认为:“气氛显然是通过人或物身体上的在场,也即通过空间来经验的。”[2](P19)气氛的必然在场与存在论的物质在场不同,而是一种现象的确定在场,气氛如光照亮处在在场的物,对具有感受质发挥映射从而觉察气氛。严肃的美的概念一旦成为客观现象时,就将美固定为某些属性上,而这些属性仅为美的属性的一部分。因而,波默将美理解为可以让此在感到幸福的东西,并将“生命力”置于在场。
二、“气氛”至“美”的在场营造
气氛作为物与主体之间的间性存在,必不能制造气氛,而只能制造在场条件以显现气氛,对于气氛条件营造者需设定气氛现象的显现条件。关于营造气氛,波默将其称为存在着一种 “审美性的工作”[8](P52)这个工作则是此在通过存在物的排列组合与在另一存在物(场域)中使得气氛这一存在物得以显现。
(一)光——“气氛核心要素”
光在波默的气氛营造中具有三重身份。其一,光本身即为气氛;其二,光营造出空间;其三,在整体气氛中起主导性作用。
波默将光作为气氛来处理,在自然经验中,自然物有赖于光的气氛制造,自然物在光的照射下获得了其独特气质与气氛。光作为一种在场气氛,体验光气氛就变成了首要。海德德尔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将“看”与“知道”的本质阐释为“解弊”(2)海德格尔认为:“知道意味着:已经看到(gesehen haben),而这是在‘看’的广义上说的,意思就是:对在场者之为这样一个在场者的觉知(vernehmen)。对希腊思想来说,知道的本质在于àλθεια亦即存在者之解蔽。”。看光即经验光,第一,传统思维将光视为不可见之物,而肯定光的确定在场。第二,在光通过媒介达到确定在场的显现时,即光变为可见物,当光照亮或点亮诸在场物时,对于光的体验便转移为某个发亮的在场物上。第三,发光这一属性下,又引出了另一问题即光源。第四,对于光的知觉经验并非是一种意向性的知觉在场,在光照亮下的在场物被人们知觉到时,光则与在场物所分离,成为独立的纯粹的光的现象。波默给予光以上帝视角,在光的照耀下,精神性的东西不需物的转换就成了感性的可知觉。看光作为一个纯粹现象所带来的明亮经验的在场感受,便显现出来。
光以明亮在时间上有限制,而在空间上则限制空间,照亮空间,使得空间得以显现,或者说,明亮创造了空间,主体对于明亮的感知,则是为一种知觉的空间在场。“在太阳出现之前,在我们或许因此而把明亮性回溯到太阳在场之前,这种变亮就已经开始。”[2](P137)光的显现问题,将先验性处理,这里做出预设,光的现象首先以明亮所显现,而经验明亮则是先于在场物的显现,看光则完美回归到明亮之中,先于在场物所感知。因而,光的客观在场,使得世界处在光亮的显现之中并使在场物显现自身。
光是气氛营造的典范且为具有主导性的气氛,在创造某种气氛时,光的介入将情调展现无疑。认为光是气氛营造者。对于光的生活经验,将光与亮赋予在场诸物,场景或是空间。这对于舞台场布而言,光的晕染格外引人注目。波默并不认可歌德的光学理论,明确指出:光在制造气氛中作为经验性的笼罩存在。哥特式教堂的光学建筑学也是建立在这一点之上的,即空中的尘埃使光束成为可见的。[2](P121)当主体知觉在场时,太阳与火等带来明亮感的物的经验,主体不需去经验,它自然在场。物经验光,沉浸其中,显现自身于定性定调的光中。
(二)空间 ——“气氛情感定调”
波默的空间理论是建构在对于光学研究新视角下的重构展开,认为知觉的“第一性”或“优先在场性”即为空间。因而波默认为空间成为艺术的关键有三点。一为优先性(在场);二为身体在场性;三为情感性。
具备气氛仅是在场物所呈现的方式,具有优先性(在场),这种第一性最先被知觉的东西即“空间”。气氛在场物的属性在光的显现下得以实现,空间整体性在光的显现下获得一种确定的定调。主体所直接感受的东西只存在于知觉的第二步,必须跨越直觉气氛(第一步)即史密茨的“身体察觉”:这个知觉由散发情调特征的环境与我分享的情调察觉这两部分构成,显然这是一种可察觉的在场。
波默认为营造空间的在场气氛具有“身体在场性”与“情感性”。尤其在营造现代摄影与建筑气氛时,将气氛转化为艺术,从而带来审美的在场。波默认为现代摄影成为艺术的原因在于去表达不可去表达之物,而这个不可表达之物则是空间,是身体性在场的空间。“‘在—世—存在’基于人类的身体性。身体性在场是空间的形成。空间意味着‘我在这里’。空间性是对人类身体性在场的确认。”[9]。此时,空间并非是具体可感之物,或者说是为背景式的存在,而是对象在其中达到展现的活动空间。对于空间的经验理论来说,空间是整体的,处在空间之中将会被完全包围,这种空间经验不是通过间接性的相片来表现,而是通过流动的主体在场经验来获得。波默指出,空间实际上是无法拍摄的,“原因不仅在于摄影是两维的,也在于人们在图片中看到的是物、房屋、也即是说,看到的仅只是空间的各种界限或者纳入空间的东西,而不是空间本身。”[2](P112)空间物的组合在与周边空间物之间关系中设定了某个地方的在场。作为设定在场的建筑,建筑物在光的作用下是如何展现的?此时空间经验便是可察觉的在场,这里的空间经验即人在一定空间下或者与周围空间中所形成的经验。“在这个空间中生活的特定自然存在是共情的。相反,这是一种从自然本身开始表达自己的生命:一种生命的日子、形式和历史赋予空间的存在以意义和意义。”[3](P39)特定的生命与自然的“共情”所营造出独特情调的空间则是营造空间艺术的关键。更是“活”的空间的“情感性”表达。
身体的在场作为基础在场为情感的体察在场提供可能性。例如,当我们感受到紧张的气氛时,作为身体性在场,紧张感环绕在空间之中,这里的紧张气氛经验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引回至紧张的在场。波默认为这种感受质是人们从一定的气氛出发而可以在对象身上发现的对象的准客观性属性。情感在场所带来的处境感受差异则是受空间气氛所影响。处境感受作为一种察觉,被我们所处的空间的各种特质所改变。[2](P155)身体性的声音营造在场性的气氛规定着身体性的体察在场,客观要求着我们以具有差异的方式在空间中在场。
光的显现使空间在场,空间并非片段性的在场而是作为整体性的在场,在场物处在空间之中,并通过光显现自身,使得在场物的属性得以展现,空间的整体为气氛效果定调。“艺术首先形成于特定存在场域,然后通过艺术方式和周围世界形成各种各样的联系,从而彰显艺术的魅力。”[10]“把气氛变成被感知者和感知者之间的一种有形的(无意的)桥梁,使我们能够维护气氛的无意性。”[3](P139)艺术作品的审美特征在此“在场性”之中显现出本源之美。主体的身体参与在场与情感等知觉在场则为气氛是否展现提供了可能性,当营造气氛的主体的想象在场与其他主体的(在场主体)感受一致或相似时,营造某种气氛的目的便达到了,更是气氛效果的好的显现。
三、美的气氛迈入显现
(一)迈入显现的发生机制:在场
气氛的显现亦是显现自身,显现以其动态性还原现象本身,此时则表明了气氛显现的客观基础,主体在场同时迈入显现,营造气氛之物的在场与迈入显现,气氛本身的居间(在场)显现的最终目的即美的气氛迈入显现。
波默指出:有意识的条件能力的在场则是研究气氛显现的发生学通道。他认为:每一种气筑现实性都带有某种不可任意支配的性质。“气氛才能使显现,不能被设想为因果性的事件,而是必须要被视为关于显现条件的知识以及有意识地来达到这些条件的能力”。[2](P275)这里波默强调两点,一是气氛(自在)与其显现(表现、外在等)之间并非因果性的事件,即气氛(自在)在场域中与其显现存在不对等性或改变。二是气氛的显现与显现条件以及带有意识地达到条件的能力有关,如达到条件的能力越强,那么气氛的自在性与显现之间的差异越小,气氛的显现程度越高。
波默认为显现并未脱离某物,而是某物的自我展现。人的身体参与,作为经验者的在场尤其重要。“超越性的意识可以构造一切 ,却不可能假设自身的不在场。”[11]“‘我们首先不是‘活着’,然后才得到一个我们称之为 ‘身体’的维持我们的生活的装置,而是某个活着的身体’所以‘每一种感觉都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协调的一种体现,一种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体现的情绪发现’。”[3](P137)活着的身体的发现则是对于感觉协调与情绪发现的基础,此时主体则是人的主体显现,正是因为主体的在场显现,才使得气氛显现效果最大化。
(二)美与美的显现
波默认为气氛是短暂的,对于气氛的划分参见其《美与其他气氛》[12],气氛暂时分为五类,气氛并非全部为美,对此波默对美下了定义“美并非美的对象所具有的某种性质,而是一种气氛,而且是一种让我们为之倾倒,可以提高自己的生命情感的明确在场的气氛”[13]由此,美的气氛被理解为“明确在场的气氛”且美的气氛与提高生命的情感结合一起。
生命情感明确在场的气氛之美如何显现?“因为我们自身就是转瞬即逝的东西,所以我们遇见的是诸显现那一闪之中的美者——诸显现对我们保证了我们的此在。美就是为我们带来此存在这种幸福的东西。”[2](P290)这诚然将美置于存在之中。“承载意义的艺术作品的显象,其基础是各种艺术质料——‘石头、木材、青铜、颜料、语言、音调’的‘显现’,这就造成了一种威胁,使所有的意义都有可能消失。”[14](P22)这里的“冲突”与“威胁”无疑都对美丽的存在造成“危险”。为了解决潜在的“内在危险”,波默以合理的“自恋”为挽救美存在的方式。主体的显现与美的显现密切关联,而美的实存化即在场(实在)则可以通过“操心结构”来阐述,海德格尔认为此在在世的本质则是操心。美是先行于自身的已经在气氛或世界之中的作为寓于气氛与生命提升的存在。过度的意图则像是做作的“恶心”,从萨特的恶心(3)萨特小说《恶心》的一段话,我们可能更加理解波默的美与生命力的确定在场。即:“第三天,……但是我害怕将要发生的事情,将制服我的东西,而且它要把我拖到哪里去呢?难道我将又得外出,又得把我的研究工作,我的书都搁下来吗?我将在几个月以后,几年以后,疲惫不堪地、绝望地在新的毁灭当中醒过来吗?我很想在时候尚未太晚之前看清楚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去理解波默的美与生命力的确定在场。这里的“我”接连发问俨然成为对于被物化了的身体的情感上的反应,具有害怕,疲惫等恶心情感,同样自恋也是在解决“刻意”与“过度意图”,而美则是自然的生命力提升的气氛,对比之下更具有生机与自然的审美体验,此刻气氛不再是其他情感,而是转换为提升主体生命力的情感,气氛则以在场为美提供了空间与情感,使气氛美迈入显现。
四、结语
波默的气氛美学似乎有着某种矛盾,他一方面强调气氛的客观性即可以独立于人而作为整体性的空间在场或影响渲染着主体,另一方面又强调主体的营造在场气氛的关键作用。这看似矛盾的存在,实则打破了主体与客体的割裂,在气氛间性存在中在场主客实现了情感定调,是现象学美学的又一突破。气氛在场域中则迈入了显现。通过对于在场问题的透视,将“模糊”不清的“气氛”走向“确定”存在。气氛美学作为新现象学美学为当代艺术研究提供新思路,同时也为气氛何以为美提供了明确在场的实存化论证,气氛的生命力在场即为美的气氛显现,美的在场在主客交互的在场中显现。同时也为中国美学的“意境”研究打开了新的视角,新的思路。更为中西方艺术实践交流与互通提供新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