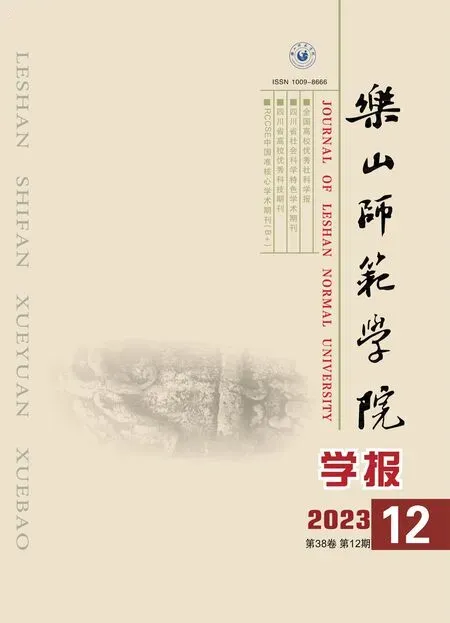论苏轼诗文对扬雄评价的二重性
徐 江
(四川师范大学 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四川 成都 610068)
苏轼诗文中有着较为丰富的涉及扬雄评价的论述,这对于理解苏轼思想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相关内容已经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如:陈冬根[1]探讨了王安石与苏轼二人在扬雄评价问题上一崇一抑的区别;徐江、赵义山[2]对《苏轼文集》中题名为《韩愈优于扬雄》一文的作者归属权进行了考辨,并认为此文之所以长期羼入苏轼文集中而未被发现,其原因之一便与苏轼好批评扬雄有关;喻世华[3]对苏轼诗文中相关的篇目进行了统计和研究,并揭示了苏轼在扬雄传播中的深远影响,等等。这些研究,从不同的角度丰富了“苏轼扬雄论”这一学术话题的价值和意义。不过,苏轼对于扬雄的评论中仍还有一些值得探讨的内容。通过文本细读可以发现,苏轼的诗歌和散文当中竟似有两个不同的扬雄一样。苏轼在散文中对扬雄多有批判,但诗歌中又屡屡称引与扬雄有关的典事。究竟苏轼的诗歌和散文中的扬雄形象有怎样的不同?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区别?本文试图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一、苏轼诗歌对扬雄的正面称引——兼与《汉书·扬雄传》对读
据苏轼诗集考察,苏诗中称引“扬雄”相关典故重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对扬雄居处的肯定
苏轼诗中常常引用“扬雄宅”这一典故,如:“恨无扬子一区宅,懒卧元龙百尺楼”(《次韵答邦直子由四首》)①、“何日扬雄一廛足,却追范蠡五湖中”(《和欧阳少师〈寄赵少师〉次韵》)、“近闻陶令开三径,应许扬雄寄一区”(《李伯时画其弟亮功旧宅图》)。据《汉书·扬雄传》所载:
扬季官至庐江太守,汉元鼎间避仇复溯江上,处岷山之阳曰郫,有田一廛,有宅一区,世世以农桑为业。自季至雄,五世而传一子,故雄亡它扬于蜀。雄少而好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博览无所不见。为人简易佚荡,口吃不能剧谈,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静亡为,少耆欲,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不修廉隅以徼名当世。家产不过十金,乏无儋石之储,晏如也。[4]3513-3514
这段文字对于扬雄“孔颜乐处”式的生活态度进行了描绘,使得“扬雄宅”成为高雅淡泊的儒士理想居所的象征。苏轼一生梗泛萍漂,其诗或引“扬雄宅”以自喻,或以之喻人,其暗含的正是对扬雄处世方式的赞誉和归耕故乡的良好愿望的追求。
(二)对扬雄年老而仍居卑官的遭际的同情
《汉书·扬雄传》谓雄:
奏《羽猎赋》,除为郞,给事黄门,与王莽、刘歆并。哀帝之初,又与董贤同官。当成、哀、平间,莽、贤皆为三公,权倾人主,所荐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4]3583
从这个记载中,可见扬雄的才高命蹇。他以奏《羽猎赋》而得微官,然历经三位帝王而未能一展抱负。虽已皤然老态,仍居执戟郎之职。与王莽、董贤等昔日同官相较,其中的意味是不言自明的。苏轼尝用此自比,有诗谓“子云三世惟身在,为向西南说病容”(《送鲜于都曹归灌口旧居》);又曾用此典以表示对友人遭际的同情,谓“寂寞抱关叹萧生,耆老执戟哀扬子”(《至秀州赠钱端公安道并寄其弟惠山山人》)、“玄晏一生都卧病,子云三世不迁官”(《王文玉挽词》)。
(三)叹扬雄之嗜酒少客
《汉书》谓扬雄“家素贫,耆酒,人希至其门”[4]3585,从对生活资料的占有而讲,贫穷生活当然是痛苦的。但从传统语境来说,君子“忧道不忧贫”,这种状态虽苦,却是高雅有以自守,不妄与俗人交的表现。扬雄又尝作《酒箴》,以寓君子淡泊而遭际坎坷,小人圆滑而终被进用之意,苏轼曾盛赞此文,谓“扬雄他文不皆奇,独称观瓶居井眉”(《偶与客饮孔常父见访方设席延请忽上马驰去已而有诗戏用其前韵答之》)。其他诗中化用扬雄与酒相关典故者如:“忽然载酒从陋巷,为爱扬雄作《酒箴》”(《陈季常自岐亭见访郡中及旧州诸豪争欲邀致之戏作陈孟公诗一首》);“载酒无人过子云,掩关昼卧客书裙”(《会客有美堂周邠长官与数僧同泛湖往北山湖中闻堂上歌笑声以诗见寄因和二首》;等等。
(四)伤扬雄之老而无子
苏轼《哭王子立次儿子迨韵三首》诗中有“非无伯鸾志,独有子云悲”之句。此诗系苏轼为王适所作,适字子立,尝从苏轼游学,苏辙以其女妻之。后苏轼、苏辙之子复从王子立学,为文颇有其师章法。元祐四年(1089),王子立年三十五而不幸早卒,苏轼甚悲之,为作《王子立墓志铭》。方苏轼湖州被逮之时,故人亲戚皆惊散,独王氏二兄不避嫌疑,慨然送之出郊,且出语慰之,此种高情厚谊足可窥见。这联诗中,上句以“伯鸾”为譬,言其志与德;下句以扬雄为喻,悲其无子。所谓“子云悲”者,扬雄之子童乌慧而早夭,扬雄曾极为伤感地感叹道:“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乌乎?”[5]166苏轼借此典以哀王氏,足见深情。另一首题为《虔州吕倚承事年八十三读书作诗不已好收古今帖贫甚至食不足》之诗,亦有“扬雄老无子,冯衍终不遇”之叹。吕倚,字梦得,少有声场屋,然而蹭蹬不遇,直到暮年,才以恩补授微官。致仕之后,老无所归,然年八十三仍读书作诗不辍,以收古今帖为乐。苏轼诗以咏之,悲其人如扬雄之无子,如冯衍之不遇。
(五)赞扬雄之识奇字、著《太玄》
苏轼诗中屡见“草玄”“问字”之语,如:“能诗李长吉,识字扬子云”(《复次前韵谢赵景贶陈履常见和兼简欧阳叔弼兄弟》),“未许中郎得异书,且共扬雄说奇字”(《张竞辰永康所居万卷堂》),“闭门怜我老太玄,给札看君赋云梦”(《用前韵答西掖诸公见和》)。《汉书·扬雄传》曾记载“刘棻尝从雄学作奇字”[4]3584,又谓:
时有好事者载酒肴从游学,而巨鹿侯芭常从雄居,受其《太玄》《法言》焉。刘歆亦尝观之,谓雄曰:“空自苦!今学者有禄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后人用覆酱瓿也。”雄笑而不应。[4]3585
传记以精炼传神之笔塑造出了扬雄的学者形象。他精研学问,独造其妙,而世人不理解,与之相形的是刘歆的“空自苦”三字断语,这不仅否定了其学术钻研的精神更是表露出后人对其学术可能持有的态度——用之“覆酱瓿”而已。扬雄之“笑而不应”,显然有儒家“安贫乐道”的精神以及古人“为己之学”的态度,甚至也有“可与知者道,难于俗人言”的自信,苏轼诗中多用此典,正是对扬雄的潜心为学态度的敬仰。
以上五个方面的内容,可在《汉书·扬雄传》或者扬雄的个人著作中找到具体事迹。苏轼诗中多非直接以扬雄为吟咏对象,但是又往往用与他相关的典事自喻或者喻人。这其中的扬雄形象无疑是正面的,也是令人同情的:扬雄学问淹博,却沉沦下僚,一身抱负不得施行;他年老而官卑,又遭丧子之痛;他不改潜心学问的态度,过着“孔颜乐处”般的生活。苏轼诗文中有如此之多与扬雄相关的典故,按道理来说,应该是对其为人极为敬慕的。然而,他的散文中却对扬雄批判甚烈。
二、苏轼散文对于扬雄的否定
苏轼所作散文涉及到扬雄的篇目很多。与其诗歌中称引的扬雄不同,他的多数散文对扬雄展开了极为尖锐的批评,其《晁君成诗集引》云:
达贤者有后,张汤是也,张汤宜无后者也。无其实而窃其名者无后,扬雄是也。扬雄宜有后者也。达贤者有后,吾是以知蔽贤者之无后也。无其实而窃其名者无后,吾是以知有其实而辞其名者之有后也。
文中所论之张汤,是汉代有名的酷吏。他手段狠辣,历史上以腹诽之法治罪的故事,就创自其人,然而他又除奸商、惩豪强,颇有政声,能够“推贤扬善”,故而《汉书》谓其“固宜有后”[4]2657,苏轼之说本此。与之相应的,便是对扬雄的评价,苏轼说“扬雄宜有后者也”而最终无后,根源在于他“无其实而窃其名”,将其视为欺世盗名之辈,未免失于刻薄。
苏轼对于扬雄的批驳,几乎是全方位的,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对扬雄立身行事的否定
苏轼有一篇文章叫做《书柳文瓶赋后》,其文如下:
汉黄门郎扬雄作《酒箴》,以讽汉成帝。其文为酒客难法度士……或曰:柳子厚《瓶赋》,拾《酒箴》之作。非也。子云本以讽谏,设问以见意耳。当复有答酒客语,而陈孟公不取,故史略之,子厚盖补亡耳。然子云论屈原、伍子胥、晁错之流,皆以不智讥之,而子厚以瓶为智,几于信道知命者,子云不及也。子云临忧患,颠倒失据,而子厚犹不足观,二人当有愧于斯文也耶?
扬雄论屈原、伍子胥、晁错皆以为“不智”,苏轼不以为然,并进而对扬雄“临忧患,颠倒失据”的政治表现进行辛辣的讽刺。这里所谓“忧患”,当指王莽新政之际,扬雄惧祸及己,仓促投阁之事。以此观之,苏轼对扬雄的立身行事,是持否定态度的。
(二)对扬雄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否定
扬雄对历史人物多有评价,而苏轼对其见解,往往持否定态度。如苏轼所作《巢由不可废》:
巢由不受尧禅,尧舜不害为至德。夷齐不食周粟,汤武不失为至仁。孔子不废是说,曰:“《武》尽美矣,未尽善也。”扬雄独何人,乃敢废此,曰:“允哲尧禅舜,则不轻于由矣。”陋哉斯言。使夷、齐不经孔子,雄亦且废之矣。
文中“允哲尧禅舜,则不轻于由矣”的说法出自扬雄所著《法言》[5]204。苏轼认为其说浅陋,并进而引出“圣人以位为械,以天下为劳,庶乎其不骄士矣”的观点,警戒在位者勿以权位为重,当去其骄矜之心,以临天下。
又如《论伍子胥》一文,针对扬雄《法言·重黎》篇关于“子胥、种、蠡三人孰贤”[5]330之论作了如下评价:
苏子曰:子胥、种、蠡皆人杰,而扬雄,曲士也,欲以区区之学疵瑕此三人者:以三谏不去、鞭尸籍馆为子胥之罪,以不强谏勾践而栖之会稽为种、蠡之过。雄闻古有三谏当去之说,即欲以律天下士,岂不陋哉?三谏而去,为人臣交浅者言之,如宫之奇、洩冶乃可耳。至于子胥,吴之宗臣,与国存亡者也,去将安往哉?百谏不听,继之以死可也。孔子去鲁,未尝一谏,又安用三?父受诛,子复雠,礼也。生则斩首,死则鞭尸,发其至痛,无所择也。是以昔之君子皆哀而恕之,雄独非人子乎?至于籍馆,阖闾与群臣之罪,非子胥意也。勾践困于会稽,乃能用二子,若先战而强谏以死之,则雄又当以子胥之罪罪之矣。此皆儿童之见,无足论者,不忍三子之见诬,故为一言。
扬雄认为伍子胥三谏不去而致灾祸是不智,而最终又“破楚入郢,鞭尸籍馆”,乃不德。苏轼则认为,三谏不去,皆因伍子胥乃是吴国宗臣,无去之理。而“父受诛,子复雠”于礼为然,甚至直斥“雄独非人子乎”?评论极为尖锐。对于扬雄所论文种、范蠡的不强谏而去,导致越王受辱、臣服夫差的观点,苏轼则又雄辩地指出“若先战而强谏以死之,则雄又当以子胥之罪罪之矣”。直斥扬雄为“曲士”,其学为“区区之学”,其看法为“儿童之见”,可谓鄙薄之极。
(三)对扬雄著述的否定
苏轼《与谢民师推官书》一文,对扬雄的辞赋、学术文章的评价最为系统,否定也最为彻底:
轼受性刚简,学迂材下,坐废累年,不敢复齿缙绅。自还海北,见平生亲旧,惘然如隔世人……孔子曰:“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又曰:“辞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扬雄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谓雕虫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类也。而独悔于赋,何哉?终身雕篆,而独变其音节,便谓之经,可乎?屈原作《离骚经》,盖风雅之再变者,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可以其似赋而谓之雕虫乎?使贾谊见孔子,升堂有余矣,而乃以赋鄙之,至与司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比者甚众,可与知者道,难与俗人言也,因论文偶及之耳。
此文作于元符三年(1100),而苏子于次年逝世。该文是苏轼晚年文艺理论的总结之作,文中特别提出“辞达”的艺文观念,这是该文的核心观点。作为批判对象的,便是扬雄的著作,苏轼认为其《太玄》《法言》都是以艰深文浅易之作,对其《反离骚》之类的赋作,也颇为轻视。
(四)对扬雄地位的否定
苏轼《醉白堂记》谓:“以孔子之圣,而自比于老彭,自同于丘明,自以为不如颜渊。后之君子,实则不至,而皆有侈心焉……扬雄自以为孟轲,崔浩自以为子房,然世终莫之许也。”苏轼指出,孔子为至圣,然却极为谦逊,而后之君子,往往自视过高,这其中就包括扬雄。扬雄自比“孟轲”之语,出自其《法言》,其语云:“古者杨墨塞路,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后之塞路者有矣,窃自比于孟子。”[5]81扬雄勇于以道自任,这种精神是值得嘉许的,而苏轼对此颇不以为然。
总之,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苏轼对于扬雄的批评十分苛刻。这与其诗歌中反复称引的“扬雄”仿佛判若两人。如果诗文并观,有些地方甚至颇为矛盾,比如既然认为其欺世盗名而应当无后,那么哀人老而无子时用“子云悲”之类的典故,则显得不甚妥帖;再如,既已认为《太玄》之类的著作为浅薄,则不当以其自喻或喻人。这其中的原因是值得探究的。
三、苏轼诗文对扬雄评价出现歧异的因由探析
扬雄在宋代地位转变较大,《四库全书总目》谓“若北宋之前、则大抵以(扬雄)为孟、荀之亚”,“自程子始谓其曼衍而无断、优柔而不决。苏轼始谓其以艰深之词、文浅易之说。至朱子作《通鉴纲目》,始书莽大夫扬雄死。雄之人品著作、遂皆为儒者所轻。”[6]这段话很好地概括了扬雄在北宋前后的遭际。宋代众多的批评声音中,苏轼对扬雄的评价所产生的影响是很大的。详考苏轼之批评扬雄,最重要的无非是两个方面:一是扬雄的立身行事,二是扬雄作品的学术价值。考其原因,有如下几点:
第一,宋代是一个忠节观念得以强化的时代,扬雄仕王莽政权之事被认为是道德瑕疵,这导致了扬雄被批评。苏轼与扬雄在历史人物评价上争锋相对的一些观念,其实质皆是从忠节观念出发,对“孝”“德”“智”“礼”等儒学精神内涵的理解产生的歧异。比如扬雄论屈原、伍子胥、晁错,皆认为他们的行为是“不智”的;苏轼则不认同此说。像伍子胥数谏吴王而不获采纳,是否应当去国的问题。如果放在宋人忠节观念日益强化的背景下,就不难理解苏轼所说“百谏不听,继之以死可也”的立场了。又如伍子胥鞭尸籍馆之事,扬雄认为这是“不德”,苏轼则认为这是符合“礼”的。
第二,苏轼批评扬雄的学术著作的价值,其实质是文艺观念的不同。苏轼对扬雄著作价值的否定,是有迹可循的。其师欧阳修尝谓“若子云、仲淹,方勉焉以模言语,此道未足而强言者也”[7]664,对扬雄的论著的实际价值加以否定。其父苏洵所作《太玄论》,谓扬雄之《法言》“辩乎其不足问也,问乎其不足疑也”[8]115,又论其《太玄》之作乃是“雄之所以自附于夫子而无得于心者也”[8]115,否定了扬雄两部代表作的学术价值。苏轼批评扬雄“以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相较于其师、父之论,已经由学术价值的否定进一步延伸到了文辞的使用方面,这与当时文风改革不无关系。
第三,苏轼批评扬雄还与当时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学一派对于扬雄称颂有关。南宋施德操《北窗炙輠录》记载有一则意味深长的故事:
荆公论扬雄投阁事:“此史臣之妄耳,岂有扬子云而投阁者!又《剧秦美新》亦后人诬子云耳,子云岂肯作此文?”他日,见东坡,遂论及此。东坡云:“某亦疑一事。”荆公曰:“疑何事?“东坡曰:“西汉果有扬子云否?”闻者皆大笑。[9]815
这个看上去颇有戏谑意味的故事难以辨别其真假,但其中体现出了王安石对扬雄的回护,以及苏轼在扬雄问题上与其针锋相对的态度。有研究者指出:“在北宋后期,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学、新党几乎牢牢占据着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制高点。他们继承了中唐以来古文运动推尊扬雄的传统,并将之制度化、意识形态化。”[10]81这一时期,扬雄的地位被拔得极高,得以从祀孔庙,其文也是举子们模拟效法的对象,而苏轼的批评也有挑战新党意识形态的意味。以上这些都是苏轼批评扬雄的原因。
但是,从寻常认识的角度来说,既已轻视某人,而仍旧以其平生事迹相比附,似不当如此。要解释这一个问题,应当从诗歌使用典事所凝结而成的文化意涵去寻找原因。前引苏轼诗歌中称引扬雄相关事迹时,我们曾特意与《汉书·扬雄传》相互对读,其结果就是几乎所有典事皆可从《汉书》中找到原始出处。无论宋人如何评价扬雄,《汉书》无疑是对其十分肯定的,甚至于一直到北宋以前,对扬雄的肯定性评价占主流。与此相应的是,扬雄的相关事迹被作为事典引入诗歌中,其形象也一直是正面的。
《汉书·扬雄传》所记“岷山之阳曰郫,有田一廛,有宅一区”其实是其五世祖杨季的事迹。但是在后人引用相关典事时,“一廛”“一区”显然已经作为一个语码而直接与扬雄关联在一起。在不断传播和接受过程中,“有田一廛”成为了在故乡有田产的象征,“有宅一区”则更进一步地升华成一个甘于寂寞、专心著述的学者的居所。前者如“务农勤九谷,归来嘉一廛”(庾信《归田诗》)[11]279、“季子乏二顷,扬雄才一廛。伊予此南亩,数已踰前贤”(权德舆《拜昭陵过咸阳墅》)[12]1946;后者如左思“寂寂扬雄宅,门无卿相舆”[13]735、杜甫“旁人错比扬雄宅,懒惰无心作解嘲”(杜甫《堂成》)[13]735。《汉书·扬雄传》与古今诗人的创作一起形成一个可以互为文本的、拥有共同文化背景的典事,灌注在诗史链条之中。
又如“扬雄老而无子”的事情,扬雄在《法言》中言其失子之痛。历来诗歌多有感叹,如:王十朋《哭孟丙》“萧瑟扬雄宅一区,不堪老境失童乌”[14]68;刘克庄《悼阿驹》“情知泪是衰翁血,更为童乌滴数行”[15]571,皆有同悲之感。苏轼自己在《邵茂诚诗集叙》中说,“夫原宪之贫,颜回之短命,扬雄之无子,冯衍之不遇,皇甫士安之笃疾,彼遇其一,而人哀至今”,指出了“扬雄无子”这一境遇是古今同哀的。原宪、颜回、冯衍、皇甫士安都是有良好德行或学问而遭遇困境的,互文以见义,也就是说扬雄显然也是如此,这一篇文章中的语境显然也是“事典”的语境。苏轼散文中极为辛辣地讽刺扬雄欺世盗名而无后,其诗中引用“童乌”的事典以表达悲痛的心情,显然不是他要皮里阳秋,用来讥讽其友人,而是因为事典已经具有了稳定的内涵,故而用来指代。苏轼诗歌当中所涉及到的“执戟”“年老官卑”“闭馆草玄”等扬雄形象显然也应当如此看待。
苏轼散文对于扬雄的批判涉及到多个方面,这其中既有立身行事、进退出处方面的思考,也涉及到儒家思想中的“忠”“孝”“仁”“礼”等核心观念的阐释,还有改革文风的需要,甚至潜含着对王安石等人的新学的批评。他的批评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之下有其积极意义。然而与扬雄相关的事典,在不断的流传过程中,以《汉书·扬雄传》《法言》等作为原始文本,围绕着其相关遭际已经产生了丰富的次生文本,它们共同构成可以单独截取出来的相对稳定的象征传统,从而演化成为文化语码。虽然由于时代的变化,扬雄成为一个被批评的对象。但是,作为与之相关的典故的内涵已经趋于固定,其象征意义不会因此而被骤然打破,这正是苏轼诗文当中对扬雄的评价产生歧异的根本原因。
注释:
①文中所引苏轼诗文都来自李文亮自编《苏轼文集编年笺注》,巴蜀书社,2011 年版。文后不再一一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