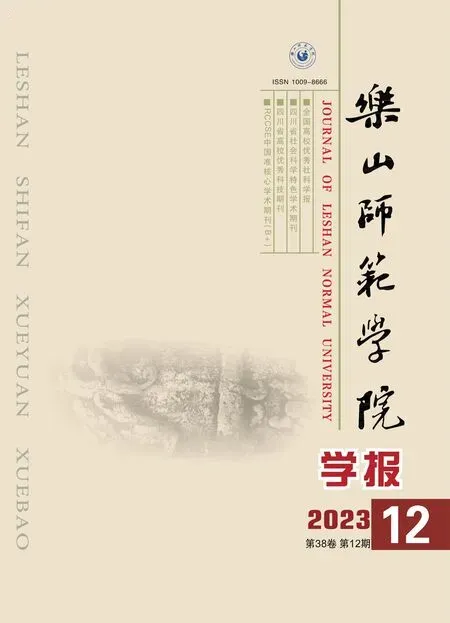史传书写到文学叙事:刘备形象发展新论
束 强
(安徽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从《三国志》到《三国志通俗演义》,从史传叙事发展到文学叙事,三国人物逐渐从历史范畴走向文学范畴。在成书各阶段中,不同创作主体参与其间,以形态各异的文本样式表现三国故事,加之以时代印记,从而各种文本所表现的人物性格特征存在着差异,刘备形象正是如此。
目前,学界研究刘备形象的文章数量众多,其中有数篇硕士论文对刘备形象的演变进行了探讨。张真[1]较早从形象生成与流变这一角度入手,对各个时期的刘备形象展开了分析,虽未立足人物形象与成书过程关系的角度,但已经初步勾勒了从历史到小说的发展脉络。不过,作者没有突出说明平话中刘备的小市民特征,在论述嘉靖本中刘备性格的前后变化时,作者更强调刘备独裁者的本质,而忽视了从仁义隐忍到任性独断的动态过程是性格发展逻辑的一种,亦没有将刘备性格变化与其事业盛衰相联系。王颖[2]简单梳理了《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前各时期的刘备形象特征,并且着重论述了《三国演义》以及影视作品中呈现的刘备形象;巩秋彤[3]依次探析了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以降三个时间段的刘备形象,又从社会横向面上,说明了上层统治阶层、中层文人阶层、下层平民阶层视野中的刘备。王、巩两人论述范围较广,对刘备形象的生成与演变都作出了比较细致的研究,不过都未强调成书过程这一角度。两人在《三国志平话》阶段没有突出刘备的小市民心理,对嘉靖本的分析亦未重点描述刘备性格变化的动态特征,其中有些论述更强调创作者的塑造手法和改造内容而不是人物的形象特征,如平话对《三国志》中刘备材料的取舍和改造,毛本对嘉靖本中刘备内容的删改。
本文立足现有的学术基础,继承学界相关研究成果,力图在具体细节的探索上展现个人特色。一方面,本文强调在《三国演义》成书的各个阶段,刘备形象内涵扩容和发展的态势,笔者意欲从史书原型出发,结合文人意识和平民视野两个维度,还原刘备形象发生历时性迁移的大致脉络;另一方面,本文在论述《三国志平话》中的刘备时,更加重视文本对其小市民心态的刻画,在论述嘉靖本时,更着力探究刘备性格的个性化运动与其事业兴衰的关系。
一、史书中明君与枭雄特征的交融
经过小说《三国演义》的塑造,刘备的“仁君”形象已深入人心,实际上有时候小说的艺术加工,往往可能使人物失去了应有的真实性,正如鲁迅先生所言“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4]113。其实史书《三国志》中的刘备具有多元化的性格特征,他既有着明主宽仁爱民、礼贤下士的一面,又有着枭雄胆略过人、胸有城府的一面。
一方面,《三国志》中的刘备是一个明君形象,陈寿评曰:“先主之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①陈寿将刘备与汉高祖刘邦相比,盛赞刘备远大之志和宽厚待人之道。主要表现为:
其一,宽仁爱民,以人为本。建安十二年(207)曹操南征刘表,刘备率军退往江陵,携“众十余万”,不忍舍弃,在他看来“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人民是成就大业的关键力量。因此曹魏、孙吴分占天时和地利,而蜀汉占人和,宽仁爱民正是刘备得以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其二,礼贤下士,任人唯用,甚得人心。刘备待人宽厚,喜结交豪士游侠,无论身份高低贵贱,皆以礼相待,因此人心归附之。平原郡民刘平曾派刺客刺杀刘备,因刘备之仁义,刺客竟然不忍心下手,告之而去。裴松之注引《魏书》曰:
是时人民饥馑,屯聚钞暴。备外御寇难,内丰财施,士之下者,必与同席而坐,同簋而食,无所简择。众多归焉。
汉末动乱,人民流离失所,饿殍遍地,刘备对外率众杀贼,抵御流寇劫掠,对内广施恩惠,救济百姓,更与贫下之士同席坐、共饮食。动乱之际,刘备能够体恤民生疾苦,乐善好施,对待下层之士,不计较身份高低,其仁君的形象逐渐鲜明。后刘备夺取西川,对蜀地人士采取安抚和招揽的策略,任才唯用,“皆处之显任,尽其器能”,刘璋的旧部、姻亲和摈斥之臣,皆不避嫌疑而用之,昔日所忌恨的蜀地之才刘巴,刘备也予以要职,可见刘备对人才的重视和爱才惜才之心。
其三,志存高远,信义显著。刘备年少时虽以织席贩履为业,但心怀大志,曾指屋边五丈余高的桑树,声言将来必乘羽葆盖车。“羽葆”即鸟羽联缀而成的华盖,乃天子仪仗之物,可见刘备素有帝王之志,这也是后来他为兴复汉室而不懈努力的原因之一。刘备以仁义为追求,讲究“不失信于天下”,虽然平生颠沛流离,而信义日益显著,诸葛亮曾劝其攻夺荆州,刘备以“吾不忍也”拒之,在他心中有着士大夫所秉持的道义,他也最终凭借这份道义吸引了人才,成就了蜀汉基业。
另一方面,《三国志》中的刘备不失枭雄气质,周瑜曾指出“刘备以枭雄之姿……必非久屈为人用者”,正是看破了刘备宽仁的另一面。主要表现为:
其一,胆识过人,杀伐果断。刘备并非只是小说中所描写的靠“哭”谋得江山,他的历史形象还呈现出刚毅勇敢、恩威并重的特征,他有着君主杀伐果决的胆略,《三国志》多次提到其枭雄之举:
督邮以公事到县,先主求谒,不通,直入缚督邮,杖二百,解绶系其颈着马枊,弃官亡命。
灵等还,先主乃杀徐州刺史车胄,留关羽守下邳,而身还小沛。
曹公遣蔡阳击之,为先主所杀。
先主大怒,召璋白水军督杨怀,责以无礼,斩之。
鞭督邮在小说中改为张飞所为,杀车胄、蔡阳的主角在小说中改为关羽,斩杨怀在小说中改为庞统以计斩之。小说的改塑是为了保持刘备仁君形象的完美性,但史书还原了刘备枭雄的原始面貌。如曹操擒杀吕布而得徐州后,上表奏封刘备为左将军,并与之“出则同舆、坐则同席”,这说明刘备谋取了曹操一定程度的信任。曹操派刘备、朱灵去阻击袁术,在朱灵等人返回许昌时,刘备并没有注重平时著称的信义,而是一展枭雄的果决之风,乘机诛杀刺史车胄,夺取了徐州。鞭督邮、斩蔡阳、杀杨怀皆体现了刘备历史形象中这种刚毅胆烈、勇武果决的特点。
其二,布局天下,颇有谋略。史书中的刘备兼具文韬武略,在临阵破敌、定计设谋方面也有着一定的能力。如小说中诸葛亮首次出山的博望坡之役,实际上出于刘备之手,据《三国志》载:“久之,先主设伏兵,一旦自烧屯伪遁,惇等追之,为伏兵所破。”先是火烧博望坡,表面假装败逃,实则引诱夏侯惇大军深入追击,遂以伏兵破之,可见刘备早已谋划好退敌之策。再比如汉中之战,刘备指挥黄忠“乘高鼓噪攻之”,大破曹军,斩杀夏侯渊,后曹操率大军欲夺回汉中,刘备又据险守城,不与曹军交锋,最终迫使曹操退军;赤壁之战,刘备与周瑜等合力出击,火烧曹军,水陆并进,追至南郡。这些都说明刘备在军事上也有着出色的指挥能力和谋划能力,只是在小说中刘备的这一特征被有意淡化了。
其三,胸有城府,善于隐忍。《三国志》曾指出刘备“少语言,善下人,喜怒不形于色”,这说明刘备能够很好隐藏自己的情绪,令人难以捉摸其内心真实想法。刘备城府极深,善于自我伪装,以此迷惑别人,自起事以来,他先后依附过邹靖、毌丘毅、公孙瓒、田楷、陶谦、吕布、曹操、袁绍、刘表、孙权、刘璋等人,虽多年颠沛流离,却始终折而不挠、屡败屡战,更重要的是他懂得隐忍和趋利避害,通过保全自我、保存实力,最终成就一番事业。如曹操曾对刘备说“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意在试探刘备之雄心壮志,“先主方食,失匕箸”,刘备以一种胆怯懦弱的小人之态掩饰自我。又如,刘璋邀迎刘备入川以伐张鲁,左右谋士劝刘备于会所袭击刘璋,刘备以“此大事也,不可仓卒”之言加以拒绝,因为刘备知晓夺取川蜀不在一时,首先要做的是隐藏自己的目的,在川蜀士人中树立权威和打下基础,以获取人心,因此“先主北到葭萌,未即讨鲁,厚树恩德,以收众心”。这些材料皆可说明刘备为人善于隐忍和伪装,外虽宽厚而胸有城府,通过一次次趋利避害之举,最终成就了蜀汉基业。
此外,《三国志》中的刘备性格也存在缺陷之处,刘备虽能容忍素有恩怨的刘巴,却也因私怨之仇而杀张裕。据《三国志》卷四十二载,州后部司马张裕曾劝阻刘备征讨汉中,他认为军出不利,后来果如其言,将军吴兰、雷铜皆战死,最终刘备还是夺取了汉中,但对张裕心怀芥蒂。张裕还曾与人私语:“主公得益州,九年之后,寅卯之间当失之。”此语妄断蜀汉之天下,刘备闻之,心中杀意难止。而且刘备夺益州之前,曾与刘璋会见于涪城,时张裕在坐,刘备因张裕脸多胡须,便以“诸毛绕涿居乎”之语嘲笑他,张裕以“潞涿君”讥讽刘备无胡须,后来一系列事件又逐步加深了刘备内心的怨恨。
先主常衔其不逊,加忿其漏言,乃显裕谏争汉中不验,下狱,将诛之。诸葛亮表请其罪,先主曰:“芳生兰门,不得不鉏。”裕遂弃市。
刘备以张裕汉中之谏不灵验为借口,不过是掩盖其内心对张裕的不满与怨怼,诸葛亮上表为其请罪,刘备以芳兰为喻,认为张裕是兰门前的杂花杂草,不得不锄去,这种借口完全是虚妄之言,显得苍白无力,但说明了刘备坚决的杀心。可以说,刘备杀张裕之举是刻意为之,是出于其个人的私怨,也有着妒忌人才和打压人才的嫌疑,这是刘备形象中的负面之处。
二、文人意识中英雄与明主的楷模
魏晋南北朝笔记涉及刘备的材料不多,也多持肯定态度。如《世说新语·识鉴第七》载曹操曾向裴潜问及刘备之才,裴潜甚赞许之,称刘备为乱世英雄,若固险自守,“足为一方之主”[5]156。这一评价十分贴切刘备的个人经历,后来他便凭借巴蜀之地,得以鼎足天下,可见笔记小说对刘备政治能力和英雄本色的肯定态度。无独有偶,殷芸《小说》卷六“吴蜀人”记叙孙策在寿阳袁术处,得知刘备来访,曰“英雄忌人”[6]119,而有意避之,可见孙策对刘备心存敬佩和忌惮之意,这也表现了刘备确是具有异于常人的英雄气质。
到了唐宋时期,诗人们更多地在诗词中表露个人情感,强调刘备礼贤下士、宽仁待人的特点,并在咏怀刘备的同时兼顾诸葛亮,对刘备三顾茅庐之举尤为赞许,主要歌颂君臣之间的鱼水之情,反映了士人理想中的明主和贤相形象。如“若非先主垂三顾,谁识茅庐一卧龙”(唐·汪遵《南阳》)[7]74,“鱼水三顾合,风云四海生”(唐·李白《读诸葛武侯传,书怀赠长安崔少府叔封昆季》)[7]51,“先主与武侯,相逢云雷际。感通君臣分,义激鱼水契”(唐·岑参《先主武侯庙》)[7]52,等等。诗人津津乐道于“三顾茅庐”的故事,对刘备、诸葛亮的君臣际遇充满着无限感慨,实际上是在心中寄寓着一种美好向往,他们期待一位如刘备般的明主,能够赏识自己、提拔自己,从而施展抱负,践行一番事业。
当然,诗人还在诗词中盛赞刘备超绝千古的英豪气概。作为三分天下的一代霸主,他身上浸染着乱世的雄风,流淌着英雄之血,这些都成为诗人笔下的表现对象。如“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唐·刘禹锡《蜀先主庙》)[7]63,“英雄只数大耳儿,仿佛芒砀赤龙子”(宋·程俱《北固怀古》)[7]113,“英风追想孙刘”(宋·程公许《沁园春》)[8]2515,“吴楚地,东南拆。英雄事,曹刘敌”(宋·辛弃疾《满江红·江行和杨济翁韵》)[8]1870,等等。这些诗作无一不强调了刘备的英雄本色,并且将他与刘邦、孙权、曹操等并称,进一步强化了他纵横天下的枭雄之姿。
此外,诗人在追怀刘备显赫事迹的同时,也表达了对其功业未竟的感慨与惋惜,像张俨的《贞元八年十二月谒先主庙绝句三首》中体现了这种思想。诗人一方面对刘备的政治功绩表示肯定,另一方面又对蜀汉政权的失败深表遗憾,传达出一种历史兴亡之感。具体如下:
(其一)仗顺继皇业,并吞势由己。天命屈雄图,谁歌大风起。
(其二)得股肱贤明,能以奇用兵。何事伤客情,何人归帝京。
(其三)雄名垂竹帛,荒陵压阡陌。终古更何闻,悲风入松柏。[9]5355
三首诗的前两联皆是对刘备高唱颂歌,肯定其汉室正统的身份,称赞他任人唯贤、用兵出奇的优点,在诗人眼里,刘备是一位青史流芳的雄主。同时,后两联又对刘备的失败充满着难以言说的悲哀感,诗人诉说着天命的势不可为,“谁歌”“何人”的慨叹表现的是一种横穿千古的忧愁,它最终化作一道风吹入松柏之间,所谓的英雄豪杰早已成为过往云烟。
三、平民视野中草莽气的仁君形象
《三国志平话》(以下简称为《平话》)结尾叙刘渊灭晋,兴复汉室江山,严重偏离历史事实,乃平话之妄语,却也反映了民众的心理预期,全书的中心论调亦在于此,即“尊刘”的思想趋向。作为蜀汉集团的首脑,《平话》中的刘备,一方面继承了《三国志》中的历史形象特征,另一方面增加了民间文学中的市井色彩。前者来源于正史中的实际记载,包括刘备的外貌特点、仁德之风;后者吸收了民间故事和传说中的因素,刘备被赋予了草莽英雄的气质和小市民阶层的特征。
刘备初次登场于《平话》中卷上“桃园结义”一节,该节介绍了刘备的家世背景和外貌情况,像“生得龙凖凤目,禹背汤肩,身长七尺五寸,垂手过膝,语言喜怒不形于色,好结英豪”[10]11。这沿袭了史书的说法,强调了刘备的帝王之相,并以大禹、商汤两位贤人作比,间接反映出刘备具有仁德的潜在特质,同时点明其喜结交英雄的个性。卷上“三战吕布”和卷中“汉献帝宣玄德关张”两节,也皆对刘备的非凡外貌进行了描写,突出其个人形象气质的卓荦绝俗。
《平话》表现刘备的仁德,主要采取侧面描写的方式,即通过他人对刘备的评价,以完成刘备“仁德”形象体系的建构。这个体系由三个方面的人物评语构成。一是蜀汉集团内部人物,如庞统曰:“天下人皆说皇叔仁德之人。”[10]98二是蜀汉集团的竞争对手,如陈宫称:“刘备仁德之人”[10]35。三是普通民众,如荆州百姓在刘备入主荆州后,皆“鼓腹讴歌,言皇叔仁德也”[10]92。借他人之口,尤其是下层百姓对刘备的肯定和拥戴,展现了他爱民如子的仁君之风。所谓“鼓腹讴歌”,指拍打着腹部以应和音乐的节奏,而放声高歌,形容一种自在闲适、安乐无忧的状态。唐代柳宗元《终南山祠堂碑(并序)》有“鼓腹而歌,以乐其生”[11]5929之句,正是对这一举动最好的注脚。可见在刘备的治理之下,百姓能够安居乐业,享受着稳定富足的生活,这恰恰说明刘备仁德爱民,是理想统治者的化身。
《平话》进一步拓展了史书中刘备在平原主政期间的内容。《三国志·先主传》载:“(备)数有战功,试守平原令,后领平原相……客不忍刺,语之而去。其得人心如此。”裴松之注引《魏书》载:“备外御寇难,内丰财施……众多归焉。”历史记载客观叙述了刘备在平原主政期间,不仅率领士卒抵抗流寇,还施舍救济百姓,做到了平原县民心之所向。刺客受命欲害刘备性命,却终不忍杀之,舍之而去,这可上溯到春秋时期鉏麑刺赵盾之事,足显刘备之仁义。《平话》继承了这一点,突出了刘备在平原施行德政的效果,强调了刘备理政牧民的过人才能。《平话》卷上“玄德平原德政及民”一节,写曹操路过平原县,见到了乱世中的世外桃源,“里堠整齐,桥道平正,人烟稠密,牛马繁盛,荒地全无,田禾多有”[10]28。在刘备的治理下,百姓安居乐业,平原县阡陌纵横,良田万千,市井兴荣,呈现一片祥和安宁的景象,这在汉末离乱的时代背景下,确是难能可贵,这有力地说明了刘备以仁德治政的良性效益。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张飞、关羽的形象塑造,淡化刘备性格中的不和谐因素,《平话》将《三国志》中的鞭督邮、斩车胄的主角分别改为了张飞和关羽,这一点也为后来《三国志通俗演义》所取。
此外,《平话》赋予了刘备民间的江湖草莽色彩,对他的小市民阶层心理展开了较为深刻的描写与表现。
首先,《平话》较为详细地展现了刘、关、张三人在桃园内祭拜天地、结为生死兄弟的基本内容,而在《三国志》的历史叙述中,刘备与关张二人只是“恩若兄弟”,并未进行过结义这一规范程序。结义这一行为是民间人伦关系中最常见的一种交际仪式,它促使多个人形成一个基于共同利益的小集体,民间底层人物往往依靠这种方式求得生存,减少生活压力,社会上层人物也通过结拜获取人脉,以追求功利[12]。平话对刘、关、张三人关系的重新定位,符合底层大众的社会心态。
其次,《平话》创造性地增加了刘备落草为寇的情节,突出了人物身上的草莽气。《三国志平话》卷上“张飞鞭督邮”一节,描叙张飞将督邮打死并分尸六段,首级和手脚悬挂于城门上,这种残忍手段体现了一种草莽心性,刘备并未加以阻拦,最后三人却一同前往太行山落草。这显然是说书艺人的有意改动,不符合刘备的汉室宗亲身份,刘备也断然不会屈为土匪贼寇。《平话》还写刘备徐州兵败后,张飞在古城称王,设立年号,见到刘备后邀之入城做皇帝。这种描写受到民间传说的影响,它展现的造反行为是市井阶层社会心理的反映,后来《三国志通俗演义》将这些不合理成分尽数删除。
最后,《平话》还强化了刘备的小市民心态,突出了他趋利避害的个人追求。《平话》中的刘备,虽然与关羽、张飞之间建立了非血缘性的“义”的联盟,但这种联盟却容易受到来自外部的利益冲击,而产生摇摆。《平话》中的刘备在面对“义”和“利”的两难处境时,倾向于利大于义。比如刘备面对赵云的追问,自诉内心所思:“今有云长,亦受汉禄,不想结义之心”[10]57。他从“利”的角度出发,表现了对关羽的不信任之心;古城与张飞相会时,刘备又再次强调关羽的背信弃义,指责关羽曰:“险送我性命,亦无桃园之恩”[10]61,这完全是出于个人利益而作出的揣测,可见《平话》对刘、关、张兄弟间的情义采取了淡化处理。《平话》中刘备与赵云之间的关系,亦是出于功利目的,赵云选择追随刘备,是一种风险投资,他看中了刘备所具备的潜质,“异日必贵”这四个字正是赵云主动投靠刘备的原因;刘备选择接纳赵云,同样离不开长远利益上的考量,两人的利益链得以结合,正是小市民阶层功利心态的作祟。同时,《平话》还点出了刘备明哲保身、趋利避害的性格特征。曹操路过平原,力邀刘关张三人参加反董诸侯军,刘备回复道:“小官武艺不会,弓马不熟,恐失国事。”[10]28暗含婉拒之意,刘备凭借破黄巾的战功发迹,却自称不善行军打仗,其虚伪掩饰的意味浓厚,不同于张飞陈言国家大义、企图建功立业的想法,刘备是出于自保的考虑,属于典型的市井心理。
元杂剧中的刘备个性并不突出,缺少戏剧性因素,基本上继承了《平话》里的主要内涵,反映了平民阶层的心态、审美和道德取向,涉及剧目主要有《虎牢关三战吕布》《刘玄德独赴襄阳会》《刘玄德醉走黄鹤楼》等。
四、小说中人物性格的矛盾运动
人物命运往往与其具体的外在行动相联系,同时其行动也受制于个人内心性格的运动,随着内心的变化,人物命运相应地产生正向或负向的发展趋势,如黑格尔所说:“即人物性格本身在横冲直撞,失去自制,直至损伤困顿的发展。”[13]346嘉靖本在塑造人物时似乎注意到了这一点,如刘备、关羽个人命运的兴衰,与其性格的矛盾运动不无关联,二人内心性格的变异,外化于具体行动,小说对此作了有意或无意的描写。
小说文本中刘备的性格随着其处境、地位、经历的变化,发生着不同的个性化运动。前期刘备其性格的主导因素主要由“仁”与“忍”构成。就前者而言,刘备无论在平原、徐州还是新野,以仁政推行于民,争取民心,也由此获得了广泛的民意基础;就后者而言,刘备在前半生颠沛流离的奔波中,掌握了隐忍保命的生存之道。
具体而言,一方面,针对刘备之“仁”,小说着重突出了州县百姓对他的拥戴和他对百姓的爱护,如刘备在安喜县施行仁政,当督邮刁难刘备时,百姓纷纷主动为刘备求情;新野兵败之际,数万民众扶老携幼,挑担背包,愿意追随刘备渡江,而面对遭难的百姓,刘备不忍舍弃,更是为之痛哭,归罪于己,甚至“欲投江而死”[14]400,足见刘备怜恤民生的慈悲情怀和仁君之心。小说还采纳了平话中“移花接木”式的创作策略,将鞭打督邮、斩杀车胄的主角由刘备替换为张飞与关羽,对刘备性格内涵作了初步整合,因为他以“仁”立身的准则与这种粗暴、勇猛的行径大相径庭,这种有意改动,主要服务于刘备宽厚仁义的核心特征。
另一方面,刘备因时、因地制宜,保全自我,其“忍”之特征在小说文本中随处可见。刘备曾失语道:“备若有基本,何虑天下碌碌之辈耳”[14]336,这暴露出了他心中建功立业的大志,同时也解释了他委曲求全、明哲保身的原因。正是缺少成大业的“基本”,才迫使他在创业初期四处漂泊,寄人篱下。可以说隐忍是这一时期他性格的主导因素,惜身全命是其最主要的外在行动,也因此造就了他往往化险为夷的结果。如依附曹操时期,刘备种菜浇园,收敛锋芒,在煮酒论英雄时,他更是故作惧怕雷电以示孱弱,最终幸免于难;依附袁绍时期,由于关羽斩杀颜良、文丑,袁绍两次欲杀刘备,第一次他以“天下有多少同姓同貌者”[14]250为由替自己开脱,第二次他又指出曹操欲借刀杀人的目的,并提出修书召来关羽,从而得以周全性命。这既反映了刘备面对生命威胁时的应变能力,也展现了他灵活应变下的隐忍避祸心态。
后期刘备在实现霸业的目标后,逐渐完成了平民向帝王的蜕变,“帝王的尊严开始在主体行为中发挥作用”[15]109,“任”成为其性格的主导因素,所谓“任”即任性独断,是他利用森严秩序以规训臣民而发展出的性格态势,刘备的个性内涵被注入了政治色彩。如果说前期的“仁”与“忍”是刘备保命的立身之本与处世之道,是其理性节制下忍辱负重的坚毅品格,那么后期的“任”则是一种情绪化的个性表达,其情感冲动挣脱了理性的桎梏。
如刘备在汉中称帝后,第一件事即降诏伐吴,为关羽雪恨是他践行桃园结义之盟的必然选择,但伐吴之举破坏了既定的联盟策略,损害了蜀汉的基本利益,联吴抗曹的正确方针被他抛诸脑后。激烈的情感冲动使得原有的理性思考荡然无存,甚至面对秦宓的苦心谏言,刘备不复昔日的仁慈与冷静,取而代之的是“大怒”,在百官求情下才将秦宓,“暂且囚下”以待伐吴之后处斩。即使最为刘备所信任的诸葛亮,在上表劝谏之后,依然徒劳无功,刘备不仅“掷表于地”,并表明决心:“再谏者插剑为令”[14]779,最终倾举国之兵征讨吴国。
此后,在伐吴过程中,刘备又多次一意孤行,不听谏言。在谋害关羽、张飞之元凶被尽数诛杀后,马良提议与东吴和解,以共图灭魏,刘备却一心报仇,致使蜀国陷入被动局面;马良还数次谏言不可轻视陆逊之才,仍然为刘备所忽视,在他看来“黄口孺子”不足为虑,最终蜀军不可避免地走向覆灭的结局。
早年谨慎沉稳和克制隐忍的性格,让刘备能够做到化险为夷,并逐渐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基业;随着个人权力的日益膨胀,此时的刘备以一种独断专行、冲动执拗的性格,在政治军事斗争中横冲直撞,乃致身陷险境,结果无非空耗蜀汉国力。总之,刘备性格的主导因素前期由“仁”和“忍”主导,后期以“任”为中心,这也直接关系到刘备事业命运的兴衰。
五、结语
通过上述的大致梳理,可以看到刘备在《三国演义》一书逐渐成型的过程中,其形象内涵不断发展和扩容。史书《三国志》中的刘备交融着“明君”与枭雄的双重特质,既有着明主宽仁爱民、礼贤下士的一面,又有着枭雄胆略过人、胸有城府的一面,同时也存在着因私怨而杀人的缺点;进入文学视野后,文人们往往重视其英雄的气概与爱民的仁心,歌颂他与诸葛亮的理想君臣关系,有意忽视其原本具有的枭雄之气;平民接受维度中的刘备又是另一番景象,像《平话》虽然继承史书里的一些描写,建构起刘备的“仁君”形象体系,同时又赋予了刘备民间的江湖草莽色彩,并且突出其趋利避害的小市民心态。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小说叙事中,小说家更加强调刘备前后期性格的转变过程,即从以仁义、隐忍为主,发展到以任情任性为主的个性化运动,而这种性格主导元素的迁移又与其命运事业紧密关联。总而言之,《三国演义》成书的各个阶段受到不同创作者迥异的叙事追求,以及文本体制的制约,在不同的书写阶段,刘备形象呈现出一种差异性,从而发展出各具特色的性格态势。因此,我们常说的刘备“仁君”形象,也只不过是其形象发展脉络的一环而已,系统性的学术考察方可窥其全貌。
注释:
①文中所引都选自《三国志》,裴松之,注,中华书局2006 年版,下文不再一一标注。